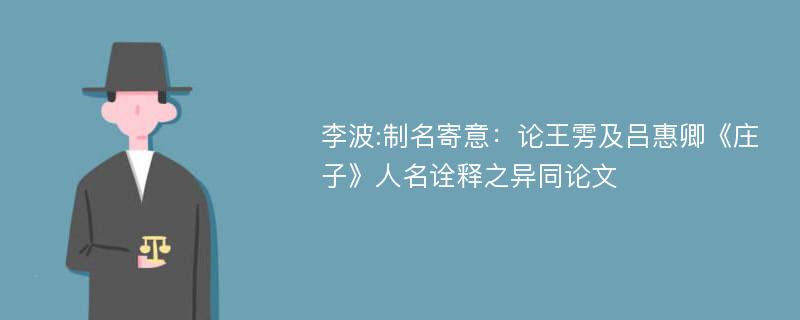
摘 要:《庄子》寓言人名取材广泛,富有深意,古今注《庄》者皆以自身理解给予其独特诠释。郭象以寄言出意方式,稍显矛盾与无奈;成玄英以儒家考证之法具证人物之来源。及至北宋时期,王雱及吕惠卿基于郭、成二人之诠释,采用具析人名字义方式,寄字义,建深意,将其观点建立在诠释字义基础上;但二人由此建立的思想结构不同,前者有意区分有为、无为概念,因此善以有序形式解构《庄子》人名的层次性,后者则平等对待人名系统,秉持一以贯之的观点,主张行迹不同,道通为一。此种差异,既见二人在《庄子注》中思想诠释方法之异,亦是二者思想建构在方法上的体现。
关键词:《庄子》;王雱;吕惠卿;人名诠释
王雱,字元泽,王安石长子,王安石新学学派成员之一。其作《南华真经新传》一书,以儒学概念使庄子思想贴近现实。吕惠卿(1032—1111),字吉甫,福建晋江人,生于宋明道元年,作《庄子义》一书,书写对人生、政治及儒道关系的看法。二人皆阶段性跟随王安石从政,王雱早逝,年仅33岁,受王安石思想影响颇深;吕惠卿则因政治立场与王安石时合时分。二人《庄子注》均受王安石学派思想影响,善融合诸家学说以注庄,但同中存异,本文基于二人《庄子注》中人名诠释方式,发掘王注、吕注之异同,窥探二人思想建构方法之特色。
一、北宋前注庄者对《庄子》人名的诠释
《庄子》以善用寓言而为人称道。大量寓言故事中蕴含意象丰富的人名系统,除为人熟知的人物,如颜回、许由、惠施、伯夷、叔齐等,还有许多人名并无出处,如叔山无趾、哀骀它等。历代注庄者致力诠释这些生僻人名,并逐渐总结出独特的诠释方法。王注、吕注出现以前,郭象和成玄英即有不同理解,二者也分别代表两个时代的诠释特色。具体而言,郭象以寄言出意方式加以诠释,既不考证人物具体事迹,也不多作字义阐释(偶见),认为《庄子》记载各种寓言人名的作用,仅是寄托作者观点的虚构方式,即“庄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1]庄子将眼光置于整个社会、世界,故每则简单寓言背后均隐藏深意,因此郭象并不具体分析寓言及人名出处与字义,而将其作为诠释方式,发掘背后深意。有学者认为这种方式是郭象为缓解其思想与《庄子》原义的矛盾所致,“‘寄言出意’本是郭象对《庄子》原文风格的定义或描述,是为弥合‘注释’与《庄子》原文明显不合的一种托辞。与其说‘寄言出意’是郭象的方法,不如说是郭象自觉本人思想与《庄子》原文不一致时的托辞或辩解之方。”[2]此说有合理之处,如郭象解释《逍遥游》“姑射神人”时,即将神人寄言为圣人,“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1]《庄子》中“神人”原带出世之意,这使郭象无法一以贯之其“内圣外王”观念,只好以此为托辞,实际仍推崇庙堂之上的圣人。观《庄子》文本发现,此说的确为郭象个人创见,但与《庄子》本义矛盾,便以“寄言出意”的诠释方法,含糊细节解释,故此主张并非郭象有意为之,而是遭遇庄子与儒家学说冲突时的无奈之举。
郭文安:从五院校《教育学》到《教育学》(新编本)(王道俊、王汉澜主编)再到《教育学》(第六版、第七版)(王道俊、郭文安主编),我们经历了一个从蒙昧到启蒙,再发展到自觉求索的历程。
回顾性分析该院收治的140例冠心病心衰合并糖尿病患者资料,按照治疗方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70例患者。对照组,男患者38例,女患者32例,年龄64~80岁,平均年龄(70.56±6.58)岁;观察组,男患者 39例,女患者 31例,年龄 62~79岁,平均年龄(71.65±5.57)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心功能分级等一般资料方面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至成玄英时期,“寄言出意”的人名诠释方式发生转变。成玄英受汉唐训诂学影响,开始具体考证《庄子》人名系统。其通过《庄子》文本论述人物来源,如“啮缺”一名,在《庄子》书中反复出现,未见于其他文献,成玄英对此有简单介绍。该名于《齐物论》中首次出现,并未引起郭象重视。成玄英标注“啮缺”是“许由之师,王倪弟子,并尧时贤人也。托此二人,明其齐一。”[1]何以得此结论?实际是搬运《天地》篇论述,《天地》篇明确说明“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1]将许由、啮缺与王倪师承关系运用于注解《齐物论》,可见成玄英熟悉《庄子》文本,并重视人物考证及背景、师承情况。再如市南宜僚,郭象也未作注,成玄英增添其为“姓熊名宜僚,隐于市南也。”[1]为儒家经典作注方式,具体考证庄子笔下人物名称,因此成玄英疏较郭象而言,呈现汉学训诂、考证之倾向。这种倾向随着宋学出现而淡化。宋代时期,面对佛学冲击,士人决定发展一套儒家心性之学①郭晓东《识仁与定性》一书中讨论到“摆在宋初儒者面前的一个巨大任务就是要从佛教手中夺回日渐丧失的精神阵地,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非要发展儒家自己的一套‘性命道德’之学不可,即儒家也只有穷深极微,才可辩彼之非,明己之正”。正是为了对抗佛教精微的心性之学,北宋儒学以心性为中心的义理之学于此基础上萌生。当时学者认为汉唐的训诂传统不能抵挡佛教的冲击,使得以训诂、考证为主的汉学被逐渐淡化并淘汰于宋人之中。,是以义理之学对训诂之学的冲击也波及到充满玄虚之言的《庄子》[3],其中对人名的诠释亦随之改变,考证痕迹被抹去,郭象的寄言方式重新占据上风。王雱、吕惠卿注作为北宋庄学代表,推动此风之长,但不同于郭象因难以融会儒、道矛盾而被动选择寄言,王、吕注更多主动诠释字义,用以衍生深意,更为细致深入地阐释庄子寄言,由此可反映宋代学者诠释义理能力的逐渐强化。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Jacket Multi-pile Structure Foundation Installation for Offshore Wind Power Engineering ZHANG Qinghai,LI Shanfeng,WANG Shuwen(126)
二、王雱对寓言人名的诠释
王雱在寄言基础上,认为庄子寓言中人名有深刻内涵。在诠释人名时,他常阐发字义,联系文章前后并作字义解释。通过人名具体内涵,说明庄子如何于一篇文章里先后构思若干人名,用以解释整篇文章的行文思想脉络,这种诠释方法巧妙回避了郭象寄言出意方式产生的矛盾,在历经汉唐训诂重视字词的风气后,成为字义考订与宋代义理之学结合的产物。有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方勇《庄子学史》写到:“王雱在《南华真经新传》中对庄子制名寓意的发微确实十分用心。”[4]以《德充符篇》为例,庄子塑造多位异形、丑陋的得道之人,用以说明形体与道德并不冲突。真正得道之人并不在意形体残缺,既不受制于外物束缚,还能游行于人世间。因此大量相貌丑陋之人,如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均成为庄子思想的寄托者,丑陋外貌与内在道德形成视觉反差,从而凸显“道”的统制性。基于此,王雱通过字义解释,挖掘人名蕴涵的深刻寓意,将其与庄子思想相互照应,形成由寓言人名构建的思想诠释系统。
较王雱有意以制名寓意方式建立次序叙述而言,吕惠卿偏向于《庄子》是一个不分先后次序的整体,他不赞同前人注《庄子》时所执庄子提供了高低评判标准之观点,认为高低评断本身即是对《庄子》之“道通为一”的遮蔽。吕惠卿于《进庄子义表》中明确指出,“夫以周之言内圣外王之道,深根固蒂之理,无不备矣。”[7]认为《庄子》全书皆以“内圣外王”和“深根固蒂之理”为主要论述思想,亦在于以此形成完整的文本结构,但并不以高下之分形成逻辑论述。这一方面是吕惠卿采取此种诠释方法,另一方面亦是其遵从“内圣外王”②梁涛认为“内圣外王”概念是新学学派会通儒道,将道家的天道自然与儒家的礼乐邢政相结合的产物。的思想而决定[8],正因吕惠卿对“圣”与“王”的双重肯定,决定其必须为《庄子》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找寻合理性,无论这些人物是出世、入世,抑或是被批评对象。
更为明确凸显这一倾向的是申徒嘉与叔山无趾的寓言,王雱解二者人名道:
叔者,与于伯仲也;山者,有形之最大也,此庄子制名而寓意也。以其次于申徒为第三,故曰叔而已;以其亦有德之大,故曰山而已。[4]
申徒者,教民之官也;嘉者,善之至也,此庄子制名而寓意。然申徒嘉者,贤人也,故次于王骀而言之。[4]
王雱将庄子第一个叙述的寓言人物王骀定义为圣人,申徒嘉为贤人,比王骀逊一等,叔山无趾再降一等,定为第三。此三人皆是“德充形不完”之人。其中申徒嘉之“申徒”一词,取教导民众的官职一义,“嘉”则为至善之代表,正因申徒嘉属人间官职之名,重视社会秩序和谐,以至善形象教化平民百姓,故王雱将其定义为贤人,从学于圣人伯昏无人,后者在王注中身份定位为“伯者,长也;昏者,晦也;无人者,无我也。为物之长能晦而无我,所以得贤人师之也。”[4]是以较圣人王骀、伯昏无人而言,申徒嘉以不重视外物,内充于德的形象引导众人向善,故曰贤人,是圣人之徒。叔山无趾则较申徒嘉贤人形象更低一层,王雱认为叔山无趾之“山”字是“有形之最大”之意,叔山无趾成为“德充形不完”中最在乎形体之人,较圣人王骀、贤人申徒嘉而言,因其更重视形体而成为内充于德中的末等之人。
从王骀到申徒嘉、再至于叔山无趾三人按位次排列,离道的距离越来越远。可见王注善于通过诠释人名中单独字义,将《庄子》寓言划分为不同等级,此为王注寓言人名诠释特色所在。从外部来看,王雱身处宋代义理之学兴盛阶段,将此风气注入《庄子》人名系统,以人名作为义理的寄存对象。同时此倾向还应源于郭象“寄言出意”的方法,又受汉唐训诂影响,一方面重视言外之意,一方面又挖掘字词的内在含义。从文本内部来看,王雱有意区分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三人等级,三者从圣人、贤人的降次,以形体束缚及与人世间的联系密切与否为区分点,可见王雱认知到有为、无为的差异,为其构建有为、无为关系的思想体系做了铺垫。
吕惠卿认为赤水之地代表重玄之极处,水即北方之意,水之北是重北,即为重玄。沿续由老子“玄之又玄”而来“重玄之道”③卢国龙在《道教哲学》一书中言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重玄之道’而言,‘玄道’阶段是站在道教的立场上融摄道家思想的一种历史传统和方向。具有这种传统和方向,使‘重玄之道’能深入老庄之理窟,即吸收玄学、佛学理论去重新阐释道家的经典著作,又归旨于道家,以道家之学为标帜,非依附于玄佛。”见卢国龙:《道教哲学》,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重玄”之道之是由老子“玄之又玄”中为有为、无为正名的思想演变而来,后吸收汉代经世致用之学,魏晋玄学以及道教“玄道”,佛学等多种因素,至于成玄英时期以“重玄”解庄。吕惠卿的“重玄”思想建立于此基础之上。,寓意黄帝游于赤水之北,则是寻求重玄之道,但因未排除形体、心知的干扰,以“玄珠”寓意的大道即遗失。而“象罔”之“象”代表消除“无”,“罔”代表排除“有”,消除有和无的概念,外物干扰即完全消失,此即为何只有“象罔”才能找到黄帝遗失的大道——玄珠。吕注在此与王注相符,二人皆将人名逐字定义,挖掘字义,从而与整个寓言相合,以此解释庄子采用上述人名构思寓言的原因。
吕惠卿要说明无论内圣还是外王,只要以“道通为一”为行事标准,均可逐渐达至逍遥,此即“迹虽有不同,而其以道为大宗师而至于命,则一也。”[6]世间人物形迹虽有不同,或以仁义著称,或以不拘为人知晓,抑或孔子、颜回等多以负面形象出现于《庄子》中的人物,只要其通于“道一”,主张内心的平静祥和,即能以平等形象为众人所解。因此,吕惠卿本着《庄子》密不可分的主张,采取以寓言人物印证此一统观念,实际上与王雱以制名寓意的方式建立次序叙述的框架意识产生分歧:王雱更为重视高下、次序型论述,并以此形成严密的逻辑结构;而吕惠卿更重视《庄子》全书的一统性与各类事物的平等性,主张“迹有不同”,道通为一。
由颜回、叶公子高、颜阖之傅卫太子、匠石、子綦五人构成的《人间世》,讲的是经世之道的延续,王雱认为由五人人名出发,主张忘身、信命以至于无我而任自然之事,其中颜回代表克己,子高求问于仲尼代表寻无我之道,但因二者皆寻求处世之道,故均为贤人之事而非脱离社会的圣人高度;至于颜阖之傅卫太子,匠石之见齐栎社,子綦观商丘之大木,皆是以寓言人名寄意有为的处世之道,因此较贤人之事而言更低,排序在颜回、子高之后,与《德充符》圣人、贤人至于叔山无趾的降次对等,皆是离道越来越远,且均以与人间世联系密切与否作为排序的依据。无独有偶,王注于《天运》篇也采用相同观点,《天运》篇以黄帝张《咸池》之乐彰显去除人为的自然之道,以孔子与师金对话说明儒家墨守成规的失误,再以孔子问道于老聃说明自然天理的永恒性[6]。但王注却以诸人物为基础,将其解释为“庄子之作篇,中言黄帝之张乐,次言孔子之西游,是皆有为之事也。故孔子之西游,而师金以其道而比刍狗,不及黄帝之事而已,故降一等而言之也。然师金止知孔子之道如无用之刍狗,而不知无用乃有用之妙也。夫黄帝之事,然为有为,而是皆有为之至也。故有为之至,则卒入于无为,故继言孔子问道于老聃也。”[4]先写黄帝,后写孔子,是由上至于下的递减过程,但二者叙述皆是有为之事,因此需要上升到第三个人物——老聃,说明黄帝和孔子有为之事须以老聃的无为为目标。因此,与前述相同,王注要为庄子运用的人名找到对应意义之后,再以人名为其文章构建有等级、有次序的逻辑框架,且等级划分均以有为、无为或与人间联系密切程度决定,可见其在注解时重视篇章内容完整性,以及对于有为、无为关系的自觉认知。
此外,《田子方》《让王》篇也有以寓言人物作为单篇记述顺序的依据。此种区分等级式的诠释在吕惠卿的笔下发生改变。二人虽同处北宋时期荆公学派,且受郭象寄言出意影响、汉唐训诂之风的洗礼,但观点仍存分歧,此为二人思想差异所致。
三、吕惠卿对于寓言人名的诠释
具体而言,王雱将寓言人名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三人为代表的“德充形不完”阶段,第二层次是以哀骀它、闉跂支离无脤二人为代表的“德充形至恶”阶段。前者中,王骀是与常季相对的人名,《庄子》原文中,常季作为贬低王骀断足的人而存在,代表看重形体、外物,为身外之物所累的大众形象,王雱言:“常者,习其庸常;季者,物之少稚。以其庸常少稚,而不足以知圣人,故曰常季,此庄子制名而寓意也。”[5]王雱解释“常”为庸常,“季”为稚嫩,说明常季因逐流于大众,且年纪尚轻,并不知圣人之道。王雱理解的圣人之道,即以王骀为代表的区别于众人,有取老子“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的状态,此类人不在意形体不完美,主张以“德充”之美代替众人对外物衍生至于容貌、肢体的追求,王骀之名即此意。王雱将其定义为“德充形不完”状态,实际隐含贬“常季”之庸常、稚嫩,举“王骀”之“德充”的意味,借人名寓意的一举一贬构成一个逻辑体系。
经世之道,必先于忘身,而其次在信命,故忘身则至于无我,而信命则任其自然。如此,则忧患不足以累之,此庄子于人间世之篇首言颜回之化卫,而次言叶公子高之使齐也。夫子高之使齐,而仲尼告之以义命,此贤人之事而已,所以降于颜回而言之。至于颜阖之傅卫太子,匠石之见齐栎社,子綦观商丘之大木,此皆有思有为之事也,故第降一等而言之。[4]
因同处于儒家对抗佛教精微心性之学而衍生出以心性为主的义理之学阶段,吕注对《庄子》寓言人名诠释也类似王雱解人名字义方式的思想建构。以《天地》篇为例,此章塑造大量人物形象,如黄帝、象罔、被衣、谆芒等,吕惠卿解构《庄子》的寓言意蕴于上述人名中。其中以象罔构成找寻玄珠一寓言,用以说明求得大道须无心无为,吕注解释:
水,北方也,水而赤则含阳者也。游乎赤水之北,则将以造乎重玄之极处也。昆仑之丘则形中之最高也,南望则向明而观之者也。将为至游以造乎重玄之极,而未能黜聪明,堕肢体,以出夫形之上,则其极不过形中之最高而已,此所以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也。……乃使象罔,象则非无,罔则无有,非有则不皦,非无则不昧;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6]
除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德充形不完”这一层次外,王注还以哀骀它、闉跂支离无脤二人代表“德充形至恶”第二层次,与第一层次对比,此二人的形体条件更加恶劣。其中,哀骀它解释为“丑恶之名也,以其德充而形恶,故制其丑恶之名矣。”[4]闉跂支离无脤解释为“闉跂者,言其忘行;支离者,言其忘形;无脤者,言其忘智。故忘行则所以无迹,忘形则所以忘我,忘智则所以无和。无迹则泯然绝世,无我则浑然同物,无知则泊然无为。故德之所以充也。此庄子制名而寓意。”[4]将哀骀它释为丑恶之名,闉跂支离无脤释为忘行、忘形、忘智,更是利用人名字义,突显庄子于《德充符》中表达的忘形之意,在王雱看来,皆是庄子有意制名而为之,况且较“德充形不完”的第一层面而言,“德充形至恶”则是通过放大形体的丑陋程度,说明得道之人并不重视形体,从而取其忘形而充德之意。因此,王注于《德充符》篇末总结:“夫庄子作德充之篇,始之以王骀,次之以申徒嘉,由次之以叔山,此三人者,皆德充而形不完也。故申徒不及王骀,叔山不及申徒,故第降一等而言之矣。至于哀骀、闉跂支离无脤者,亦皆德充而形至恶也,又第降一等而言之,与人间世之篇次序相同矣。”[4]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闉跂支离无脤,五人层次呈递减排列,用以说明离道德亦越来越远。有意诠释庄子的寓言人名,王雱构建起一个逻辑思想体系。不仅在《德充符》篇如此,其余篇目也常见此倾向,如《人间世》解释颜回、叶公子高等人名时,王雱写到:
将门理解为“开阖在我”,接受了老子“天门开阖,能为雌乎”一义,是将“天门”定义为人体百会穴,此穴贯达全身,为百脉之宗。因此成为修行身体的开关及中心点。有学者解释为“人的心思由此进出而通天,治理国家者,当谨慎人心之动静,顺天地之节候,理阴阳之进退。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就是‘天门开阖’,实际上是比喻治国理政应该动静进退有序。”[9]吕注就门无鬼之“门”大做文章,是引用老子“天门开阖”之意,只是更多强调个人体道情况,门无鬼因能在天门自由出入,并非如常人“出而不反”,故能够掌握人体及社会的天门,成为达道之人。此与王安石《老子注》异曲同工,有学者认为王安石“反对贵无贱有论,主张有无同出于道。”[10]吕惠卿主张或源于此。赤张满稽之“赤”“张”“满”“稽”四字则分别寓意“阳色”“不弛”“不虚”“考”,均未接近道家虚静境界,仅考量人之迹象,故赤张满稽并非得道之人,在他与徐无鬼代表的得道之人共观武王军队时,便会提出有虞氏与武王之治这种在迹象层面的区别问题,而徐无鬼作为达道之人,便会将有虞氏和武王之治皆划分为“乱而后治”,本质上均非“至德之世”,自不必用军队作高下之分。因此吕惠卿从人名字义解释说明寓言人物行为举止,与王雱注庄异曲同工。如前所述,王雱基于字义解释,善将寓言人名相对的故事做出层次区分,且此区分均由有为、无为或与人间联系密切程度决定,可见王注对有为、无为的区别对待。吕惠卿反对注庄者以次序法看待《庄子》中的寓言人名及其代表故事,其在《大宗师》篇中解释孟孙才、颜回、子桑等人言到:
除却上述人名外,《天地》篇中随后论述,亦与以上观点相符。通过门无鬼和赤张满稽的讨论,庄子欲说明有虞氏及武王之后之世,远不如无乱无治的至德之世,大有老子所谓小国寡民的清净之治的设想。吕惠卿又通过论述徐无鬼及赤张满稽二人之名,引入其解读:
门则开阖在我,而出入之所由也。出而不反,见其鬼灭而有实,鬼之一也。门无鬼则非出而不反,灭而有实者也,是体道者也。赤则阳色,张则不弛,满则不虚,而稽则考也,赤张满稽则非知考于玄妙弛虚之处者也,以迹稽之而已矣,故观武王之师以为不及有虞氏而离此患也。[6]
体育本来是一个来自于游戏,发展于游戏的学科,体育课受到小学生的喜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么,如何让“快乐”重回小学体育课堂呢?笔者认为,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庄子之论大宗师,而卒之以孟孙才颜回者,以为如孔子之徒,能体性抱神而游乎世俗之间,而后可以为至也。然恐学者以子桑之徒为不及孟孙氏,而子舆之徒为不及子桑,遂以为异趣,于是复合二人而论之,而其言则皆至于命而安之之辞也。以明子舆子桑与孟孙才颜氏之徒,其迹虽有不同,而其以道为大宗师而至于命,则一也。[6]
进一步研究了动态初始压溃应力和应变硬化参数的相对密度敏感性。结果表明,两个参数均随着相对密度的增大而增大,可以使用幂函数进行拟合。利用实验的方法得到了一个显含相对密度的D-R-PH模型,可以给研究不同相对密度泡沫铝动态力学性能提供相关的实验依据。
吕惠卿认为,庄子叙述各类寓言人物并非要将其区分层次,而是要告诉读者,尽管子舆、子桑、孟孙才、颜回等人故事与行为有所不同,但共有“道通为一”的核心,因此只要他们能够在世俗之中保持自我,就能够达到宗师之道。吕注明确提出“然恐学者以子桑之徒为不及孟孙氏”,是言庄子担心后世误认自己以孟孙才高于子桑,便在后面将二人合并讨论。实则是再次重申:人物之迹虽有区分,先后顺序虽有不同,但同样符合宗师之道。反观王注此篇,其明确提到“此庄子之为书,篇之终始皆有次序也。”[4]相对王注有次序地看待《庄子》由人名系统构成的寓言故事而言,吕惠卿有意反驳次序型论述。纵观吕注前说,除王注建构次序型论述外,郭象、成玄英等人皆无此说,吕惠卿是否针对王注所言尚无从得知,但目前可见,王注与吕注皆以寓言人名字义解释为基,以此构建庄子思想结构,但差别在于,王注主张以次序型论述区分各类人名深层涵义,代表王雱有意识地区别对待有为、无为;而吕注则予以反驳,可见吕惠卿更为平等地看待各类事迹不同之人物在本质上的同一性。此为二人思想构建之不同在诠释方法上的体现,前者建构由天到人,以与人世间的联系密切程度为区分点的递次发展;后者利用大一统观点,说明内圣、外王,或其他迹象不同之人在本质上的平等。寓言人名的诠释与解读,恰凸显二人思想建构于方法上的差异。
除此以外,《让王》篇也印证了吕注的人名诠释倾向,篇注:
颜阖列御寇屠羊说原寭曾参颜回以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禄施予,以至贫贱冻馁,虽滨于死,而不改其所乐者也。其次公子牟,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世俗之情,沉于人伪者,闻许由善卷之风狂而不信,故历叙圣贤人莫不乐道以忘其生,明乐道以忘其生为难,犹且为之,则不以天下国家伤其生为易,其信可知矣。[6]
王注对此篇也有论述:
大峡谷村游客中心应考虑游客心理,设置宣传资料发放点与免费自取点,在人工服务窗口与咨询台、行李寄存处进行宣传手册发放;在主干道边、景点巴士候车区与游客中心入口处设置宣传手册自取发放点,扩大信息输送的范围。
她觉得自己已经不配再穿它们了。她在整理它们的时候,看到了那一年生日,简东亮送她的那双GUCCI鞋,她早已经知道,那不是A货,是正版的GUCCI。因为当初认定了他不会买这么贵的鞋给她,所以一次也没有打开过,后来打开了,她认出了那是正版。
夫庄子之作此篇,所以叙至人之所为,而明无心之妙道,其为言各有序矣。夫中天下而帝者,人之所乐也,故首言尧、舜不以天下为意而相让。君一国,亦人之所乐也,次言大王、子搜不以邠、越累心而逃去。贫贱者,人之所恶也,故言颜阖、孔子、原寭、曾子、颜回不以贫贱为意而务去。及其终则言孔子之穷于陈、蔡、汤、武之除于桀、纣,所以明无心之道也。夫孔子之在陈、蔡,岂有心于忧患乎?故弦歌不绝而自适也。汤、武之除桀、纣,岂有心于得天下乎?故去其残贼而反正也。庄子能知古人之意而言之,所以觉天下之蔽俗也。[4]
对比言之,王注凸显以“为言有序”的次序方式,认为庄子寓言人名均有其独特思想层级,通过论述层级的递次演变,挖掘庄子思想内涵。该篇以尧舜、大王、子搜逃人之所乐为第一层次,颜阖、孔子、原寭、曾子、颜回安于贫贱为第二层次,孔子的无心之道为第三层次。三个层次呈递进关系,揭露“无心之妙道”;而吕注认为人物事迹虽有不同,至乎道的程度或有差异,但皆有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存在,即“不以天下国家伤其生”,是以颜阖、列御寇、屠羊说、原寭、曾参、颜回以至孔子,包括公子牟,皆是历叙圣贤人莫不乐道以忘其生的事例所在。二者关于寓言人名诠释虽均寄人名之字义探求庄子之深意,但在具体的人名及由此形成的寓言故事结构诠释上存异。
四、结语
在经历郭象“寄言出意”的人名诠释方式,成玄英考证《庄子》人名系统后,处于北宋及荆公新学时代的王雱、吕惠卿形成其关于《庄子》人名独特的诠释方法。二人皆以“制名寓意”方式,具析《庄子》人名字义,探究庄子思想之深意,拓展郭象寄言出意方式,并在具体解释中摆脱郭象无法融通庄子与儒家学说的困境。同时考证具体人物出处的诠释,明显受魏晋玄学及汉唐训诂之风双重影响。但同中存异,王雱有意识地区分有为、无为概念,因此善以有次序、有等级的形式解构《庄子》人名层次;吕惠卿则秉持一以贯之观点,将所有人名系统置于同等水平中,主张以行迹不同,道通为一。此差异源于二人诠释方法不同,同时与王雱重视得道程度、吕惠卿重视道通为一的思想差异有关。
仿真实验中,设L个地面移动IoT设备被初始布署在5×5×0.2(km3)的城市环境里,移动后其布署位置满足正态分布.仿真参数如表2所示.
参考文献:
[1]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刘笑敢.从超越逍遥到足性逍遥之转化[J].中国哲学史,2006(3).
[3]郭晓东.识仁与定性[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方勇.庄子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王水照.王安石全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6]方勇.庄子诠评[M].成都:巴蜀书社,2007.
[7]吕惠卿.庄子义[M].汤君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
[8]梁涛.北宋新学、蜀学派融合儒道的“内圣外王”概念[J].文史哲,2017(2).
[9]詹石窗.身国共治——《道德经》第十章解读[J].老子学刊,2018(1).
[10]尹志华.王安石的《老子注》探微[J].江西社会科学,2002(11).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805(2019)02-0061-06
收稿日期:2019-0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庄子》评点史”(12BZW063);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庄子》文学经典化的历程及其文学史意义”(2015YBWX071)
作者简介:李波(1971-),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
标签:庄子论文; 人名论文; 寓言论文; 字义论文; 二人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道家论文;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庄子》评点史”(12BZW063)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庄子》文学经典化的历程及其文学史意义”(2015YBWX071)论文; 重庆师范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