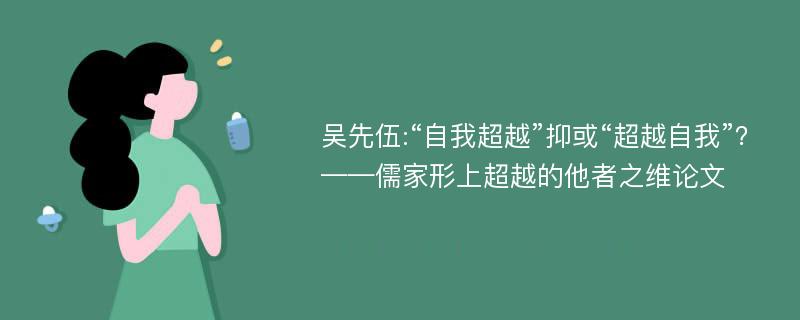
摘 要:近代以来,受到中西互竞的文化背景影响,为了给儒家哲学提供合法性证明,学者们一方面强调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一样都有超越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外在超越不同,是一种内在超越。由于这种证明没有注意西方哲学的超越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超越,从而使得儒家哲学的建构最终与西方哲学殊途同归,成为一种自我超越。实际上,儒家哲学否定自我中心论,要求“毋我”,希望在现实世界中通过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走向他者,实现一种与自我超越截然不同的对自我的超越——超越自我。正是因为儒家哲学强调超越自我,使得儒家哲学不太重视自我的权利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自我对他者的义务,而是更加重视自我对他者的道德责任,这对于现代社会中由于权利意识的盛行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具有消解作用。
关键词:儒家哲学;自我超越;超越自我
自从中西文化交通以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的儒家哲学受到“欧风美雨”的强势挑战,处于存亡绝续之际。为了延续复兴中华文化之慧命,学者们焦心竭虑地进行儒家哲学的建构工作,在强调儒家哲学超越性的同时,又强调它不是西方式的“外在超越”,而是独特的“内在超越”,以期突出儒家哲学的独特性。这虽然有利于为儒家哲学争得生存发展的空间,但是这种空间非常有限,因为其在不经意间已经将儒家哲学附属于西方哲学,从而接受了西方哲学的“自我超越”,抹杀了儒家哲学的“超越自我”,这必然会严重削弱儒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价值。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儒家哲学,重新发掘儒家哲学独特的超越自我路向。实际上,儒家哲学超越自我的路向,不是追求一种同一化本体论的建构,而是要建构起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关系,从而为他者承担责任。
一 “自我超越”:西方哲学样板下的儒家哲学建构
“超越”是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哲学就是一门超越性的学问。雅斯贝尔斯指出,在人类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国、印度、西方同时涌现出大量影响深远的哲学家,而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追求超越,“中国的隐士与漫游思想家、印度的苦行僧、希腊的哲学家、以色列的先知休戚相关,尽管他们在信仰、内容、内心状态上各不相同。人能够在内心与整体世界对照。他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起源,由此他超越自身与世界”。(1)[德]卡尔·雅斯贝斯:《论历史的意义》,《卡尔·雅斯贝斯文集》,朱更生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哲学家之所以追求超越,是因为哲学乃是一门安家的学问,要为人类建造安身立命之所。就像海德格尔所言,人是“被抛”到世界上的。人被抛向的世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充满偶然性的世界,“一切皆流,无物常驻”。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就像无根的浮萍,任由风吹浪打,四处漂泊,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感。因此,人类力图超越这种变动不居的充满偶然性的生活状态,将自身置于一个充满必然性的世界,让自己稳定下来,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事变都可以提前加以准备。
就像哲学概念来源于西方一样,中国在过去也没有“超越”这个概念。譬如,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曾经围绕康德的transzendent和transzendental如何翻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2)熊伟:《先验与超验》,《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7—22页。这就生动地说明,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概念来源于西方。在西方,“超越”概念最初出现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中,后来被康德用之于哲学。这不是说西方哲学过去没有相关的超越思想,超越思想在古希腊时代的本体论(或译存在论)形而上学中就已经存在,但尚未明确地加以概念总结。杜维明就曾经指出,西方人的超越观念来源于一元宗教或一元上帝的出现,“西方的上帝是从一个特殊的文化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宗教性,其精神性(spirituality)对世界上很多人而言,不仅是实在的真实的,而且是惟一使他们能超越转化的助源。舍此,则无法进行超越转化”(3)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9页。。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学者对于超越一词的基本看法,像对理解儒家哲学之超越性起到扛鼎作用的牟宗三就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超越概念,“凡可以成教而为人人所接受而不能悖者,必非某某主义与理论(学说,theory),亦必足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由之以印证并肯定一真善美之‘神性之实’,即印证并肯定一使人向上而不陷溺之‘价值之源’”(4)牟宗三:《生命的学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页;第63页;第61页。。后来,新儒家学者刘述先说得更为直接,“‘超越’的因素不能不是界定‘宗教’的一个重要的成分”,明确地肯定了超越的宗教信仰性质。(5)刘述先:《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5页。因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强调儒家哲学的超越性实际上与信仰之间具有内在联系。
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盛行,压抑了人们价值上的信仰追求,从而导致生命干枯萎缩,而西方犹有宗教可以弥补科学的不足,为人提供神圣的价值之源。对于中国来说,在科学主义的冲击之下,儒家哲学能否承担起超越性的信仰追求,这不仅事关儒学的生死存亡,同样也关系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历史的挑战,学者们纷纷论证儒家哲学同样具有超越性。自从中西会通以来,西方诸多学者就对中国哲学的超越性持怀疑态度,像黑格尔就认为孔子只是讲了日常道德智慧,并没有高深的哲学思想。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念,那么,中国文化生命就难以延续,“若谓中国文化生活,儒家所承继而发展者,只是俗世(世间)之伦常道德,而并无其超越一面,并无一超越的道德精神实体之肯定,神性之实、价值之源之肯定,则不成其为文化生命,中华民族即不成一有文化生命之民族”(6)牟宗三:《生命的学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页;第63页;第61页。。因此,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以及其他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学者都高度肯定儒家哲学的超越性,竭力为儒家哲学的合法性提供证明,从而重新确立人们的价值追求,为人类建造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主要目的,只在疏导时代学风时风病痛之所在,以及造成苦难症结之所在。如此疏导,点出主要脉络,使人由此悟入,接近积极健全之义理,重开价值之门,重建人文世界”(7)牟宗三:《生命的学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页;第63页;第61页。。
如果说儒家哲学只是与西方哲学同样追求超越,那么,儒家哲学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无法获得其存在的必要性,不能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因为在近代,儒家哲学已经在西方的坚船利炮所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冲击之下“花果飘零”,因此,儒家哲学要想在现代社会中慧命赓续乃至强势复兴,就必须具有独特性甚至是优越性。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学者们强调儒家哲学不仅追求超越,而且追求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超越。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基督教的上帝,都不属于现实世界,而是属于与现实世界相对的理念世界或天国,因此,无论是走向理念世界还是走向天国,都是对于现实世界的脱离,都是一种外在超越。虽然儒家哲学也追求超越,这使得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宗教具有一致性,但是儒家哲学更进一步,不追求“外在超越”,而追求“内在超越”,“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天道贯注于人自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Immanent)。因此,我们可以康德喜用的字眼,说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Transcendent),另一方面又是内在的(Immanent与Transcendent是相反字)。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此时兼具宗教与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8)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作者简介:赵敏荣,女,陕西西安人,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机械基础与化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程图学。
正如前文所言,超越本身具有宗教的意味,宗教就要讲神。因此,在西方,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讲神,柏拉图认为世界是由神创造的,亚里士多德指出善的理念就是神,就连死于“不敬神”之罪名的苏格拉底同样也认为只有神才最有智慧。所以,西方的哲学家都希望实现对于自身有限性的超越,希望再生如神明,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是无限的,能够在看似充满偶然性的世界中开出必然性之序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超越不是对于自身的否定,而是对于自身有限性的否定。这也就是说,西方的超越实际上是对于人类自身主体性的高度肯定,人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向上超越,从而最终摆脱现实世界对于自身的限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现实世界,把自己变成世间万物的根源,不仅要把握世界的本体,甚至要像神一样创造出一个充满必然性之序的新世界。当然,人类没有神所拥有的法力,不能全知全能,只能借助于科学技术才能认识改造世界。虽然在古代社会中人类也觊觎神的宝座,但惧于力量的悬殊,不得不对神顶礼膜拜;而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改天换地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具备了与神争位的资本,所以人类无情地斩杀了上帝,篡夺了神的宝座,从而将过去一切以神为中心变成了一切以人为中心。因此,对于西方哲学来说,不论是古代普罗提诺的“知己则知其源”,还是现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实际上都具有主体性哲学、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也正是缘此之故,列维纳斯得出结论,“他异性只能起源于自我”(9)Levinas,TotalityandInfinity, 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9, p.40.,“哲学是自我学”(10)Levinas,TotalityandInfinity, p.44.。虽然中国学者对此有所体认,但是他们却并不愿意因此而将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分割开来,而是要强调二者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从而自觉地接受西方的超越性,因此牟宗三在讲儒家哲学的内在超越时就说,“分解地言之,它有绝对普遍性,越在每一人每一物之上,而又非经验所能及,故为超越的;但它又为一切人物之体,故又为内在的”(11)牟宗三:《现象学与物自身》,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第14页。,从而将儒家的内在超越归属于本体论(或存在论)哲学范畴,“故中国无静态的内在存在论,而有动态的超越的存有论。此种存有论必须见本源”(12)牟宗三:《圆善论》,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338页。。与西方哲学相同,这种“本源”最终都要回到自我这个主体身上,人类安身立命最终是要实现自我的超越,而不是超越自我,就是要将自我从自然万物中超拔出来,置身于自然万物之外的同时将自身变成自身万物的根源、根据,从而肯定自我的本源性,“无论耶教,或儒释道三教,皆是最内在性的事,皆必通过最内在之主体以求人生之基本态度、信念与立场”,“儒释道三教皆不为依他之信。此三教本质上皆是从自己之心性上,根据修养之工夫,以求个人人格之完成,即自我之圆满实现,从此得解脱,或得安身立命”。(13)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84页。
孔子所强调的“时”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它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时间,更是现代意义上的时机、时势的意义,顺时而为更应该理解为顺势而为。就像朱利安所说的那样,“‘势’既表示‘条件’(condition)也表示‘变化’(évolution)”(21)朱利安:《从存有到生活:欧洲思想与中国思想的间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第14页。。儒家哲学认为人不是处于特定的周围环境之中,而是处于特定的境域之中,环境将人从环境中剥离出来,而境域则与人融而为一,人既在境域之中,又构成了境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境域在我与他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不断发展变化。人就像长江大河中的一颗水滴,既被水流裹挟不断向前奔流,同时又作为水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这股水流推波助澜,从而推涌成潮。因此,自我与他者彼此交织,构成一个整体,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自我超越现实世界的可能性,自我没有办法从整体当中抽身而出,将自己作为独特的主体置于一切他者的对立面。因此,孔子不仅否定自己是什么“天纵之圣”,强调自己与普通人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而且强调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自己就是普罗大众中的普通一员;自己之所以比别人懂得的东西要多,是因为自己小时候生活的特殊境遇造成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2)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610页;第1227页;第583页;第436页。,总的来说,自己与普通人的差别只不过在于自己更加勤奋、更加善于学习而已:“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23)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610页;第1227页;第583页;第436页。既然自己是普通人,连“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圣人都遥不可及,就更不用想着超越众生而成为超凡绝俗的神人了,人只能生活于现实世界之中。
虽然新儒家学者“内在超越”的概括引发了诸多争议,但是我们应该肯定其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内在超越的概括突出了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重要差异,从而突出了儒家哲学的重要价值。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价值仍然是有限的,因为这种概括虽然具有表面上的差异性,但是本质上仍然是以西方哲学的超越作为样板,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哲学的自我超越模式。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学者们对于儒家哲学超越性的建构,虽然有意强调中西哲学的差异性和儒家哲学的独特性,但是其本质上仍然是以西方哲学为样板,没能逃脱西方的本体论、主体论、“自我学”的陷阱,最终仍然要突出自我的中心地位,走向了与西方哲学相同的自我超越之路,这一方面与儒家哲学的“毋我”精神之间存在着冲突,另一方面也无助于解决当今社会中自我中心主义所引发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冲突,从而削弱了儒家哲学的现代价值。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地探讨儒家哲学超越的本来路径,而不是与西方哲学之间进行勉强比附。
在第3部分具有调节机体功能的食品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学习内容更加与实际生活结合,每个知识点都会安排1个或多个实验。例如,具有抗衰老作用的功能性食品,这个部分对应的实验内容为茶多酚含量的测定。众所周知,茶多酚具有抗衰老、防辐射等功能,茶叶的品种繁多,不同茶叶样品中茶多酚的含量不尽相同,实验过程中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让学生自主进行实验,选择不同的茶叶样品进行测定,对不同的样品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二 超越自我:儒家哲学的本来样貌
既然人要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那么,人就没有必要去关心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而要集中注意力于现实世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即使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也不过是现实世界的翻版;在中国哲学中,不是彼岸世界为现实世界奠基,而是现实世界为彼岸世界奠基。因此,“未知生,焉知死”的另外一种解读,就是“知生”也就“知死”,在生死之间,在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要自觉地将自身放置在现实世界之中。对于儒家而言,世界不是“我的世界”,世界不是由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世界是一个自然的世界,世界当中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自我生成,自我发展,自己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此,孔子面对世间万物,一方面感叹其变化不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8)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610页;第1227页;第583页;第436页。一方面感叹其不受人的操控,但又秩序井然,“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9)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610页;第1227页;第583页;第436页。。世界非但不是我的世界,反而要将我纳入其中,我不但不能支配世界,反而要受世界支配。对于古代儒家学者而言,重要的事情不是创造一个世界,也不是征服改造世界,从而成为造时势的英雄,而是恪守“时势造英雄”的信条,遵循世界发展的规律,顺时而动。孔子是世所公认的圣人,但他不是伯夷那样的“圣之清者”,不是伊尹那样的“圣之任者”,也不是柳下惠那样的“圣之和者”。他们要么太过重视自己的原则,要么放弃自己的原则,其最终都忽略了当时的特殊情势。孔子则特别重视时势、时机,要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时”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他是一个“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圣之时者”。(20)焦循:《孟子正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72页。这也就是说,孔子与伯夷、伊尹、柳下惠的重要不同在于,他不是将自己从现实世界当中超拔出来,不顾一切外部他者的影响,要么在现实世界当中强行推行自己的理想,要么从现实世界中抽身而退,而是将自己植根于现实世界之中,认识到自己就是现实世界之中的人,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现实世界的影响和制约,任何超越具体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想法都不可能变为现实。
既然在儒家哲学中,人不是神,不能像西方哲学所讲的那样生活在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只能生活在此岸的现实世界,那么,难道儒家哲学就不追求超越?就不害怕被浩瀚莫测的世界所吞没?就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安身立命之所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儒家哲学就缺少形而上学,就不能被称为哲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显然,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正是儒家哲学为大多数中国人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使得人们在世界发展的历史大潮中头出头没,始终没有被汹涌的潮流吞没消灭,人就像大江大河中的任由水流冲刷的芦苇,尽管被冲得东倒西歪,但是它却始终植根在现实的土壤之中,坚如磐石。实际上,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其真正的差别不在于有没有超越的问题,而是在于如何超越的问题。这也就是说,中西哲学在超越的目标、超越的方式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西方哲学所追求的是自我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自我要上天入地,成神成鬼,因而西方哲学要强调自我的独特主体地位,要将自我与自然万物对立起来。儒家哲学强调自我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强调人必须在现实世界之中安身立命。既然人要在现实世界之中安身立命,人生天地之间,那么,人就必须顶天立地,建立起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而不能将自身封闭孤立起来,所以人类就必须走出自身,超越自我,走向他者,通过与他者的联系为自我奠立稳定的存在根基。
西方哲学之所以追求自我超越,是因为它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预设了一个不生不灭的彼岸世界,并且这个彼岸世界是现实世界得以产生、发展、变化的原因。与此不同,中国哲学认为世界本身就是圆融一贯,混而为一的,现实世界之外不存在另外一个世界。道家的庄子讲“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4)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4页;第12页。,就是对于彼岸世界的拒斥。即使道家会讲到神,但是这个神与西方的神截然不同,“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5)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4页;第12页。。首先,神并不与人相对,而是与人相统一的,因为他是“神人”,具有人与神的双重品格;其次,神虽然与普通人生活在平原开阔地带有所不同,但并不居于与现实世界相对的理念世界或天国,而就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故射之山。中国人用来描绘世界的词汇是宇宙,“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就是由现实的时间与空间所构成的,从而彻底地否定了彻底超脱现实时空限制的彼岸世界,否定了像上帝那样超越现实世界的神灵。儒家更是对神敬而远之,像《论语》当中就有关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明确记载。(16)程树德撰:《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0页;第760页。儒家学者的目标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而是“人伦之致”的“圣人”。“圣人”虽然出类拔萃,但与普罗大众并无本质的不同,毕竟还是人类当中的一员。既然人只能作为人而存在,那么,人就应该作为一个人而活着,人应该活得像个人,就要生活在人群之中——“与人为徒”,就要关心人的生活,而不是关心死后成神还是成鬼,因此,要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现实生活上,“未知生,焉知死”(17)程树德撰:《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0页;第760页。。
图书馆面临新一轮的转型。这场转型不仅要求图书馆保管好已有的资源,而且要增强大局意识,融汇本地资源与全球资源,共同建设可持续的全球型知识共享空间;要加强服务意识,增强加值服务能力;并积极与出版机构合作,有力推动知识资源的开放获取化。为此,图书馆应充分发挥自身在资源管理、编目技能以及项目策划方面的专业优势,在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的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从表4可以看出,非常喜欢和喜欢学习汉语的学生占88.33%;有89.44%的学生觉得汉语非常有意思和有意思;91.67%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汉语水平进步很大或有进步。可见,学生学习汉语的态度是积极的,效果也非常明显。
既然人注定处于现实世界之中,要生于斯,死于斯,那么,人如何实现形而上的超越呢?人的在世特征就决定了,儒家哲学不可能像西方哲学那样追求自我超越,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人只能存身于现实世界之中,并在现实世界之中实现超越。因此,儒家哲学选择了一条与西方哲学不同的超越之路,但这并不是所谓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的区别,而是自我超越与超越自我的差别:西方哲学是自我超越现实世界,儒家哲学是在现实世界中超越自我。形而上学的超越本身是对于有限性的超越,西方哲学之所以要“摄多归一”,是因为具体的差异性的杂多都是有限的,而“一”则是至大无外的大一,一切都出于一而复归于一,而这典型地表现于本体论或存在论,“在我看来存在者是一个共同体,我就从这里开始;因为我将重新回到这里”(24)巴门尼德:《论自然》,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1页。。本体论最终回归到自我中心论,而我作为此时此地的存在者,作为众多存在者中的一员,实际上仍然是有限的,因此,西方哲学的超越最终仍然没有摆脱有限性的窠臼,以一个有限的存在者来排斥其他有限的存在者,从而导致存在者之间的互相对立与斗争。在儒家哲学看来,每个自我都是有限的,自我始终处在生死之间,“慎终追始”标示的是有限的生命长度;同时,人作为特定时代背景和生活境域中的人,其所能达到的认识和所成就的业绩都是有限的,孔子面对奔流不息的河流和“翔而后集”的飞鸟所发出的由衷感叹,实际上也是出于人生有限性的无可奈何。不过,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动物安于生命的有限性,在本能的牵引下而生活,人之为人,则在于不安于自己的有限性,总是试图突破有限去追求无限,从而实现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
对于自我来说,自我始终处在时空当中,因而自我的有限性也主要表现在时空当中的有限性,因此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也主要表现为时空的超越,西方哲学做法则是将自我超拔到时空之外,从而把自我变得无限起来——无始无终,无所不能。儒家哲学则认为,宇宙本身就是无限的,因为宇宙本身就是无始无终,至大无外的,所以,实现对有限的超越并不需要脱离现实世界,而只需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对于有限自我的超越。超越有限的自我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长度,而这两个方面都不是依靠自我所能达到的,因此,对于儒家哲学而言,我们必须要迈出自我而走向他者,只有借助他者,我们才能不受时空的限制,既能胸怀天下,心忧万世,又能使我们的所思所想在现实中得到落实。
宇宙包含时间与空间两个重要的维度。从空间来说,它包罗四面八方,世间的一切人和事都被纳入其中,并且这些人和事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事物都在其中承担着特定的功能和作用。我也是整体中的人,所以,我也有自己特定的功能和作用,我作为子女,需要赡养父母、延续香火;作为父母,需要抚养教育子女;作为教师,需要教书育人……。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特定的功能和作用,世界这个整体才能得以维持,才能健康有序地运行发展,也只有这样,我才能获得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我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存身立足。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我与所有他人、一切自然万物之间形成了互相支撑的关系,只有一切他者都获得了安身立命之所,都在世界上“立”住了,我才能“立”得起来,否则,我就失去了依靠,失去了支撑,就会东倒西歪,所以,我们不仅要让自己“立”起来,也要让他者立起来。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25)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428页;第958页。,这不仅告诉人们:在考虑“己立”欲望的同时,也要推己及人,顾及他人“立”的欲望,而且也告诉人们: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立起来的同时,更应该首先让他者立起来,他者的“立”构成了“己立”的前提和条件,没有他者的“立”就没有“己立”。这也就是说,对于自我,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己立”,反而是“立人”,我们在心里装着的不是自我,而是“他人”,而是“他者”,从而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因此,儒家是“毋我”的,不以自我为中心,这典型地表现在中西哲学对于爱的理解上。像柏拉图所讲的爱就是一种自私的爱,我们之所以会去爱他人,是为了找回那个曾经完满的自我,因而柏拉图的“爱”是“为我”的。儒家的爱是“毋我”的,儒家爱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仁者爱人”(26)焦循:《孟子正义》下,第595页;第783页。,爱一切他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且仁爱他者是一种不求回报的忘我付出:“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27)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428页;第958页。有时为了他者,我们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死而后已,曾子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8)焦循:《孟子正义》下,第595页;第783页。因此,儒家始终将他者置于自我之前之上,我们不是要拘执于自我,而是要超越自我,走向他者。
汪、谢之流可谓深得庆亲王父子的真传,在贪腐中深谙“舍小取大”“以退为进”之策。“退贿交贿”是为“沽直名”,以“廉”掩腐。纪检部门对这类贪腐现象,须擦亮眼睛。
既然宇宙包含时空两个维度,那么,我们不仅要在空间中超越自我,同样也要在时间中超越自我。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其中最重要表现就是人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虽然历史上有关于彭祖长生不老的传说,但也不像上帝一样不生不灭,不过“千岁”而已,“千岁”虽然比之常人,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但仍然是有限的。对于普通人而言,人生基本不过百年,只有短短几十个春秋,因此,庄子常以“朝菌”“蟪蛄”“夏冰”来比喻人生的短暂。人生虽然短暂,但是人始终都有无限性的要求,“人生不满百,却有千岁忧”,有限的人生如何能实现无限性的超越呢?为了使生命走向无限,道家后学走向炼丹修身,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然而他们始终无法打破“人生自古谁无死”的自然规律。对于儒家而言,出生入死乃自然规律,我们要做的是顺应这个自然规律,“死而后已”、“舍生取义”本身就是对于死亡的慨然接受,因此,儒家不是通过逃避死亡来实现无限性的超越,而是通过“生生”来实现无限性的超越。世界之所以为无限,就在于世界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29)惠栋:《周易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00页;第259页。,“生生之谓易”(30)惠栋:《周易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00页;第259页。。因此,人类要想实现无限性的超越就要顺应天地之德,同样要生生不息,从而要实现人类的生产,在生产与再生产中不断超越自我,所以,儒家特别重视后代的生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31)焦循:《孟子正义》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32页。。
329 HPLC-TOF/MS 快速鉴别相思藤中的化学成分 付振贺,黄玉凤,黄超君,谢从景,吕 磊,杜红丽,赵 亮,焦 杨
生儿育女是实现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方式,正是在不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人类绵延不绝。儒家产生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而农业经济是以家族为单位,因此,儒家特别重视家族的繁荣兴旺和长盛不衰,尤其是家族中人丁兴旺,儿孙成群,因为只有“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才能保持家族的香火长明。因此在儒家哲学当中,家族的生命延续居于重要地位,为此,我们需要新生命的不断诞生,从而让自我的生命在他者的生命中延续流传,而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血脉相传。这并不是说,传宗接代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色彩,它恰恰是对自我中心论的克服,因为这是让自我融入家族的历史,从而超越自我最为有效的方式。一方面,我们作为家族当中的一员,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与家族联系在一起,都是为了家族而非自我本身,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无我”的,就像我们考取功名,是为了“光宗耀祖”,我们结婚生子是为了“传宗接代”,这些本来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私人事务变成了事关家族兴衰的公共事务,似乎成了他人的事务。结婚本来是两情相悦,结果却非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我的感受被排除在本应着重加以思考的问题之外。另一方面,孩子出生之后,虽然他身上流淌着我的血液,他是“我的孩子”,我们在他身上似乎又能看见自己的影子,但是他的身上也流淌着家族的血脉,同时他身上也流淌着自身的血液,他既是属于家族的,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恰恰不属于我。孩子出生之后,就像我们写出的作品一样,又与我们这些作者之间产生了间距,他具有了自身独立的品格,他自我生成,自我呈现,不再按照我的设想来成就自身,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儿大不由娘”,孩子做了我们所没有做的事,成了一个我们所不能成为的人。孩子对于自我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他者,他超越了自我的同一性,同样,孩子又有孩子,子子孙孙,连绵不绝,自我就在此绵延不断的“生生”之中,趋向无限,从而实现了对于自我有限性的超越。
三 重视责任:超越自我的后果
西方哲学强调自我超越,实际上就预设了自我在世界当中的特殊重要性。哲学的超越本身就是要为人类解决安身立命之所,自我超越采取了一种向上超拔的方式,使自我脱离现实世界而高居于现实世界之上,这就是西方人追求脱离现实世界的原因之所在。在西方,人们总是坚信“人类不会永远束缚在地球上”,古代人希望成神进入天国,现代人则希望摆脱地球。首颗人造地球卫星被发射进入太空之后,“在事件发生的一瞬间,直接的反应是大松一口气,人类总算朝着摆脱地球对人的束缚迈出了第一步”。(32)[德]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1页。现实世界被看作对于自我的束缚,我们脱离了现实世界也就意味着我们彻底获得了自由。过去,上帝生活在天上,上帝拥有无限的自由;在现代,人们通过科学技术谋杀了上帝,从而篡夺了上帝的特权,从而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上帝死了,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人们“跟随科学,想单靠自己的理智来建立合理的生活,而已不用基督,像从前那样,已宣告犯罪是没有的,罪孽也是没有的”。(3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卓夫兄弟们》,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言论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588页。在过去,人们是替上帝“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34)《圣经·创世记》1: 26。。现在,世界上的一切都属于我,我无需再征得谁的同意就可以自由地处置世间万物。因此,自我超越实际上就是将自我提升到自然万物之上,将自我从自然万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拥有征服改造自然万物的特权,迫使它们为自我服务。由于儒家哲学不追求自我超越,而是追求超越自我,这使得儒家哲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儒家追求超越自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儒家认为人是整体当中的人,人不能从现实当中脱离出来,否则人就无以为家,就无法获得安身立命之所,就无以为“人”(具有身份规定性的“人”)。自我作为儿子,就不能脱离家庭而存在;自我作为教师,就不能脱离学校而存在;自我作为商人,就不能脱离市场而存在……。正是因为儒家将人置于整体当中,并将整体置于个人之上,这导致儒家不像现代西方哲学肯定个人绝对的自主权。在现代西方,“社会不仅是个人活动的舞台,而且也是依据个人自己的目标进行再造的潜在原料”,“个人不受任何社会的约束,他自己的目标——不仅是权力,而且是荣誉和名声——是他的行为的唯一标准”。(35)[美]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9页。在儒家看来,人作为整体中的人,整体与个人相比具有优先性,虽然儒家特别重视个体的自我修养,但是其最终的目的,还是服务于社会整体。“修身”作为起点,其最终目标是要服务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否则,如果一个人起于“修身”而终于“修身”,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独善其身”的贤人,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兼济天下”的贤达之士。贤达之士心中所怀想的始终是作为整体的天下,而非作为个体的自我,这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家对于整体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我的中心地位、主体地位,这必然会抑制中国人自我中心意识、权利意识的发育,而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大公无私”观念的盛行。在古代中国,“公”与“义”联系在一起,“急公好义”生动地诠释了天下为公之人就是一个道德高尚之人;“私”与“利”联系在一起,“自私自利”则生动地诠释了只知谋取个人利益的人是道德低下之人,从而否定了人们对于自我权利追求的合法性。崇公抑私、重义轻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人权利意识淡漠,这在近代引发了启蒙人士的激烈批判,“无权利者,非国民也”(36)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73页;第480—481页。,这不能不说确实是儒家哲学的一个不足。
虽然儒家所追求的超越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人追逐权利的现代化步伐,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当今这样一个权利至上的时代里,争权夺利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人与人之间相互敌视,相互防范,缺乏关爱,缺乏信任,因此,我们更应该反思儒家对于权利的抑制所带来的重要启示。权利是与义务相对的一个概念,二者相互支撑,相互制约,这种相对关系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此消彼长的错觉,因此,当人们认识到中国人权利意识薄弱的时候,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人义务意识强盛。在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甚至因此而认为中国人只知有义务,而不知有权利,所以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人的道德称作“奴隶的道德”。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确实承担了太多的被动性的义务,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将这看作儒家哲学的本来面目。由于义务与权利相对,权利义务是现代法律上的概念,“德意志硕儒莱布尼紫曰:‘法律学者,权利学者也。’旨哉言乎!权利之表为法律,法律之里即权利,不可分而二之者也”。(37)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73页;第480—481页。而儒家既对法律有所批判,又缺乏权利意识,那么,儒家自然也就无所谓法律上与权利相对的义务意识,而这实际上就是梁启超说中国有私德而无公德的原因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按照现代法律观念,义务“一般指某种我们在某些情况下被要求去做的事情,诸如对已签订的合同,已作出的诺言要履行”,“普通的意义指归属于任何社会位置的拥有人(如父母,公民或在职人员)的要求、义务或分派的任务”。(38)[美]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8、 280页。前者是指订立契约所带来的义务,后者是指由特殊社会地位或角色身份所带来的义务。对于公然宣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39)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927页。的儒家来说,契约精神是相对缺乏的,就更不用说由此而带来的义务,即使是被安乐哲等学者所高度推崇的角色义务,实际上也不符合儒家哲学的本来面目。因为角色义务从属于自我的社会角色,具有强烈的被动性,而儒家哲学往往强调突破角色的限制,“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40)焦循:《孟子正义》下,第633页。,在角色义务与道义之间选择积极主动地承担道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41)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29—530页。。因此,儒家的超越自我不仅是对于权利的否定,同样也是对于义务的否定。由于权利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义务是权利的派生物,义务是服务于权利的,所以,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同样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而,儒家的超越自我必然要超越权利及与之相应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中,承担义务表示的是自我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万物的关心付出,如果说儒家否定权利和义务,是不是就意味着儒家不关心他人、社会和自然万物,就不为他者付出了呢?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儒家讲仁爱,不仅要“爱人”,而且要不断外推,做到仁民而爱物,并且要为他者尽心竭力地付出,做到“死而后已”。儒家这样做不是承担所谓法律的义务,而是承担道德的责任——“仁以为己任”。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义务与责任密不可分,甚至可以直接等同,当我们说“我们有责任……”和“我们有义务……”的时候,往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这是现代道德法律化的结果,并不意味着道德责任就等同于法律义务,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第一,义务与权利相对应,而责任并不与权利相对应。在现代法律中,为了确保公平,每个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要承担与之相应的义务,因此,义务实际上是从属、服务于权利的。在儒家那里,人们承担道德责任并不是因为人们享受了什么权利,而是出于人的仁心善性——“不忍人之心”,就像孔子、大禹、后稷承续道统、治理洪水、教民稼穑,并不是因为他们享受了什么权利、处于什么特殊的工作岗位,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忍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见其生不忍见其死”(42)焦循:《孟子正义》上,第83页;第311页。,所以,他们要主动地承担起救民于水火的责任。第二,义务以自我为中心,责任以他者为中心。由于义务是权利的派生物,而权利本身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现代人强调权利,就是强调自我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权利以及由权利派生出来的义务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儒家讲道德的责任则是“毋我”的,因为儒家讲责任是不顾个人利益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3)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王继如:《汉书今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499页。。唯其如此,孔子才能超越个人得失,“知其不可而为之”(44)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1029页;第817页;第721页。,全心全意地为他者付出,心里装着的都是他者。
正是由于儒家所提倡的责任是不顾个人利益的全心全意地付出,并不符合法律的公平性要求,因此,它不是法律的义务,而是道德的责任。从道德责任与法律义务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强调道德责任的儒家明显地超越了自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他者为中心。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儒家彻底地抛弃了自我,儒家所超越的是权利的自我,而非道德的自我,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表达,儒家所超越的乃是权利的主体,而非责任的主体。实际上,儒家非但没有抛弃道德的主体,而且是高扬道德主体的大旗,儒家非常重视道德的自我。虽然儒家一再强调“毋我”,反对人们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但是儒家却一再强调人们要有责任的自我担当意识:“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45)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1029页;第817页;第721页。“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46)焦循:《孟子正义》上,第83页;第311页。儒家之所以如此重视道德的自我,就是因为“舍我其谁”的问题。对于权利,人们可以放弃、可以让渡,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他者,但是道德责任则不能放弃、更不能让渡,我们之所以是道德的,就是因为我们主动地担当了我们本不需要承担的道德责任。就像孔子的朋友死了,虽然孔子并没有收殓的义务,但是孔子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却主动地将这个责任担当起来——“于我殡”(47)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1029页;第817页;第721页。,对于这样一个为朋友收殓的道德责任,孔子没有办法将它让渡给别人,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代替自己来为老人让座、为贫困人口捐款一样。道德责任必须由道德的自我来承担,否则,我们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之人。也正因如此,儒家哲学在超越自我的时候,主要是对于权利自我的超越,而没有超越道德的自我。也正因如此,儒家哲学对于当今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为平息人们由权利主体意识高扬而引发的争权夺利提供重要的资源借鉴,从而促进世界走向和谐。
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6.005
【作者简介】吴先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23)。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创新与中国行动方案”(项目号:18VSJ014);江苏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原始儒家责任伦理研究”(项目号:19ZXA002)。
(责任编辑 付长珍 王成峰)
标签:儒家论文; 哲学论文; 自我论文; 世界论文; 现实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创新与中国行动方案”(项目号:18VSJ014)江苏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原始儒家责任伦理研究”(项目号:19ZXA002)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