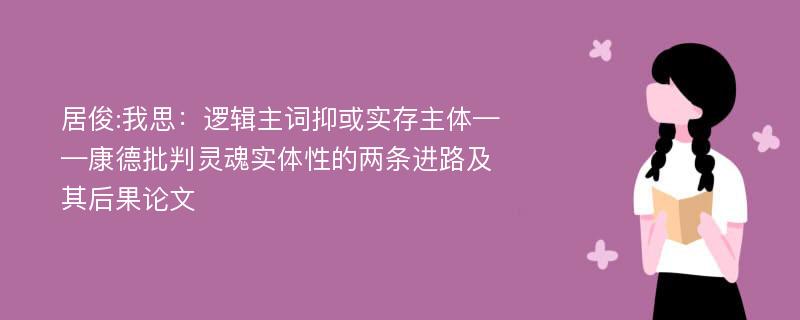
摘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呈现了两条批判灵魂实体性的进路:A版关注于灵魂实体性谬误推理的无结果性,B版着重于该推理的无效性。A版对实体的先验规定与灵魂的经验规定,遗留了灵魂实体的理念性,也与理性心理学不符。B版将实体视作先验与经验的融合,将作为灵魂的“先验我思”定为逻辑主词,否认了它在实体名下的实存主体之义。“我思”被阐释为,在不确定的经验性直观中被给予的“我实存”。在无关实体的意义上,“我思”是逻辑主词与实存主体的合一。它作为实存主体,既是区分现象自我与自我自身的基点,也是灵魂不死公设的先导。
关键词:灵魂;实体;理性心理学;主体(主词)
将灵魂视作实体,一直是传统哲学的基本信条。近代对于灵魂实体性(Substantialitt)的断言起自于笛卡尔。他明确宣称:“我是一个实体,它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1](P28)这一断言规定了唯理论讨论灵魂问题的总体方向。但康德在批判时期意识到: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心理学家奉为圭臬的“灵魂实体性”原则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谬误推理”(Paralogismen)一章中,他对这一原则进行了犀利的批判。然而,在第一批判的A、B两版中,对“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一章的论述是差异较大的。霍尔斯特曼(Rolf-Peter Horstmann)将两版“谬误推理”的区别概括为体系批判(Systemskritik)与方法批判(Verfahrenskritik)。也即是说,A 版塑造出理性心理学‘四个推论的体系’(实体性、单一性、同一性与观念性)的实质性错误,而B版证明了从灵魂的分析判断导出综合判断的方法是行不通的①与霍尔斯特曼不同,克琪尔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康德在B版之所以压缩并重述了A 版的“谬误推理”一章,更多是出于B版行文简洁的考虑。她这样说道:“正如我随后将指示的,B版演绎具体化了许多关于统觉的在第一版谬误推理中已经被处理过的要点。由于这种已经涵盖的材料,康德能够呈现一条简略得多的批判线索:理性心理学家在试图从分析性前提中抽取出实质性结论上犯了错。”(Cf.Patricia Kirtcher.Kant’s Transcendental Psycholog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83.)无疑,她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就掩盖了康德在A、B两版中操作理路的差别。这种差别不应仅仅限制在行文的详略之上,而理应指向康德内在思路的变更。在这一点上,霍尔斯特曼的解读显然是更令人信服的。[2](P411)。由此,两版对灵魂实体性的批判也采纳了不同的进路。这两条进路可以概括为:三段论推理的“无结果性”与“无效性”之分[3](P334-335)。其中,A 版对该推论“无结果性”的判定,遗留了对灵魂实体性的理念性认同。而它对大前提实体概念的先验规定与小前提灵魂概念的经验规定,与理性心理学的设定相矛盾。B 版对该推论“无效性”的分析修正了A 版的失误。它将大前提的实体概念视作先验与经验的融合,将小前提中的“先验我思”定为逻辑主词,从而否认了作为“我思”的灵魂能够兼得逻辑主词与实存主体的实体之义。随后,B 版又将 “我思”阐释为非实体化的“我实存”,后者在不确定的经验性直观中被给予。在无关实体的意义上,“我思”既是逻辑主词,又是实存主体。“我思”的这种实存非但是区分现象自我与自我自身的基点,更是灵魂不死公设的先导。下面,我们将从A 版“谬误推理”开始讨论。
一、A 版灵魂实体性推论的无结果性
康德在A 版“谬误推理”一章中认为,理性心理学对灵魂实体性的论证可以被归纳为如下三段论推理:大前提:实体是我们判断的绝对主词(主体)①“Subjekt”这个词需依据语境分别译作“主体”或“主词”。实际上,正由于这两种意义的混淆引发了谬误推理的发生。另需注意的是,这个词的拉丁文为“subiectum”,意为“位于下面的东西”,并不涵盖“自我”之义。,因此不能被用作谓词。小前提:我是我的一切判断的绝对主词(主体),而且不能被用作任何谓词。结论:所以,我(灵魂)是实体[4](P217)。
在他看来,这一论证只具有形式上的正确性,因为在其中对实体概念的理解是不当的。一般而言,理性心理学家(比如鲍姆加登)将实体解释为“仅依凭自身而不依赖他物的持存之物”,并认为它们就其本性来说必然是永存的[5](PP50-51)。康德反对这种独断的实体观,在他的眼中,实体作为范畴,亦即纯粹知性概念,只是一个主谓判断的机能或形式。他明确地说道:“关于任何一个一般的事物,就我把与事物纯然的谓词和规定区别开来而言,我都能够说它是实体。”②下述康德原文需调整之处,笔者将按照邓晓芒译本与德文本进行改动,不再赘述。[4](PP217-218)由此,这种实体的意义仅是一个主谓判断的主词。如果我们要使实体指涉一个经验中的现实之物,那么我们就必须用作为内容的直观杂多来充实该概念。这也是第一批判的主导观念——“直观无概念则盲,概念无直观则空”的题中之义。所以,依照康德的观点,实体概念仅仅是我们判断的绝对主词(主体),也即一种单纯的思维机能。因为在范畴表中,实体范畴是从定言判断中抽引出来的,而康德明确地宣称,在此判断中发生的是“谓词与主词的关系”[4](P55)。换言之,这种在与谓词的关系中的主词就是实体范畴的原初之义。这大大削减了理性心理学设定在大前提的实体中的原先含义——非物质性、不可毁灭和永恒持存等。
工作人员放走了成年虎鲸,他们拉起的网越收越拢,把幼年的虎鲸都围在里面。有一只小雌虎鲸被渔网缠住,它拼命挣扎,小虎鲸的妈妈发现情况不妙,转身撞向渔网,可是渔网都是尼龙绳做的,虎鲸妈妈失败了。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捕捞上船,虎鲸妈妈悲伤地低鸣着,开始是它,接着是两头,三头……最后整群虎鲸开始鸣叫,既是对小虎鲸的呼唤,也是对人类对虎鲸捕捉的抗议。
接下来,在小前提中,他对“自我”(灵魂)的理解同样只在纯粹思维层面展开:我是我一切判断的绝对主词,不能被作为谓词。而将自我视为所有判断的逻辑主词,是他先验统觉学说的自然结果,因为“一切不同的经验性意识都必须结合在一个惟一的自我意识中,这个综合命题是我们一般思维的绝对第一的综合原理”[4](P81,注1)。换言之,经验性意识必须与一个先验自我意识(先验统觉)相关,进而一切意识才成为我的意识。这就等于说:所有的判断必须以一个形式化的“我”作为绝对主词,才能成为我的判断。这样,在结论中,“我(灵魂)是实体”只相当于如下一点:我是“思维的恒常的逻辑主词”[4](P218)。这就彻底消解了理性心理学孜孜以求的灵魂实体的永存。康德的结论是:灵魂“只在理念中、而不在实在性中表示一个实体”③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以下皆同。[4](P218)。
在此背景下,康德再阐明他们所犯的“中词含混”之错误,就让他们心悦诚服了。他们现在必须承认:他对他们观点的归纳是正确的。首先,他们眼中的实体就是“逻辑主词”和“实存主体”的合一。其次,理性心理学实际上只针对着,思维着的存在者(自我、灵魂)作为“逻辑主词”的先验规定。由此,他们在推论中“通过言说式的诡辩”所犯的错误就昭然若揭了。大前提中的实体是逻辑和现实双重含义上的主词(主体)。而小前提中的思维着的存在者只意味着“逻辑主词”。但最后的结论,却让自己从“逻辑主词”偷取到了“实存主体”的含义。这一推论自然是非法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只能从中得出,“思维着的存在者”是一切判断的“逻辑主词”,此外无他。因此,该三段论“是一个同一的命题,它对我的存有方式不能有丝毫揭示”[8](P264,注1)。这样看来,赫费对这个三段论推理的注解是存在问题的。他认为:“大前提中的主词(主体)是指一个客体化的自我,作为内在经验对象的实在自我,与之相对,小前提中的主词(主体)是指单纯被思考而内容空洞的‘所有一般概念的载体’(B399)。”[10](P232)在他看来,大前提的主词(主体)是指一个客体自我或作为内在经验对象的自我,而小前提中的主词(主体)则是指形式化的“思维自我”,这就导致了主词(主体)概念在大小前提中的不一致,该推论进而失效了。很明显,他在小前提中将主词(主体)视为形式化的“我思”,合乎康德的原意。可当他在大前提中将其径直定为客体化的经验自我时,这就显得不太准确。如前所述,大前提中的主词(主体)只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实体,而非特指经验自我,后者毋宁说是这个谬误推理所力图达到的结论。因此,该推理对主词(主体)概念的规定的确是不一致的,但这种不一致并不发生在上述两种自我之间,而发生于主体(主词)概念的逻辑和现实两种含义之间,更确切地说,发生在“逻辑主词”与“实存主体”之间。当然,就理性心理学家所预想的实体概念中,主体(主词)概念的两种含义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当他们将实体概念运用到自我(灵魂)概念上时,这两种含义就不可能自然过渡了。相反,自我只能取其中的“逻辑主词”之义,而无法兼得“实存主体”之义。换言之,自我在逻辑上可以将自己保持为不变的主词,在现实中却无法作为主体持存下去。这样,理性心理学宣称的命题——“我可以作为实体而实存”,就宣告破产了。
总之,由于康德在A 版中更注目于灵魂实体性命题的“无结果性”,因而遗留下了两个难题:首先,他对灵魂实体理念性的赞同,使得他对灵魂实体性的批判有不够彻底的嫌疑;其次,他对灵魂实体性三段论推理作出的判定——先验-经验的混淆,与理性心理学的原初规定似乎有所矛盾。所以,虽然他从未公开道明A 版谬误推理的不足,但他在B 版的前言中坦承,在对第一版的改进中,“有的是要纠正对从理性心理学得出的谬误推理的误解”[8](P22)。下面,我们来考察B版的纠正是如何进行的。
(1)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高。在县级地方,政府机关大多以发展经济为主,忽视了自然环境保护。为了尽快获得更多GDP产值,县级政府并未严格规定工业生产排污标准。另外,县级政府对于农业生产污水熟视无睹,没有积极推广沼气设备等科学处理措施,使得县级土壤、水和大气污染较多。
由此,实体不仅被思考为判断的主词,而且也作为主体而实存。换言之,实体不仅在思维中、而且在可直观的经验现实中持存。显然,这种实体观是理性心理学家所认可的,因为大前提中的“实体”在先验和经验的两重意义上被采纳。而在A 版中,他只是说“实体是我们判断的绝对主词(主体)”[8](P217),并声称这一实体仅在先验意义上成立。因而,这种实体观就不应归于理性心理学家,毋宁说应归于康德自己。然而在概括前者的实体观时,他毕竟不能越俎代庖,将前者的观点置换为自己的。这可能正是A 版大前提的失误所在。而在B 版中,他很好地修正了这一错误①康德自己的实体观大致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一)一个作为逻辑主词的实体范畴,(二)该范畴与感性直观杂多结合所形成的现象化实体(物)。所以,在我们看来,康德在A 版中似乎没有十分清晰地对理性心理学的实体观与他自己的实体观进行区分,而在B版中,他在这一点上做得更为成功。。随后,上述推理的小前提和A版中的相比在论述上做了简化,但意思实际上是一致的。也即是说,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自我、灵魂)只能被思考为主词(主体),不能用作谓词。B 版中真正与A 版有差别的,是对这个小前提的解释。康德在此强调,小前提中的“思维着的存在者”只是相关于思维的统一性才作为主词,却不同时在可直观的经验现实中成为主体。换言之,这里对“思维着的存在者”的规定是在先验意义上的,不再是在A 版所称的经验意义上。这一规定的颠倒是合理的。如前所述,当他在A 版的小前提中将“思维着的存在者”定为在经验意义上成立时,这同样只是他自己看待该存在者的方式。该方式与理性心理学对它原初的先验设定是正相反对的。而在B 版中,和对大前提的处理相契合,他在小前提中就如其所是地表达了理性心理学的观点,没有在其中混入他自己的观点。这样,在B版的这个三段论中,大小前提都维持了理性心理学家的基本观点。
然而,问题在于:理性心理学家真的是以康德描述的此种方式推出灵魂实体性的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因为在该推理中,他对理性心理学观点的上述归纳是不当的。首先,在大前提中,理性心理学家绝非只在先验意义上才将实体视作绝对主词(主体)。毋宁说,在他们的眼中,实体既是谓词所述谓的“逻辑主词”,更是偶性所依存的“实存主体”。换言之,实体的先验意义可以直接转换为经验意义。因此,对他们而言,实体的思想性与现实性是须臾不可分的。其次,在小前提中,当他们将灵魂(自我)视作我的一切判断的绝对主词(主体)时,这反倒是在先验意义上说的。这一点恰好是康德自己总结的。在他看来,理性心理学就是一门“纯粹理性关于我们的思维着的存在者之本性的科学”[4](P215)。因此,它的惟一文本正是作为思维先验主词的逻辑自我。但在A 版对第一个谬误推理的批判中,他反倒裁定,理性心理学在经验意义上将自我(灵魂)规定为绝对主词(主体)。无疑,这两种说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或者可以说,康德没有很好地澄清,理性心理学如何从自我的先验设定滑落到自我的经验性理解。总之,在A 版“谬误推理”中,他将“实体”先验化和“自我”经验化的解读,似乎并不符合理性心理学对两者的原初设定。在此意义上,理性心理学家完全可以将他随后的反驳斥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他在曲解他们的基础上,再对之进行了攻击。所以,他对第一个推理“无结果性”的洞见,于反驳灵魂实体性诚然有一定的效力。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对该推理的解读既不合乎理性心理学的源始教条,又与他前述对理性心理学的规定有抵牾之处。因而在整体上,A 版对灵魂实体性谬误推理的界定是有一定缺憾的。
当然,即便我们能够这般为康德辩护,他对第一个谬误推理的分析依然存在着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也即是说,尽管康德将灵魂实体性限定在无结果的理念性之中,但该推理的“无结果性”毕竟不同于推理本身的“无效性”。因为他所意指的“无效性”是指:大前提在先验的意义上使用实体范畴,而小前提和结论在经验的意义上使用归摄于该范畴的灵魂概念①康德没有在对灵魂实体性谬误推理的分析中单独说明,其中存在着大前提的先验运用与小前提的经验运用的混淆。但他的确在随后宣称:在四个谬误推理中,“大前提就范畴的条件而言对范畴做了先验的应用,而小前提和结论则就被统摄在这一条件下的灵魂而言对同一范畴做了一种经验性的应用。”(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A].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C].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50.)据此,阿利森、克琪尔和克莱默都认为,在灵魂实体性谬误推理的大小前提中,这一情况同样是成立的。(Cf.Henry E.Allison.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337.Patricia Kirtcher.Kant’s Transcendental Psycholog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84.Heiner Klemme,Kants Philosophie des Subjekts:Systematische und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en zum Verhaltnis von Selbstbewusstsein und Selbsterkenntnis[M].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96:314.)。这就使得,理性心理学家将大前提中先验意义上的一般实体冒充为结论中经验意义上的灵魂实体。这样,灵魂实体从中获得了一种骗取来的现实性。
战争年代早已远去,和平时期的军队没有经历过战场,没有经受过战火洗礼的军队,很难在突然发生的战争中发挥应有的实力。而全息投影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利用全息投影模拟战场环境,为军事行动提供高空间感的仿真环境支持。这在陆军方面或许作用不是非常显著,但是在海空军中用来模拟飞机飞行,舰队行驶,不仅训练了参战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还节省了使用真实装备进行演练的经费,减少了设备的损耗。
不过,阿利森站在为康德辩护的立场上指出,该推论中“绝对主词(主体)”这个中项确实存在含混之处。因此,该推论的“无效性”是毋庸置疑的。他认为:由于大前提仅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的实体范畴,因此该推论的问题必然出现在小前提之中。小前提将作为一切判断的绝对主词(主体)的“我”,归摄在大前提的实体范畴之下。但在其中,绝对主词(主体)两种含义——所述谓的逻辑主词与客体性的实存主体——却被巧妙地混同了。换言之,这两层含义在大前提的实体范畴中都被采纳了,而在小前提中,仅有第一层逻辑主词的含义运用到“我思”之上。但在结论中,“我思”的逻辑主词之义却被暗中替换为实存性的思维主体之义了[3](P336)。更进一步说,正是在小前提中,“作为思维的绝对主词的我思”被塞进了“思想所依存于的现实自我”这层含义。这一操作是使得推理发生谬误的真正原因。由此,灵魂的现实持存就被偷运进结论中了。
这样看来,虽然康德在A 版中认定,理性心理学关于灵魂实体性的三段论推理本身存在着谬误,但他的解释更多指向理性心理学对此推理的不当理解。阿利森(Henry E.Allison)指出:“在他对第一个谬误推理的批判性注释中,康德集中关注的是推论的无结果性,而非无效性。”[3](P335)这一论述是合理的。因为所谓的“无结果性”是指:当我们最后在三段论中得出,灵魂在“理念中”表示一个实体,该推理实际上是无结果的,没有达到理性心理学所预想的“现实效果”,虽然该推理从形式上来说是正确的。而康德在此强调的正是:我们可以接纳灵魂的实体性,但必须在理念或纯粹思维的层面上,不能在实在性的层面上,例如不能想当然地从灵魂的实体性中引申出灵魂不死。因此,康德区分了灵魂的两种实体性:“纯然概念式的”与“现实的”。不过在阿默里克斯看来,这一区分是误导性的,因为倘若一个实体不能在现实中持存,那么它在纯然概念中是毫无意义的[6](PP66-67)。他的上述观点必须辩证地加以看待:首先,他的判断有一定道理。因为在此,康德的确没有对纯然概念的灵魂实体作出清晰说明。但同时,这一判断又显得过于激进。因为从批判哲学内部来看,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一纯然概念意义上的实体正是实体范畴,而后者在批判哲学中有其先验意义,尽管它只具有单纯思维的机能。
然而,即便我们认可阿利森的上述辩护,但这依旧无法改变如下一点:该推理对大前提的“先验界定”与对小前提的“经验界定”,似乎不符合理性心理学的基本前提。这样,虽然康德所持的核心观点——理性心理学将思维自我的持存混同于现实自我的持存——是合理的,但他在注解这个推理时的欠缺之处仍然是很明显的。克琪尔就评论道:“到目前为止,对于我们为何从被给予的前提那里得出那个结论,我们只有一个令人困惑的表述,也即是说,因为我们没有认识或理解那个含糊的术语。为何任何人(每个人)要接受这些前提呢?”[7](P185)在她看来,康德批判理性心理学家的焦点在于,他们犯了“中词含混”的错误。但这一点并不十分有用,因为他没有清晰地说明,上述先验-经验的混淆为何产生。所以,倘若他未能很好地解释谬误推理的来源,那么即使这些推理真的犯有“中词含混”的错误,这也会使它们被指为他自己的思想游戏。由此,它们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力就大打折扣了。
现实生活中,每个大学生身上都具有很多才艺或技能,但是在平常生活中他们不愿意去展示,或者没有合适的机会展示。有的大学生可能是由于性格的原因,不敢直接面对其他人来表达真实的自己;有的可能是害怕自己表现欲太强,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二、B版三段论推理的无效性
通过同时代学者的批评与他自己的反省,康德意识到了A 版对灵魂实体性的分析存在的不足。克莱默指出,康德之所以改变进入理性心理学的方式,是由于理性心理学家们反驳说,A 版将灵魂称作实体(等等),使得我们已经有一只脚站在本体世界了[9](P362)。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何B版对“谬误推理”一章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压缩。并且,A 版对灵魂实体性的理念性认同也一并被抛弃了。在其中得到详细讨论的,只剩下这个新的关于灵魂实体性的谬误推理,其他的都被简化了。它被表述如下:“凡是只能被思考为主词的东西也只仅仅作为主体实存,因而也就是实体。如今,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仅仅作为一个这样的存在者来看,只能被思考为主词。因此,它也仅仅作为一个这样的存在者,亦即作为实体而实存。”[8](P264)在他看来,在大前提中所谈到的实体,是从思维和直观的双重关系中加以规定的。而在小前提中谈到的“思维着的存在者”,却只相关于思维层面的统一性,因而并不在直观的关系中被视作主体。所以,这一结论是通过一种言说式的诡辩而得到的[8](P264)。
胎儿肢体畸形在产前诊断时,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从而导致检查结果不理想[2]。通常上肢肢芽在受精后6d开始发生,而下肢肢芽则延迟2~3d发生,因此目前通常在妊娠8周左右对胎儿的肢芽发育情况进行检查,在妊娠11~12周时对胎儿手指、关节等进行检查,故而目前有研究指出,妊娠13~14周时是胎儿肢体畸形筛查诊断的最佳时期[3]。本次研究选取孕妇均超过13周,适宜开展胎儿肢体畸形筛查。
政府设置产业园区对当地的工业企业给予政策扶持对当地的经济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园区可以实现劳动力、资本和原料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流动,而土地、基础设施、交通等资源的共享可以产生集聚效应,为园区内的各工业企业的发展带来助力。政府的各项优惠以及扶持政策给中小企业以及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帮助,优化企业的融资环境,优化金融环境,使得小微企业得以存续。工业园区的发展使得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得以改善,进一步降低了生产的相对成本,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园区内工业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不过,理性心理学的实体概念归根到底是一种幻相。因为单纯依靠该概念,从“逻辑主词”到“实存主体”的直接过渡也是不成立的。易言之,如果一个号称实体的某物只是作为“逻辑主词”而成立,那么这并不代表它直接晋升为“实存主体”了。相反,它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个持久的直观才能成为真正的实体,也即在现实中持存常驻。现在,正如阿默里克斯所指出的:“尽管对于康德来说持存性(permanence)给予了‘实体’一种经验的和在那种意义上现实的定义,但它定义的不是真正实体性的东西,而仅仅是物质性的和现象化的东西。”[6](P67)易言之,由于康德所描绘的实体是现象化和时间性的,与主观条件相关,因而远离了理性心理学所预设其中的客观性持存。他承认,现象中的实体作为一切时间现象的基底是存在的。但他只是从时间之物的流变中,发现了时间统一性的必要性,因而将实体概念预设为该统一性的图型(Schema)。在此意义上,该概念只是相关于时间的持存之物,并不指涉超时间的自在之物。理性心理学家的失误即在于,认为实体的自存性可以脱开时间的主观条件而成立。
同样地,自我(灵魂)若想成为实体,就不仅要把自己确立为一切思维的逻辑中项,还要将自己证明为在时间中持存的自我。显然,它需要一个持存的内直观,才能达成这一目的。“但现在我们在内直观中根本没有任何持久的东西,因为自我只是我的思维的意识;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思维上面,我们也就缺乏把实体……应用于作为思维着的存在者的自身的必要条件”[8](P265)。因此,这正是我们无法证明自我(灵魂)实体性的根本原因。因为内感官以时间为先天直观形式,而在时间中只有作为基底的不可见实体,却绝对不会有任何可见的持存之物。相反,“一切皆流,无物常驻”。这样,内感官所呈现的自我必然只是休谟意义的“知觉流”。在其中,根本不会有任何持存性的自我。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康德眼中的内感官,恰好就是指这种随时可变的、不断流动着的经验性自我意识[4](P75)。
因此,内感官作为经验性的自我意识,区别于康德所说的先验自我意识或先验统觉。这两层自我意识,是理解康德自我(灵魂)观的基本架构。由这两层区分,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为何自我(灵魂)无法被证明为持存常驻。如前所述,先验自我意识首先意指着一个持存常驻的逻辑自我。它是形式化的“我思”表象,是一个伴随着一切概念的空洞意识。而对灵魂实体性谬误推理的批判从逻辑的角度证明了:我们无权从形式化的“我思”表象,推论出质料化的“我思”实体。与之相对,所谓经验性的自我意识可以被称为经验性的“我思”,更确切地说,“我在思维时实存”[8](P274)。它之所以能够出现,正由于在我内部经验性的直观杂多充实了形式化的“我思”表象。但是,这种“充实”不可能在时间中无限延伸下去,因为“我们只拥有灵魂一直到死时的经验,我无从知道上述经验是否会在死后留存下来”[11](P271)。因此,一个经验性的自我意识所能觉察到的,就是它的此世。对它而言,此世之外就属不可知的超验之域了。然而,一个质料化的“我思”实体所要求的,正是该实体超出此世的不生不灭。从经验现实的角度看,这一要求必然是僭越的。所以在经验中,一个质料化的“我思”实体没有任何成立的理由。当然,上述论证在休谟那里就已被揭示出来了①具体参见休谟《人性论》的第四章“论怀疑主义哲学体系和其他哲学体系”的第五节“论灵魂的非物质性”。。康德接纳了它,并用作反对灵魂实体观的利器。总之,无论从逻辑的抑或经验的角度,一个质料化的“我思”实体,都必须被判为无根据的存在者。这样,理性心理学所笃信的灵魂实体性,彻底地陷于失败了。
三、先验我思的实存
的确,康德在B 版中更为清晰地否证了自我(灵魂)的实体性。相比于A 版注目于三段论推理的“无结果性”,B版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推理的“无效性”。总的来看,B版对于灵魂实体性的批判远比A 版要成功。但B版对自我意识或“我思”的表述,却终结于先验自我实存的可能性。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一般而言,只有经验性的自我意识才能在现实中实存。这种实存是我们能自明感知到的内知觉,因而是一种稀松平常的内在体验。从这种熟知的体验中,我们在理论上否认了在它之外灵魂的持存。而在康德看来,与这种通常可体认的实存方式不同,先验自我意识完全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实存。这堪称他的自我(灵魂)学说中的“未解之谜”②考察“实存”一词的在康德哲学中的用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先验自我意识之实存的特殊性。最新的《康德词典》对“实存”概念的解释如下:“实存并非任何一物的谓词或规定。实存是对物的绝对设定。当我们声称某物实存时,我们并未给出对于某物的内容型描述,而我们只是说,存在着与我们的概念相应的某物。实存只能通过知觉综合性地被认识。”(Marcus Willaschek,Jürgen Stolzenberg,Georg Mohr,Stefano Bacin(ed.),Kant-Lexion(Band1)[M],Berlin/Boston: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5:587.)由此可知,“实存”不是述谓判断的谓词或规定。换言之,“实存”不能在谓词的位置上,从作为主词的某物中以分析性的方式得出。这正是康德在对上帝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中所立足于的著名论断——“存在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dikat.)”。因此,在康德看来,我们不能通过对某物概念的纯然分析,就将该物的实存作为它的谓词抽引出来,比如我们不能经由上帝的概念就直接从中导出上帝的实存(安瑟论关于上帝的本体论证明就是这一操作的典型代表)。由之,实存必须以综合判断的形式通过知觉(Wahrnehmung)得到界定。换言之,如果我们说某物实存了,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这个物的概念之外,相应的直观被给予了。只有通过概念与归摄在它之下的直观相结合,综合判断才能够出现,一物才能真正实存。正是在此意义上,经验性自我意识(内感官)的实存在现实中是显明的。而当我们把自己作为主体在现象层面上来认识时,那么所发生的是:先验自我意识将我们的内感官所接受的杂多表象综合统一起来,由此一个现象中的经验性自我才呈现出来。因此,我作为一个思维着的主体,并不能够通过这个“我”的概念直接证实我的实存,而必须经由我在内感官中对我自己的知觉,来认识我的实存。然而,这一实存却不再是先验自我意识的实存,而是经验自我意识的。如果按照康德对“实存”一词的上述用法,先验自我意识恰好是不能使用它的。这样,先验自我意识之实存才成其为康德哲学中的“未解之谜”。。
他在B版“范畴的先验演绎”中指出,先验自我意识“既不是像我向自己显现的那样,也不是自在地自身所是的那样,而仅仅是‘我在’(ich bin)”[8](P117)。换言之,先验自我意识所表达的“我在”,既非现象之我,亦非自在之我。现在,现象之我就是经验性的“我思”,而自在之我则是实体化的“我思”①“我”自在地作为实体,是理性心理学所寻求的终极目标。对此,康德归纳道:“如果有可能先天地证明:一切思维的存在者都自在地是单纯的实体……那么,这将是反对我们的全部批判的重大的、乃至惟一的绊脚石。因为以这种方式我们毕竟就已经跨出了超越感官世界的一步,踏入了本体的领域……”([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A]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C]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63.)。而根据前述的分析,先验自我意识作为形式化的“我思”表象,的确与这两者不同。在康德看来,先验的“我思”只有通过行动(Actus)才能规定我的存在,但我存在的方式仍未被给予[8](P118)。问题在于:“我思”作为行动,何以就直接规定了我的存在呢?虽然他没有明确给出该问题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尝试从他的先验统觉学说中寻求解答。一般而言,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以如下方式得到表述:“我思”表象“必须能伴随所有其他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8](P103)。由此,它才以“我思某物”的形式,将一切表象统摄在先验自我意识的统一性之下。这种“我思”一方面体现为一种先天固定的形式化表象,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一种自发性的行动[12](P391)。其中,作为形式化表象的“我思”是我们所熟知的,但它如何成为自发性行动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说明。如上所述,“我思”表象作为“我”之意识的普遍形式,对我意识中呈现的任何表象都具有统摄作用,而这一作用体现在它对其他表象的主动伴随中。但“我思”表象对其他表象的伴随活动并非外在的,相反,它必须以“我思某物”的形式完全渗入那些表象之中。由此,“我思”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表象,而是一个表达了我之统一性行动的命题(Satz)。
在康德看来,“先验我思”的行动对“我在”或“我实存”的规定,反倒是经验性的[8](P270-271)。无疑,这种说法是让人困惑的。因为这似乎使得“先验我思”与“经验性我思”对“我实存”的规定完全混同了。不过在他的眼中,这两者是可以分开的:“先验的我思”表达的,只是某种不确定的经验性直观,仅意味着在一般思维(Denkenüberhaupt)上被给予的“我实存”。这一实存既非现象意味上的,亦非物自体意义上的。与之相对,经验性的“我思”却表达了一种确定的、与思维之外的客体相关的经验性直观,进而意指着在内知觉中可感知的“我实存”[8](P270-271)。就此而言,即便两种“我思”都被称为经验性命题,但其内涵是不一样的。两者的差别只是在于,所基于的经验性直观是否是确定的。经验的直观一旦确定,落入思维之外的客体之中,那么“经验性我思”及其意指的“我实存”也一并确定了。而当这一直观是不确定的,因而“先验我思”及其表征的“我实存”尚属于一般思维,仍是未被规定的。进言之,“先验我思”“就意味着意识到自己实存着,尽管这并不带来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之本性的任何进一步知识”[3](P353)。
由此,一种围绕着“先验我思”的蹊跷倒转发生了。可以看到,康德对灵魂实体性的批判,似乎将“先验我思”定格在了空洞的逻辑主词之中,彻底消解了它在经验中成为实存主体的可能性,因为它的逻辑主词功能不能直接导出作为客体的实存主体[8](P270-271)。但现在,康德对于灵魂实体性的最终陈述,却将它拉回到确凿无疑的实存主体地位。他承认,在“我思”中“已经有属于感性的感觉作为这个实存命题的基础”[8](P270-271)。质言之,“先验我思”虽然是纯粹知性的最高象征,却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在事实上实存着了。然而在批判哲学中,知性与感性作为知识的两大来源是截然二分的,两者只有以时间图型为中介才发生连接。现在,康德将先验统觉的“我思”,未加中介地放置在感性经验的层面上,这的确让人诧异。他的理由是:只要“我思”作为行动发生了,那么这种行动必然关涉经验性的表象。也正是“我思”所具的行动特性,使得“我”这个纯然智性的表象在“思”中变成了经验性的“我实存”[8](P270-271,注2)。这样看来,康德灵魂(自我)学说内部的那个“未解之谜”,似乎可以按如下方式破解:静态地看,“我思”是持存不变的逻辑主词,即所谓“我=我”的自同一;动态地看,“我思”通过“思及某物”的伴随行动变成了实存主体,尽管我如何(wie)实存仍是未知的。
庭中的花再未开过,也可能是坛子少了的缘故。老爷爷把剩下的几坛花放在一旁的小架子上,那几坛花再未开过,没过几天那几坛花也不见了。行人来来往往地走着,阳台上还有一个身影,弓着背坐在阳台上,那景象似乎和以前一样,却又有些不一样——安静了,花也没了。
确定的然而,这种我应如何实存的未定性,不应视作康德“我思”观念的局限,反而是其开放性的明证。因为即便内感官所提供的确定性的经验性直观,在现象上规定了我的实存,但这只是规定“我实存”的一种方式,别种方式于我而言仍是可能的。而按照康德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别种方式”将只能是物自体的方式,亦即自我自身(das Selbst an sich)的方式。不过,自我自身的实存,当然不会在确定性的经验性直观中呈现。事实上,“我通过首次向我启示出道德法则的意识的那种值得惊叹的能力……将会拥有一条规定我的实存的、本身是纯粹智性的原则”[8](P270-271,注2)。所以,人不仅拥有“现象化自我”的经验性实存,而且还以“自我自身”的方式在道德法则的约束下实存。这两种实存方式的基点,在于上述“先验我思”所确证的“我实存”。
就此而言,康德对灵魂实体性的批判,似乎将“先验我思”所具的逻辑主词与实存主体的意味拆解开了,但最后又建设性地将两者统合在“先验我思”之中。如果说“我思”的逻辑主词地位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它作为实存主体的独特意味就鲜为人知了。海德格尔就批判说,康德将“我”把捉为逻辑主词(主体)是不当的,因为主体描述了“一种总已现成的事物的自一性与持存性”[13](P364)。他的这一评价当然以其“存在论差异”作为思想背景,但很明显,他也忽略了暗含在“先验我思”中的实存主体之义。事实上,康德对“先验我思”实存性的阐述,已经打开了一扇通向非认知的与非现成的“实存之我”的大门。不过,他想通达的,并非海德格尔阐释的“我作为‘我存在在一世界中’向来所是者”,而是“他对……《实践理性批判》灵魂不死公设进行涵括的意向”[13](P366)。换言之,尽管他对灵魂实体性的批判摧毁了唯理论者对灵魂不死的经典论证,但他只是反对他们的论证方式本身,他本人对灵魂不死依旧抱有虔诚的信仰。现在,灵魂永恒持存的可能性,藉由“先验我思”确证的“我实存”得到了保留。而以休漠为代表的经验论者对灵魂不死的任何否证,都将流于破产。因为这种可能性是由“先验我思”保存的,经验性条件并不能使之受到丝毫影响。但康德与唯理论的差别在于,他并未通过“先验我思”直接证实灵魂不死,而只是“暗示认知者可以将他们自己理解为独立于他们所有特殊的直观形式而作为思者实存”[14](P196)。因此,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思想性实存是悬拟的(problematisch),在经验性直观塑造的世界中无法得到证明。这样,他对唯理论灵魂观的批驳依然是有效的,因为灵魂(自我)不可以超验的方式,只能以先验的方式在经验中持存。也即是说,灵魂(自我)以纯思的方式构成经验可能性的基础。虽然它自身确定无疑地实存着,却不可能为我们直观到。毋宁说,如其所是的灵魂(自我)本身永远也不可知。由此,无论是灵魂不死的理性证明抑或灵魂必死的经验证明必须被判为无效。因为两者都在理性的界限之外,作出了某种可知的断言。
但这两种对立意见的“同时倒台”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对“灵魂不死”存而不论。相反,正如赫费所说的那样,“在理论理性失灵之处,纯粹实践理性及其上帝与灵魂不死的公设开始发挥作用”[10](P234)。我们理应“把我们的自我认识从无益浮夸的思辨转用到有益的实践运用上去”[8](P228)。所以,康德对灵魂实体性的批判,一方面终结了关于灵魂(自我)的诸种知识性论辩,另一方面也为灵魂(自我)的实践效应夯实了地基。如果说“先验我思”的逻辑主词功能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那么它的实存主体意味则是完成第二个目标的先导。因为灵魂(自我)本身毕竟实存着,尽管不可以“知”的方式,却能够以“行”与“信”的方式得到把握。而这正是灵魂(自我)在道德法则之下的实存。由之,对灵魂(自我)的讨论从思辨性的知识进入了实践性的信仰,一个广阔的道德世界籍此呈现了。世人皆知自由乃批判哲学的“拱顶石”,是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转换的“节拍器”。然而绝少有人注意到,在灵魂(自我)概念内部同样暗含着两者变换的关键环节。事实上,在“我思”作为行动的实存中,这一转变就已开始了,因为一个行动着的自我的雏形已经具备了。但更重要的也许是,我思的行动性实存为追随康德的观念论者展开了一幅自我意识的伟大图景[2](P425)。由此,德国观念论走上了发展的康庄大道,哲学的一个黄金时代诞生了。
(本文初稿曾于2017年6月24日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与演进——纪念苗力田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得到先刚、余玥、刘作、李季璇、王庆节等诸位师友同仁的批评和建议。由此,笔者对文章进行了针对性的修订。但限于时间、精力与水平,文章也许未能一一回应他们的问题。这里,笔者对他们的帮助深致谢忱)
参考文献:
[1][法]笛卡尔.谈谈方法[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Rolf-Peter Horstmann.Kants Paralogismen[J].Kant-Studien,Nr.4,1993,(411).
[3]Henry E.Allison.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A].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C].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Metaphysik[M].Halle im Magdeburgischen:Carl Herrmann Hemmerde,1766.
[6]Karl Ameriks.Kant’s Theory of Mind-An Analysis of the Paralogisms of Pure Reas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7]Patricia Kirtcher.Kant’s Transcendental Psychol-og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8][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A].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C].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Heiner Klemme.Kants Philosophie des Subjekts:Systematische und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en zum Verhaltnis von Selbstbewusstsein und Selbsterkenntnis[M].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96.
[10][德]奥特弗里德·赫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M].郭大为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1]Immanuel Kant.Lectures on metaphysics[M].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Karl Ameriks and Steve Narag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12]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14]Patricia Kirtcher.Kant’s Thinke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I Think:Logical Subject or Existential Subject——TwoApproachesofKantianCritique
oftheSubstantialityoftheSoulandTheirConsequences
JU Jun
(SchoolofGovernment,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46,China)
Abstract:Kant showed two approaches to critize the substantliality of the soul:The A-Edition focused on the unfruitfulness of the paralogism of the substantliality of the soul,while B-Edition emphasized the invalidity of this paralogism.The transcendental definition of the substance and the empirical definition of the soul in the A-Editon retained the ideality of the substance of the soul and didn’t fit the rational psychology.The B-Edition regarded the substance as the unity of transcendental and empirical elements,determined “the transcendental I think” as the logical subject,but not as the existential subject in the name of the substance.“I think” was interpreted as “I exist” given in an undetermined empirical intuition.Without the meaning of the substance,“I think” was still the unity of logical and existential subject.Regarded as the existential subject,it was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henomenal self and the self as such could be made.Furthermore,it was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ostulate of the immortality.
Key words:soul;substance;rational psychology;subject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9)03-0056-09
收稿日期:2017-08-08
作者简介:居俊,男,哲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春梅
标签:康德论文; 主词论文; 实体论文; 灵魂论文; 实体性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齐鲁学刊》2019年第3期论文;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