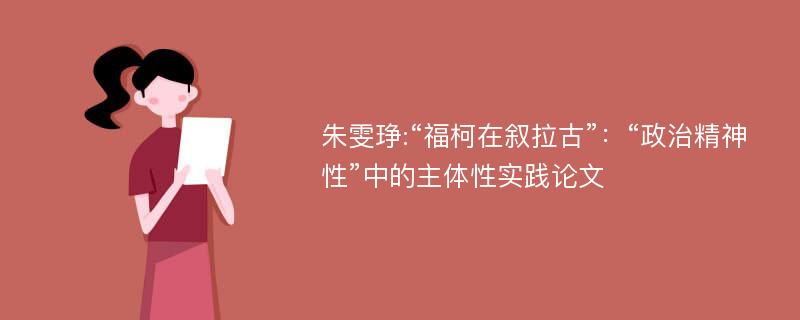
摘 要:福柯对伊朗革命持支持立场而被人称为他的“叙拉古问题”。他为伊朗革命中的“政治精神性”所着迷,然而遭到了知识界众多批评和指责。本文尝试理解“政治精神性”,并对福柯所持的赞许态度做出明证。通过分析福柯1978年以及之后的思想著作,文章试图阐明福柯支持“政治精神性”的两种层面,它体现出人的集体意志和超越世俗性的力量,在福柯眼中它们就是反抗西方理性政治的有力武器。加上福柯对多元文化的偏好,造就了他对伊朗革命的支持态度。 “政治精神性”同时联系起了福柯思想中后期从政治到主体的两大元素,他从政治领域的“生命政治”到伦理领域的“自我技术”,都在探究个人如何转变其自身主体性,并沿着主体性实践开展他的现代性研究。福柯并非完全正确,但他借伊朗革命所体现的政治精神性,为公共政治领域讨论提供了一种主体性实践视角的新立场。
关键词:福柯 伊朗 政治精神性 生命政治 主体性
一、导言:知识分子的“叙拉古问题”
本文试图从福柯生命经历中的一个“叙拉古问题”来探索他关于政治反抗和主体性思想之间的关系。“叙拉古问题”喻示着知识分子干预政治而遭遇“滑铁卢”的困境,它由来于柏拉图“三进叙拉古”的典故。第一次,年近40岁的柏拉图拜访叙拉古的老狄奥尼索斯,冒着生命危险向这位僭主进言。 20年以后,老狄奥尼索斯去世,他的儿子小狄奥尼索斯继位,年逾60的柏拉图由好友狄翁的请求,携弟子二进叙拉古,教导年轻君主。小狄奥尼索斯尽管一开始显得愿意学习,但却缺乏将哲学运用于自己统治活动的决断,第二次叙拉古之行不欢而散。公元前363年,柏拉图应小狄奥尼索斯之邀,第三次进叙拉古,而此时的小狄奥尼索斯显然已经成了完全的僭主,这一次柏拉图遭到扣留和驱逐。总之,柏拉图试图影响僭主的期望也最终落空。
马克·里拉曾借用过这则典故:当1934年海德格尔担任已被纳粹控制的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时,一位德国同事讥讽道:“君从叙拉古来?”(Lilla, 2016: 279)从此“叙拉古问题”对知识分子无异于一个警示:当哲人或知识分子干预政治,他们是否会对现实状况缺乏必要判断?海德格尔事件“只是二十世纪诸多有关爱智慧的哲学,如何沦落为‘爱僭主’的鲜活记忆中最具戏剧性的那个”(Lilla, 2016: 282)。里拉反讽式地问出如下问题:西方传统的政治思想里,知识分子似乎都容易受到诱惑而错误干预政治;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又该如何避免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陷入相似困境呢?
里拉同样也批评过福柯在1968年政治运动中的左派态度,但他却忽略了福柯最广为人知、更贴合 “叙拉古问题”一说的政治参与,那就是福柯对伊朗革命的支持。1978年时值伊朗革命如火如荼之际,福柯于10月和11月两度赶赴德黑兰进行采访,报导当时伊朗革命的时局,并与后来霍梅尼(Khomeini)政权下的伊朗总理巴扎尔冈(Mehdi Bazargan)进行会谈。福柯在两次伊朗之行期间及之后分别写了11篇新闻报道(包括对批评的回应)和一次访谈,来阐述他自己支持伊朗革命的观点。福柯将在伊朗发生的政治革命看作是“政治生活中的精神性维度(dimension spirituelle)”的表现,而伊朗运动中所出现的集体宗教精神性也使福柯感到“深受触动”,甚至“为之感到深刻着迷”(Foucault, 2005a: 207,208 2005c:256)。福柯对伊朗革命如此痴迷的原因就在于他所说的“政治精神性”(political spirituality)1。在他看来,伊朗人民 “不惜为之付出生命去追寻的可能性(政治精神性)”自文艺复兴后就被西方所彻底忽略了,而欧洲、特别是以政治中的知性主义所著称的法国应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Foucault, 2005a: 209)。
1.本文中所用概念“政治精神性”,法语原文为spiritualité politique,英文译为political spirituality。请注意,对于法语原词及英语译文,汉语可以有多种译法,已见的译法有澎湃新闻社的苏子滢以及阿法利和安德森的中译者徐亮迪译为“灵性政治”等。——编者注
当然,福柯对伊朗革命的支持态度招来了知识界几乎一致的反对声。报道一经发出,署名为“Atoussa H.”的伊朗女权主义者就对福柯进行了猛烈抨击;历史学者罗丁森(Maxime Rodinson)等人也批判福柯作为“一名聪明且富有洞见力的思想家,却拜倒在这种腐朽且粗俗的精神性概念下”(Rodinson, 1993)。学者们对福柯的批评主要围绕三点展开。第一是福柯为伊朗写的新闻报道被认为缺乏对真实局势的整全看法(Leezenberg, 1999:73),利兹伯格(Leezenberg)甚至直接评价福柯在分析伊朗的政治局势时是“断裂的”,没能将革命的运动局面结合到他曾经的微观权力分析框架之内,甚至和他之前所持有的权力的普遍性伦理所相悖。第二则是女权主义者反感福柯对霍梅尼政权的“无条件支持”,因为霍梅尼基于伊斯兰法规的统治会使伊朗地区女性失去更多自由,而对霍梅尼的不满自然也扩散到福柯身上。2第三点则是围绕“政治精神性”的广泛批判。譬如罗丁森(Rodinson,1993)批评福柯不仅不了解伊朗,而且认为福柯将霍梅尼政权视为“政治意志”的幻想不切实际,因为所有以政治精神性为起始的政权都会“渐渐臣服于其俗世典范,它们开始还是以精神性或理念为方向,而后则转到权力斗争的永恒政治法则里”(Rodinson, 1993: 271),后来的批评则指出,福柯把霍梅尼的什叶派政权归纳为“政治精神性”,这一做法限制了什叶派自身的权力意图,错误地估计了霍梅尼的野心,而“政治精神性”只是福柯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自由乌托邦”(Beaulieu, 2010: 814)。在收到各方负面评价后,福柯表示自己无意参与任何论争,在发表完最后一篇有关伊朗的文章“反抗没有用吗?”(Is it Useless to Revolt?)之后,福柯就一直保持沉默,转而继续他的生命政治研究和《性史》后几卷的写作。3
2.基于女性问题视角批评福柯最集中的一本书是Ramanzanoglu (1993)所编的论文集《反抗福柯:对福柯和女性主义间紧张关系的探索》(UpAgainstFoucault:ExplorationsofSomeTensionsBetweenFoucaultandFeminism);更早一些的则有Diamond和Quinby (1988)所编的文集《女性主义与福柯》(FeminismandFoucault)。直观地看来,福柯思想中对反抗权力的内在支持、加上他对疯癫病人、同性恋者、无名者等的“偏爱”等都很容易受到女性主义群体的喜欢,毫无疑问女性主义视角对福柯的批判性态度始于福柯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进而女性主义者们再把批评转移到其他方面,诸如认为福柯所专注的全是“白人男性特权阶级”思想(Taylor, 2013:403)等,但这些批评错误地将思想家的研究先验性地纳入到有预判的价值判断领域,导致评判者无法全面地理解福柯的思想本质。
3.关于伊朗革命福柯前前后后总共写了15篇文章——8篇刊载于意大利报纸《今日晚报》(Corrieredellasera)上的新闻报道、3篇刊载于法国《新观察家》的分析类报道、1篇刊发于法国《晨报》(Le Matin)、1篇刊发于《世界报》(Le Monde)以及2次访谈。根据埃里蓬的传记叙述,福柯自己既不想将他以意大利语形式发表的报道编辑成册,也不希望将它们翻译回法文,因为他认为这些只是“新闻报道,而不是成书文本”(Eribon,1991:289),因此连法国人都少有人完整看过福柯关于此问题的全部文章。 直到 2005 年阿法利与安德森 (Afary and Anderson)在其著作《福柯和伊朗革命》以及Ghamari-Tabrizi编著的《福柯在伊朗》(FoucaultinIran)的附录里将所有文章全部翻译成英文,学界或才得以观其全貌。
1954—2017年,全市9个县(市、区)中,报告病例数最多的为临海(43 686例);其次为温岭(26 643例);报告发病率最高的为天台(107.70/10万),其次为三门(104.63/10万)。
4.相关争论可见阿法利和安德森(Afary and Anderson,2005)以及Ghamari-Tabrizi(2016)对阿法利和安德森的反驳。前者批判福柯支持霍梅尼政权源自对意识形态政权的过分乐观幻想,而后者则质疑前者错误地贬低了福柯及霍梅尼的政治预见性。对伊朗时政做出表态和发声的不仅有福柯,还有法国当时左派团体萨特、波伏娃、萨义德等一群知识分子,其观点各异更能看到他们意想不到的一面,碍于本文主题限制不一一展开。
电力通信网是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的专网。在电力通信网中传送的业务有远动通道、数据采集通道、监视控制通道、继电保护通道等等业务。[1]其中继电保护的信号具有允许传输时间短、通道发送几率低、发送时间不确定等特点,因此对保护通道的传输性能有严格要求。继电保护通道一旦出现异常,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修复,以保障电网运行的稳定。本文将分析电力通信中继电保护通道的两种方式,并为两种方式的继保通道深入探讨故障定位的流程和技巧,为快速处理继保通道故障奠定坚实的基础。
与阿甘本逃离生命政治的设想恰恰相反,泰勒在面对现代政权渗透于个人主体性的境况时主张个人的主动参与。他曾经批评过福柯对权力的阐释,“若没有任何涉及自由的思考,权力就显得毫无意义”(Taylor, 1984:173)。泰勒所说的正是福柯对不同权力制度加以批判并反抗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立场,以至于只是在逃避各种所有可能的权力约束,却没有对如何建立起一个能够实现个人自由的权力制度作出建树。泰勒认为,福柯面对政治时的主题一直围绕着哪些不同的实践会塑造出哪些特定的权力,以至于忽视了思考应该建立哪种可能的、能够实现个人自主启蒙的成型立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当世界上出现了某种和传统理性政治制度所不同的新型力量时,福柯急于探索其内部的发展结构及其对个人所产生的权力影响,却不能判断它对个人的自主实践所产生的影响,究竟是比从前更能宣扬其所希望的多元和自由之人格的塑造,还是使整体境况变得更糟。
文章切入这一“叙拉古问题”的聚焦点有两个:反抗与主体。首先关注伊朗革命中出现的“政治精神性”本身,结合福柯在那段时期(1977-1980年)有关“生命政治”的研究重心,从而试图推论他为伊朗运动中“政治中精神性的维度”所着迷的原因,不是被霍梅尼的“自由乌托邦”式幻想所诱骗而支持僭主统治,而是因福柯在伊朗看到了除传统西方基督教治理以外的另一种宗教性治理的可能,这恰好切合他寻找“生命政治”出路的目的;另外本文还将基于福柯“治理-反治理”的框架,以发现政治精神性不仅启发福柯从现实中寻找反抗治理技术的力量,而使他将政治治理逐渐转化到“治理自我和他人”的主体性实践中去。
其次,另一个焦点就是主体性,虽然福柯的研究范围广泛,从早期的监狱研究、中期考察国家“生命政治”,到后期的“伦理转向”,各种问题看似没有一个连续的核心,但我们可以将“主体性”作为理解福柯中后期思想的关键词。无论是他的治理问题还是伦理问题,甚至是本文所讨论的政治与精神性主体之关系,其本身始终关注个体作为主体,如何反抗从宏观的国家权力到微观的个体政治技术的问题。作为连接政治权力和主体伦理问题之间的桥梁,“政治精神性”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福柯的批判与评述的线索。文章正打算在此路径重点考察这一独特“政治精神性“,它或许只是福柯七八十年代时期诸多重要问题中的一个方面,但从中能窥见他反治理和提倡主体性实践的核心思想。
二、理解“政治精神性”
时值1978年10月,福柯刚从伊朗回来,亲眼目睹了在血腥的“黑色星期五”事件后伊朗局势的混乱,以及伊朗人民坚定推翻沙阿政权的决心。于是,他相当乐观地在《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上发表了“伊朗人梦想什么?”( quoi rêvent les Iraniens?)的文章5,其中他启用“政治精神性”一词,并将伊斯兰宗教影响下的伊朗作为整个欧洲长期缺失的某种精神性典范:
5.这篇报道最早发表于1978年10月16日的《新观察家》,主编为Jean Daniel,他同时也是福柯交往已久的朋友;后来它被收录于福柯文集《言与写》(Foucault, 1994a:688-694)。《新观察家》将福柯标为该报驻伊朗的“特别记者”(参见Afary and Anderson, 2005: 87)。
6.事实上,这并不是福柯第一次使用“政治精神性”一词。在1978年5月和一群法国哲学家就《规训与惩罚》的圆桌讨论上,福柯就提出过“政治精神性”概念,以用以作为现代规训机制的高压理性下的另一种选择(参见Foucault,1994a:30)。
对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来说,他们不惜付出自身生命代价也要追寻的东西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自文艺复兴和基督教的重大危机以来就被我们所彻底遗忘了,那就是一种政治精神性(political spirituality)。我已经可以听到法国人在笑了,但我知道,他们错了。(Foucault, 2005a: 209)6
政治精神性不是福柯整体思想中的关键词,福柯也并未赋予它以明确定义,因此这一概念常遭到误解。阿法利与安德森(Afary and Anderson,2005:99)就觉得政治精神性受福柯从东方社会中政治与伦理相结合的治理方式的启发;甚至,有人认为“政治精神性”只是福柯的时政用词,不应该将其上升到正式的哲学思想高度(Leezenberg,1999:69)。这些看法错误地理解了政治精神性的来源与重要性。因为福柯对伊朗“政治精神性”的发掘,几乎成为他后来从古希腊-罗马传统到基督教思想中寻找治理体系中“精神性”作用以及其与个人实践之关系的开端。
那么,政治精神性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福柯对伊朗政治精神性的着迷,不是因为他喜欢任何现实宗教或信仰中的某些教义,而是来自于他将宗教作为一种和历史现实、社会实在相关的存在所产生的兴趣(Carrette,2013:372)。也就是说,“精神性”7 在福柯意义中可以指称任何一种由宗教实在或非宗教信仰而产生的力量,是某种“主体对某种存在形式和转变的获取,以让主体在自身贯彻这种形式的存在”(Foucault,1994c: 294)。但福柯有意将在伊朗所出现的宗教精神性与基督教权威相区别甚至对立,在指称基督教元素时他会直截了当地用“基督教精神性”(Christian spirituality)或“清修精神性”(monastic spirituality)来替代。此外,政治精神性的表现形式也绝非仅包括出现在伊朗的政教合一式统治,在福柯意义中,日本禅文化也是某种精神性模式,他更是鼓励日本本土出现的反抗权威性运动。8甚至,他还相当期待到中国来看看这里的政治精神性,只可惜,有生之年他未能成行。因此伊斯兰宗教权力中出现的政治精神性发展出霍梅尼的政教合一治理或是一个巧合,又或者可以说,这种既包含某种“俗世权力”,又拥有一种“朝向彼世的力量”(Foucault,2007:154)的精神力,本身极有可能滑入僭主陷阱之中。然而,抛开实际政局,仅去探索政治精神性本质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既身处权力不断扩展和对人进行支配的人类此世社会,同时这种力量还具有超越现世、超越自身限制的可能,这使伊朗事态的发展呈现出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治理形态所完全不同的价值。
7.尽管卡雷特在他相当细致且文献丰富的文章里记载,福柯从60年代的“文学时期”受巴塔耶和先锋派文学的影响就谈起了非神学上的“精神性”,譬如将性经验和宗教起源相联系(Carrette, 2013:56-7;2000:45-7),但笔者认为这时期的“精神性”概念和后来经过伊朗革命之后福柯所采用的精神性概念是全然不同的。原因之一是受文学艺术影响的福柯所关注的问题和后来“政治-伦理”时期的福柯有非常大的差异;其二则是时间上断裂,上世纪60年代福柯对“精神性”的提及仅有几处访谈的只字片语,但经由伊朗的“政治精神性”后,福柯在接下来几年的法兰西学院课程和《性史》后三卷里都连续性地出现了有关精神性的叙述。
8.福柯在写作《性史》第四卷《肉体的自白》时曾对朋友说,“我要是不是个无神论者,我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修士”(Macey,2004:130);而他1978年访问日本时则写了数篇日本禅宗文化的文章,还痴迷于穿着浴袍和日本武士道精神(Veyne, 2010:139)。
9.该文法语标题原文为L’espritd’unmondesansesprit。如我们在注1中提及有将spiritualité译为灵(性)一样,澎湃新闻社将该标题中译为《伊朗:无灵世界之灵》。——编者注
(一)集体意志的力量
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福柯对政治精神性的相关叙述,以从中发现两条支撑福柯支持政治精神性的“合法性”线索。这两条线索皆来自于1979年福柯与布兰奇特(Pierre Blanchet)和布希埃(Clare Brière)关于伊朗的讨论“伊朗:无精神世界之精神”(Iran: the Spirit of a World without Spirit)9。第一条线索,是政治精神性所带来的集体意志力量,这种集体意志将会导致人在主体性方面的巨大转变。福柯认为,在历史上很少有某个地区的人能拥有这种绝对的集体意志,然而,在伊朗它出现了:
伊朗的民族敏感性相当旺盛,他们拒绝对外国人表示服从,厌恶他们劫掠国家资源,反对依附国外政策和美国干涉,这些声音在沙阿被看作西方傀儡存在时随处可见。但我看来,民族感受只是一种更激烈拒斥力量里其中一种元素:人民不仅反对外国人,还反对一切这个国家经年累月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命运的一切……伊朗打动我的地方在于,不同元素之间没有斗争,而只有一种对抗,那就是在整个人民和用枪炮警察威胁人民的国家之间的对抗,这种整齐的斗争赋予了它如此的美丽,与此同时还有如此的沉重。(Foucault,1988a:215-216)
在福柯看来,当一个地区所有人都在宗教思想下表现出相同的政治和司法行动、共同废除国家主权时,集体意志就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同时还存在着特别的美感。福柯的批判者认为,福柯看到了一个“完全整齐划一的社会”,却没想到以宗教情绪为基础的社会体系会产生出“斯大林主义或法西斯极权主义”政权(Afary and Anderson,2005:98,131)。然而,这种看法错误地估计了福柯的权力观。正如福柯屡次对权力和反抗权力机制所进行的研究那样,他历来反感“一种权力压倒另一种权力”的支配过程,“强加于人身上的权力总是危险的”(Foucault,1994b:452);他期待看到在某种现有的、由理性建筑起来的“铁的牢笼”秩序下,能有某种力量出现来加以反抗,使权力机构产生断裂。“起义属于历史,但在特定情况下,它们从历史中逃离。某个个体、一群人、一种少数群体或一整个民族说,‘我将不再服从’并赌上性命来面对他们认为不正义的权威时,那种推动在我看来是不可消灭的。”(Foucault,1994b:449)福柯为之报以好奇和着迷的,不是集体意志驱动下产生压倒权威权力的暴力,而是在个体、群体甚至民族在权力压迫下产生的强烈反抗力量。这种近乎于集体意志的情感在伊朗的宗教文化之下,催生出了强烈的反抗力量,并成为人民挑战国家主权的武器。
实际上,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中曾对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过阐释。他认为,极权的法西斯主义并不遥远,西方现代国家将活人作为治理单位来进行考量、用控制牲口的方式来作为治理的新手段,从而实行的“生命政治”治理形式,会极端发展为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雏形(Foucault,2003: 253-260)。当人不再被看成个体,而是被视作“物种人”(man-as-species)来加以看待时,治理权力就能决定它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以维系国家或某种主权稳固发展。福柯在这里影射了西方“生命政治”极端化下可能出现的极权危险,但没有提及伊朗乃至中东地区的宗教权力治理,或许因为福柯对穆斯林文化的不甚了解,他没有将极权主义研究范围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方。
(二)超越世俗
精神性,以及精神性事实(spiritual facts)成了上世纪80年代的福柯常常提及的词。举例来说,最新出版的《性史》第四卷写就于1980年,里面福柯无意识地用了不少“精神性”字眼。14对“精神性”一词,福柯作出的解释为,它是“指向主体,让主体变成某种特定存在方式,并且让主体为了变成某种存在方式,而凭借自己完成转变”的力量(Foucault, 引自Carrette,1999:1)。精神性假定主体拥有追求自身真相的权利,但他或她必须通过某种转变、变革使自我达到某种程度,再来追寻自身真理;并且,获得这种主体转变的过程必须依靠主体对自我的种种实践。质言之,精神性要求“主体拥有权利,去获得改变、转化自我的真理,来让他得以变成某种程度上所不同的人”(Foucault,2005f:15)。它是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长期存在的力量,指向个人灵魂而实践于主体行动,并对主体做出转变。
除了眼下沙阿的继位问题,至少还有另一个问题同样使我感兴趣:一年多来,这个独特事件让人民群起揭竿、无畏枪炮,但它是否还有力量越过自身边界、去超越它赖以为基础的东西呢?这些限制和支持,是会随着人民内在狂热的消退而渐渐消失,还是反之生根发芽、变得更强大?这里很多人、包括伊朗某些人都在期待世俗化最终回归的时刻,因这预示着我们所熟知的、老派的“好”革命出现。(Foucault,1988a:224)
福柯认为,只有宗教文化产生的政治精神性,才或许拥有那种突破自身界限、超越原本拥有明确界限场域的力量。伊朗革命之所以拥有特殊性,在于其中出现了某种由西方熟知的、“老派的”理性分析框架所无法解释的精神性要素——马克思可以用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来照例分析巴黎公社或路易波拿巴的雾月政变,但同样的模型在面对伊朗问题时却显得束手无策(Foucault,1980:76)。当世俗化最终回归的时刻,排山倒海的反抗力量将冲破原本政治权力的呆板机制,而促成“好”革命、即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巨大变革出现。世俗化使人们不禁想起了韦伯,在强烈宗教性目标和极为世俗化的手段之间,这两种元素有着完全相反的精神气质却形成充满矛盾的融合,产生出的巨大影响不仅改变了基督教内部权威运行模式,还塑造出了当下的现代社会和现代的个人存在形式(Sung, 2004, 32)。而政治精神性并不只出现在伊朗或东方国家,它是一种经由宗教精神而超越世俗,并影响到政治领域的精神权力,是某种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曾经存在的事物,它区别于政治理性,或者说独立于自十六、七世纪启蒙时期过后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义,而政治精神性具有政治理性无法预测分析的效果。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户籍的城镇化,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失业保险问题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巨大动力。通过对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现状的描述,得出以下思考与建议。
与其说是集体意志与超越世俗常规的力量这两种因素使福柯对伊朗的政治精神性着迷,不如说他是借这两者以期脱离西方社会一直以来的治理形式框架,去探索另一种理性以外的治理形式的可能。伊朗革命的爆发所反映出人民强烈的驱逐沙阿、抵制外国人的意愿,这些无论是在巴黎公社还是“五月风暴”中都未曾出现过。巴黎的起义和游行一般是由某个阶级所特别发起,再逐渐扩展到全社会的;然而,伊朗人几乎是以某种决绝的革新方式推翻一切旧有传统秩序,给世俗生活注入超越传统的新力量。政治精神性产生的革命性力量像极了法国大革命,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所爆发出的全体性和单一性的斗争,为了推翻整套权力体系而在短时间内催生出规模不等的、迅速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抗争运动。然而,那种背后由卢梭哲学思想乃至整个18世纪哲学思想充实的群众运动,到20世纪已经不复存在了。“自从1789-1793年以来,至少在西方,时代就被革命精神以一切可能手段所支配或垄断,尽管革命垄断的消失也不意味着改革主义再次兴起”(Foucault,2018:197)。福柯认为伊朗革命中的政治精神性“自文艺复兴和基督教的重大危机以来就被我们所彻底遗忘了”,并且“法国人已经在笑”,暗含的就是自法国大革命以后就被西方社会所遗忘的反抗性力量。
(三)多元宗教性文化
福柯支持伊朗革命的第三个理由,就是他希望破除欧洲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文化的固有偏见,想要使人们正视伊朗人用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西方理性去破除沙阿“落后百年多的好古主义式现代化”。他同时还呼吁更多的西方人能改变对中东“百年以来落后腐朽的偏见”(Foucault,2005b:195)。
福柯对多元宗教文化和精神性生活长期持包容甚至喜欢的态度,这从他倾注大量心血探讨日本禅宗、美国各种少数教派以及希腊异端学说的诸多尝试可见一斑。究其原因,正是在这些偏离西方“正统”宗教文化的土壤中,可能孕育出在生命经历以及超越性精神方面与传统所完全迥异的个人存在形式。一直以来,人们对中东地区的认知都伴随着宗教的神秘和恐怖主义气氛,直至今日也是如此。人们甚至常常援引马克思的语句,来说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Marx, 1972:2)。但福柯恰恰借用马克思这句话的前几句来提出自己的观点:宗教不是“人民的鸦片“,而是“没有精神的世界的精神”(Foucault,1988a:218)。10
老太医高兴地道:“太好了,亲不亲,家乡人。”与秦铁崖互致问候之后,老太医放下托盘,“先请喝杯茶,我去准备一下,弄点下酒菜。”
10.这句话引自马克思(1972:2)发表于1843年的《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宗教里的苦难即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11.较为人知的福柯谈及马克思这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出处在福柯与布赖尔、布兰切特(C.Brière et P.Blancht)所做的访谈(见Foucault,1988a:218)。在这次提及里, 福柯告诫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要过分夸大马克思反宗教的思想,而认为马克思并非将宗教批得一无是处。但相对鲜为人知的是,福柯对这句话的陈述不仅有这一次,他于更早前就在和伊朗知识分子Baqir Parham对谈时说超过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但先前这次的提及是针对伊朗人民而说的——因为福柯不止一次听到伊朗人说马克思在这句话上错了,宗教不是鸦片,特别是对伊斯兰什叶派来说——这次对谈被收录在阿法利与安德森著作的附录里(见Foucault. 2005d :183-9)。这两次提及,福柯所面对的谈话方不一样,但可以看出他都试图说明,他所理解的马克思,在对待无论是基督教的宗教、还是作为普遍性的宗教上,都不是那么绝对的。近来有一些学者也试图为马克思的这句话“平反”, 但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支持过宗教”,这未免有些矫枉过正。很难说明马克思对宗教的绝对看法是什么,鉴于马克思在写《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同一年,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也批判过犹太教,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这里所指的宗教已经不单单再是特定基督教,而是普遍意义上的宗教本身。
19.亨尼斯(Hennis, 1983,135-180)认为韦伯的问题域是有关“实践伦理的形式”和“生活方式的理性化”, 他顺着腾布鲁克对韦伯宗教论文集的重视而提出韦伯的中心问题聚焦于个体的人格塑造,笔者对韦伯的理解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腾布鲁克、亨尼斯和布鲁贝克这些人关于人格塑造的思想线索。当然,这种对韦伯的理解方法也存在争议,本文是以福柯为主角而按照理论思路“修剪”韦伯的人格塑造思想,其中或有不妥当之处,欢迎学者们指出和讨论。
福柯对一般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进行了反驳,其意图也在为宗教的精神性找到合法理由。他试图证明,马克思不是一个反宗教者,因为宗教使人民在苦难中得到慰藉。因此他有理由去质疑常规的“马克思主义”看法。也就是说,当现实充满苦难而没有任何解决办法时,宗教成为了人民的庇护所,这是在没有足够力量对现实进行反抗时人民产生的迷醉自我的办法。在马克思的叙述中所称的宗教无疑是基督教,它对人民起到安慰、迷幻剂的效果,成了整个被理性“祛魅”后现实仍到处于存在压迫的世界中唯一一处富有精神灵光的场所。与此相同,在福柯的叙述中,伊朗的什叶派也拥有“唤起人民政治觉醒、保留其政治良知,以及激发起它们政治意识”的作用,这使政治精神性在中东历史变革中承担起了不可磨灭的责任(Foucault,2005d:186; 1988a:218)。11在福柯的意义中,相对于鸦片,伊朗的宗教精神性则显得更像是人民手中用于反抗的武器——用来撕裂传统社会变革的利器,成为唤起人民政治意识崛起的号角。
如此,我们可以理解福柯面对伊朗革命时关注“政治精神性”的意图。一方面,伊朗历史现实中出现的集体意志不仅表现出推翻沙阿王朝的决心,还对西方文化输入抱着抵制情绪,这种情绪酝酿出一种与长期在“牧领权”统治之下的西方社会所完全不同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伊朗人民渴望日常生活的急剧转变,超越性宗教文化渗透入日常生活而产生革新力量。两者的结合造成对西方传统理性的冲击,加上福柯自身对多元宗教精神性的兴趣,促成了他在伊朗革命爆发之际成为了伊朗“政治精神性”的支持者。那么,当集体意志成为反抗的主导力量,它会拥有突破自我底线并超越那些自己作为基础的那些东西吗?历史的答案或许是消极的,然而,福柯恰恰从伊朗革命那里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属于西方理性系统,同时值得引起重视的新奇而强大的力量。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40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的历程可谓波澜壮阔。历史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是我们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一个伟大历史贡献。经过改革开放,一方面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得以不断巩固。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首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
当然,福柯对伊朗政治精神性的看法依旧建立在将西方文化权力作为中心的前提之上。倘若非要评价福柯的话,笔者更同意将福柯看成一个“欧洲中心论者”(Said,1988:9)——他不像萨义德那样,是以一种“异乡人”的视角看待西方诸制度,并对伊斯兰文化抱有本真性看法;福柯察觉到了一直以来西方治理制度中产生的问题,并且思考用另一种选择来对制度加以革新,这使他在政治治理和个人伦理精神问题上打开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理性的新型方式。
三、 “政治精神性”对抗“生命政治”
伊朗的政治精神性之所以使福柯产生如此之兴趣,很大原因在于它几乎恰好是基督教“牧领”权力的反面。在那些年的研究中,福柯花了很大精力涉及对西方现代国家“生命政治”的分析,其中,他花了大量篇幅谈及基督教文化如何在治理上实现对个人的控制(Foucault:[1979]2015)。12他试图勾勒出“牧领”权形态在基督教时期的发展,同时说明这种牧领权是如何与它的对立面——国家——恰好结合在一起,以致使“生命政治的诞生”成为可能。而后来的伊朗政治精神性,对福柯来说则成了反抗西方国家以“生命政治”为主题的理性治理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保护的作用.漏电保护器的功能检测;为了经常检查漏电保护器的动作性能,漏电保护器装有实验按钮,在漏电保护器开关闭合后,按下实验按钮 SB,如果开关断开,则证明漏电保护器正常.一般一月应检查一次.
首先,我想要说,这二十年来我的研究工作,其目的不是分析权力的现象,也不是阐释这种分析的基础。我的目标是创造某种多样方式的历史,而我们文化里的这种历史是人被塑造为主体的历史。(Drefus and Rabinow,1983:208)
其次,基督教的“牧领”权挪用了希腊化时期牧领技术的两个重要手段——自我审查(self-examination)和良心指导(direction of consciousness)。这两种手段在早期基督教时期还只适用于修道院的修士,存在于隐者和其指导者之间,但在中世纪以后的“牧领”权力中,它甚至被扩展到平民百姓身上。基于自我审查技术可以使个人的自我意识完全向治理者敞开,以便于治理者借助这种敞开来对个人形成持续的约束和引导(Foucault, 1988c:70)。至此,基督教的“牧领”权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建构出了一个“希腊人和希伯来人都未曾设想过”的奇怪游戏,它的元素包含生活、死亡、真理、顺从、个人和自我认同;它不是通过让城邦中的个体公民牺牲以获得城邦的生存,恰恰相反,它要让城邦内的个人遵照城邦要求的方式活着来维系城邦的运行(Foucault,1988c:71)。这代表此种治理术把有关个人的真理置于城邦或国家的知识体系之中,唯有城邦或国家拥有如何让个人“好好活着”的知识,而个人所能采取的行动,就是依照城邦或国家的意志而无意识地服从。福柯直观地将现代国家治理个体的形式称为“生命政治”:“在18世纪下半叶,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联系,构成了知识的首要对象和生命政治控制的首要目标”(Foucault,2003:243)。西方国家“生命政治”形式产生的治理术不仅可算作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过度发展,也是基督教精神性逐渐世俗化后导致的宗教后果。由此,摆在现代人面前的后续问题则是:我们应该如何对这种治理术说“不”呢,是诉诸于审判理性,还是去加以反抗?
13.在那一年演说中福柯谈到了苦行主义、社团、神秘主义、《圣经》释读和末世学信仰等宗教性力量等(具体参见Foucault,2007:191-226)。
14.譬如在“论贞洁”那一章中,福柯谈到,“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图特良(Tertullian)发展出的(禁欲)思想都以对其的延续来结束:也就是说,与耶稣基督结婚,或是以一种接近精神现实的条件下的贞洁”(Foucault,2018),笔者自译。
福柯否定了前一种出路:“我们要拿理性开刀吗?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么干更徒劳无功的了”(Foucault,1988c:59)。而福柯学者戴维森(Arnold I. Davidson)则为后者——“反抗规训”——梳理出一条路径(Davidson,2011)。他强调了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重要的一节,即有关“反治理”(counter-conduct)的一节,认为福柯提出了反抗“牧领”权、抗拒灵魂指引的尝试。戴维森指出,福柯在1978年演讲中谈及欧洲反抗“牧领”权的种种可能13喻示着在他整套话语体系中建立起在政治和伦理之间、道德与政治哲学之间富足而精彩的联系,使个人在多种伦理实践中为反抗政治治理提供多种形式。在这些多种形式中就包括了1978年福柯所看到的伊朗之“政治精神性”,福柯从这种新的精神指导方向中找到了反抗西方长久以来“牧领”权治理的有效形式。
第二条线索则是政治精神性对日常生活的巨大变革,即它拥有产生突破世俗、超越政治原本界限而延伸至该领域以外的力量。这意味着政治精神性没有如实体政治权力那样的“边界”感。众所周知,福柯的国家权力观围绕着国家主权的“国家理由”(Raison d’Etat)展开,而“国家理由”意味着国家治理必然在某个特定政权体制之下进行运作,譬如需要保护国家安全、领土和人口等要素,因而使用治安、外交军事技术和牧领权等手段来确定它的治理技艺范围(Foucault, 2007: 87-114)。也就是说,从“国家理由”出发的政治权力具有明确定义的主权范围。然而当宗教精神进入政治范畴时,界限就显得不那么明确了。人民的政治参与力量不来自于界限分明的理性化政治理由,而强烈受到所谓的“非理性”意志的驱动,进而“激烈地改变了他们的主体性”:
在西方社会及发生伊朗革命的社会中我们看到了两种精神性指向。一种是在基督教中所呈现出的完全服从形式:宗教和国家之间产生的交叠使每个人都在无意间被原子化,成为治理术的治理对象。而另一种精神性,则成了福柯试图突破前一种精神性的武器——它们是反抗“牧领”、反抗服从性精神指引的政治精神性。以“政治精神性”对抗基督教的“牧领”精神性,在福柯看来它不仅是一条反抗“牧领权”治理的道路,也是关乎于个人实践的一种行动指向。后一种道路,在福柯看来就具象化为1978年的伊朗人民的英勇反抗。在当时的福柯看来,伊朗革命产生的政治精神性,起到了团结伊朗人民以转变自身主体为诉求而反抗的效果,它有效地冲破了传统的政治治理机制。地区性反抗的成功使福柯看到了希望,他期待用另一种非西方化的宗教精神,来破除旧的生活方式乃至复兴某种新的生活样式。伊朗出现的精神性看上去将个人灵魂从以身体为监狱所形成的多种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以贯彻自我的思想(Ghamari-Tabrizi,2016:63)。反观盘踞欧洲社会许久的“牧领权”,它已经在西方社会发展愈演愈烈,成为治理国家政治事务以及细致关心治理微观个体的政治技术,福柯在考察其产生和运作机制之余,更是对它保持警惕,所以伊朗政治精神性无异于促生了要寻求另一种宗教精神性来反抗这种基督教垄断式精神性的渴望。以诸“精神性”来对抗“生命政治”的渴望最终转换到他在面对治理体系分析时,推出了一套反治理、或者说“反抗指引”的主体性实践尝试。
四、回归“主体”的政治精神性
从上面叙述里不难看到,在伊朗革命中呈现出的政治精神性里暗含着一种更深层、更个体化的含义——主体性实践。福柯不止一次地强调主体与政治精神性之间的联系,1978年5月第一次提到“政治精神性”概念时,他就将其带入自我和他人之关系的主体性实践范畴:
为每一种在自身和在与他人关系的实践来追寻新的基础,通过一种不同以往的判断对错的方式来发现治理自己的不同办法, 这样的意愿就是我所说的“政治精神性”。 (Foucault,1991:76)15
另外,在1979年福柯和布赖尔、布兰切特的对谈中,福柯思想里精神性和主体性之间的关系转变就变得更为明显:
总而言之,在伊朗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上,宗教对他们来说,就好像给予他们一种承诺或保障,以让其找到某种能够激烈改变他们的主体性的东西。(Foucault, 1988a: 217)
Basin as the example in Dehong state, Yunnan province MIAO Yu HE Mao-yuan(67)
15.Foucault(1991:76)的这篇访谈进行于1978年5月,最先出自由Michel Perrot编写的L’impossibleprison:RecherchessurlesystèmepénitentiareauXIXesiècleetdébatavecMichelFoucault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80),后又由Colin Gordon译成英文,收录在《福柯效应》(The Foucault Effect)和《福柯集粹:权力》(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Power)中。
近期,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官司的民事判决书。在这起官司中,原审原告杨某某把装有罗曼尼康帝、作品一号等多款名庄酒的酒柜置于小区物业地下室,结果地下室一旁的换热站发生爆管,导致名庄酒被长时间浸泡在80℃高温的热水中,遭受损坏。杨某某便把换热站的管理方济南热电公司告上法庭,索赔245.696万元,并获得胜诉。
16.国内对生命政治的讨论已经成果颇丰,这里就不再赘述。主要文献参见高奇琦(2016)和蓝江(2016)等。
尽管在这场对谈后福柯对伊朗问题几乎避而不谈,声称不想再持续陷入论争之中,德菲尔对此的描述是“福柯感到非常不安”(Defert,2013:71),但主体性在福柯的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性却在此凸显了出来。政治精神性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对权威采取反抗行动,更重要的是它试图塑造主体,让“主体拥有权利,去获得改变、转化自我的真理,并让他得以变成某种程度上所不同的人”。由此政治精神性也成了联结政治与主体之间的桥梁,使主体性实践进入政治领域。
虽然对课程强度的评价反映了学生对课程时长与内容量的满意,但四天的动手操作与讲解涵盖了现今临床常用的所有影像学设备与机理,笔者观察认为时间仍是较为紧张的。然而学生实习总学时的限定使得更长时间的物理课程实习不现实、不利于将该课程整合进原有的实习计划。另一个是资源数量问题,因为学生较多而实验室可供操作的设备数量有限,只能分批轮流进行。显然更多的操作资源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师资力量也是一个短板,专门安排一位老师脱产带教势必将加重其余医师的工作负担,这也是设计课程时长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政治和主体这两个看似不相关联的领域内,又是如何在政治精神性方面产生交叠的呢?现代社会的政治已经不仅仅只关心政治议题,它早就成了“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的反面就是人的主体“客体化”。福柯指出,“在18世纪下半叶,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这些过程,构成了知识的首要对象和生命政治控制的首要目标”(Foucault,2003:243)。16而为了便于治理与管控,政治技术要求掌控出生、死亡、寿命、婚姻等种种统计数据,在这些冰冷的数据下面存在着的是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个人在经过一系列反思、规训、服从等技术改造后,基于国家理由所裁定的特征来塑造自己的主体形态,他被教导为怎么出生、何时工作、何时结婚、用什么方式思考。作为被治理的个体,他要么和自我分离要么和他人分离,并在种种分离性实践的进程中,被建构成了“客体化”的主体形式(Foucault, 1994b:326)。个人被政治技术所治理而成为客体化主体,这是福柯认为自16、17世纪以来“人”出现的很大问题。
不是主体在政治实践里被不断消解,而是政治试图按它所想要的方式将人塑造成特定个体。于是,如何实践主体、如何将塑造主体的主角转回自身,去建立主体性的问题才显得重要。在此之前,“主体性”(subjectivity)这个词极少出现在福柯的话语中。但从1979年之后,也就是伊朗革命后一年开始,伴随着《主体性与真理性》、《主体解释学》等法兰西学院诸演讲的出版,福柯对主体性研究的关注便大大提升了。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在对欧洲新自由主义的治理研究中,福柯细致考察了西方传统“生命政治”的产生与发展肌理;而在国际政治层面上爆发的伊朗革命则使他关注起了一种新的政治精神性,使之成为突破传统西方生命政治的新途径。对福柯来说,伊朗的精神性展现了在实现政治和伦理在个人平衡方面的另一种可能。伊朗推翻旧王朝所呈现出的新鲜力量充满了未知与新奇,更使福柯找到了一种反抗“生命政治”权力的新主体实践形式。但这种力量在现实中既可能与民主制度结合,也可能被专制制度利用,而发展到后来,表现为像霍梅尼政权那样的神权高压统治,那又是福柯当时所未曾设想过的。伊朗革命不仅仅是一个孤立事件,政治精神性的社会意涵在于精神性思考开始进入政治权力领域。现代个体所面对的一方面是政治权力集中化,另一方面则是个体越来越趋向于分离,并且两者之间还持续存在着某种张力。在此种环境下,如何引入政治精神性,而让个人依旧保有建构其主体的自由权?关于这类问题,无论是福柯,还是其他社会政治理论家们,对此都有种种思虑与讨论。
答案在1978年。在这关键的一年,福柯经历了几件事情。这一年他重新开始了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主题延续了他1976年生命政治的探讨,并直接将对权力的关注点迅速转移到新的领域——“治理”(governmentality)。“治理”不同于以往的权力关系,它是历史进程上以各种手段进行治理的治理技术集合,其中就包括他所发现的出现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治理形式之前的、从基督教而来的“牧领权”治理形式。1月下旬他开始写作《肉体的自白》(Lesaveuxdelachair),这本书原定作为《性史》系列第二卷,其主题专注于从基督教禁欲思想中提取出西方主体化形式。17在写作过程中,福柯对古代思想——希腊诸学派和早期基督教——中关于自我控制的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使他在后期极大地转变了《性史》的写作路径。4月份福柯出访日本,在那里做了几次演讲,并对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禅文化”感兴趣。这一年夏天,福柯差点拥抱死亡——他被一辆车撞飞,产生了短暂的濒死体验。“有那么两秒钟,我觉得自己要死了,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快感突然袭来……”(Foucault, 1988b:12)死亡的私人体验令福柯更加关注个人的主体性经历。而就在这一年的9月,福柯接受意大利《今日晚报》的邀请,赴伊朗做了系列报道,并为伊朗革命中由宗教文化产生的政治精神性而深深着迷。18
这一系列经历都将福柯推向了他研究体系中的新概念:主体性。虽然学界在争论中常常认为在福柯长达三十多年的研究道路上缺乏某种正面的、确凿的研究主体,但还是有人认为他的研究尤其是中后期在政治制度和伦理实践方面的探索都可用“主体性”这一关键词来串联(Cook, 1987, 219)。如果说从前的《规训与惩罚》、《古典时代疯狂史》所研究的是外部权力系统对人的规训控制以及探讨如何反抗这种外部权力的话;那么,福柯“生命政治”和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研究虽然也是属于外部权力治理范畴内,只不过权力机构从现代机构体系转向了以国家为理由。而他写作《性史》后两卷和《主体性与真理》、《主体解释学》以及最后两年的《对自己及他人的治理》等系列演讲,则都是在探讨人如何运用主体来对自我加以塑造,也就是主体性的自我塑造。他在1982年为德里弗与拉比诺的《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后记中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他二十多年来的研究就是围绕主体性展开的:
从欧洲帝国早期开始,基督教将原本用于规制一部分修道士个人生活的实践技术加以普及化,让国家内每一个人都遵从特定生活方式,以实现细致到每一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个体化权力。而到了中世纪以后,基督教的个体化权力就显得愈发细致。首先,借用上帝和信徒之间“牧羊人-羊群”的比喻来带入统治者和人民,把个体比作一群温顺、需要照管的羊,而把国家或统治者喻为“好牧人”。只有牧人知道如何照管羊群的生命,知道何时喂养他、让他生活,这就使国家的“牧领”权力泛化于政治领域而更加涉及到个人的生命问题。
18.关于福柯在1978年的生平经历,笔者主要参阅了德菲尔为福柯整理的年表(见Defert, 2013 :66-70)。同时也对照了Eribon (1991)与James (2000)的福柯传记相关部分。埃里蓬(Eribon,1991)的《福柯传》被德菲尔指控为“不真实地报道了福柯本人”,故笔者认为这本书可信度不高,不过后文对这本传记的内容还是做了相关参考。
塑造主体的历史有三种,其一是科学知识对人的塑造作用,这涉及到科学、知识和学科体系对人认知上的规训;其二是自我和他人的“区隔式”实践,譬如人被区别为疯人、病人和罪犯加以对待;第三种主体化模式,则是个人自己将自己变成自我实践的主体(Drefus and Rabinow,1983:208)。在第三种模式中,人本身是将自己塑造成主体的动者(mover)。它既不同于第一种知识规训的模式,在认知和行为上被动地被规制;也不同于第二种区隔实践,被他人定义为“非正常”而受到规制。这种自我实践的主体化形式,一方面对自我塑造起到推进作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是个人在意识到政治、知识、国家权力对人的规训时,对“个体化的治理”所采取的反抗形式(Drefus and Rabinow,1983:212)。自我实践的主体化模式要求个人专注于和自我的关系,试图转变从前与自我的关系,转变他人意志对自己所施加的影响,以塑造出一种致力于自我的主体性及其关系。这和现代国家中政治技术为了治理而创造主体性的过程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先治理自己,用不断实践创造自我主体,形成属于自我的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如何经历的一系列形式,再进而参与到政治领域,对权力权威保持警惕。
由此,对福柯来说,1978年的伊朗革命恰恰是作为随其他外部事件一起促使他产生对“主体研究”兴趣的直接动力之一。在这场革命中,伊朗人的反抗是唤起每个人转变自身主体性的重要标志。而找到主体性的途径,就如前所说,在持续实践中不断转变自己,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真实存在形式(Foucault,1989:437)。彼时的福柯还没有后来1984年时所说的“自我塑造”的哲学生活态度,但他在1978年也提出要改变成为关系的自我形式: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存在,我们和他人、事物、永恒、上帝等关系必须被完全改变,并且要让我们产生这种急剧变化,只能通过经历真正的革命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伊斯兰人扮演了重要角色。(Foucault,1988a:217-218)
将主体进行转变,在某种转向中找到自我的主体性位置,这意味着个人将自我从对他者的服从中解放出来。将“我”作为自我实践的根本缘由,这不同于以往“把个人作为原子而形成每个人的整体被奴役系统”(Foucault,2007:184),而是意味着每个人都对如何塑造自己负有一份责任。运用并实践精神性,其意义就在于使主体拥有“获得自身真理的权利,为此他必须改变、转变、转向而成为从某种意义上和从前的自己不同的人”(Foucault,2005a:15)。这样的精神性本身就彰显出主体的重要性,而从政治精神性中能看出福柯对主体性实践的兴致,亦标志着福柯在关注主体性的过程中,转变了他自身的主体性,无论是在研究中还是在自我的实践中,他都开始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五、问题与图景:从主体性到政治自由
17.也即2018年2月伽利马出版社刚出版的福柯《性史》第四卷。从内容上看,福柯探讨了基督教文本里基督教神学家们(图特良[Tertullian]、卡西安[Cassian]等人)有关个人检查、惩罚、贞洁、婚姻等思想论述,并将这些论述和个人主体性联系起来。从大体来看,这是一次福柯对早期基督教(公元4-5世纪)时期的历史谱系考察,他认为那时期基督教对个人行为的私人部分(婚姻、性关系和其他行动等)有着严密检查,伴随着国家权力以“牧领权”形式所形成的个体性权力,人从伦理到政治都成为了“治理的客体”(详见Foucault,2018)。
福柯曾说,他梳理出一种治理和反思自我的主体并进行批判思考的路径,“从黑格尔开始,经由尼采和韦伯,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Foucault, 2010:21)。缠绕在西方政治与社会思想史上的“精神性”一直没有消散,福柯吸取了黑格尔的精神性,尼采的基督教仇恨思想,和韦伯关于人格塑造的阐述来拓宽这条政治与主体的道路。韦伯实际上早在福柯之前就有过在政治领域内谈论精神性问题的尝试,历史上卡里斯玛式领袖就是以强烈的信仰精神作为支配手段的类型,他们有着相当非理性、革命性的力量,几乎和任何其他权力类型都产生冲突。而当面对当代立志于投身政治的年轻人,他不无担忧地提醒他们,现代个体必须将政治与虚假伦理区分开,不然那些从事政治之人极有可能只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韦伯,2010:253)。韦伯清醒地意识到,非理性时代已经是过去式,现代政治中的精神性是以“牺牲理知”为代价而出现的。倘若个人偏要求在充分理解政治领域的实际境况后,依旧对这份事业保持“献身于一个掌管着这项事业的上帝或恶魔的激情”的话,他依旧要保持理智诚实,即要祛除那种激情下的幻觉:“任何想要步入世俗政治的人都应该祛除这种幻觉,认识到存在这里的一个根本事实: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俗世中人与人之间的永恒争斗中去”(Weber,1994:29)。 同样,他还说过,“我们不会给我们的子孙带来什么和平或人类幸福,相反,我们为了阻止与提升民族的品质,反而会带来无尽争斗”(韦伯,2010:78)。韦伯的策略在于,只有清醒地对自我和政治实践有着明确的认知,人才能真正认清自己身处于怎样的境地,进而做出的政治主张才可能“理知清明”。人首先认识到政治实践本身的严酷性,接着在使人找到政治中作为志业的守护神精神,呼吁知识分子和有志于从事政治的人用自己的意志建立合法性,以期待在严酷的政治实践中找到个人的伦理依托。福柯塑造主体、进行主体化实践,以完成某种精神性转变的思想,很大一部分从韦伯的理智诚实、人格塑造那里而来。19不再是由政治权力塑造出个人主体性,而是反过来,在自我拥有主体自由的前提下,以理知投身政治。
12.这些有关“生命政治”的研究,除了福柯1978-1980年间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和“对活人的治理”外,还包括他一系列在海外大学所作的演讲,它们分别是1979年10月10日和16日在斯坦福大学所发表的“整全与单一:一种政治理性批判”两篇演讲,最初以英文收录于(Raymond Aron, Brian Barr, Jonathan Bennett, Rober Coles, George T Stigler, Walace Stegner and Michel Foucault.1981.)TheTannerLecturesonHumanValues, edited by S. M. McMurrin. Salt Lake City: Cambridge Univeritity Press;“福柯考察国家理性”(Foucault, M. 1979.“Foucault Examines Reason in Service of State Power. ” CampusReport [12]6: 5-6);以及1982年10月在达特茅斯学院所做的演讲“个体的政治技术”(最初收录于TechnologiesoftheSelf, edited by L. Martin etal.Amherts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s Press,1988.)。 汪民安教授主编的《福柯文选》第三册《什么是批判?》里收录了“全体与单一:论政治理性批判”和“个体的政治技术”两篇演讲。
(3)智能化。煤矿机电设备的智能化发展是提高煤矿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有效措施,可以借助智能化系统动态监测煤矿开采状况和机电设备运行情况,能够及时反馈故障信息等,不仅增强了机电设备的控制程度,更提高了煤矿生产的安全性。
在这条政治与主体的脉络上还需要关注一下阿甘本,他同样对生命政治基础下的个人生命感到担忧,但他与福柯有所不同。第一,阿甘本在生命政治的基础上重申了极权国家下主体消亡的现状。阿甘本评价道:尽管福柯对生命政治和个体生活的叙述专注于主体化的诸种过程,并将建构起来的主体与外部控制的权力相关联,但福柯却“从未把他的洞见同那似乎很可能是现代生命政治的典型场地——20世纪诸多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相关联”(阿甘本,2013:164)。不过,阿甘本或许没有注意到,即使福柯在批判现代国家极权对个体的建构时,其焦点也不是权力,是权力机制下的个人如何塑造自我主体。第二,阿甘本更关心的是,在生命政治化背景下“身体”被作为政治权力的祭品,非“主体”的自由或独立。阿甘本对生命政治的批判沿着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方向是朝向坎特洛维茨(Kantorowicz)的神圣身体,认为身体通过神化的方式不断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和工具;另一方向则是朝向福柯的生命政治,认为现代性的国家政治强调对每个人的身体加以全权掌控和管制。主体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被阿甘本戏剧性地增强为一方是赤裸生命另一方为至高权力的二元对立,自然生命在随着不断被纳入权力机制和计算的过程中转化为政治“动物”。此外,阿甘本过分地忧虑于现代国家政权会向极权国家靠拢——他汇集了福柯之民主国家“政治计算”式权力机制,阿伦特之人权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加上霍布斯之自然状态下的个体政治形态,“拼凑”出了一个现代集中营式的图景。在该图景中,个人生存权利将被带着民主伪装的极权主义所侵蚀,使身体、生存、自由等基本状况都处于高压支配之下。鉴于该集中营图景只存在于阿甘本个人的政治哲学推测中,我们很难确定现代国家是否会出现如此可怖的状况。然而,不管怎么说,阿甘本在福柯的基础上对生命政治及个体权利做出了演进式诠释,“本世纪的极权主义是以生命和政治这一动态的合一性为基础的”(阿甘本,2013:199)。在经历了德国法西斯和斯大林政权的种种遭遇后,不难想像在这条生命政治的道路上,现代政权机制会对个人主体乃至身体产生多大影响与控制。
福柯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与所作所为仿佛体现了他生命经验里一次独特的“叙拉古之行”。福柯错了吗?首先,本文不打算卷入政治立场论争,4况且福柯本人也极力避免在研究或生活中参与任何论战(Foucault, 2005e: 249)。文章也不准备对霍梅尼的“僭主政治”作赞美性的论述,因为福柯对伊朗革命的支持并不来自于受僭主政治诱骗的范畴,而来自于对社会权威的警惕和对反抗精神的赞许,这在文章后面会详细提及。本文所要关注的是,如何将这次“叙拉古事件”置于福柯整体研究框架之内来思考,以期能够把握其此次经历在福柯本人生命和社会理论思想脉络中所具有的合理性。
我的家乡萍乡是一片拥有光辉革命历史的红色土地。在我童年的生活里,到处都可以听到红色的故事、见到红色的旧址、感受到革命的基因。学校组织活动的时候,也经常是带我们去红色遗址。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去安源纪念馆参观。到了那儿,我大概地看了一下安源纪念馆的外观。纪念馆主馆的正前方竖立着一根笔直的旗杆,旗杆上的国旗迎风飘扬;再往后一点,是一座毛主席石雕;而主馆的大门上方是一幅毛主席肖像。跟随着讲解员阿姨的脚步,我仿佛回到了过去,逐渐了解了少年儿童团的起源,知道了安源故土的红色故事,我才渐渐明白自己脖子上系着的红领巾蕴含了多少层含义、多少的故事。
福柯的反权力化政治实践本身也包含着另一种意义的积极自由。福柯长期致力于反抗权威、解构政权、消解权力乃至个人,而很少提出“应该”如何确定自由的立场。倘若要用伯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区分对此下判断的话,福柯并非倡导个体免于他人和政治的干涉来实现自由,而恰恰因为他在长期历史研究中发现了自由的局限,使他致力于脱离“自由”讨论主体。自由这一概念实际上一直是福柯思想的核心,但他未将该词用有形的、限定的形态描述出来——因为该概念的适用范围在每种文化乃至每个学者的叙述中都呈现出不同的边界——而是转而叙述哪些权力和技术使人被治理、被塑造,以致变得不“自由”。在这一意义下,自由虽然缺乏一个主体,但自由的进程实际上却对个体自由造成有效影响(Patton, 1987: 266)。个体自由深受普遍环境下诸文化领域之间冲突的影响,进而塑造与治理自己,因此,在福柯看来,政治问题不是将人从制度中解放出来,而是将我们从某种特定形式的制度,及特定种类的作用于个体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这也就是福柯在面对权力时所强调的,“我们必须促进新形式的主体性”(Foucault, 1994:216),在多种实践下促成自由的新主体形式。倘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泰勒和福柯在面对现实政治下的主体时是殊途同归的:泰勒强调个人动机或所欲目标将放在第二位,以维护本真性观念和实现积极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徐冰,2017:35),有鉴于此,泰勒才批判福柯过于强调自我而忽视公共领域的立场。然而,福柯着重于思考人类行动将如何塑造出一种新形式的人格,而这类新形式的人又如何在原本同质化的公共领域创造出更多元的选择可能性,以使个人能够去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个体,塑造怎样的主体。所以,实际上这两人共同希望在公共政治领域范围内个人依然能实现自己的积极自由,只是在思考积极自由的主体时的侧重有所不同而已。
近年时兴埋藏酒。有人把瓶装好白酒、红酒和坛装的粮食酒埋藏在自家阳台、小院的苗圃,或者寄埋在农家田园,说是要埋它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待儿女婚嫁或者自己六十大寿再挖出来开怀畅饮。其实,并非什么酒都是越陈越好,勾兑白酒和许多红酒,品牌虽好却不宜久藏。能藏的酒,对温度、湿度和通风条件亦有严格要求。
六、结语
重新回到开头所提及的“叙拉古问题”,福柯在他最后一次回应伊朗革命的文章的末尾写道:“我的伦理就是‘反策略’(counter-strategy)。我既不是这么做的第一人,也不是唯一人选,我只是选择了这么做”(Foucault,1994b:453)。这句话涵盖了福柯支持伊朗人民反抗的原因,也喻示着他接下来继续探索主体性实践的研究方向。这次不算“成功”的有关政治精神性问题的思考,就像是投入湖中的一颗石子,它是福柯强调主体领域思考如何确立“反策略”伦理的一次尝试。在这之后经过持续不断的对反抗权威和现实政治制度的种种考察,福柯逐渐确立起了一条“反治理”(counter-conduct)的新路径,来突破欧洲基督教和理性主义建立起的治理体系。这样的尝试可见于福柯在转向古希腊伦理实践后对犬儒派思想产生的亲和态度,提出了犬儒派的“直言”(Parrhesia)技术,并采纳了此派系的中心思想——“重估流通价值”(change the value of the currency)——作为主体的实践技术。
“重估价值”意味着转变,它不是说去贬低现有的流通价值,而是旨在对旧有价值加以重估,并赋予其新的意义(Foucault,2011:227)。同样,犬儒派的“直言”也被福柯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在现代社会里,践行“直言”技术意味着在自我技术实践过程中,个人说出自身的真话,并投身政治话语活动。知识分子在自身领域内诚实地说出真相,为争夺该领域的话语权而向公众发声,以防止这一领域被“假专家”或既有的任何一种权力机构所占据;并且在此基础上,使人们重新检查作为思考基础的规则和机制,以承担揭露真相、转变思想的任务。这成为了福柯所认为的现代知识分子之职责——说出真话,并投身政治(Foucault,1988c:263,265)。
“直言”可以说直接地与政治精神性息息相关。“如何获取真话和精神性实践,这两个问题,这两个主题从不会分离。”(Foucault,2005f:17)这种说出真话的话语模式可以说是福柯在政治精神性的尝试失败后,面对现代政治话语所找到的新途径。政治精神性本身就包含了个人在多种领域实践、经历并说出真话的过程,将个人主体用实践形式带入政治权力话语,以促成在真理、权力和主体间的三角关系。所以置身于上述三角关系中的“直言”所承载的角色也和政治精神性类似,正是在政治领域中发挥主体权力的作用。这条途径自福柯以后几乎再鲜有人探寻。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学派中汲取主体性形式,这一做法虽被阿多等古典学家批判为“好古”,但这正体现了福柯在政治的主体塑造下的不断尝试,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试图改变个体,实践新的主体化模式。
“民主并不是‘直言’的优渥土壤,它反而正是最难实践‘直言’的地方”(Foucault,2011:29)。恰恰因为政治精神性和“直言”因享有相似的主体和政治联系——唤起主体主动塑造自我,促成政治领域“说真话”的勇气,以至于这句话对于在福柯语境下的政治精神性来说,或许同样适用。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主体之间并非前者规训后者,或者彼此处于剑拔弩张状态的两极,它们恰恰是互相成就的:以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形式作为建构基础的治理体系发展出一套相关治理技术,使建构个体真理和塑造主体变得难以在个人主体之内进行,而需要仰赖外部治理体系;反过来,这群由治理技术建构起来的主体又会参与政治活动实践,以进一步巩固这种现代政治体系。如何抵抗现代社会建构下诸治理技术对个人的约束,并进而改变塑造主体的整体社会政治框架,是福柯对政治精神性和“直言”所赋予的共同期待。至此,福柯的政治和伦理,在作为主体的自我的问题上产生交叠,个人将自我看作为实践和思考的主体,拥有“对他人的权力和对自我的权力技术”,并“至此治理他人并必须治理自己”(Foucault, 2016:281)。这就是福柯所说的“自我塑造”(self-formation)的模式或“存在形式”(mode of being),且这种模式横跨伦理、政治和精神性三大方面。福柯还归纳了在主体塑造和参与政治实践方面,政治精神性所要实现的方向:
或许当下的目标不是发现我们是什么,而是拒绝我们所是。我们必须尽力去想像和建构我们所能成为的存在,以克服那种政治的“双重束缚”,即现代权力结构里既个体化又极权化的东西……我们必须通过拒绝那种强加在人身上好几个世纪的个体性, 来促进一种新的主体性形式诞生。 (Foucault,1983: 216)
不是去抵抗权力结构的压制,而是试图拒绝那“强加在人身上好几个世纪的个体性”,即改变长此以往在西方社会绵延到现代社会政治建构中的那种以民主自由为门面、实则在福柯看来“既个体化又极权化”的思想——这正是福柯在伊朗革命中发现的独特精神性能对现代个体产生的影响。
20.在福柯后期著作中,“治理”成为一个庞大的思考框架,它打破从前真理-权力-自我的三角,将“伦理”、“精神”和“政治”覆盖入一个框架内, 治理不仅包括技术机构对人的规训, 还包括自我通过实践对自己进行塑造,更包括自我对他人所产生的影响。有关“治理”概念,可见勒薇尔(2015)的《福柯思想辞典》里的相关阐释。而政治精神性在这一框架内,被卡雷特看成为“治理的问题化“,在“作为被他人控制的主体”和一种“被自我良知和知识所定义的主体”两种意义上重塑了主体性的政治(参见Carrette,2000:138)。卡雷特在政治精神性的解释上过于强调宗教精神的联系,且他过于重视“精神性”和“实体”之间的对立;但他将政治精神性置于“治理”框架内的思考依旧有一定道理。
在其2013年3月发表的“美国小学数学结构之批评”一文中,马立平博士用下图比较了传统数学(左)和发现式数学(右)在内容和结构上的差异[7]:
正如福柯不喜欢将他思想中每个概念划定出确切的界限那样,政治精神性也不是一个有着确定边界的词汇,它的内涵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作为特定事件的伊朗“政治精神性”是昙花一现的事物,但作为普遍现象的“政治精神性”,在之前和之后都以各种产生方式不断轮回于诸多社会之中。我们可以说,政治精神性本身既涵盖政治因素,更重要的是它又拥有伦理与精神的交织,是“将宗教的整个领域进行重整而成为‘治理’的内在进程”(Carrette, 2000:140)。因而它如“治理”(governmentality)一词一样,跨越政治、真理、主体这三大框架,运用它独特的权力技术在其间不断实践发展。20西方社会历史上,前者兼具“政治”和“精神”主体的形式便是“强加在人身上好几个世纪”的基督教治理技术,而作为独特实践形式为福柯所提出的政治精神性概念,其扮演的或许正是“反基督”(或者说尼采意义上的基督教精神)的角色;若再进一步将其实践范围聚焦于现代生活方面的话,政治精神性或许指向现代新自由主义式治理体系的反面,用诉诸于个体的诸反抗实践来发展出一系列主体塑造自我、进而改变政治话语和形式。由此可以说,政治精神性作为特殊现象来看,是伊朗革命中人民转变自我的精神指导,是一种反抗治理的实践方式(Ghamari-Tabrizi, 2016:108);而作为普遍意义来看,它则是覆盖了政治、伦理和精神性三方面,为个体的治理自我和他人的实践提供了反抗权威、反塑造、认识到自身存在主体意义并加以改变政治话语的精神力量,并且在接下来的政治社会领域里将会不断出现。
作为政治和主体的相互结合,“政治精神性”这个原本的“时政用词”会被赋予新的意义,它随着世界格局与宗教发展动荡而产生时代性变化。不存在“没有精神性的政治”,在面对今天各种暴力与精神对抗的动荡不安的世界时,理解时代中政治精神的意义,以将之引入主体性实践来反思现代治理体系,或许能为当下愈演愈烈的“生命政治”形式国家发掘出不同的思考路线。或者,我们更可从政治精神性的角度思考政治空间中各种价值冲突和韦伯所说的“在这些好战的诸神中间,我们该侍奉哪一位”(韦伯,2010:173)的价值选择问题,以看到在这些斗争中,各种话语主体在不断斗争的过程就是政治真相被不断生产、演进和确立其“真”的过程。福柯将新出现的政治力量当成“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接下来的时代会面临的问题”(Foucault,2005a:209),而不是某种可怕的、激烈的力量——就像“理性”人对待精神错乱者那样。那么至少在面对新的政治情势时,我们是否能去思考,福柯所提供的这种塑造主体进而实践政治的形式,这种具有“反治理”态度的政治精神性是否可能?也许,它能在现代社会找到一条具有一定“合理性”,又能塑造现代人之主体性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阿甘本,吉奥乔.2013. 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 吴冠军, 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高奇琦.2016. 填充与虚无:生命政治的内涵及其扩展[J]. 政治学研究(1):24-33.
韩升. 2008.查尔斯·泰勒的自由观述评[J]. 哲学动态(3):67-73.
蓝江. 2016. 赤裸生命与被生产的肉身: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发凡[J]. 南京社会科学(2):47-55.
勒薇尔, 朱迪特. 2015.福柯思想辞典[M]. 潘培庆,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1843]1972.《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G]//中共中央马·思·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15.
汪俊昌.2003. 泰勒对自由主义的批评[J]. 浙江学刊(6):58-67.
韦伯, 马克斯.2010.学术与政治[M].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冰.2017. 本真性和公共领域:查尔斯·泰勒的自由社会观[J]. 社会37(5):24-58.
Afary, Janet and Kevin B. Anderson. 2005. FoucaultandtheIranianRevolu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aulieu, A. 2010. “Towards a Liberal Utopia: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oucault’s Reporting o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Ethical Turn.” PhilosophyandSocialCriticism36(7):801-818.
Bernauer, J. 2006. “An Uncritical Foucault? Foucault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PhilosophyandSocialCriticism32(6):781-786.
Broyelle, Caudie and Jacques Broyelle. 2005. “What are the Philosophers dreaming about? ” In FoucaultandtheIranianRevolution, edited by J. Afary and Kevin B. Ander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qo Press: 247-250.
Carrette, Jeremy R.(ed.). 1999. ReligionandCulture:MichelFoucault. New York: Routledge.
Carrette, Jerency R. 2000. FoucaultandReligion:SpiritualCorporalityandPoliticalSpiritu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Carrette, Jeremy R. 2013. “Rupture and Transformation: Foucault’s Concept of Spirituality Reconsidered.” FoucaultStudies(15):52-71.
Cook, D. 1987. “The Turn Towards Subjectivity: Michel Foucault’s Legacy.” JournaloftheBritishSocietyforPhenomenology 18(3): 215-225.
Cooper, Melinda. 2014. “The Law of the Household: Foucault, Neoliberalism,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In TheGovernmentofLife:Foucault,BiopoliticsandNeoliberalism, edited by Lemn and Vatter.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Davidson, A.I. 2011. “In Praise of Counter-conduct.” HistoryoftheHumanSciences (24/25): 25-41.
Defert, D.2013. “Chronology.” In ACompaniontoFoucault, edited by C. Falzon, T. O’Leary, and J. Sawicki.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11-83.
Dillon, M. 2017. “Political Spirituality: Parrhesia, Truth and Factical Finitude.” In FoucaultandtheModernInternation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79-96.
Diamond, I. and L. Quinby. 1988. FeminismandFoucault. Boston: Northeast University Press.
Dreyfus,H. and P. Rabinow. 1983. MichelFoucault:BeyondStructuralismandHermeneutics. Brighton: Harvester
Eribon, D.1991. MichelFoucault, translated by Besty W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 1980. “Questions of Geograghy.” In Power/Knowledge:SelectedInterviewsandotherWriting1972-1977, edited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oucault, M. 1983.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MichelFoucault:BeyondStructuralismandHermeneutics, edited by Dreyfus and Rabinow.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8-228.
Foucault, M. 1988a. “Iran: The Spirit of a World Without Spirit.” In Politics,Philosophy,Culture:InterviewsandotherWritings,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etal. New York: Routledge:211-226.
Foucault, M. 1988b. “The Minimalist Self.” in Politics,Philosophy,Culture:InterviewsandotherWritings,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etal. New York: Routledge:3-16.
Foucault, M. 1988c. “Politics and Reason.” In Politics,Philosophy,Culture:InterviewsandotherWritings,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etal. New York: Routledge:57-85.
Foucault, M. 1989. FoucaultLive: Collected Interviews, 1961-1984, edited by Sylvère Lotringer, translated by John Johnston. New York: Semiotext(e).
Foucault, M. 1991. “Questions of Method.” In TheFoucaultEffect, edited by Gordon, Burchell and Mill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73-86.
Foucault, M. 1994a. Ditsetécrits,1954-1988.Vol.3.1976-1979. Daniel Defert and François Ewald, with Jacques Lagrange(eds.). Paris: Gallimard.
Foucault, M. 1994b.“Useless to Revolt?” In EssentialWorksofFoucault:Power, edited by J.D. Faubion. New York : New Press:449-453.
Foucault, M. 1994c. “The Ethics of the Concern for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In EssentialWorksofFoucault:Ethics, edited by J.D. Faubion. New York: New Press: 281-301.
Foucault, M. [1997]2003. SocietymustbeDefended,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Foucault, M. 2005a. “What are the Iranians Dreaming about?”In FoucaultandtheIranianRevolution, edited by J. Afary and Kevin B. Ander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3-209.
Foucault, M. 2005b. “The Shah is a Hundred Years Behind the Times.”In FoucaultandtheIranianRevolution, edited by J. Afary and Kevin B. Anderson: 194-198.
Foucault, M. 2005c. “Iran: The Spirit of a World without Spirit.” In FoucaultandtheIranianRevoution, edited by J.Afary and Kevin B.Ander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50-259.
Foucault, M. 2005d. “Dialogue 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Baqir Parham.” In FoucaultandtheIranianRevoution, edited by J. Afary and Kevin B. Ander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83-189.
Foucault, M. 2005e. “Foucault’s Response to Claudie and Jacques Broyelle.” In FoucaultandtheIranianRevoution, edited by J. Afary and Kevin B. Ander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49-250.
Foucault, M. 2005f. TheHermeneuticsoftheSubject,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Foucault, M. 2007. 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Foucault, M. 2008. TheBirthofBio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Foucault, M. 2009. 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Foucault, M. 2010. TheGovernmentofSelfandOther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Foucault, M.2011. TheCourageoftheTruth,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Foucault, M. 2014. OntheGovernmentoftheLiving,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London : Palgrave Macmillan.
Foucault, M. 2018. Lesaveuxdelachaire. Paris:Gallimard.
Ghamari-Tabrizi, B. 2016. FoucaultinIran:IslamicRevolutionaftertheEnlightenmen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acking, I. 1986. “Making up People.”In ReconstructingIndividualism, edited by T. C. Heller, eta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23.
Honig, B. 2008. “What Foucault Saw at the Revolution: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ology for Politics.” PoliticalTheory 36(2): 301-312.
Lilla, Mark. 2016. TheRecklessMind:IntellectualsinPolitic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Leezenberg, M. 1999. “Power and Political Spirituality: Michel Foucault o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In J. Neubauer. CulturalHistoryAfterFoueault.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63-80.
Lorenzini, D. 2016. “From Counter-Conduct to Critical Attitude: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Quite So Much.” FoucaultStudies(21):7-21.
Macey, D. 2004. MichelFoucault. London: Reaktion Books.
Mascaretti, G. (tran.). 2018. “The Analytic Philosophy of Politics.” FoucaultStudies(24):188-200.
McCall, C. 2008. “Foucault, Iran, and the Question of Religious Revolt.” InternationalStudiesinPhilosophy 40(1): 89-100.
McCall, C. 2008. “Ambivalent Modernities: Foucault’s Iranian Writings Reconsidered.” FoucaultStudies (16): 27-51.
Miller, J. 2000. ThePassionofMichelFoucault,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tton, P. 1989. “ Taylor and Foucault on Power and Freedom.” PoliticalStudies. XXXVII: 260-276.
Rabinow, P. 2013. “Foucault’s Untimely Struggle.” In ACompaniontoFoucault, edited by C. Falzon, T. O’Leary, and J. Sawicki.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189-204.
Ramazanoglu, C.1993. UpAgainstFoucault:ExplorationsofSomeTensionsbetweenFoucaultandFeminism. New York: Routledge.
Rodinson, M. 1993. L’Islam:Politiqueetcroyance. Paris: Fayard.
Said, E. 1988.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In AfterFoucault:HumanisticKnowledge,PostmodernChallengers, edited by Jonathan Arac.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11.
Stauth, G. 1991. “Revolution in Spiritless Times: An Essay on Michel Foucault’s Enquiries into the Iranian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Sociology 6(3): 259-80.
Sung, H. Kim.2004.MaxWeber’sPoliticsofCivilSocie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1984. “ Fouault on Freedom and Truth.” PoliticalTheory 12(2): 152-183.
Taylor, C. 1985. “What’s Wrong with Negative Liberty?”In CollectedPap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D.2013. “Towards a Feminist ‘Politics of Ourselves’.” In ACompaniontoFoucault, edited by C. Falzon, T. O’Leary, and J. Sawicki.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403-419.
Veyne, P. 2010. Foucault:HisThought,HisCharacter,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Cambridge: Polity.
Weber, Max. 1946. FromMaxWeber:Essaysin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ax. 1994. PoliticalWritings, edited by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oucaultinSyracuse:TheSubjectivePracticeinthePoliticalSpirituality
ZHUWencheng
Abstract: “Back from Syracuse?” is a phrase used to satirize an intellectual who unwisely intervenes in political issues. Foucault received multiple denunciations and attacks for his interest i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of Iran in 1978. Foucault’s fascination with the Iranian Revolution is rooted in his inspiration of the politicalspirituality manifested in the Revolution, which in his words, is a “negleted possibility” in the West that “we have forgotten since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great crisis of Christian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ssays and interviews by Foucault during the year of 1978 and afterwards to illustrate that however primafacie it might be, Foucault’s approval of politicalspirituality should not be seen as a “mistake” since it is a reflection of his work on the forms of subjective practices of individuals at the time and subsequently a main topic of his life work. Political Spirituality exhibits two aspects: an outburst of enormous collective will and a force transcending secularity. To Foucault, these two things are powerful weapons to resist against the rational regime of politics in Western societies. Foucault’s open-mindedness to multi-cultural phenomena also contributed to his interest of the Revolution. It is suggested here that Foucault’s reading o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influenced his change of interest from bio-politics in political sphere to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n ethical sphere. His work on the forms of subjective practices follows the same pattern as his work o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starting from how individuals change their forms of subjectivity in modernity. Foucault is not always right, but his insights on politicalspirituality and his claims on Parrhesia from the Stoic remain valuable to this day, for at the very least, they provide an invaluable perspective, if not better, in the sphere of public political discourse.
Keywords: Foucault, Iran, Political Spirituality, bio-politics, subjectivity
*作者:朱雯琤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Author:ZHU Wenc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Southeast University)E-mail:binglanaishang@126.com
本文初稿曾在2018年社会学年会“青年学术论坛”上进行宣读,得到谢立中老师和严飞老师的点评指导,在修改过程中也得到《社会》匿名评审专家详细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路英浩
标签:政治论文; 伊朗论文; 精神论文; 主体论文; 主体性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社会》2019年第3期论文;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