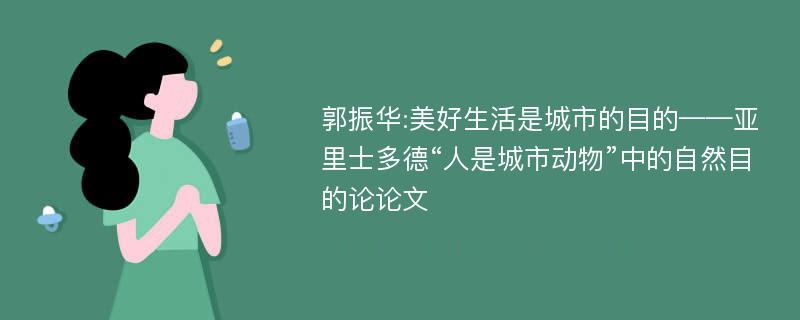
摘要: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一)中提出“人是城市(政治)动物”,这揭示了城市本身的自然目的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城市以成全人的自然潜能、实现人的美好生活为目的。该目的包含竞争发展与平等包容两个维度,并且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个人单靠家庭和村落无法实现美好生活这一目的,必然走向城市;城市比家庭和村落更自然、更能成全人的潜能;人天生是城市动物,人需要成为好市民,使自己的自然潜能在美德之城中得到成全。
关键词:《政治学》; 城市; 美好生活; 美德之城
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城市成为人的重要的生活和生产场所。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也面临很多的需要深思的有关美好生活和城市关系的探讨。对于从乡土社会中发展的中国,城市其实可能意味着更多。从历史和现实看,城市可能比普通的理解具有更多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当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天生是政治动物”[1]10时(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2,亦可译为“[人]自然是城邦/城市动物”。本文中的《政治学》引文以英译本巴克译本为主,部分译文综合参考洛德译本、吴寿彭译本以及颜一、秦典华译本有所调整。,“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一定义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特征”[2]379。 马克思的研究强调了人和城市、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马克思提到的这一定义出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政治学》(Politics)探讨的对象是polis(以下按马克思的解释统称城市),国内相关研究尤其是具有哲学特色的研究和译介也逐渐增加。 亚里士多德探讨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如何管理城市,而在于促进市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因为城市的成长“是出于人类生活的需要,但其实际的存在是为了美好生活”[1]10。古希腊的城邦(polis)往往既是邦国,也是城市,从形态上看,一般是以一座城市(city)为中心、结合周围乡村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我们这里侧重讨论城邦的城市特性,尤其是它的自然目的论特征即城市的目的是美好生活。
一、自然目的论中的城市:人的共同体及其两个维度的对立统一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是一个自然目的论的体系,是在自然合目的意义上的决定论。自然事物的运动并不是随意而盲目的,而是成全自身潜能的实现过程[3]155-200。这一自然目的论不仅适用于其形而上学,而且贯穿于其实践学问。《政治学》作为以研究实践中的至善为目的的学问,开篇即从自然目的论角度探讨城市的意义。其立论为一个标准的三段论:大前提是“所有共同体的建立都是为了追求某种善”;小前提是“所有城市的建立都是共同体的建立”;结论是“所有城市的建立都是为了追求某种善”[1]7。因为人皆以善为目的而行动,而且城市是人所建立的共同体,所以城市的建立作为人的一种行动必然以善为目的。
人的行动基于人性,人性有争高低与求平等两个维度,与之相应,人的行动的目的也在这两个维度上展开。为实现人的目的而建立的城市就是“最高且最广”[1]7的共同体。这里的“最高”不是强调城市作为政治共同体本身的权威、至高无上、从外在让人服从,而是强调内在于城市的良性竞争,能够让人在不同层次、不同高度上以善为原则充分激发自身潜能,实现自身目的,最大程度主动追求和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这里的“最广”指的是对各种不同人的包容,一个都不能掉队,每个人都要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既然我们都是共同体成员,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人人平等。凭借其人性,各种人都允许进入共同体”[4]8。
《政治学》(卷一)的另一个说法,若离开城市,“人要么是兽,要么是神”[1]11,也需要在这两个维度上得到理解。人性在高度上的极致就是超越的神圣性,在广度上的极致就是基本的动物性。神不需要过城市生活,但人不是神;兽没能力过城市生活,但人要活得“异于禽兽”,这是人之为人的底线。因此,从天性上讲,人就不得不过城市生活。
二、美好生活的实现:城市比家庭和村落更能成全人的潜能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早形成的共同体是家庭,然后是村落,最后形成的共同体是城市。只有在城市这种社会共同体中,人类生活才能够“自足”。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自足是幸福的标志。“我们所说的自足是指一事物自身便使得生活值得欲求且无所缺乏,我们认为幸福就是这样的事物”[5]19(2)《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译主要参考廖申白译本,部分参考巴特莱特和柯林斯英译本有所调整。 。幸福就是不但活着(live),而且要活得好(live well),活出美好生活(better life)。美好生活不是为了其他任何目的的手段,美好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亚里士多德还提到家庭中的第三种至关重要的关系,即父子关系:“就一个完整的家庭而论,其最单纯最基本的要素包括主与奴、夫与妇、父与子”[1]16。戴维斯注意到,父子关系是理解为何城市比家庭更自然的关键[4]3-38。首先,父子关系决不能处成主-奴关系,一个只会听父亲话的儿子,永远无法学会自己做主,永远无法活出自己的主体性。但是,父子关系也决不能处成奴-主关系,儿子再长大,父亲再衰弱,儿子也只能做自己的主,决不能把父亲当做奴隶。这也就注定了儿子在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必须走出家庭,走进更大的共同体,活出自己的主体性。比家庭更大的共同体是村落和城市。村落毕竟空间和资源有限,因此个体往往必须走进城市,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从而更好地面对和回馈自己的原生家庭,与原生家庭的家长形成一种主体间性。其次,父子关系也意味着儿子的男女关系必须在家庭之外发展。作为儿子的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除了立业问题,还有成家问题。成家必然意味着走出家庭,必须与家庭直系亲属之外的女性通婚、生育。这是成长中的个体必须走向更大的共同体的第二重原因。个体必须从家庭中独立出来,在村落或城市中去成立自己的家庭。单纯从成家角度看,在村落中和城市中分别不大,但考虑成家立业无法分割,而且好的事业更能促进个体和家庭的美好生活的实现,再加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每个个体再自然不过的愿望,因此,城市是比家庭更“自然”的共同体。
在分析家庭中的个体结合方式时,亚里士多德主要提到两种:一是男女关系,二是主奴关系,“由于男女与主奴这两种关系的结合,首先就组成‘家庭’”[1]9。 亚里士多德特意强调,家庭中的男女关系不是有高低落差的主奴关系,而是自由人之间在广度上的平等关系。野蛮人才不区分女人与奴隶,文明人不会把女人当奴隶看。而主奴关系,更像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的权力关系服从于内在的自然目的论:管理者之为管理者,在于“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被管理者之为被管理者,在于“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1]16。男人与女人作为自由人的平等关系,体现着家庭中的“广度”;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高低关系,体现着家庭中的“高度”。
(一)城市比家庭更“自然”
在追溯城市的起源时,亚里士多德提到三种前城市的结合形式:(1)个体之间的结合;(2)家庭的结合;(3)村落的结合。三者加上城市,构成递进关系:个体间的结合是家庭的前提,家庭的结合是村落的前提,村落的集中结合是城市的前提。
美好生活的实现,单靠个人无法做到。因为作为美好生活标志的自足并不是遗世独立,而是需要家庭关系(如有父母、子女、伴侣),又需要社会关系(如有新朋故友和同城邻里),这些一定程度上都是条件——“人在本性上是城市的”[6]11。《政治学》的目的是“属人的善”,尽管个人和城市都追求这种善,但城市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善的善”[5]6。城市的产生后于个人,但在自然上讲优先于个人。因为个人是城市部分,而整体自然优先于部分。任何个人都无法自足,只有“共同集合于城市整体”[1]11,作为市民的人们才有可能在相互满足需要的意义上获得自足。
(二)城市比村落更“自然”
速冻蔬菜是指加工处置新鲜蔬菜,通过低温使其迅速冻结,且在-18℃环境下贮藏,以实现长期保存的一种方法。其相较于其他加工手段更可以保证新鲜蔬菜原本的色泽、风味与营养价值。
戴笠这次派特务无故搜家,更激起黄炎培的无比愤慨。他想,你戴笠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我这回一定不饶你。不然,特务们以后还要来欺负的。
首先,村落“最自然的形式”往往由一个家庭衍生而成,全体村民可以说是血脉相连。村落里的家族、宗族的血缘关系自然会导致家长式、宗族式的治理方式,这是一种“人治”而非“法治”。戴维斯注意到[4]5,当亚里士多德提及家长式治理方式时,所引用的“人人都给孩子和配偶立法”[1]10这句话出自荷马《奥德赛》。在荷马原诗中,此话用来描述原始村落中圆目巨人库克罗普斯的生活。梅因在《古代法》第五章“原始社会与古代法”中[7]71-72引同样的诗句说明,这种“由于对父辈的服从而结合在一起”的“家族的集合体是”“不进步的文明的典型”。这种宗法集合体的组织原则就是以“家父权”为典型的家庭专制,父对子的权力没有限制,可以严酷惩罚,甚至可以将其杀死[7]78。亚里士多德为城市之前的原始村落描绘了一种可怕到“吃人”的极端情景[8]30-40。由此可见,村落必须集中于城市,城市远远大于个别村落。非血缘关系的市民之间的关系无法单靠村落中的家长式统治来维系,而更需要靠法律来维系[1]9-10。不同于村落中的熟人社会,城市是“陌生人以适合于陌生人的方式的相遇”[9]167。
其次,城市比村落更具备整体性,故城市比作为其部分的村落更能实现社会的有效分工。在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甚少进行物物交换,因此,物物交换一般发生在家庭与家庭之间。由于资源相对匮乏、单一,村落内部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物物交换受到极大限制。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物物交换往往发生在城市的市场上。A村村民擅长打铁,B村村民擅长织布,C村村民擅长种地,D村村民擅长榨油,如此等等,只有在比村落本身更大的共同体即城市中,才能更大限度地进行资源配置和物品交换,从而充分地为共同体成员提供生活必需品[1]22-23。城市比村落更能满足人们的自然需要,是比村落更完美的共同体。
亚里士多德主要从法治和分工两方面对此加以论述。
医疗行业具高风险性,临床风险管理的应用,旨在降低医疗事故差错发生率,为患者提供安全、高效的护理工作。急诊科建立风险管理时,通过识别、评价及处理护理期间可能存在的风险事件,避免护理纠纷发生、经济损失及形象受损[2]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护理缺陷发生率1.67%低于对照组的15.0%,护理质量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说明,风险管理在急诊科护理中应用,可减少护理缺陷事件,提高护理质量,应用效果较高。
三、美德之城:好人与好市民的对立统一
好的市民或者居民,必然形成富有德性的美德之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角度(3)“美德之城”这一提法,可参见田海平:《美德之城的空间正义之维:从城市生命伦理及其‘场域发生’看》,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人们聚集于城市是出于共同的利益,作为市民共同生活,“无论对于作为整体的共同体还是对我们每一个个体而言,最主要的目的都是美好生活”[1]98。 美好生活的前提是美德,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勇敢、节制、正义或者智慧[等美德]”,没有任何人会称他享有美好生活[1]252。“具备了足够的需用的美德以至于能够拥有适合于德性的行为的生活,对于个人和城市共同体而言,才是最美好的生活”[1]253。物质财富作为外在的善,是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美德作为灵魂的善,则是美好生活的充分条件。
于是,在《政治学》(卷三),亚里士多德从美德角度考察“好人”与“好市民”。理论上最好的城市应该完全由最好的人组成,但这并不可能。城市由市民组成并鼓励市民努力成为好市民,通过“做得好”而“过得好”[5]9。好市民强调社会分工、恪尽职守。只要一个人能做好本职工作,“即便不具有一个好人应具有的美德,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市民”[1]91。人的自然差异极广,各位市民不可能完全彼此相同。城市提供的是一个各就其位、各尽其责的空间,以便不同特点、不同天分的人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使自己天性中的潜能得到成全。
通过对参与实验研究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20份,全部回收,回收有效问卷116份,有效率96.7%,具有较高的效度。
9.价值观等方面的认知错乱。多元文化使学生价值观形成多元化,在面对价值观的判断和选择时,统一的标准难以形成,引起在价值观等方面的认知错乱。
好市民的美德与好人的美德不同之处有三。第一,一个城市的全体市民有维护城市安全的共同任务,不受政体影响;但是,不同政治体制对美德的认定不同,同一个城市在不同政体下对好人的认定也不同,因此一个人可能始终是一位好市民却不一定被认为是一位好人[1]91。 第二,不是所有人都能被认定为好人,但每一位市民都可以通过做好本职工作成为好市民;最好的城市不是其中所有人都是好人的城市,而是其中所有人都是好市民的城市[1]91-92。第三,城市由相异的市民构成,而相异的市民不可能具备使之成为好人的相同的德性[1]92。因此,美德之城的建设应重视差异化教育和针对性管理,既树立少数好人模范典型,突出美德和美好生活人人仰望赞叹高度,又做好普及性的市民素质教育,各率其性、各美其美,呈现美德和美好生活人人可以企及的广度。
结 语
亚里士多德基于自然目的论的城市论,是在城市文明形成初期对城市为何兴起的哲学探究。他认为城市的目的是人的美好生活,人天生是城市动物,城市比家庭和村落更“自然”,人的潜能可以在城市中得以成全。虽然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国城市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其关于城市的自然目的以及个人、家庭、村落与城市关系的深入思考,依然能够为我们对当下城市与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反思的方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城市论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作为源初问题的提出和探究,《政治学》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当下以美好生活为目的的城市建设中的具体问题。例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应该更加明确美好生活这一主要目的,同时兼顾这一目的的高度与广度两个维度,促进良性竞争与社会包容的有机结合。亚里士多德的城市论,有助于我们从成全个体潜能的自然目的论意义上理解城市人口扩大的深层原因和进城务工人员的真正诉求。我们的城市应该建设为美德之城,让生活更美好。
参考文献:
[1]Barker, E. Aristotle: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马克思:《资本论》,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李猛:《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义:一个存在的解释》,载《世界哲学》2011年第2期。
[4]戴维斯:《哲学的政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疏证》,郭振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6]Bartlett, R. C. and Collins, S. D., Aristotle’sNicomacheanEth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7]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8]李猛:《自然状态与家庭》,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9]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BetterLifeistheAimoftheCity ——On the Natural Teleology in Aristotle’s Definition of Human Being as “Political Animal” in Politics
GUO Zhen-hua, NorthwestUniversity
Abstract: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better life? In Book I of Politics, Aristotle defines human being as political animal / animal of city. This definition is an exposure of the natural teleology of the c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heory of city in Politics, shows that, a) the city develop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ctualization of human potentiality and better life, b)the two dimensions, height and breadth / competence and equality, of its purpose needs to be in balance, c)the city comes from family and village but is more natural than both of them, d)by making good citizens and good person, the city of virtue actualizes the natural potentiality of most people.
Keywords:Aristotle’sPolitics; polis; better life; city of virtue
作者简介:郭振华,西北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柏拉图《美诺》疏证”(14CZX033)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9-04-10
DOI: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5.08
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9)05-0064-04
责任编辑 吴兰丽
标签:城市论文; 亚里士多德论文; 美好生活论文; 村落论文; 目的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古代哲学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柏拉图《美诺》疏证"; (14CZX033)论文; 西北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