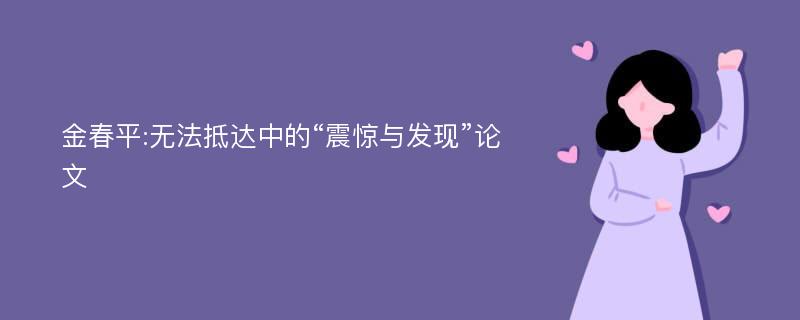
首先,《主观书》重新确立了“写作”之于个人的思想、情感、生命和灵魂的艺术自发性意义。与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的不期而遇,以及灵魂气象的某种相通性,促成了作者持续多年执著于《主观书》系列的抒写与雕刻,这种写作行为本身,构成了一种极具个人实验色彩的语言、文本与创造行为的一种外化表征,在作者写作的预谋、过程、整理与反顾中,其思想经验、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巧妙转化为一位拒绝外在“物”的牵制的灵魂漫游者和精神孤独者,所进行的语言狂欢、词汇恣肆和言说迷幻,这一方面造就了《主观书》作为一种独特文体的开放,包括箴言体的哲思性、现代诗的诗意性、叙述体的虚构性、语录体的自白性、典籍体的训导性等等,由此赋予《主观书》作为一种创造性文体的无限,兼容了诸类文体的思想或美学形态;另一方面,与其将《主观书》视为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文体实验,不如说作者寻找到了一种契合自身的存在底色、生命姿态和艺术气质表达的自由文体,这种自由的写作包含了对自我以及对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多重“解放”,解放了必须恪守某种文类的言说姿态和言说范式的硬性规约,解放了写作对外在事物或时间空间的理性逻辑的依附,解放了对自我乃至一切客体事相的强制确认,感觉主义、未来主义乃至超验主义成为作者支配文字编码的内在逻辑,这是对主体写作的一种高度自信,也是对主观写作的一种深度经营。
其次,《主观书》以极具个人化的灵感、情感性的敏锐、思想性的辩驳、探寻性的深度,将个体精神与灵魂世界的“丰富的真实”予以呈现,从而抵达一种“不断发现”的生命境况。这种“发现”或者聚焦于外在世界的现象、表象、规则等投射于个体感知领域的种种镜像,或者是作为写作者的作者集中于对自我的意绪世界、思想质地和灵魂隐秘的不断开掘、拷问、审视、解剖。于是,《主观书》充满了对自我与自我的多层次对话和激辩,比如,对庸常生命的表象姿态臣服,却暗藏着热烈尖锐的生命热情;某种高度确信的自我构建,却暗藏着一种虚妄的不自觉的质疑乃至解构;对此在的强烈反叛与超越,却暗藏着对未来或彼岸的更深的失望乃至绝望;一种对语言词汇组合与创造的高度信任,却暗藏着的语言词汇无以复现生命经验无限性的无力与焦虑,等等,正是借助于象征、隐喻、虚构、意识流等层面的言说构建,同时赋予语言词汇以“中西文白”形式下的“思想意味”,《主观书》片段式的自白、叙述或训导,特别是其中处处彰显的“自我辩驳”,包括质疑与自信、犹疑与确认、否定与反否定,触及到的不仅是作为个体世界的真实质地,而且往往通达了某种人类存在的普遍性的真实境况,由此,作者发现着一个个被生活逻辑、大众逻辑乃至意识逻辑所遮蔽的情感性的、意识与无意识混杂的、隔绝于外在世界的孤独者自我体验与凝思的“复杂而本体性的真实”,从而完成着一种主观世界自主性的自觉构建。
第三,《主观书》在拓展散文文体表现和汉语语言表达疆域的艺术创造中,将语言本体、言说本体与人之存在本体进行了一体化的勾连与融合,努力抵达对人的内在性的深度、广度、厚度的自然化(意识流)表述,可以说,这是作者对自我作为存在之在的“惯性”的反制,是作者对自我作为情感之人、思考之人、精神之人、灵魂之人的一种回归、追问和确认。《主观书》一系列片段式的言说,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自我或主观的内在性、无限性或丰富性的呈现,那些吉光片羽的诗情或思辨的火花,烛照的正是被外在惯性甚至无意识的内在惯性所掩盖的人之本真、人之本体、人之本性,这种对“主观性”的略带偏执的捍卫与彰显,尽管其中处处充斥着矛盾或悖反性的思想张力,但是,恰恰是其中极其显著的记忆与想象、虚幻与现实、梦幻与哲思、诗情与反省、激情与沉思、逻辑与意绪、秩序与流动等的确定性言说和言说性的解构,构成了多重的话语与声音,这种多重性既彼此支撑与构建,又彼此消解与证伪,但这种独特的话语声音,反复验证着这是一位具有深邃灵魂世界的孤独者的强悍在地(在场),他的精神生活体验、思想先锋体验和生命内在体验,都化为《主观书》当中那些极度精炼雅致而又富有内涵张力的箴言性文字,尽管这个主观言说者处处表达着对这种文字的不信任,但是,正是在对自我作为存在之体的反复洞悉、探求、确定、否定的言说循环或语言编码中,一位诗性的沉思者、一位激情的孤独者、一位不屈的虚无者、一位犹疑的行动者,隐喻出当代人乃至人类性的带有“分裂性”的普遍精神处境和存在境况,而《主观书》在此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硬而冷僻的灵魂独白,而是对后现代语境下人如何确立自我、如何呵护精神圣地、如何构建存在的理由的深刻的人文悲悯和宏广的人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