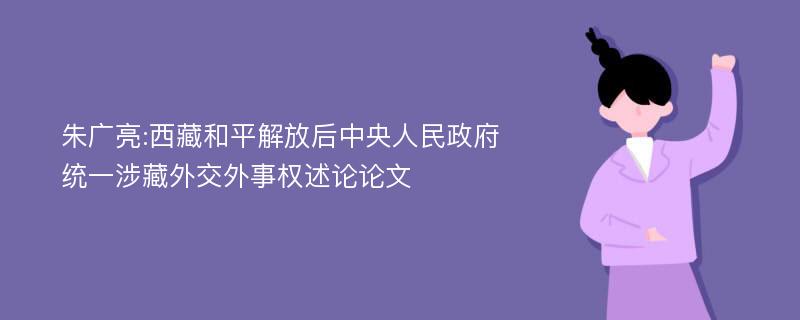
摘 要: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废除印度在藏特权与西藏政治整合相交织,统一涉藏外交外事权也一时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经营西藏和对印外交中的焦点之一。作为同一问题的两面,中央统一涉藏外交外事权,是在与印度协商解决其在藏特权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的,并在“统一对印外交”的实践中逐步实现的。中央将涉藏外交事务纳入正常的中印国家关系轨道,取缔原“西藏外交局”,实现对西藏外交外事权的整合和掌控,不仅对推进治藏战略,而且对建立与印度在西藏地方的新关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西藏外交局”;外交权;历史遗留问题;中印关系
西藏和平解放后,历史遗留的所谓西藏地方外交权并没有因和平解放的实现而随即统一于中央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央),“西藏外交局”一直持续存在,直至1953年中印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前夕才被最终废止。中央在与印度交涉其在藏特权过程中,利用两国协商建立在西藏外交新关系的契机,一方面通过设立中央代表外事帮办“立新”,一方面在对印外交实践中规制“西藏外交局”的活动,“逐步统一、稳步前进”,最终取缔“西藏外交局”,收回西藏地方的外交权,实现对西藏外交外事权的整合和掌控。囿于资料所限原因,学界虽然对该问题进行了一定研究(1)主要论著有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宋月红编著:《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梁俊艳:《历史时期印度、尼泊尔在藏特权及其被废除探析》,《西北民族论丛》第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但属于简略概述,并未综合梳理及阐述。本文根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尝试对中央统一涉藏外交外事权的决策背景及过程加以阐述,以呈现给学界。
一、中印交涉印度在藏特权问题的开启与中央处理西藏涉外问题的政策
历史上,西藏自纳入中国版图以来一直处于中央政府有效行政管辖之下,并无外交权问题。1792年,清王朝在整顿藏政的基础上颁布《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驻藏大臣“总揽事权,主持藏政”,明确西藏地方一切涉外事宜由驻藏大臣全权负责。(2)参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72页;张羽新:《驻藏大臣政治地位和职权的历史考察》,《中国藏学》1998年第2期。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发动两次侵藏战争并制造“西藏问题”后,情况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英国强迫清政府先后签署了一系列条约或协议,攫取了诸如驻军权、商埠权、治外法权在内的一系列特殊权益,确立了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不仅如此,为达到把西藏变为英属印度与中国之间“缓冲区”的目的,英国还炮制“宗主权”理论,宣称西藏在“宗主权”之下享有“特殊地位”,借此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管辖,分裂西藏。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初建,政局动荡,英国借机策划“西藏独立”,而西藏分裂分子在英国的扶持下,明目张胆地谋求“西藏独立”,并采取一系列步骤将“独立”内涵付诸实施。在此背景下,为在外交上分裂中国,英藏勾结制造了所谓西藏地方外交权问题。1913年,英国主导的西姆拉会议召开。为彰显西藏地方的缔约能力,英国坚持西藏以“平等”身份参与中英藏三方会议讨论西藏地位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西藏分裂势力直接提出“西藏独立”和“汉藏划界”的分裂主张,并与英印当局私下缔结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及其附件。尽管会议策划“西藏独立”阴谋因中国坚决反对而以破产告终,但其遗毒贻害至今。20世纪40年代,随着亲英的达扎活佛出任摄政执掌西藏噶厦权力,本已缓和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再度恶化,西藏分裂势力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势头猛增。1942年7月,西藏噶厦在英印势力的唆使下擅自设立“外交局”,函告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称,“今后汉藏间事无巨细,请径向该机关冾办”。鉴于“外交局性质系与外国冾办实践之机关”,噶厦此举是“视中央为外国,示西藏为独立国”(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卷,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2页。,迈开了“西藏独立”的严重步骤。对此,国民政府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和拒绝。然而由于中央统治权威衰落,西藏噶厦并没有因此撤销,仍然存在。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外交局”仍与印度、尼泊尔等国保持直接往来关系。据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1952年调查:“目前西藏外交局……仍有活动。如去年派人去尼泊尔,根据一八五六年藏尼条约进贡一万卢比,有专门人员与尼泊尔在拉萨的代表处联系。汉人、回民去印经由其介绍至印代表处签证,(藏人去印在亚东印代表处登记即可)。在江孜、亚东、噶伦堡有其商务代表,与印方交涉联系等。”(4)参见《中共中央就同意印度在拉萨设领事馆事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来往电》(1952年2月26日—1952年9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5。
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中央统一涉藏外交外事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基本任务之一。在标志西藏和平解放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中,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关系,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睦邻和平共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5)《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人民日报》1951年5月28日。概言之,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管理外交事务的主张是“中央统一对外”。“十七条协议”系当代历史上决定西藏主权地位的指导性文件,据此,中央将处理西藏地方涉外问题的指导原则从法律层面确定下来。
如何将“中央统一对外”加以实施,以实现西藏对外关系从不正常状态到正常状态的转变呢?据杨公素回忆,当时去西藏执行任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收回外交权;二、取消外国特权;三、建立与邻国正常的关系。但由于“西藏长期与中央及内地隔绝”,中央工作人员同解放军入藏后主要任务是与西藏分裂分子作公开斗争,集中力量谋求在西藏站稳脚跟,因此执行“中央统一对外”的规定并没有立即提上日程。(6)参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198页。然而,随着印度正式提出通过商谈解决其在藏权益问题,中央统一涉藏外交外事权揭开了序幕。
对于中国解放西藏,印度曾持反对的态度,但干涉失败后印度调整了对藏政策,争取维持其在藏权益成为外交主攻方向。1952年2月11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会谈。会谈中,潘尼迦在表示承认西藏现状后提出:印度在西藏有“权益”,表现为“在拉萨有使团,在其它地方有商业机关以及为保护这些机关而所有的措施”等七点,希望“通过交谈来保护双方的利益”。(7)参见《章汉夫副外长与印度大使潘尼迦就印度在西藏利益问题的谈话记录》(1952年2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1。对此,中方表示加以研究,未即答复。
事实上,此次会谈后,中央即把解决印度在藏特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前期准备工作从两个方面开始进行:一是明确指导思想和原则;二是开始调查研究,弄清印度在藏特权现状。2月26日,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和驻印度使馆对印度在西藏的各种特权进行研究。(8)《中共中央就同意印度在拉萨设领事馆事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来往电》(1952年2月26日—1952年9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5。在电文中,中央首先阐述了对待印度与西藏的外交、文化和商业关系的态度:“准备在将来经过谈判全盘解决”,但强调须在具备“解放军到达西藏南部边境,西藏军政委员会成立并公开设立外事机构而且了解和研究了当地的外交及其历史的情况”这些条件后“才能开始这种谈判”。关于处理上述关系的原则,中央指出:“准备关于印度侨民问题,同意在西藏设一总领事馆;印度在藏驻军及其他特权必须全部取消,只对于正当商业关系允予保留。至于朝圣问题,因涉及长期宗教关系,须研究后,方能提出意见。”这一指导性意见的提出,表明了中央已经初步形成拆解印度在藏特权的思路,即通过“设领”(设立领事馆的简称)首先解决代表权问题。然而,这一思路只是中央作出的初步考虑,是否符合西藏的形势,如何具体化,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因此,电文最后,中央指示:“切实了解情况报告中央,并对上述问题提出你们的处理意见。”
人工智能会吓到许多人,因为他们不相信它会听话。科幻小说中都认为计算机或机器人产生意识的可能性很大,不久之后就会试图杀死所有人类。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人工智能会变得更聪明而发展出意识。相反,我们应该担忧人工智能对人类主人的绝对服从而非反抗。人工智能与人类开发的任何其他工具和武器都不同;它会使得强者进一步巩固其权力。
在充分参考西藏工委意见,并与驻印大使袁仲贤反复商量之后,中央形成了关于西藏外事机构及印度“设领”问题的决策方案。从6月8日周恩来指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的电报看,方案包括三点内容。一是“拟先解决设领问题”。电报中说:中央认为,基于西藏形势,印度在西藏的权益问题“不宜作全面解决”,但考虑到“与印度通商的实际需要起见,并为安印度之心”,可“允许印度在拉萨设立总领事馆,换取我方在孟买设立总领事馆”,以此作为解决印度在藏权益的第一步,而其他各项问题,“仍然作为悬案,等待情形弄明,准备好了之后,再逐步解决”。二是设置外事帮办。中央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下,设一外事帮办,作为我代表处理外事问题的助手,即行定名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外事帮办,以杨公素担任之”。中央强调,外事帮办的设置,“事前应与阿沛商量,并通知达赖,然后公开宣布,公开对外”,其目标是“将西藏地区涉外事宜逐步收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三是“关于西藏政府外事局问题,目前仍然采取原封不动的方针,但应逐渐停止其活动”。(10)《中共中央就同意印度在拉萨设领事馆事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来往电》(1952年2月26日—1952年9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5。以上三点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中央处理西藏涉外问题的逻辑。6月12日,西藏工委复电,对此表示拥护。
另一方面就是理顺西藏与印度错综复杂的关系,谋划落实“统一对印外交”方针。9月11日,西藏工委就西藏涉外新形势向外交部提出建议,关键内容有两点:(一)公开外事帮办办公地点。工委指出,“目前杨公素协助张代表(即张经武)与沈书美洽商接待等,皆临时借用原十八军部会客厅。这在将来处理经常对外工作时,是不妥当的。印既设立总领事馆,我必须有一外事机构,始能正常进行工作。”因此,请示可否将外事处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名义公开,并刻一临时印鉴。(二)统一外交。工委表示,“现既已改印代表处为领事馆,则已表明印藏旧的关系在形式上已不存在,今后应由我中央统一处理对印事宜,中印在西藏的关系,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西藏地方政府过去单独与印代表处交往的情况理应停止,今后印总领事若需要与西藏地方政府交往接洽,及西藏地方政府有事须与印总领事交往接洽时,均必须通过中央政府代表外事帮办办理。这在逐渐执行和平协议办法第十四条及逐渐收回外交权上是应该的,必须的。”关于此点,工委报告还说,将先由张代表与阿沛商妥后,再正式通知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噶厦。9月14日,外交部复电西藏工委,对工委的第一条建议表示同意,对第二条建议则指示:可商谈,但“应审慎进行”。(20)《中共中央就同意印度在拉萨设领事馆事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来往电》(1952年2月26日—1952年9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5。
中央首先考虑的是说服西藏噶厦接受“设领”带来的西藏涉外局面新变化。前已述及,西藏工委曾于6月12日向中央表示拥护印度在拉萨“设领”的决策,但同时指出:“根据西藏过去历史,在形式上不轻易允许外人常住拉萨,而我反允许其正式设领事馆,恐易引起坏分子之挑拨”,因此建议“有步骤地取消印方在藏某些权益,作为西藏方面实际取得之利益,及奠定中央之威信”,具体为解决印度在江孜、亚东的驻军和商务代理处问题。(13)《中共中央就同意印度在拉萨设领事馆事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来往电》(1952年2月26日—1952年9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5。虽然西藏工委的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但关于“设领”弊端的考虑仍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因此,在印度8月2日提出“同时宣布设领”建议之后,8月9日,周恩来电告张经武:“中央考虑在宣布前,仍应转告达赖及噶厦,较为妥当。望你接电后即与阿沛商量,加以布置,然后再找达赖,并正式通知噶厦。”通知的主要内容为两点:一是说明中央筹谋解决印度在藏特权的“一个原则”和“逐步解决”的办法,指明“这种改变是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的”;二是提出“此后我国与印度在西藏凡涉及通商、侨务事宜,即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外事帮办与印度驻拉萨总领事办理,凡涉及两国外交事宜仍统一在北京或新德里经过外交部与大使馆办理”,即“统一对印外交”。(14)《中共中央就同意印度在拉萨设领事馆事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来往电》(1952年2月26日—1952年9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5。然而,当8月14日西藏工委副书记兼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通知达赖时,达赖对于“设领”表示拥护,对中央将采取措施逐步结束印度在藏旧关系,废除不平等条约表示感谢,但对“统一对印外交”问题态度暧昧,不置可否。(15)《中共中央就同意印度在拉萨设领事馆事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来往电》(1952年2月26日—1952年9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5。
二、“统一对印外交”方针的提出与西藏噶厦的态度
中印达成“设领”方案的微妙在于,意味印度“破天荒第一次取得在拉萨建立一个常设领事馆的权利”。(12)卡.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因此,两国均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以应对“设领”时刻的到来。
综上所述,中印交涉印度在藏权益问题之进程的开启,将结束两国在西藏之旧关系提了出来,同时也将如何建立两国在西藏之正式外交商务关系提了出来。随着“设领”方案的达成,中央需要对统一涉藏外交外事权作出安排,“统一对印外交”方针旋即被提了出来。
此时,印度为促成其驻拉萨代表处向总领事馆的转变,可谓煞费苦心,相关人事安排及维持代表处的延续性在有条不紊地运作。7月9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报告称: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已任命前上海总领事雁谒森为驻拉萨印度代表团负责人,以代替现驻拉萨代表沈书美。8月7日,雁谒森即离开德里赴拉萨。(16)《关于前印度驻沪总领事雁谒森代替沈书美驻拉萨的来往电》(1952年7月9日—1952年9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26-02。从时间上看,这一情况反映出印度的迫切心情。印度为何如此迫切?那就是印度想在雁谒森的“身份”问题上作文章,中印之间几次相关交涉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早在7月17日高尔代办与陈家康司长会谈时,高尔就表示,雁谒森将于8月中旬至拉萨,并强调“他是去接替沈先生,并不是任总领事。将来他可以担任总领事。”对此,陈家康当即向其表明中方不承认旧关系的立场。至8月29日,何英副司长约见高尔代办,向其正式表示中方同意印方提出的“同时宣布设领”建议,并希望与印方商讨宣布日期时,高尔的答复耐人寻味。他表示,“印度政府所关心的不是何时宣布设领,而是何时设领”,并称“在中国政府未作好一切准备在孟买设领前,他(雁谒森)仍要去,不过是去接替沈书美先生。”至于会谈中何英提出的9月10日双方同时宣布设领的建议,高尔则表示报本国政府请示后再告,但此后印度并未就此及时答复。(17)《关于中国与印度互设领事馆的谈话记录》(1952年7月17日—1952年9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4。而9月4日,沈书美则向西藏方面透露:“印度派驻拉萨新代表雁谒森已于三日抵江孜。九月四日由江孜动身来拉萨,估计九月八日可到。”(18)《中共中央就同意印度在拉萨设领事馆事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来往电》(1952年2月26日—1952年9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5。不难看出,上述印度的一系列周密安排显然有目的,那就是造成既定事实,赋予雁谒森“新代表”身份。9月10日雁谒森抵达拉萨。
在接到中央的指示电后,西藏工委立即进行调查研究,于3月24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印度在西藏现在占有之权益情形”报告。报告具体列出印度在藏权益的内容,包括印度驻藏代表情况、印商情况、朝圣情况、邮电情况、兵营房地台站等五项,并针对性地提出七点处理意见。总体说来,这七点意见是面向“谈判解决”提出的,具有全盘解决的倾向。其中对于印度驻藏代表的“代表权”问题,西藏工委同意允许印度在拉萨“设领”之意见,同时建议“在印度孟买增设一总领事馆,噶伦堡设一领事馆”。而对江孜、亚东及噶大克之商务代表,则建议“一律取消”。(9)《报中央转部关于印度在西藏现在占有之权益情形》(1952年3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53-05。至此,关于“设领”问题,中央与西藏工委的意见达成一致,并进一步延展为“互设领事馆”。
与此同时,“印度驻拉萨外交代表沈书美本着印代表处继承英帝遗留的旧关系,较为活跃,经常请客,赠送书报及其它方式等从事各种活动”,政治影响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为使有关西藏的外交事务步入正常的中印国家关系轨道,中国做了两方面的应对工作。一方面,加紧与印度商谈“同时宣布设领”,既而明确雁谒森的身份。最终,双方商定9月15日发表公报宣布互设总领事馆,而西藏将按总领事接待雁谒森。(19)《关于前印度驻沪总领事雁谒森代替沈书美驻拉萨的来往电》(1952年7月9日—1952年9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26-02。
在此基础上,6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举行会谈,答复中国关于印度在藏权益问题的意见。会谈中,周恩来首先向潘尼迦说明了一个原则,即不承认旧中国与英国所订的有关西藏的条约,不承认由此产生的特权,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接着,周恩来告诉潘尼迦:中国决定“允许印度在拉萨设立总领事馆,与我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外事帮办发生正式外交商务关系,作为解决中印在西藏关系的第一个步骤……等到印度在拉萨设立总领事馆之后,就可逐步解决其他问题。”同时,周恩来向潘尼迦提出中国在印度孟买设立总领事馆的要求。对此,潘尼迦表示报告本国政府。6月23日,“印度代办高尔向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口头转达印度政府意见,赞同我方建议”。8月2日,“高尔又向陈家康司长面交备忘录一件,用书面再次表示同意双方各在拉萨和孟买设立总领事馆,并准备派遣中印建交后曾任上海总领事的雁谒森为驻拉萨总领事。同时表示,印度政府愿与中国政府同时宣布设领事。”(11)《周恩来外长与印度大使潘尼迦就西藏问题的谈话记录》(1952年6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2;《中共中央就同意印度在拉萨设领事馆事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来往电》(1952年2月26日—1952年9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5。以此为标志,中印交涉印度在藏权益问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3.愚昧麻木的犹大庸众戏弄耶稣,称他是“世界的王”,实际表达的意思却是:耶稣是一个十足的疯子!面对这群愚昧而残忍的庸众,耶稣心里有的只是悲悯。他发声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那群庸众根本就不懂耶稣的话意;夏瑜向愚昧的庸众宣传说“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结果,庸众们众口一词,认为夏瑜是疯了。阿义打了他耳光,夏瑜却对他说“可怜可怜”,同样,晚清的这群愚昧麻木的庸众根本就不懂夏瑜的“可怜”的含义。
1952年10月25日,中国外交部指示西藏工委:“中央准备继续与印方谈判印度在西藏有待解决的问题,望你处收集材料,对各个问题详加研究,分别提出处理意见,尽早报告中央。”(22)《关于印度驻藏新总领事雁谒森来拉萨后有关情况的来往电》(1952年9月22日—1952年10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26-03。以此为标志,中央开始考虑并着手准备全盘解决中印两国在西藏的关系问题。而此时,印度为了维持其旧有特权,试图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维持旧例,迫使中国承认其过去之特权地位,由此引发中印双方之间激烈的“维护主权”与“维持特权”之博弈。在此背景下中央加快了统一西藏外交外事权的步伐。
9月底,在与阿沛、夏苏两噶伦就“统一对印外交”问题进行商谈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张经武召集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全体五噶伦进行了座谈。张经武首先解释了中央外交政策,说明西藏地方要结束与印度的旧关系,建立新关系,希望内部团结,统一对外。接着外事帮办杨公素介绍了印度驻拉萨总领馆的性质、职务以及其执行任务时允许做与不允许做的活动等。对于“统一对印领馆行动”问题,杨公素提出三点请噶厦考虑:“(一)原噶厦派与旧代表处联系之联络员可否参加到中央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并在外事帮办领导下工作。(二)原噶厦外交局有关对印交涉来往事件,可否移交外事帮办办公室办理,原外交局办理这些工作的人员选择优秀者参加外事帮办处并在其领导下工作。(三)在印已设总领事馆,中央代表已设外事帮办的情况下,为了通商来往便利,我们准备建议中央统一由外事帮办处发给护照事,请对此提出意见。”(21)《西藏地方政府对印度在拉萨设领事馆等事应持态度问题》(1952年11月7日—1952年11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6。对于张经武和杨公素在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西藏噶厦地方政府虽然表示考虑后再答复,但却拖延下来。究其原因,客观上是因为国庆节和西藏的林卡节延缓了答复时间,主观上则反映出西藏噶厦在“外交局”人事和职权问题上的权衡和摇摆。
稳定流模拟的河道边界条件为1981年最大流量和平均流量,初始条件为河道比降。非稳定流模拟的河道边界条件为1981年至1982年逐月流量,初始条件为河道基流。根据稳定流模拟所得水深和流速情况调整模型几何数据并进行保存。建立非稳定流模型时,运用稳定流模拟中调整过的几何数据再现河道情况。模型所用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见表1。
三、中印外交博弈与外交权完全收归中央
不同软件土方量计算分析及特殊地形地貌土方量的计算方法探讨……………………………………………… 薛德君,李富荣(6-16)
印度在赴印商人护照问题上的阻难,成为影响中央统一西藏外交外事权的重要因素。每年10月、11月为藏印通商旺季,大批藏、汉商人赴印贸易。依据旧例,西藏商人入印只需持有“西藏外交局”之执照,而西康及其他地区商人则需要取得“西藏外交局”路条始可通行。印度在拉萨设领后,外事帮办办公室对这一旧例进行了修正,加强签证管理,统一发护照。这一举措得到西藏噶厦的配合,并“准备派人参加办理”。然而,印度对此极尽挑拨之能事,一方面表示维持旧例,但在实际入境时多方阻难,并且拒绝给持有外事帮办办公室所发护照的藏商签证。(23)参见《关于印度在西藏特权问题简述》(1953年12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53-02。鉴于藏印贸易的重要性,西藏噶厦不得不与西藏工委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前文述及的关于“统一对印外交”的意见答复也无法再拖延下去。于是,11月6日,西藏噶厦、译仓、孜康各官员与张经武代表会谈时,就“统一对印外交”问题提出书面答复七点,主要为:西藏未承认旧印(英)代表处及其在藏的权益;旧印(英)代表处在时只供应柴火、马匹、乌拉,并由其给付(极)少代价;赞成中央采取逐步解决印度在藏不合理情况的办法;有关外事,中央地方应团结合作很好,同意中央统一规定的办法;希望中央收复印度占去失地,如门达旺;原“外交局”局长索康已死,由另一负责人柳霞参加外事帮办处工作;很多商人需要赴印经商,可否由原“外交局”发给执照。(24)《西藏地方政府对印度在拉萨设领事馆等事应持态度问题》(1952年11月7日—1952年11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6。
在西藏工委看来,噶厦的答复除表示过去与印(英)代表处无特别关系外,还有复杂的含义。工委认为,噶厦“强调要求收复失地,即门达旺”,一方面是想“以此为对付中央统一外交权之难题”;同时,鉴于过去几次谈话中均提过,也说明“此确为西藏对外重要的,并为若干人关心之问题”。而“在外交局人员参加外事帮办处工作问题上,其称是在合办对外事宜,故提出柳霞参加问题。看我态度,再决定其余人员及其他问题。”鉴于此,西藏工委没有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把“统一对印外交”与即将开始的中印“西藏问题”谈判联系起来,整体进行考虑,为此向外交部就中印谈判亟需解决问题作了详细的处理意见报告,包括签证、统一对印外交、收复失地及印驻兵等10项内容。其中,报告特别强调:“印现驻藏之护商队必须撤退,此事解决,对我在藏之影响与威信极大,并将为完全收回外交权打下极好基础。”至于“西藏外交局”的处理问题,西藏工委认为,“虽然彼等有合办涉外事宜,而非如协议之中央统一办理之精神,但我们在目前情况合在一起,在中央领导下,比任其单独活动要好”,因此“第一步做到人事合在一起”,具体为:柳霞参加中央代表外事帮办处工作,可用副帮办或外事帮办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名义;吉甫给以副科长或秘书名义;其他人员经审查后按级给以名义;死去索康之缺额可不补上。对此,外交部研究后,于11月25日电示四点意见:(一)关于西藏“外交局”的处理问题。鉴于西藏目前具体情况,对收回西藏外交权统一于中央问题,“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过渡统一办法”。“西藏外交局与外事帮办办公室名称,暂仍并存。对外交局的人员,采取全部包下来,不加裁撤,照常供职的办法。其外交局副局长可兼任副帮办,吉甫巴可任副帮办助理或秘书,并与外事帮办合署办公。”以此掌握对外事务,并打下完全收回外交权的基础。(二)关于出入境签证问题。“除我方与印方官员出入境必须经我外事帮办发给签证外,一般来往人等(包括藏、康、汉等族人入印)仍沿用旧例,维持原状,由外交局办理,作为过渡时期的办法,暂不严格限制。”(三)“关于统一对印领行动问题:因西藏长期受英印侵略,受英印影响也深,西藏与印度的现有关系一时难以完全扭转,将门关死,应采取耐心解释,慢慢协商,逐步统一,稳步前进的原则,不宜操之过急。”(四)“关于西藏噶伦提出要我解决印藏条约及印在藏之驻兵及门达旺等重大外交问题,可请其供给充分有关材料,并告其报告中央研究处理。”(25)《西藏地方政府对印度在拉萨设领事馆等事应持态度问题》(1952年11月7日—1952年11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25-06。不难看出,外交部在处理西藏地方涉外事宜及“外交局”问题上是持谨慎态度的,除了使用中央机构名义、实行人事合并之外,其它方面都是采取“暂维现状”的办法。
但是,随着印度试图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维持旧例引发中印交涉不断,“暂维现状”办法因形势变化而发生改变,并成为中印外交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1953年4月21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雁谒森向杨公素提出,印度驻锡金专员卡布尔将于本年7月间来亚东、江孜巡视印度驻各地机关,并谓“此次前来系按照旧例”。(26)《外事处关于印度驻锡金专员卡布尔来亚东、江孜巡视的请示电》(1953年4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14-01。接着,5月8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彭巴副领事告知西藏外事处称,印度驻江孜、亚东之卫队,将按旧例换防。(27)《关于印度驻亚东、江孜卫队换防的请示电》(1953年5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14-03。与此同时,据中共阿里分工委报告:印度商务代表团一行十余人携两部电台于6月下旬进入阿里区,为便于前往目的地,该印商代表团还自行向沿线藏民发出通知,命藏民准备毛牛、马匹。(28)《关于西藏外事处对印度商务代表团来阿里区处理意见》(1953年8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15-04。鉴于前两事比较具有代表性,本文将以此为案例来展现中印外交斗争的特征,至于阿里印度商务代表团事将另文论述。
对于卡布尔来藏巡视和印兵换防两事,中国政府认为,“均系表示印度方面有意迫我承认其过去特权地位。在西藏贵族面前显示威风,以便增加我对内对外之困难”,因此必须表明中国不承认的态度。中国外交部指示驻印度大使馆告知印方:“这两个问题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拿印度驻在中国西藏地方的武装卫队问题来说,这不是一个普遍问题。这是一个有关我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中印两国都是独立国家,中国的立场应为印度政府所理解。”因此,“如果印度政府提出撤退印度政府驻在亚东、江孜的武装卫队,作为解决中国与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的一个步骤,这是中国政府所欢迎的。如果印度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尚需一些时间,我们也不反对,但对换防办法则中国政府不便同意。”关于“卡布尔先生前来视察印方驿站,只能当作一种临时性的视察行为,他不是旧例的沿用”,因为“这种旧例”是“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基于不平等关系而产生的特权。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有鉴于此,“现在我国政府已指示我馆给卡布尔先生签证。如果卡布尔先生持有外交护照,我国政府按照外交人员身份待遇。”(29)《外交部就印度驻锡金专员卡布尔来藏及印兵换防问题复我驻印大使袁仲贤的电文》(1953年8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14-14。8月24日,中国驻印大使馆申健参赞向印外交部联合秘书高尔申明了上述立场。
10月15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开馆,宣告印度继承自英国驻拉萨代表处之历史的终结。这样,印度在拉萨设领之前,虽然中央提出的“统一对印外交”方针因西藏噶厦的态度有所保留而未能尽快落实,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和推动还是对西藏噶厦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和影响。只要西藏噶厦接受西藏外交格局的新变化,势必就会接受中央设计的路线。这种现实,就为中央在对印外交实践中统一涉藏外交外事权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文献[21]的研究表明,掘进机机身偏转角改变引起光靶特征点对应图像之间的距离改变与特征点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与光靶和摄像机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反映了检测系统的灵敏度并决定检测系统的精度。
国家层面的交涉得到西藏噶厦的配合。早在7月24日,印总领事馆曾就卡布尔来江孜、亚东事致信张经武要求给予便利,同时亦向噶厦发出了通知,但据阿沛与张经武谈,噶厦“因涉外事宜须由中央统一处理,已将雁信退回”。(30)《西藏外事处就印度驻锡金专员卡布尔来江孜事的请示电》(1953年8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14-12。不仅如此,噶厦在柳霞的建议下还立即采取了实际行动阻止印方人员来藏出行。在柳霞看来,如果雇不到牲口则卡布尔来藏将不能成行,因此建议“假若印方不向中央外交部提出而自行前来时,噶厦政府将通知邦(达养)壁在亚康之管家,以为奉噶厦指示为词不予雇牲口”,并表示“准备与噶厦谈后即发电与邦达养壁之管家”。(31)《西藏工委关于印度驻锡金专员卡布尔来亚东事的请示电》(1953年8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14-15。事实证明,停止向印方提供出行便利,成为阻止卡布尔来藏、印兵换防的一个重要因素,效果突出。据西藏外事处8月26日报外交部的电文得知:“印兵已到亚东五十余人,因藏方未予雇牲口(此系经我与柳霞谈妥,经噶厦下令卡布尔来及印兵换防未得指示不许为其雇牲口)不能去江孜。”(32)《西藏外事处对印兵自行换防处理意见的请示电》(1953年8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14-23。据9月4日西藏军区报称:卡布尔托病往岗多缓来(估计不一定来了),而已抵亚东之印兵则因雇不到牲口而被阻于亚东,仍未前进。(33)《西藏军区就亚东印兵营情况电告西南军区并中央军委》(1953年9月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14-33。
西藏噶厦在配合中央对印外交斗争过程中的态度和表现,表明收回西藏外交权的时机已成熟。中央由此加紧了整合西藏外交的步伐,任命柳霞为外事副帮办;9月初,西藏噶厦设立的“外交局”正式并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至此,中央政府从机构层面上实现了对西藏外交外事权之统合。(34)关于“西藏外交局”撤销的时间,据杨公素先生回忆,是在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后噶厦同意撤销,参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第200页。本文根据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的相关间接资料推断:中央任命柳霞为外事副帮办至迟为1953年8月13日;“西藏外交局”并入外事帮办办公室的日期至迟为1953年9月15日,因无法确定具体日期,故采用9月初这一模糊说法。参见《西藏工委关于印度驻锡金专员卡布尔来亚东事的请示电》(1953年8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14-15;《西藏外事处与外交部关于西藏商人入印护照问题的往来电报》(1953年9月15日—1954年1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8-00311-01。
结 语
对中央人民政府而言,解决“西藏问题”,在西藏地方建立完全、完整与独立、统一的主权,是其成立之初面临的一项历史使命。“西藏问题”的解决,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结束西藏地方政府与旧中央政府的“不正常关系”;二是要结束外国势力(主要是印度)与西藏地方的“特殊关系”,废除印度在西藏地方的特权。而中央对西藏外交外事权的统合刚好处于这两大要项的枢纽位置,其决策与实际运作,不仅事关西藏政治整合的成效,也影响清除印度在西藏地方之特权的速度与幅度。
道德,是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一个体现,道德也是衡量我们自身行为的一个标尺。纵观目前的社会,无德之人不在少数。屡次出现的幼儿园虐童事件、教师体罚学生的事件,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我们的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培养出这些残忍无情的人呢?
中央统一西藏外交外事权过程中所触及的“西藏外交局”问题,是具有相当复杂含义和影响的历史遗留问题。1942年英国唆使西藏噶厦成立“外交局”,其目的是展现西藏“独立国”的面貌,因此,一定意义上说,它是英国(印度)与中国争夺对西藏主权与治权之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也是西藏分裂势力与中央政府渐行渐远的极为严重的步骤,更是谋求“西藏独立”的象征性符号。因此,废除“西藏外交局”的政治意义重大:沉重打击了西藏分裂主义势力,达到了肃清帝国主义在西藏残余影响之目的,从而丰富了解放西藏的内涵。
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决定承认西藏现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但并不意味着印度会放弃在西藏的权益和影响力。印度的策略是:一方面要“大方地放弃所有无法得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坚持更带根本性且不必一定有条约作依据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35)B.N.Mullick,MyYearswithNehru:TheChineseBetrayal,Bombay:Allied Publishers,1971,p.147.因此,印度的“维持特权”与中国的“维护主权”形成了博弈的局面。这客观上推动了中央对西藏外交外事权的整合,并成为西藏噶厦接受中央“统一对印外交”方针的潜在因素,因为在解决英藏旧约、印度攫取西藏利益等方面双方的目标是共同的。在这种态势下,印度维持英国在藏旧有特权屡屡受挫。为此,1953年9月2日,尼赫鲁总理就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向周恩来总理致电表示:两国政府应尽早就此进行谈判。(36)《印度总理尼赫鲁关于西藏问题的来信》(1953年9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32-01。同年12月31日至1954年4月29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关系问题的谈判在北京举行,历时4个月。经过激烈的谈判,最终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互换照会一份。“协定和换文清除了过去英国侵略我国西藏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特权的痕迹,如在我西藏境内驻扎卫队、经营邮电、驿站等,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确定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及便利两国人民的互相朝圣和往来的各项办法。”(37)《章汉夫副外长就中印关系问题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谈话记录》(1953年10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32-05。中印在西藏地方的旧关系得以废止,新关系在协商的基础上确立起来。
无独有偶。前不久浙江湖州有位农民在做红烧肉时误将包装设计酷似饮料的一瓶百草枯当成调料,结果这锅“百草枯红烧肉”将一家三口人都送进了医院救治。应该说,百草枯的功效与它的包装无关,然而这些“非功能性缺陷”却直接导致该产品面临着极大的市场挑战和品牌危机。
OnUnifiedAuthorityoftheCentralPeople’sGovernmentoverTibet-relatedForeignAffairsafterthePeacefulLiberation
ZHU Guang-liang
(School of Marxism,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232001,China)
Abstract:Early in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rescinding Indian privileges were mingled with political integration,the unification of Tibet-related foreign affairs had also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n how to govern Tibet well and its diplomacy with Indian for a while.As the other side of the same issue,the central government’s unified authority over Tibet-related foreign affairs developed gradually in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ng with India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issues of its privileges in Tibet.which was realized progressively in the practice of “unified diplomacy with India”.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put Tibet-related foreign affairs on the track of normal Sino-India relations;and with the former “Tibet Foreign Bureau”abolished,the integration and control of power in Tibet’s foreign affairs was achieved.The event had a profound impact not only on the strategy of advancing the governance of Tibet,but also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relations with India in Tibet.
Keywords:“Tibet Foreign Bureau”;power of diplomacy;historical issues;Sino-India relations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9)06-0107-09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中国清除印度‘在藏特权’的历史梳理及经验研究”(16YJA770018)、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新中国废除印度‘在藏特权’史”(gxyqZD2017042)、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中国废除印度‘在藏特权’的历史及其经验研究”(SK2016A029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广亮(1977- ),男,江苏新沂人,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标签:西藏论文; 印度论文; 外交论文; 拉萨论文; 中央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论文; 《安徽史学》2019年第6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中国清除印度‘在藏特权’的历史梳理及经验研究”(16YJA770018)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新中国废除印度‘在藏特权’史”(gxyq ZD2017042)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中国废除印度‘在藏特权’的历史及其经验研究”(SK2016A0298)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安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