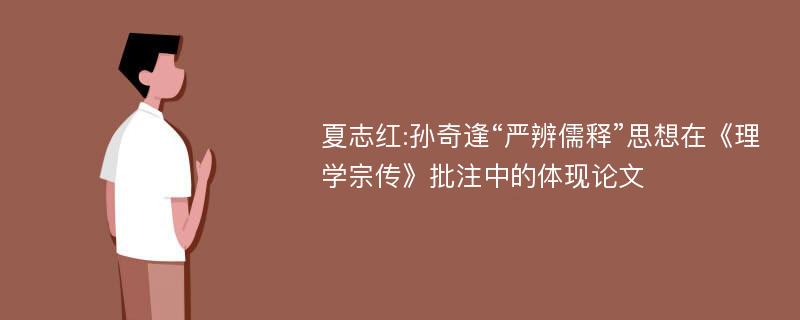
摘要: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向来众说纷纭,《理学宗传》可谓其晚年定论。该书本主辅内外之原则,对自董仲舒以迄周汝登等汉唐宋明之170位儒者,先作评传,次辑录其所著或语录,于眉端或段落中施批注,最后给出学行总评。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孙氏自身的学术立场,他试图通过“严辨儒释”实现归宗孔孟的学术志向。
关键词:《理学宗传》;批注;孙奇逢;严辨儒释
《理学宗传》为孙奇逢平生大著作,稿经三易,年逾三十,孙氏自序说:“此编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与偕者,逾三十年矣。”[1]16最后于康熙五年(1666)成书。孙氏视《理学宗传》的成书为第一快事,日夕玩味,胜过一切,他寄书长子立雅说:“自端午抵夏峰,四阅月,日夕与博雅料理《宗传》,日前始就。思录一清本,出入携带。此是老夫饥食渴饮第一快事。”[2]1048“近年功课,料理《宗传》一编,共得百四十余人,有主有辅,有内有外,人人有悦心自得之处。日夕玩味,觉无物可以胜此。”[2]1054-1055可见珍视重视之程度。孙氏弟子汤斌在序《理学宗传》时说:“盖五经四书之后,吾儒传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见于此。”[1]12张沐序也说:“盖八十年中,下学上达,有不可以告诸人,人亦终不得而知者,悉著此。”[1]13两人都把《宗传》看成是孙氏学说的晚年定论。
《理学宗传》计26卷,本主辅内外之原则,传自董仲舒以迄周汝登等汉唐宋明之170位儒者,先立传记,次辑录其所著或语录,于眉端或段落中施批注,这些批注对于考论孙氏之学术倾向颇为重要。从这些批注,可以看出孙氏自身的学术立场,以及在本体与工夫问题上的基本见解。本文从孙奇逢在《理学宗传》对诸儒学的批注入手,分析其“严辨儒释”思想,讨论其学术倾向。
孙奇逢认为,当时要讲明儒者之道以接续道统,首先必须分清儒释的界限。薛瑄表彰唐韩愈及有宋道学君子距邪闲正之功,孙氏深表认同,批注说:“儒释之辨既明,儒者之功不见其大;儒释之辨未明,儒者之功原自不小;彼以儒为名,犹匍匐而归之者,独何心欤?”[1]138因为当时“儒释未清,学术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极”[1]17,所以,《理学宗传》的首要任务是严辨儒释。诚如孙氏弟子汤斌在叙《理学宗传》时所说:“近世学者或专记诵而遗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行,又有为儒佛舍一之说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与吾儒相近,而外人伦、遗事物,其心起于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国家……容城孙先生集《理学宗传》一书…… 其大意在明天人之归,严儒释之辨。”[1]11那么,《理学宗传》是如何严辨儒释的呢?
一、区分本天本心
这一区分源出程颐。程颐说:“《书》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3]274问题是朱熹在程颐之后就把儒家道统相传的内容坐实为虞廷的十六字心传,以致在朱学广泛流传并被确立为官学之后,要将本心之学说成是释氏之学,并说服广大士子,难度极大。周汝登言:“后世论学有本心、本天之判,然观虞廷则止言心矣。明道谓:即心便是天,更不可外求。邵子亦谓:自然之外别无天。自然者,即吾心不学不虑之良也。故天与心不可判,判天与心而二之者,非惟一之旨矣,先后诸儒皆明大舜惟心之旨,夫惟心乃所以为惟一也与?”[4]7-8孙氏当然会面临这一难题,当时就有人质疑说:“虞廷之人心道心,非心乎?孔子之从心所欲,非心乎?何独禅学本心也?”孙奇逢回答说:“正谓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必精以一之,乃能执中,中即所谓天也。人心有欲,必不逾矩,矩即所谓天也。释氏宗旨,于中与矩相去正自千里。”[1]17可见,诚如张沐所指出的那样,“人知本体为天,不知工夫为天……舍本体而言工夫,固其为工夫皆伪,舍工夫而言本体,则本体又附于何所乎?此先生所为宗天之义也欤?”[1]11孙氏重提本天之说,认为“本天本心,毫厘千里”[1]42,其实是针对阳明后学现成良知派之荡越,先重将道德实践的根据本体宇宙论化,再把天道内化为人之善性,这同程颐之学还是有区别的。孙奇逢说:“圣学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无善无恶也。”[5]589“心无善无不善,此禅宗也,释氏本心之说也。性命于天,自是至善无恶。孟子所以道性善,此圣学本天之说也。本天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能兼善天下。本心只了当一已,故谓之自私自利。有统体之理,有一偏之理。理有偏全,学术自别。”[5]589在夏峰看来,这种差别表现在本体、功夫及境界三个方面。
对2.3的全部数据进行对比和综合之后,研究者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死亡凸显和亲密关系丧失会显著降低高自尊被试的职业期望、职业承诺、职业价值观及职业认知,除此之外,死亡凸显还会显著降低高自尊被试的职业情感,但二者对低自尊被试的职业认同及其各因素无显著影响。
这些思想,表现在《理学宗传》上,就是孙奇逢所说:“学之有宗,犹国之有统,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国之统有正有闰,而学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国之运数,当必分正统焉;溯家之本原,当先定大宗焉;论学之宗传,而不本诸天者, 其非善学者也。”[1]15以十一子为传圣贤之学的大宗,并且将那些有不本诸天倾向的儒者列入补遗,严加辨析。
从本体上说,“释氏之失,一言以蔽之,曰不能穷理而已。范围犹裁成也,天用即化育也,诬天地日月一切皆空,岂非妄天性者乎?”这是以天地万物之理为诚为妄的差别,也是肯定世界与舍离世界的差别。“释氏之学,始终本末,以一念之背驰,而遂至于陷溺。盖吾儒志在维理,而释氏意在破理,此其大较也。篇中既暴其罪状而又不抹其偏长,是从来辟异端第一首文字。”[1]101从功夫上说,儒学是道德心自作主宰,“心一而不二,人心道心,操存舍亡,尽心存心,总只是此一个心,非心之外复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而“释氏观心之说,是以心求心,若两物之相持而不相舍,故与吾儒相似而实不同”[1]100。因为对性、理认识不同,所以儒释对于生命的最后蕲向也不同,“佛氏以觉为性,谓人虽死而觉性不散,为鬼,重复受生,轮回循环,遂指为苦海,求免。是不知鬼也”[1]57。
二、辨析补遗诸儒
因此,在如何去做的问题上,陆九渊心学如同增能理论一样,也完成了一场由用外部规范内部到从内部寻找资源去增强内部的范式转换。
对于张九成以觉训仁,孙奇逢直下断语说:“觉字是无垢宗旨。”[1]506当然,孙氏也反驳了那种因张九成拈出觉字即谓其为禅的观点,认为不独伊尹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即使孔子也认为先觉者是贤,所以并无可议。张氏的可议之处在其行教的许多话头乃是学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说得,“其立论多凌遽棒喝语,人故以禅归之”[1]507-508。
所谓补遗,孙奇逢说,就是“其超异,与圣人端绪微有不同”,故“不得不严毫厘千里之辨”[1]42。立足于儒释之辨,孙奇逢一一辨析收在补遗卷中诸儒的近禅之处。
(2)推动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催生了许多重大、高质量的科研、专利成果和高于其他计划的商业价值;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受益于该计划的资助。
Ⅱ号矿体:出露在3343高地向北延伸的山脊的东坡上,位于Ⅰ号矿体的330°方向460m处。矿体向西受SN向的断裂控制尖灭,向东延伸被第四系冰碛层覆盖,呈EW向分布,总体产状与灰岩一致产状,355°∠55°。矿体呈较规则的板状、似层状,矿体内有大小不等的灰岩夹石或灰岩残留体,造成矿体边界参差不齐和矿石品位的贫化。矿体出露地表长度为90m,矿体厚度为2~3m,铅+锌平均品为8.73%。
王畿以为“良知不学不虑,终日学,只是复他不学之体;终日虑,只是复他不虑之体”,孙氏认为这不是可以施与人人的共法,批注说:“说得本自然,学者便无所持循,总是接上根话头。”[1]518认为“龙溪之言满天下,后传龙溪之学者流弊滋甚”[1]515,但这并不是杨明学本身有什么问题,恰恰是像王畿这样的传阳明之学者的过错。孙氏还不忘检讨自己,在罗洪先力救其偏之时,却颇爱龙溪学之简易透彻,晚年才清楚地了解到其学之流弊。
总之,收在补遗卷的这些人,要么是程门弟子,要么是陆王后学,“皆世所推为大儒”,但为了严辨儒释,孙奇逢以其“学焉而未纯者”,有悖师教,而将之驱出程朱、陆王之门墙。孙奇逢自设问答说:“补遗诸子皆贤,乌忍外?尝思墨子固当世之贤大夫也,曾推与孟子并,何尝无父?盖为著《兼爱》一篇,其流弊必至于无父,故孟子昌言辟之。愚敢于补遗诸公效此忠告。”[1]17在补遗卷最后,孙奇逢又回应了他人之质疑:“补遗诸公,皆世所推为大儒者也,而谓其为近于禅。夫诸公居官立身,皆卓然自见。即议论有疑于禅者,亦借禅以为用。所谓不以世间法碍出世间法,不以出世间法让世间法。庸何伤?”[1]533孙氏又引顾应祥之说,强调儒者如果借佛教以明道,其流弊将至儒释同归而不可解,所以孙奇逢认为,对于混合儒释之行为,真正的儒者一定要辞以辟之,而不可助其波,扬其焰,以致得罪于圣人。
对于罗汝芳,孙奇逢肯定其以孝弟慈为明、亲、至善之实乃是极其透彻之论,认为“非尧舜不能满孝弟之量,惟孟子看得出,惟近溪发得透”[1]526。对于近溪以戒慎为入道之首、进德之先而所持守虽到道明德立之时亦不可缓的看法,孙氏批注说:“以戒始,以戒终,尧舜文王无非此戒。”[1]527认为近溪说得非常确实。但对于近溪以不要虑不要学为宗旨,孙氏同样批注说:“不学不虑是宗旨,但须达之天下,才有究竟。”[1]522近溪以为究人之所觉悟得只是现在不虑不学之良知良能,孙氏认为此说固有醒人处,然不善理会,亦不免误人。最后引曹真予所说加以总评,认为罗近溪透彻心体虽然可尚,但不免阔略之病,学者得其阔略,以为可便其私,以致多放荡不羁[1]527。
对于杨简,孙氏肯定其于《易传》亦有所窥,乃其所自得,但也明确指出“不起意一言邻于虚灭”,又说“慈湖不起意之说自穷矣,人谓慈湖之病总在自持”[1]196。有人问陆门弟子以杨简为最,为什么宋儒考陆门弟子卷弃置不录,反而置诸补遗卷,孙氏回答说:“学以躬行实践为主,圣门高第,回之克复,参之忠恕,损之孝友,雍之简然,由之果,赐之达,求之艺,皆取其实德而有适于用,非徒言而已也……敬仲以不起意为宗,令人无所把捉,然按其所言,亦何能不起意也?至诋思、孟为小觉,未免失言矣,子静之学,岂如是乎?……敬仲訾议圣贤,弃捐经典,师心自足,恐不可以为训。故于敬仲不敢不严其辨。此亦《春秋》责备贤者之意。”[1]294批评杨简行不顾言,不能躬行实践,而且毁弃经典,非议圣贤,完全不像其师,“传象山者,失象山也”[1]513。
4.平均初生体重。采用人工授精为(1.726±0.16)kg/头,采用自然交配为(1.718±0.21)kg /头,差异不显著(P﹥0.05)。
三、表彰排佛诸儒
孙奇逢严辨儒释的第三个做法,就是在《理学宗传》中极力表彰内编中的那些勇于排佛的儒者。在传唐朝韩愈及其门人时说:“唐自中叶,老、佛显行,儒道媮末滥竽,显仕称儒者,愿相助为怪神。文公锐然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争四海之惑,屡跲复振……得赵秀才一人, 能排异端、宗孔氏,便可为同心之人矣。”[1]244不胜其赞赏之情。批《原道》说:“帝王平治天下,全在人伦日用上经纶位育,如灭伦常、遗事物,便不成世界。此韩子《原道》大头脑,议论平贯,直令二氏无安顿处。末幅‘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一段,高识创论,迥乎不可及也。”[1]236程门弟子朱光庭“常谓释氏为世教大患,高明之士既沉溺于性宗,中下之材又缠缚于因果,故力排异端以扶圣教”[1]264。朱门弟子蔡元定于“方技、曲学、异端邪说,悉拔其根而辨其非;使千古之误旷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1]282明初大儒曹端认为“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子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孙氏说他“天生成一个铁板道学公,真明代开山,不独冠冕中州也。”[1]334何塘“七岁时,入郡城。见家有弥勒佛塑像。乃抗言,请去之。人皆大骇”。冯从吾于“凡世儒所易惑处,辄为道破。吾儒之家宝,始复其旧,佛氏之流弊,始塞其源,虞廷心法于是乎晓然复明于天下矣。”[1]236孙奇逢认为这是丰功伟绩。
四、分疏经世出世
孙氏本天本心之辨,并不是对程颐之说的简单重复,实际上是强调儒释在人生态度上的肯定世界与舍离世界的大分野。不同的人生态度,自然表现为不同生命形态,所以陆王心学不是禅学,完全可以从象山、阳明的道德事功上看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陆象山、王阳明学说的分判上。
象山学问,当时被认为是禅学。孙氏批注说:“朱陆同异,当时聚讼,没后鼓煽,群以为禅。” [1] 129孙氏引黄道周之说:“子静在荆门,如许心手,岂是寻常穿衣吃饭者?凡事业勋猷是上天所命,道德行谊是自家成立。” [1] 129黄道周认为“阳明全是濂溪学问,做出子静事功”。孙氏又引朱子说:“子静实见得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 [1] 130孙氏认为不怕天不怕地有两种含义,“愚人无知,醉生梦死,故冥然不悟”,所以不怕天不怕地;而“君子内省不疚,浩然充塞,视天地如父母”,所以也不怕天不怕地。在孙氏看来,象山之所以有事业勋猷,是因为他对天地实理有真切的体悟,“平生所言所行,其直接孟子处,却被文公一口打迸出来,直是传神写照之手”,所以其学绝对不可能是禅学[1] 130。孙奇逢认为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从道理上看,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因为无善无恶四字是禅门宗旨,阳明失于回避,遂招指摘。孙氏认为把阳明学看成是禅学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禅与不禅宜就其行事上论,岂有拼九死以安社稷而谓之禅者耶?”[1]355陈龙正认为“入门不妨异,朝闻夕可,归宿必同;用力不妨异,设诚致行,起念必同”,所以朱子不应推驳象山,阳明不应推驳朱子。孙氏认为“此论甚平”,但陈龙正“必以阳明为禅,又似多却一番推驳”[1]497,不同意他的结论。
崔铣“谨守程朱之学,品行自无可议”,但他非要认为陆王是禅学、为异端邪说,孙奇逢争辩说,“夫二人者,且不必论其学术。荆门之政,有体有用;宁藩之事,拼九死以安社稷。吾未见异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4]398,认为崔氏发刻薄之论,实在有伤恕道。总之,孙奇逢虽然反对混合儒释,借释解儒,但是也认为不应该把真儒学指为禅学,这同样是严辨儒释。
孙奇逢对程朱陆王不分轩轾,而且还在儒家道统元亨利贞的四阶段演进中给自己编排了位置,表明了自己要做新时代的儒家道统的完成者的学术志向。为实现这一志向,他严辨儒释,分其所不当合;融汇朱王,合其所不当分,一生躬行实践。孙奇逢一生任道重,自修苦,以经世为蕲向,以励行为途径,严辨儒释,以最终实现归宗孔孟的学术志向。
参考文献:
[1] 孙奇逢.理学宗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2] 张显清.孙奇逢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3]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一[M]//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4] 周汝登.东越证学录:武林会语:卷三[M].济南:齐鲁书社,1997.
[5]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SUN Qifeng's Thought of "Strictly Discerning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Reflected in the Annotations of TheBiographyofNeo-Confucianism
XIA Zhihong, WAN Hong, WU Jinghong
(Library,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China)
Abstract:SUN Qifeng's academic idea has always aroused controversies, and his TheBiographyofNeo-Confucianism can be regarded as the final conclusion of his later years. This book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It reviews 170 Confucians from Han, Tang,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such as DONG Zhongshu and ZHOU Rudeng, and then compiles their writings or quotations, makes annotations on them in the top margins or between the lines, and finally gives a general commentary on the academic circles. From these comments, people can see SUN's own academic standpoint: He tried to realize his academic aspiration of returning to Confucius and Mencius by "strictly discerning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Keywords:annotations of TheBiographyofNeo-Confucianism; SUN Qifeng; strictly discerning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收稿日期:2019-03-19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LS1408)
作者简介:夏志红(1968-),女,江西上饶人,馆员,从事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研究。E-mail:731023809@qq.com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19)04-0012-04
DOI:10.3969/j.issn.1004-2237.2019.04.003
[责任编辑 邱忠善]
标签:理学论文; 儒者论文; 矿体论文; 象山论文; 本心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清代哲学(1644~1840年)论文;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LS1408)论文; 上饶师范学院图书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