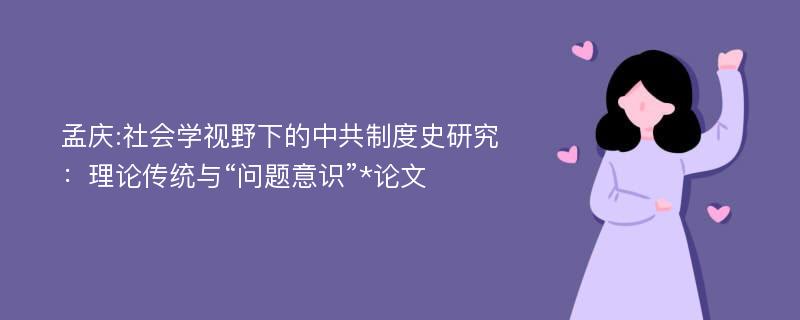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制度是各个学科关注的焦点议题。经济学、政治学偏重于对制度结构的总体分析,并多以“结构—功能”视角理解人类的行为;社会学更强调对制度的社会过程与运行机制进行考察;在历史学领域,制度史是贯穿从古代史到近现代史的经典论题。近年来,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内部跨学科研究的推进,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不断突破学科藩篱相互融合,围绕制度史这一经典论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而聚焦的中共制度史研究更呈现方兴未艾的新局面。笔者尝试从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出发,以相关的社会学经典理论为基础,结合近年来社会学领域内有关近代中国社会革命与转型的实证研究,揭示中共制度史研究的跨学科理论传统与“问题意识”,讨论社会学视野下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可能路径。
藏羊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一种具有生物功能的天然蛋白质,由于其具有特殊的结构以及诸多优良特性,使其在食品、医药、化妆品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14-16]。目前我省的大部分藏羊皮都是以原材料的形式销往皮革地区产业地区进行皮革的加工。因此,青海省可以充分利用藏羊皮中丰富的优质胶原蛋白含量高的特点,运用成熟的生物技术,发展藏羊皮胶原蛋白的生产,可用于食品、医药、美妆等行业,这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藏羊肉的经济附加值。
一、制度史研究的社会学路径
在历史社会学视域下,关于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传统的核心“问题意识”在于考察不同社会历史环境中制度衍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呈现制度的社会基础。在方法上,它多以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为框架,呈现不同文明系统中的革命事件与制度特征并加以比较,或者通过跨越时空和文化的对比,从具体历史中抽象出共同性要素,作为解释制度形成与革命行为的共同变量,并提升为相关的理论概念或者归纳出不同文明类型与社会条件下的不同制度生成路径。摩尔的著作《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开启了这一研究传统,分析了不同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注]〔美〕巴林顿·摩尔著,王茁、顾洁译:《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斯考切波接续这一研究进路,通过比较中国、俄国和法国的革命进程,提出了“国家自主性”与“社会革命”的重要概念[注]〔美〕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比较历史分析介入革命与制度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路在提供独特的理论概念和解释路径等方面极具启发意义,但也受到很多批评,如对史料的粗线条处理、理论概念本身存在的不完全解释力等。需要注意的是,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核心“问题意识”就在于探寻革命现象的普遍性原则和一般性规律,却由于跨越过长的时空而无法深入社会历史处境中展开讨论。
在社会学领域内,对于制度的讨论还存在着其他范式,它们尤其注重制度的“运作机制”及其历史效果。在有关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中,孙立平、郭于华所开创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计划”即是围绕制度的社会过程展开的。这一研究进路通过对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试图在实践机制层面理解中国革命的社会过程,将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土地革命的历史场景。其中,他们将“诉苦”作为中共构建新国家观念的中介机制加以理解,并强调“诉苦”作为一种组织动员技术,在土地革命的历史场景中,不仅完成了革命的社会动员,而且将全新的有关个体与国家关系的观念重新植入底层农民的日常生活,完成了原子化个体的塑造以及对旧有社会秩序的颠转[注]郭于华:《倾听底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78页。。方慧容关于土改的研究则通过对底层农民集体记忆中“无事件境”特征的归纳与提炼,一方面指出了作为制度实践方式的“诉苦”与原有乡土社会中村民集体记忆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诉苦”这一权力技术在实践过程中对底层农民集体记忆特征的型塑[注]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中国社会学》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371页。。李康通过对华北西村土改历史过程的“重述”,呈现了底层农民从“革命”走向“革命”的历史过程以及具体革命实践场景中权力运作的日常状态[注]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1999年。所谓从“革命”走向“革命”,是指中共在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以“诉苦”等组织技术完成社会动员,从而激发原本没有政治觉悟与政治意识的普通农民完成了从被动卷入革命洪流到主动参与革命进程的历史过程。。
一方面是环保政策。近年来,环保政策的持续加码对整个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环保的高要求促使行业整体转型升级,大量落后产能退出,行业整体开工率始终处于低位,尿素的整体供应量也大幅度减少。据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统计,2018年1月-8月,我国尿素产量为3387.6万吨(实物量),表观消费量则为3312.9万吨。可以看出来,1月-8月我国尿素供需基本属于平衡状态。且今年尿素的整体库存处于历史低位,企业供应压力也有所减轻,为尿素价格提供了更多的可操作空间。这也是上周尿素价格在失去了国际市场利好之后,依然能够再度上调的原因之一。
学术界更多地从“底层视角”去理解这一口述史研究传统,但忽视了这一研究传统的核心“问题意识”。口述史研究者所关心的乃是通过基层材料的搜集去理解“作为文明的共产主义的微观机制与运作逻辑”[注]郭于华:《社会学的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社会学家茶座》总第1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35页。。换言之,口述史研究者讨论与关注的乃是制度的实践状态。这一研究传统背后有着深厚的福柯权力理论的色彩。福柯以权力运作机制的转变为核心视角来分析现代性的转变,其理论洞察力不仅在于权力之光所照亮的地方,而且表现在被权力之光所遮掩的地方[注]马学军、应星:《福柯权力思想中的史观、史识与史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在这个意义上,口述史研究传统揭示了组织动员与制度实践的社会过程。
笔者近年来也围绕土地革命中“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技术展开了制度源流意义上的历史社会学考察。与既往研究更多以“动员”视角考察土地革命的社会过程不同,笔者关心的核心问题在于,“查阶级”的组织动员技术究竟从何而来?这一组织动员技术是一种怎样的实践形态?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理念?在这一组织动员技术不断演化和实践的过程中,有哪些 “历史担纲者”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人又具有怎样的“精神气质”?上述“问题意识”的产生基础,大致缘于下述经验事实。从1927年到1934年,在中央苏区范围内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分田地”的具体流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与程序化,最初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的“阶级”也开始有了具体的量化标准并不断细化。自1933年查田运动始,赣南闽西地区在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同时,各地方也同时存在着各种脱离量化标准的“闹革命”的群众性革命动员。由此,关于“查阶级”这一制度实践方式与组织动员技术的发生学问题便浮现出来。而对这一发生学意义上的“问题意识”进行回答的核心,就在于对制度演进关键节点的识别。如以朱毛红军初上井冈山为线索,伴随着开拓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过程,土地革命中的分田流程与组织动员技术也在不断演化:从初期以“平分一切土地”为核心的宁冈土地法,到1929年下半年红四军入闽吸收了邓子恢等人“抽多补少”的地方经验,再到1930年6月南阳会议之后以富农为核心展开的从意识形态领域到现实政治斗争层面的一系列运动,直到1933年查田运动,“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技术终于初具模样。
上述两种制度史研究的社会学路径目前都存在着各自的力量与限制,这也构成了展开新制度史研究的起点。在下文中,笔者将聚焦于当前社会学领域中的典型制度史研究,分析其基本的“问题意识”。
二、关于“制度源流”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应星在近年来提出把中国革命带回到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主张打通学科界限,在充分借鉴、吸收与学习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前提下,重新在社会学视野内,围绕制度源流与政治文化这一核心“问题意识”进行研究[注]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从研究对象上看,他的一系列研究聚焦于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四军,主要涉及包括赣南闽西在内的中央苏区的地域范围。表面上看,应星的一系列研究似乎并未直接处理制度史的问题,也并未过多使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概念。但如果从“问题意识”层面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其研究的核心关注都在于一种“作为政治文化”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源流。如在对万安暴动的研究中,应星通过个案讨论了早期革命暴动中的地方领袖与组织纪律之间的内在张力,并勾勒了以曾天宇为代表的地方干部的独特精神气质和革命伦理[注]应星、李夏:《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社会》2014年第5期。。而他对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细致入微的比较研究,则呈现了根据地在组织形态上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揭示了上级党组织、外部军事力量以及地方根据地组织形态与武装能力之间的复杂关联,突破了既往研究对“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僵化理解[注]应星:《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形态——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在对红军整编的研究中,应星对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关怀体现得更为明显。他通过对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历史源流与演化的考察,深入探究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的不同体现方式和运作逻辑,并揭示了主力红军与从省委到特委的各级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注]应星:《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苏区研究》2016年第3期。。尽管上述研究并未过多着墨于理论讨论,但在“问题意识”层面实质上构成了对“民主集中制”早期源流的社会过程研究。
与比较历史分析注重抽象普遍性不同,口述史研究传统更为关注微妙的制度实践过程,但也同样存在一些不足:口述材料本身的限制使得口述史研究往往陷入“求真”与“求解”的张力之中;口述史研究方法天然受到时间的限制,往往无力处理制度的起源问题。
由此,笔者通过对查田运动的考察,勾勒了“查阶级”成型的具体社会历史场域:在意识形态层面,查田运动的发生本身是在当时“反富农”的诉求下展开的;在现实政治斗争层面,发动查田运动并任用王观澜推行量化阶级标准,本身和毛泽东当时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通过查田运动重塑革命路线的正当性以对抗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国际派”路线);在地域社会层面,查田运动又和瑞金地区地方宗族势力之间的固有冲突裹挟在一起。因而,量化阶级标准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算不清”“不能算”又“不能不算”的多重困境。“查阶级”便是在这样的具体历史场景以及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生长出来的。[注]孟庆延:《苏区革命与地方社会:查田运动发轫之新探》,《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同时,对“查阶级”这一制度生成起着重要作用的两类干部也终于浮现出来,即以彭湃为代表的侧重宣传鼓动的“农运派”干部——他们负载着共产主义等社会思潮,是革命实践中的“深耕者”与“鼓动家”,以及以王观澜为代表的强调量化阶级标准的“算账派”技术官僚。简言之,这一系列研究并非局限于政治运动和革命行为的发动动机或影响因素,而是尝试从整体上去理解一项制度或政治传统的现实发生过程。
上述分析是围绕当前国内社会学领域对有关中共制度史的典型研究的内在逻辑进行的初步梳理。那么,上述研究又有着怎样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视野?又以何种社会学理论资源为基础?
三、“问题意识”:从“实践形态”到“制度源流”
当研究者试图将中共制度史纳入社会学研究视野时,究竟有着怎样的核心“问题意识”就构成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在这一层面,陈寅恪开创的关于制度源流的问题传统、埃利亚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发生学研究以及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文明基础的研究,可为社会学重新研究中共制度史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陈寅恪在相关著作中指出:“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兹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注]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北京三联书店, 2009年,第3页。他在讨论制度源流的时候,并非仅仅呈现了制度的更迭过程,而是揭示制度源流背后的诸多复杂社会历史要素。他所使用的“社会集团”概念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对制度源流的考察呈现的乃是制度变迁背后的社会过程,因而在“问题意识”层面对当下的革命史与制度史研究构成了新的启发。对于中共制度史研究而言,在“事实”层面澄清制度变化当然重要,但在社会发生学的意义上去追溯制度的源起与流变也非常重要,因为制度并非基于纯粹抽象的理论设计,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同诸多原有社会结构与秩序的不断碰撞中产生的。
大丫说,这个女佣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丈夫和儿女都不要她了,她留在我这里,说愿意服侍我一辈子。人非常可靠,忠心耿耿吧。
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对欧洲中世纪专制主义国家进行了社会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他以中世纪的宫廷礼仪为起点,一方面揭示了礼仪作为一种制度的社会发生过程,另一方面呈现了这样一种“文明”进程的实质,即对本能的自我强制机制的不断演化。他进而指出,包括人口激增、货币需求量增加、社会分工细化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条件的变化构成了文明进程和民族国家形成背后的关键历史与社会变量。[注]〔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译:《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这一成果启发研究者以权力技术的社会源起为视角,在具体革命历史场景中考察中共制度的社会发生过程的可能性。
“对啊!制作蜡像时,用蜡是很有讲究的。白蜡和石蜡的比例必须调配合适,这样做出来的蜡像才能既逼真,又有足够的硬度,不容易变形。”
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为制度史研究提供了另外一重可资借鉴的资源。韦伯围绕西方独特的宗教类型,展开了关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系统论述。他将论述焦点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担纲者——清教徒身上,对下述问题展开追问:一群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基督新教徒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气质,使其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形成的重要担纲者[注]〔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韦伯的研究提示研究者,制度是由活生生的人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因而,在对中共制度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可以从如下角度提出新的“问题意识”的可能性:一项制度的创设,究竟是由具有怎样的性情倾向、负载着何种思想资源的革命者所完成的?他们所具有的精神气质与制度本身的理念及其实践特征之间具有何种关联?
第一,作为“底色”的经典社会理论。尽管唯物史观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实质上在理论层面提供了关于人类社会变化动力的社会学解释。在这个意义上,经典社会理论往往比中层理论具有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实际上,对于产生于西方历史过程与社会经验的经典社会理论,研究者很难直接将其镶嵌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制度史研究中,因为这些理论所追求的乃是普世意义上的普遍性问题;同样,也正是这样一种对普遍性的追求,使得这些经典理论具有了“理论底色”的意涵[注]王汎森:《思想史研究方法经验谈》,许纪霖等编:《何谓现代,谁之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7—63页。。简言之,一个熟读涂尔干相关理论的研究者和另一个熟读马克思相关理论的研究者,如果同时到同一个村庄去做研究,那么前者很可能对村庄中的“社会团结”问题更为敏感,而后者则更容易体察到村庄中的“阶级分化”。同样,受福柯影响很深的学者,在研读与整理史料的时候,也自然会对史料呈现的“权力运作”具有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也容易将制度的发端、衍生与运作理解为一整套权力机制。
四、理论传统:从概念移植到“理论底色”
第三,理念与行动之间的“虚实”张力。无论是社会学研究还是历史学研究,在“实证”原则的情境下,普遍存在着虚与实、思想与行动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很难找到可以直接证明某一行动者行为动机或钱穆所谓某一制度之“理念”的“证据”并建立“可证明”的因果解释链条——而最容易“被证明”并为现代人所理解与“共情”的行为的动机,莫过于上面所讲到的“权力—利益”逻辑。
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是历史社会学领域主要的理论范式之一,但它“平列式”地给出跨地域、跨文化、跨时间的诸多要素,通过将不同历史情境下的事件及其要素在同一语境下加以比较,得出某些具有抽象普遍性的结论。这一传统尽管追求普遍性,但抽离了历史本身存在的“分叉”、复杂及其具体情境。这样一种单纯面向“求解”的“中层理论”所提炼出的普遍性概念,往往无法应对不同文明类型下的具体社会历史处境。例如斯考切波的“国家自主性”概念,实质上将“阶级”理解为一种同质性的存在,而没有注意到在中国革命场景中的“阶级”概念之下极为复杂的实践状态。
除此之外,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传统也为理解制度及其变迁提供了另一种框架。尽管年鉴学派本身经历了内部的范式转向,但是年鉴学派贯穿长、中、短时段的分析框架一直保留下来,并被应用到有关中国革命的分析中去,如饶伟新在关于土地革命历史背景的考察中,就通过对“土客分野”“宗族聚居”“阶级分化”等三种不同社会分化机制的中长时段的勾勒,呈现了“土地革命”这一事件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注] 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 2002年。。
第二,今天的革命史研究往往通过个案讨论制度的“在地”过程,但是在具体讨论个案的时候,却通常只是将“地方”作为纯粹的背景加以理解。“地方”往往只是一些没有实质性含义的地名,无法在研究中真正构成对某一事件、某一行动者抑或某一制度的实质性理解。既往研究往往容易忽略独特的民情状态、社会条件对制度实践的实质意义,也经常忽略不同地域中不同民间宗教或不同社会思潮对行动者的重要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经典理论传统各有其“问题意识”,它们的产生也和整个人类文明的现代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产生了包括“支配类型”“历史担纲者”“身份群体”等在内的一系列理论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各有自身的衍生背景和具体意涵。因而,当研究者尝试将上述理论概念应用于中共制度史研究时,尤其需要进一步甄别,并结合具体的历史经验加以调整与限定。实际上,在将上述理论传统引入有关制度史研究的过程中,已经有学者作出了有益尝试,他们所采用的具体进路,并非对概念的套用和理论判断的直接移植,而是更多地从“问题意识”层面汲取有益资源。例如,周雪光借鉴韦伯“官僚制”的理论传统,重点讨论了帝国治理逻辑与传统官制之间的内在关联,重点发掘了魏晋以来的“官吏分途”这一制度的内在理念:它既是帝国面对越来越大的治理规模的制度因应,也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复杂结构性关系[注]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社会》2016年第1期。。而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应星从历史社会学视角所展开的江西苏区史研究,则是在充分汲取韦伯有关文明类型的问题传统、陈寅恪有关制度源流的中古史研究以及福柯权力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其背后的“问题意识”就是对“民主集中制”这一独特制度的源流考察。
第二,挖掘中共自身话语体系的关键概念与理论意涵。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一样,共产党作为革命实践的主要“担纲者”和制度的主要“创设者”,其理论表达本质上亦是一系列关于政治与社会的话语解释体系,但这一话语体系往往由于其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为学术研究所忽视。应星就明确主张要真正在学术理论的意义上,去理解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群众路线问题[注]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应星所讨论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群众路线问题实质上具有深刻的学术理论意涵。其一,政治路线的本质是以“阶级”这一重要概念来界定社会性质、判断革命性质进而决定革命的具体策略。这实际上是社会学经典理论曾重点讨论过的问题,也是围绕现代社会变迁所构建的重要解释机制。因此,无论是对阶级政策的讨论还是对“阶级”概念的研究抑或是对“查阶级”这一制度实践方式的考察,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涵。其二,组织路线的核心在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民主集中制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形态,究竟如何在革命政党的实践过程中得以“形成”?在其形成过程中,革命政党在理论层面又是如何处理现代民主理念与集体主义理念之间的张力的?在实践层面又是如何处理现实制度实践中的各种冲突与矛盾的?上述问题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含义。其三,群众路线问题本身就蕴含着复杂的代表先进意识形态的革命政党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简言之,作为先进意识形态代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具体进程中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便是如何向当时并不具备明确政治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底层民众阐释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和社会蓝图。实际上,对上述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从社会科学的视角和政治文化的层面,去理解“群众路线”的理论意涵。
第一,研究者往往容易按照当前生活世界的经验与情感来理解处于历史中的人物的思想状态与行为动机。今天的研究者生活在一个韦伯意义上的“除魅”时代,对自身生存处境的理解,往往出于理性人的“成本—收益”假设,因而难以真正还原历史现场,去理解一个处在历史现场中的革命者的复杂情绪体验,也无从真正明了他们的时代困惑。因此,很多革命史研究在解释历史中人物的行为的时候,往往同样陷于“权力—利益”的解释逻辑而在无意中忽视了革命者的理念与伦理维度。
五、社会史、思潮史与制度史:从“权力—利益”到“民情—人心”
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当研究者更多地“眼光向下”,在“制度实践”的层面将问题聚焦于基层革命精英乃至普通行动者,并尝试建立因果解释逻辑的连续谱系之际,往往容易陷入“权力—利益”的叙述模式。简单来说,在有关制度实践的革命史研究中,无论研究对象是何事件、行动者是谁,最终都难逃“政治精英的争权夺利”这一解释脉络,这实质上构成了研究者在更高层次上理解中共制度的某种困境。面对这一问题,笔者尝试从下述层面做些讨论。
对于社会学视域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而言,经典社会理论由于有其产生的具体历史土壤,同时又因为追求普适性解释和一般因果律而难以处理不同文化系统中的“分叉”,因而无法“直接”应用于关于中国革命的制度史研究,但可以提供一种考察革命者行为与理解制度的“视野”,这也构成了在本土历史文化中发掘资源、构建自身话语体系并形成面向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阐释的重要前提。
面对上述学术传统与理论资源,社会学究竟如何围绕中共制度史研究展开“理论分析”呢?实际上,对于以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介入中共革命史研究而言,可以从下述两个层面理解“理论”的具体涵义。
1)将样本数据集M={m1,m2,…,ml}中的样本点存入邻距离矩阵Ndm=Nn×Nn中,其中Nn为数据集合M的数据总数,矩阵的每一行表示数据集M中的数据m1与其他数据间的距离.之后对粒度变量Gv初始化.
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很多研究者都曾围绕中国乡村社会展开研究,并贡献了包括“内卷化”“权力的文化网络”等在内的诸多中层理论与概念。杨念群也通过对本土社会资源的挖掘来提炼“中层理论”,试图促进中国社会与历史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注]杨念群:《“中层理论”应用之再检视:一个基于跨学科演变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由此来看,在社会学视域下展开中共制度史研究,还要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即究竟“使用”何种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用怎样的概念来进行阐释?换言之,社会学必须回应这一“理论的焦虑”。
由此,对于制度史研究而言,或许更要拓展的问题在于,不仅要见“人”,而且要能够见到更为丰富的“人”;不仅要关注制度的实践过程,还要关照制度的生成过程;不仅要讨论制度的历史效果,还要考察制度的理念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与思潮史的深入展开,或可为中共制度史研究的进展提供更多的可能路径。
前两次的被捕都只是被短期拘留之后就被释放了出来,然而1930年5月又一次被逮捕,只是这次不像前两次很快就被释放了出来,中野重治在监狱里待到同年12月,直至被保释出狱。以这次八个月左右的入狱经历为素材,中野重治于次年1931年6月在杂志《改造》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菊花》。
(2)在地下室的底板上纵横向设计后浇带,后浇带的间隔为30 m,这样底板以下的地下水可以通过后浇带汇集到两侧的集水井中,再用潜水泵抽出。
对于思潮史而言,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去理解行动者本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所处的社会思潮状态。当时的革命者与行动者究竟读过怎样的书?受到过何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与熏陶?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及其生命经历又都赋予了其怎样的性情倾向与思想资源?笔者认为,对这些“历史虚处”的考察有助于理解革命者的行动以及制度的内在“理念”。因而,王汎森有关“主义时代”与“烦闷”的研究就具有较大的启发性。他勾勒的“主义”来临时社会的普遍状态与新青年的思想倾向,提供了理解革命者的复杂行动和基本的社会思潮背景[注]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165—250、113—164页。。笔者亦在关于“查阶级”的研究中,尝试勾勒包括“农运派”与“算账派”在内的不同革命者的“思想图景”并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即具有何种成长经历、性情倾向和精神气质的革命者,在复杂的革命实践中推行着原本属于理论层面的“量化阶级标准”?同样,始终存在于土地革命斗争场景中的那些脱离量化阶级标准而侧重强调“情绪动员与暴力斗争”的斗争方式,是哪些重要的农运干部完成的?进而,笔者勾勒出王观澜作为算账派技术官僚身上所具有的“对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谨慎理性的计划管理干部”等鲜明特点,以此去理解其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努力和局限。[注]孟庆延:《“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社会》2016年第4期;《“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社会》2017年第3期。
对于社会史而言,无论讨论制度的实践状态还是讨论制度的社会源起,都需要研究者对制度所在的地域社会的民情状态作出更为深入的具体理解。换言之,只有理解制度具体产生与演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例如宗族形态、土客关系、民间信仰、教育状况、经济类型等,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制度的起源、发生以及演化,才能真正明了制度理念与现实地域社会之间的张力,进而理解革命政党为弥合这些矛盾所做出的努力,由此才可能理解在这些实践与调整中所形成的新的“常规性做法”即制度。
本文采用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方法(TOPSIS法)对新疆产城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首先确定各项指标的正负理想解,再求出各待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加权欧氏距离,然后确定各待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度,这就是综合评价得分。
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下,应星在深入考察赣西南地区错综复杂的土客关系、宗族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共早期革命进程中复杂的组织形态,呈现了“民主集中制”最初形成时的社会过程。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所讨论的“查阶级”这一制度实践形态,同时包含的“算”与“闹”的双重意涵才能真正呈现:当意识形态理念作用于有着悠久历史并形成特定社会结构的地域社会之时,阶级标准与宗族、土客之间难免产生不相适应的地方;也正是在复杂的张力缝隙和激烈的斗争环境下,处于具体社会历史处境中的革命担纲者推进着“查阶级”这一组织技术的形成。
综上所述,笔者围绕“问题意识”与理论视野,在社会学的视域内对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作出一些简要讨论。对于社会学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或许并不是发明新概念,也并非贸然提出新理论,而是要真正在深入阅读理论经典的同时,去从事“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注]〔法〕福柯著,苏力译:《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4—138页。。同样,对于历史学和社会学而言,更为重要的事情或许并不在于学科分化本身,而在于研究者面对历史与社会事实,究竟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又能够对这些重要的“研究问题”作出何种解释?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回应,才是跨学科研究的内在意涵。
(本文作者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北京 100088)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专项资金”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吴志军)
标签:制度论文; 社会论文; 这一论文; 理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党史参考资料论文; 《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专项资金”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