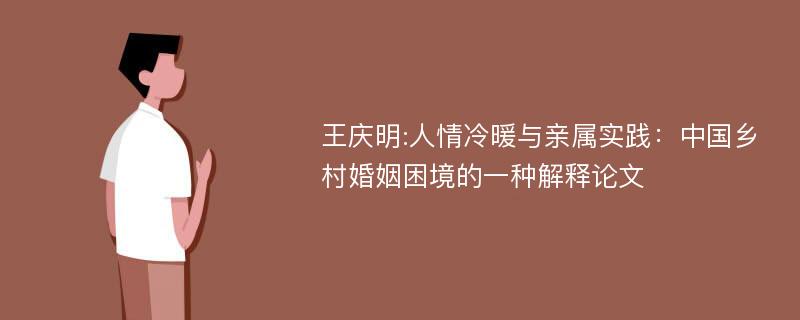
人情冷暖与亲属实践:中国乡村婚姻困境的一种解释*
■ 王庆明 王朝阳
王庆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王朝阳: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内容提要]既往婚姻困境研究主要着眼于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层结构等外生变量,强调乡村婚姻困境是这些结构和制度约束的后果。本文以豫东南一个相对闭塞的村落为个案,聚焦村落内部,探究“同村不同婚”的问题。研究发现,在家庭经济、空间区位、人口分布及信息流通等条件相似的前提下,血缘为依托的宗亲网络、姻亲为纽带的亲缘网络、认干亲达成的拟亲属网络和乡邻互助、礼尚往来为基础的人情网络是影响媒人产生和婚姻缔结的关键变量,四者共同构筑了一种实践性亲属网络。在亲属网络的实践及再生产过程中,宗亲、姻亲、干亲和乡亲关系之“亲不亲”,要看走得近不近,这不单取决于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疏,亦取决于礼物流动、人情往来造就的关系远近。村东荒地转租纠纷、离婚增多、拟亲属关系减少、外来媳妇对既往礼尚往来秩序的破坏引发不同宗姓之间人情淡漠和实践性亲属网收缩,导致无媒人,进而出现婚姻危机。
[关键词]人情冷暖 亲属实践 婚姻困境 实践性亲属网络
一、研究问题:同村不同婚
中国乡村研究领域,婚姻缔结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议题。婚姻既是两性结合的社会制度,也是影响两个家庭资源分配的经济制度(韦斯特马克,2017:35)。婚姻作为乡村社会的头等大事,不单意味着合法的双性抚育以及两个家庭(族)的联结,还是乡村社会亲缘网络以及各种关系再生产的基点。不同时代的婚姻缔结模式以及婚姻形态,是透视特定时空条件下乡村社会秩序及其内在权力结构的重要维度。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城乡关系的变化,乡村的婚姻困境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亦是学术研究的焦点。在事实层面上,乡村婚姻困境主要表现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男性青年的婚姻缔结困难,即俗称的“娶媳妇难”,一些地区甚至光棍增多。很多学者针对光棍产生的原因、分布结构以及类型展开讨论(刘燕舞,2011;宋丽娜,2015;陈文琼、刘建平,2016;李永萍,2015;邢成举,2011、2013;陶自祥,2011;谢小芹,2013;余练,2011、2017),呈现乡村婚姻困境的真实状态。纵观既往研究,除个别强调经济贫困和身体缺陷等个体因素对婚姻缔结的影响,研究者主要聚焦于外在结构因素,如有的着眼于性别结构,以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强调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或适婚青年的男女比例失衡是男性婚姻推迟或婚姻危机的原因(李树茁、胡莹,2012;姜全保等,2010);也有研究者从地域结构、城乡结构和阶层结构等视角强调村落以外的宏观结构性因素对乡村内部婚姻缔结的影响(童辉杰、赵郝锐,2015;靳小怡等,2016;方丽、田传浩,2016;苏玫瑰、张必春,2008)。这些研究从经验出发,描绘出乡村社会婚姻缔结的现实图景,揭示乡村婚姻困境的具体形态和成因,为反思婚姻缔结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事实参照。
然而,当笔者秉持这种认知走进田野点“郑村”①,河南省东南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村落,通过长期驻村调查,却发现与以往研究者刻画的婚姻困境完全不同的景象,即“同村不同婚”。所谓“同村不同婚”,就是在同一自然聚落,同样生存环境以及相似的经济条件下,以村落庙宇为分界的村西和村东两个(生产)队,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婚姻缔结模式。村西普遍遵循“说媳妇”的传统模式,以及与“媒妁之言”相关联的传统仪式和婚姻过程;村东却“无人说媒”②,婚姻缔结被迫选择“领媳妇”③以及其他变通的婚姻策略。从2000年④到调查截止的2018年6月底,村西婚姻缔结36例,除1例“流动婚”⑤,其余都是按传统模式缔结的“介绍婚”;同期村东婚姻缔结40例,按照传统模式缔结的“介绍婚”23例,“流动婚”1例,“领媳妇”的“外来婚”16例。
郑村的“同村不同婚”不单表现在婚姻缔结模式不同,还表现在婚姻稳定程度上的差异。具体而言,2000年至今,村西除了1例流动婚解除之外,没有出现过离婚案例,村东则有14起离婚案例,其中介绍婚破裂的11例,外领婚破裂的2例,流动婚破裂的1例。现在郑村25岁至45岁大龄单身男青年共有17人⑥,全部在村东。地理空间、经济条件、人口分布与信息流通皆无明显差异的同一村落,为什么婚姻缔结和婚姻破裂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形态?为什么婚姻困境唯独在村东出现?“村东无媒”(村东人语)与高离婚率背后潜藏着哪些村落内在权力结构的密码?
这些蹊跷的现象刺激着笔者进入郑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寻找答案。当地人给出的解释是:“村西风水好”“村东不团结”(“村西人护窝子,村东人各管各”)。第一种解释的根据是,郑村原有东西两座土地庙,“文革”中都被捣毁,后来只有村西复建了庙宇。第二种解释的依凭是,村西人都姓郑,由两个比较大的宗族和一个小家族构成,20世纪80年代这两大宗族之间又出现了联姻,亲上加亲使得原本就比较团结的郑姓族人更为亲密,平时红白喜事都相互支持,共同参与;村东为杂姓,包括郑、刘、胡、瞿、张五个不同姓氏,村东郑姓有三个宗族,彼此没有血缘关系,其中一个是村西郑姓一房的分支。限于篇幅,我们暂且舍弃“风水论”的第一种解释,试图从“团结论”的第二种解释入手“再解释”⑦,探究以宗族联结为基础的团结机制与婚姻缔结的逻辑关联。
以这个问题为指引,本研究将视域聚焦于村落内部,对郑村整体状况和两种不同的婚姻缔结模式作“深描”,在此基础上以事理逻辑反观以往的学理解释。为避免以偏概全,笔者历时性考察郑村1949年以来近七十年的婚姻模式,以丰富的婚姻事实为基础,呈现本个案的完整性。本案例是中原地区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村,是典型的“半工半耕”的农业社区,在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有一定典型性,具备乡村婚姻困境的一些基本特征,具有可观察性。我们从人情冷暖与亲属实践的历史维度分析“同村不同婚”现象背后的深层机理,并力图在与以往研究对话基础上拓展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
二、婚姻缔结理论的反思性回溯
在中国乡村,婚姻缔结与社会联结的方式及范围有着紧密的关联。通常一个村落的“社会边界”直接影响着该村落婚姻缔结的信息来源。由此,乡村社会关系网成为研究者分析乡村婚姻缔结的重要依据。研究者基于对乡村社会联结方式的认知,建构对乡村婚姻圈的不同理解。下文将围绕婚姻缔结的几种经典理论展开讨论,力图呈现既有研究的贡献和不足,继而从经验事实出发分析当下乡村婚姻困境的具体形态及其深层原因。
(一) “两族之婚”与亲属网络:宗族论的婚姻解释
陶希圣先生分析中国社会及其内在结构,指出“在宗法制度之下,婚姻是两族的事,不是两人的事。这个前提直贯到现代中国社会还是有效的。”(陶希圣,2015:204)在宗族与婚姻缔结的相关研究中⑧,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当属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他基于福建、广东宗族活动的考察,提出宗族是一种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地方性和组织性构成东南地区宗族网络的基本特征。弗里德曼强调血缘关系构筑的地方性宗族形塑了宗族内部不同家庭的婚姻交换来源,任何个体家庭的社会联系均建立在宗族的社会联系之上,依托社会联系缔结的婚姻很难摆脱宗族的界限而单独存在。外婚制出现以后,虽然社会联系构筑的通婚关系有时会跨越宗族间的界限,但在众多社会联系当中,由地方性宗族提供的社会联系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弗里德曼,2000:130-132)。
弗里德曼受到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水利社会”和“氏族家庭主义”(Clan Familism)分析的启发,将通婚、水利和械斗视为汉人区域社会形成跨村落联系的三种重要机制。在外婚制习俗的延续过程中,数个汉人宗族村落会逐渐形成一种交换婚配资源的圈子,这种圈子往往与械斗形成的联盟相互重叠。而水资源与婚姻对偶逻辑相似,都是流动的。水资源流过不同村社,围绕水资源的争夺会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了有效配置和共享水资源,不同利益群体又需要结合为超越村落范围的合作圈子(王铭铭,2004)。弗里德曼对通婚圈、械斗联盟圈和水资源合作圈交叠互动的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组织基础和互动机制,进而为分析婚姻缔结提供了广阔视野。
弗里德曼对中国东南地区分化社会中单系亲属组织的考察,参照了葛学溥描画的凤凰村以及林耀华笔下的义序村的生活图景(葛学溥,2012;林耀华,2000),由亲属制度构造出从宗族制度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该理论模式从宗族之间的联姻关系入手,试图在亲属制度和乡土社会结构之间建构一套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特征的理论范式。弗里德曼开创的这种理论模式是随后一系列中国宗族研究的源头(Watson,1982)。弗里德曼明确指出,在中国,一旦超出我们称之为“宗族”(lineage)的意义谈亲属关系时,涉及的便是“氏族”(clan)。宗族是严格按照单系血缘纽带组成的亲疏分明的拥有共同利益及活动的持续性群体,而氏族可以是同姓的不同宗族之间以共同的姓氏和祖宗祭祀结成的联合体(Freedman, 1966:21)。
从亲属制度和村社组织理解中国乡土社会内在秩序和婚姻缔结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中国宗族的复杂性出发,针对弗里德曼的“lineage”与中国“宗族”意涵的不同展开争论,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杨春宇、胡鸿保,2001;吴作富,2008;师云蕊,2010)。更有历史学者指出,在中国,宗族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国宗族实践展现的不是祖孙、父子之间代代相传的纯洁的父系血缘关系,而是在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条完整悠久的父系世系,并以此确保死后有人祭拜(钱杭,2009)。这种父系世系的建立和延续是通过婚姻来实现的。由此可见,无论强调“血缘”还是“世系”,婚姻缔结都是宗族再生产的前提,这一共识也为婚姻制度与亲属制度研究上的融合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 基层网络与宗族分化:市场论的婚姻解释
在亲属关系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将之视为一种有秩序的整体,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两性交往对于超地方社会形成的重要意义。传统的乡村社会,亲属关系成为跨村落群体间婚姻交换的重要资源。这一事实在既往的乡村研究多有呈现,如林耀华的《金翼》中描述黄姓新娘大多数是来自邻村欧姓一族(林耀华,2015:28-29),杨懋春也曾提到,山东台头“一个家庭的几个成员都与分布在一两个邻村的家庭结亲。比如一杨姓家庭的女儿嫁到台头村南五英里处的一个村庄,而这个家庭的儿子和孙子都娶了该村的女孩”(杨懋春,2012:103)。这些研究描绘了宗法社会体系里,村庄社区内以单系血缘为基础的亲属网络形塑婚姻缔结的生动图景。但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看来,这种理论似乎只适用于“聚居型村庄”,那如何解释中国分散型村社内部的婚姻缔结呢?
郑村祭祀,村西以宗族祭祀为主,村东多为家庭或家支祭祀。两种祭祀体系及其对待先祖的方式和态度不同,是影响亲属实践的重要范畴。村西的两大郑姓宗族,各自都有自己本族的祖坟地,且两家坟地相距仅50米左右。村西郑姓这两个家族在原村落就属同宗,迁到郑村,仍保持亲密互动。族中已婚成员去世,埋入祖坟,全体成员都会参与葬仪。村西祭祀常以集体形式出现,由族中长房带领族人完成“请祖”⑨“添坟”⑩等仪式活动,请回的祖先常供奉在长房家中,其他族人会在除夕夜和大年初一早晨到祖先灵位前磕头。村东祭祀有很大不同,除了村西郑武一房的分支郑赋家族外,村东大部分宗族以家户祭祀为主。
祖先祭祀作为血缘群体的一种重要活动,不单有香火延续、缅怀祖先的功能,还有团结群体成员和维系亲属网络的作用。这两种功能因祭祀主体的不同会有很大差别。在家庭祭祀体系下,被祭祀的对象通常是去世不久的人,一般不包括超过四代以上的逝者,祖先也不再是宗族的各裂变家族的中心,而是一种象征性存在,联结着各个继嗣单位。由子孙形成的几个家庭分别祭祀的人,仅仅是供奉对象,他与超越一个家户所在家庭之外的亲属单位的维持没有直接关系。在家族祭祀语境下,祖先则不再是单一家庭的供奉对象,而成了宗族群体意识的一部分。家庭祭祀更多是出于对祖先的缅怀和纪念,对固定亲属组织的作用不大;宗族祭祀是集体行为,在这一集体行动中,亲属体系各分家单位之间的情感在仪式过程中得以表达和强化(弗里德曼,2000:104-114)。
宗族视域下的婚姻缔结,一般是一个宗族按照传统方式将本族内的年轻女子嫁给另一个宗族男子为妻的结构模式,这种婚姻缔结遍布基层市场社区内,而且因婚姻缔结形成的姻亲网络使得基层市场社区的结构更为完整。一个村落的婚姻缔结形态与该村落的历史形成密切相关。通常新的村落是由一个家庭或由一部分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建立。这种新村落中的家庭,构成他们原来村落宗族的一个支系。经历数百年演变,很多村落仍然维持着大量的同姓氏的地方化宗族。施坚雅在这里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在地理区位以及组织结构都相似的不同宗族之间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互动模式:一种模式是相近的地方宗族之间的联系会持续存在并进而演化成有组织的统一体;另一种模式是,具有同样的历史祖先的宗族之间却各自独立?他的结论是,不同的基层市场对不同的地方宗族构成了分割和形塑(施坚雅,1998:46-47)。
施坚雅的市场论分析揭示了在特定的村社结构下,基层市场对地方宗族及其亲属网络的分割作用,以及对婚姻缔结的独特功能。施坚雅强调乡村社会关系网是以基层市场为单元的跨村落的社会联结,造成该联结方式出现的原因是分散型村庄的存在和生产流通的需要(施坚雅,1998:7)。基于此,施坚雅认为市场社区的范围构成了乡村青年择偶的地理边界和选择区间,市场圈与婚姻圈重合,是分散型村社婚姻缔结的重要特征。
一如施坚雅强调宗族论的婚姻解释不适合四川盆地一样,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指出施坚雅市场论的婚姻解释并不适用于华北聚村而居的乡村社会。不同的是,杜赞奇试图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概念来整合“宗族论”和“市场论”的分歧。杜赞奇强调,不同的村庄类型,社会联结形态以及婚姻缔结模式有所不同,他提到:“曾有13个村庄向寺北柴村嫁女超过5个”,此外“昌黎县侯家营的村民称,他们多从新金堡寻觅新娘,是因为他们与该堡的邢、朱二姓多有亲戚关系”(杜赞奇,2003:7-8)。聚村而居的村落相对来说社会联系较为紧密,村民纽带、街坊邻里关系等在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基层市场对于这两种类型村庄,功能和形态明显不同,表现在,基层市场对于分散型村庄有可能是唯一的联结中心,对于聚居型村庄不仅有基层市场,还有宗族、宗教、会社、水利组织(杜赞奇,2003:7-8)。各村社以不同的组织实现社会联结,这些组织相互交织,构筑巨大的网络。可见聚村而居的村落可能是多中心联结结构,多中心交叠互动构成权力文化网络,是乡村婚姻缔结的基本范畴。
以上几种理论解释,均是从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组织出发,试图在婚姻圈与社会联结方式及其范围之间建构一套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理论范式。弗里德曼侧重分析血缘组织、姻亲组织及其范围在婚姻圈中扮演的作用,施坚雅和杜赞奇侧重探讨婚姻缔结的组织基础,如宗教、会社、水利、市场及其伸缩范围与婚姻缔结的联系。尽管他们对构成乡村婚姻圈的组织要素认知上存在分歧,但都揭示了影响乡村婚姻缔结的要素不是单一的。这些研究呈现了中国乡村静态结构下不同关系网络对婚姻缔结的影响,忽略了社会变迁以及动态演化过程中关系网络的伸缩和弹性机制。
(三) 亲属实践与婚姻策略:弹性亲属网络的解释
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亲属网络是最重要的。然而,当社会急剧变迁,原本相对稳固的关系网络也明显地伸缩。这既关乎亲属关系的概念范畴,亦关乎亲属关系的实践逻辑。亲属关系的概念,不同学科的界定有很大差异。从法学上讲,亲属是自然人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发生的身份关系,通常包括血亲、姻亲和配偶。遗传学和社会学上,亲属则泛指婚姻缔结和血缘谱系链接的一切具有血缘同源性、姻缘相关性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亲属只包括血亲、姻亲,不包括配偶,亲属关系是一种网络化的生物遗传结构和婚姻社会结构的交叠(梁慧星,2013:18-19)。然而在实践中,亲属关系的范畴和边界不是恒定的,而是随着特定场域中的习性而不断变化。
为了超越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静态观念,以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简单二元对立,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经由亲属实践和婚姻策略提出了实践逻辑的概念。布迪厄发现,一个社区内的民众对同一种类型的婚姻有不同的解读,且解读的多样性自有其客观依据,即仅在系谱上相同的婚姻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义和功能。这很难用简单的主客观标准来分析。在真实的世界中,婚姻的缔结及其形式,并不全部由正式亲属关系内部的结构决定,而多基于实践性亲属关系的状况影响(布迪厄,2012:274-282)。
在实践中,不同的性别对同样的关系结构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塑和意义诠释,即男人和女人对相同的(血亲或姻亲)系谱关系场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人们对于因婚姻圈狭窄而造成的边界模糊的亲属关系有不同的解读和利用。作为一种重要策略,人们可以将系谱上最远的亲属关系拉近,也可以将最近的亲属关系疏远或分离(布迪厄,2012:272)。在这里,布迪厄注意到了实践的过程性,以区别于制度和结构,但布迪厄的过程甚少考虑历史因素。基于此,黄宗智先生提出需要引入实践的“历史维度”,进而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特定场域实践的完整性(黄宗智,2015:263-264)。阎云翔在布迪厄亲属实践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东北汉人移民村落亲属网络的历时性考察,对实践性亲属关系的伸缩性做了进一步探讨。
阎云翔发现,亲属关系网络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不断变化。借用布迪厄“实践的亲属关系”(practical kinship)概念,阎云翔指出实践中的亲属关系实际上是一套既可以“收缩”亦可以“扩张”的人际关系。在传统汉人社会宗法体系下,以“血缘”和“世系”为基础的宗亲(血亲)是亲属网络的主导机制。但阎云翔发现,黑龙江下岬村这个以移民为主体的东北汉人社会的亲属网络中,姻亲占有更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婚事、寿诞及建房等重要庆典和仪式,还是农业生产、经济合作以及政治联盟,姻亲较之于宗亲都是更重要的纽带(阎云翔,2017a:95-96)。
此外,亲属关系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在阎云翔笔下,“文革”时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下,同宗老人葬礼期间,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纽带使得不同家庭出身的孝子们逾越了阶级差异形塑的政治界限。基于此,阎云翔强调亲属关系具有可变通及易变性本质,这既造成亲属关系结盟的不确定,又重塑着亲属关系的实践过程。虽然亲属关系研究并未超越宗族理论范式,但指出了在持久性结构原则之外,由日常实践造成的亲属关系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亲属纽带成了一套在不同的语境下意义不同的关系建构体(阎云翔,2017b:129-130)。此外,阎云翔还注意到随着个体的不断解放,以朋友为纽带的私人性关系对于亲属网络的独特作用。阎云翔拓展了布迪厄“实践的亲属关系”的概念范畴。
布迪厄所说的亲属关系人为“拉近”或“疏远”,意在强调实践活动既受内在规则、信念、习性的影响,还受制于时间、空间、情境等因素(布迪厄,2012:87-109)。阎云翔在布迪厄的基础上,具体揭示了亲属关系在实践中的伸缩过程和其他关系网络对亲属网络的形塑作用。其实,其他社会关系在实践过程中同样具有易变性特征,由此需要对中国乡村婚姻缔结形态的变迁进行多元的立体性分析。社会关系及其联结方式是影响婚姻缔结的重要因素,循此逻辑,我们试图从社会关系的实践逻辑入手探究郑村内部“同村不同婚”“村东无媒”和婚姻缔结困境的内在机理。
郑村是豫东南一个相对闭塞的自然村,原住民瞿姓家族人丁不旺,现在主要由垦荒种地的外来农民及其后人聚居而成。郑村外来户的姓氏主要有郑、张、刘、胡四大姓。从当地家谱和口传故事了解到,郑姓族人18世纪40年代最早迁入,胡姓最晚,只有五六十年历史。这些外来的不同宗姓,除了投奔亲戚的郑文家族,其余所有家族都来自郑村四周5公里以内的邻村,而且都不同程度地和原村保持联系,详细情况参见表1。
表1:郑村各姓氏迁移情况统计表
三、案例呈现:一个村庄内不同的婚姻形态
(一) 作为个案的郑村
然而,在中国地域差别极大,且急剧变迁的乡村社会,追寻日常交往轨迹时,拘泥于“婚姻圈”“祭祀圈”等“普适”的解释论,很难发现乡村社会中婚姻缔结的实践逻辑和日常交往轨迹,任何认识或定论都不可能是普适的(吴重庆,1999)。基于此,笔者试图从经验出发完整地呈现郑村婚姻缔结的特征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婚姻缔结与村庄权力秩序的逻辑关联,通过对“同村不同婚”这一经验现象的分析,从长时段考察郑村婚姻缔结的独特逻辑,进而对当前中国的婚姻困境提供一种经验连接理论的学理性解释。
郑村规模较小,与附近其他5个自然村共同组成一个村委会(大队),行政中心设在距郑村3里的刘村。大队下辖的5个自然村又细分为15个生产小队。郑村有2个生产队,即村西十四队和村东十五队,每个生产队内又分2个生产小组。与同一村委会下辖的其他5个村子相比,郑村最小,该村只有一个村委会委员(被村民称为“村长”),负责管理本村事务,村党支部书记多由村委会所在地刘村的人担任。
郑村行政权力边缘化和地理位置的偏僻有一定关系。郑村位于几个不同市县交界处,是比较孤立封闭的小村落。该村的位置远离各级行政中心,距离村委会1.5公里,距离乡政府4公里,距离县级政府约36公里。该村交通不便,东西方向是乡间土路,向北的道路被界河阻断,只有向南的方向修了两条水泥路通往村外。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老人过去把自己的村子叫“郑涯”,“涯”字反映出了当地人位于边缘角落的村落心态。郑村的封闭性使得该村婚姻缔结与人口增长的“内生动力”更具有分析的价值。截至2018年6月底,郑村共有187户,790人。其中,村西77户,359人;村东110户,431人,详细数据参看表2。
表2:郑村各姓户数人口情况统计表
注:本表中的户,是指子代成家并和父母分 家单过之后组成的家庭。
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郑村的生活水平一般,该村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外出打工和做小生意为辅。农业生产遵循传统,冬季作物以冬小麦为主,夏季作物以大豆和玉米为主。土地是郑村人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20世纪50年代土改后郑村划分到土地1440亩。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村社中,不同宗姓人口繁衍速度的不同往往与婚姻缔结的差异有关。例如集体化时代,村东和村西两个生产队的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基本持平。至改革开放初期,村东的人口慢慢超过村西,到现在村东比村西多72人。主要原因是村西郑姓地主家族的男性青年因成分不好出现了婚姻危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村西郑姓有十多个光棍儿,降低了人口增长速率。
20世纪80年代初期,郑村人民公社解体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最初郑村所有村民人均耕地面积相同,后来家庭人口数量变化以及土地承包政策限制,造成村东、村西两个生产队之间以及生产队内部不同生产小组之间人均耕地面积的不同。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分田单干后,郑村仍然保留了生产队和生产组的行政设置。在国家延长土地承包期的政策下,一方面郑村贯彻执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每个生产队及生产组占有的土地没有增减;另一方面,因人口变化,每个生产组内部变通性地调整土地,由此造成村西和村东之间以及各生产小组内部人均土地资源占有的差异。详细情况参见表3。
其次,通过“说媒”缔造新型亲缘关系的机会大大降低。在介绍型婚姻中,大部分媒人与男方或女方家庭有一定的亲戚关系。新婚姻一旦缔结,媒人与双方家庭变成更稳固的亲缘关系。亲属关系转变强化人情关系,同时也扩大了彼此的社会联系。但是外来媳妇这种“无媒”婚姻的增多,新型亲缘关系的再生产面临困难。
虽然村东人均土地较少,但因村民外出打工早,且做生意的多,村东与村西总体的经济水平并无明显差别。历史上,村东和村西的边界也并不清晰。前文已经交代,郑村曾有两座土地庙,一座在村西,一座在村东,并不存在严格的边界。此外,村东、村西生产队的划分虽构成一个行政边界,但人民公社解体后这一边界愈渐模糊。加之村东的郑赋家族本来就是村西郑武家族一房的分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亲网络时常冲破并不严格的行政边界。由此,笔者概括的“同村不同婚”并不是指涉两个边界清晰的村社聚落,而是针对同一村落共同体内部不同的婚姻模式。从“同村不同婚”的经验事实出发,本研究试图揭示郑村人朴素认知背后潜藏的社会连接与婚姻缔结的特殊逻辑。
在土壤中分别施加质量百分数为0、2%、4%、6%、8%的生物炭后,测得土壤水吸力值与含水率之间的关系曲线,然后将实测数据用Van-Genuchten模型进行拟合见表1,得到实测数据和拟合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如图1所示,图中各点为实测体积含水率,曲线为拟合体积含水率,可见拟合效果较好,实测值与拟合值近于重合,须计算其相关性系数来比较实测值与拟合值的差别。
表3:郑村人均占有土地情况
(二) 何人为媒?郑村媒人的类型与分布
在郑村,明媒正娶依然是婚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绝大多数年轻人通过媒人介绍实现婚姻缔结。媒人主要来自农户家庭的关系网。具体主要由四种关系网叠加而成: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亲属网;二是以姻亲关系为纽带的亲缘网;三是通过认干亲达成的“拟亲属”网;四是礼尚往来和乡邻互动为基础的人情关系网。即便是职业型媒人通常也与这几种关系网相互交叠。
出于对媒人类型学及其背后社会关系的关切,笔者对郑村现存231例婚姻关系进行调查,其中最早一例婚姻1954年缔结,当事人已年过八旬,最近一例婚姻2018年2月1日(即农历腊月十六)缔结。郑村231例婚姻,媒人属于宗族亲属型的98例,占比42.42%;媒人属于姻亲关系型的54例,占比23.38%;媒人属于人情关系型的36例,占比15.58%;媒人属于拟亲属型的11例,占比4.76%;2例媒人属于职业型,其余30例属于其他,主要是无媒人类型,占比12.99%,具体情况参见表4。
笔者希望通过对郑村现存婚姻缔结形态的调查和初步统计,以历时性视角刻画郑村婚姻缔结模式变迁的完整图景。下文将对不同婚姻类型及其特征作详细讨论。
在郑村,地方宗族和制度性亲属常常为同宗家庭成员提供婚配对象信息。例如村东的刘继承20世纪80年代初把妻妹介绍给堂弟刘继连,他们不仅是堂兄弟还成了连襟,1995年刘继连的父亲为刘继承的儿子保媒成功。这种通过宗族亲属网络获取婚配信息的现象在华北地区比较普遍。调查发现,231例婚姻,有98例的媒人属于血亲关系,占比42.42%。村东刘姓宗族的案例反映出,宗亲关系与姻亲关系有时是相互叠加的。
作为血亲关系的补充,姻亲关系在郑村的婚姻缔结过程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到“在栾县30宗婚姻缔结中,13宗是由男女一方的亲戚充当介绍人,7宗婚姻的介绍人是同村的亲友”(杜赞奇,2003:7)。外村亲戚和同村亲友充当媒人在郑村也非常普遍,“亲戚说媒”甚至构成亲缘互动的一种重要方式。例如邻村的张权是村西郑安民的堂姐夫,两家往来频繁,1992年张权为郑安民的妹妹说了一桩媒,2006年又为郑安民的儿子保媒成功,2008年郑安民把外甥女介绍给张权的大儿子,促成一桩婚姻,让原本就是亲戚的几个家庭亲上加亲。这样经由姻亲关系达成婚姻缔结,在郑村比较多见,通常男女双方或一方与媒人之间有姻亲关系。郑村现存婚姻有54例中媒人属于姻亲关系,占调查总数的23.38%。
中原地区村社杂姓混居,通婚关系通常很少能在两姓宗族之间稳定地存在。这使得每个宗族内的家庭,尤其是宗族规模小的家庭不得不借助其他宗族的社会联系,在村东,这尤为普遍。村东小宗族多,与其他地方社区的联系有限,不得不借助其他家庭的社会联系,弥补婚配资源和信息的不足。不同家族的成员之间为了子代的婚配而充当媒人,会促进并加深相邻家族之间的人情关系。例如村东张文龙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邻居刘革荣保媒成功,后来刘革荣给张文龙的二儿子、两个侄子以及一个孙子说了4桩媒,再后来张文龙的侄子又为刘革荣的女儿保了媒。这种以乡邻互动为基础的“中间关系人”可称为“人情型媒人”,男女双方或一方与媒人之间存在人情关系。在郑村,人情网络构成了实践性亲属网络的一个重要类型,现存婚姻中有36例的媒人属于人情关系型,占调查总数的15.58%。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作为国字头的标准化研究机构,从标志上展示了自己全国化、国际化的品牌定位(见图2)。除本身外,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品牌信息还来自其下属的15家研究机构。比如,2017年5月至7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开展了其下属机构“标准情报研究所”的LOGO有奖征集活动,最终征集到92件作品。征集活动提高了社会对“标准化”和“情报所”的认识,也加深了社会对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品牌认知。
表4:郑村婚姻形态与媒人类型
乡邻互动,尤其在说媒过程中,人情关系有时会转化成直接的亲缘关系。人情关系型的媒人大部分是将自身血亲关系网或姻亲关系网内的女性介绍给被说媒的一方。婚姻缔结后,这种血亲或姻亲关系,使得媒人与男(女)方家庭之间便达成了间接的亲缘关系,这种实践过程常常使得郑村的人情关系在“说媒”后朝着亲缘关系转变。
除了原有关系网络之中的礼尚往来,通常新人情关系还可以通过认干亲、拜把兄弟等“拟亲属关系”实现。拟亲属关系是在人情关系基础之上的一种类亲属实践,即试图突破人情关系,向着更进一步的亲属关系靠近。除了简单的认干亲仪式,“说媒”是这种非亲属关系“亲缘化”的另一种实现路径。问及郑村人为什么要“认干亲”,他们解释说“这是老传统了,老辈人常说吃百家饭的孩子好养活”;问到如何选择“干亲”,他们解释是“如果两家关系处得不错,就把自家的孩子‘认给’另外一家”。调查发现,拟亲属充当婚姻中间人并不鲜见,并构成了一种“拟亲属型媒人”的独特类型。例如郑启忠的母亲认张赓为干儿子之后,为张赓的弟弟说成了一桩亲事,张赓后来又做了郑启忠的媒人。到张赓的孙女张莉莉长大成人,郑启忠又为张莉莉保媒,将自己的远房外甥介绍给她。郑村现存婚姻关系有11例属于拟亲属关系型,占总数的4.76%。
以上四种关系构成了郑村历史上婚姻缔结的主要来源范围。此外还有2例职业型媒人充当婚姻中间人的情形,再有就是30例“非介绍型婚姻”,占郑村婚姻总数的12.99%。郑村近六十年婚姻缔结过程中,媒人作为中介的婚姻占绝对多数,而媒人的类型,除了宗亲和血亲的主导性关系,以乡邻互动为基础的人情型媒人和拟亲属性媒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变迁加剧和城乡关系的调整,郑村的婚姻圈也呈现动态变化。总体而言,婚姻圈与上述几种关系保持密切的联系,使得婚姻圈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展现结构性特征,表现为社会联结方式及其范围常常决定着郑村婚姻缔结对象的来源。
(三) “村东无媒”:村东的婚姻危机与变通策略
分田单干后一段时间,因为人均土地较多,郑村婚姻缔结相对容易,基本都能“说上媳妇”。2000年开始,郑村的婚姻缔结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一是,彩礼数额突破1万元,让处于适婚年龄的男性青年家庭倍感压力;二是,村东因为盐碱地转租引起宗姓之间纠纷,一些农户之间彼此见面甚至“不再说话”(即“结仇”,不再交往),这使得村东人情关系变化很大,“说媒”由“大家的事儿”逐渐变成了“自家的事儿”。这种背景下,村东与村西之间在婚姻缔结上出现分化,具体表现为村西依然遵循着传统的婚姻缔结模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与之相关的婚姻缔结仪式;村东却“无人说媒”,并呈现出诸多变通性的婚姻策略,具体包括外领婚、(村社)内部婚、买卖婚、入赘和“娶过门女”等。
“去媒人化”之外,“去仪式性”也是郑村外来媳妇的一大特征。外来媳妇进门一般是没有结婚仪式的,多数是“领回来” 直接同居,直到第一个孩子出生办满月酒席,才会通知亲朋好友来祝贺。在乡村社会,特殊而庄重的仪式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它唤醒集体之间的身份认同,促进情感交流。仪式性场合也增加彼此间的社会认可,原本相对生疏的社会联系通过特定场域内的互动得以恢复或增强。外来媳妇“去仪式性”和“去媒人化”,改变了乡村社会传统的联结方式。
四、人情冷暖与亲属实践:村东与村西的比较
日常生活实践中,以亲缘网络和人情互动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并非恒定不变,而会“收缩”或“扩张”,对于不同宗族群体来说,社会关系的伸缩影响该群体内部青年的婚姻缔结及其亲缘网络的再生产。村东的婚姻危机以及同村不同婚的现实样态,又折射出村东和村西在社会关系的收缩及其实践上怎样的差异呢?
传统的钨、钼加热炉只是在炉内通有保护氢气,在炉外没有保护,因此在高温材料从炉内取出时,因为炉膛内压力的降低,造成炉外空气进入炉内,增加的火封装置能够在炉口形成火帘,阻止空气进入炉内,保持炉内气氛稳定,同时避免爆炸。
(一) 祭祀体系与亲属实践的差异
亲属关系的转变构成了近年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事实。很多学者注意到,血亲关系地位下降,姻亲关系地位上升以及乡村社会关系进一步亲属化(阎云翔,2000;贺雪峰,2003;张庆国,2003),体现为农村生产合作中,姻亲参与的比例增加以及村内联姻增多。然而,郑村的婚姻实践却不完全相符。在郑村,血缘亲属关系仍然占据社会关系的主体地位,村内通婚往往是无男孩家庭的被迫选择;血缘亲属和宗亲关系的实践上,村东与村西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在祭祀实践中尤为突出。
通过采取科学有效的识记方式,学生在记忆单词时的难度明显降低,对于词汇学习的兴趣也会提升,自然能更好地融入英语课堂。
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可以给管理者们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更可以让员工约束其自身,促进工程进度,打消员工消极怠工的状态,增强团队的管理体系,完善制度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村东和村西祭祀上的差异,与宗姓间对自家坟地及祖宗的认同有关。如村东张姓虽然有统一的祖坟,但已多年不再埋入逝者。后来张姓“老哥仨”开辟了各自的坟地,目前这三处坟地也有两处已经废弃,再后来一些家庭大都在自家承包地开辟了更多的新坟地。村东一些宗族的坟地分裂往往有三个原因:一是原祖坟地已经没有足够空间,被迫开辟新坟地;二是宗族成员在新坟地的选择上不能达成共识,各房各支都不愿意将自家田地作为共同坟地使用,最终不得不“各埋各家”;三是不同代际对先祖和“老家”的认同有差异,如村东刘姓第一代老人去世后,多数选择送回“老家”即原村安葬,第二代之后对“老家”不熟悉也没有认同,便各自选择了新坟地,形成了以各房支为主体的开坟现象。以上各种原因造成了村东在祭祀上,以家庭或者说以家支祭祀体系为主。
在施坚雅调查的四川盆地,农民住在分散的或三五成群的农舍中,这种“分散型村庄”通常以土地庙为中心,构成一种独特的社会体系(施坚雅,1998:6-7)。这种社会体系需要经由基层市场,将分散居住的自然村社连接起来,以实现资源的有效互通。在分散型的村社,婚配信息的交换以及婚姻缔结通常需要借助基层市场来实现。在分散型的村社结构下,农民的社会区域边界并不是由所在村落的狭窄范围决定,而是由基层市场的辐射范围决定。基层市场不单有明显的经济边界,还具有重要的社会边界和社会范畴。基层市场是农民日常交易的场所,也是宗族、宗教、秘密社会等社会组织的载体。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市场社区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独立性特征,一个地区的基层市场社区在语言、饮食和衣着穿戴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性、独特性(施坚雅,1998:40)。可见基层市场不单是分散型村社日常交往和社会流动的交汇点,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和中间社会结构。但问题是,在婚姻缔结上,地方性宗族及其亲属网络与市场网络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联呢?
家庭祭祀丧失了固定亲属组织的作用,造成了村东与村西人在亲属实践上明显不同。具体而言,村西的亲属实践仍然以血缘关系的亲疏作为判定关系远近的主要准则,当然因分家等矛盾造成兄弟纠纷的情况除外。村东的家庭祭祀体系,使得非共同祭祖的同宗族人之间的亲疏远近,不再以血缘关系为单一纽带,它同时取决于单个家庭之间的互惠和交往程度。如村东刘武的三个儿子成家后关系不睦,三兄弟在刘武过世后各自祭祖,在生产或其他重要事件中也交往不多,他们的关系甚至远不如与其他远宗家庭或邻居的关系好。这种亲属实践的差异,使得村东和村西的宗族密度明显不同,造成村民印象中“村西人护窝子,村东人各管各”的局面。
在郑村,实践性亲属关系不单包括以血缘为纽带的宗亲关系、以婚姻缔结为前提的姻亲关系,还包括由亲属实践而产生的其他“类亲属”关系。实践性亲属关系在村东与村西之间同样存在着一定差异,具体表现在:相较于村西而言,村东的实践性亲属关系不断地被削弱和破坏,如村东离婚增多、干亲关系减少以及外来媳妇对礼尚往来秩序的破坏等。
(二) 离婚与失序:姻亲关系的实践困境
1978年至2018年,郑村共有20桩离婚案例,村东占18例,村西只有2例。就离婚的时期来看,最早的在1993年,5例出现在2000年以前,15例出现在2000年以后。就离婚的类型来看,3例是流动婚、3例是外领婚、14例是介绍婚,具体情况参见表5。
因为时代在不断变化,所以“互联网+”模式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相比较传统的组织结构会发生较大的改变,整体的组织结构会更加扁平化,还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组织形式不断出现。所以人力资源管理者要不断跟随时代的变化,并且及时进行调整。
经表5可见,村东与村西的离婚率明显不同,这是开篇所说“同村不同婚”的内涵之一。郑村的介绍型婚姻,一般是先由媒人介绍认识,在得到子女同意后,由父母全权主持操办的传统模式。介绍型婚姻虽然一定程度上要征求子女意见,但大部分决定权在父母,谈婚论嫁的过程中子女会受到家庭、媒人或亲戚的“胁迫”。问题在于,同样是介绍婚,为什么离婚主要在村东出现?村东如此多的离婚又给村社内在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哪些重要影响呢?
通常婚姻缔结形态不同,离婚过程也不同。郑村多为事实婚,领取结婚证的不多,这三种离婚类型各有特征。按传统模式缔结的介绍型婚姻,若夫妻不和想离婚,必须男女双方的家庭(族)与媒人同时介入,经过几轮撮合,三方都认可后才能离婚。村西郑姓宗族内部的介绍婚通常是内在宗族网络、亲缘网络以及人情网络交叠而成,宗族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对男女双方都构成了重要约束。在村东的离婚事件中,宗族的约束作用不明显。“领媳妇”这种婚姻模式的离婚相对简单,具体体现为外来媳妇“出走”;“流动婚”破裂则表现为男女双方“散伙”。当地人对这三种离婚有不同称谓,介绍婚的破裂才用“离了”,外领婚的破裂用“走了”,流动婚的破裂多用“散了”。介绍型婚姻最被乡邻郑重看待,其破裂过程是本文关注的主要议题。
在分析我国南方集体林区的发展现状后,能够从比较科学的角度,掌握林下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影响林下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为经营主体文化程度。一般来说,林下经济活动开展的主体多为林区农户,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其文化程度和学历水平呈现出相对较低的现象。因此,在日后促进林下经济效益发展时,应加强对经营主体文化程度的重视。
表5:1978年—2018年以来郑村离婚情况
村东大量的介绍型婚姻的破裂,给村东造成三种社会后果:首先,离婚造成原通婚宗族之间关系敌对,在乡村社会,由通婚关系构筑的宗族联结是地方社区之间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通婚关系破裂,不仅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终结,同时意味着双方所属宗族间联系的中断。其次,在血缘关系地位日益下降,姻缘关系地位持续上升的今天,通婚关系的破裂会导致该家庭丧失来自姻亲家庭的帮助与合作,家庭的整体社会关系网削弱。最后,随着婚姻失败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宗族或家庭在子代婚姻缔结上面临更大压力。对于过度依赖社会关系的介绍型婚姻来说,与其他地方社区联系的减少意味着婚姻交换机会减少和婚姻缔结秩序的解体。概而言之,随着离婚增多,不单对村东婚姻缔结的双方家庭构成消极影响,还对传统介绍型婚姻的缔结秩序构成冲击,实践性亲属关系失去了持续再生产的基础。
媒人介绍、达成婚姻,是郑村实践性亲属关系再生产的前提。前文提及,郑村的媒人大都来自宗亲、姻亲、干亲以及人情关系网,媒人通常是将自己血缘关系网或姻亲关系网内的女性介绍给男方。婚姻达成后,与女方家庭的这种关系,使得媒人与男方家庭从邻里或朋友关系演变成间接的姻亲关系,在“说媒”后郑村的人情关系朝着“更亲”的方向转变。然而,随着离婚增多,村东多数人总体上开始回避或者拒绝为人说媒。
通过强化监督队伍,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延展,监督的探头越布越多,监督的专业能力越来越强;各单位对监督队伍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渐提升 ,完善激励与保障机制。
没有媒人,打破了村东传统的介绍型婚姻的缔结秩序。1993年至2018年,村东18例离婚案例中有3例实现了再婚,1例复婚,其余14例一直没有婚姻的再缔结。郑村青年一般在20岁左右谈婚论嫁,如果男子25岁没娶上媳妇就被称为“难题”。离婚增多及其对社会网负面作用的累积,使得郑村大龄男青年不断增多,截至2018年6月,村东25岁至45岁的大龄单身男青年有17人,具体情况见表6。
没人说媒是村东大龄男青年增多的直接原因,小家族亲缘网络的收缩以及人情关系的破坏造成了“无人说媒”的窘境,有的家庭甚至“一门俩光棍”,如表6所示,张金铭与张金仁、郑伟与郑阳、刘广阔与刘广远都是“光棍儿兄弟”。调查发现,村东拟亲属关系减少,是媒人减少的重要原因。历史上,村东和村西之间以及村东不同宗姓之间均有认干亲的传统。这种拟亲属关系对于双方家庭情感、社会关系以及其他资源的互换交流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郑村内干亲关系减少并出现干亲地理半径收缩的现象。此外,外来媳妇增多对传统乡村社会内部人情互动秩序构成了一定挑战,让原本就脆弱的人情关系雪上加霜。下文从拟亲属关系变化和外来媳妇的意外后果讨论村东实践性亲属关系的伸缩机制。
表6:村东大龄单身男青年情况表
(三) 实践性亲属关系的伸缩
1. 拟亲属关系的减少
中国乡村社会人际关系有三种类型:亲属关系、非亲属关系和“拟亲属关系”。拟亲属关系通常通过认干亲和拜把兄弟(或认姐妹)实现(尚会鹏,1997)。拟亲属关系是建立在人情关系上的类亲属实践,即试图突破人情关系,向着更进一步的亲属关系靠近。拟亲属关系双方虽非制度化的亲属,但双方行动常表现出积极、热切的特征。一般来说,拟亲属关系主要在两个异姓或同姓不同宗的家庭或个人之间建立。
早期郑村拟亲属关系大部分存在于村西和村东之间,尤其村东刘姓和村西郑姓互认干亲频繁。20世纪90年代后,村东西间建立拟亲属关系的行为开始减少,村东人之间建立这种关系的行为增多。2000年以后,不论村东村西之间,还是村东内部,认干亲的行为都在减少。调查显示,近60年来郑村共有21对干亲关系,涉及41个家庭,其中有1例两个家庭的男孩同时认了一个干娘。这21对干亲关系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5对,都是在村西村东之间。1980年—2000年有14对,其中9对在村东村西之间,4对在村东内部,1对在村西内部。2000年至今只有2对,1对在原本就同宗的村东郑赋家族与村西郑武家族之间,另外1对在村东张姓同宗之间。一方面干亲关系减少,另一方面认干亲的半径收缩,由村东和村西转向各自内部,甚至转向同一宗姓远房之间。这削弱了村庄内部的人情关系网,也一定程度阻断了情感、资源在不同家庭之间的流动和交换。
2. 礼尚往来中断:外来媳妇的意外后果
外来婚姻指的是相对于婚出地而言,婚入地所具有的异文化特质。因此,对“外来媳妇”的界定总是依托于对“本地媳妇”的区别而言(谭琳、柯临清,1998)。郑村人所说的“外来媳妇”是指“从外边领来的媳妇”,“外边”不仅仅指村庄的空间边界,还指传统的婚姻缔结网络。郑村较早的外来媳妇在20世纪80年代,家庭贫困和政治成分是这一时期“外来媳妇”出现的主要原因。2000年以后,村西再没新进外来媳妇,村东却不断增多,截至2018年6月,村东共有16位。这种情况,村东人的解释是“没人说媒”,“如果有人说媒的话,谁还会让自家孩子去外面领,领来的媳妇能不能过下去很难说,如果有一天她跑了,你去哪儿找去?”⑪领媳妇是迫于无奈,“无人说媒”才是外来媳妇增多的关键原因。前文就“无人说媒”的原因做了一定解释,接下来讨论外来媳妇增多给村东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
嘉兴市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及成果应用的实践与思考(韩向宇等) ...................................................................2-38
婚姻缔结是乡村社区不同家庭或家族之间重要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常常跨越家庭、宗族甚至基层社区,不断向内向外延伸。向内延伸主要是通过媒人完成,向外延伸则借助亲属网络。这两种延伸随着外来婚姻的增多而削弱。
首先,不同层面的人情“亏欠”或“互惠行为”交织一起,使得乡土社会人情关系得以延续。各种人情“亏欠”中,没有比保证自己宗族延续和子孙绵延的人情更大的了。因而婚姻缔结中,“人情亏欠”在维系人情往来上有重要作用。然而,外来媳妇的“无媒”或“去媒人化”,使得村东人之间的人情互惠遭到削弱。
计算机检索EMbase、PubMed、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MB)、维普数据库(VIP)和万方数据库。中文检索词为阿替普酶、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急性脑梗死、不同剂量、中国人群、随机对照研究(RCT)等。英文检索词为alteplase,acute ischemic stroke,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different doses,Chinese patients,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等。检索时间从建库-2018年3月。
表4参数与Ea间相关系数大于0.5的项数11/19=58%,而且大于0.7的项数有2项,粗略判断初选的结构参数是有效的。如果相关性普遍较低,就应考虑调整、扩充特征参数的选择范围。
村东出现婚姻困境以及策略性的婚姻缔结现象,村民的解释是“无人说媒”,“说媒”由“大家的事”演变成“贴身人的事”之后,村东的婚姻缔结陷入困境。至于为何无人说媒,村民的回答是“村东的人和过去的人不一样了,现在谁都不管谁”。“谁都不管谁”这句话折射出村东人情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在同一村落,为什么人情冷暖只给村东带来了婚姻危机呢?是什么使得“说媒”在村东成为“难事”或“闲事”?
(四) 荒地纠纷:人情关系的破裂
人情关系的差序格局有时并不是因为群己界限的伸缩,而是源自直接的利益分配。村东人情关系淡漠的又一个原因,恰恰是荒地资源配置引发的不同宗族之间的纠纷。郑村有一块二百多亩的“碱场”荒地,因为长不好庄稼,早年常用来放牧牛羊,20世纪60年代公社为落实“五七指示”,将碱场作为公社副业生产基地,建立一所“五七”高中,又在剩余土地上种苹果树。
改革开放以后,“五七”高中撤销,果园荒废。乡镇将碱场(当时乡镇测定为218亩)以极低价格分别租给村东和村西两位村干部,起初每亩2元,90年代每亩3元。2000年乡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2001年以每亩80元的价格将大部分碱场(166亩)承包给在外经商的村东人胡明,少部分(52亩)承包给村西的郑某,为期两年。2001年—2003年胡明雇人耕种,土地贫瘠,收益不高。2003年乡政府将碱场土地承包价涨到每亩90元,胡明再次承包以后,改变策略,不再雇人自耕,而是转租给其他村民。胡明委托同村好友刘云,以每亩160元的价格将119亩土地转租给同村村民,每亩70元的差价二人均分。剩余47亩留给弟弟胡亮培育树苗。胡明多年在城市生活,并不十分了解村庄内部的人情与势力,这次土地转租主要由刘云运用其社会关系网络组织实施,涉及34户,其中16户与刘云是宗亲关系,6户是姻亲关系,1户是拟亲属关系,11户是礼尚往来的人情关系。
2005年,两年承包合同到期,改由胡亮和刘云共同承包。刘、胡争夺土地承包权,发生矛盾,最终刘云获得119亩承包权,胡亮获得47亩。这次土地转租过程中,转租刘云承包地的有25户,其中13户与刘云是宗亲关系,6户是姻亲关系,1户是拟亲属关系,5户是礼尚往来的人情关系。由于胡、刘二人关系交恶,“承包谁的地”让村东人面临抉择,引起“站队”问题。用村民的话说就是“跟谁一势的,就租他(承包来)的地”。例如,与刘云同宗的刘大、刘二、刘三原本租种刘云的土地,后来感觉刘云“近姻亲、远宗亲”“不把他们当回事儿”,一气之下转租胡亮的地。再如张襄原本想租种刘云的地,但他与胡亮的叔叔是干亲,不得不投到胡家阵营。那些感觉与胡家关系不好的则选择租种刘云的地,原本与刘云关系不太好的人迅速集聚到胡亮一边。跟谁都不是“一势”的家庭,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放弃租种土地。
这次土地承包使村东人情关系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冲击,并开始新的人情关系的选择性互动。重新选择和组合往往围绕着与刘家和胡家的互动展开。如刘翔辱骂刘云请的收割机师傅,第二年想再转租刘家土地,没有实现,而转投胡家。刘宏因为自己家的猪跑到刘云地里吃庄稼,两家闹僵,不再承包刘云的土地。土地转租带来的村东权力再分配和村民的“站队选择”,破坏了村东人长期礼尚往来和乡邻互助形成的人情网络,同时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种仇恨夹杂着其他的利益冲突,最终催生了一连串打架事件,还造成多个宗族之间的关系紧张,“不给胡家说媒,不是跟胡家不好,而是怕得罪刘家”,这种人情关系的冷漠是“村东无媒”的重要原因。
(5)科学技术水平。从表5可以看出,专利申请量和研究与实验人员与旅游经济网络呈正相关,且相关性水平基本维持在0.4左右,但有下降的趋势。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与科学技术水平息息相关,旅游服务设施的改善、旅游吸引物的创新等都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但随着体验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业的发展不再拘泥于观赏性旅游,随着驴友群体的出现,探险游等一些不拘泥于景区游览的旅游新形式逐渐成为旅游业中值得关注的新现象,非景区化的旅游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技术水平与旅游经济网络的相关系数。
五、结论与讨论
郑村“同村不同婚”现象反映了新时期中国乡村内部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与既往从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层结构等外生变量解析乡村的婚姻困境不同,本研究以豫东南相对封闭的一个小村落作为个案,将分析视角聚焦于村落内部,发现在家庭经济、空间区位、人口分布及信息流通等条件给定的前提下,宗族血缘关系、乡邻人情冷暖、弹性亲属网络是影响乡村婚姻缔结乃至婚姻困境的关键变量。村东因高离婚率、荒地转租纠纷引发不同宗姓之间人情关系的破坏,加之拟亲属关系减少、外来媳妇对既往礼尚往来秩序的破坏,导致“村东无媒”,产生婚姻困境。
为学生练习书写方便,利用学校教学资源将老师每节写字课用微视频录下来,然后课下让班级学生播放,学生跟着视频再次模仿练习,自己边练习边对照视频找出笔画写错的地方,及时进行改正。对于笔画多的字重点强调结构搭配,这种写字教学比普通写字课堂教学更具有示范性。突出了微课能以其特有的再现特征,激发了学生练习字的兴趣,促进了对语文知识的学习和掌握。
乡村社会的婚姻缔结受多方因素制约。具体而言,影响乡村婚姻缔结的组织要素主要包括: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亲属网络(宗亲)、以姻亲关系为纽带的亲缘网络(姻亲)、认干亲促成的拟亲属网络(干亲)和以乡邻互助、礼尚往来为基础的人情网络(“乡亲”)。 在特定场域下,宗亲、姻亲、干亲和乡亲四者交叠互动构成一张“实践性亲属网络”。中国乡村亲属关系网络的建构和再生产,所谓“亲不亲”关键要看“走得近不近”;“亲”不单取决于正式的以血缘或姻亲关系为基础的“亲疏”,亦取决于互惠性的亲属实践以及频繁的礼物流动和人情往来造就的彼此认可的关系“远近”。一定条件下,“实践性亲属网络”实际上是一套既可“收缩”亦可“扩张”的人际关系。
最近几次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当地彩礼不断上涨,一般要十万元左右,但当地人仍然不觉得是“大问题”。按照当地惯例,虽然女方要的彩礼高,但大部分都能带回到新组建的家庭中,这“并不亏”。另一些新的现象引起笔者注意:一是,婚姻困境在郑村附近的村庄开始不同程度蔓延,问到“为什么不好说媳妇”,他们称“好女孩都进城了”;二是,以血亲和姻亲关系为主导的亲属型媒人减少,职业型媒人增多。这些现象折射出,传统的婚姻缔结模式在个性解放、市场化浪潮冲击、人情淡漠和实践性亲属网收缩的多重冲击下更加困难。
本研究从经验出发刻画乡村社会婚姻缔结的过程和形态,力求逼近事实并努力呈现事理逻辑的完整性,为乡村婚姻困境提供一种解释。当代中国不同地域社会的村庄类型有很大差异,不同类型村庄内的权力结构和婚姻形态也明显不同,但乡村社会的实践性亲属网络和婚姻缔结,却具有相对一致的逻辑关联。恰恰基于此,本项研究试图从类型学意义上呈现同村不同婚这一乡村困境的独特图景,进而揭示婚姻困境背后的隐秘逻辑。
参考文献:
[法]皮埃尔·布迪厄,2012,《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陈蕊,2013,《双重的摧残:近代淮北女性婚姻困境的形成》,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陈文琼、刘建平,2016,《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载《人口与经济》第6期。
陈友华,2004,《中国和欧盟婚姻市场透视》,南京大学出版社。
方丽、田传浩,2016,《筑好巢才能引好凤:农村住房投资与婚姻缔结》,载《经济学(季刊)》第2期。
冯尔康等,1994,《中国宗族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美]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 ,2012,《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周大名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桂华、余练,2010,《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载《青年研究》第3期。
[美]黄宗智,2015,《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北京:法律出版社。
姜全保等,2010,《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研究》,载《人口与发展》第3期。
靳小怡等,2016,《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民工的“跨户籍婚姻”研究》,载《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李树茁、胡莹,2012,《性别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评述与展望》,载《人口与经济》第2期。
李晓霞,2010,《国家政策对族际婚姻状况的影响》,载《新疆社会科学》第5期。
李永萍,2015,《渐衰与持守:宗族性村庄光棍的生成机制——基于广西F县S村40例光棍的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李煜、徐安琪,2004,《婚姻市场中的青年择偶——转型社会研究文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梁慧星(主编),2013,《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亲属编》,北京:法律出版社。
林耀华,2015,《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庄孔韶、方静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林耀华,2000,《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刘中一,2012,《身体迁移与性别遭遇——基于外来媳妇城市融合经历的分析》,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第3期。
刘燕舞,2011,《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美]莫里斯·弗里德曼,2000,《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钱杭,2009,《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乔素玲、黄国信,2009,《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载《社会学研究》 第4 期。
尚会鹏,1997,《中原地区的干亲关系研究——以西村为例》,载《社会学研究》第6期。
师云蕊,2010,《古老异域的“迷思”——读弗里德曼〈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及其他》,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
[美]施坚雅,1998,《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丽娜,2015,《“重返光棍”与农村婚姻市场的再变革》,载《中国青年研究》第11期。
苏玫瑰、张必春,2008,《转型加速期门当户对婚姻的错位与危机——阶层封闭视角下离婚率上升的新解释》,载《西北人口》第5期。
陶希圣,2015,《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外一种:婚姻与家族)》,北京:商务印书馆。
陶自祥,2011,《代内剥削: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渝北S村长子打光棍的调查》,载《青年研究》第5期。
唐利平,2005,《人类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载《开放时代》第2期。
童辉杰、赵郝锐,2015,《社会阶层差异对婚姻关系的影响》,载《广西社会科学》第7期。
王铭铭,2004,《“水利社会”的类型》,载《读书》第11期。
王庆明,2008,《社会学的社会学:从反思性到自主性》,载《晋阳学刊》2008年第4期。
王郁芳,2014,《论现代女性婚姻策略的困境——基于经济理性的视角》,载《湖湘论坛》第5期。
[芬兰] E. A. 韦斯特马克,2017,《人类婚姻史》第1卷,李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韦艳、张力,2011,《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载《人口研究》第5期。
吴重庆,1999,《社会变迁与通婚地域的伸缩——莆田孙村“通婚地域”调查》,载《开放时代》第4期。
吴毅,2002,《亲缘网络》,载《开放时代》第1期。
吴作富,2008,《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批判》,载《社会学研究》第6期。
谢小芹,2013,《“主位”视角下光棍社会地位的再研究——基于江汉平原的经验调查》,载《南方人口》第5期。
谢宇、胡婧炜,2013,《导论》,载谢宇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6页。
谢宇等,2014,《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理念与实践》,载《社会》第2期。
邢成举,2013,《光棍与上门女婿:理解农村弱势男性青年婚姻的二维视角》,载《中国青年研究》第3期。
邢成举,2011,《男性光棍构成差异的地域性解释——基于凤城和新县两个村庄的比较分析》,载《青年研究》第1期 。
徐安琪,2000,《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载《社会学研究》第6期。
许琪等,2013,《婚姻与家庭》,载谢宇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第305—343页。
阎云翔,2017a,《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 、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阎云翔,2017b,《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杨春宇、胡鸿保,2001,《弗里德曼及其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兼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载《开放时代》第11期。
杨懋春,2012,《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叶文振,徐安琪,1999,《中国婚姻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载《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余练,2017,《婚姻连带: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新视角——对鄂中和鄂东三村光棍成窝现象的解释》,载《人口与经济》第1期。
余练,2011,《多重边缘者:基于对D村光棍群体社会地位的考察》,载《南方人口》第6期。
赵丽丽,2008,《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和社会支持研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周海旺,2001,《上海市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Freedman, Maurice,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Freedman, Maurice, 1963,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4, No. 1.
Freedman,Maurice, 1958,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James L. Watson, 1982, “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2, pp. 589-622.
注释:
①“郑村”是笔者为田野点取的一个学术名称,按照学术惯例,本文中的地名、人名都做了匿名化的处理。
②“村东无媒”并不是指村东适龄青年的婚姻无法通过媒人中介来缔结,而是当地人对村东光棍增多的一种自我解释,村东人说因为“没人说媒”那些娶不上媳妇的人不得不出去“领媳妇”。
③所谓“领媳妇”是相对于媒人介绍的“说媳妇”而言的,指在缺乏媒介资源的条件下,郑村男性青年外出打工时与合适对象恋爱同居,待女子怀孕后领回本村待产,在孩子满月时举办庆祝仪式。调查发现虽然领媳妇表面上看是自由恋爱,但对郑村的大部分青年来说却是无奈之选。一些男青年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领媳妇”,当问及是想“说媳妇”还是“领媳妇”时,他们回应“咋不想说,没人(介绍)嘛,不领咋办?”
④笔者在郑村的田野调查中慢慢体察到,郑村人常以2000年(即“那一年”)作为重要的时间点来谈论村里的婚事。在进一步调查后发现:“那一年”彩礼普遍上涨让郑村人感到压力,“那一年”村东几个宗族之间发生了矛盾,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村东与村西的婚姻形态出现分化。基于此,笔者将2000年作为考察郑村婚姻变迁的重要节点,同时为了解郑村婚姻的全貌以及变迁的整体特征,我们对婚姻缔结以及离婚破裂都做了历时性考察。
⑤本文中的“流动婚”是郑村人自己的一种说法,指外村的一些已婚妇女因某些原因从原夫家出走,途经郑村时经人撮合与郑村未婚男子同居的一种事实婚姻状态。虽然这种婚姻结构也有“中间人”,但在当地人看来与正式的介绍婚明显不同:一是这些妇女并未与此前的丈夫正式离婚,通常会存在一些纠葛;二是,这些女性多有身体残疾或智力(精神)障碍,“再娶”她们的郑村男性也多是年龄偏大或身体有残疾的人。
⑥郑村年轻人大多在20岁左右成婚,本文统计的大龄单身男青年仅限于在郑村居住生活的,不包括在外上学、工作和其他长期在外生活的人。
⑦一定程度上,社会科学就是针对普通行动者对意义解释的基础上,建构一套专业化概念体系进行再解释的“双重解释学”,对此,涂尔干、吉登斯和布迪厄从反思社会学的角度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王庆明,2008)。
⑧需要说明的是,“家族”和“宗族”在概念上是有差异的,通常前者的范畴小于后者,家族是宗族的一部分。但在笔者调查的郑村,这个封闭的杂姓混居的小村落中,二者的边界并不明显。行文中,除了讨论既往研究中涉及的宗族或家族之外,在对郑村血缘群体进行描述和分析时并不对二者做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⑨请祖,每年除夕日,当地人上坟请祖先回家过年,请回的祖先供奉在由布或纸书写的牌位上。
⑩清明节为自家祖坟添土是本族成年男丁的重要责任,在郑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人没人,清明看坟”,是说要想知道这家人是否有后代,清明时看这家祖坟上是否有新添的土。
⑪ 2018年1月20日对郑村“村长”即村委会委员的访谈。
责任编辑:刘 琼
Fickleness of Human Relationship and Kinship Practice: An Explanation of Marriage Dilemma in Rural China
Wang Qingming & Wang Chaoyang
Wang Qingm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Wang Chaoyang,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es on rural marriage dilemma have focused on exogenous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structure, urban-rural structure, regional structure, and stratum structure, arguing that these external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al restraints have led to marriage dilemma in the poor villag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in a relatively isolated village in the southeast of Henan provi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asons for different marriage patterns within one village. Given similarities in family economy, spatial locati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four critical variables are identified that affect rural marriage and contribute to marriage dilemma, including the network of clan relatives rooted in consanguinity, the kinship network rooted in marriage, the quasi-kinship network rooted in relationships among ritualized relative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rooted in neighborhood assistance and reciprocal courtesy. These four variables jointly build a kind of practical kinship network. In such a network, the key to intimacy depends not only on “closeness” in blood or by-law relationship, but also on interactions in terms of gift exchanges and other social exhanges. Problems such as land disputes, growth in divorce rate, quasi-kinship reduction and informal marriages have eroded the traditional ethics of reciprocal courtesy and led to clan fissions and the contraction of practical kinship network. The result: there are fewer matchmakers and, consequently, the marriage dilemma.
Keywords: fickleness of human relationship, kinship practice, marriage dilemma, practical kinship network
*本文是提交给2018年6月16日—17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召开的论文工作坊的论文。感谢黄宗智的宝贵意见和工作坊所有同仁的讨论,李勤璞、袁同凯、刘集林、王琰、张江华、狄金华、计迎春等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历史、经济与社会”读书小组的张震和李冠锐对文章亦有帮助,谨致谢忱。本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宅基地产权界定与流转机制的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18CSH029)的阶段性成果。
标签:婚姻论文; 宗族论文; 亲属关系论文; 村东论文; 关系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宅基地产权界定与流转机制的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18CSH029)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