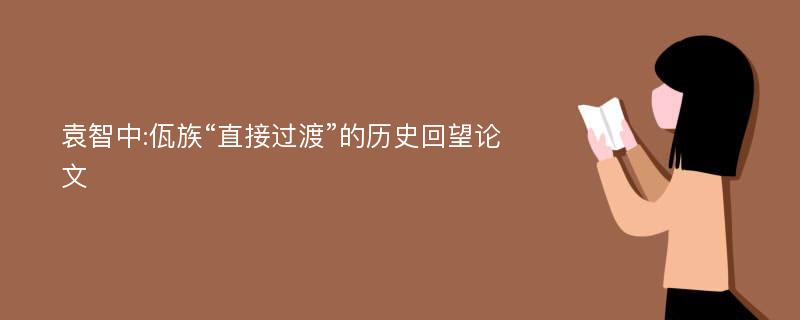
摘 要:“直过民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使用的概念。它是特指一部分保持浓厚原始公社残余的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未经民主改革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族。本文以云南“直过民族”佤族为研究对象,论述“直接过渡”给佤族居住的“阿佤山区”带来的不仅是传统思想中的生产方式的跨越。更重要的是,通过民族识别,使佤族实现了从政治文化边缘族群的“他者”向新中国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转换,并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纳入到新中国民主政治的框架内,以及采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革除猎头祭谷等传统习俗、破除旧有生产关系等系列柔性策略,全面建立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关键词:佤族;“直接过渡”;社会主义制度
佤族居住的“阿佤山区”地处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的怒山山脉地带,山岭重叠、平坝极少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佤族一方面深受大自然资源丰富的馈赠,而获得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其形成相互分割、以山为界、以血缘为纽带的、初级的小型社会群体,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在自给自足、自成一体的封闭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佤族社会形态基本上处于原始社会解体和阶级社会形成初期,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形态基本特征仍带有深厚的原始社会的遗风。新中国成立后,为帮助“阿佤山区”平稳过渡,云南省委在开展民族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将佤族纳入新中国民主政治的框架之中,并从“阿佤山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点出发,采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革除猎头祭谷等传统习俗、破除旧有生产关系等系列柔性策略,全面建立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为佤族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跨越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通过民族识别,完成了向新中国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转换
佤族因迁徙路线的差异和分布区域不同,自称和他称也有所不同。大体来说,西盟、孟连和缅甸联邦特区佤邦的大多数佤族自称“阿佤”“阿卧”“阿佤莱”“勒佤”,意为“住在山上的人”,是元代文献记载中被称为“野蒲”的佤族先民逐步形成发展的。被“阿佤”的,其居住区域是佤族社会中发育程度最低的地区;耿马、双江、沧源、澜沧一带的佤族大多自称“巴饶”或“布饶”,是元代文献记载中被称为“生蒲”的佤族先民逐步形成发展的。被称为“巴饶”的,是佤族三大支系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民族特征最为复杂的支系;镇康、永德一带的佤族自称“佤”“本家”,是元代文献记载中被称为“熟蒲”“熟佧”的佤族先民逐步形成发展的。被自称为“佤”的,其居住区域是佤族社会发育程度最高的地区,1949年以前已经进入封建地主制。汉族、傣族、拉祜族等对佤族的称呼也有所不同。对镇康、永德一带的佤族,傣族称“拉”“腊”,汉族称“本人”;对其他地区的佤族,汉族、傣族、拉祜族等大多统称“阿佤”或“佧佤”。在明清文献资料中,“佧佤”又有“大佧佤”和“小佧佤”之分,“大佧佤”指的是西盟等地的佤族,“小佧佤”指的是沧源、双江、耿马、澜沧、孟连等地的佤族。“佧”为傣语,是“奴隶”的意思,即“佧佤”含有贬意和侮辱性。[1]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历史遗留的一些民族问题,让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人口多少不一的“直过民族”平等参与到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1954年3月,我国政府依据斯大林有关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和“民族特征、民族意愿、历史依据、就近认同”的实践标准,对云南自报的260多个民族群体展开第一轮民族识别。佤族成为云南第一批21个被初步识别的民族,族称仍沿用清雍正以来使用的“佧佤族”。1963年4月2日,在沧源佤族自治县和西盟佤族自治县筹备成立期间,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将“佧佤族”正式更名为“佤族”,与“佧佤族”相关的称谓、地名、匾额等也进行了相应的更换。除了为佤族正名外,民族识别之于佤族的重要意义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这位导事,在念诵《指路经》(死者入棺时念诵)之后,就不再参与仪式的其他环节。剩下的祭奠活动,交给其他的人完成。
一是民族识别终结了佤族族称混乱的历史,强化了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支系佤族的同根意识和内聚力。虽然在佤族创世神话《司岗里》中,佤族是因不同的迁徙路线而形成了不同的分布区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汉文史籍也在断断续续的记载中,呈现出佤族千年民族迁徙与流变的轨迹,为佤族不同支系同归一族提供了依据。但“阿佤山区”天然的封闭生境,使佤族形成了相互分割、以山为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不同部落区。仅解放前的沧源阿佤山区,就形成了东部岩帅部落区、中部傣族土司管理下的部落区、西部班洪部落区等三大相互分割的势力区域,每个部落区又由若干相互独立的部落组成。这种相互分割的历史状况,决定了部族成员的族群认同大多遵循的是家族认同到部落认同到支系认同,再到民族认同的自下而上的认同逻辑。基于自然封闭生境的局限,大部分部落成员的认同视域仅限于家族认同到部落认同。加之长期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械斗等造成民族隔阂的历史现实,更是让生活于不同部落区的佤族囿于各自部落区,无法实现从部落认同到民族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升华与超越。
二是民族识别让“阿佤山区”打破了以山为界的历史局限,成为佤族共同生活区域的一个整体概念。虽然自清朝中期之后,佤族就基本形成了今天以滇西南地区和缅甸北部地区为中心区,跨中国和缅甸边境而居的稳定分布格局。但以山为界、不同部落区割居的历史现实,历史上对“阿佤山区”不仅有着不同的称谓,地域指向也有所不同。《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记载中,佤族聚居区的“葫芦国,一名卡瓦,在永昌东南徼外,地方二千里。北接耿马宣抚司、西木邦、南生卡瓦,东孟定府。”自此,“葫芦国”或“葫芦王地”一度成为了佤族分布地区的称谓,指代区域也大多限于前述所指的“阿佤山边缘区”耿马、双江、沧源、澜沧的佤族“巴饶”支系的居住范围。方国瑜先生的《滇西边区考察记》中的“葫芦王地”,则主要代指“滇之西南,顺宁府属边外,——即今之孟定土司以南,南卡江下流以北,东接耿马猛角董募乃孟连诸土司地,西以潞江与木邦冻景为界。”且“有上下之分,……以班洪为上葫芦,班况为下葫芦。……以南坎乌为界,南坎乌以南为下葫芦,其北则为上葫芦。上葫芦部落以数十计,争长称雄,莫能相属,自命为王子,故有五王十七王之号。”[2]基于1934年“班洪抗英”事件的影响,许多文献直接以“葫芦王地”代指班洪部落所辖的十七部落领地。直至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之后,“阿佤山区”才成为佤族共同生活区域的一个整体概念。
1951年3月,宁洱专区结合“阿佤山区”的实际,在佤族人口最为集中的沧源成立了“阿佤山区”第一个县级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推举沧源岩帅佤族头人田兴武出任沧源县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第一任县长,实现了临时人民政府向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过渡,翻开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佤族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和意愿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新纪元。1953年3月,沧源县召开了第四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在“阿佤山区”享有崇高声望的班洪佤族代理王子胡忠华当选沧源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岩帅班坝部落头人肖哥长当选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赵安民、田老大、胡中义、保卫国、胡玉堂等13名佤族上层人士和代表当选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佤族上层人士高耀星、肖哥长、包尼搞当选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二 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建立新型民族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阿佤山区”中心区隶属普洱专区。当时的普洱专区辖今天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和临沧市的沧源县,人口120万左右,面积 7 万多平方千米,边境线长达1400 千米,全区15个县中有8个县分别与越南、老挝和缅甸三国相连,是祖国西南边疆国防前沿,国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全区居住着哈尼、彝、傣、佤、拉祜、布朗、基诺、傈僳、回、苗、壮、瑶、白、景颇、汉等 26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人口的 70%,其中哈尼、彝、景颇、傈僳、拉祜、佤、傣等多个民族跨境而居。境外盘踞着国民党李弥残部,对敌斗争任务十分艰巨。各民族间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社会形态各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根深蒂固,民族之间及民族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民族问题和边境问题、外交问题、宗教问题相互交织,情况十分复杂。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大多数教师对学生进行填鸭式教育。这种教学方法只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以及他们的升学率,丝毫不注重学生对所学知识内容的掌握程度。教师只是一味地给学生灌输知识,学生也像机器一样被动接受知识。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他们的创新能力。国家对学生的要求不再是考试拿到好成绩,更要注重学生学习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能力将会伴随学生一生的发展,在学习文化知识时,找到学习乐趣,并注重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兴趣的带动下激发自身的创造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为增进边疆民族上层对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认知,增进对新中国、新政权和祖国的了解,增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建设新中国的信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庆典之际,党和政府组织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周年庆典观礼。1950年8月,10名佤族头人代表与普洱专区傣族、拉祜族、哈尼族、布朗族、傈僳族等25名民族头人和代表组团一路北上到京,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观礼之后,又随代表团先后到天津、上海、南京、重庆等大城市参观访问,感受到了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见证了祖国的辽阔伟大,破除了狭隘民族主义,增强了对祖国的了解、热爱和认同。1951年1月1日,35名普洱专区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代表回到普洱后,与参加“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的各族各界代表一起,按照佤族、傣族盟誓习俗,举行镖牛、喝咒水仪式,用傣文、拉祜文、汉文签名盟誓立碑,表示从此“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民族团结誓词碑的落成,标志着云南边疆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仇视,彻底结束了民族纷争与冲突的历史,开启了云南边疆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征程。
自此之后,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外出学习参观成为了党和政府争取和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人士、疏通民族关系、建立新型民族关系的一种政治策略。仅1950年9月至1956年底,云南省共计组织民族参观团103个、13515人次到昆明、北京等地参观学习。正如一位部落头人所感慨的那样:“过去也晓得自己是中国人,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总认为阿佤山大,自己管的那个山头大。这次党和政府关心,组织我们到昆明参观,坐汽车走了四天才到昆明,经过祥云、弥渡大坝子,看了昆明的工厂、商店、飞机场和风景区,使我们大开眼界,认识到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地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阿佤山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自己在的那个山头更小,而且很穷,很落后。回去后要向百姓好好宣传,要听毛主席、共产党的话,热爱祖国,加强团结,搞好生产建设,缩小边疆与内地的差距,用优异的成绩感恩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3]125云南民族关系也在党的民族政策推动下,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三 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纳入新中国的政治框架内
虽自汉代以来,历代中央王朝在阿佤山区均有建置。但无论是唐南诏、宋大理国时期统治者对“望蛮”地区的军事征讨、征发卫士,还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土官土司作为朝廷“命官”来实现对佤族地区的管理,以及民国时期,在“阿佤山区”实行的以部落窝郎头人制为主,土司制和国民党区乡保甲制三种政治机构并存的政治建制,佤族从未平等地参与到本地区政治事务的管理。以沧源县勐角董傣族土司管理的佤族地区为例。勐角董傣族土司是中央王朝授命管理该片区的国家代理人,勐角董土司则依据其政权的管理传统,将管辖区划分为9个勐,设“拉勐”领管;将各“勐”管辖的佤族、拉祜族和彝族村寨设为25个“圈”,设“圈管”“伙头”(即“头人”)领管。土司除了向各圈征派劳役、兵役、门户钱外,各圈领地内的动植物均属土司所有,圈民猎得虎豹要上交皮,猎获马鹿、大象要上交鹿茸、象牙。属地靠近土司府驻地的各圈每年要出工帮土司砍柴禾。“圈管”和“伙头”是土司管辖的封建小领主,与中央王朝并不发生直接统辖隶属关系,各圈虽为同族彼此却不隶属,而是呈各自为政、相互独立的分散状态,各片区势力发生冲突爆发战争或械斗时,还会互为战斗的敌人。
受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突破和石油供给结构性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世界石油价格将持续低迷。
三是民族识别使佤族实现了从政治文化边缘族群的“他者”向新中国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转换。正如前述指出,因地处远离汉文化中心的“王朝的边疆”,佤族在历代王朝建制中从未作为“国家”“民族”的一员纳入到统治王朝的政治构架内。而是在“瘴疬之乡”“蛮夷之地”等传统词汇的描摹和遮蔽下,始终以政治文化边缘族群的“他者”存在于“王朝的边疆”,并在“羁縻政策”“朝贡体制”的传统治理模式中,作为“被奴役”“被压迫”“被征服”的边地土著群体。民族识别使佤族从“受歧视”“受奴役”“受压迫”的历史记忆中解放出来,并在新的民族身份的命名和塑造过程中,实现了从政治文化边缘族群的“他者”向新中国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转换,并以新中国56个民族的平等一员,参与到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为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享有党和国家所制定的系列民族政策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持续提升,人们的生活条件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改善。在当前持续出台的有关法规与政策里,正在不断地加大农村危房的改造建设的力度。4类重点对象安全住房保障工作是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以及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明确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紧跟形势发展,围绕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任务,全面聚焦4类重点对象,解决基本住房安全问题[1]。
生活中,我们如果用好比喻,生动、形象地阐释道理,就能变抽象为具体,变繁复为简单,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微班会时间短暂,更需要班主任用好比喻,启发思考,活跃思维,促进学生提高思想认识。
在随后的两年里,伴随着澜沧拉祜族自治区(1959年更名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勐连傣族拉祜族佧佤族自治区(1963年更名为勐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佧佤族自治区(1963年更名为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等少数民族自治区(县)成立的步伐,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文化精英和优秀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感召下,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参与到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成为了推动和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新型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忠实力量。至1961年初,沧源县共建立佤族乡49个、傣族乡3个、拉祜族乡3个、彝族乡1乡、民族联合乡6个,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条件。
The trajectory parameter equation is in the following
1964年2月28日,经过12年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建制的探索和实践,全国第一个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成立。岩帅班坝佤族部落原头人肖哥长当选沧源佤族自治县第一任人民政府县长,勐角董傣族原土司罕富民、佤族上层人士李华新、汉族干部赵元仁当选第一届人民政府副县长,佤族干部陈德昌当选沧源佤族自治县法院第一任院长,保洪忠、田子民、肖丽珍等17名佤族干部当选为沧源佤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965年3月,经过10年的筹备,全国第二个佤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成立。自1956年就当任西盟佤族自治县筹备委员会主任的魏岩景当选西盟佤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政府县长,拉祜族上层人士张光明、佤族部落头人之子隋嘎、汉族干部李文福当选第一届人民政府副县长。佤族实现了依法行使自治权、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跨越。
四 革除猎头祭谷习俗,促进社会从封闭向开放变迁
在佤族传统社会中,为获得无处不在的精灵和鬼神世界的庇护,从佤历新月各瑞月(公历十二月)的祭水鬼、拉木鼓,到佤历耐月(公历一二月)的盖大房子、修寨门、做老母猪鬼,再到佤历阿木月和倍月(公历三四月和四五月)的砍牛尾巴、砍人头、接人头、供人头、送人头、修木鼓房、修人头桩,再到佤历格拉月和阿代依月(公历六七月和八九月)的叫小红米魂、叫谷魂,宗教祭祀活动几乎贯彻于一年的始终,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以谷魂为主题话语的猎人头祭祀习俗,更是让“阿佤山区”成为了谈之色变的“瘴疠之乡”“蛮荒之地”,让本就身处封闭生境的佤族社会趋于更加封闭的原始状态,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也变得更加单一闭塞。
由于发展不平衡,新中国成立初期,“阿佤山区”仍处于原始社会残余、奴隶制特征和封建领主制三种并存的社会形态。但从整体上看,阶级分化不明显,土地占有不集中,生产力水平低,社会经济仍带有深厚的原始社会的残遗。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委省政府从“阿佤山区”的实际出发,对处于土司制度和封建领主制下的傣族、佤族地区,采取“自上而下、和平协商解决土地问题的改革”和赎买的方式,废除土司及其属官的特权,将封建领主的官田、官奉田、份田调整给一般农民群众耕种,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新旧交替。
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直接关心、教育和引导下,从1957年开始,曾经盛行于整个“阿佤山中心区”的猎人头祭谷习俗迅速走向衰落。西盟地区砍人头祭谷的数量从1956年的156个头减少到1957年的30个头,到了1958年,整个上半年只是零星地砍过一两个头。[5]35到了1958年底,以西盟为代表的“阿佤山中心区”,不仅彻底革除了猎人头祭谷的习俗,镖牛祭祀、砍牛尾巴等传统习俗也一并被彻底革除。牛也从昔日的祭坛中解放出来,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投入到农业合作社的生产劳动中,成为佤族从原始农耕向传统农业过渡的一个标志。
1950年10月,拉勐等10名佤族头人代表与普洱专区25名少数民族代表赴北京参加国庆周年庆典观礼期间,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向佤族头人代表拉勐提出“可不可以不用砍人头,用别的代替呢?”的建议,当拉勐回答说“不行”时,毛泽东主席便拉着拉勐的手说:“你们回去与佤族群众商量商量,看如何改。”[3]401957年5月,西盟佤族部落头人之子隋嘎随云南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参观学习期间,毛泽东主席再次就革除佤族猎头祭谷习俗,对隋嘎提出“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要搞好民族团结!”[5]32的殷切希望。
五 破除旧有生产关系,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新旧交替
革除以猎人头祭祀为代表的原始宗教祭祀习俗,以唯物主义和科学精神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原始社会文化形态进行改造,促进佤族社会从封闭向开放变迁,成为新中国政权对“阿佤山区”进行文化改造的首要任务。为促进佤族文化的平稳过渡和变革,在改造过程中,严格按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4]要求,采取的是“谨慎对待”的柔性过渡策略。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的“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的要求,以及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及建立民族联合政权的意见》,采取先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再全面转向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灵活策略,对民族上层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吸引和团结他们聚集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引导、鼓励、帮助各少数民族从多元社会形态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
为进一步掌握工程地质情况,对施工地层进行复勘,确定各地层界限,绘制准确的地质剖面图,提供合理的防渗墙施工参数,本项目进行了10个先导孔的施工,完成造孔进尺350.34 m。先导孔的施工及成果分析为本项目采取泥浆、锯末固壁,减少回钻进尺等措施,为合理解决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施工的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以沧源县为例,1956年和平协商改革中,即:一是根据佤、傣、拉祜、彝等各民族上层人士的人数、传统领地和影响范围的大小,在政治上给予不同层面的安排。其中:佤族上层人士中,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3人,省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4人,任专区副专员1人,县政府副县长1人,县、区政协常委和副主席8人,乡、村级副主席、常委和委员58人;傣族上层人士中,任县政府副县长1人,县政协副主席2人,县政协常委3人,县政协委员6人,区政府区长1人;拉祜族上层人士中,县政协委员3人;彝族上层人士中,县政协委员1人。以确保各族各界民族上层人士和代表参与国家、省、地区和县、乡、村政治协商和民主决策的权利。①
二是结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实际,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采取“赎买”政策。1957年,沧源县委根据临沧地委相关文件要求,以及民族上层的安置情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对胡忠华、胡玉堂、肖哥长、罕富民、高耀星、保洪忠等87名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给予每月20~237.60元不等的固定生活费。为解除民族上层人士的生活顾虑,政府还给予胡忠华、罕富民、胡玉堂、高耀星、罕富权、罕富国、胡忠信、胡忠义、胡德胜、肖哥长、胡忠银、班忠国、双干、赵安民、赵布景等15户、88名民族上层家属、子女每人每月5~60元不等的固定生活费,以确保他们的生活水平不因改革而降低,①为和平协商解决土地问题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三是对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阶段分化不明鲜、土地占有不集中、生产力水平低的“民族直过区”,采取“互助合作”的道路,将原始协作关系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营、原始平均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使一直处于经济关系中最低层的“直过区”佤族村落成员个体,从旧有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在“生产互助合作双跃进”口号的感召下,以互助合作社成员的全新身份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劳动者的内生动力也在这种生产关系的转换中和全新身份的激发下释放出来。1956年,沧源县岩帅联合大寨佤族群众,在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依靠人背马驮和锄头、十字镐、撬杠等原始劳作,历时3年,挖通了长达40千米的岩帅联合大沟;1964年,沧源县岩帅建设大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蓄水塘、挖水沟、挖隧洞,还根据当地地形山势,创造性地把开水田与解决蓄水结合起来,以人背马驮的原始劳作方式削平了8座山头,开挖了96亩的“母子田”,建成了“佤山第一大田”。在这样兴修水利、开挖梯田、“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边疆的热潮中,沧源县水田面积也由1949年的17000亩增加到1965年的89836亩;西盟县水田面积也由1950年的2000亩增加到1965年的16600亩,为“阿佤山区”从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六 结语
总之,“直接过渡”给佤族居住的“阿佤山区”带来的不仅是传统思想中的生产方式的跨越,更重要的是通过民族识别,使佤族实现了从政治文化边缘族群的“他者”向新中国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转换,并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纳入到新中国民主政治的框架内。采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革除猎头祭谷等传统习俗、破除旧有生产关系等系列柔性策略,全面建立了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为佤族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跨越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杜建东.中共沧源佤族自治县历史资料.中共沧源佤族自治县委党史征研室编印:第二辑,内部出版,第104-105页,第109-110页。
参考文献:
[1]赵明生.当代佤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5.
[2]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4-5.
[3]王德强,等.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4]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 年6月6日)[M]//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5.
[5]隋嘎,毕登程.从部落王子到佤山赤子[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
Review of the Direct Transition of Wa Ethnic Minority
YUAN Zhi-zhong1, ZHANGYUAN Yi-min2
(1.West Yunnan University, Lincang 677000,China;2.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China)
Abstract: “Direct-transition ethnic group”, a term to be used under certain historical conditions, particularly describes the ethnic minority who remained primitive-communism production relations was directly transformed into the socialist ones without democratic reform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is research revolves around Wa ethnic minority, one of the directtransition ethnic groups, arguing that what direct transition brought to “Mountainous Areas of Wa”, the living regions of Wa, was more than simpl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ode, like being argued traditionally. More importantly, Wa not only successfully changed the identity from a periphery minority to an essential member of PRC’ people by virtue of the recog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for ethnic groups, but also was included in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system through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policy. In addition, by uniting the elites of Wa society, coupled with the eradication of beheading tradition for sacrificial ceremony and the reform of production relations,PRC had built up a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 which could enable the equality, unity among ethnic groups as well as co-prosperity all-round way.
Key words: Wa ethnic minority; “Direct Transition”; Socialist System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9)01-0065-05
DOI:10.13963/j.cnki.hhuxb.2019.01.016
收稿日期:2018-0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民族直过区”佤族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研究(17XMZ051)
第一作者:袁智中(1967-),女,佤族,云南沧源人,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
[责任编辑龙倮贵]
标签:佤族论文; 民族论文; 傣族论文; 拉祜族论文; 土司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红河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民族直过区”佤族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研究(17XMZ051)论文;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论文; 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