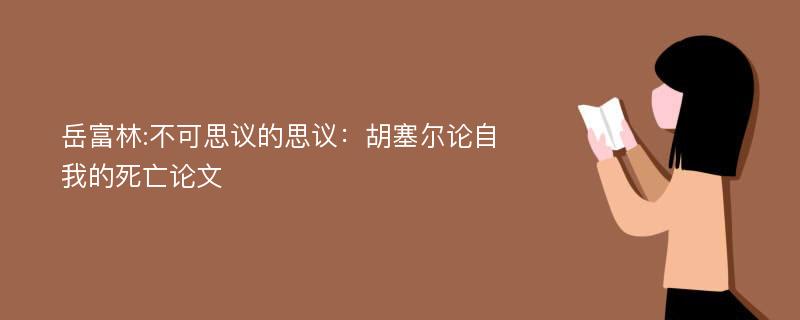
[摘 要]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死亡无论对于自我构造还是世界构造都至关重要。然而,大多数研究都采取事实性原初经验的思议模式,从而忽视了本我论前标识(Vorzeichnung)的思议模式。结合这两种思议模式,作为自我生活停止的自我死亡与作为触发力为零和身体瓦解的自我死亡无可避免地形成了自我之有死性与不死性的构造悖谬,进而导致理性与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胡塞尔的解决方案是区分世界性自我与超越论自我,并且以绝对理性扬弃一切非理性。尽管在方法上和实事上都还存在质疑的空间,但毋庸置疑,胡塞尔的死亡分析既为现象学对话绘制了基本图式,又为伦理学对话提供了更多可能。
[关键词]死亡;思议;自我;绝对理性
一、引言
对死亡的思考贯穿胡塞尔整个超越论时期,尤其集中在1920年代中后期和1930年代早期。这些思考的结晶大多在胡塞尔生后才被陆续公开发表,例如,《主体间性的现象学》(第一卷)(附录四十八),《主体间性的现象学》(第二卷)(附录二十),《被动综合分析》(附录八 第 10 节),《关于时间构造的晚期文本》(第21号,第43号),《现象学的界限问题》(第1号,附录二,附录三),《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增补》(第28号 第2节)等。如此丰富的研究手稿表明,死亡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并非无足轻重,对死亡的现象学理解也并非一蹴而就。
现象学必然是一门关于死亡的哲学,死亡在其中具有至关紧要的地位。现象学是一门关于构造的现象学,“构造问题包容了整个超越论现象学”[1]①为了术语一致,本文引文在必要处有所改动,下同。。构造的目的或顶点是一个客观同一的绝对世界,后者不仅包含当下世代的构造性成就,而且包含所有过去世代的构造性成就(传统)。一切活着的主体原则上都可以通过身体的直接移情而将自身构造为一个世代,而世代之间则要跨越死亡进行间接移情才能形成关联。一方面,高阶主体间性奠基于低阶主体间性,一切主体间性都奠基于自我的自身构造,对自我之自身经验和自身构造进行说明的本我学乃是整个构造现象学的基础。[2]另一方面,从外部的主体间性经验出发研究死亡很容易就将死亡看作一种平均状态,难以切入本己死亡的原初现象。因此,本文主要在原真领域内部考察自我的死亡,暂不处理社会人格统一体中的自我死亡、他者死亡、世代死亡,乃至整个人类的死亡。
我们应当从何处着手自我死亡?诚如上面所列举的那样,在文本上势必要随着《关于时间构造的晚期手稿》(2006)、《现象学的界限问题》(2013)等文本的晚近面世,今人才有机会一窥胡塞尔死亡观的全貌。而实际上,胡塞尔早在《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就预示了关于自我死亡的整个问题域和研究线索。
“在事实性单子领域内,作为在每一个可设想的单子领域内的观念的本质可能性,出现了……死亡、命运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在特殊意义上作为‘有意义地’要求过一种‘真正’人类生活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些伦理—宗教的问题……这些问题……必定会被提出来。”[1]190-191
首先,死亡如何作为“本质可能性”而必然出现在单子领域内?死亡可以事实性地出现在单子领域内吗?其次,死亡所出现的领域是事实性单子的领域,事实性单子不是一个抽象的纯粹自我,而是具有其本己身体、人格习性和周围世界的具体自我,那么,死亡会出现在纯粹自我乃至比纯粹自我更为原初的原自我领域内吗?再者,死亡规定了个体单子的有限性,自我在面对这终有一死的命运时,又当如何应对人生意义这种伦理难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核心论域,但在处理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应当澄清自我死亡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含义。
二、自我死亡的三种含义
胡塞尔一方面主张自我死亡是不可思议的(undenkbar),[5]97另一方面又宣称自我死亡是完全可思议的(denkbar),[5]167要理解胡塞尔这种悖谬性的表述,我们需要厘清“思议”的不同模式。
(一)自我生活的停止
自我生活之停止的不可思议性使自我意识到自身是理性主体。自我在所有事实性经验中都绝然内在地被给予,这个原必然存在的自我是构造世界和自身的最终功能主体,正是通过其超越论的构造功能,包括自我自身在内的一切超越存在者才获得可理解性,“这种可理解性(Verstandlichkeit)是理性(Rationalität)最高可设想的形式”[1]31。理性包括逻辑理性、评价理性和实践理性,一切理性都追求明见性的真理,自我作为一切明见性构造的最终根源,必然以认识原初实事、正确评价价值和做正当之事为目的。[9]
感性对象、本质对象、想象对象等任何现象都必须通过某种时间性样式才能够被给予,一切时间性样式都由作为原进程的自我生活所构造。而自我生活的停止取消了一切时间样式的构造基础,进而也取消了一切现象被给予的必要性条件,因而,一旦自我生活停止,那么,“一切都停止,于是什么也没有”[6]。
(二)触发力为零
(2)冻融损害。冻融损害主要发生在寒冷地区的春融季节,路面结构中滞留的水在冬季环境温度作用下凝固成冰,体积膨胀,影响沥青路面的骨架结构以及沥青与石料的黏附性,导致沥青面层粒料的脱落,形成松散、麻面等病害。而当环境温度升高时,结构层中的冰融化成水,在交通荷载的重复作用下,原有的病害扩展速度加剧,最终形成坑槽。
当下的原初凸显不断地触发并引起自我的关注和回应,远距的无差别性则既不呼唤自我而自我也处在绝对迟钝的涅槃状态。鉴于将醒觉与睡眠分别对应于强触发和弱触发,胡塞尔又将触发力为零称作无梦睡眠、绝对睡眠、深度睡眠或原睡眠。虽然死神(Thanatos)与睡神(Hypnos)在神话中是孪生兄弟,但死亡毕竟不是睡眠,睡眠必定具有苏醒的可能性,而死亡不存在任何苏醒的可能性。因此严格说来不能在睡眠的意义上理解无梦的睡眠,毋宁说,无梦的睡眠仅只是对一种类似于睡眠的消退进程界限的类比性标识。
(三)身体的瓦解
世界的显现具有“一种人体工程学的(somatologisch)结构”[3]411,自我对世界的统觉以身体的感受、定位和运动为前提条件。身体是由各个器官组成的功能统一体,具有正常与异常的模态,即正常身体与病变身体、成熟身体与幼嫩身体或衰老身体。正常是异常的构造性前提,异常是正常的意向变更。静态地看,身体会由于生病、受伤或年迈而机能失常,这种失常从较小区域到较大区域,从不重要的器官到致命的器官,从程度较轻到程度较重,最后的极限则是功能完全失常。动态地看,自我的身体会由于疾病而日渐消瘦或随着年华逝去而逐渐衰老,病变或衰老的过程是由健壮向垂危的过渡,过渡的速度可能因人而异,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没有人能减缓”[5]170这种过程,直至最终的死亡。死亡不是生病或衰老,而是它们的极限。
死亡意味着身体的“瓦解”(Zerfallen)[5]157。瓦解不是作为物理有机体的躯体肢解为各个块片或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细胞分子,而是身体不再发挥感知功能,导致“支配自我的停止,在世界中生活的停止”[7],身体失去了移情的可能性条件,导致一个共同世界构造的停止。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的死亡意味着身体变成完全受自然因果规律制约的尸体或单纯物体,“身体‘失去灵魂’(entseelt),身体停止存在”[5]22。
佛像的当代性,是指以当下的审美理念塑造的佛像,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习惯,并在理念、形式、样式上有别于其他时期,但这种时代特征必须是在如法的范围内,目前国内有许多艺术家在探讨尝试中,能否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之作需要塑造者不断的探索与时间的沉淀。
胡塞尔对自我死亡的表述纵然五花八门,但是根据如上三种含义,自我死亡的所有含义都将获得奠基性的澄清。例如,死亡作为“一切经验复多性的停止”[5]97表示触发力为零,死亡作为“意识—自我本身的停止”[5]160指的是身体的瓦解,甚至身体的瓦解还可以解释作为“一种单纯历史性事件”[7]404的我从主体间性的故去(Verscheiden)或退出(Ausscheiden)[5]442,因为身体是移情构造的前提。但是,这三种自我死亡并非同样都出现在事实性单子的领域内,因为它们有的是可思议的,有的则是不可思议的。
三、不可思议的思议
概括地说,自我死亡意味着“单子意识的……停止……单子处在完全迟钝的状态中,在其中没有凸显、没有触发、没有区分……特定生命的、本己多样体验的河流中断了”[3],这种一般性的理解要以如下三种含义为基础才能得到清晰的把握。
(一)“思议”作为事实性的原初经验,在这个模式下,一切自我死亡都是不可思议的。自我是一切对象(Gegenstand)得以显现的“原象”(Urstand)[8],对任何现象的观看或描述都是一个活着的自我活动。鉴于胡塞尔并未给死亡赋予一种进行时态,而是将之看作一瞬间之事,因此,要么自我活着地进行经验活动,要么自我及其一切经验活动都停止,绝不会出现自我活着地经验其自我死亡的情形。具体到自我死亡的三种含义,首先,自我生活之停止不可能原初地被经验到,因为所有原初经验活动都在当下持续地进行,自我生活的停止恰恰使得当下不再生成,因而死亡不可能是当下体验。其次,对触发力为零的原初经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行为以受到触发刺激为前提,而触发力为零意味着零刺激,因此想要对自我死亡进行原初经验乃是一个悖谬。再者,身体瓦解也不可能得到原初的经验,因为自我对这种身体死寂状态的经验要以身体发挥功能为前提,因此,“自我不可能看到身体瓦解”[5]157。总之,在原初事实性经验的思议模式下,无人能够在自身经验到死亡,无论是自我生活的停止,还是触发力为零或身体瓦解。
自我的死亡属于世界性事件,自我的不死性属于超越论事件。[11]作为世界性自我的人或人格必然是有限的,而超越论自我则是永恒无限的。死亡不过是超越论自我存在的模态化,即超越论自我从其自身客观化中“退出”[2]332。据此,不仅关于自我死亡的构造悖谬得到了调和,而且,我们可以在现象学中合法地谈论一种“不朽论”(Unsterblichkeitslehre)[3]123。因此,“并非悖谬的是,在流动当下中生活,我必须无可拒绝地相信,我将生活,即使我知道我的死亡就在前面。”[5]96
(二)“思议”作为在本质可能性上对极限情形的前标识,在这个模式下,自我生活的停止仍然是不可思议的,而触发力为零和身体瓦解则是可思议的。自我生活的停止不仅对于事实性经验是不可通达的,甚至对之进行本质可能性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如前所述,作为本质对象,自我生活的可能停止必须在某个时间样式中被给予,但自我生活的停止已然摧毁了构造一切时间样式的原进程,从而使得它本身不可能被给予。反之,触发力为零和身体瓦解这两种界限虽然不可能具有事实性的感性被给予性,但却可以在“前标识”[5]97中作为本质可能性而得到思议。对这两种本质可能性的思议都是通过将程度或等级推至极限而达到的,因而并非直观性的达及,而是一种抽象性的“建构”或“假设”[5]158,309。但这种建构或假设并非毫无根据的随意发挥,而是具有入睡、生病、受伤、衰老等过渡现象的经验基础,正是从这些内在的本己实事出发,“出生与死亡被‘看’作极限情形”[5]154。
(三)“思议”作为理智思维或判断。在这个模式下,一切自我死亡都是可思议的。如果将思议定义为作为理智思维或判断的客体化意向行为,那么,只要遵循逻辑规律和语法规律,不仅上述三种自我死亡是可思议的,甚至在自然态度下作为生物有机体之一切机能停止的自我死亡(例如脑死亡)也是可思议的。然而,这种思议仅仅是单纯表述或空乏意指,不能帮助我们获得明见性的洞见。而想要获得对作为思维对象的自我死亡的充实,势必就要诉诸于第一种思议模式,即事实性的原初经验。所以,本文将主要根据前两种思议模式面向自我死亡这一实事本身。
SW2(config)#spanning-tree portfast defau //二层交换机SW2上所有 access端口启用portfast特性
结合自我死亡的三种含义与两种思议模式,现在我们可以理解胡塞尔为什么说自我死亡既是不可思议又是可思议的了。当胡塞尔说自我死亡是不可思议的时候,他要么说的是在事实性原初经验模式下一切自我死亡的不可思议性,要么说的是自我生活停止的完全不可思议性。当胡塞尔说自我死亡是可思议的时候,他说的只能是前标识模式下的触发力为零或身体瓦解。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毫无悖谬地谈论不可思议(事实性原初经验)的思议(前标识)。但紧接着的问题是,自我生活停止的绝对不可思议性或不可表象性构造起自我的不死性,触发力为零或身体瓦解的可思议性却构造起自我的有死性,那么,自我究竟是有死的还是不死的?
四、关于自我死亡的构造悖谬与伦理困境
从不可思议的自我生活的停止来看,自我是不死的必然存在者,从可思议的触发力为零和身体瓦解来看,自我是有死的偶然存在者,但它们都是关于一个自我单子的规定,这无疑首先会导致自我既是有死的又是不死的构造悖谬,进而还会导致自我作为理性存在者必然面对非理性命运的伦理困境。
(一)有死性与不死性
一方面,自我生活之停止的不可思议性体现了自我的不死性。不死性意味着自我生活具有其无限的将来而永恒地流动着,将来的被给予性以当下和过去的被给予性为前提。作为起点的原当下,是时间视域之核心的核心,且不可分离地具有其滞留的彗星尾巴,而无论在普遍准则上还是在个别规定上,滞留都不断地且必然地引发着前摄,以及前摄的前摄,直至无限。[8]441,452原当下、滞留与前摄的交织统一使得意识流无限地延展,而意识流延展得有多远,作为意识流主体的自我就延展得有多远,所以自我是不死的。自我的各种体验会出现与消逝,但自我本身作为形式上的、观念上的同一者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结束,它是全时间的、非时间的、超时间的。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肯定了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关于灵魂不朽的论断:“一切灵魂都是不死的,因为凡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的事物都是不死的”。
胡塞尔对构造悖谬的解决是通过区分超越论自我与世界性自我,以及相应的超越论事件和世界性事件而完成的,对伦理困境的解决则由贯穿自我之一切发展的绝对理性所实现。
在选聘中,朋辈导师来源应多样化,因为不同专业、年级和地域的朋辈导师对团队成员的影响和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对导师进行多种方式的选聘,并进行相对严格的培训选拔。
在自我的自身构造中,自我既从自我死亡的不可思议性出发将自身构造为了一个不朽的永恒主体,又通过将死亡前标识为触发力为零和身体瓦解而将自身构造为了一个终有一死的有限主体,这不仅在此形成了自我之不死性与有死性的悖谬,进一步还将导致理性与非理性的伦理困境。
(二)理性与非理性
胡塞尔区分了两种自我生活,一种是自我的意识流,另一种是由行为与触发构成的生活,[4]自我死亡的头两种含义分别对应于这两种自我生活。自我生活作为意识流的原进程,具有原当下以及与原当下不可分离的滞留和前摄。自我生活(Ichleben)的活性(Lebendigkeit)就在于原当下与滞留和前摄的活的(lebendig)流动关联,即,原当下作为对前摄的充实而滞留化自身,同时前摄着更新的将来当下,滞留作为原当下的滞留不断地滞留自身,同时动机引发前摄,前摄作为有所滞留的前摄不断朝向原当下以充实自身。相应地,自我死亡表示原进程不再进行前摄,也不再生成原当下和滞留,从而原当下、滞留和前摄不再形成流动的关联,即“活的流动当下的具体停止”[5]。
对触发力为零或身体瓦解的前标识使自我意识到其非理性的命运。如前所述,死亡作为本质可能性,必然出现在事实性单子的领域之内,死亡在每个瞬间都以其不确定但必然的降临恐吓着自我。对死亡的前标识使自我意识到自身并非必然存在,而是会在将来的某一时刻不再存在。这种“意识到”即明白“死亡警示”(memento mortis)的本己“命运”(fati)[7]422,这种不可理解又不可摆脱的意外将会打断我生活的计划和目的,并使我反思甚至质疑整个生活实践的可能性和意义,进而导致人生意义或生活价值的虚无化,甚至由于确信无价值但又看不到克服的可能性而最终导致自杀。
一般而言,“顾忌”是中性词,而本文作者显然充分挖掘了“顾忌”一词的负面影响。仔细想来,非常有道理。正如作者所言:“内心足够强大,便可无所顾忌。”而相反,顾忌重重,则变成畏首畏尾,也就自然贻误了时机。阅卷经验告诉我们,好的议论文总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甚至于乍看起来,观点还有些“故作惊人之语”之嫌,而仔细一读,才觉很有道理。
理性与非理性都“从属于整个超越论主体性的最一般结构形式”[1]20,二者之间的冲突在自我面对死亡问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和急迫。虽然亲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次子沃尔夫冈(Wolfgang Husserl)的牺牲,胡塞尔仍然满怀希望地对多伦·凯恩斯(Dorion Cairns)说他“尝试通过使其(理性)构造变得明见而使残酷事实变得可理解(understandable)。这最终会为人们提供一种人们在一个可接受的世界中能够完全诚实地接受生活,尽管有战争与死亡这样的残酷事实”[10]。在胡塞尔所吐露的心迹中,他无疑想以理性理解非理性的命运,问题在于,“如何构建理性主体与理性自身的观念?”[3]532
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许多管理者的经济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有待提升。大多数管理者本身文化水平较低,没有接受正规的信息技术教育,导致他们对信息化手段的专业管理、应用及维护知识知之甚少。他们的日常经济管理工作仅限于利用信息化手段搜索、整理和发布一定的经济信息资源,结果是即使农村已经广泛铺设了信息网络,搭建了过硬的信息技术设备和设施,因缺乏信息化手段应用专业管理人才,农村经济管理也不能实现信息化手段的有效应用。
五、胡塞尔对悖谬与困境的解决
另一方面,对触发力为零或身体瓦解的前标识规定了自我的有死性。首先,触发力一旦下降为零,自我就再也不能通过其原促创的行为继续发展他的人格习性,因而自我的人格在死亡之时就被固定为了其整个生活的遗产。再者,身体如果瓦解,自我就会失去其世界性统觉的条件,失去在空间中的定位零点,失去其原真的周围生活世界。尽管自我无法原初地经验到这两种极限情形,但通过在醒觉当下对它们的前标识,活着的自我仍然能够意识到他自身的有死性。
(一)世界性事件与超越论事件
面对自我死亡的悖谬,胡塞尔首先在超越论自我与世界性自我之间做出了明确区分。超越论自我是在内在时间中的“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5]173,世界性自我在世界时间中与其他单子共存在,前者是活的当下的原自我或抽象的纯粹自我,后者是具有人格习性、本己身体以及周围生活世界的具体单子,前者是比后者更为原初的构造层级,后者是前者自身客观化(世界化:习性化和具身化)的成就。①尽管胡塞尔经常在自然态度上理解世界性自我及其死亡,但本文仅仅将世界性自我理解为超越论具体自我,以免将超越论现象学拉回到自然科学的水准。
自我是一个实行着意向行为的主体,行为以触发为前设。触发由内容所组成,内容根据其内部组成之间的差异大小和与当下的距离远近形成不同的凸显性等级,差异越大、距离越近等级越高,差异越小、距离越远等级越低,等级越高触发力越强,等级越低触发力越弱。在直观性阶段,我们不仅经验到触发力较强的对象,而且还经验到触发力伴随滞留化的消退或贫乏化,即触发力的减弱。触发力减弱的极限就是零,即触发性内容在远距的无差别性。这个零被胡塞尔类比于空间透视中的灭点,在触发和透视这两种情形下,内容统一体之间的差异都会随着(时间或空间)距离的变大而不断缩小,最终消失在一个非直观性的、“在自身中未被区分的零”[5]191。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依托地理优势,周边桃种植面积在百亩以上。为了扩大云天化品牌在临猗市场的知名度,让农民朋友感性认识云天化系列复合肥,积攒老百姓的口碑,通过与当地农户交流、探讨,共同制定了本次试验示范。此试验使用“镁立硼”15-15-15复合肥,“四全”系列13-5-27+TE复合肥。在当地相同土壤、环境和气候条件下,通过与使用其它品牌复合肥,在作物生长、产量提高及品质改善方面进行了对比,为云天化“镁立硼”、“四全”系列复合肥在桃种植和在农安市场的推广上提供相关依据。
作为触发力为零和身体瓦解的自我死亡是世界性自我的死亡,自我生活由于“超出”[5]442了世界性自我而并未停止。自我的死亡意味着自我不再在时间空间性的世界之中存在,意味着我不再受到刺激并进行统觉,我停止过一种世界性生活,即世界性意义上的无。但完全可以思议的是,无物进行触发,自我也处在绝对困顿的极限状态之中,自我生活作为“一种内在时间形式的设定性充盈化(Füllung)”[4]157仍然外在于世界地、未被区分地流动着,形象地说,超越论意义上的“无”这个暗夜本身仍然在隐匿而单调地延续着,因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无。
200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制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并发布,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人民的食品安全及身体健康形成了有力保障。
(二)绝对理性
自我在实践上具有自由权能的明见性,因为我原初地意识到我能够对经验性倾向和偏好进行批判性思虑,“能够说出意志是和意志否”[7]305。我能够与盲目的本欲和随意的偏好进行斗争,根据思虑(Überlegung)进行决断,而且唯有如此我才是自由的。既然是自由选择,自我就“对于在其所有活动之中的正确与不正确负有责任”[12]。而伦理归责必定以主体的一致性为前提,所以自我的生活意志不断追求自身保存(Selbsterhaltung)。在这个意义上,自杀是自我矛盾的,因为任何生活意志都是为了寻求与自我相一致的价值,而自杀的成功恰恰是对价值和价值主体的取消。[7]431单纯的实事并不具有价值,正是与命运阻力英雄主义般的斗争以保持自身统一的自由理性才使得伦理意义得以可能,它们本身就使得自我的生活具有崇高的价值。
在具体行动中,即便面对死亡的威胁,自我仍然应当出于自身立法(Selbstgesetzgebung)而践行绝对命令,并感到自身满足。作为自由自主的理性主体,我进行彻底的自身思义、自身立法并且自身负责。我明察到内在良知的绝对规范,即对我事实性的有限化进行普遍批判,完全生活在绝对真理和绝对辨明的行为之中,将自身实现为真正自我、真诚自我或永恒自我。而只要我忠于自身地对这种理念的呼唤进行回应,只要我践行善,完成了我的绝对义务,那么,“我就做了我的事情(Meine),我就不能够谴责自己。我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于自己。”[7]311这种满足不是享乐欲望的满足,而是不依赖于物质性后果的精神性满足。通过这种自身满足,我获得巨大的伦理确定性和力量以对抗一切意外。以母亲对孩子的爱为例,假使母亲预见到她自身及其世界都即将毁灭,她“知道世界不具有‘意义’”,但正直的母亲仍然会坚定地担负起“在爱之中对孩子进行操心”[7]310的绝对义务。
自我是承载着绝对理性或纯粹理性的存在者,一切非理性都在绝对理性中得到理解,因此自我的生活及其世界必然具有意义。首先,非理性不过是绝对理性的隐匿模态。自我在本能与本欲的被动领域中具有其隐含的持续目的,绝对理性在其中潜在地生成着,直到自我出于自发决断而规定自身(自律),将真正人格实现出来,绝对理性才变成显在的理性。[7]225其次,局部的非理性通过整体的绝对理性而被扬弃。在个体自我内部,个别不幸的意外、磨难、不满预设了和谐统一的整体生活,而且只有在整体一致性中才具有其意义。[7]495从世代来看,个体自我不过是超越论世代链条中的一员,我知道绝对理念的无限发展不会在我这个有限自我中完全实现自身,但只要我成为永恒使命共同体中一个谦逊的工作者,那么自我面对死亡就会得到安慰,因为他知道他有限的价值将在整体和谐中得到升华。[7]317
六、质疑与对话
诚然,无论在现象学方法还是现象学实事上我们都可以对胡塞尔关于自我死亡的讨论提出诸多质疑,甚至批判。但毋庸置疑,胡塞尔从原真领域出发所进行的描述,例如,自我绝不可能原初地经验死亡,自我以某种方式可以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死亡构成自我之生存意义的挑战,自我是自由意志的理性主体,等等,一方面为在现象学内关于自我死亡的对话绘制了基本图式,另一方面也为现象学和伦理学的对话提供了诸多可能。
(一)质疑
1.非明见性的建构
电气设备在运行中往往不易引起企业领导的重视,只有发生故障后才会在一定程度得到关注,这就导致电气设备管理存在严重延后,企业缺乏主动规划,不能主动的进行研究电气设备出现故障特点。
现象学之一切原则的原则是直观,死亡要获得现象学的思议,首先面临的就是直观问题,然而,上述第一种思议模式已经表明了对死亡的原初经验是不可能的。胡塞尔显然不满足于此,他用第二种思议模式——前标识的建构——将自我死亡纳入现象学论域,尽管这种建构具有过渡现象的实事基础,但无论如何,这种建构都超出了原初被给予性的范围,它不可能是真正现象学的看,而只能是非批判性地加引号的“看”。现象学的直观原则难道不是在一开始就反对任何形式的建构吗?对死亡等极限现象的建构难道不是现象学的自我瓦解或“越界”[13]吗?面对这种质疑,我们或者应当对自我死亡保持沉默,因为它是不可描述的;或者应当重新审视自我死亡的可见性,它可能是发生意义上的本质直观,[7]170也可能是现象学考古学意义上的重构[5]357。
2.独立的超越论自我
胡塞尔对自我之有死性与不死性悖谬的解决在于对自我构造的分层,只要不在同一个层级上谈论自我的有死性和不死性,悖谬就会自然消解。但是,如果死亡仅仅意味着超越论自我从世界性自我中退出,仅仅意味着自我从世界性生活向纯粹超越论生活的转换,那么,超越论自我的自身客观化不就成为可进可退、可有可无的了吗?进而,超越论自我不就成为一个真正柏拉图意义上可以独立于身体而存在的灵魂实体了吗?而这种结论显然与胡塞尔将超越论自我看作本质上属于具体单子之不独立的抽象层面的观点相抵牾。
3.非理性的可能性
胡塞尔对关于自我死亡之伦理困境的解决是将一切非理性都理性化,但非理性难道不是“此在之不可消除的剩余”[7]350吗?对于一个生活在其周围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单子来说,他时刻都面临着理性实践与非理性实践的抉择。“我们不可能在实际的直观明察基础上度过整个生命”[14],毋宁说,每一自我活动都对非理性的意外保持着开放的可能性。如果伦理危机恰恰就在瞬间非理性中爆发,如果力量有限的自我没有信仰上帝并且感到绝望,那么,自我难道不可能背叛其真正自我,从而陷入一种颓废的自我生活之中吗?[7]395自我始终能够“忽视”并“忍受”[7]304,323他的命运吗?
(二)对话
1.现象学对话
以《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中对死亡问题域的提出为标志,胡塞尔对自我死亡的分析为现象学研究绘制出了基本图式:(1)现象学致力于以非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的方式,从主体内部描述死亡;(2)现象学承认对死亡的事实性原初经验是不可能的;(3)但现象学试图以某种方式切入死亡,如胡塞尔的前标识,海德格尔的畏等①胡塞尔对海德格尔那“炫目而深奥的对待死亡的方式”(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rgänzungsband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34-1937[M]. Hrsg. Reinhold N. Smid.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332.)持批判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比较前标识和畏这两种对本己死亡的通达方式。;(4)现象学突出了死亡的悖谬特性,例如胡塞尔之不可思议的思议,海德格尔之不可能性的可能性;(5)现象学家在自我最终是否是不死的问题上莫衷一是,布伦塔诺和萨特都认为意识是不朽的,胡塞尔认为超越论自我不死,世界性自我有死,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认为此在在本质上是有限的;(6)现象学关注死亡对于自我的生存意味;(7)虽然现象学试图从主体内部分析死亡,但现象学也对主体间性中的自我死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最后,胡塞尔还为现象学对话提供了时间性这条重要线索:胡塞尔对自我之不死性的分析以时间河流的永恒流动为基础,海德格尔以向死而在展现了此在的时间性整体,列维纳斯对前两者都进行了“兜底置换”[15],从而将不能被总体性吞噬的死亡看作时间绵延的前提。
2.伦理学对话
腥膻气味较重的原料,如不鲜的鱼、虾、牛羊肉及内脏类,调味时应酌量多加些去腥解腻的调味品,诸如料酒、醋、糖、葱、姜、蒜等,以便减恶味增鲜味。
胡塞尔对自我死亡的论述从现象学的独特视角出发为伦理学的对话提供了诸多可能。首先,胡塞尔对自我之不死性的分析与布伦塔诺一道为柏拉图、基督教、康德等灵魂不死的主张提供了现象学的依据。不惟灵魂不朽,胡塞尔在实践理性中对自由意志、上帝存在的规定,都与康德的道德公设若合符节。此外,胡塞尔之自身保存、自身完善的理念也与费希特的完全自身同一性形成呼应。最后,有趣的是,胡塞尔与伊壁鸠鲁同样主张自我死亡的不可经验性,但据此形成的人生态度却截然不同,前者希望自我积极追求最终明见性,后者则奉劝人们耽于享乐。
采用SPSS16.0和Origin 9.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有数值均为三次重复试验所得数值的平均值。
参考文献
[1] [德]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M].张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2.
[2] 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Ergänzungsband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34-1937[M].Hrsg. Reinhold N. Smid.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332.
[3]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心理学[M].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31.
[4] 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Texte aus dem Nachlass. Zweiter Teil:1921-1928[M]. Hrsg. Iso Kern.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3: 45-46.
[5] Edmund Husserl,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M]. Hrsg. Dieter Lohmar. Dordrecht: Springer, 2006:96.
[6] [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M].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29.
[7] Edmund Husserl, Grenz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M].Hrsg. Rochus Sowa und Thomas Vongehr. Dordrecht:Springer, 2013: 221.
[8] [德]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M].肖德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39.
[9] John J. Drummond, Self-Responsibility and Eudaimonia[A]// eds. Carlo Ierna, Hanne Jacobs, Filip Mattens, Philosophy, Phenomenology, Sciences[C],Dordrecht: Springer, 2010: 442.
[10] Dorion Cairns, Conversations with Husserl and Fink[M].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 4.
[11] 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M].Hrsg. Sebastian Luft.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475.
[12] Edmund Husserl,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22-1937)[M].Hrsg. Thomas Nenon und Hans Rainer Sepp. 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32.
[13] 方向红.现象学的一次越界:与晚期胡塞尔一起思考死亡[J]江海学刊,2011(5): 49.
[14] [德]乌尔里希·梅勒.胡塞尔的人格伦理学[M]//陈联营,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十三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84.
[15] 王恒.时间性:自身与他者[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5.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9)03-0069-07
[收稿日期]2019-02-10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201706190032)
[作者简介] 岳富林(1989-),男,四川绵阳人,南京大学哲学系与哥本哈根大学主体性研究中心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象学;王 恒,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现象学与法国哲学。
(责任编辑:肖德生,邓文斌)
标签:自我论文; 现象学论文; 胡塞尔论文; 身体论文; 理性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留学基金委“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201706190032)论文; 南京大学哲学系论文; 哥本哈根大学主体性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