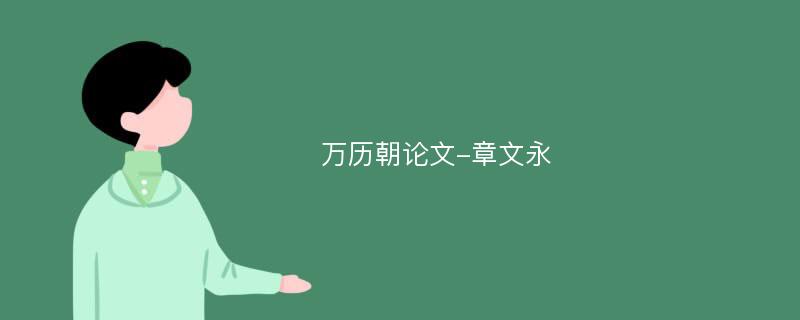
导读:本文包含了万历朝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历史文化类展览,万历朝,内容设计,展览解读
万历朝论文文献综述
章文永[1](2019)在《藉“走近”而“走进”——谈“回望大明——走近万历朝”展览的内容设计》一文中研究指出历史文化类展览是博物馆展览的一个主要类型,它既具有博物馆一般展览所具有的共性——应用博物馆的一切"展示语言"向公众呈现一个立体的阅读文本,又具有区别于艺术展、专题展等类型展览的个性——对历史文化现象的解读尤其要注重全面性、思想性、启发性。"回望大明——走近万历朝"展览在提炼主题、构建内容框架、发掘文物内涵、利用辅助展品等内容设计上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和探索,进而提炼了博物馆历史文化类展览内容设计方面可供借鉴的一得之见。(本文来源于《首都博物馆论丛》期刊2019年00期)
吕成龙[2](2019)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朝景德镇御窑瓷器略谈》一文中研究指出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叁朝历时99年,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时期正值欧洲文艺复兴盛期,是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科学技术初步发展时期。在中国,这一时期是明代社会剧烈变革时期,主要表现为启蒙思想开启、市井文化达到巅峰、手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等。在制瓷业方面,景德镇御窑瓷器烧造总体呈现产量空前大增、造型更加繁多、大件器物增多、胎体趋于厚重、工艺略显粗糙、装饰愈加繁缛、色彩流行华丽等风貌。民窑瓷器产量和质量则比以往有了很大提高,"官搭民烧"制度普遍实行。由此导致此叁朝瓷器颇具特色。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和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崇古和收藏之风的盛行,仿造嘉靖、隆庆、万历叁朝御窑瓷器的作品出现很多,更有甚者,利用原胎加彩,给鉴定带来麻烦。鉴定时主要还应从造型、纹饰、胎釉彩、制作工艺和款识等方面寻其破绽。(本文来源于《收藏家》期刊2019年02期)
吕成龙[3](2019)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朝景德镇御窑瓷器简述(下)》一文中研究指出(接二〇一八年十二期)万历朝御窑瓷器享国最久无所不贪明神宗朱翊钧系明穆宗朱载垕第叁子,明代第十叁位皇帝。生于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叁年)八月,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年)六月即皇帝位,改元万历,以翌年为万历元年。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朱翊钧九岁即皇帝位,由于年幼,不得不由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等辅政,母亲李太后听政。执政前十年,朱翊钧全力支持内阁首辅张居正以整顿赋役为主的社会改革,逐步营造出政治清明、经济大发展的中兴局面。但接(本文来源于《紫禁城》期刊2019年01期)
吕成龙[4](2018)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朝 景德镇御窑瓷器简述(上)》一文中研究指出明代晚期是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此时启蒙思想开启、市井文化达到巅峰、手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而制瓷业方面,景德镇御窑瓷器烧造总体表现为产量空前大增、造型更加繁多、大件器物增多、胎体趋于厚重、工艺略显粗糙、装饰愈加繁缛、色彩流行华丽等。民窑瓷器产量和质量则比以往有了很大提高,"官搭民烧"制度普遍实行。然而"无所不贪"的风气——盲目追求数量及特异器形,致使景德镇御器厂走向衰落,最终于万历叁十六年停烧。(本文来源于《紫禁城》期刊2018年12期)
宋立杰[5](2018)在《谏诤与妥协:沈一贯与万历朝矿税问题》一文中研究指出自万历二十四年,明神宗派遣矿监税使,直至其逝世时,以遗诏废除矿税,此项政策推行达二十五年之久。明神宗欲建立一套由他掌握的税收体系,故推行矿税政策。然外廷官员的不配合,使明神宗任命宦官负责征收矿税。而宦官为得圣意,丝毫不考虑实际情形,惟以进献为务,从而对万历朝政局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阁臣沈一贯对矿税持反对态度,然阁臣对皇帝、皇权具有绝对的附属性,在这种形势的支配下,他没有采取强谏的方式,而是以权变为主,在奉承圣意的前提下,委婉劝谏,适度地提议修改矿税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没有促使明神宗废除矿税。(本文来源于《贵州文史丛刊》期刊2018年04期)
张佳[6](2018)在《明代万历朝内阁荐举权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内阁荐举权是内阁职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施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内阁对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缺候选人的特定荐举权;另一种是内阁派遣官员负责行政管理事务(包括编纂史书、清理贴黄、经筵讲读、玉牒纂修等)时存在的荐举。二者都涉及内阁对官员的荐举,但荐举的方向有所不同。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高官(仅国子监司业)缺员时,内阁负责荐举某官填补官缺;而内阁派遣官员中的荐举,是内阁对翰林官、詹事府官员、国子监官员的荐举。也就是说,对于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高官而言,无论是他们候选人的提名,还是这些官员的升转,都由内阁题请。万历时期(1573-1620年)是明代内阁发展和变动的重要时期,内阁荐举权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的流动。然而,由于内阁荐举权的实施是对吏部人事权完整性的破坏,内阁与吏部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同时,内阁的权力受到皇权的牵制,这种牵制在万历后期愈发凸显。明神宗怠政后,内阁的荐举奏疏被留中,仅有少数得到皇帝的理会,内阁的荐举权受到皇权的制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万历后期,内阁荐举官员的奏疏很多,但真正下达实行的奏疏却很少,缺官与乞休的现状愈加严重,内阁与吏部就选官权展开的斗争愈加激烈,明神宗的懈怠与派系之间的斗争加剧了万历王朝的衰落。(本文来源于《山西师范大学》期刊2018-06-30)
陈旭[7](2017)在《明万历朝总兵吴广死因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贵州播州(今遵义)海龙囤是播州杨氏土司险要的军事城堡,近年有关海龙囤及播州土司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进攻海龙囤的明军总兵吴广在囤顶的战斗中受伤而亡。张廷玉在所纂《明史》中说,吴广是因"中毒矢"受伤而严重影响身体健康,遂致次年身亡。而明代的史料多未记载吴广为"中毒矢"者。比较明清时期的众多文献史料,关于吴广死因的记载不一,这是什么原因呢?(本文来源于《历史档案》期刊2017年04期)
李佳[8](2017)在《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本文来源于《求是学刊》期刊2017年06期)
陈旭[9](2017)在《“化龙”遇“卧龙”:程正谊与明万历朝的平播战争》一文中研究指出在播州宣慰使杨应龙灭亡之前,当时才堪御变的四川左布政使程正谊对上级官员总督李化龙提出了可行的剿播总计划,甚至涉及到播州平定后改土为流的善后问题。这就大大地坚定了李化龙讨播的信心,以致他自比叁国时的刘备,而高度地称赞程正谊为再世的卧龙。在定策军事讨播之后,程正谊还积极地协助李化龙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为此忙碌了数月。虽然他因升任顺天府尹而离任未能亲自在四川见证杨应龙的灭亡,但是他大力地协助李化龙讨播的运筹决算之功不可埋没。(本文来源于《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7年04期)
向广宇[10](2017)在《明弘治至万历朝治贪立法研究(1488年-1620年)》一文中研究指出明代对于贪腐问题的治理方式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界的关注,这一关注以往主要集中在明代的前期。明王朝建立初期,元末政治腐败带来的后果使明太祖朱元璋触目惊心,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对贪腐行为采取“重刑主义”严加惩处且贯彻始终。在《大明律》中,对于贪腐行为的处罚要远较唐律与元律为重。而且,为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还制定了《明大诰》,其用刑又远较《大明律》严酷。即便如此,在处理与贪腐有关的案件时,还存在着大量酷烈的法外用刑。但是,“重典治贪”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终洪武一朝,贪腐行为始终存在。此外,朱元璋还规定子孙后代不得变更他所确立的“成宪”。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不断地发展变化,“祖宗成宪”在规范、调整社会关系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再加之条例开始出现冗杂与相互冲突矛盾,对法律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俱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因时对法律进行修订的呼声越来越高,经过一系列的论争,终于在弘治十叁年颁布了《问刑条例》,自此“律例并行”。《问刑条例》在嘉靖朝与万历朝进行过两次修订,并于嘉靖朝正式附于律后,万历朝则开创了“律例合刊”的法典编排形式,这一形式也为清律所直接继承。《问刑条例》的出现,首要的进步性在于打破了“祖宗成法不可变”对法律发展的束缚,“度势立法”的思想占据主流地位,成为立法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法律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发展提供了前提,对避免法律的僵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到对于贪腐的治理上,《问刑条例》力图纠正《大明律》中的“重刑主义”,主要体现在减少死刑的适用,而大量使用充军刑、赎刑以及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等方面。这种宽缓体现出了“少杀”、“慎杀”的法律思想,符合法律理性化发展的趋势,是一种进步。而且,《问刑条例》在对贪腐问题的处理上更为具体和细致,对许多《大明律》中没有涉及到的新问题作出了规定。起到了较为良好的“以例辅律”的作用。必须承认的是,尽管《问刑条例》在立法上对于明代前期来讲有其进步性。但仍没有解决贪腐问题。也即明弘治至万历的主要立法成就《问刑条例》,同明前期的立法一样,在治贪问题上存在着立法目的与实效之间的缝隙,这个缝隙越大,立法的实施效果就越有限。研究这一时期的立法,探求立法目的性结构与实效性结构之间的缝隙及其成因,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在立法中尽量缩小所制定法律的立法目的与实效间的缝隙,最大限度地促进制度的完善。此外,研究立法离不开立法文本自身,但不能仅就立法文本来讲立法,立法是为了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因而必须要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对于立法的影响。反之,从立法成果出发进行研究,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状况。明代前期的立法成果以《大明律》、《明大诰》、《大明令》为主要代表,中后期则以《问刑条例》为主要代表。明代前期尤其是洪武朝对治理贪腐采取的是“重刑主义”,这种立法指导思想下产生的“重典”并没有起到良好效果,反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恐怖主义”。以《问刑条例》为代表的明中后期立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以宽缓为主,减少刑杀的做法符合人类社会历史的理性发展趋势。但是,这样的立法虽有其积极影响所在,却也对明代中后期官场的贪腐行为的治理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立法实施效果的有限性问题进行研究,因为立法不仅要追求合理制度的构建,还要使合理制度能够发挥实效。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在人治条件下,立法主体在立法过程中、司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要对各种利益集团与权力集团作出让步,这是造成明代该时期立法实施效果有限性的重要原因所在。在明弘治至万历朝的治贪立法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央巡视官员和地方官员颁布了大量的榜文告示,数量多于之前的朝代,也多于明代前期。这些榜文告示根据中央立法的条文与精神,针对地方具体情况,对一些具体事宜作出了规定,这其中包括了很多禁止性规定,还包括了对中央立法的阐释与重申,也属于法律渊源。这些榜文告示,是在遵循中央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制定,又结合了地方的实际情况。因此,不但易于推行与接受,而且是中央立法与地方实际沟通的桥梁,是中央立法很好的补充与推进。所以也应当加以梳理与研究。总之,从明弘治至万历朝治贪立法文本的梳理与研究入手,研究探讨这一时期立法的成就及局限性两个方面,并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总结其经验与教训,目的在于能够对当今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上的借鉴。在研究的过程中,文章通过以下结构安排来争取达到研究目标:在导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文章选题的意义,认为明弘治至万历朝的治贪立法较明前期具有进步性,但由于明代中后期贪腐盛行的史实,使得这一时期的立法成就易为人所忽视,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明代前期。因此有必要作出详细梳理与进一步研究。而且,对于这一时期地方立法的研究,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应当纳入该时期的立法研究范畴。研究该时期的立法,在学理上,可以总结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对明代本身治贪立法的实效性进行了解。同时研究中央与地方在立法上的联动,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法律规范性结构和实效性结构,探索合理制度的构建以及制度如何良好运行。在现实意义上,可以以此为借鉴,力图使立法成果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具有良好的互动,同时研究法律在适合社会变化的动态发展中如何保证其权威性、稳定性与统一性。导言还回顾了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重点梳理了明代廉政建设以及监察机制的研究成果、明代中后期治贪的研究成果、明代宗室与官员犯罪的研究成果、明代厂卫与司法关系的研究成果、明代内阁的研究成果、明代《问刑条例》的研究成果、明代地方立法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八个方面的学术史。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对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有了了解,发现《问刑条例》和地方立法的研究相对于明代前期的研究仍是比较薄弱,为文章找到了研究的重点所在。同时,导言阐明了文章的研究方法,即文本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综合分析法。第一章主要是对明弘治至万历朝的立法在该时期内进行一个阶段划分。划分的首要标准是叁版《问刑条例》的颁布时间。有如下原因:第一,《问刑条例》是明代中后期最为重要的立法成果,其出现打破了“祖宗成宪”对于法律发展的束缚。律例合编的法典编排体例对整个中国古代法典编排来讲也是具有创新性的,该体例更是为清代所直接继承。在内容上,《问刑条例》针对明代中后期社会上出现的新情况,对条例适时作出调整,对《大明律》等明代前期立法起到了良好的补充与辅助作用。并且对于明初立法的“重刑”作出了具有宽缓趋势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初“重典”带来的弊端;第二,《问刑条例》从弘治十叁年第一次颁行,到嘉靖朝正式附于律后,万历朝定型,作为有司判案的依据,一直到明末未有改变,其权威性与稳定性远远高于其他单行条例;第叁,叁版《问刑条例》的修订与颁布,有不同的背景,也反映着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弘治《问刑条例》的修订,争议较大,最终是“度势立法”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问刑条例》能够出现的思想前提;嘉靖朝时,对于《问刑条例》的修订争议没有弘治朝大,但是仍然有反对的朝臣,加之“大礼议”之争等政治事件的影响,嘉靖《问刑条例》直到嘉靖二十九年才颁布;此后,到万历朝时,法律应当适时进行修订成为中央层面的主流思想,因此万历《问刑条例》的修订从提出到开始着手修订再到正式颁布,没有经历像之前修订的争议与波折,中央立法修订体现出一种自觉性。万历十叁年《问刑条例》颁布以后,《问刑条例》的修订基本上已经完成,之后至万历四十八年,又有十六条新增条例编入。此后至明末没有再进行过修订。无论是从重要性、立法成就还是修订时体现出的立法指导思想的变化,都应当以《问刑条例》作为立法发展阶段划分的首要标准。除了中央层面的立法,该时期是明代地方立法的活跃时期,地方立法的阶段性体现不如以《问刑条例》为代表的中央立法明显。但是,从目前可见的地方立法内容看,应当是以嘉靖朝中后期发展最为迅速,之后到万历朝虽然数量不及嘉靖朝,但总体上发展还是较明代前期繁盛。因此在对该时期的治贪立法的阶段划分以《问刑条例》的立法发展为基本标准,以地方立法的发展为辅。第二章梳理了明弘治至万历朝治贪立法的法律渊源。虽然《大明律》的内容在明代中后期的行用中出现了对现实问题调整不力的情况,但是,由于“祖制”等因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大明律》仍然是整个明代最为基础与重要的法典。《问刑条例》在修订时就明确提出是以例辅律而非代律,在法典编排上也是附于律后。《大明律》是这一时期首要的法律渊源。在《大明律》中,赃罪被分为六种,分别是监守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坐赃、常人盗与窃盗。在这“六赃”分类中,常人盗与窃盗与贪腐没有关联。监守盗是典型的贪污,受财枉法与不枉法则是受贿犯罪,差别在于犯罪情节不同------即受贿与枉法是否相联系。坐赃是情况最为复杂的,坐赃罪名主要用于惩治渎职犯罪,但是也与治贪关系密切:第一,坐赃用以处罚行贿;第二,坐赃处罚除了贪污与受贿之外的官吏利用职权取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第叁,一些坐赃行为如果和具体情节如“入己”等联系起来,则会转化为监守盗或者受财枉法等犯罪。此外,《明会典》作为综合性法律文件的汇编,亦属于法律渊源之一。而作为这一时期立法的代表性成果的《问刑条例》,不但是重要的法律渊源,亦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叁版《问刑条例》在立法发展上,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与沿革。但是,每版《问刑条例》不仅仅是对之前版本的简单抄用,在修订过程中都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条例进行了增删与创制。因此可以说每一版《问刑条例》都有其在立法发展史上的意义。此外,《问刑条例》在立法上号称的是“以例辅律”,但由于其与社会实际生活联系的紧密,在实际行用中出现了“律例并行”的局面。因此,《问刑条例》是该时期重要的法律渊源。除了上述法律渊源。诏令在中国皇权社会下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而且,诏令虽然不是常规法典,但颁布之后却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梳理法律渊源必须考虑到诏令的地位与作用。在没有《立法法》规定与划分各级政权的立法权限与范围的情况下。明代地方官员发布的条约与榜文告示的性质不像今天这样明确。不过,这些条约与榜文告示都是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对中央立法的具体贯彻与补充,是沟通中央立法与地方实际的桥梁。而且,其中一些具有强制性效力,也应当属于法律渊源。第叁章的内容是研究该时期治贪立法的内容。在内容分类上,主要考虑叁个主要方面:打击贪污犯罪、打击贿赂犯罪以及打击特殊领域贪腐犯罪。贪污与贿赂犯罪是最为常见的贪腐犯罪。在《大明律》中贪污犯罪主要是“监临主守盗”,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贪污犯罪的形式较明代前期复杂,因此,在《问刑条例》中对这些犯罪形式也做出了处罚规定。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将新出现的犯罪形式作出梳理,然后规定以“监临主守盗”处罚;二是将具体的犯罪行为、情节与具体的处罚方式直接规定出来,而不使用“监临主守盗”或“监守自盗”的罪名。但后一种犯罪仍然是贪污性质。因此在打击贪污犯罪一节中又根据是否使用“监临主守盗”或“监守自盗”字样作为依据划分为两目。贿赂犯罪中最常见的是行贿与受贿。《大明律》中对于行贿没有专门的罪名,只是在一些条文中规定了对具体行贿行为的处罚,《问刑条例》也遵循了这一处理方法。但是,对于受贿犯罪,无论是《大明律》还是《问刑条例》都明确为“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两种情况。其处罚程度也不相同。当时的立法者还考虑到了两个特殊情况,一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一旦社会权力与地位较高者用各种形式向较低者索取贿赂,则后者很难抗拒;二是有人可以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或社会关系介绍贿赂。这两种行为都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不良冲击,又与贿赂犯罪关系密切。因而在立法中都有规定。在分类中也应当归入贿赂犯罪中。在治贪问题的立法上,还有一些特殊领域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叁个方面:第一,军队中的贪腐犯罪。其特殊性首先是军队的职能,作为对外起到国防保卫功能,对内起到维护统治作用的军队。对于统治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立法上对其内部出现的贪腐现象,处理往往与其他部门不同。目的是为了维护军队在秩序与人员上的稳定性,保证其职能的正常实现。同时,也正是因为军队职能的特殊性,在军队中会发生其他政府部门不会出现的贪腐犯罪,如军官贪功抢夺士兵所获敌军首级等。这些也需要单独加以规定;第二,明代社会是一个皇权下的等级制社会,这就决定了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总体说来,等级越高,权利越大而义务越小,等级越低,权利越小而义务越大。在加之皇权不可能管理到每一个具体地方与问题,需要各级官吏的支持与工作。因此,对于勋戚官豪在立法上不得不做出让步,以保证统治阶层内部的结构稳定。但是,这个让步也是有其底线的,就是不能对整个统治秩序产生冲击。而且,社会等级越高的人,有机会与能力做出社会等级低的人无法做出的犯罪行为,因此勋戚官豪的贪腐行为在立法中往往单独规定;第叁,特殊行业领域的经济犯罪,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盐务。盐作为最为重要的生活资料之一,在中国古代一直采取官府专营,目的一是控制百姓生活,二是会带来大量财政收入。到明代出现了盐引制度,使得官吏与商贩在贪腐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之前没有过的犯罪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而且,一些产盐区的官员发现了在盐的生产、运输过程中的一些具体腐败行为在中央立法中没有考虑进来,因此在自己所颁布的地方条约中对这类行为都加以规范。与盐业有关的立法是因行业性质而具有特殊性的代表。第四章探讨的是立法的实施问题。在立法实施机关方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司法机关以往探讨较多。但关于厂卫机关的司法权行使,以往多总结为“干预”、“破坏”等。从史料记载来看,厂卫机关在最初设立时,是被赋予了司法权的,明中后期的皇帝也是认可这一点的。过往对于厂卫机关的司法权视为“干预”、“破坏”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厂卫机关在行使司法权的时候经常法外用刑,且手段残酷暴烈,为人所诟病;第二,厂卫机关在行使司法权的时候,由于和皇帝的关系密切,往往不是在自己应有的权力范围内行使,而是时有干预乃至侵夺叁法司权力的现象出现;第叁,司礼监本身没有司法权,但东厂、西厂、内行厂又往往为司礼监所控制,甚至有司礼监秉笔太监直接管理东厂的情况出现。但是,即便如此,厂卫机关在司法权问题上仍具有合法的权力来源,问题在于权力有遭到滥用与越界现象,而不是厂卫机关在完全无权状态下强行行使司法权。在贪腐人员的纠劾、审判与执行上。一般官员的处理会因级别与从事工作性质等原因而有所不同。总体来讲,级别越高,处理程序越复杂、谨慎。至于宗室贵戚,则必须上报皇帝,其最后的处理没有固定模式。在用刑方面,这一时期由于立法指导思想的宽缓,赎刑适用范围有所扩大,充军刑也开始大量使用,更重要的是对贪腐人员的处罚中出现了“以罚代刑”的现象,也就是开始使用行政处罚手段来代替刑罚手段。上述用刑上的变化,在法律的理性主义发展角度来讲,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宗藩贵戚等带来的社会问题,在该时期要较明代前期严重,因而在立法中,对这部分人的管理有所加强。但是,即便是该时期的立法,仍然是等级法与特权法,受到立法宽缓带来益处的首先是特权阶级。因此,宽缓在某种程度上又给了特权阶级更多的特权。第五章研究治贪立法的特点。从立法指导思想与最终的立法成果来看,这一时期总体上体现出的是宽缓。虽然最初在《问刑条例》的修订问题上,是否破坏了“祖宗成法”曾经有过争议,但明初立法的严苛在此时已经体现出对社会问题调整上的弊端,这些弊端也为各级官员尤其是司法官所认识到。因此,在经过争论,当《问刑条例》的修订成为现实时,修订法律的官员也是力求能够纠正之前法律严酷所带来的问题。在内容上,同样的犯罪也往往采取了较明初为轻的处罚。各级官员在这一时期的立法积极性也很高,而且在实际立法过程中的作用比重也有所加大。弘治《问刑条例》和嘉靖《问刑条例》在修订之前,都是朝臣有大量的呼吁,万历《问刑条例》由于皇帝年幼原因,基本上没有发生争议,就在以张居正为首的朝臣主持下进行了修订。而且,即便是在弘治《问刑条例》修订前出现了对立观点以致引发不小的争论,但朝臣对参与争论的积极性从侧面说明了他们对于立法的关注。此外,地方官员与中央下派官员在该时期对于颁布地方条约与榜文告示热情很高。这些条约与榜文告示针对性强,与地方实际联系紧密,又是在中央立法精神与规定下颁布的,对申明中央立法精神,加强地方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在法典编排上。“以例辅律”的出现解决了“祖宗成宪”对于立法发展的束缚,使得“因时立法”成为了可能。这对于法律的发展要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来说,具有进步意义。嘉靖朝开始,正式将《问刑条例》附于《大明律》后,万历朝则实行律例合刊,这一体例为清朝直接所继承。《问刑条例》在立法上采取“辅律”而非“代律”的指导思想,使得条例的内容既能对《大明律》中对一些问题处理的缺失与弊端进行补充与修正,又能尽量避免与律文产生冲突。从而在实施中能够较好地做到“律例并行”。第六章主要研究与该时期治贪立法相关的一些问题。首先是治贪立法与社会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经济的发展与运行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推动力,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就包括法律。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对法律的发展变化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法律的发展状况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此外,从掌握的法律文本,可以对一定时期的经济状况有所了解。比如《问刑条例》中在计算经济犯罪的数额时,不再使用《大明律》中的宝钞以“贯”来计算,这与宝钞在明代的迅速贬值与中后期的实际停用有关,再如宗室藩王到明代中后期的增多,在俸禄问题上给中央与地方财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这部分人又经常私占土地,进一步影响财政税收。因此立法中加强了对他们的管理。至于政治与法律,向来联系十分紧密,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模式下,影响立法的政治因素很多,比如边疆安全问题,就涉及军队中的贪腐会影响军队稳定与战斗力。而流官对于土官的科索剥削则会造成西南等边疆的内乱;还有君臣关系的变化,明初的重典治吏与大量法外用刑不利于君臣关系的和睦与稳定,也不利于各级官吏发挥工作积极性,因此要采取较为宽缓的立法等等。其次,明弘治至万历朝的立法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从明代自身来说,从弘治《问刑条例》到万历《问刑条例》,修订中的争议越来越少,而法律应当适时修订的观点则渐渐变为了主流认识。这使得明代中后期在立法修订上越来越具有自觉性,成为一种常态化行为。主要表现是弘治《问刑条例》修订后终弘治朝没有再修订过,而万历《问刑条例》直到万历叁十五年还有新的条例编入。此外,万历之后,也曾有过对《问刑条例》再修订的提议,只不过是因为明末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此起彼伏的起义而未能成行。至于清代,在立国之初对于明代的立法成果几乎整体继承。在体例上采取“律例合编”,将法典直接命名为《大清律例》。在条例内容上,除少部分进行了修改或停用,绝大部分直接继承。不过,随着清朝政权的逐渐稳固,开始不断对继承于明代的条例进行修订与增删,从顺治到乾隆朝都有。乾隆中期以后,这种修订与增删逐渐停止。但是,这并不影响明代条例对于清代的巨大影响。并且,通过清朝建立以后条例的变化还可以得窥清代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最后,通过研究该时期的治贪立法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当时地方官员对于立法的热情很高,他们通过两个方面影响当时的立法:一是通过上书朝廷言明现行法律中的问题,推进中央层面的立法修订;二是根据中央立法来颁布具有地方针对性的条约与榜文告示。这种各层级在立法上的联动与互补有助于更好地使用法律来进行社会治理,尤其是对基层的治理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当时的立法与司法是处于人治社会环境下的。因此绕不开该社会背景下的局限性,特权阶级的存在以及皇帝出于维系统治考虑所作出的让步,使得在治理贪腐上,无论是立法和司法都难以做到实质意义上的公正。即便是海瑞这样的清官,也不可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精神与理念,在他所处理的案子中也会有不依法的嫌疑---虽然出发点是为“小民”争利。总之,明弘治至万历朝在治贪立法上,无论是从立法精神、指导思想还是法典形式与内容,都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时代与历史原因其存在的局限性。这也启示我们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如何进一步追求合理制度的构建以及有效实施,这是社会发展的应有追求。(本文来源于《华东政法大学》期刊2017-05-15)
万历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叁朝历时99年,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时期正值欧洲文艺复兴盛期,是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科学技术初步发展时期。在中国,这一时期是明代社会剧烈变革时期,主要表现为启蒙思想开启、市井文化达到巅峰、手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等。在制瓷业方面,景德镇御窑瓷器烧造总体呈现产量空前大增、造型更加繁多、大件器物增多、胎体趋于厚重、工艺略显粗糙、装饰愈加繁缛、色彩流行华丽等风貌。民窑瓷器产量和质量则比以往有了很大提高,"官搭民烧"制度普遍实行。由此导致此叁朝瓷器颇具特色。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和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崇古和收藏之风的盛行,仿造嘉靖、隆庆、万历叁朝御窑瓷器的作品出现很多,更有甚者,利用原胎加彩,给鉴定带来麻烦。鉴定时主要还应从造型、纹饰、胎釉彩、制作工艺和款识等方面寻其破绽。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万历朝论文参考文献
[1].章文永.藉“走近”而“走进”——谈“回望大明——走近万历朝”展览的内容设计[J].首都博物馆论丛.2019
[2].吕成龙.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朝景德镇御窑瓷器略谈[J].收藏家.2019
[3].吕成龙.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朝景德镇御窑瓷器简述(下)[J].紫禁城.2019
[4].吕成龙.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朝景德镇御窑瓷器简述(上)[J].紫禁城.2018
[5].宋立杰.谏诤与妥协:沈一贯与万历朝矿税问题[J].贵州文史丛刊.2018
[6].张佳.明代万历朝内阁荐举权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8
[7].陈旭.明万历朝总兵吴广死因探析[J].历史档案.2017
[8].李佳.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J].求是学刊.2017
[9].陈旭.“化龙”遇“卧龙”:程正谊与明万历朝的平播战争[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10].向广宇.明弘治至万历朝治贪立法研究(1488年-1620年)[D].华东政法大学.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