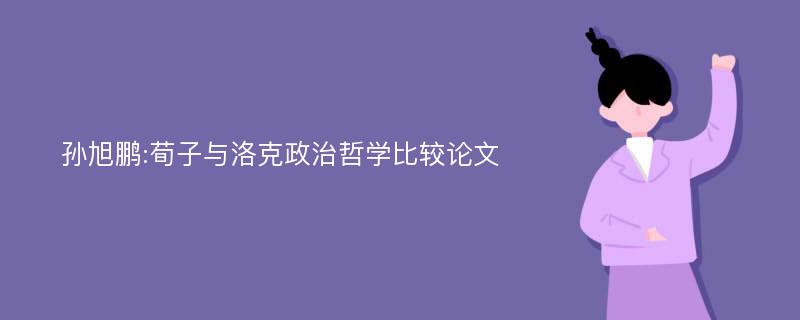
摘要:作为中国儒家思想代表的荀子与作为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代表的洛克,二者都具有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理论。荀子与洛克的政治哲学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差异:相通之处在于荀子与洛克的政治哲学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状态”的认知基础之上;差异之处在于荀子与洛克分别以“君权”与“契约”的方式来完成政治社会的构建。基于“君权”与“契约”,荀子与洛克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也存在重大差异,并且个人与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巨大张力。分析比较二者的哲学理论有助于加深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维护个人权利,促进社会安定。
关键词:荀子;洛克;自然状态;君权;契约;个人;社会
荀子是中国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是17世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二者都对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入的思索,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哲学思想。荀子生活在战国中后期各个诸侯国战争频繁的时期,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而洛克则生活在英国内战时期,此时西方的封建社会正处于没落时期,个人自由思想开始觉醒,这就导致了二者的政治哲学既有思考起点的一致性,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中西方差异性以及时代差异性。荀子与洛克在探寻人类政治社会的起源时,都关注了人类的“自然状态”。但是二者对于人类“自然状态”的认知并不相同:荀子认为,人类在欲望的驱使下,“自然状态”必然是充满纷争的;而洛克则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是充满理性的,他们天然地遵循“自然法”的要求而倾向于和平。正是由于对人类“自然状态”认知的不同,导致荀子与洛克采取了不同的社会构建路径:荀子认为必须依靠“君权”来制定出约束个人欲望的“礼”,才能够使人类走出充满战争的“自然状态”;而洛克则认为人类会在充满理性的自然法的指引下,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来结成社会共同体,从而克服“自然状态”中的不足。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以“君权”为中心的荀子政治哲学和以“契约”为中心的洛克政治哲学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荀子那里,君主是整个社会主导者,忽视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极容易导向君主专制,引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而在洛克那里,个人是组成社会的主导者,个人可以通过“契约”的形式来结成社会,从而实现一种长久的和平,然而,当代表社会的立法机关不遵守“契约”之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会重新进入战争状态,从而导致社会的瓦解。其实,荀子与洛克都没有消除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张力,个人与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的风险,通过对二者政治哲学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维护个人权利与社会安定。
一、自然状态
荀子与洛克的政治哲学共同建立在对人类“自然状态”的认知基础之上,只不过,二者对“自然状态”的认知存在着巨大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荀子与洛克政治哲学最终走向的不同。荀子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几乎就等于战争状态,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必然陷入纷争与混乱当中;而洛克则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会在理性的指引下遵循自然法,天然地倾向于和平。
在荀子那里,人类的“自然状态”几乎就等同于战争状态,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之下,纷争与混乱将变得不可避免。荀子讲:“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很明显,在荀子看来,人生来就是有欲望的,而欲望的“无度量分界”必然导向“争则乱,乱则穷”。那么,为什么欲望是生而具有的呢?荀子是这样看待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性的:“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徐复观先生认为:“荀子虽然在概念上把性、情、欲三者加以界定,但在事实上,性、情、欲,是一个东西的三个名称。”[1]也就是说,在荀子看来,欲望本身就是人性,注定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才会讲:“虽为天子,欲不可尽。”(《荀子·正名》)
一方面,荀子认为人类的欲望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荀子认为可供人类利用的物品是有限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争斗,荀子讲:“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荀子·王制》)杨倞对此句注解曰:“既无等级,则皆不知纪极,故物不能足也”[2]180很显然,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们之间是“势位齐”的,也就是没有等级区分的,每个人都会顺从自己的欲望,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与此同时,可供人们利用的物品却是有限的,因此,顺从每一个人的欲望去争夺有限的物品,必然引发人们之间的争斗。进而,荀子便推出了其“性恶”学说,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必然是“性恶”的,他讲:“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荀子·性恶》)也就是说,在欲望的驱使下,人性必然会丧失其原本质朴的一面,进入到人与人之间互相争夺的“性恶”状态,郭沫若先生这样评价荀子的“性恶”学说:“他认为人性具有好恶食色的情欲,让这种情欲发展下去,那就只有争夺暴乱,完全和禽兽无别。”[3]由此可见,荀子眼中的人类“自然状态”几乎就是一种战争状态,充满了争夺与纷争。
整体而言,麦克尤恩的《时间中的孩子》用文学之镜映衬了斯蒂芬丢失的那个孩子,在自然之镜中反思了丢失的那个孩子在自然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所受到的种种磨难。尽管斯蒂芬没有能够找回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个悬而未决的隐喻结尾却展示了积极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流逝,斯蒂芬与妻子孕育着新的生命,《时间中的孩子》的荒原镜像伴着“一声哽咽,接着是一声清亮的啼哭”(《时》:239)。不再是一种虚幻中的文学叙事,它被再次拉入现实社会并充满未来生命的勃勃生机。这最终也让麦克尤恩完成了对《时间中的孩子》标题隐喻的一个完美解释:在时间中丢失的孩子,最终会在时间中找寻回来。
荀子首先考查了“礼”的起源,认为“礼”就是作为化解人们欲望的方式而出现的,他讲:“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这里的“养人之欲”并不是纵容人们的欲望,而恰恰是通过约束人们的欲望,来达到“养”的效果,正如孔繁先生所认为的那样:“礼的发生非是要压制人的欲望,而是要使欲望得到合理解决。”[7]“礼”对欲望并非采取单纯的压制,而是采取了“化”的方式,荀子讲:“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杨倞对“化性起伪”注解曰:“言圣人能变化本性而兴起矫伪也”[2]518总之,荀子认为“礼”能够起到“化性”的效果,从而改变人类“自然状态”中的“性恶”,实现“性伪合而天下治”。
二、君权与契约
正是由于荀子与洛克对人类“自然状态”的不同认知,导致了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社会建构路径。荀子认为,既然人类的“自然状态”几乎就是一种战争状态,并且人们之间的争斗完全是由欲望的驱使所致,那么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就必须依靠一种强力的“君权”作保障,采用“礼”的方式来约束人们的欲望,通过“化性”来使人类最终走出“自然状态”。而洛克则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就受到理性的指引,他们天然地愿意遵循自然法的要求来谋求和平,但是由于在“自然状态”中的和平是不稳定的,因此,人们便通过“契约”的方式来结成社会,将自己的权力移交给一个权威的裁判者,来公正地代为行使每个人的权力,从而避免战争并形成长久的和平局面。
荀子与洛克分别通过“君权”和“契约”的方式,完成了政治社会的构建,使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体进入了社会状态。荀子依靠“君权”的强力保障,使社会中的个体遵循一种统一的“礼”的标准,从而实现一种“群居和一”的社会;而洛克则依靠“契约”的方式,由个体将个人权力移交给社会,立法机关来行使受人民委托的权力,从而达成一种维持和平的公民社会。荀子与洛克分别通过自己的方式,较好地处理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然而这并不代表在荀子和洛克那里,个人与社会就不会存在任何的冲突和矛盾了,其实,在荀子与洛克的政治哲学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始终都存在,并且这种张力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极容易引发个人与社会的激烈冲突。
然而,洛克并不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绝对完美的,固然人们在理性的自然法的指引下呈现出一种和平状态,但这也并不排除有一部分人违背理性的要求,从而造成一种“战争状态”。洛克认为:“人们受理性支配而生活在一起,不存在拥有对他们进行裁判的权力的人世间的共同尊长,他们正是处在自然状态中。但是,对一个人的人身使用强力或表示企图使用强力,而又不存在人世间可以向其救助的共同尊长,这是战争状态。”[4]13由此可以看出,洛克认为人类由于受理性的支配,虽然在“自然状态”中总体上趋于和平,然而也时刻面临着由于某些人违背理性而造成“战争状态”的风险。可以这样认为,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时刻处于战争威胁的和平状态,尽管人们在理性的指引下趋于和平,但是并不必然地会实现和平,正如乔纳森·沃尔夫所断言:“其实,洛克已经接近承认,自然状态可能并不像他最初所设想的那样和平。”[6]由此可见,尽管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受理性的支配,有利于实现一种和平局面,然而“自然状态”仍然是不完美的,时刻存在着由于使用强力而引发战争的风险。
高校非计算机专业的Access数据库一般是按照课程主线,简单地介绍数据表、查询、窗体、报表、宏等基本操作,没有结合专业特点进行理论分析和案例实践。教学与专业脱离,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差,学习之后依然不了解该技术在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应用。
洛克则主张个体采取“契约”的形式来结成社会,将每一个人的权力移交给社会的公正裁判者,便可以避免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时刻面临的战争风险,从而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由于洛克认为人类天然是独立平等,且具有理性的,因而他们能够自发地通过“契约”的方式来结成社会,洛克讲:“在任何地方,不论多少人这样地结合成一个社会,从而人人放弃自然法的执行权而把它交给公众,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才有一个政治的或公民的社会。”[4]54洛克认为,个体之所以愿意放弃自己在“自然状态”的自由而结成社会,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全自身,洛克这样讲:“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4]77,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个体正是通过“契约”的形式,将个人权力移交给社会的公正裁判者,从而避免“自然状态”中的风险:“设置在人世间的裁判者有权裁判一切争端和救济国家的任何成员可能受到的损害,这个裁判者就是立法机关或立法机关所委任的官长,而由于这种裁判者的设置,人们便脱离自然状态,进入一个有国家的状态。”[4]54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荀子那里,“礼”所得以产生的主体始终是“圣人”,没有“圣人”就不可能有“礼”的产生,也就不能通过“化性”来实现“天下治”,由此,“圣人”在荀子那里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荀子讲:“圣人也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又讲:“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在荀子看来,“圣人”或者“君子”才是人类社会的组织者,其实不管是“圣人”还是“君子”,落实到现实层面便是“君主”,从而形成了一种绝对的“君权”。美国汉学家狄百瑞如此评价儒家思想:“由于儒家思想中缺少这样一种立约,缺少履行誓约过程中百姓的积极参与,所以变革世界的重任最后完全落在了统治者及其辅佐者身上。”[8]儒家思想的这种特征在荀子政治哲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礼”完全是由统治者制定的,而统治者就是现实中的“君主”,因而“君主”必然获得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人们无法对之形成有效约束。可以这样认为,在荀子那里,绝对的“君权”是实现人类社会良序的保障。
洛克的政治哲学同样建立在对“自然状态”的认知基础上,然而,洛克眼中的人类“自然状态”却总体呈现出一种和平状态。洛克同荀子一样,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们之间是彼此平等的,也就是荀子所谓的“势位齐”,洛克讲:“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4]3既然人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状态,为什么不会如荀子认为的那样,最终导致彼此之间的争斗呢?洛克认为这是由于理性的自然法在起作用:“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能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4]4由此可见,在洛克那里,人类的“自然状态”是天然倾向于和平的,人们不仅是独立平等的,并且是具有理性的,正如格瑞特·汤姆逊所认为的那样:“在洛克看来,在先于任何公民社会的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5]反观荀子的“自然状态”,人们恰恰是由于没有“理性”与“理智”的约束,从而走向了争斗。
设计因素对于路基沉降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主要是因为设计错误所导致的。高速公路设计方案确定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进行交通量的预估,然后才能进行承载载荷的计算,从而确定路基的承载能力。但是如果交通量超出了规定的要求,公路路基需要长期承受汽车动载荷的影响,预期之外的路基沉降也会出现。这种沉降多数都是在公路施工结束之后所存在的,具备有明显的滞后性,所以控制难度较高。
日益壮大的读者群体为阿诺德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的思想不仅逐渐得到学界认可,还逐步培养了众多普通读者。除学界前辈外,一批又一批的学者逐渐加入研究阿诺德的行列中来。自《文化》出版后,又接连推出第2版和第3版。为了更好地让我国读者了解阿诺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推出了英文版 《文化》,这必将为其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日益庞大的读者群体成为阿诺德思想传播的稳定舞台。阿诺德自然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异国他乡的文化土壤上会有这么多与他心心相印之人,会有这么多知音。
三、个人与社会
在荀子那里,既然认为欲望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欲望必然引发人们之间的纷争,因此就必须以外力来对人们的欲望加以约束,才有可能使人类走出“自然状态”,而这种外力在荀子那里就是“圣人”,即为现实中的“君权”。荀子讲:“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荀子认为“归于治”的条件便是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其实,“师法之化”所化的是人类的天然欲望,所化的方式是“礼义之道”,“礼义之道”则是出自于“圣人”,而“圣人”落实于现实层面便是一种绝对的“君权”。
在荀子那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靠“礼”得以维系的,而“礼”的背后则是以绝对的“君权”作保障。可以这样认为,荀子通过将绝对权力赋予君主的方式,来实现一种整体的社会秩序,这固然可以解决“自然状态”中的纷争,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荀子看来,整个社会的构建几乎是靠“圣人”的一己之力来完成的,所谓的“圣人”落实到现实层面也就是“君主”,荀子讲:“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礼论》)显然,“圣人”的作用就是“治人”,这里的“人”即为组成社会的个体,由此可见,个体在社会之中几乎完全丧失了主动地位,而完全是被君主所治的,“在荀子看来,对于国家的治乱,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即作为政治主体的君主或作为礼法之源的君子”[9],于是,整个国家或者社会几乎就成为君主的一己之私,而作为普通的个人,则在社会中丧失了主动地位,沦为君主所治理的对象。
然而,洛克却并不认为君主专制政体是一种公民社会,而是认为在专制君主统治之下的人们仍然处于“自然状态”。究竟原因就在于,洛克认为君主并没有充当裁判者的角色,其拥有的权力并不是用来公平地解决人们之间的纷争,而只是满足自身的利益,洛克讲:“只要有人被认为独揽一切,握有全部立法和执行的权力,那就不存在裁判者;由君主或他的命令所造成的损失或不幸,就无法向公正无私裁判的人提出申诉,通过他的裁判可以期望得到救济和解决。”[4]55,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其实,从本质上讲,君主专制政体恰恰违背的是洛克的“契约”精神,洛克认为,社会的结成必须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同意和授权的基础之上的,在结成社会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中却不是这样,君主完全脱离于“契约”之外而拥有无法限制的权力,洛克这样评价君主专制政体:“这仿佛是当人们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时,他们同意,除一人之外,大家都应该受法律的约束,但他一人仍然可以保留自然状态中的全部自由,而这种自由由于他掌握权力而有所扩大,并因此免于受罚而变得肆无忌惮。”[4]57,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在洛克看来,违背“契约”精神的君主专制政体,甚至比人类在“自然状态”中的处境还要槽糕。总之,洛克认为,只有建立在个人“契约”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才有可能切实保护个体的权利不受侵害。
由于荀子理想中的君主是作为“圣人”形象而出现的,因而荀子便对“君权”给予了无限的信任,将整个社会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君主,荀子讲:“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在荀子那里,君主就是整个社会的组织者,而社会中的个人只需要听从君主的安排。如果现实中的君主恰好是一位明君的话,个人的权利倒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而万一现实中的君主是一位闇君,那就无疑会激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荀子也明确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明主与闇主的区分:“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荀子·君道》)从本质上看,荀子的“圣人”在位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此现实中闇君的产生便不可避免,正如倪德卫所认为:“圣人也如常人一样有‘恶’的性。”[10]一旦现实中由闇君来掌管整个社会,那么社会中的个人必然深受其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就如同回到了充满战争的“自然状态”,只不过不同的是,“自然状态”中是个人之间的争夺,而在闇君掌管的社会之中则是个人与君主之间的战争。在此种情况下,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除了推翻暴君的统治之外别无他法,荀子也认为,个人有权利通过推翻暴君的统治,来重新恢复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荀子赞成汤、武革命:“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荀子·议兵》)
而洛克则认为,公民社会的形成必须建立在个人同意的基础之上,这种对个人与社会的看法迥异于荀子。也就是说,在洛克那里,首先重视的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代表社会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行使的只是一种受个人委托的权力,始终是受制于个人的,“立法权既然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一种受委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享有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4]94,由此可见,在洛克的政治哲学中,每一位普通的个体才是整个社会的主导者,而并不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君主。并且,洛克认为,尽管作为受委托而拥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拥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其并不具备执行法律的权力,立法机关并不是长期存在的,它只负责制定法律,而法律一旦制定完成就可以暂时解散,“立法权属于若干个人,他们定期聚会,掌握有由他们或联同其他人制定法律的权力,当法律制定以后,他们重新分散”[4]91,而负责执行这些制定出来的法律则必须依靠执行权。由此可见,在洛克那里,立法权和执行权是分离的,正是这种分离使得法律的执行者始终受到立法机关的制约,洛克讲:“当立法机关把执行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权力交给别人之后,他们认为有必要时仍有权加以收回和处罚任何违法的不良行政。”[4]96在洛克所阐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个人有权收回作为立法机关的权力,而立法机关又有权收回执行者的权力,无疑,个人在社会中处于一种主导地位,彼得·拉斯莱特这样评价洛克政府论的主要论点:“整个论点是从人人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这一判断中出来的。”[11]也就是说,在洛克那里,个人才是权力的最终拥有者。
然而,洛克并不认为受委托的立法机关总是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一旦拥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使用强力来侵害大部分个人的权利,那么个人与社会又会重新进入一种战争状态,直到人民解散立法机关,并取回自己原本拥有的权力为止。洛克讲,“所以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因此就无须再予服从,而只有寻求上帝给予人们抵抗强暴的共同庇护”[4]139,很显然,在洛克那里,个人与社会之间也始终存在着战争的风险,这种风险很大程度上源于作为拥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个人通过“契约”来结成社会,将个人权力移交给统一的立法机关,固然相比于“自然状态”可以获得一种长久的和平保障,然而这种和平保障的实现却并不是一劳永逸和完美无缺的。约翰·麦克里兰这样评价洛克的国家观:“国家有其用途,是人发明的机器,就像人发明的一切机器,可以改善甚至拆掉。”[12]很显然,洛克认为,如果国家的立法机关违背人民的意志,人民随时都具有权利将其瓦解,个人是整个社会的主导者,并且个人与社会之间并非永远处于和平状态。
荀子与洛克的政治哲学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然状态”认知的基础上,然而由于二者所生活时代背景的差异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社会建构路径。荀子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在欲望的驱使下,必然是一种混乱的战争状态,因此,必须赋予君主一种绝对的“君权”,来确保人类走出“自然状态”;而洛克则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天然倾向于和平,人们可以遵循理性的自然法,以“契约”的方式来结成社会,从而保障人类的长久和平。荀子的“君权”路径固然可以有效地解决人们之间的纷争,但很容易导向君主专制,使整个社会成为君主的一己之私,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侵害;洛克的“契约”路径有助于实现人们之间的长久和平,切实保障个人权利,然而也始终存在着立法机关违背人民意志的风险,从而导致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尽管荀子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已经非常久远,洛克所生活的文化背景与时代背景与我们也有显著差异,然而这并不妨碍从对他们的思想比较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为当下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启发: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个人社会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努力克服荀子政治哲学中忽视个人的一面,切实保障个人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尽量化解洛克政治哲学中立法机关违背人民意志的风险,维护社会安定。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的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地方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源泉,能为地方产业的创新和转型注入活力。但是,伴随着知识型社会对人才发展的要求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在教育模式和专业水平等方面存在的矛盾日益突出,职业教育改革和升级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211.
[2] 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9.
[4] 洛 克.政府论·下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 格瑞特·汤姆逊.洛克[M].袁银传,蔡红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101.
[6] 乔纳森·沃尔夫.政治哲学导论[M].王 涛,赵荣华,陈任博,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24.
[7] 孔 繁.荀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18.
[8] 狄百瑞.儒家的困境[M].黄水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
[9] 林存光.政治的境界: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315.
[10] 倪德卫.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M].万白安,编.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31.
[11] 彼得·拉斯莱特.洛克《政府论》导论[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40.
[12] 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M].彭淮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43.
收稿日期:2019-03-12;修订日期:2019-04-02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8JK0599);西安石油大学2018年"立德树人"研究课题(LD201815)
作者简介:孙旭鹏(1981— ),男,山东海阳人,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哲学比较;赵文丹(1984— ),女,山西运城人,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儒家哲学。
中图分类号:B222.6;B56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476(2019)04-0027-05
(责任编辑:徐 杰)
标签:荀子论文; 洛克论文; 状态论文; 社会论文; 自然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8JK0599)西安石油大学2018年"; 立德树人"; 研究课题(LD201815)论文; 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