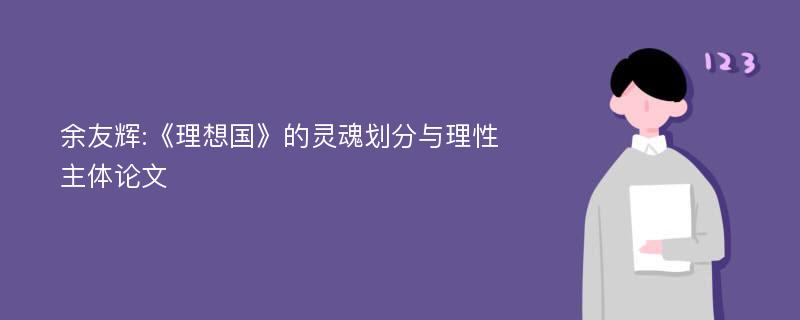
[摘 要] 柏拉图《理想国》依据“对立原则”进行的灵魂划分把灵魂的三种欲求分别归属于灵魂的三个不同部分。许多研究者认为,《理想国》的这一灵魂划分在肯定灵魂非理性部分和非理性欲求存在的同时,会导致灵魂统一主体的缺失。但细致考察依据“对立原则”划分出的灵魂的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的关系,发现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并不独立地与灵魂的理性部分共在;相反,非理性部分代表的非理性欲求只在与理性发生冲突时才会出现。如此,《理想国》灵魂划分建构的正是理性的统一主体。这样来理解《理想国》的灵魂划分,不仅能够更好地解释人类的行为,也能与近代观念相比,彰显柏拉图乃至希腊哲学家强调理性能够独自构成一种行为动机的理论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理想国》 灵魂划分 理性主体
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对灵魂划分之前,预先向读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人的所有行为或人的三种主要行为中,灵魂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发生作用呢,还是灵魂的不同部分分别为不同的行为负责?[1](436A-B)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柏拉图引入和详细探讨了一个“对立原则”,并以此展开对灵魂的划分。但就《理想国》的文本而言,柏拉图的相关分析对以上问题到底给出了什么样的回答,并不那么直观和明确。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给出否定回答,认为柏拉图的灵魂划分会直接导致灵魂统一主体的缺失;已有的正面回应也总有些不尽人意。基于此,我们力图在对灵魂划分原则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围绕着灵魂的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表明柏拉图依据“对立原则”进行的灵魂划分,实际上建构的是一个理性的统一主体,并进而依据这一理论消解相反解读可能导致的种种疑难。
一
首先从对灵魂划分原则的分析开始。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首先把这个原则表述如下:
同一事物的同一方面(;in the same respect)[2]关系着同一事物,不能同时有相反的动作或受相反的动作。因此,每当我们在灵魂中看到这种相反的情况出现时,我们就会知道,这不是同一事物而是不同的事物在起作用。[1](436B-C)
这一原则一般被人们称作是灵魂划分的“对立原则”(the principle of opposition)。为了进一步表明这个对立原则的内涵,苏格拉底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它。一个例子是,同一个人可以站着不动,但是他的头和手在摇。苏格拉底指出,如果有人说这是同一个人同时既动又静,那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说法是,这个人的一部分(躯干)静另一部分(头或手)动。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陀螺可以在其尖端保持在同一点上发生旋转。苏格拉底指出,这个时候说整个陀螺同时既动又静也是不正确的。但正确的说法是什么,苏格拉底没有清楚地言明,学者们有争论。一个较为传统的解释以解读第一个例子的方式来解读它,也就是说,这个陀螺的中轴线部分是静止的而它的圆周部分是运动的:它部分静而部分动。但近年来,这个解读遭到强有力的反对。据新的解读,这个陀螺是静止的,是就其尖端保持在同一点上没有任何倾向性运动而言的;而它是运动的,是就其在做圆周运动而言的。换言之,这整个陀螺从一个“方面”(倾向性运动方面)看,是静止的,从另一个“方面”(圆周运动方面)看,是运动的。在这种解读看来,即使从陀螺的轴线部分看,它也是运动而非静止的。[3](P90-92)[4](P228-231)
如果这个解读是正确的,那么这两个例子的内涵显然不一样。前一个例子围绕着“部分”,说的是同一物的部分“动”而部分“静”,后一个例子围绕着“方面”,说的是同一物从一方面看“动”从另一方面看“静”。把这两个不同的例子运用到“对立原则”上来,会出现意义差别甚大的解释模式。从陀螺例子来看,陀螺同时既静又动,并不会出现这个既动又静的主体(陀螺)是一还是多的问题;相反,正是这同一个陀螺,从一个方面看动,从另一个方面看静。但在人既动又静的例子中,不是这个人从一方面看动从另一方面看静,而更似乎是头(手)和躯干这不同的事物、或身体的不同部分,分别解释着身体的动或静:从头(手)看这个人在动,从躯干看这个人静止。显然,只是在后者这里,整体(身体)和部分(头或手和躯干)这一和多在运动的解释中的关系才成为问题或需要解释。
链接导航服务。将整理好的网络资源挂接到图书馆主页上,对网络资源的网址进行链接,使学习者可以点击学习、参与本课程讨论与作业。这些课程学习结束后,帮助学生获得相应的学分和结业证书。如牡丹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主页读者服务内容下设有 “慕课推荐”的专栏,提供中外知名“慕课”的网络链接,学习者可以点击进行自主学习。
当苏格拉底运用这个原则来解读灵魂内的冲突时,他明显把它看作是第一个例子那种类型的:当灵魂内部发生冲突时,例如渴了但不想饮时,冲突的双方是针对同一物同时具有的拉和推的相反倾向,而不能说是,灵魂从一个方面看有“拉”的倾向,从另一个方面看有“推”的倾向。正如苏格拉底描绘灵魂冲突的“射箭者比喻”所表明的那样:“关于射箭者的那个比方里,说他的手同时既拉弓又推弓是不妥当的,应当说他的一只手推弓另一只手拉弓才对。”[1](439B)因此,为了使“对立原则”更能描绘这种冲突类型并被用来分析人类灵魂运动,苏格拉底在分析灵魂冲突之后把“对立原则”重新表述如下:
如此,在《理想国》灵魂划分理论中,灵魂的非理性的欲望和意气部分各有其理性的因素,而作为独特理性行为动机的承载者的灵魂理性部分所涉及的理性,只能是完全超出欲望和意气之外的哲学理性。但这就是最终结论吗?
同一事物以自己的同一部分(,by the same thing of itself)在同一事情上不能有相反的行动。[1](439B)
油菜技术组利用高产创建这个平台,开展了品种比较、密度、免耕、夏播、烟后旧膜利用、地膜油菜、油菜-蚕豆套种、油菜-萝卜等蔬菜间作、油菜-玉米套种、品种展示等试验示范32组次,让项目区农户看得到、学得到,提高了群众科学种田的积极性,努力为山区农民节本增收探索新途径。
非常清楚的是,苏格拉底把正在论证的灵魂的部分看作是诸如欲求和回避这些心理状态的承载者,因此看作是为不同动机状态负责的东西。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苏格拉底关于灵魂部分的理论,不只是在说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欲求,或不同形式的人类动机。它还关键性地包含了这样两个主张:第一,肉体化人类灵魂是由许多不同的可具体指明的部分所构成的复合体;第二,正是从这种不同的部分,而不是灵魂整体,不同形式的人类动机得以产生。[3](P92)
或许还有更好的解释方式——据此,我去吃饭这一行为是由理性欲求单独导致的;换言之,因为我得出结论说,从全方面考虑,去吃饭是好的,所以我去吃饭。在这一解释中,“饿”并不独立构成一种行为动机或欲求,直接推动行为的产生,而只是我得出“去吃饭是好的”这一理性判断的一个原因,不管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原因。这恰如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ede)所言:“一个人感到饥饿这一纯粹事实还不能解释为什么他在找东西吃。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即使一个人确实感到饥饿或想要找东西吃,他也可以选择或决定不去吃东西,因为他认为现在去吃东西并不是好。一个人也可以决定去吃东西,尽管他根本不感到饥饿,因为他认为现在去吃东西是好的。”[7](P8)因此,在这里,是我的选择或决定而非我饿了这一纯粹事实,解释着我去吃饭这一行为。
2.3 枢纽基因确定 在棕色枢纽模块中,通过|GS|>0.2、|MM|>0.8筛选得到59个备选枢纽基因。另外将该模块中的基因上传至STRING构建蛋白互作网络,以degree≥68筛选得到9个备选枢纽基因。综上,取二者交集最终得到TOP2A、CDK1、CDC20、KIF11、CCNB2、BUB1这6个在共表达网络及蛋白互作网络均重要的枢纽基因(表1)。
为了在灵魂划分的基础上建构主体的统一性,学者们设想了各种可能的方式。有些学者诉诸对灵魂划分原则的这样一种解释,它强调“对立原则”的“方面”含义,贬低它的“部分”含义,以表明划分是在“同一主体”的“不同方面”或“不同功能”讲的。如此,这种解释认为灵魂的划分,主要指称的是对统一灵魂的不同功能或属性的划分。毕竟,像说身体的部分那样说灵魂的部分,始终不过是一种比喻。但这种解释,难以与苏格拉底一直致力于将不同行为动机归属为灵魂不同部分的努力保持一致,不管我们是否把它们称作是“部分”。[6](P204-205、P221)
也有学者试图在肯定灵魂部分在灵魂划分中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建构灵魂整体的统一性。这里不妨以亨德里克·洛伦兹为例。如前所言,洛伦兹相信柏拉图的灵魂划分旨在把不同的欲求或行为动机归于灵魂的不同部分,但他仍然反对波博尼奇,认为这并不必然会导致灵魂的整体性或统一主体的缺失。[3](P94,n.22、23)他的观点是,《理想国》的灵魂划分确实导致柏拉图对灵魂(至少是肉体化灵魂)是单一之物的否定,但是对灵魂是单一之物的否定并不就意味着对个体灵魂统一性的否定,因为当我们说灵魂的不同部分是不同行为动机的承载者时,同样可以如下的方式在派生意义上说灵魂整体是所有行为动机的承载者:一个主体,因为它的一个部分是一个特性的恰当主体,而被派生性地看作是这个特性的主体。在洛伦兹看来,灵魂整体作为所有欲求和动机的派生性主体,就足以保障灵魂作为部分构成的复合体的主体统一性。但是,洛伦兹没有,实际上也不能告诉我们,这种复合体的主体统一性到底是什么样的,在灵魂中有什么表现,在行为中有什么作用等等。他最后只有诉诸直觉说,我们关于个体统一的通常直觉,很难足够确定到特别要求灵魂是非复合性的,或要求存在着作为所有心理谓述的非派生性的单一主体。但这个直觉并不能拯救洛伦兹的理论,因为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更强的普遍直觉,它告诉我们灵魂要构成主体的统一性,必须要具有某种独特功能,例如综合、管理、指导、计划等,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卷最后分析灵魂的德性时所指出的那样。但很难看出洛伦兹这个派生性的灵魂主体如何能够承担这类功能;相反,作为派生性的东西,灵魂整体更可能只是作为行为动机直接承载者的部分的外在聚集,或自己各种动机和行为的纯粹被动旁观者。
如此,就陷入这样一个两难:要么《理想国》的灵魂划分理论只是在一般性地阐述人类灵魂所具有的不同的行为动机,并主要把它们划分为三种类型;要么它还要进一步把灵魂的不同部分而非灵魂整体,看作是不同行为动机的承载者。但前者很难得到《理想国》整体文本的支持。事实上,如果只是要泛泛谈论人类灵魂具有许多不同的行为动机,柏拉图根本没有必要引入灵魂划分,因为柏拉图引入灵魂划分的目的,是为了表明这些不同行为动机间可能存在的根本冲突,并进而界定这些不同行为动机的三种主要类型。显然,“方面”式的理解无法揭示这种冲突,因为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方面”有相反,无法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冲突;但另一方面,如果坚持对立原则的“部分”的含义,以彰显不同行为动机的对立冲突,似乎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灵魂的统一性或整体性的否认,或至少是对它的解释性失败。我们能走出这个两难困境吗?
二
如果《理想国》依据对立原则做出的灵魂划分理论旨在把不同的行为动机归属于灵魂的不同部分,我们是否仍然能够以某种方式来建构《理想国》的灵魂理论所需要的灵魂的内在统一?学者们之所以会经常陷入肯定前者就不得不否定后者的困境,是因为他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主要考虑的是灵魂整体和它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未触及灵魂的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样一个思考的前提:在灵魂中被划分的不同行为动机,或者分别作为它们的实际承载者的灵魂的不同部分,是各自独立、并列性地存在于灵魂之中的。例如在渴了不想饮的例子中,把追求肉体满足的行为动机直接归属于灵魂的欲望部分,基于计算而追求好的东西的行为动机直接归属于灵魂的理性部分,同时认为它们并列存在于灵魂之中。但尽管这种理解看起来非常切合柏拉图对灵魂划分进行的分析,通过研究仍然可以发现,这不仅不是唯一正确的理解方式,而且依据它对人类的行为进行解释会产生许多复杂难解的问题。
不妨举例来说明这里的问题。“我饿了,所以我去吃饭。”这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日常表达,但如果我们进一步问:“我去吃饭”这一行为的原因是什么,或什么样的行为动机导致我这一行为的?问题就出现了:按照上面提到的那种并列式理解模式,答案似乎只能是,提供行为动机的是我饿了这一肉体性欲望。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理性在这里有没有发生作用?如果没有,那么说我们的有些行为会完全不涉及理性,似乎并不是个很好的理论;如果有,那理性提供的行为动机,也即“经过计算,我判断说,去吃饭是好的”这一理性判断产生的理性欲求,在我这一行为中有什么解释性作用?对此我们或许只能说,我去吃饭这一行为是欲望欲求和理性欲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至于它们如何共同发生作用,我们无法具体确定。这同样未必是个好的结论。
如果是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产生了:尽管在灵魂划分依据的“对立原则”中出现了“同一事物”的说法,尽管苏格拉底在分析灵魂划分时经常会谈到灵魂整体,但如果是灵魂的不同部分为人类不同的行为动机负责,构成人类行为的解释性要素,那么灵魂整体的作用何在?换言之,人类行为者的主体统一性何在?难道我们的灵魂不过是各种不同的行为动机相互冲突的战场,主体自身不过是自己行为和生活的纯粹被动的旁观者?进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何对人的行为责任进行归属,如何能说主体自身可以是他所有行为的责任主体?可以看到,确实有一些学者,特别如克里斯多夫·波博尼奇(Christopher Bobonich),依据这种分析,相信柏拉图《理想国》灵魂划分会导致对统一主体的否定:“《理想国》的划分理论导致柏拉图否定了个人的统一性……促使他否认了在所有个人心理状态和活动之外的单一的最终主体的存在。”[4](P254)但如果这是柏拉图的结论,那么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甚至可以说是坏的灵魂理论。即便是波博尼奇也承认,这是个错误的灵魂理论,虽然他相信柏拉图在他更晚的著作中对其进行了纠正。但许多学者仍怀疑柏拉图会在《理想国》中给出这样错误的理论。[5]
对此,有人可能会反对:这样来解释行为,就无法区分早期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的道德心理学与中期对话中阐述的柏拉图的道德心理学。确实,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苏格拉底的道德心理学只承认有理性的欲求,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只依照理性判断而产生,而灵魂的非理性的因素,例如肉体性欲望,不构成一种独立的行为动机,它只是影响理性判断的一个因素;相反,柏拉图的成熟道德心理学,特别是在《理想国》灵魂三分中阐述的道德心理学,明确地把灵魂的非理性的因素,例如欲望和意气,也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行为动机,承认在理性欲求之外,还有非理性欲求的存在。[8]上面的解释显然未把“饿”代表的欲望看作一种独立的欲求,而只看作影响理性判断的一个因素,因此它不可能是对《理想国》灵魂划分的正确解读。但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国与矿产资源资产评估工作相似的是矿业权评估,矿业权评估与资产评估二者有相似性又有区别,见表1。矿产资源资产评估是对矿产资源资产价值化的过程,其更注重于整体矿产资源及其附属(包括矿业权及其产生的附属权益和收益等内容,相当于不动产)价值大小,强调的是价值大小,反映的是资产属性;矿业权评估的对象则是探矿权和采矿权,其目的是为各种矿业权流转变动而发生的经济行为提供矿业权价值意见,注重权利的归属和评估,更侧重法律属性。
她个子很高,瘦削有精神,但不能算漂亮。长长的头发,中分,额头饱满且窄,皮肤倒很好,一想到自己天天对着电脑已经被辐射的惨不忍睹的脸,去洗了把脸,顺手贴了面膜躺在沙发上胡思乱想。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她为什么大白天在自己家里戴着墨镜,想多了就头疼,正在恍惚间,有人敲我的房门。
情况未必如此。当灵魂内部没有冲突时,例如说,当理性和欲望不发生冲突时,不应当僵硬地把欲望处理为一种独立的行为欲求,而应当只依据理性来解释相应的行为;但当灵魂内部有例如理性和欲望的冲突时,欲望会作为一种独立的与理性判断相反对的行为欲求出现。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现在的情况是:“我饿了,但我认为现在去吃饭是不好的”,那么我们首先会有因为理性判断而产生不去吃饭的理性欲求,同时又会有因为饿而产生的推动我们去吃饭的欲望欲求。如果克服了这种相反的欲望欲求,我们自制地行事;如果我们最后屈服于这种欲望欲求,则不自制地行事。在这种灵魂内部冲突的例子中,仍然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道德心理学的不同:在苏格拉底那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只是影响理性判断的东西,它们至多会导致行为者理性判断的改变,但不会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欲求直接导致违反行为者理性判断的行为:不自制行为是不存在的;但在柏拉图那里,当欲望等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判断发生着冲突时,它们作为独立的行为欲求会直接导致与理性判断相反的不自制行为。因此,《理想国》依据“对立原则”进行的灵魂划分要说的是,当灵魂发生着冲突时,欲望以及意气构成一种独立的、与理性判断相违背的非理性的行为欲求;它并不试图表明欲望和意气作为独立的行为欲求,不管与理性判断有没有冲突,总是与理性欲求并列地存在于人类灵魂当中。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里的问题,再来讨论艾尔文引入的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我又困又饿。当我又困又饿时,我并不径直体会到,如艾尔文所认为的,两种冲突的欲望欲求:去吃饭还是去睡觉;[6](P205-206)相反,面临这种情况时,我首先要做出的是这样一个理性的判断或选择:考虑所有因素,去吃饭还是去睡觉更好?如果我做出判断:去吃饭是更好的,那么推动我去吃饭的就是由理性判断而来的理性欲求,这时不必引入饿这种欲望欲求来共同解释去吃饭的行为;但如果尽管做出了这样的理性判断,我仍然由于困而有去睡觉的相反欲求,那它就构成了一种非理性的欲求。另一方面,如果我做出的判断是:去睡觉更好,那么困就不构成一种非理性的欲求,相反,由于饿而导致的相反欲求则构成一种非理性的欲求。
65个活性化合物中除M46没有预测靶点,剩下64个活性化合物共预测靶点473个,与TTD、Drugbank、DisGeNET数据库中所获得的2 245个AD相关性基因网络进行映射,473个预测靶点中有215个与钩藤散防治AD密切相关。
如果上面的解释正确,那么在解读《理想国》依据“对立原则”进行的灵魂划分时,就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需要得到强调:首先,在理性人的所有行为中,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关于某行为是好是坏的理性判断,以及依据这一理性判断而产生的理性欲求;其次,在人类行为中可能出现的非理性的欲求,并不径直就是像饿这样的欲望因素或像愤怒这样的意气因素。相反,只有在灵魂的内在冲突即只有在这些因素违反着理性的判断时,它们才构成一种非理性的欲求。
依据这一新的“对立原则”,苏格拉底指出,当同一个灵魂在指向同一个对象,例如饮料,同时体验着相反的“趋向”和“排斥”的力量牵引时,这不是灵魂的同一个部分,而是灵魂的不同部分在起作用。在渴了不想饮的例子中,推动我们去饮的是灵魂的欲望部分(),而阻止我们去饮的是灵魂的理性部分()。正如不是身体,而是身体的不同部分,解释着它同时的动和静,同样,不是灵魂整体,而是灵魂的不同部分,分别解释着它同时体验到的相反趋动。这似乎表明了上面关于灵魂“整体和部分”问题的最后回答:当我们在学习、愤怒和满足自然欲望时,我们运用的是灵魂的不同部分,而不是灵魂整体在所有活动中起作用。用亨德里克·洛伦兹(Hendrik Lorenz)的话来说,苏格拉底依据“对立原则”进行的灵魂划分,不只是要表明人类灵魂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行为驱动力或动机,还进一步把人类灵魂的不同部分看作这些不同动机的承载者或解释主体:
如果是这样,那么柏拉图承认非理性欲求并把灵魂的非理性部分看作这种欲求的承载者的理论,并不会消解灵魂整体的统一主体性。因为,当未有灵魂冲突时,人类按理性的方式行事,不存在非理性的欲求;当灵魂出现冲突时,非理性欲求同样也以理性的判断及其相伴的理性欲求为先导,因为对后者的违反而成其所是。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术语来说,非理性欲求本体性地依赖于理性判断,以之为前提,并不具有真正的脱离理性的独立性。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灵魂整体都不独立于理性来成就其主体统一性,而是依据理性而成就为一个理性的统一主体;可能存在的非理性欲求的相反作用,表明的也不是对统一主体的根本分裂,而至多只是对理性统一主体的某种内在分裂倾向。
三
以上解读不仅能够更好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在肯定《理想国》灵魂划分的主旨的同时,建构灵魂的理性统一主体,还能够消解相反解读可能导致的在灵魂划分中有关理性的界定难题。
众所周知,中国人具有善于隐蔽、不溢于言表的性格,认为含蓄是一种美。无论是日常的生活学习、文学话语还是艺术欣赏,都体现出含蓄的特点。然而,另一方面,含蓄性意味着人们不太喜欢真实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意愿,从而使准确、快速深入地理解明白他人的思想看法变得困难。而隐喻,作为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能帮助人们更容易理解他人的看法、猜透他人的态度。正如张磊(2010)在认知隐喻的社会功能分析一文指出,“隐喻有着显著的社会意义”,隐喻性表达具有委婉功能,感情功能等社会功能。
综上所述,经过长期的发展,政府引导基金在撬动社会资本、政府意愿体现、政府参与公司治理能力和多阶段投资引导能力等方面为新兴产业发展进行了以FOF为代表的制度创新,但现有模式在考虑新兴产业融资的多阶段性、行业不对称性等方面仍有较大不足,推动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对融资特征进行准确定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创新融资模式。
柏拉图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休谟。在柏拉图看来,不只是理性不应该,尽管它可能,成为情感的奴隶;说理性,即使是在它被奴役的状态,不能产生动机,也是错误的。即使在理性的整个目的和对象,正如它能却不应该的那样,已经完全为非理性的欲望(例如财富或“肉体性”快乐)所设定的情况下,也不能得出结论说理性不能形成自己的,部分建立在推理或计算(例如关于如何最大化财富或快乐的推理或计算)基础之上的追求和回避……柏拉图的理论公正地把理性的独特性质界定为一种动机状态,它产生并受控于推理。像例子中要喝水的这种欲望则相反,不仅在来源上独立于推理,而且会在个人充分意识到有决定性的理由不按它行事时仍持续存在着。[3](P101-102)
首先,在对灵魂的欲望部分及其欲求进行描述时,苏格拉底经常赋予了它某种理性的能力。例如在界定灵魂的节制德性时,苏格拉底说道:“当人的这三个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性起领导作用,意气和欲望一致赞同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不是有节制的人吗?”[1](442D)在这里,欲望能够赞同理性的领导,说明它具有某种理性的能力,至少是理解理性判断的能力;再如,在第九卷中,[1](580E)苏格拉底依据“金钱”是满足欲望的主要手段而把欲望部分也称作是“爱钱”部分,这似乎是在把进行“手段—目的”推理的理性赋予了欲望部分。而所有这些都表明,灵魂的欲望部分也具有某种理性的能力,借此它能够形成自己的观念,并进行自己的推理。这是欲望部分特有的不能被归属于灵魂的理性部分的理性。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灵魂的意气部分。因此,灵魂理性部分的理性应该是某种更为独特或高级的理性。
必须指出的是,柏拉图与休谟的不同,不仅在于柏拉图认为所有的理性计算,不管它的标准如何,都会产生自身的理性欲求。更在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促使他相信,还有一种独特的理性欲求,会产生理性超出欲望和意气之上,完全依据自身标准,也即真实之善的知识标准而得出的计算。柏拉图把理性处理为一种行为动机,明显基于他对人类理性统一主体的理解。无论何人依据何样标准进行着价值的衡量,他都在理性地安排和控制着自己的行为。只不过依据柏拉图的价值排序,越是依据高级或真实的理性主导自己行为的人,就越能够获得灵魂的内在统一,越是依据低级或不那么真实的理性来生活的人,就越可能遭受相反的非理性欲求对其主体的分裂。僭主是最不幸的人,因为他“最不能做自己想做之事”。[1](577E)
一些礼仪习俗会导致交流障碍。比如,澳大利亚男性土著人忌讳说姐妹的名字,所以当律师问到其姐妹的名字时,他可能回答“不知道”。如果译员只是直译,显然不能促进各方的交流。
这种理论不仅具有自身的理论困境,而且它的理论依据也并不像它的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决定性的。
首先这一理论本身包含难题。一方面,这一理论必然会陷入“否认灵魂统一主体”的困境,在把形成自我的观念并进行目的—手段的实践推理的理性归属于灵魂非理性部分时,甚至会把灵魂的所有三个部分都看作像主体般行事的东西,即得出灵魂部分的“类主体”(agent-like)学说;另一方面,如果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例如欲望部分,也具有理性,会像主体一般行事,那么就不得不在行为分析中对它再进行理性和欲望的划分,如此以至无限后退:灵魂划分最终失去意义。
再从它的理论依据来看。第一,文本的依据并不可靠。事实上,认为苏格拉底对欲望的描述赋予了它某种理性功能,恰以承认灵魂的欲望部分与理性部分并列性分裂存在为前提。相反,如果把灵魂看作是以理性为主导的统一主体,那么说一个人(灵魂)的欲望会赞同理性的统治,并不会有什么问题;同样,苏格拉底在把欲望部分称作是“爱钱”部分时,也并不是在把追求钱财这种价值目标和相关的实践推理归属于欲望部分,而只是在说,某一个人,特别如灵魂当中以欲望为主导的人,在行动中以钱财的获得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进行着理性的思考和推理。因此,说欲望部分是“爱钱”部分,意气部分是“爱敬”部分,理性部分是“爱智”部分,并不是在说,同一个人的灵魂内部有这三种“类主体”的部分在各行其是,而是在说,有三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追求着不同的价值目标。对应于这一区分,苏格拉底明确地说有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1](581C)第二,就休谟式理论而言,我们恰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柏拉图就一定要接受休谟式的理论?换言之,难道因为休谟等近代哲学家否认那种仅在欲望层面上操作的理性能构成一种独特的行为动机,就说柏拉图也不能把这种理性理解为一种独特的行为动机吗?更进一步而言,休谟式的理论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站在休谟等人一边,柏拉图这样做是错误的;但站在柏拉图的一边,休谟等人的观点则是错误的。就这后一点而言,亨德里克·洛伦兹就为柏拉图做了如下辩护,尽管他的观点仍然带有把非理性欲求和理性欲求并列处理的理论痕迹:
在对灵魂的欲望部分和理性部分进行最初划分时,苏格拉底明确指出,在渴了不想饮的例子中,那个阻止我们去饮的是基于理智计算而出来阻止的,它属于灵魂的理性部分。[1](439C-D)但苏格拉底没有明确说明,灵魂的理性部分是基于什么标准而得出“去饮是不好的” 这样理智计算结论的。正因为如此,学者们经常把最初在灵魂三分中出现的理性称作“形式理性”,因为它没有指明这一理性进行理智计算的实质标准。[9](P185)从字面上看,不管理性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得出它的结论,都可以把基于这种结论产生的理性欲求归属于灵魂的理性部分。例如,它可以纯粹依据快乐主义标准,说去饮是不好的,因为这会在将来带来更大的痛苦,也可以依据更高的道德标准,说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去饮是可耻的、不道德的。但这种最符合苏格拉底字面说法的解释,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他们的理由大抵如下。
其次,学者们普遍承认,与近代哲学家特别是霍布斯和休谟的灵魂论相比,柏拉图灵魂划分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相信有理性的欲求会自然伴随理性的判断而生,即理性能够自我形成一种独特的行为动机。休谟等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相关信念及欲望的联合产物,其中,欲望单独提供行为动力,理性的信念则无关于动力,只为满足欲望提供应如何行为的信息。许多学者据此得出结论,如果柏拉图的理性部分(,字面意思是计算部分),也只是在为满足欲望提供信息,基于欲望满足的最大化计算为行为提供目的,以及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那么这种理性根本就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动机来源。这些学者认为,柏拉图灵魂理论的理性部分要构成一种独立的行为动机,就必须指向某种独特类型的理性,这种理性独立于欲望和意气之上,如欲望指向快乐、意气指向荣誉一样,完全依据自身的标准形成自己的价值目标,用《理想国》后面几卷的话来说,这种理性必须是指向真实之善、整体之善的哲学理性。[10](P123-126),[11](P146)
与传统的重力式码头相比,板桩码头结构强度大、质量稳定、受船行波影响小、施工便捷,非常适用于沿海码头工程。尤其是近年来钢材材料价格持续走低,钢管板桩码头在造价方面优势进一步凸显,成为目前沿海码头建设类型的主要选择。
注释:
[1][古希腊]柏拉图(Plato)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英文参照Plato. John. M. Cooper (Ed.). Plato Complete Works[M].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引用只标明其标准编码。
[2]埃里克·布朗(Eric Brown)发现有一些英文译本把“”错误地译为“同一个部分:in the same part of itself”,助长了一些误解。参看Eric Brown. The Unity of the Soul in Plato’s Republic.[C]//Rachel Barney, Tad Brennan and Charles Brittain (eds.). Plato and the Divided Self.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58, n.18.
声光报警器是一种用在危险场所,通过声音和各种光来向人们发出示警信号的一种报警信号装置当检测到儿童被锁车内时,单片机通过内部定时器产生按一定规律变化的PWM信号,经过三极管构成的驱动电路来驱动蜂鸣器和指示灯产生报警信号[5]。
[3]Hendrik Lorenz. Desire and Reason in Plato’s Republic[J].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2004 (Vol.27).
[4]Christopher Bobonich. Plato’s Utopia Recast: His Later Ethics and Politic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按R.F.史丹利(R. F. Stalley)的说法,我们在解读一个哲学家时,要奉行“宽容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charity),对哲学家所说的东西进行最可能好的解读,而不是把一个明显错误的理论归属于他。(R. F. Stalley. Persuasion and the Tripartite Soul in Plato’s Republic[J].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2007 (Vol.32).p.68)
[6]Terence Irwin. Plato’s Ethic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特伦斯·艾尔文一方面在解读“对立原则”时,诉诸于灵魂主体的不同属性的差异,认为“对立原则”说的是,当灵魂内部出现既追求x又回避x的相反倾向时,不能依据灵魂某个相同的属性来解释它们,而必须依据它的不同属性来解释它们。而正是在同一主体“不同属性”的意义上,才说灵魂有不同的部分;但另一方面,他在解释灵魂的不同部分时,实际上又赋予了灵魂的欲望和意气部分很强的主体性。
[7]Michael Frede. A Free Will: Origins of the Notion in Ancient Thought[M].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8]对此的详细讨论,参看余友辉. 不自制与希腊伦理学[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
[9][美]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著.徐向东、陆萌译.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10]John M. Cooper. Plato on Human Motivation[C]//Reason and Emotion: Essays On Ancient Moral Psychology and Eth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倒立摆控制系统是一种经典的研究自动化控制的实验装置,其应用已经广泛分布于机器人控制、工业自动化控制、航空航天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在自动化控制领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倒立摆因为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等特点,许多学校和相关研究机构都将其作为教学、实验平台,进行控制理论教学和开展各种控制实验[1]。近年来,倒立摆控制系统的运用越来越广泛,控制技术与方法也愈加成熟。人们通过对倒立摆控制系统的研究,处理各种多变量问题、非线性问题及不稳定系统问题,进而延伸到各类工控领域,与工业应用相结合,对解决实际问题有着显著的帮助[2]。
[11][美]余纪元.《理想国》讲演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余纪元的评论颇为典型,不妨引述如下:“柏拉图的理性概念与休谟不同。在休谟看来,理性自身没有动力,只是欲望的奴隶。欲望告诉我们要什么,确立目的;而理性告诉我们如何得到,决定有效地获得目的的手段和途径。而对于柏拉图,理性对整体的善有所知识,所以能根据这一知识选择并控制欲望的类型和内容。理性有工具性的一面,但更是实质性的。它并不仅是实现欲望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不仅告诉我们如何达到已确立的目标,而且自身确立价值和目标。它可以告诉我们,按照事物自然的秩序,按照我们的真实本性,什么才是最好的值得追求的。问题是,理性从哪里得到这种关于整体的知识?这一问题,我们在讨论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后才能回答。”
[收稿日期]2018-11-05
[作者简介]余友辉(1977-),男,江西宜黄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希腊伦理学‘自我’理论研究”(17BZX096)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06-0120-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12
标签:灵魂论文; 理性论文; 柏拉图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欲望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古代哲学论文; 《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 希腊伦理学 '; 自我'; 理论研究"; (17BZX096)论文;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