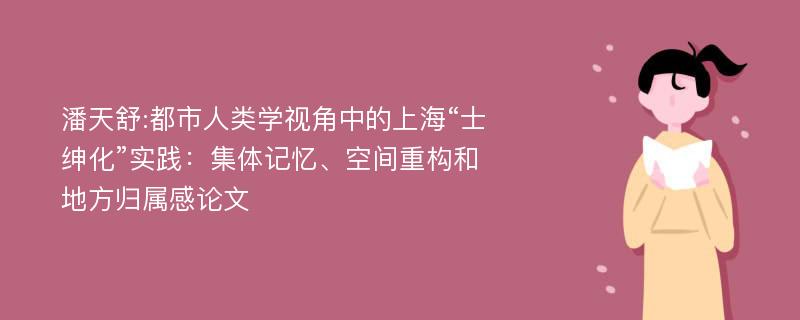
摘要:本文对始于1998年的田野体验和实地观察进行反思,以普通民众话语实践中的空间二元论入手,探讨上海城市转型语境中记忆与地方归属感之间的关系,同时观察、了解、体会和分析具有新上海特色的“士绅化”进程对于城市社区重塑的深远影响。初步发现表明:摧枯拉朽般的造城运动未曾减弱当地人对于特定场所和公共空间的集体记忆和想象,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地方归属感会随着社会分层的加剧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以各种方式加以呈现,成为当代都市话语和实践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都市人类学 空间记忆 地方感 “士绅化”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上海城市的每个角落都经历了开埠以来最大的一次改造。其变化程度之剧烈,可谓沧海桑田。为重振昔日东亚经济中心雄风而推出的一系列市政建设项目,完全达到了规划者所预期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效果。在转瞬间就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环路、南北高架桥、横跨浦江两岸的斜拉桥、隧道、地铁、轻轨和磁悬浮列车,同林立的摩天大楼一起,改变着城市居住者原有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也呈现出21世纪“魔都”上海前所未有的人文和社会生态景观。
目睹世纪剧变,我们也许会认为本地人的那种区域性的地方情结也将随之淡化或消失。然而,笔者在从1998年至2002年以及2010年世博会期间,在位于上海东南部湾桥社区所进行的田野体验和实地观察显示:上海的普通民众在话语实践过程中,仍然以自己居住地所在城区的所属地段来喻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并借此抒发文化优越感或者自卑感,甚至会在不经意地运用早该过时的“上只角”和“下只角”陈旧说法[注]Tianshu Pan and Zhijun Liu, “Place Matters: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on Historical Memory, Place Attachment, and Neighborhood Gentrification in Post-reform Shanghai,” ChineseSociologyandAnthropology, vol. 43, no. 4, 2011, pp. 52-73.笔者不无惊奇地发现:这种理应存入历史语言学档案的老掉牙的空间二元论,在特定社区和特定场合,还具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仍然可以作为一个象征符号,来探讨今日上海城区结构调整和公共生活变迁的具体空间体现形式。不久前由于闸北和静安两区合并在网络论坛和微信朋友圈引起的众说纷纭,即是明证。
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市民类似,在上海世代生活和工作的居民都习惯在日常交谈闲聊时借用地段或者“角”这样的传统说法,来特指其在城市生活的街坊邻里,并以居住地点来暗示其社会和经济地位。这种微妙的表达方式所透露的,是社会关系与空间等级布局之间的逻辑关系。“角”在实际使用产生的多层含义,涵盖了阿格纽(Agnew)所阐述的有关“地方”概念的几个方面:首先是指形成社会关系的场所或地点(即所谓的locale);其次是地段(location),是由社会经济活动而拓展的更广的范围;当然还有人们对特定地点和场所产生的“地方感”。[注]J. A. Agnew, PlaceandPolitics:TheGeographicalMediationofStateandSociety,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7, p. 28.一百多年来在上海方言中颇有市场的“上/下只角”之说,仍然不失为现时魔都居民以生活所在地在城市的地理方位来确定自己和他人社会坐标的一种策略性话语手段。
本文试图探讨城市中心特定地方的集体记忆对于公共话语构建和特定地方营造的现实意义。在上海,承载极具地方色彩的记忆,在公众话语中的表述,便是代代相传的“上只角”和“下只角”之说。著名人类学家阿鲍杜莱(Appadurai)曾经吁请人类学者在后现代语境中进行田野研究之时,务必注意“将等级关系(在特定地方)定位”的方法。[注]A. Appadurai, “Putting Hierarchy in Its Place,”CulturalAnthropology, no. 3, 1988, pp. 36-49.作为呼应,笔者在文中将以上/下只角的说法为观察切入点(而非分析框架),来进一步论述“上只角”和“下只角”作为带有上海方言特征的话语构建物,是如何被作为文化和社会标签“粘贴在想象的地方和场所之上”[注]A. Gupta and J.Ferguson eds., Culture,Power,Place:ExplorationsinCriticalAnthropolog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7.。
1.2.3 数理统计法 为了获得更多信息,先用Excel进行数据整理和转换,如:根据班级编号换算为学院代码、根据出生日期换算为2017年12月时的年龄、根据家庭地址换算为各省份代码、根据学生1000m或800m成绩(包含分秒数值)转换为秒数计算等。然后再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探寻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大小及是否显著。男女生在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差别较大,测试指标也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分别对男女生进行分析。具体方法是在控制年级、生源地2个变量下,进行男女生体质测试各指标间的偏相关分析方法。
二、“上只角”/“下只角”二元论与都市空间重构
在上海方言里,“上只角”可直译成英语里离人口繁杂地段有一定距离的幽静的富人住宅区(uptown);而“下只角”则是拥挤的穷人聚居区(如棚户)的代名词。“上/下只角”二元论,在身处欧美工业社会语境的社会学家看来,在体现阶级和族裔差异的空间和地方感方面,不失为一种绝妙的表达方式。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间,上海历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洗礼,成为“十里洋场”和华洋杂居的繁华都市。在此过程中,这一空间二元论,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个人或家庭乃至社区邻里层面的生活历程。它在话语表述中所展现的,是一种对于本土或出生地的认同感和对于目前所处生活环境的体会。社会史学者早已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空间二元论所凸现的社会优越感和市井势利性。[注]详见E. Honig, CreatingChineseEthnicity:SubeiPeoplein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8-35;H. C. Lu, BeyondtheNeonLights:EverydayShanghai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316.如下文所述,作为历史想象力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表征,这一空间二元论不失为本地居民(包括已经扎根立业的“新上海人”)、各级官员和房地产商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定位参照点,尤其是在新世纪上海城市的方方面面发生剧变之际。
具体地说,所谓的“上只角”就是指上海在鸦片战争之后成为租界之后来自英法美等国的洋人的住宅区。现在的衡山路、华山路和武康路地区,静安区南部,和卢湾区(现已经归属黄浦区)北部,是久居上海的市民公认的典型的“上只角”。[注]徐中振、卢汉龙、马伊里:《社区发展与现代文明:上海城市社区发展研究报告》,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42页。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瓜分上海,以租界形式来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成了“上只角”的历史雏形。不管是昔日公共租界内的外滩和南京路十里洋场,还是法租界内幽静的旧别墅区,如今都是“上海怀旧”产业的文化地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1949年以后,那些收归国有的西式楼宇也继续在为新政权的各个相应政府部门服务,其建筑风格也得以维持保留。在“上只角”地段,人们不时能看到在梧桐掩映之中的多数已经易主的旧宅大院,青苔挂壁,却风韵犹存。控制人口和固定户籍是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规划的一大特征。[注]详见L. J. C.Ma and E.W.Hanten, eds., UrbanDevelopmentinModern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M.K. Whyte and W.L. Parish, UrbanLifeinContemporary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由此上海内城的“上只角”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始于上世纪90年代城市改造的浪潮而下降。居住在“上只角”内的众多宁波籍居民在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优越感,往往源自居住地的象征意义。比如当某位带有浓重宁波口音的老人说“我住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附近”时,我们完全可以猜测其实际居住地点不过是一栋相当拥挤的年老失修的公寓楼。但在房地产开发尚未成气候时,居住方位(即“上/下只角”)对于宁波移民的后代们来说远比居住条件重要。
本次2018 NALLTS秘书处收到135篇论文,经审改后选109篇论文编辑进入国际会议文集Proceedings of 2018 NALLTS,由美国新视野出版社出版。
(6)结核索条灶可牵位胸膜,致胸膜局部增厚,粘连,累及胸膜时可出现胸膜腔积液(叶间积液),可以在CT定位下抽取并化验胸水进行定性。
就实际居住条件和环境而言,在上海闹市区与“上只角”相对应的“下只角”是那些拥挤不堪的棚户区。在城区大规模改造之前,上海的“下只角”通常包括从周家角到外白渡桥的苏州河两岸,北部的沪宁铁路和中山北路之间地区,南部的徐家汇路以南,以及中山南路以北地区。[注]徐中振、卢汉龙、马伊里:《社区发展与现代文明:上海城市社区发展研究报告》(未刊本),第42页。“下只角”的传统居民是来自邻近苏北地区的移民或难民的后代人,经常说一口带有浓重家乡口音的上海方言。在最能体现上海普通市民文化生活的滑稽戏表演中,苏北口音就是演剧中一种象征小人物处于“下只角”卑微社会地位的符号。这种艺术的真实确实是生活现实的反映。而宁波口音由于甬籍经济势力的强大而成为上海方言的一种标准音(如从“我伲上海人”到“阿拉上海人”的变化所示)。早在20年前,加州大学教授韩起澜(Honig)就指出:“苏北”在语言使用中实际上已失去指代籍贯的作用,而是一个充满歧视色彩的词汇。[注]E. Honig, CreatingChineseEthnicity:SubeiPeopleinShanghai, 1850-1980, pp. 28-35.由此在上海的社会空间中,“下只角”成了针对以苏北人移民为主的下层平民的偏见的源头。与世界上多数地方对贫民居住区固有的误解和成见相似,上海“下只角”的棚户区常常被认作充斥陋屋和违章建筑,破碎家庭,社会风气败坏和陷入贫困泥潭而难以自拔的“都市中的村庄”。可以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上只角”是以宁波移民群体为代表的、中上阶层上海市民努力追求的一种代表现代和文明的美好理想,那么“下只角”只能属于落后、愚昧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下层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上海研究专家瓦瑟斯特穆(Wasserstrom)曾质疑中外学界将租界时期定位成中国现代性发展重要标志的倾向,从而间接对“上/下只角”二元说法在学术探究上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注]J. N. Wasserstrom, “Questioning the Modernity of the Model Settlement:Citizenship and Exclusion in Old Shanghai,” in M. Goldman and E. J. Perry, eds., ChangingMeaningsofCitizenshipinModernChin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0-132.笔者在对他深邃的历史眼光表示钦佩的同时,不得不指出:作为都市生活集体和个人生活体验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上/下只角”的二元论在地方行政区划实践中,确有参照系的作用。1949年以后,新政府对上海城区重新划分,力图改变租界时代留下的格局。新设立的区中,常常将“上只角”和“下只角”一并纳入,以体现新社会所倡导的对居住条件不同的居民区一视同仁的平等精神。在地图上,“上只角”和“下只角”的界限随着地方政治版图的改变(如静安和闸北两区合并),已几乎消失。然而,为什么在日常话语系统里,这一本该作古的二元论为何还有市场呢?
我们选择了现实主义,我们坚定地走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遵循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实践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现实主义绘画创作方面,关东画派艺术家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群体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
诚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言,革命者在取得胜利后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去承继其前任的历史文化遗产[注]B. Anderson, 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pp. 160-161.,而并非真的在物质上毁灭旧时代留下的一切东西。如原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在成为浦东发展银行之前,一直作为市政府行政大楼,是外滩的标志性建筑。在外滩的其他风格各异的西洋建筑,长期以来也发挥着市政府和其他部局单位的日常办公以及商贸功能。正是由于这些足以成为上海历史文化遗产的楼堂会所的客观存在,使得“上只角”的符号表征意义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而1949年后新的区划不但没能使人们心中的“上只角”和“下只角”消失,相反,这一“上/下”二元论在不同社会交往情境中,继续成为人们在日常谈吐中区别高低和贵贱的重要指标。
第一,建立一个公众号,“客家生态旅游之路”,建设“导航、导购、导游、导览”四导产品架构,完善旅行模式。
三、城市社区的“士绅化”进程
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基建和商业发展项目,在快速地重构中国沿海和内地城市的社会空间。与经济和社会转型同步的城市化进程,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重塑城区的新旧邻里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中国城市面貌改变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楼宇和道路,更是过去十年以来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弹指之间,昔日宁波帮的后代已成为地道的老上海。在日常会话中,经过宁波方音改造的上海话比原本听上去更接近本地土话和吴侬软语的上海方言要更为标准和自然。当然上海话的实际发音体系也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了个别苏北方言的元素,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多源。这一过程暗示苏北移民的后代在随着下只角被推土机碾为平地之后,告别了不堪回首的个人和社区的过去。而他们在城市社会生活中饱受不公待遇的地位已被如潮水般涌入的民工群体迅速代替。
随着改革的深化,新一代具有专业知识和国际眼光的政府官员开始主导城市管理实践。与老一代相比,他们有新颖的思路和强烈的进取意愿,来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城市扩张和“流动人口”剧增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国企重组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包括消肿和分流在内的措施,使得数量可观的待岗和下岗职工逐渐代替老弱病残,成为社区“困难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上海有领先全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应付下岗带来的社会问题仍然是城市管理的当务之急。由于上海在上世纪一直是国家重轻工业集中的超大型城市,纺织等产业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冲击。许多传统的制造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下岗现象存在。市内未开发的“下只角”一度成为“吃低保”的下岗工人和其他困难人群的主要集中地。许多待岗和下岗职工,在一夜间发现,他们得努力去适应一种以他们居住的社区而不是单位为轴心的所谓“社会人”的生活方式,不管他们对此有无思想准备。
图2为C/C试样热解碳的偏光显微图.由图可知,C/C试样中CVI制备的热解碳具有规整的“十”字架消光轮廓及环向裂纹,为光滑层结构,因此C/C试样的摩擦系数相对较低,具有耐磨的特性.在摩擦过程中,热解碳形成的磨屑膜隔离材料与对磨销的直接接触,起到了减小摩擦系数、降低磨损率的作用;热解碳消耗后,树脂碳支撑碳纤维,与碳纤维共同保持材料的结构,承受应力作用;树脂碳被犁削后,碳纤维因失去支撑而断裂或脱出,形成硬质磨屑.
近几年来因商务和学术研究久居上海的欧美人士,在谈到上海市中心及周边地带在近十年发生的瞩目变化,都会使用“士绅化”这一词汇。但要更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士绅化”进程,我们不能脱离住房改革、地方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基建发展的大背景。在20世纪末上海城市改造的具体语境中,“士绅化”首先表现为一系列旨在美化市容和改变文化景观的市政措施和建设项目。与欧美国家城市发展所经历过的富裕人士因穷人不断迁入,“放弃”内城,在近郊购置房产所不同的是,在上海,即便是拥挤的闹市区就有相当部分属于“上只角”。而来自海内外各种社会和经济力量近年来对这部分“上只角”所展开的空间重构,是值得城市研究者认真关注的“士绅化”进程的重要方面。总之,“士绅化”作为一股造就上海文化生态景观的结构性力量,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决策和规划机构,也是自下而上的植根于邻里社区的组织和网络。
有意思的是,就地理位置而言,湾桥与市内地处边缘的“下只角”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是湾桥距其北部“上只角”街区的步行时间不过十来分钟,离众多历史地标也仅一箭之遥。湾桥之北是中共一大会址和在此附近的“新天地”高档娱乐区。湾桥之南则是被称作中国工人阶级摇篮的江南造船厂(原江南制造局)。湾桥之东是豫园城隍庙旅游景区,由湾桥向西行20分钟,便是远近闻名的徐家汇地区。在湾桥北部的“上只角”,由于上海怀旧文化产业和政府历史建筑保护措施的作用,租界时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修葺一新。老洋房、老公寓楼和里弄石库门等,或整旧如新,或整新如旧。建筑文化的再次发明似乎在暗示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该区法租界的昔日风采。而位于南部的湾桥却相形失色,“下只角”的阴影挥之不去。已成为交通干道的徐家汇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上/下只角”的分界线。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笔者的主要田野点湾桥社区以北的“上只角”地段,各类租界时期的公寓楼,别墅和洋房修缮一新,与时下兴建的风格迥异的高层住宅和办公楼相映成趣。的确,日渐多元化的建筑与景观设计,在卢湾北部商业中心周边高档消费区(以新天地为代表)刻意凸显的新“上只角”氛围,与美国波士顿城旧区改造“士绅化”杰作之一的昆西市场旅游景点,可谓异曲同工。公共艺术和灯饰的巧妙使用,使一些历史建筑旧貌换新颜。同时,一些废弃的老厂房和车间经翻修重整,成为时尚设计室、画廊和工作坊。位于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界处的新天地多功能消费和娱乐区,与红色圣地“一大”会址比邻而居,集历史凝重、现实思考和未来憧憬于一体。在这里投资者煞费苦心,耗资千万,打造以展示上海石库门民居风格的新旧混合建筑群体,其轰动效应非同一般,引得远近游人纷至沓来。新天地在商业上的初步成功,使市内其他地段(尤其是位于“上只角”附近住房条件陈旧的一些街区)纷纷效仿,以重建文化街和维护沪上旧别墅群为目标,试图再造“新天地”,从而人为地加快和加深新时期海派“士绅化”的程度。从理念上讲,在城市改革语境中依靠市场和文化重建的力量来促进街区“士绅化”,比单纯依赖行政手段来美化市容和塑造文明社区要更为有效和持久。然而,与后工业化城市复兴实践经历相仿的是,真正受益于“士绅化”的往往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宠儿,而低收入人群却难以欣赏和分享良好的家居环境和治安状况带来的好处。上世纪90年代末,南部湾桥的“士绅化”进程较其北部“上只角”地区要缓慢得多。
跨国公司和私有企业的涌现,也使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多元。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各种知识、技术和观念的普及,也在渐渐地影响上海都市“上/下只角”的社区改造思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专业化和细分化,以及强调社区有序发展和注重经济效益的路径选择,正在主导着城市旧区改造中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士绅化”进程(gentrification)。作为后工业化社会所特有的城市社区重构和住宅建设变化模式,“士绅化”(高档化)这一社会学家所造的词汇所描述的是最近二三十年欧美大城市(如伦敦、纽约和华盛顿等)的一种复兴和重塑过程。[注]详见 E. Anderson, Streetwise,Race,ClassandChangeinanUrban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T. Butler, LondonCalling:TheMiddleClassandtheRemakingofInnerLondon, Oxford: Berg Publishers, 2003; J. Caulfield, CityFormandEverydayLife:Toronto’sGentrificationandCriticalPracti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城市社会学视角内的“士绅化”表现形式通常是:高收入的专业人士迁入改建后住房条件和治安状况显著改善的内城,同时社区重建所引起的房价和租金上涨,使久居内城的低收入居民(以少数族裔和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为主)被迫外迁。房地产开发商、当地政府官员和新近迁入的高收入人士都在“士绅化”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应该说,在1949年之后租界时代遗留的以路标、马路和建筑区隔“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做法已被摈弃。然而,在新设区内设立的街道和居委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又延续了以行政手段区分“上/下只角”的做法。如卢汉超所指出的,街道组织领导为了方便日常工作和管理,索性按居民出生地的地名来命名居委会。[注]H. C. Lu, BeyondtheNeonLights,EverydayShanghai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316.在上海人眼中,“苏北里委”和“南通里委”这些实实在在社区的地位及其名称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上只角”原法租界的霞飞路,尽管在崭新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被更名为淮海路,但是对于居住在那里的普通居民或者是慕名而来的“老上海迷”来说,它所代表的特殊的历史风貌、艺术品味乃至文化资本(Bourdieu,1984)仍然未见丝毫减少。[注]P. Bourdieu, 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Judgmentof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016-2022年中国有机农业行业深度调研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有机生产面积已经达到272.2万公顷,有机产品总值800多亿元。2016年,有机产品销售额与2014年相比增长20%。追求每一口的安心味道,正在成为更多百姓的期待与选择。
以湾桥所在城区的街道设置为例,我们不难看到这“上/下”二分论在考察“士绅化”过程中的实际意义。该区北部的三个街道大致位于“上只角”内,而位于南部的湾桥则是闻名遐迩的“下只角”,是由一个街道单独管辖的小型行政单元。与市内其他的“下只角”相类似的是,湾桥街道的老居民多是1949年以前逃荒和躲避战乱的难民和本地菜农的后代。在1998年初次进行人类学田野研究时,笔者注意到:那已经变了调的苏北和山东方言,在某些里弄,是比上海话更为有效和实用的沟通语言。[注]详见Tianshu Pan, NeighborhoodShanghai,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24; Tianshu Pan and Zhijun Liu, “Place Matters: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on Historical Memory, Place Attachment and Neighborhood Gentrification in Post-reform Shanghai,” ChineseSociologyandAnthropology, vol. 43, no.4, 2011, pp. 52-73.如下文所述,湾桥在地段、居民出生籍贯和当地人口的社会成分方面,的确具备“下只角”的一些污名化特征。
笔者发现:不管是上海本地人也好,或是研究上海的专业学者也好,对于“上/下只角”二元论,难免会有一种莫衷一是的态度。这种难以启齿的感觉,类似于笔者与来自印度的学者谈到种姓或与美国同学论及族裔和阶级差异话题所遭遇的尴尬。一般来说,相对于其他阶层,具有婆罗门背景的印度同学更愿意带有一种优越感来谈论种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而低种姓阶层的人士则会高谈阔论圣雄甘地废除种姓差异的壮举,而闭口不谈平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在笔者曾任教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来自中上层背景的美国白人学生会轻松地谈论起他们所居住的高尚住宅区以及同样高尚的邻近学区(school district)。而来自华府东南黑人区的学生则干脆以“巧克力城”(喻指其所属种族的肤色)作为首都的昵称,在心理空间上与居住在华府西北部的精英人士保持距离。
笔者的童年是在黄浦区的一个住房类型混杂,与卢湾区北部一街之隔的社区(位于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界处)度过的。然而多年来笔者从不记得街坊邻里提起过在本市东南部有一个叫湾桥的地方。在与街道和居委会的朋友谈起自己竟然对湾桥这一近在咫尺的实实在在的社区如此无知而感到羞愧时,他们却十分大度地告诉本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用他们的话来说,湾桥不过是“卢湾的下只角而已”。言下之意,没有人会在乎下只角的存在,尤其湾桥这个下只角还有“卢湾的西伯利亚”这一别号。在田野研究过程中,笔者逐渐感觉到,湾桥的“下只角”地位,因为一些附加的历史因素而变得更加独特。首先,1949年前兴盛的当地殡葬业,是数代居民坚信的败坏本地风水的重要根源。1937年日军空袭上海之后,成千上万的无主尸体未经丧葬仪式,便掩埋在湾桥,填平了众多臭水沟,也进一步污染了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在解放战争期间,湾桥的某些传说中的“鬼魂”出没之地,成了国民党残兵、流寇和因土地改革而逃亡来此的地主的歇息场所。这段当地老居民觉得难以启齿并希冀尘封忘却的历史,却又在上世纪90年代大兴土木的基建和住房改造高潮中破土而出,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有些建造摩天办公楼和高层住宅的工地,挖土机掘地数尺之后,工人们便会惊恐地会看到遗骸和尸骨。这些不经意的发现,又会勾起老一代人的记忆。难以考证的琐碎叙述,经过街坊内外的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醋,变成一种“历史事实”,成为工地附近的居民寝食不香的缘由。
对于居住环境中处于“上/下只角”之间的南市老城厢来说,这种夹在地段优劣程度与实际住房条件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现在已成为黄浦区(其辖区覆盖了原公共租界地段)一部分的南市,曾是上海市人口极为稠密的居住区。区内本地老屋和旧式石库门里弄鳞次栉比,是极富上海本土特色的居住模式。近年来,旅游业的兴盛使该地区焕然一“新”的城隍庙、豫园、文庙、茶楼、老字号的饭店乃至遗存的上海县城城墙,成为重要的文化地标。但是,这些地标周围的居住环境,却令地方官员难堪。本地居民不愿迁往近郊新开发的住宅区,宁肯忍受合用公共厨卫以及马桶带来的不便、烦恼和尴尬。一方面老城厢的悠久历史使他们对于世代居住的街区有一种归属感。另一方面,由于“上只角”近在咫尺,老城厢的居民还时而庆幸自己能在心理上保持与“下只角”的距离。
1949年前的湾桥,乱草丛中,死水潭旁,处处蚊蝇滋生。据老居民回忆,夜出无街灯,受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打劫乃是家常便饭。白天外出常会看到弃婴和饥寒交迫流落街头的乞丐,甚至还有破草席包裹的冻死骨。一位已退休多年的街道干部告诉笔者,湾桥在1950年之前本是一片藏垢纳污之地,连一所学校也没有。与北部“上只角”的居民区相比,湾桥无疑是被历史遗忘之地。在区政府派往湾桥工作的干部眼中,湾桥与该区北部的反差巨大,缺乏文化、历史和传统,简直就是他们的“伤心岛”。
“士绅化”进程的催化剂是以怀旧为主题的老上海文化产业。以上海怀旧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影视剧、摄影集、回忆录、散文、音乐和物品收藏等一系列文化产品的创作、营销和消费,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无非是对当年十里洋场繁华旧梦的回味、想象和咏叹。这一怀旧产业的兴盛,得益于上海在城市改革进程中涌现出的来自海内外社会精英人士的精心策划和推介。当然,上海怀旧的产业化也为研究观察都市文化变迁与城市规划和社区构建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宝贵契机。透过怀旧的表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老上海集体记忆的重新发掘、重新评价和再度包装,以期重现和重构文化的复杂过程。基于笔者的观察,对于记忆的策略选择和历史的想象重构,是人们在经历城市百年未有的社会和经济领域巨变时的回应。从某种程度上讲,上海怀旧能使城市的新生代精英(如各级政府官员、作家和艺术家、建筑师、地产开发商和白领人士等)回味大都市的昔日辉煌,为实现规划蓝图,营造新世纪的全球化都市做好热身准备。从新天地到思南公馆以及徐汇和静安的学区房,都是特定地段和社区士绅化程度在崭新语境中的鲜明体现。
直到上世纪末,你如果从卢湾北部向南往湾桥方向走去,不难发现你视线中房屋建筑风格会“移步换景”,从夹在后现代风格摩天大楼之间的欧式洋楼,到传统的石库门排楼以及式样统一的新村楼房。到了湾桥,你会看到老工房,低矮的本地老房和尚未拆迁的棚户内为拓展生活空间“违章搭建”的小屋。在鳞次栉比的高楼还处在城建规划馆的模型展示盘的发展阶段,你在湾桥所看到的是新旧交替的真实生活图景。
在1995年成为文明社区之前,湾桥从未被外界重视。在厚达两百多页的区志中,占地三平方公里,拥有八十多万常住户口居民的湾桥,只有区区两三页的介绍。在眼界甚高的地方官员眼中,本区的亮点从来就应该是其北部文化气息浓厚的“上只角”,而决不是相形见绌的湾桥。难怪在2000年夏天当笔者将刚完成的一份涉及湾桥1949年前历史的田野报告面呈一位街道干部时,他颇不以为然地说道,过去的事情有什么好研究的,而且这么小一块地方也值得大书特书吗?显然新一代的街道和局委干部,似乎没有那种怀旧情绪,他们的着眼点是社区的现状和未来,而湾桥作为“下只角”的过去,只是一个可以甩去的历史包袱而已。
出于现实的考虑,街道的干部朋友们对湾桥社区在1949年前历史的兴趣永远停留在茶余饭后的议论,但笔者对于湾桥地方性知识的进一步探求,也许冒犯了那种人类学家所说的充溢着“文化亲密度”的集体空间。[注]M. Herzfeld, APlaceinHistory:SocialandMonumentalTimeinaCretanTow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0.笔者在随后的几次访问中得知,有关湾桥过去的讯息(尤其是有关风水的说法),如果被好事者大肆渲染,会间接地损害到地方发展的经济利益。比如说,位于大路两侧的硬件和设施相似的新建住宅区,由于一个接近“下只角”,另一个则属于原租界的南侧,两者间每平米的房价可相差近1000元人民币。其中来自港澳台的风水先生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湾桥的历史对于房价的高低起了市场之外的“调节”作用。与城内其他原“下只角”地段的街道和居委会干部一样,湾桥的地方官们竭尽全力,通过积极参与文明社区和其他社区发展活动吸引传媒的注意力,以改变人们对社区的刻板印象。从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每一届的街道领导都倾注无数汗水,试图在这白纸一张的“下只角”中,描绘出美妙的图画。他们意识到存在于湾桥历史记忆的潜在力量,并未随着时间而消逝。而他们的努力方向,恰恰是要使这种集体记忆转化成社区“士绅化”的驱动力。
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使上海走向从制造业逐渐发展成以服务和金融业的面向高科技未来的国际大都市的轨道。这一城市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卢湾北部(“上只角”)和南部(“下只角”)的“士绅化”过程。在北部,保存完好的租界时期的洋房和傲然屹立的摩天楼宇,似乎预示着新一代城市的主人在努力恢复昔日东方巴黎和亚洲商业中心地位的决心。在这里上班的白领们充满自信和活力,体验着其父辈所梦想不到的职业人生。而与此同时,南部的湾桥却在目睹国有企业重组关闭、职工分流和下岗的尴尬场景。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展现在卢湾的这种反差极大的南北生活方式,似乎又拉大了上下角之间的距离。
上午十点,大林起床了。他一头濡湿地从小间里出来,就看见倩倩坐在门厅的一堆鞋子里搭积木。大林问女儿,你妈妈呢?倩倩说,打牌去了。大林说,宝宝肚子饿不饿?宝宝吃了饼干,不饿。爸爸肚子好饿。爸爸你吃宝宝的饼干呀。爸爸不吃宝宝的饼干,爸爸要吃宝宝的肉肉。大林说着就捉住倩倩的胳膊,张大嘴巴。倩倩咯咯地笑起来,并不躲避,还把另一只细小的胳膊也伸到大林的嘴边。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在湾桥的众多工厂关门大吉之后,房地产开发商在厂房拆除后的土地上建造起了高级住宅小区。在新生代街道领导的眼里,迁入这些小区的居民大都有相当高的教育程度和专业背景,能极大地提高街道的人口素质,是湾桥保持其文明社区光荣称号的重要保证。于是,湾桥的新建小区,开始代替工人新村,成为街道社区发展项目试点和推广的主要对象。尽管迁入高档小区的居民对湾桥社区毫无感觉,他们却成为街道干部在参加市级文明社区评比中的取胜关键。由于新建小区的“软硬件”设施较湾桥的普通新村更为完善,街道将其视作向外界展示其促进社区发展的示范点。结果,还未完全认同湾桥社区的新居民,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居委会选举和业委会组建的生力军,在媒体中曝光率极高。而在多数传统新村中的老居民却在社区日渐“士绅化”之际,成为的陪衬“边缘人”。而正在城区之内蓬勃兴起的“上海怀旧”产业,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在城市生活中的服务对象而言,还是以重现“上只角”当年风貌,迎合当今时尚潮流为主要特色。对于同属一区但地处湾桥“下只角”的平民百姓来说,其意义实在有限。
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的湾桥文明社区建设,似乎又再次印证了地方归属感和集体共享记忆的珍贵价值。日新月异的时空变幻图景,通常会使管理者忽视社区邻里内部原有的人情和伦理资源对城市凝聚力、城市治理的公共文化意义和实际价值,而无形的社区内道德传统力量一旦流失,则需要有形的公共资源来弥补,被割裂的社区网络也平添了公共的治理成本。湾桥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仅一箭之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世博会举办期间所占据的展示社区文明舞台的重要性。在增强邻里功能、追求管理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新一代的街道干部在实践中尝试降低日常行政运营的间接成本,同时积极迎应士绅化的趋势,适时营造对社区成员产生影响的公共文化氛围。而这种公共文化氛围是以自发的和受到激励油然而生的志愿精神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社区内原有的各种关系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感和责任感以及对行为规范和道德伦理的认同和行动上的默契,也为志愿精神的培育和发扬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充沛的能量。熟悉的乡音、对于小区里弄新村内一草一木的共同记忆以及源自孩童时代的同窗友情,也会使志愿精神得以延续和拓展。
四、结语
本文以沪人皆知的“上/下只角”空间二元论入手,论述特定社会语境中历史记忆对“上/下只角”这些想象社区的空间重构的作用。城市人类学者所强调的将个人与集体记忆与权力结构和特定地方相连的研究手段,有助于我们观察、了解、体会和分析具有新上海特色的“士绅化”进程及其城市中心社区发展的推动和限制作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摧枯拉朽般的造城运动,实际并未造成人们地方感的消失,相反,这种地方感会随着社会分层的加剧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成为城市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ThePracticeof“Gentrification”inShanghaifromthePerspectiveofUrbanAnthropology:CollectiveMemory,SpatialReconfiguration,andtheSenseofPlaceAttachment
PAN Tianshu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flect on the ethnographic field research launched in 1998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al memory and place attachment in the context of Shanghai′s ongoing transformation, using the spatial dichotomy from the everyday discourse of the city-dwellers as an entry point. Meanwhile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profound impact of “gentrification” process 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communities in urban Shanghai. As initial findings suggest, the sea change brought forth with decades of city-building has hardly weakened the power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imagination pertaining to particular localities and public space. Meanwhile in routine life the sense of place attachment will manifest itself in different forms at particular times and on various occasions, and hence become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contemporary urban discourse and practice.
KeyWords:urban anthropology; spatial memory; the sense of place attachment; the practice of gentrifica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边疆民族公共记忆的跨学科研究”(16BMZ037)。
作者简介:潘天舒,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陈沛照
标签:上海论文; 士绅论文; 社区论文; 上只论文; 租界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边疆民族公共记忆的跨学科研究”(16BMZ037)论文;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论文; 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论文;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论文; 上海人类学学会应用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论文;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哈佛校友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