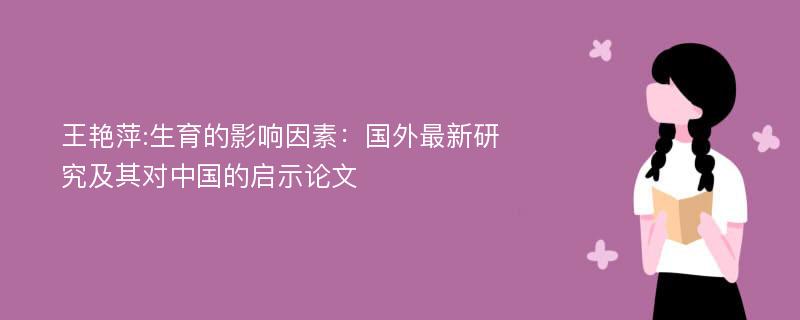
[摘 要]从国际范围来看,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或者是低收入国家,均存在总和生育率(TFR)的下降趋势。针对此现状,国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从最新研究成果来看,生育的影响因素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外部环境因素,又包括诸如生育成本、教育水平、家庭谈判或契约、生育方式及性别偏好等家庭内部因素,与生育相关的政策效果也具有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基于国外最新研究对中国的生育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启示,建议一方面要关注影响中国生育的关键因素和独特因素,另一方面要基于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关键词]生育;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国外研究
最近几十年,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国家已从高生育率低寿命的人口特征过渡到低生育率高寿命的人口特征,这种转变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从跨学科角度对最佳生育率的确定、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及生育率的影响因素等三大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生育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既包括涉及法律和制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外部环境因素,又包括诸如生育成本、教育水平、家庭谈判或契约、生育方式及性别偏好等家庭内部因素。同时,与生育相关的制度效果和政策效果也具有不确定性和差异性。
从中国目前的生育状况和生育趋势来看,放开二孩生育的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女性的生育意愿偏低依然限制了二孩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低生育率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根据预测,现有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并不能适应我国长期的人口均衡发展及经济发展的要求[1]53,也可能无法使中国摆脱老龄化局面[2]。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期对中国的生育研究和生育政策产生一定的启示。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众多。本文收集的最新文献主要来自人口经济学领域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9—2018年十年间有关生育影响因素的论文。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等方面均可以看出生育的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一、影响生育的家庭外部因素
(一)制度因素
1.公共养老金制度
国外学者认为,养老金制度与生育之间呈现复杂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公共养老金制度对生育率既可以产生正向影响,也可以产生反向影响,或者同时产生正向或反向影响;另一方面,生育率变化对公共养老金的可持续性也会产生影响。
关于养老金制度对生育的影响,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
(1)养老金制度对生育产生正向或反向影响取决于育儿成本和利率等因素。假定育儿成本包含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生育率是否会随着现收现付社会保障的扩大而提高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养育子女的金钱成本相对于时间成本的大小;二是生育率与市场利率的比较。从长远来看,如果时间成本在养育成本中所占比例大于金钱成本,且市场利率低于生育率,那么,现收现付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刺激生育。否则,生育率将会下降[3]。
(2)较高养老保险缴费率会导致较低生育率。假设一个家庭有了孩子,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放弃的终生收入意味着生孩子的机会成本,那么,一方面,较高的养老金缴费率降低了这种机会成本,从而生育率提高(即价格效应);另一方面,养老金体系的高缴费率会降低终生收入,以至养老金体系中存在隐性税收,从而生育率降低(即收入效应)。总效应取决于两种效应中较大的一个,其数量多少取决于养老金制度的内部收益率。基于德国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证实,较高养老保险缴费率会导致较低生育率[4]。
(3)养老金制度导致生育率提高。Makoto Hirazawa et al(2010)的研究证明,在美国,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导致缴费率的提高,倾向于较高缴费率的退休人口比例也提高;若该制度涉及不同养老金缴纳额的退休人员之间的再分配,由于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的代际再分配,缴费率的提高会使更多人选择生育孩子(即未来的缴费者)[5]。
关于生育率变化对养老金的影响,西方有这样一种说法,即生育率下降是公共养老金可持续性的一颗定时炸弹。虽然此说法似乎已得到充分证实,但是Luciano Fanti和Luca Gori(2012)却认为,从长远来看,出生率下降不一定会导致养老金下降[6]。为了使长期现收现付的公共养老金能应对生育率的变化,生育率下降时应当重新设计最佳方式的政府养老金计划,保持公共养老金规模增加或不变。
1.失业
从发达国家来看,福利制度改革的目的主要为了刺激生育。以瑞典为例,2002年推行的育儿费改革带来育儿成本降低,未生育的已婚夫妇做出积极反应;增加生育的主要是低收入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并没有增加对孩子的总需求,但为确保在最大时间范围内从低成本中受益而推迟了二胎生育;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因边际成本(多生一个孩子所增加的养育成本)下降而增加生育。该项改革所减少的边际成本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18%。据估计,这一效应意味着高胎次(higher-order births)出生人口将增加约14.5%。然而,总体生育的增加并不明显[7]。
Rainald Borck(2014)以OECD国家为例,提出一个由文化态度①文化态度变量取自国际社会调查方案中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个人提出的不同问题(如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等)的回答,如“如果他或她的母亲工作,学龄前儿童可能会受到伤害”,“男人的工作是挣钱,女人的工作是照顾家庭”,等等。然后,将回归后的国家固定效应作为每一个国家的文化态度。所驱动的内生生育、女性劳动力供给和育儿选择的模型[25]。通俗来讲,当人们认为母亲去工作会使学龄前儿童受苦,或认为女性应该照顾家庭和家人时,就不会使用公共提供的托儿服务,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往往很低;当人们认为外部托儿会节省母亲时间时,就会选择公共育儿服务,进而增加了生育率和劳动力供应,并缩小了性别工资差距。该模型的政策含义:如果社会对公共育儿服务的态度保持不变,那么增加育儿服务可能不会影响生育或女性劳动力供应。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以某种方式影响社会态度或预期,这些政策就会提高生育率和女性劳动力参与度。
以德国为例,为了提高生育率,2007年1月1日,德国推出一项产假福利计划,即政府将大幅增加在孩子出生之前就业或在职父母的福利。根据这项计划,如果一名女性在新的一年分娩,那么一年休假福利最高可增加约2万欧元。调查发现,有接近任期结束的在职女性想尽办法将分娩时间推迟到了新的一年,以便从新福利制度中受益[9]。此外,福利计划带来变相的收入分配,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对经济激励的反应不同。例如,1996年的德国儿童福利计划改革总体上增加了儿童福利,但增加的确切数额因家庭收入和孩子数量而异。不同收入的夫妇对福利改革的反应不同,低收入夫妇的反应并不明显,而高收入夫妇决定生育二胎的比例更高[10]。而对于2007年的福利改革,大部分低收入的家庭中刚刚有资格享受新福利的已生育母亲最初减少随后的生育并延长生育间隔[11]。
从发展中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来看,福利制度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减少人口增长。以尼加拉瓜“红色保护社会”(RPS)①红色保护社会(RPS)是一个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项目,是尼加拉瓜全面反贫穷战略的一部分。该项目明确针对赤贫家庭,并受到严格的监测和评价。它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家庭在食品上的开支;增加7~13岁儿童的入学率和出勤率;增加9岁以下儿童的基本保健和营养;改善对女性的产前和产后护理。项目为例,现金转移的扶贫项目鼓励贫困家庭投资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该方案降低了分娩风险,导致生育间隔延长、生育率降低[12]。
印度于2005年启动安全孕产计划(JSY)以应对持续升高的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该计划对那些在保健或分娩设施方面处于不利处境的女性提供现金奖励。研究结果显示,在已经历高人口增长的州,三年期间内,安全孕产计划可能使分娩或怀孕的概率增加了2.5~3.5个百分点,出生人数的增加这一意外结果与贫穷国家的计划生育目标产生很大冲突[13]。
自然灾害或灾难性事件可以导致卫生、经济和人口数量方面的重大变化。2001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地震导致了出生率的显著上升,地震对人口的影响因地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存在相当大的差异[32]。在美国,低严重程度的飓风警报与生育显著正相关,而高严重程度的飓风警报具有显著的负生育效应。最严重的警报级别即飓风警报导致生育率严重下降。生育受影响的大多是以前至少有过一个孩子的夫妇,表明对第一个孩子的需求相对来说是无弹性的,但当夫妻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需求弹性会变大[33]。
(二)经济因素
2.儿童或女性福利制度
失业对生育产生的影响表现得比较复杂。实证研究发现,失业和生育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失业导致生育率降低;而理论研究则强调失业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较低,进而生育率提高。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矛盾。Héctor Pifarré i Arolas(2017)通过将失业区分为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为这一矛盾提供了解释。研究发现,结构性失业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但周期性失业的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年龄[15]。对某些年龄组来说,周期性失业增加也可导致生育率上升(25岁之前和35岁之后);对另一些年龄组的人来说,失业的暂时减少对生育既有积极影响(25~30岁)又有消极影响(30~35岁)。而Emilia Del Bono et al(2015)则认为,失业本身对生育没有影响,但是,经济不稳定导致的工作岗位变动对生育有消极影响[16]。他考察了奥地利白领女性失业和工作变换两种情况各自对生育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与自己未来事业发展相关的工作岗位上被取代会导致生育率下降。
2.女性劳动参与率
“可是您为什么要与她分手?”思蓉的声音,充满了“母性的光辉”,“您应该先找出分手的理由,然后再去想这个理由是否成立,是否值得。并且,您能确定您还会遇到比她更好的女人吗?”
有限元法需要如图1(a)所示的兼容网格,然而,网格加密和部件集成等许多技术原因会导致如图1(b)所示的不协调网格。
3.育儿成本
推迟生育是近三十年来一个重要的人口趋势。Pierre Pestieau和Gregory Ponthiere(2015)通过考察家庭早期和晚期儿童直接成本的变化为推迟生育提出合理解释[21]。具体来说,生育的最佳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和晚期儿童在物品与时间方面的成本结构。如果晚期儿童在其童年时期比早期儿童花费更多,而早期儿童一旦成年就不再花费的时候,那么,最佳生育状况只涉及早期儿童。但是,如果已成年的早期儿童在某种程度上对父母来说仍然是需要花费的,或者说虽然早期儿童消费得较早,但因存在较长共存期,可能导致额外的机会成本。若辅助生殖技术等医学进步已降低了晚期儿童的直接成本,那么,晚期儿童生育可能会被推迟。
一是打造“生活精致的田园新城”。吸收田园城市理论的有益成果,置身扬子江城市群、江淮生态经济区大格局中,统筹空间布局、土地布局、产业布局等,严格控制生态红线、城市边界线、耕地保护线,推动城市精明增长。以融入长三角经济带为导向,加速启扬高速姜堰东互通等节点建设,畅通328国道、红旗大道等泰姜融合通道,优化城乡道路“微循环”,构建通江达海的交通路网体系。巩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效,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完善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构建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有效消除行车堵、停车难等民生问题,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4.国际贸易
通常来说,生育和贸易是两个独立的研究主题,Oded Galor 和 Andrew Mountford(2008)通过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贸易结构对生育的影响将两者联系起来[2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产生不对称影响,进而导致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上升。具体来说,出口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国家生育率下降,而出口初级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生育率上升。制造业出口所导致的生育率下降主要发生在中等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结构现代化和制造业密集型出口部门不断增长。高技能的制造业激励父母投资儿童教育,减少生育,因为如果有办法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父母会更看重孩子质量而不是数量。总之,只有当出口来自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时,贸易一体化才可以有助于高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实现降低生育率水平的目标。如果初级或低技能密集型生产仍占主导地位,生育率水平只能通过其他手段来降低。
Ulla Lehmijoki和 Tapio Palokangas(2010)探讨了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影响[23]。一般来说,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收益通过收入效应(即收入提高,作为正常品的孩子需求增加)提高了生育率,产生储蓄和资本积累,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工资水平提高并通过替代效应(即收入提高,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孩子需求减少)降低生育率。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从长远来看,当储蓄和资本积累对贸易收益的变化不敏感时,贸易带来的收益就会表现为长期的人口增长,经济停滞不前,进而陷入高生育率低资本积累的贫困陷阱[24];当储蓄和资本积累对贸易收益的变化敏感时,人口增长就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路径。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供给最初随着女性生育率提高而下降,但随着成年子女及其父母都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开始上升。
“宝剑锋从磨砺出”。面对纷繁复杂的食品安全形势和变化多端的违法犯罪行为,哈斯巴彦尔不顾个人安危,勇挑重担,身先士卒,在全区各地,留下了拼搏的身影和跋涉的足迹。2014年以来,他克服执法人员少、队伍新、任务重等困难,带领同志们主动出击,查办多起在全区有影响的食品类大案要案,涉案货值金额2亿多元。执法过程中,他多次受到威胁,但从未退缩。
(三)文化因素
以英国为例,1999年英国针对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改革,按实际价值计算,政府对每个孩子的支出增加了50%。由于工作福利(Welfare-to-Work,WTW)的机会成本效应,福利改革的效果在已婚女性和单身女性之间存在潜在差异。单身女性的生育率没有增加,已婚女性受影响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已婚女性生育率因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较低而增加了约15%[8]。
在欧洲,文化传统对生育存在一定影响。Massimiliano Bratti和Konstantinos Tatsiramos(2012)认为,存在两种推迟生育的相反力量:生理学和社会文化因素产生延迟效应,职业相关因素导致追赶效应[26]。推迟生育的影响因国家而异,也因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依恋程度而异。具体来说,对于劳动参与率低的女性,由于生理和社会文化因素,推迟头胎生育可能会降低二胎生育的可能性;对于那些非常依赖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来说,因具有更多的劳动力市场经验和更高收入而产生职业追赶效应[26],推迟头胎生育反而有可能提高生二胎的可能性。当职业效应大到足以抵消对所有女性消极的生理和社会文化影响时,就会过渡到二胎生育。在此过程中,推迟生育所产生的这两种相反力量是并存的,其大小取决于国家制度特征。在提供较高水平托儿服务和兼职机会以及家庭和工作更容易协调的国家,如丹麦、法国和德国,积极的职业效应更大,总体上导致了人口的追赶效应;在南欧国家和爱尔兰,消极的生理和社会文化影响较大,因劳动力市场疲软和缺乏家庭友善型工作政策①家庭友善性政策主要指兼职机会、长期产假、公共儿童保健、工资水平等方面有利于生育的政策。,总体上导致推迟效应。
(四)其他外部因素
1.关注影响中国生育的关键因素和独特因素
非洲艾滋病流行对生育带来的影响非常复杂,具有多样性和异质性。Yoo-Mi Chin等人(2018)的研究表明,撒哈拉以南14个非洲国家的艾滋病增加了总和生育率(TFR)和幸存儿童的数量[27];Chinhui Juhn 等人(2013)的研究发现,尽管感染艾滋病毒女性的生育能力明显降低,但当地社区的艾滋病毒流行对未受感染女性的生育能力没有显著影响[28];Dick Durevall和Annika Lindskog(2011)通过考察马拉维所有女性的生育行为发现,艾滋病流行对不同年龄和先前不同生育数量的女性的影响程度不同[29]。艾滋病增加了年轻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可能性,同时减少了年长女性和已生育女性的生育可能性。Martin Karlsson和Stefan Pichler(2015)的研究表明,艾滋病流行对三个不同国家(南非、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出生率有不同影响[30]。南非、津巴布韦的预期寿命和死亡率受影响较大,而出生率受影响较小且不显著。而在莫桑比克,艾滋病毒对预期寿命和死亡率的影响似乎小得惊人,这并不是因为艾滋病在莫桑比克造成的死亡人数少于在其他两个国家,而是由于儿童死亡、呼吸道感染和受伤等原因导致的死亡率降低导致总死亡率减少。此外,基于马拉维农村地区的考察显示,艾滋病毒对儿童质量-数量产生影响。当母亲有较高的感染艾滋病毒风险时,则降低了儿童质量(用教育和健康来表示)和儿童数量[31]。
2.自然灾害或灾难性事件
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至少在过去40年里一直是劳动经济学和人口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大量研究表明,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反映了角色不相容假说,即母亲和职员(或者就业和生育)两种角色是相互影响的,女性就业率上升导致生育率下降。ParaskeviK.Salamaliki等人(2013)的研究发现为贝克尔和威利斯的新家庭经济学①即女性工资作为生育的机会成本决定生育,女性工资提高导致生育率降低。以及伊斯特林相对收入假说②即相对收入较低的育龄夫妇会鼓励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推迟结婚,进而减少生育。提供了经验支持[17-20]。
然而,赞比亚儿童资助计划即非洲政府针对处于高贫困和高生育率环境的有孩子家庭大规模无条件现金资助计划并没有提高生育率。这些发现应该会减轻那些想要投资儿童发展的决策者的担忧[14]。
在长春市各大院校(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吉林体育学院,吉林艺术学院,吉林农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随机抽取一部分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3.居住条件和购房成本
Cecilia Enström Ös(t2012)探索了瑞典自置居所与首次生育或家庭形成的关系[34]。研究发现,住房与生育这两个人生事件之间存在潜在的同时性。对那些当时在住房市场上面临诸多问题的年轻人来说,成为房主与成为父母具有显著相关性;而对进入住房市场时经历住房过剩和优厚住房补贴制度的人而言,住房与生育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性。此外,潜在购房成本对生育决策影响更大,获得住房的困难可能导致推迟生育,这意味着住房政策可能是未来人口增长的关键。
二、影响生育的家庭内部因素
(一)家庭谈判或家庭契约
Matthias Fahn等人(2016)基于契约理论得出,离婚费用和离婚后赡养费支付影响夫妻生育决策[35]。较高的分居费用和较高的赡养费有助于夫妻合作,从而提高生育率。德国近期的一项改革减少了离婚后赡养费支付的权利,降低了婚内生育率。
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 Ship Inverter Control Strategy Based on Virtual Synchronous Generator
Mizuki Komura(2013)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模型[36]。谈判能力不仅取决于家庭成员时间的相对价格,还取决于社会对性别角色的相关压力。谈判能力与生育的关系有两种经济模式,即女性无赋权与高生育率和女性赋权与低生育率。基于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UNDP 2007)的横断面数据,研究发现,低GEM① GEM,即性别赋权指标(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是一项旨在衡量性别平等的指标。GEM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试图衡量全球各国性别不平等的程度,其依据是对女性相对经济收入的估计、女性在拥有经济权力的高薪职位上的参与及获得专业和议会职位的机会。它是与性别有关的发展指数(GDI)同时提出的,但衡量的是该指数没有包括的诸如赋权等主题。(即女性地位低)的国家显示高总和生育率(TFR),而高GEM(女性地位高)国家则相反。
Akira Yakita(2018)研究了家庭纳什议价模式下的生育、教育决策和育儿政策效果[37]。对儿童福利偏好的不同及父母对抚养子女时间投入的不同要求,影响着夫妻讨价还价的结果。如果女性在家抚养孩子,那么扩大公共育儿服务覆盖面的政策就会以母亲为目标,增加其劳动力供应,从而增加工资收入。当母亲的教育水平非常低时,扩大正规儿童保健覆盖面的政策将提高生育率,并长期减少对儿童教育的投资;如果母亲的教育水平很高,那么政策会降低生育率,并长期增加对儿童教育的投资;值得注意的是中间情况,即当母亲的教育水平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时,该政策会提高生育率和对女孩的教育投资,同时可能会减少对男孩的教育投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收入和生育率的变化才能正相关。孩子数量-质量的替代可能并不成立。随着公共托儿服务的扩大,生育率会上升,女孩的教育水平也会提高。
2.1.1 暴力行为 患者常患有被害妄想、夸大妄想、幻视、幻听、兴奋、行为冲动等精神异常症状。部分表现为抑郁,此类患者常在幻觉、妄想等精神障碍的支配下发生突然的冲动行为,导致意外的发生。
Marc Frenette(211)考察了生育与有酬和无酬劳动的性别分工,即夫妻间有偿和无偿劳动的分配关系[38]。生育更多孩子会导致带薪工作时间的减少,甚至会使母亲的无薪工作时间增多。多生育还导致在职母亲及全职带薪就业母亲的比例下降。相比之下,生育更多孩子与父亲的带薪工作时间无关,尽管有证据表明,父亲育儿方面的无薪工作时间略有增加。
(二)女性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水平与生育之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对美国的考察显示出两个相反的结果。Qingyan Shang和Bruce A.Weinberg(2013)发现,受过高等教育(即大学毕业)的女性生育率经过多年下降之后可能正在上升,其主要原因如下:大学毕业的女性可能不再以职业为导向;个人私人服务供给的增加降低了女性生育成本,使女性把养育负担转移到市场;男性可能在照顾孩子方面承担了更多责任;一直迅速缩小的性别工资差距,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相对于男人的时间不再增加[39]。而Vikesh Amin和Jere R.Behrman(2014)基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双胞胎数据却发现学校教育和生育之间存在很强的反向因果联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生育的孩子就越少且越推迟生育,或者可能没有孩子[40]。
孟加拉国的考察结果显示,受过教育的女性生育率较低。Youjin Hahn等人(2018)基于孟加拉国女性中学助学金计划(该计划为农村女孩提供免费中学教育)的研究表明,受过教育的女性生育率较低,并且更多地使用产妇保健,她们的子女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有更好的健康状况[41]。
Luca Zanin 等人(2015)对马拉维15~49岁的女性生育进行研究的结果也显示:教育是生育率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42]。但是,女性的教育对子女数量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因女性出生队列①将同一时期出生的人列为一队。和居住地区(农村或城市)而异。在农村地区30岁以上的女性中,存在一种强倒U型生育-教育关系,其转折点是8年左右的受教育年限;对于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女性,生育-教育关系呈现出随出生队列而变化的非线性反向关系。这些发现凸显了马拉维生育-教育关系的复杂性。对倒U型关系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受教育年限越短,因缺乏有意识的节欲避孕,生育能力越有可能提高;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因具有较多知识和技能而更容易找到工作,也更有可能使用现代避孕方法,因此,生育率下降。基于这些发现,决策者应将其行动战略调整为有助于更多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获得更多受教育机会、提高教育质量及促进节育。
(三)性别偏好
在印度,许多父母遵循重男轻女的停止生育规则。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存在,当生育孩子的性别构成正好符合意愿时才停止生育。Daniel Rosenblum(2013)考察了这种生育决策对印度女性死亡率过高的影响[43]。停止生育规则既影响孩子数量又影响孩子的性别组成。头胎是男孩儿的父母比头胎是女孩子的父母更早停止生育。平均而言,与头胎生女儿的父母相比,头胎生儿子的父母会少生孩子,生儿子的比例也更高。终止生育规则会加剧歧视,导致多达四分之一的女婴死亡。
(四)育儿成本的转移
Matthias Wrede(2011)基于德国在线调查数据,使用一个简单的三周期模型,研究了(准)双曲贴现② 双曲贴现(hyperbolic discounting)又称非理性折现,是指人们在对未来的收益评估其价值时,倾向于对较近的时期采用更低的折现率,对较远的时期采用更高的折现率。双曲贴现者对现在和未来的同一件事的判断是不一致的。双曲贴现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对生育时间和生育数量的影响[44]。他使用储蓄模式不一致性作为时间不一致性的指标,研究结果证实:没有机会将育儿成本转移到未来,即如果没有借款能力,双曲贴现者将会少生孩子;如果育儿成本可以完全转移到后期,双曲贴现对生育的影响取决于为人母的根本动机,即儿童被视为消费品还是投资品。存在一个完美的资本市场时,如果儿童的机会成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下降,并且母亲的投资动机占主导地位,双曲线贴现就会减少生育人数。否则,贴现率下降可能导致生育数量增加。
(五)家庭规模
Emla Fitzsimons和 Bansi Malde(2014)对生育的数量-质量模型进行了实证验证[45]。他们通过考察墨西哥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家庭规模对女童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家庭规模对教育有不利影响,或者说家庭规模对女童受教育的影响非常有限。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母亲的劳动力供应,即母亲在大家庭中从事的工作比在小家庭中更多。规模相对较大的家庭通过增加母亲的劳动力供应来补偿人均儿童资源的减少。
(六)生育方式
Karen Norberg 和 Juan Pantano(2016)考察了分娩方式(如剖宫产)与生育的关系问题[46]。基于若干国家和跨国人口数据的研究发现,接受剖宫产的女性会减少生育。在剖宫产与生育负相关关系的形成中,产妇选择起着重要作用。女性在剖宫产后更有可能采取积极的避孕措施。因此,有意避免剖宫产后再次怀孕似乎是导致剖宫产与随后生育能力负相关的部分原因。
(七)自愿或非自愿无子女家庭
在发达国家,无子女群体在女性群体中占高达30%左右的比例。无子女分为两种模式:非自愿无子女和自愿无子女。发展中国家的无子女主要是因营养不足和疾病引起的非自愿无子女,而发达国家的无子女多是自愿的。Paula E.Gobbi(2013)认为,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增加了女性就业机会,性别工资差距缩小,成为父母的机会成本增加,无子女群体增多,导致生育率下降[47]。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一)对生育研究的启示
从国外最新研究来看,生育的影响因素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生育问题虽然属于微观家庭决策,受生育成本、教育水平、家庭谈判或家庭契约及生育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同时也与家庭外部因素,如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法律和制度等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对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不同人的生育的影响结果是不同的。全方位、多维度地考察生育的影响因素,对中国研究者来说也是有必要的。
(二)对生育政策的启示
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政策的传导机制。生育政策的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同一种政策对不同国家(如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同一国家不同的家庭或个人(如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可以概括为国家差异、时期差异和群体差异。这一结论对中国的生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见到下级的脸——是包公脸。面部僵硬,眼睛向上,嘴角歪曲。他挺胸叠肚,双手交握抄在背后,两只眼微眯着,嘴角下拉,满脸傲气,仿佛不可一世。脸一变,嘴就变,嘴一变,吐出的文字自然生硬,冰冷。你哪儿痛,它就拣哪儿挑。你没问题,他也要鸡蛋挑骨头。如果你在某个场合向他打招呼,他听而不闻;你走到他跟前,他视而不见;你上前与他握手,他傲然屹立于原地,很不情愿地伸出两根手指与你草草一拉;你点头鞠躬致意,他昂然挺胸还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取得巨大发展,但是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经济差异依然明显。就生育现状来看,二孩政策之后,生育政策调整效果同样呈现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比如,东中部与西部地区的生育水平差异在逐渐缩小,但东北地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长期处于很低水平,生育意愿偏低[48]40。对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实施情况的认识不仅关系到生育政策调整的进程,同时也关系到中国人口的长期战略,更关系到家庭生育计划[49]。二孩政策所导致的总量或结构的矛盾与偏差应该成为未来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需注意的问题。
(三)相关对策建议
1.艾滋病流行
著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说:“单纯的劳动,不算做,算蛮干,单纯的想,只是空想,只有将操作与思维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思维的目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思维特点,让全体学生动眼看、动手做,理解和掌握抽象的物理规律和概念,不断发展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关于生育的影响因素,从未来研究方向来看,除了文中所提及的外部因素如制度政策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及家庭内部因素如育儿成本、家庭收入、教育程度等因素,研究者还要关注影响中国生育的关键因素和独特因素,如人口流动、住房制度、农药残留、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要多因素综合考察,根据生育的关键影响因素制定相关针对性政策。
(1)关注流动人口的生育负担问题
美学的培养就要培养学生对于美的觉察、辨别和感知能力,让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审美的能力对于人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自远古时代,人类就用各种兽皮、各种香草、各种颜料作为自己的装饰物,这就是人类天生的对于美的感知。到我们现代社会,审美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感恩生活、感恩父母、感恩社会。
调查显示,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远低于预期,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很可能是主要原因[50]。针对此类状况,可以考虑一些专门降低流动人口生育负担的政策建议,例如:促进流动人口家庭三代同堂居住或者给予老人育儿补助;均等配置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为无老人照看的家庭提供入托入学的便利。
(2)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住房制度
冠状动脉造影采用Judkin氏法,所有患者的造影时间在心肌梗塞发生时间的30天到1.6年。由有经验的医生阅读分析冠状动脉造影,管腔狭窄≥50%即为有意义病变,将狭窄100%定为完全堵塞,狭窄75%~99%定为重度狭窄,狭窄50%~74%定为中度狭窄。根据病变部位分为单支、双支和三支病变。
一辆2014款上汽通用别克君威,搭载排量为2.4L的LE5发动机,行驶里程为145 800km,据车主反映:该车发动机能正常启动,但怠速运行一段时间后,发动机会发出“哗啦、哗啦”异响,同时发动机抖动严重,踩下加速踏板,发动机转速不上升,发动机故障灯点亮。该车进4S店检修,被维修人员告知应更换正时链条,因为正时链条可能出现拉长的问题,考虑到更换正时链条需要8 000多元,所以车主将车送到我店维修。
据调查,房价快速上涨是居民二孩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原因。房价每上涨1%,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降低 3.6%,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生育意愿受房价上涨的影响更大[51]。因此,政府需进一步通过土地政策以及金融政策的改革和完善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或租房的需求,从而减轻或缓解房价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
(3)改善环境,提升食品安全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指出: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破坏男女生育能力的祸首。比如,广州地区肠癌、卵巢癌、宫颈癌的发病率快速增长与农药、各种类型的添加剂、防腐剂以及催生剂的过量使用有着很大关系。由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男性的精子浓度大幅下降[52]。因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为消费者的健康提供保障。
2.基于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3 发至《草原与草坪》编辑部邮箱的稿件视为正式投稿, 不接受其他形式的投稿,本刊编辑部是通过邮件形式通知作者交纳稿件审稿费和版面费。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东西部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及原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规定及实施情况、居民生育观念、不同收入阶层妇女的工作生活状态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也必然表现出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群体差异。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应考虑以上差异,既要关注时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又要关注队列生育水平的变化[1]55。同时,加强生育水平、生育意愿及政策实施效果的跟踪监测,建立人口监测预警机制,为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与完善提供数据支撑[48]44。
参考文献:
[1]石人炳,陈宁,郑淇予.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效果评估[J].社会科学文摘,2018(10).
[2]WANG F,et al.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and their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7,30(1).
[3]MIYAZAKI K.Pay-as-you-go social security and endogenous fertility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3,26(3).
[4]FENGE R,SCHEUBEL B.Pensions and fertility:back to the roots-Bismarck’s Pension Scheme and the fir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7,30(1).
[5]HIRAZAWA M,et al.Aging,fertility,social security and political equilibrium[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0,23(2).
[6]FANTI L,GORI L.Fertility and PAYG pensions in the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2,25(3).
[7]MÖRK E,et al.Childcare costs and the demand for children-evidence from a nationwide reform[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3,26(1).
[8]BREWER M,et al.Does welfare reform affect fertility?Evidence from the UK[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2,25(1).
[9]NEUART M,OHLSSON H.Economic incentives and the timing of births:evidence from the German parental benefit reform of 2007[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3,26(1).
[10]RIPHAHN R,WIYNCK F.Fertility effects of child benefits[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7,30(4).
[11]CYGAN-REHM K.Parental leave benefit and differential fertility responses:evidence from a German reform[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6(29).
[12]TODD E,et al.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 on fertility:the case of the Red de Protección Social in Nicaragua[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2,25(1).
[13]NANDI A,LAXMINARAYAN R.The unintended effects of cash transfers on fertility:evidence from the Safe Motherhood Scheme in India[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6,29(2).
[14]PALERMO T,et al.Unconditional government social cash transfer in Africa does not increase fertility[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6,29(4).
[15]AROLAS H.A cohort perspective of the effect of unemployment on fertility[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7,30(4).
[16]BONO E,et al.Fertility and economic instability:the role of unemployment and job displacement[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5,28(2).
[17]SALAMALIKI P,et al.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ale labor supply and fertility in the USA:updated evidence via a time series multihorizon approach[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3,26(1).
[18]BECKER G.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
[19]BECKER G.A Treatise on the Family[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20]WILLIS R.A new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behavior[J].Journal Political Economics,1973(81).
[21]PESTIEAU P,PONTHIERE G.Optimal life-cycle fertility in a Barro-Becker economy[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5,28(1).
[22]GALOR O,MOUNTFORD A.Trading Population for Productivity:Theory and Evidence[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8,75(4).
[23]LEHMIJOKI U,PALOKANGAS T.Trade,population growth,and the environ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0,23(4).
[24]GALOR O,MOUNTFORD A.Trad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The Family Connec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
[25]BORCK R.Adieu Rabenmutter-culture,fertility,female labour supply,the gender wage gap and childcare[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4,27(3).
[26]BRATTI M,TATSIRAMOS K.The effect of delaying motherhood on the second childbirth in Europe[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2,25(1).
[27]CHIN Y M,WILSON N.Disease risk and fertility:evidence from the HIV/AIDS pandemic[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8,31(2).
[28]JUHN C,et al.HIV and fertility in Africa:first evidence from population-based surveys[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3,26(3).
[29]DUREVALL D,LINDSKOG A.Uncovering the impact of the HIV epidemic on ferti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the case of Malawi[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1,24(2).
[30]KARLSSON M,PICHLER S.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HIV[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5,28(4).
[31]CASTRO R,et al.Perception of HIV risk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the case of rural Malawi[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5,28(1).
[32]NANDI A,et al.The effect of natural disaster on fertility,birth spacing,and child sex ratio:evidence from a major earthquake in India[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8,31(1).
[33]EVANS R W,et al.The fertility effect of catastrophe:U.S.hurricane births[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0,23(1).
[34]ÖST C E.Housing and children:simultaneous decisions?a cohort study of young adults’housing and family formation decision[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2,25(1).
[35]FAHN M,et al.Relational contracts for household formation,fertility choice and separation[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6,29(2).
[36]KOMURA M.Fertility and endogenous gender bargaining power[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3,26(3).
[37]YAKITA A.Fertility and education decisions and child-care policy effects in a Nash-bargaining family model[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8,31(4).
[38]FRENETTE M.How does the stork delegate work?Childbearing and the gender division of paid and unpaid labour[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1,24(3).
[39]SHANG Q Y,WEINBERG B A.Opting for families:recent trends in the fertility of highly educated women[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3,26(1).
[40]AMIN V,BEHRMAN J R.Do more-schooled women have fewer children and delay childbearing?Evidence from a sample of US twins[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4,27(1).
[41]HAHN Y,et al.The effect of female education on marital matches and child health in Bangladesh[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8,31(3).
[42]ZANIN L,et al.Modelling the impact of women’s education on fertility in Malawi.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J].2015,28(1).
[43]ROSENBLUM D.The effect of fertility decisions on excess female mortality in India[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3,26(1).
[44]WREDE M.Hyperbolic discounting and fertility[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1,24(3).
[45]FITZSIMONS E,MALDE B.Empirically probing the quantity-quality model[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4,27(1).
[46]NORBERG K N,PANTANO P.Cesarean sections and subsequent fertility[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6,29(1).
[47]GOBBI P E.A model of voluntary childlessness[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3,26(3).
[48]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等.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J].人口研究,2018(11).
[49]王广州.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J].中国人口科学,2015(2).
[50]黄秀女,徐鹏.社会保障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来自基本医疗保险的经验证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4).
[51]刘中华.房价上涨对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物价,2019(3).
[52]钟南山:食品安全问题已成破坏男女生育能力的祸首[N].南方日报,2004-03-26.
Factors Affecting Fertility:the Latest Foreign Researc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Wang Yanping Gan Mengfang
Abstract:Internationally,the total fertility rate(TFR)is declining in all high-income,middleincom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To address this situation,foreign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the fertility factors that matter include not only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 and social factors,but also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fertility cost,education level,family negotiation or contract,fertility mode and gender preference.And the policy effects related to fertility are also uncertain and differentiated.The latest foreign research has two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fertility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one is to focus on the critical and unique factors that impact China's fertility;the other is to consider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group differences when adjusting and perfecting fertility policy.
Key words:Fertility;External Factor;Internal Factor;Overseas Study
[中图分类号]C913.9;F0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616(2019)05-0074-13
[收稿日期]2019-07-22
[作者简介]王艳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郑州,450046);干梦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郑州,450046)。
[责任编辑:丁浩芮]
标签:生育率论文; 女性论文; 家庭论文; 政策论文; 因素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创新》2019年第5期论文;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