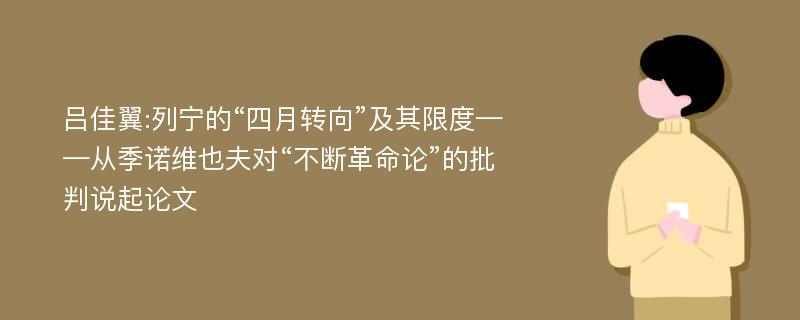
摘要:围绕列宁的“四月转向”及其限度问题,讨论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批判。文章从是否存在列宁的“四月转向”(俄国革命是二阶段抑或一阶段)、“四月转向”中的农民问题、列宁“四月转向”的限度(托洛茨基在列宁身后对“不断革命论”的完成)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从而澄清了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理论变化及其与“不断革命论”的关系。
关键词: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四月转向
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虽名为对列宁主义的研究和阐释,实则用大半篇幅批判托洛茨基,特别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以服务于当时“三驾马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虽然后来季诺维也夫也被斯大林打倒,他对列宁主义的阐释随之也无以立足,但他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歪曲性批判却奠定了后世误解和曲解这一问题的理论张本。然而对“不断革命论”的误解和歪曲,也是对列宁与托洛茨基关系的误解和歪曲,从而也导致对列宁主义的误解和歪曲,因此澄清对这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全面讨论季诺维也夫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论述,而主要围绕一个问题展开论述:在俄国二月革命之后是否发生过列宁的“四月转向”,如何理解列宁的这一“转向”及其限度。
一、是否存在列宁的“四月转向”——俄国革命是二阶段抑或一阶段
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立即摒弃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并对农民作出不同评价。季诺维也夫当然不是不清楚列宁的这些相关论述,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在理论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因而并不认为有什么“四月转向”。季诺维也夫认为,二月革命后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了工农民主专政[1]85,因而进入了所谓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1]46,因而之前的口号自然过时了,自然需要提出新的任务。而整个转变过程是列宁早就有的理论设想,因而谈不上什么新的理论“转向”。笔者认为,季诺维也夫倒是真诚地这么认为,而不是为了批判托洛茨基而使用的什么障眼法,也就是说这里所体现的季、托之间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理论分歧,而非派系之争。因为在1926年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组成联合反对派时,季诺维也夫所守住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求托洛茨基放弃“不断革命论”,转到老布尔什维克所共同持守的“工农民主专政——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二阶段论上来。托洛茨基也的确让了这一步。
的确,列宁在二月革命前早就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设想,但这绝不意味着事实上的转变情况与列宁原先的设想相同,不意味着列宁(实际上是俄国历史)完全遵循了原先的设想,因而不需要对原先的理论设想作出任何的修正。那么,实际上,二月革命后是否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实现了工农民主专政呢?答案是否定的。
老大妈推着婴儿车走了,突然,苏母问他:婷婷是不是也快生了?苏穆武不解地:生什么?苏母说:外孙呀!结婚前她不是说怀孕了吗?苏穆武恍然地:我把这档子事差点忘了。苏母沉吟地:奇怪,怎么一点看不出来呢?
我们先来说二月革命后是否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对此有论者正确地指出:“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却出现两重政权的局面,一方面成立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工人、士兵却自动地组成了工兵苏维埃。这个为列宁称作巴黎公社式的半政权的工兵苏维埃从一开始便为孟什维克等的妥协政党所把持,按照‘革命阶段论’的观点,孟什维克把苏维埃自愿地作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属物,甘愿充当资产阶级政权的奴仆。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却无力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它不能给人民以和平,却继续奉行沙皇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把人民继续推向战争的深渊。它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却继续维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它更不愿人民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却暗地同反动的贵族、军官、士官相勾结,串通一气要向起义的人民进行反攻。这一切都说明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的统治,而革命的民主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还在向纵深发展,工人、士兵、农民群众还在为争取和平、面包、土地而继续进行斗争,客观的形势表明只有无产阶级夺取全部政权,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注]《歧途与正道——斯大林与托洛茨基》,(2004-03-17),http://www.xici.net/d18111433.htm。托洛茨基也指出: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头八个月到十个月中”[2]才完成的。季诺维也夫在引用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的话时也指证了这一点,并对此加了着重号:“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动摇的终结,意味着君主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完全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没有破坏)。”[1]59列宁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是一篇不长的文章,季诺维也夫在论述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时引述了其中的一些话[1]49,但恰恰漏掉了颇能说明问题的一句点睛之笔:“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3]172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二月革命后远没有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而且是指民主革命中的主要任务,因此绝不是“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1]35问题。
那么,如何理解列宁在农民问题上的矛盾呢?如果细读上下文,把其中断裂的意思打通,就会发现列宁刚好表达了相反的意思,即在民主革命还没完成或者说还在进行的过程中,农民就已发生了分化。何以这么说呢?在该文前后相衔接的几页中,列宁指出:1917年4月后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4]657;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后,农民就分化了,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民主革命任务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若干时间内才完成的[4]659。根据这三层意思,运用形式逻辑的规律,就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1917年4月后,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开始发生某种重合;二是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十月革命前)也即民主革命进行过程中,农民就已分化。那么,如果进一步追问一句,在这里为何出现列宁在表面上表达的意思,与实际上隐含的意思有出入呢?列宁倒不是要故意这么搞,故意把真实的意思隐藏起来。笔者以为,这与列宁对考茨基争辩、批判的特定语境有关。考茨基是反对十月革命的,他认为俄国革命应当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与农民的冲突。列宁为了理清“这个被考茨基搅乱了的问题”[4]657,就用几句比较简明的话解释说:我们先是与全体农民一同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没有跳跃阶段,只是当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后,才发生了农民的分化以及无产阶级与分化农民的冲突。这么说确实显得条理比较清楚,有利于反拨考茨基的“混乱”。相反地,假如列宁果真按二月革命后实际进程中的“不断革命论”逻辑与考茨基争论,对于考茨基本就混乱的逻辑只会平添混乱。
伴随着对工农民主专政的观点的变化,列宁对农民的观点当然也有所变化,因为这两个问题本是关联在一起的。关于农民的分化问题、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等,列宁达成了与托洛茨基相同的认识,如列宁1919年《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4]827(列宁在同一段中又重复了这同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不可能有什么农民与工人相并列的专政的,列宁这句话也足以推翻工农民主专政的可能性了。至于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关于农民的分化,以及无产阶级应当团结贫雇农、中立中农、坚决反对富农的论述比比皆是,季诺维也夫也引证了不少,我们就对此无需多说了。季诺维也夫本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这些观点和政策不仅非常同意和支持,而且据此反对当时掌握实际政策的斯大林-布哈林联盟在新经济政策中对农民的分化、富农的崛起,并由此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产生的威胁估计不足。当然在《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一书中对斯大林派的批判还比较隐晦,但后来就发展到公开决裂,并与托洛茨基组成联合反对派。但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的关键分歧就在于,他认为这些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才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讲农民分化、革命的国际性等才是正确的,而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应当讲与农民联盟以及民族革命。季诺维也夫的“死脑筋”就是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划为这样两个不可通约的阶段。而托洛茨基则认为从民主革命一开始就存在这个问题,尽管它的呈现也是逐渐发展的。因为托洛茨基压根没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为两个明确的阶段。它们即便能算两个阶段,也不是明确的,而是连通的。
通过对研究区以及各县NDVI与RUE均值进行统计,并求得各自趋势,分析2000—2014年15年来研究区与各县植被的变化情况,并对趋势线进行对比,总体上判断人为干扰对牧区植被变化的影响。另外,在空间上对NDVI与RUE趋势图进行叠加,基于像元来讨论研究区人为干扰对植被变化的影响,将人为干扰对植被变化的影响分为七类。
从托洛茨基这方面来说,经过俄国革命后,他也没有就彻底否定掉列宁早期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彻底地否定掉是中国国民革命以后的事,这一点后面会论到)。在此之前,托洛茨基则在某种程度上宁可把它看成含有未知变量X(X即农民的革命作用)的代数式,这个未知变量X保持着随具体情况而变动的未定性,如他在某处所说:“这个假说(即关于农民的独立性,是否可能存在一个独立的农民党、农民专政,进而工农民主专政——笔者注)被证实了吗?不,没有。可是,在历史能够提供完整、确凿的证据之前,这个假说却使列宁对革命政府问题作出了代数式的回答。”[7]46也就是说,托洛茨基的“得到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后来为历史所实现的定论固然可以说比列宁的未加确定的代数式正确,但也不能说后者完全错误。但在中国的国民革命以后,托洛茨基几乎对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达到深恶痛绝的程度。
这里想就势对托洛茨基在中国国民革命上的相关理论多说几句,因为它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与季诺维也夫的理论也有一定关系。前面已经提到,托洛茨基在1926-1927年与季诺维也夫组成联合反对派时,托洛茨基作为让步,应季诺维也夫的要求放弃了“不断革命论”,转到老布尔什维克所认定的列宁的革命二阶段论上来。而正是在这一阶段托洛茨基集中关注和论述了中国国民革命问题,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不能不受到季诺维也夫的掣肘。
二、“四月转向”中的农民问题
我们再来说二月革命后是否实现了工农民主专政。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回答,因为事实并不纯粹,列宁的论述也带有某种矛盾性(是辩证矛盾的“矛盾”,而非自相矛盾的“矛盾”)。我们还是回到1917年4月的《论策略书》这部伟大作品中,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但对此加注道“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并接着说:“这个‘公式’(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结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使它变了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得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变异。……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3]26-27关键问题在于,工农民主专政是实现了,然后又过时了?还是本身就很难说实现,或基本上未实现,就已经过时了?季诺维也夫明确地认为,工农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它的不足之处只是“实行自我‘限制’,自己使自己一时成为大资产阶级的附属品”[1]85-86。我们看列宁的表述,在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这一点有很多保留,指出“它变了样”,只是“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工农民主专政并没有真正实现,就已经过时了。其实作为一种专政,本应有一定的稳定性,一种极不稳定的或还没真正实现就已经过时的专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工农民主专政不仅是过时的问题,而且并不真正存在。其实这里已经相当接近托洛茨基了,因为托洛茨基是早就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不可能性,以及须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季诺维也夫在《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的第二章中,对托洛茨基批评布尔什维克“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带有“自我限制”的性质,进行大肆批判;但到了该书第六章中,即在我们上面的引文中,季诺维也夫也开始指出工农民主专政“自我限制”的缺陷了。由此可见:其一,季诺维也夫对工农民主专政是否存在“自我限制”的问题存在自相矛盾;其二,托洛茨基对工农民主专政“自我限制”的批评其实是正确的。“自我限制”在俄国革命中的最大表现其实就是季诺维也夫等老布尔什维克固守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阻挠革命的发展,幸被列宁及时批判和扭转。
那么,列宁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即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是否已经开始分化;还是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尚与农民整体携手而行?前面已经指出,前期列宁是持后者的观点。但在经过了1917年的“四月转向”之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远未完成,列宁已经关注到农民的分化,比如他指出“贫雇农和农民业主之间发生着更深刻的分裂”[4]28,要求“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4]14,并且要求“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离”,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4]14,等等。由此可见:在民主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农民的分化是实,这种分化不是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才出现的;列宁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并对他之前的农民论作出相应的修正。这样就与上面所说的托洛茨基的观点相当接近了。
我们上面论述了列宁前期与托洛茨基的分歧,以及列宁的“四月转向”。我们说,二月革命后的实际历程和列宁的“四月转向”比较接近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证明了这一点:首先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才能完成民主革命。因此,这很大程度上是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后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阶段论,而非列宁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阶段论。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郑异凡研究员这样评论列宁的前后转变与列、托之间的分歧:“从提出‘四月提纲’起列宁的实际主张已经与托洛茨基的历来主张完全一致了。托洛茨基后来说,他是经过战斗走向列宁的。这是他的谦虚之词,实际情况至少应当说是两人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多伊彻就此写道:‘他们两人都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其中一个得出这些结论早得多,而另一个却为这些结论作了长时间的艰苦的辩论。……他们的思想从不同的出发点,通过不同的过程向前发展走向他们此刻的汇合点。’”[5]郑异凡研究员的结论是比较客观的,一般而言也是托派的固有观点。否则,就很难理解列宁在1917年后对托洛茨基的多次赞扬,如同年11月1日在彼得格勒党委会的激烈辩论中,列宁赞叹说:“再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6](一说“自从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决裂以来,再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出色的布尔什维克了”[注]列夫·达维多维奇·布朗斯坦,http://www.renwen.com/wiki/。。由此也佐证了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早期分歧更主要在于派系之争)否则,也很难理解越飞遗书中所载的列宁对“不断革命论”的赞同之语。当然,列宁的这些话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是被隐藏起来的,为了权力斗争,列宁的话被删改或任意加以“注释”和解释的情况不知几何。本来托洛茨基根本没有必要“死抠”列宁对他的这些赞扬之语,但在对手挖空心思以列宁名义曲解理论和历史的时候,这么做就很有必要了。
1.2 研究方法 患者因可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收治入院,给予常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替格瑞洛、硝酸酯类、他汀类药物治疗,按既往病史、门诊处方或自行服药情况将患者分为瑞舒伐他汀组(n=171,患者每晚睡前服用瑞舒伐他汀10 mg)和阿托伐他汀组(n=174,患者每晚睡前服用阿托伐他汀 20 mg),再将这两组患者分别分为<70 岁和≥70 岁两个亚组。所有患者在接受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时应用碘普罗胺或碘克沙醇,后根据造影结果选择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即不予处置、球囊扩张和(或)支架置入术,术后用药依据检查结果而定,且服用方法与术前一致。
今年,青海油田计划生产66亿立方米天然气,比上年预计增产1.99亿立方米。东坪、尖北气田属于基岩气藏,埋藏深、钻井周期长、产建速度慢、开发难度大。为了弥补今冬明春天然气资源保供区的缺口,青海油田追加了采气三厂产气量,产能建设计划由1.85亿立方米增加至2.35亿立方米,并一改以往产能建设冬休的机制,采取不停工连续生产模式,推进天然气产能建设提速提效,厚实天然气资源根基。
当然,列宁在此以后也不是没有说过与此有所出入的话,如为季诺维也夫所征引的、列宁在写于1918年10-11月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所说的话:“资产阶级革命由我们进行到底了。农民整个说来是跟着我们走的。他们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对抗,一时还不会显现出来。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显露出来。”[4]659;“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4]657按这两段话,列宁似乎完全回到了农民问题上的老观点,即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农民毫无分化,农民是完全稳定的,等等。这与上面所引的1917年4月所写的那些文件中的话有明显的出入。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篇文章中,列宁也绝没有认为二月革命以后就完成了民主革命,相反,正是在这里,列宁指出民主革命任务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完成的[4]659。
三、列宁“四月转向”的限度——托洛茨基在列宁身后对“不断革命论”的完成
但是,是不是说俄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实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证伪了列宁的二阶段论,因而列宁完全转向托洛茨基的观点了呢?托派一般倾向于如此认为,但实际倒也未必。如日本学者对马忠行所认为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各对了一半,因为虽然二月革命后实现的工农民主专政发生了重大的变形,并随着新的革命任务的提出立即成为过时的,但毕竟短暂地存在过这个阶段[7]52。但在这一半对一半中,天平更倾向于托洛茨基一方。此外,如对马忠行所指出,列宁后来也并未在公开文本中明确否定工农民主专政,尽管列宁后来已不太使用这个提法,但毕竟还偶尔用之。这也似乎表明列宁并未完全放弃他原先的这个理论,尽管肯定已对之作出了重要修正。但对马忠行又指出,列宁后期所使用的“工农民主专政”一词的实际意思已倾向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专政,从而与他早期所使用的该词意思不同了[7]65,等等。总之,列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论是一个难以确定也不必要精确界定的问题。然而不管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结论性地指出:在二月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在革命理论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到二月革命后,这种分歧转变为差异。像大多数托派那样,把“转向”后的列宁与托洛茨基完全同质化,认为他们在革命理论上已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任何差异,是有失偏颇的。但像季诺维也夫等人那样把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早期分歧固化,并说成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分歧,则更是离谱。
既然如此,二月革命后工农民主专政并未实现就过时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未完成就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了,这就说明列宁对原来的理论设想是有所修正的,甚至是比较重要的修正,以至于老布尔什维克们作为列宁长期的“好学生”都没及时转过弯来。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而为季诺维也夫所绝对否认的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十月革命前的“重新武装”。这个事实大概还是不能否认的,尽管这个措辞显得夸张了点。
从图1可以看出,料液碱度对铷、钾的萃取率有显著的影响,随着料液碱度的提高,铷、钾的萃取率先快速上升,后逐渐趋于平缓。铷的萃取率随着料液碱度的提高而迅速上升; 当料液碱度C(OH-)>0.4 mol/L后,铷的萃取率逐渐趋于稳定。钾的萃取率随着料液碱度的增加而迅速提高; 当料液碱度C(OH-)>0.6 mol/L后,钾的萃取率逐渐趋于平缓。铷钾分离系数随着料液碱度的提高而迅速上升,当料液碱度C(OH-)>0.4 mol/L后,铷钾分离系数逐渐趋于平缓。因此,从铷钾的分离效果并结合提高料液碱度所需的成本,选择料液碱度为0.4 mol/L。
从托洛茨基的论文发表时间上看,在与季诺维也夫的联合反对派时期(1926-1927年),也即被流放之前,他对中国革命基本持二阶段论,认为当前阶段的中国革命是民主、工农性质的,应当建立的是工农民主专政,“进一步的发展前景就是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它完全彻底地取决于世界革命的进程和作为这个世界革命组成部分的苏联的经济政治成就”[8]22。这个观点类似于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俄国革命所持的观点,因为列宁不仅认为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工农民主专政下的民主革命,而且也认为俄国须在西欧革命的推动下才能从民主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甚至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写于1927年4月19-20日的《蒋介石政变后的中国形势和前景》一文中,列宁还认为工农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的必经阶段,它的前途或是资本主义,或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后者的发生取决于国际形势。托洛茨基首次明确提出,同时也是在联合反对派时期或流放之前唯一一次提出在中国革命中应当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一阶段论的,是写于1927年9月的《中国革命的新机会、新任务和新错误》一文,该文指出:“正是帝国主义时代使中国的阶级关系变得如此尖锐,使得不仅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而且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下,都不能解决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从而把依靠城乡贫农的无产阶级专政提上日程。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社会主义介入到财产所有制的关系中,转到国家负担生产费用,即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功将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提供巨大的推动,巩固苏联,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新的可能性。”[8]146这里不仅直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不像上述论述中那样,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须要在世界革命和苏联的推动下才能进行,而是反过来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有力地推动世界革命和巩固苏联。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系列论文中思想发展的一个质变点。从联合反对派解散或流亡之后的1928年起,托洛茨基进一步巩固了这个理论,并在后续的一系列文章中反对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指出这个口号将带有欺骗性,诱使工人阶级重蹈服从资产阶级的覆辙。实际上也就是明确回到了他的“不断革命论”。
对于托洛茨基的这个转变,相关论者如王凡西[注]王凡西(1907-2002),中国托派活动家和理论家,做了较多介绍、翻译托洛茨基著作的工作。、对马忠行和丹尼尔斯[注]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美国托派学者,著有《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等都认为,托洛茨基在与季诺维也夫的联合反对派时期所持的革命二阶段论,是与季诺维也夫等人妥协的产物。因为季诺维也夫等人虽然也反对当时掌握实际政策的斯大林-布哈林派在中国革命路线上更“右”的观点,但也只是本着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二阶段革命公式,而不能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因此,认为托洛茨基在1927年底之前对中国革命所持的理论是妥协的产物不无道理。“丹尼尔斯教授也做了说明,‘为了与季诺维也夫派和解,托洛茨基在“把它与列宁的真正观点区别开来的条件下”,声明放弃了不断革命论(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作为交换,季诺维也夫集团承认托洛茨基对党的机构——即便是在它包括了季诺维也夫派的情况下——的抨击是正确的。’但是,托洛茨基后来说,这个‘原则性妥协’是错误的。因此,1927年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派投降后,托洛茨基又恢复了他原来的论点。”[7]127-128这里所说的“列宁的真正观点”就是十月革命前的公式。
但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不认为托洛茨基1927年9月前关于中国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和二阶段论完全是妥协的产物。也就是说,其中有妥协的成分,但也体现了托洛茨基自己思考的轨迹。笔者觉得托洛茨基明显的妥协成分包括:其一,在联合反对派时期不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原则性错误,而只是指出在当前阶段这一策略的历史使命已尽,应尽快退出国民党;其二,认为中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须要在世界革命的推动下才可能。因为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已表明,在落后的一国范围内虽然没有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但绝不意味着不能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在首先提出工农民主专政口号,其后再伺机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上倒不完全是妥协。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在联合反对派后期,上面提到的、写于1927年9月的《中国革命的新机会、新任务和新错误》一文中已经明确放弃工农民主专政论,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论。因此丹尼尔斯指出是在1927年底季诺维也夫向斯大林派投降后托洛茨基才回到他的“不断革命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从托洛茨基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看,很可能是在汪精卫的武汉分共、1925-1927年中国革命完全失败之后,托洛茨基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认识,即认识到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已变得完全不合时宜,将成为使无产阶级继续追随资产阶级的可怕幌子。托洛茨基在1927年9月的这篇文章中也确实这样写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口号,如果是从北伐开始时,就把它与苏维埃和武装工农的口号结合在一起提出的话,它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就能发挥巨大作用,保障它的完全不同的进程,孤立资产阶级,然后再孤立妥协派,导致在比今天更加有利的条件下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但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资产阶级主动背离了革命……在这些条件下,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口号显得过于不确定和过于模糊。而在革命中,所有不确定和模糊的口号对革命党和被压迫群众来说,都是危险的。”[8]144第二,在1928年流亡时期,已不存在妥协的问题,因此托洛茨基在写于1928年4月底的《我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答复》中所述的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轨迹无疑是可靠的:“关于在中国不会出现任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我是从武汉政府成立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8]255“从1927年4月到5月,我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适用于中国(更确切地说,我赞成这个口号),由于社会力量尚未作出自己的检验,虽然中国的形势对这个口号要比在俄国不利得多;在宏大的历史行动(武汉的经验)已经提供这个检验之后,民主专政的口号成了反动力量,它必然不是导致机会主义,就是导致冒险主义。”[8]259
我们前面指出,工农民主专政是包括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特殊形式在内的未定型的代数式,因此,可能的情况是:托洛茨基一开始实际上对于中国革命是否应当直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应当暂时保留工农民主专政的代数式并无完全的把握,因为俄国革命也并没有完全逾越工农民主专政这个阶段,况且中国的情况还有所不同(还要落后),因此这个时候托洛茨基并不直接坚持“不断革命论”,而是宁肯坚持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个代数式,以便根据革命的具体发展再对这个代数式进一步加以确定。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回过头来学习列宁的经验,他并不是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就把他的“不断革命论”作为教条一成不变地坚持下来,而是试图在中国革命中再经某种验证。这也是托洛茨基与那些把托洛茨基的某些理论教条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不同之处。但武汉分共之后,托洛茨基认识到工农民主专政这个公式还未实现就已经过时了,中国比俄国更不可能经过革命的两个阶段。虽然中国更落后,或者说正由于中国更落后,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更深的勾结,而与无产阶级有着更深的敌对,因此在中国不能指望还能实现一种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民主专政。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性质的专政在中国的情况下,必然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而不会是革命的,因此再提这个公式就纯粹是为国民党对无产阶级的欺骗做掩护了。“他们以此对无产阶级说,专政将不在它的手中。这意味着还有某个目前尚未知道的力量能够在中国实现革命专政。这样,民主专政的公式为从资产阶级民主方面来欺骗工农打开了新的大门。”[8]365因此托洛茨基认识到,是把工农民主专政这个代数式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了。并且,托洛茨基回过头来再次确定,认为工农民主专政这个公式不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才没有实现,而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实现。这就是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对工农民主专政的思考过程,革命的失败使托洛茨基再次否定了这个公式,确认并正式提出了“不断革命论”。
参考文献:
[1]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M].郑异凡,郑桥,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2]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M].柴金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141.
[3] 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郑异凡.托洛茨基的两个预言[EB/OL].(2013-07-18).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104/wenzhang/detail_2013_07/18/27656151_0.shtml.
[6]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M].石翁,施用勤,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296.
[7] 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M].大洪,译.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84.
[8]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M].施用勤,译.西安:陕西出版集团,2011.
Lenin’s“ChangeinApril”anditsLimits:onZinoviev’sCritiqueon“TheoryofUninterruptedRevolution”
LVJia-yi
(School of Marxism,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Around Lenin’s “Change in April” and its limits, this paper discusses Zinoviev’s critique on “Theory of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put forward by Trotsky. After the analysi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whether Lenin’s “Change in April” existed (Were there two stages or one stag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peasant problem in Lenin’s “Change in April”; the limit of Lenin’s “Change in April” (“Theory of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finished by Trotsky after Lenin’s death), it is clarified about the theoretical change of Lenin after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nin’s change and the “Theory of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KeyWords: Lenin; Zinoviev; Trotsky; Theory of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Change in April
中图分类号:A7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2-0038-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2.006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7FKS025);2017年度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SKY-ZX-20170020)
作者简介:吕佳翼(1986-),男,江苏无锡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研究。
(责任编校:夏玉玲)
标签:托洛茨基论文; 列宁论文; 民主革命论文; 工农论文; 民主专政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唐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7FKS025)2017年度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SKY-ZX-20170020)论文; 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