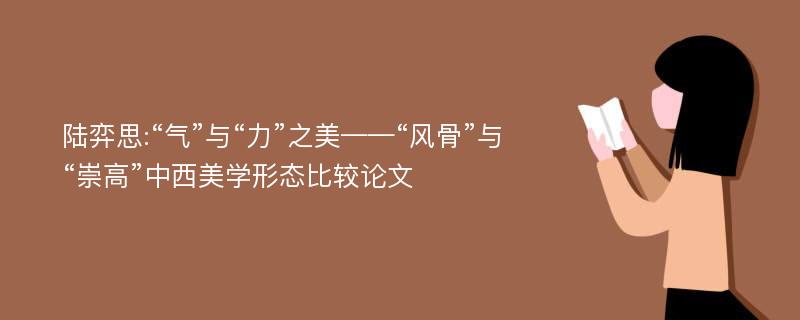
摘 要:“风骨”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自南朝刘勰提出并首次进行完整阐述之后,成为了影响后世文学创作与文学评鉴的重要美学标准。“风骨”强调一种刚健之美,推崇“气”与“力”的壮大,这一点与西方的“崇高”理论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指向作为主体的人的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不是指狭义的伦理规范,而是指一种植根于人心灵深处的“德性”光辉。但二者在具体的内涵及理论发展上又有明显差异,“风骨”偏向于古典的和谐美,而“崇高”则强调由“痛感”向“快感”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张力。“风骨”论主要运用于人物品评、文学书画理论、实践等方面,其美学范式已经定型,而“崇高”论还注重对“自然美”的探讨,后现代以后,以利奥塔为代表的理论家还提出了“后现代崇高美学”,使其内涵变得更为复杂。
关键词:风骨;崇高;气;力;理性;刚健
“风骨”与“崇高”这对中西美学范畴,在内涵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强调“气势”与“力量”的壮大,同时还具有浓厚的“道德”意涵,两者都反身到主体心灵深处的“德性”光辉,这是本文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而比较的基点在于看到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以探寻二者之间具体的理论差异和差异背后的原因,将“风骨”与“崇高”进行比较,更能明确“风骨”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本民族特色,认识到“风骨”论对中国文人、文学及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开放视域,去吸纳西方“崇高”论对我们的启示,找到融会中西的可能,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化添砖加瓦。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风骨”与“崇高”概念的溯源,主要以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和朗吉弩斯的《论崇高》为依据对各自的内涵做解读;第二,进一步细化“风骨”与“崇高”的特点及其在后世的理论延伸,比较二者在阐释对象和运用范围上的差异;第三,深入到文化层面,比较二者背后的“德性”精神。
一、“风骨”与“崇高”的概念溯源
“风骨”作为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是由南朝刘勰提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立“风骨”一篇(第二十八篇),这篇文章虽精短,但意涵丰富,第一段先是论述了“风”与“骨”的内涵及特点,第二段则引入“文气”的概念,进一步说明“风骨”与“气”的特殊关系,最后则从创作角度探讨了达成“风清骨峻”美学理想的途径。“风骨”的内涵本身有着极强的包孕性,再加之,刘勰以华丽而诗意的骈文写就《文心雕龙》,给后世留下了极大阐释空间,也带来了概念理解上的众多分歧。笔者简要梳理了学术界对“风骨”内涵的解读,大致总结出三种看法:第一种是“拆解法”,即把“风”与“骨”看做两个相对的概念,认为“风”指“文意”,“骨”对应“文辞”。黄侃先生就曾这样定义:“文之有意,所以宣达思理,纲维全篇,譬之于物,则犹风也。文之有辞,所以摅写中怀,显明条贯,譬之于物,则犹骨也。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不蹈空虚之弊。”[1]这里强调了“风”是情思的感性生发,而“骨”是语言的铺展。第二种是“以西释中”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形式—内容”二分法来解释“风骨”,即将“风”与“内容”对应,将“骨”与“形式”对应,令人迷惑的是,尝试以此解释“风骨”的学者竟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陈友琴认为,风是内容,骨是形式;舒直先生认为,风是形式,骨是内容。”[2]持两种不同观点的人似乎都在《文心雕龙》中找到了支撑自己观点的依据,以达到“自圆其说”,然而这种矛盾恰恰说明此说法无法站住脚。第三种是“整一”法,即把“风骨”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学风貌来把握,王运熙先生提出:“风是指文章中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骨是指作品的语言质朴而劲健有力,风骨合起来,是指作品具有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3]笔者认为,要将“风骨”还原到其最初的语境当中理解,《文心雕龙》全书由骈文写就,语句之间均是上下对举的互文关系,将“风骨”作为一个统一体去把握显然更为妥帖。
以上三种方法各有优劣,笔者认为应该各取所长,采用“先拆分后整合”的思路去理解“风骨”的内涵。中国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这决定了“风”与“骨”必然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所指,另外,又要注意到“风骨”的互文性及其内涵的互渗,看到其定型为一个整一的美学范畴的生成过程。
《文心雕龙·风骨》开篇有云:
在自测步速阅读的反应时数据处理之前,首先去掉阅读理解问题回答错误的小题以及单个片段阅读时间超过5000毫秒或者低于100毫秒的数据,以确保学生专注于实验,并能完整理解句子。去掉的数据占英语母语组总数据量的0.65%,占中低水平组的0.91%,占中高水平组的0.79%。三组被试在合乎语法句与不合语法句的关键词(sg.4)以及关键词之后两个片段(sg.5,sg.6)的反应时如表 2。
这就是说,“风”的语词内涵可追溯到《诗经》“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刘勰强调“风”是“化感”之本源,与《毛诗序》的解释一脉相承:“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而所谓“化感”又不同于单纯的“讽喻、教化”之意,更融入了“情感”、“感染”的意味,与后面的“志气之符契”联系起来看,刘勰所表述的“风”是指作者的情志在作品中的抒发和外现,也即作品感染力的生发。相对来说,“骨”是对文辞和构架方面的要求,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需“结言端直”,树牢文之“骨骼”。值得注意的是,“风”与“骨”并不是抽象或者泛指的概念,而是有明显特指的,“风”是由生命之气灌注的诗情,“骨”是精爽有力的语言与架构,这是反驳前文提到的第一种解读的最有力的论据。
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 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 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 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鸣凤也。[4]293
“风”与“骨”之间是互相成就的,正所谓:“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4]290而文学作品之“风骨”又映射着作者的人格、情志,李建中先生认为:“作家的风骨有由内而外、由性而体的过程,要把内在的气质个性文本化为文学作品。这个转化过程就是‘深乎风’、‘练于骨’的过程,就是‘述情’、‘析辞’的过程,……”[5]这就把“人”与“文”统摄起来了,实际上,“风骨”论将“气”看做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即是将人的精神气质与文的生命活力联系起来。关于主体生命情志与“风骨”的关系问题,后文还将详细探讨。
相似的,西方理论中的“崇高”也注重对主体人格精神的讨论,古罗马的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首次提出了“崇高”的五个来源:
事实证明,昌乐蓝宝石不仅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优质蓝宝石,而且还伴生多种宝玉石矿物,昌乐方山蓝宝石原生矿是世界唯一的宝石原生矿床,是世界宝石矿的圣地。
基于前文的分析,大致可以总结出“风骨”与“崇高”二者之间的以下几点差异:第一,“风骨”总体上归于古典和谐美,“崇高”则强调矛盾与对立。第二,“风骨”范畴的内涵较为稳定,指刚健充实的文风,贴近文艺批评与实践,“崇高”则从修辞论转向抽象的哲学探讨,注重主体心理内容和鉴赏判断,更将自然界纳入到阐释对象中。第三,“风骨”与中国古代的“气”论有紧密联系,“崇高”则有“理性”作为形而上的支撑。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4]290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西方的“崇高”范畴在朗吉弩斯之后发生了流变,其阐释对象扩展到自然界,其阐释重心更是转移到了主体的心理感受和鉴赏判断上,由具体的修辞论走向了抽象的哲学探讨。反观中国,“风骨”说则一直处于创作论和批评论的语境中,到初唐的时候,陈子昂大力批判当时萎靡华奢的文风,高举“风骨”之大旗,发扬了刘勰和钟嵘的理论,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审美理想,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风骨”、“骨气”、“风力”这些范畴一直活跃在后世的诗论、画论、书论当中。
二、“风骨”与“崇高”的理论特征
在后世的理论延伸上,可以明显地发现,“风骨”论与“崇高”论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从大的文化背景上看,中西诗学在理论发展上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中国的理论形态较为零散,在概念上有相当的模糊性,但其内部又有一条潜在的“线索”,其“发展像滚雪球,由许多时代的许多人围绕同一个传统轴心建立起来。”[7]23而西方的理论形态体系较完整,概念较明晰,“一种理论的产生,以批判的姿态出现,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7]23回到“风骨”与“崇高”,我们也能明显见出这种差异性。
“风骨”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美学范畴,有赖于历史上“风”与“骨”各自文化内涵的积淀。前文提到,“风”起源于诗三百之六义,有歌咏、教化、讽喻之意;而“骨”本义是“骨骼”,曾用于相命之学和人物品评,《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以“骨”形容人的精神气质的例子。另外,魏晋书画品评也大量运用了“骨”的概念,这说明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中较多地保留了形象思维。在刘勰这里,“风骨”已经吸纳了之前所积淀下的文化意涵,只不过发展为更加专门化地讨论文学。无独有偶,同时代的钟嵘在《诗品》中更加细化地将“风骨”范畴运用到文学批评上,他赞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称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还提出了“风力”说,以“建安风力”为典范。在审美旨趣上,他推崇“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将“风力”与“丹彩”并举,这与刘勰关于“风骨”与“采”的论述具有一致性:
①详细说明术后DVT的发生原因及后果,使患者做好预防DVT的准备,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②术后早期功能锻炼能有效的预防术后并发症,促进术后恢复,护理人员应指导患者进行有效的功能锻炼,并嘱患者如有下肢的酸痛不适或感觉异常,应及时通知医护人员;③积极劝导患者戒烟戒酒,防止烟草中的尼古丁刺激静脉收缩,增加血液黏度,从而增加DVT发生的风险。
由此看出,“风骨”之美既是“气”与“力”之美,又是一种中和之美,也就是说,“风骨”非但不排斥“文采”,反而将其包孕其中,二者不可偏废。这就提醒研究者在解释“风骨”范畴的时候,要注意其相对性和中庸性。
西方的“崇高”理论在朗吉弩斯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已经完全跳出了修辞论的范畴。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选取伯克和康德对“崇高”的阐述做简要分析。英国经验派美学家伯克于1756年发表了《对崇高与美的观念起源的哲学探索及关于趣味的引论》一书,他主要从主体心理上论述了“崇高感”的起源,并将阐释对象扩展到了自然界和社会,强调了“痛感”在其中的作用。伯克指出:“当我们有痛苦与危险概念而不实际处于这种境遇时,就是欣喜,这种欣喜我不称它为快乐,因为它注重痛苦,而且因为它与任何确定快乐概念差异很大,这种欣喜我称之为崇高”[8]也就是说,崇高的来源不是快感,而是痛感。进一步,他认为恐怖或惊惧是崇高感的主要心理内容,并说明了“审崇高”需要与引起惊恐的外物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这些观点对康德产生了重要影响。
成熟期:毕业生心态平和,具有合作精神和相当的工作技能,技能稳步增长,并逐步在团队内部显示出其人格魅力,得到其他人员的认可,更加注重工作的成就感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因此,用人单位一方面要为他们提供干事创业、实现发展的平台,让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干;另一方面要及时把优秀人才选拔到更高的职位上来,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康德哲学是一种先验的哲学,更加强调主体的“理性”,他早年写过一部小书《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相比于后来的《判断力批判》,康德在这部小书里更多地以“观察者”的眼光,而非哲学家的眼光来看问题。他认为崇高感与美感有着不同的对象,例如“一座雪峰耸入云端的山脉景色、一场狂风暴雨的描述、或者弥尔顿对冥界王国的叙述,都激发出欢愉,但又带有恐惧”[9]286,这便是崇高感。“崇高令人激动,美则令人迷恋”[9]286。康德不止将“崇高”与“美”对举,还把“崇高”与人的品性联系起来,他说:“在道德品性中,惟有真正的德性是崇高的”[9]291,即使在康德早期略带经验色彩的观察中,主体的“理性”也是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的。
笔者认为,上述第三点值得进一步探讨,“风骨”和“崇高”在根源上都强调主体的生命精神和人格力量,“气”与“理性”恰可看作是二者德性精神的本源。
虽然,朗吉弩斯主要从修辞学的角度论述“崇高”,但他明确指出,辞藻作为技术手段可以后天学习,而“高尚的心型”却是天生而非学来的,但是另一方面灵魂可以得到相应的锻炼。对此,他提出应该仿效古希腊的诗人和哲人,以获得伟大精神的指引。因此他极为推崇荷马、柏拉图、德谟西尼士。在辞藻和架构方面,朗吉弩斯认为应该联合运用不同的修辞方式以保持文辞的遒劲:“两三个(修辞方式)互相联合,会互相加强言语的气势、说服力、和美”[6]123。对于语言上修辞的运用,朗吉弩斯不主张过分堆砌,换句话说,应该让情感与文辞相匹配,以强烈的情感和思想作为内力来牵引出大胆的比喻,而这些比喻是为表情达意所必需的。那么什么是“整个结构的堂皇卓越”呢?与“风骨”相似,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文本的整体风貌,也就是满足了前四个条件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美学效果,恢弘遒劲而充满高尚的思想。这种“堂皇卓越”并非意味着全然完美和精致,但一定是浑然天成的,朗吉弩斯认为:“最恢弘的智力并不是最精细的。常常专求精确的心灵是容易溺于琐屑的。”[6]125由此可见,他所论述的“崇高”以高贵的灵魂为内核,而这与“风骨”之“气”的人格显现不谋而合。
任务驱动教学法的教学实践初步表明:其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建立了学生主体地位,激发了学生主动性,强化了学生实践能力,提高了教学效果。
三、“风骨”与“崇高”中的德性精神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庄严伟大的思想,……第二是强烈而激动的情感。这两个崇高的条件主要是依靠天赋的,……第三是运用藻饰的技术,藻饰有两种:思想的藻饰和语言的藻饰。第四是高雅的措辞,它可以分为恰当的选词,恰当的使用比喻和其他措辞方面的修饰。崇高的第五个原因包括全部上述四个,就是整个结构的堂皇卓越。[6]119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更为系统地探讨了“崇高”范畴,他认为崇高的判断与美的判断的不同之处在于,崇高不涉及对象的“形式”,这种“无形式”就是“无秩序”,它“和我们的判断力相抵触,不适合我们的表达机能,……对于想象力是强暴的。”[10]也就是说,当人们面对一个无限大的对象时,无法通过想象力与知性去把握它,就会陷入到痛苦无措的境地,而这恰恰是“崇高”的来源。康德将“崇高”划分为两种类型: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数学的崇高强调一种体积上的绝对的大,力学的崇高则强调既引起恐惧又引起崇敬的那种巨大的力量或气魄。康德对崇高的分析皆以自然界为对象,说的是人面对可怖的压迫性的事物,在保证一定审美距离的前提下,能在主体的理性中唤起超越自然的力量,这种激越的情感体验就是崇高。这是一种“消极的快感”,有一个从“痛感”向“快感”转化的过程。然而,崇高感不是任何人随时随地都能体会到的,这需要主体自身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文化教养,能够唤起内心超感性的能力,崇高本质上与外物无关,只与人的理性和观念有关。
“骨气”相较于“风骨”,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频率更高,而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中,所有围绕“风骨”的讨论几乎没有离开过“气”这个中介。这与中国古代的哲学观有关,《乐记》有云:“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暖之以日月,而百化生焉。”天地之气融会,阴阳相合,即万物生焉。可见,“气”充盈于宇宙间,化育了万物,也就是说“气”是终极的本源。那么“气”与“风”是什么关系呢?《庄子·齐物论》云:“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大地吐气,气流动起来,则生成了风。[11]将“气”的概念引入到文学理论中,最典型的是曹丕的“文气”说,其内涵很宽泛,融合了当时用于人物品藻之“气”的概念,即气质品貌,也指文人的自然禀赋和个性精神。曹丕还将“文气”分为“清”、“浊”两种,恰与“阴”、“阳”对应,这已初见风格论的雏形,“文气”是“文风”形成的基础。从根本上看,以“气”论文,即是把文学当作活的生命体,它是诗人个性气质和精神品格的外现。再进一步,刘勰所推崇的“骨气”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呢?笔者认为,《文心雕龙》是宗经论文的的典范,内核是儒家的道德理想,其注重的是君子人格,此“气”可以说是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其“至刚至大”,既充盈笃实,又恰好与刚健的文辞相通。
图10为两种开挖顺序顶板中部下沉位移分布,由图可见,先开挖小断面时巷道顶部表面位移量比先开挖大断面时小约7.0%(约3.0mm),向顶板深部发展两种开挖方法引起的位移量逐渐趋于一致,由此可知,两种开挖方法引起的位移差别主要集中在巷道顶部附近。在顶板深部4m处煤与上部岩层交界面,两种开挖顺序引起的顶板位移量曲线斜率均发生明显变化,位移增加率开始变小,表明煤与直接顶在此处发生离层,因此顶板支护应该以顶部煤层为重点。
再看西方的“崇高”理论,我们会发现,从朗吉弩斯到伯克再到康德,他们都非常注重源自主体心灵的理性精神。前文提到,朗吉弩斯认为,在“崇高”的五个来源中,最重要和最具决定性的条件就是“高尚的心型”,而这种伟大的灵魂是天生的,此观点已带有明显的先验性特征。到了康德,他在吸收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将“崇高感”的产生过程细化,提出崇高是“无形式”,是对象的不可把握,是主体调动强大的理性精神以求对不可把握之对象的超越,这是一种“消极的快感”。“崇高”不涉及感性形式,而完完全全出自于主体的内心,外物的绝对的大一方面让人感到惊恐无措,压迫着人的知性和想象力,另一方面又唤起人超凡的理性力量,唤起在平常未曾显露的强烈使命感。这么看,自然或文艺作品作为对象,并非是产生“崇高”的根源,而只是激发崇高感的一个外在因子。
“风骨”论虽没有涉及“恐怖”与“痛感”,但却注重“悲悯”与“深沉”。以“建安风骨”为例,其整体的美学特征可用“慷慨悲凉”概括,值得注意的是,这“慷慨悲凉”背后是对现实的深切关怀。曹操既看到战争带来满目疮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也不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的壮志豪情。在这样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体会到的便是一股刚健壮大的浩然之气,于悲苦之境,仍不负壮志。当然“风骨”不止一种形态,在不同的文人笔下又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如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苏轼的放达,这就更说明了诗人自身的“骨气”于作文的特殊影响。
表中:ρ为土体密度,ω为天然含水率,ωp为土体塑限,ωL为土体液限,c为粘聚力,φ为内摩擦角,k为土体的渗透系数。
相对来说,西方的“崇高”理论适合与其悲剧形态放在一起分析。在古希腊神话及英雄史诗中,人格精神就非常突出了,例如奥德修斯在返乡旅程中,面临自然环境和精神上的巨大恐惧,遭受了种种艰难险阻,最终以强大的意志力量征服了磨难。再比如俄狄浦斯王与命运抗争的故事。两者虽然结局完全不同,却都给人带来了“崇高”的情感体验。这说明,“崇高”理论在鉴赏判断的角度,精准地把握住了主体的心灵特质和理性精神。
本文之所以将“气”与“理性”单独拿出来对比,是因为这涉及到“风骨”与“崇高”各自深层的文化基因,它们的本源正是中西方不同的德性传统。此处使用“德性”一词,是将其与狭义的伦理道德做一个区分,它是一种更为根本性的价值体系。我们大致可以窥见,“风骨”背后有儒家的道德意蕴,“崇高”背后有基督教的道德意涵,因此“风骨”论是现实的、具体的,而“崇高”论是抽象的、神性化的。“崇高”强调命运的不可把握,强调“痛感”的刺激,较为消极和警醒,而“风骨”强调生命力的光辉可贯通宇宙,可化作慷慨激昂的、审美化的生命存在,持存下去。
图3为动态实验的装置示意图,主要由高速摄影系统、放大器-应变仪系统和Taylor-Hopkinson杆装置组成。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冲击动力学实验室的37mm的Hopkinson压杆装置开展动态冲击实验。动态实验试件也是从上述三块不同相对密度的闭孔泡沫铝中经由线切割系统加工出来的,试件的直径d为36.5mm,长度L0为100mm,相对密度为0.127±0.006、 0.171±0.002、 0.207±0.003的闭孔泡沫铝试样,通过控制氮气罐的气压值,分别做了6次、5次和5次不同初始冲击速度的动态实验,实验所涉及的全部试件的参数见表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审美形态与人的心灵结构有密切联系,无论是偏重创作论的“风骨”,还是偏重鉴赏论的“崇高”,归根结底都取决于人(作者和欣赏者)的“心灵活动状态”[12]179。胡家祥先生提出,人的心灵结构由三层面、两系列构成,即“感性包括直观表象和体验情感,知性作用于认识抽象和评价价值,志性兼有自性原型和自由意志两个维面,它们表里互动……形成两大对立系列……认识性系列和意向性系列。”[12]83认识性系列,心灵活动是由外而内收敛的,追求和谐整一的法则;意向性系列,心灵活动则由内而外发散,要求自我实现。对于“风骨”与“崇高”背后德性精神的比较,恰好可归于心灵结构的“志性”层面,“志性”的提出为融会中西美学理论话语提供了重要启示。需要注意的是,两系列之间的互动是相对的,“风骨”与“崇高”虽都强调自由意志的发散,却各自处于不同的程度,“风骨”偏向于“中和”,而“崇高”偏向于对立。如果把意向性系列看成是“动力因”,把认识性系列看成是“形式因”,那么,“风骨”所推崇的美学形态,其“形式因”要相对强于“动力因”,而“崇高”则相反。也就是说,“风骨”接近于美,而“崇高”则接近于丑。这种内部要素的差异也决定了两者在理论发展上的走向。
“风骨”论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此美学范式在批评和创作实践中逐渐定型,而西方的“崇高”范畴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出现了“后现代崇高美学”,此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理论家利奥塔,他抓住“无形式”、“无限”等要素,以解释后现代的立体主义和抽象派艺术。从理论发展上看,中国的“风骨”论似乎停留在了古代,但笔者认为,其对“刚健壮大”之气的追求对于现今的文学、艺术现象仍具有特殊引导意义,不同于西方理论“批判”、“颠覆”的多元性特点,中国古典美学更注重“和谐整一”的风雅气度,我们应该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无论在做人还是艺术创作上,继承和发扬其“刚健笃实”的精神。
参考文献:
[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95.
[2]曹顺庆,马智捷.再论“风骨”与“崇高”[J].江海学刊,2017(1).
[3]王运熙.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C]∥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483.
[4][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90.
[5]李建中.文心雕龙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0.
[6]伍蠡甫,胡经之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7]黄药眠,童庆炳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8][英]伯克著.卢善庆译.崇高与美——伯克美学论文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53-54.
[9][德]康德著.李秋零译注.康德美学文集(注释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0][德]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85.
[11]胡经之,李健.风骨:古典艺术的美学风范[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4).
[12]胡家祥.审美学(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Feng Gu”and “Sublimity”: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s Forms
LU Yi-si
(Sout-cen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 “Feng Gu”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in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Since Liu Xie, who lived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elaborat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it has became an aesthetic standard that exactly influenced the literary creation and evaluation of later generations. “Feng Gu” emphasizes a kind of beauty full of power and strength,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theory of “Sublimity” in the West. In a sense, both point to the moral spirit of a person. This spirit refers to the “virtue” rooted in a Chinese’s or a Westerner’s heart. However, there are also obvious differences. “Feng Gu” lays particular stress on the aesthetics of classical harmony, while “Sublime” emphasizes the tension generated by the process from “pain” to “pleasure”. The theory of “Feng Gu” is mainly applied to the evalu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ts aesthetic paradigm has become fixed . In contrast, the theory of “Sublime” theory is applied to expounding “natural beauty”. During the post-modern period, Lyotard, a France theorist, even puts forward the a new concept named “Post-modern Sublime”, which made its connotation more complicated.
Keywords: feng gu; sublimity; qi; power; reason; vigorous
收稿日期:2019-01-28
作者简介:陆弈思(1994-),女,湖北黄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2019)5-0008-05
责任编辑:彭雷生
标签:风骨论文; 崇高论文; 康德论文; 美学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