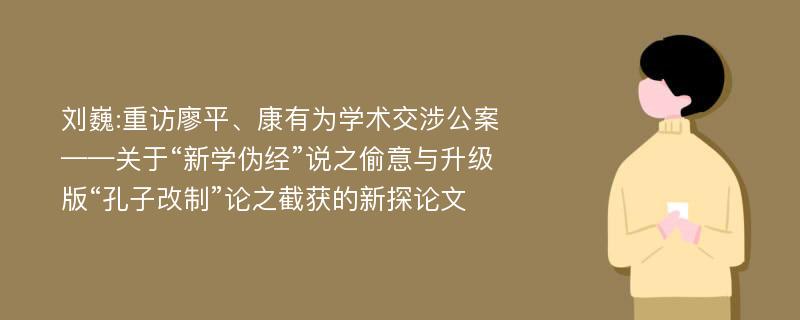
摘 要: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关键词:廖平;康有为;羊城之会;“新学伪经”说;升级版“孔子改制”论
一、引子:未了的公案,重访的契机
康有为有没有攘窃廖平的学术思想成果,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最为重大的学术公案。现如今学术界一般公认1889年冬、1890年春的廖、康羊城之会对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路线的确立有直接的启发作用,但是康氏本人的躲闪、回避、反击,尤其是其变本加厉地渲染自己的孤明独发并不是毫无作用,他的《新学伪经考》等著作也曾得到过钱玄同、张西堂、顾颉刚等知名学者的激赏与认可,其中隐情,像张之洞、梁启超、章太炎等年辈相近、人脉相通、议论相交的故人们还是很清楚的,来自廖平的叙述揭发自然较康氏所言为近情可信,但是廖氏的后人后学尤其是同乡后继的研究者们又敷衍出许多不根的传说,反而使得此案变得扑朔迷离。出于对康有为学品人品的怀疑,不仅他的代表作品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等的著作权遭到质疑,连他早期作品如《教学通义》也被卷入到这一大文抄案之中去了。所以学术界对此案的讨论不是在消歇,而是在扩大。
我生也晚,与康党素无渊源,与廖门亦无“籍”与“系”之类的关联,然深感康氏之经世怀抱及其走向开拓保国、保种、保教之政教事业而至确立今文经学思想路线(带有强烈而明确的“合民权”诉求)的心路历程,需要加以不抱成见的梳理与厘清;另一方面,正是后学们日用而不知地承袭廖康以来的今古文门户之见,妨碍了有关议题的讨论,在对他们两人之间交涉的研究上更是如此,所以需要作方法论上的反省与超越。于是草为《〈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有为与廖平的学术纠葛》一文,刊载于《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注]后收入拙著:《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四五年后,黄开国、唐赤蓉撰文《〈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对房德邻《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公案》(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和拙文一并加以商榷。作者认为我也“从康有为早期思想来寻求‘两考’的源头,以说明康有为早年就有后来的思想,以此否认康有为受到廖平的影响”[注]参见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97-98页。,此类推论的主观臆测成分实在太大。他们也不顾我与房氏见解的基本差别(涉及到诸如公羊学与今文经学的区分及其在整个文本中的分量比重等问题),就将我与房氏捆绑一处,这样做是否得当?笔者原文具在,读者自有明断,先不管他。让大家明了讨论的进程更为重要。
房德邻于两年后,对此文作了回应,他借答辨的机会,既调整了又进一步发挥其自《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一文以来的见解,其《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之内容提要云:
康有为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写的《民功篇》和《教学通义》受到今文经学家龚自珍的影响,表现出某些今文经学观点。光绪十四、十五年康在京师进一步转向今文经学,这是受到了喜好今文经的当朝权臣翁同龢、潘祖荫等的影响,也受到了廖平所著“平分今古”的《今古学考》的影响。光绪十五、十六年之交康在广州会见已经转向今文经学的廖平,受廖平谈话的影响,他完全转向今文经学。随后康在弟子们协助下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这“两考”没有袭用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因为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看过他的“两篇”。长期流传的康“两考”抄袭廖“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1](P100)
他认为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渊源是多元的,康氏“完全转向今文经学”受到羊城之会廖平影响的只是限于其“谈话”而不涉及文本,从而彻底否认了“长期流传的康‘两考’抄袭廖‘两篇’之说”。大体来说,廖平影响康有为的权重大为减弱。房的说法新奇而专执,而心情则颇为急迫:“康有为的‘两考’是否袭用廖平的‘两篇’这桩学术公案已经有100多年了,应该有个了断了。”[1](P109)不过,稍后2013年出版的黄开国著《公羊学发展史》论及此段公案仍然延续其惯有的思路,而其为乡贤廖平不断揭示“两篇”与“两考”之间笼统的一一对应关系的努力也没有止息(详见后文),他一直努力搜寻为康有为所一再掩饰的廖康学术关系的“证据”,也已经由7个[注]参见黄开国:《廖康羊城之会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转变》,《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4期,第75-77页。此前,李耀仙已经罗列了“三方面的证据”,参见李耀仙:《廖季平的〈古学考〉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5期,第14页。进而为9个[2](P239-243),更扩大至11个了[注]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3-678页。黄氏后又撰文针对房氏疑似之说作了澄清。他批评房德邻认为康有为早年就有今文经学观念,不仅《教学通义》有,连《民功篇》也有的看法。他认为房氏“提出的三个新论点都不能成立。……这再次说明康有为早年确无今文经学观念,硬要在康有为早年的著作中去寻今文学观念,只能徒劳无功。”参见黄开国:《〈民功篇〉无今文经学观念论》,《现代哲学》2016年第2期,第113、117页。一年后出版的黄开国主撰:《清代今文经学新论》且列为专节“康有为早年无今文经学观念辨”:“一、《教学通义》无今文经学辨”;“二、《民功篇》亦无今文经学观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1-526页。。当然,房氏的观点也获得了某些学者的热烈响应[注]如王申说:“我完全赞成房氏的推论。笔者也曾早于房氏对康有为剽窃廖平说提过质疑,认为康剽窃廖平学说没有道理(苏全有、王申《康有为剽窃廖平说质疑》,《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38-142页。——此为作者原注,引者按)。康有为受到廖平的影响应是可能的,但谈不上抄袭。”参见王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今文经学问题的考辨》,《天中学刊》第33卷第5期,2018年10月,第124、126页。。
其实在《文》中能体现道家思想的地方并不仅仅上面两个表格中所列举的那些表层内容那么简单,只是上面表格列举的内容更为明显和深层化。《文》中每一处的引用(化用),包括对名字、典籍和名词的引用(化用)都有深刻的用意,都能略见一斑《文》中的观点立场和价值标准。下面本文将分类进行简略分析:
从“己、庚冬春之际”初晤于广雅书局,“庚寅春”再会于安徽会馆(用钱穆说)[3](P644),即1889年冬、1890年春廖、康的羊城之会至今,星转斗移,两个甲子之后,迷案还是迷案。论辩的各方各持所据,远未达成共识。事实上,正如有学者归纳的,关于此公案,纷纭之说,大体可分三派:“一,康氏剽窃廖氏学说。代表学者为钱穆”;“二,康氏受廖氏影响说。代表学者为李耀仙、陈德述、黄开国、汤志钧、马洪林”;“三,康氏独创说。代表学者为萧公权”[4](P4-9)。我们在这里也只是略记最近研究进展的一鳞半爪。疑窦并未消泯,迷雾反更深沉。
我自己14年前的旧作所涉及的只是廖、康羊城之会公案之后案,即它所波及到的对康有为早年文献《教学通义》的讨论。我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商榷,这跟批评者的理解误差有关;反躬自省,也与我尚未将该案子之整个见地和盘托出有关。坦率地说,我当时对钱穆案断之深刻有力是了然于胸的[注]今知其于案情小节亦有判断不确之处,详下文。钱氏论说,详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章:康长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在文中也指出了“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却不为师讳”[5](P49-50),其实也隐约尊重了钱氏的见解。但是该文之着重点是在揭示康有为早期政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所以权宜采用了杨向奎的说法:“《新学伪经考》之作,受有廖平学说的影响是没有问题的,无论康氏是肯定廖说,或否定廖说,是先有廖说而引起康氏之著《新学伪经考》。”[5](P66)今天来看,我从“经世”的观点对康有为心路历程的同情了解丝毫未有改变,这对他来说或许是其行动哲学转变的内在面,但是机缘凑迫的关键时刻,廖平的启发是他重新出发的发条或启动机,康氏对此大节死不认账,影响极为恶劣,说他“攘窃”并不过分。不仅如此,“祖述”自廖平的升级版“孔子改制”说,还成为康有为的主体思想架构,意义非同寻常。他,从而他的党徒,那种凡事无不假托的作风也造成一种恶劣的政治文化,对晚清民国儒学的式微要负很大的责任。这样看来,议题的严肃性与重大程度也远远超出了公案本身。风起于青苹之末,君子慎始,岂仅在谈辩鼓吹之间。值得深思之处,历久而弥多。
为确保业务人员可以对备选经销商进行全面的调研,以筛选相对更加合适的经销商,建议B公司针对市场业务人员薪资方案进行改进。比如在经销商出现空缺时,根据市场容量以及其他市场指标,明确经销商的设立期限,在市场空白的前几个月给予业务人员一定的达成工资。比方说,在经销商出现空缺时,第一个月按照达成100%进行达成工资兑现,第二个月按照80%进行达成工资兑现,第三个月按照60%进行兑现,第四个月按20%进行兑现。如此在市场存在经销商空缺的前期,业务人员有足够的动力去寻找经销商,针对备选经销商的市场调研也会更加充足和全面。
这一切都要从重审此案开始。由于晚清民国文献整理出版的新进展,给我们重访此案提供了新的契机。在重新出发之前,对前贤的研究我们有许多质疑,不揣冒昧,质言如下,以为此案的引子:
张西堂否认康著承袭廖著的看法固有片面之处,但是,不能用后出文献与先出文献对勘以定先出文献反而受后出文献的影响,这样的方法论原则难道不应该遵守吗?流行的将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或者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一一对应以论廖康源流关系的比较法(以晚出之廖氏《考》、《篇》为根据去推度《辟刘》、《知圣》“两篇”对康氏“两考”的影响),是否违反了这一原则,能得出什么可靠的结论呢?
此为廖平首次也是以后罕见的将《古学考》与康氏《新学伪经考》对应起来,述其因袭关系,而不再涉及《知圣篇》了。廖平为说一变。所谓《左传》、《周礼》云云,那是以自己已变之后的见解攻驳康说,先不论他。
所谓只有“辟刘之议”之“谈论”、“谈话”而没有文本过目而引出大篇幅的移书相驳,进而长时讨论商量并导致康氏完全转向今文经学,这是合情理的事吗?
像廖平的《周礼删刘》一样将《教学通义》中“《春秋》第十一”及其后诸如“孔子改制”论述删去试试看,是条理顺畅了,还是完整之篇反而俄空了环节?《教学通义》中有关的“孔子改制”论述与康氏确立今文经学立场后的“孔子改制”说是一回事吗?……
一个一个的疑团牵引着我,让我坠入其中,不能自拔,当我历经曲折走出来时,眼前的光明让我快慰,我愿意将我的所获娓娓道出,与读者诸君分享,也期待一切诚意的批评。
二、重访廖康羊城之会,从廖平的叙述再出发
钱穆敏锐地发现了廖平自说自话不能自圆其说之处:
(一)前奏——廖俞之会的启示
《经话甲编》[注]《经话甲编》,《井研艺文志》著录为“《经话甲集》”,盖有二名。若《经话乙编》,《井研艺文志》亦著录为“《(经话)乙集》”。参见廖平等撰,杨世文、张玉秋校点:《井研艺文志》,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6·附录》,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2—1213页。,《廖平选集》版“点校说明”云:“廖平所著《经话》,分为甲、乙两编。《甲编》共二卷,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讫稿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六年。——引者按:应为一八九七年)二月……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十一月由尊经书局刊行。”[7](P395)《廖平全集》版“校点说明”又云:“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尊经书局刊入《四益馆经学丛书》,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四川存古书局印行《六译馆丛书》收入。”[8](P165)则其中论说或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二月已成,而为世人所知乃在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十一月之后。
《经话甲编》首揭廖康羊城交涉之事。这件事又有一个前奏,就是廖平与俞樾的学术交往。卷一云:
己丑(1889)在苏,晤俞荫甫先生(按:此当廖先在苏,后至粤也。——此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按语,引者按),极蒙奖掖,谓《学考》为不刊之书。语以已经改易,并三《传》合通事(此六字钱氏未引,引者按),先生不以为然,曰:“俟书成再议。”盖旧误承袭已久,各有先入之言(此六字钱氏未引,引者按),一旦欲变其门户,虽荫老亦疑之。乃辟刘之议,康长素踰年成书数册。见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此九字钱氏未引,引者按)[注]李纯蛟点校、李耀仙审订:《经话》,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第447页;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群经类:经话(甲、乙)》,第228页。并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45页。标点作了调整,将“《辟刘》之议”改正为“辟刘之议”。《廖平选集》、《廖平全集》、《廖平经学思想研究》等书文多将“辟刘之议”标点为“《辟刘》之议”,即认为专限于《辟刘篇》的论述,是不确的,盖承袭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误(自初版以降均如是标点)。。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原名《我史》),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页。或以“康的《新学伪经考》刊行于光绪十七年八月”,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1970年版,第37页;或以“《新学伪经考》刻成于一八九一年秋初”,康有为著,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朱维铮所作《导言》,第12页;或以“该书初刻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秋七月”,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1》所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编校者“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页。无大分歧,且从康氏自述。。廖平所谓“康长素踰年成书数册”,指的就是《新学伪经考》。在这里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康氏此书受其“辟刘之议”的启发而成,而此类“辟刘之议”,他早就与俞樾讨论过了。康有为的影响太大,或者说人们太受康有为中心论的影响,以往学者引上述文字多作为讨论康廖学术关系的材料,其实此段主要讲的是廖平与其前辈大师俞樾的交往。文末“贤者”就是指俞樾,廖平不满于他拘于“习俗”之见,虽认可《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书”,却不能接受其日后厘定为经学二变之重要内容的“辟刘之议”,并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为自己张目。大有后来康有为致书廖平“惟执事信今攻古,足为证人,助我张目”[9](P833)的意味。而“其中位置”[9](P664)谁主谁从,是很清楚的。这种并非无根而颇嫌夸张之谈,显然也激化了康有为的深自隐讳倾向。康有为自不在话下,此处廖平更有与俞樾一较高下的意味。
关于土的渗透系数,Baligh and Levadoux(1980)建议通过土的水平向固结系数评价土的水平渗透系数,即用下式估算:
廖平所谓“辟刘之议”何所指?《经话甲编》卷一上接此段的一则(很少为学者所引用)明确地说:
前刊《学考》,于康成小有微词,为讲学者所不喜。友人遗书相戒,乃戏之曰:“刘歆乃为盗魁,郑君不过误于胁从。今由流溯源,知歆为罪首,乱臣贼子,人品卑污,谁更为之作说客?贾、马以下,可不问矣。”(说详《古学考》——此为廖平原注,引者按)[注]李纯蛟点校、李耀仙审订:《经话》,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第447页;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群经类:经话(甲、乙)》,第227-228页。
我们只有紧扣此上文,乃可以获知下文“辟刘之议”的确切意味。代表廖平经学第一变的《今古学考》批评郑君混合今古文家法,引起尊郑学友的戒责,这激起廖平的反批评,而将乱学之源推咎于刘歆,所谓“辟刘之议”就是承此而来,可谓廖平经学二变的发源地。这里所谓“友人”,不必指康有为甚至就不是康有为。而这“辟刘之议”,也是他与俞樾讨论的重要话题,否则就不必援康有为以自辩了。我们万不可对“辟刘之议”作过于狭隘的理解,以为只是周旋于廖康之间而已。
3.1 教学目标达成度 工作坊教学模式突出了学生学习的主题性以及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导性,提高了学生课程学习的参与度,并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持续学习能力,增强了学生实践操作技能、独立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效果明显。
但廖平显然没有说服俞樾,这从“语以已经改易,并三《传》合通事,先生不以为然,曰:‘俟书成再议’”一句话,可以看得很清楚。对这句话的理解关乎两个重要问题:一、俞樾有没有从廖平那里获睹廖平的《知圣篇》、《辟刘篇》?二、该“两篇”此时有没有完成?
中国科学院专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学者解焱提到,评价一个区域环境健康的指标除了有PM2.5和绿化植被覆盖率外,更重要的是周边野生动物的存在状况和健康状况。野生动物不仅指包括濒危的鸟类、老虎、大熊猫、藏羚羊等大型物种,还包括像蜜蜂、蝴蝶、青蛙、蚯蚓和松动土壤中很多其它的动物,它们都是对我们生态环境非常重要的物种,野生动物数量的减少,会造成灾害、无法授粉、虫害、病害、土壤板结、湿地退化的问题等,保护野生动物因而能最大限度地维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类的农业、牧畜业乃至整个生存环境的发展。
我们的重访还是要从廖平的控诉出发。从廖平的叙述出发审理廖康交涉公案,并不是什么时髦的新方法、新取径。如学者指出:“廖平曾屡道及康有为是受他的影响而作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后人谈及他们二人交往经过,亦多本于廖平的说词。”[6](P238)今严格按照其说法面世的时间先后来考察,乃发现一系列重要的事实:廖氏最早提到此段交涉过程(亦即相当于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是《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但是其中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对,对,是我!你先别说话,我得赶快把话说完。告诉你,我的世界只有6000人,电视广播新闻中说这个世界有几十亿人,全是假的。
丁亥(光绪十三年【1887】,廖氏年三十六。),作《今古学考》(按:廖氏《古学考》序,自称《今古学考》刊于丙戌【1886】,此又云作于丁亥【1887】,必有一误。)。戊子【1888】分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论古学为《辟刘》(按:据此则《知圣》、《辟刘》两书均已成,何以又云“己丑【1889】在苏见俞荫甫,曰俟书成再议”乎?抑犹未为定稿乎?大抵廖既屡变其说,又故自矜夸,所言容有不尽信者。)[注]参见李纯蛟点校、李耀仙审订:《经话》,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第497页;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群经类:经话(甲、乙)》,第278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45页。。
上引正文为《经话甲编》卷二中的话,括号内为钱穆按语。钱氏揭示“廖既屡变其说,又故自矜夸”,可谓深悉其病,切中要害。不过我们也应该公正地指出,这与他记性很差的性向与专求“意”通的学风有极大的关系[注]他的女儿廖幼平对此有亲切的体认:“父亲曾自叙其幼时用功之方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见《经学初程》原稿)又曾对人说:‘吾于《春秋》几无字不烂熟于胸中,然试令予背,则不能及半页。’”廖幼平:《我的父亲廖平》,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6·附录:传记与评论》,第982页。善忘的记性兼以逞“思”(王闿运就说他“思而不学”)好胜(不光与王闿运争胜,俞樾也在超越之列)的性格,复加以学尚多变为美的取向,在在使得他的前后叙述矛盾百出,自己既理不清楚,研究者只好以苦为叹。。钱穆案断“所言容有不尽信者”颇有分寸。而房德邻略本此而推演至极端,认为不仅在廖平会见俞樾时尚未完成《辟刘篇》与《知圣篇》,更别说给俞樾过目,就连此后羊城之会时廖平也没有向康有为出示过“两篇”中的任何一篇,“廖对康的影响主要是在安徽会馆长时间的‘谈论’,即‘辟刘之议’”,而所谓廖平有《辟刘篇》和《知圣篇》交给康有为等说法均为不实之辞[注]房德邻:《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引文见第93页);房德邻:《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上文所引房德邻《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一文(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再度维护了这一看法。陈其泰接受了房氏之说,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283等页;陈其泰:《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251页。。
《经话甲编》之《廖平选集》版“点校说明”又云:“《经话》甲、乙两编,迄今仅有上述一种版本(指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本——引者按)。因此,这次点校,别无他本作为参校和互证。”[7](P395)我们参验以其中涉及之廖、康交涉公案,确可以作为《孔子改制考》出版之前的文献来了解。所以其中没有也不可能提到《孔子改制考》,而只是风闻康氏有《孔子会典》之作:“闻康长素有《孔子会典》之作,以经包史,于近事尤详,不泥不违,卓然大备,其有益经济,尤胜于《三通》也。”[7](P425-426)如此评价,不可谓不高。
(廖平)自序欲以《公羊》中兼采《穀》、《左》,合通三《传》以成一家[注]廖宗泽撰、杨世文编校《六译先生年谱》引《潘序》,而于此句下作按语云:“按,甲午作《春秋经传汇解》,当即此意。”参见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5·附录》,第478页。则“合通三《传》以成一家”的取向绵延很长时间,有关之书亦颇多。。继因三《传》各有专书,乃刊落二《传》,易以今名。……公羊、穀梁,班《书》无名遗姓绝少,季平据三《传》人名异文,以为齐、鲁同音异字,本为卜商。是说也,本于罗万而小易之,非观其全说,鲜不以为怪也。
此序作于“光绪庚寅(1890年)三月”[注]以上引文见廖平:《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正》(选录)之《潘序》,蒙默、蒙怀敬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廖平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9-450页。,时间上与廖、俞苏州之会——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七月[注]廖宗泽撰、杨世文编校:《六译先生年谱》,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5附录:六译先生年谱》,第485-486页。颇为接近。可知《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正》亦有“合通三《传》以成一家”的倾向,廖氏一本其以“意”为主本不可通而强通之的牵强附会作风,如运用一种奇怪的小学功夫七转八折将公羊、穀梁[注]《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廖平卷》的编者与《廖平全集》的编者,均将“公羊、穀梁”姓氏人名误标为“《公羊》、《穀梁》”典籍书名,致使文理不通,殊为失当。而《廖平全集》未载《潘序》落款中“光绪庚寅三月”六字,亦莫名所以。参见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7·春秋类: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正》,第741页。硬说为卜商子夏,好比妙手套用一气化三清的手段,将原本不同的人物推合为一,以证成其“合通三《传》”的主张。让人即使看了成书,都“鲜不以为怪也”,更何况尚未成书,难怪俞樾要强调“俟书成再议”了!
我们进一步要指出,“俟书成再议”的例子,对此案不期然而然产生的绝大启发意义,即:为什么一定要“俟书成再议”呢?很显然,对学者来说,对于有过学术经验的人们来说,不难理解:像“辟刘之议”等“已经改易”的学术见解思想主张,仅仅靠谈辩而不依据文本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也很难让讨论深入下去。反之亦然。“成书”与“议”辩,是学术交流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环节。这就让我们严重质疑房德邻所谓仅仅通过“谈论”仅仅通过“谈话”,就能让廖平影响康有为“完全转向今文经学”的说法。请看,《经话甲编》紧接着就连文本线索也提供了——这就是《知圣篇》。
(二)前《孔子改制考》时代的指控——《知圣篇》及其“谈论”决定了《新学伪经考》的速成,与康有为的缺席
《经话甲编》卷一,又云:
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己间(1878-1879),从沈君子豐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及还羊城,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按:赵豐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长素返粤,在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之冬,而移居羊城安徽会馆,则在十六年庚寅【1890】之春。”[注]此处标点,参考了钱穆著、钱宾四先生全集编委会整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7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842页。季平己丑【1889】在粤,庚寅【1890】至鄂,二人初晤,应在己、庚冬春之际【1889-1890】。),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行止。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按:此在庚寅【1890】春。),黄季度[以]病未至,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注]李纯蛟点校、李耀仙审订:《经话》,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第447页;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群经类:经话(甲、乙)》,第228页;并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44页。括号内文字皆为钱穆按语。。
我们跳过一切细节,直奔主题。在今天看来,最值得注意的是廖平说自己“以《知圣篇》示之”,明确说是有文本给康有为过目的,而且“两心相协,谈论移晷”。通过热烈而长时间的讨论,在学术思想见解上是达成共识了。我们在上文分析过的学术交流两大要素,在这里是兼备的。廖氏说康氏曾“驰书相戒,近万余言”,这容有记忆不确或言语夸张之处,但事情大体不会子虚乌有。事实上,若没有文本以为基础,“驰书相戒”致使廖平有如此深刻的印象是不可能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从著述文本渊源关系来看,他明确地说是《知圣篇》影响了《新学伪经考》。重要的话再说一遍:是《知圣篇》而不是《辟刘篇》,是《知圣篇》与《新学伪经考》对应,而不是《辟刘篇》。
《经话甲编》卷二,又云:
丁亥(光绪十三年【1887】),作《今古学考》。戊子【1888】分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论古学为《辟刘》。庚寅【1890】,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合(“合”,钱穆引作“克”,非是——引者按)。逾年《伪经考》出,倚马成书,真绝伦也[注]李纯蛟点校、李耀仙审订:《经话》,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第497页;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群经类:经话(甲、乙)》,第278页;并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46页。。
《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的完成之年,确如上引钱穆所辨,“所言容有不尽信者”。黄海德点校、李耀仙审订之《今古学考》“点校说明”云:“《今古学考》初版刻于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为廖编《四益馆经学丛书》之一。……卷首有廖平自述,谓是书成编于丙戌六年。成都刻印。”[7](P31)今检廖平自述:“丙戌六月朔日,编成识此。”[7](P34)则“点校说明”之“丙戌六年”当为“丙戌六月”之讹。是知《今古学考》于“丙戌(1886)六月”已经完稿,初版亦在该年——丙戌(1886)。《经话甲编》卷二廖平自叙此事已经误差挪后一年。《经话甲编》之卷二当晚成于卷一,我们考虑到廖平的记性、学风等因素,宁肯相信时间较相接近的卷一所言,至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注]参见廖宗泽撰、杨世文编校:《六译先生年谱》,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5·附录:六译先生年谱》,第486页。廖平与俞樾苏州之会时“两篇”尚未完成,所以“光绪戊子季冬分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篇》,古学为《辟刘篇》”之自述年份,我们也不予尽行采信,至少我们不将“戊子(1888)”作为“两篇”已经完成之年来看,我们宁可相信“戊子(1888)”为分篇草创起稿之年,而绝非“两篇”结束完稿之期。另外,他未尝不会因为记忆不确或者因缘夸张康氏祖述自己的心理,而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两篇”著述系年提前。
也必须强调指出,尽管廖平在这里已经将后来厘定为经学二变的经学思想分述为“两篇”,并认为《新学伪经考》渊源于此,而仍未将《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一一对应,更未说及“庚寅(1890),晤康长素于广州”时将“两篇”一并给康氏过目等等直到现如今不少学者都仍在热衷铺陈的捕风捉影之谈。所以《经话甲编》卷一提到“余以《知圣篇》示之”一句仍然是案中的关键。多年以后,“议论相合”的总印象是不可磨灭的,此点也不容抹杀。当然,这时的所有指控都是指向《新学伪经考》的。
《皮锡瑞日记》丁酉(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即1897年12月29日记云:
梁卓如送来《新学伪经考》,又从黄麓泉假廖季平《古学考》、《王制订》、《群经凡例》、《经话甲编》。康学出于廖,合观其书,可以考其源流矣。[10](P744)
谈思想送政策、谈表现送动力、谈困难送温暖。中国石化青工委乘势而上,巩固“走访寻”工作成果,建立“与基层青年面对面”常态化交流沟通机制,做好青年思想状况调查研究,定期向党政报告青年思想状况和动态,用心倾听青年心声,及时反映青年呼声,有效解决青年实际问题和困难。活动共解决青年实际困难上万件,各单位共推送优秀案例326个,推送“走访寻”工作和“寻找最美”典型2300多期。
廖平的指控既指向《新学伪经考》,皮氏也是通过《新学伪经考》来了解廖、康之间的学术源流关系的。皮氏显然早已风闻的这一公案,不过他得康书甚迟,在《新学伪经考》出版六年后才见康门奉送;而得廖书甚速。《古学考》初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注]赵载光点校、李耀仙审订:《古学考》“点校说明”云:“清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八),成都尊经书局刻本,称《原本》。……为最初版本”。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第113页。光绪二十三年当为1897年,非1898年。,《王制订》亦初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注]参见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5·三礼类:王制订》“校点说明”,第107页。,《群经凡例》亦初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11](P310),又如上所述,《经话甲编》亦初版于此年。廖氏诸书,均初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且均为成都尊经书局所刻。在同一年中,书甫出后不久,皮氏就得借观,以定廖、康学术交涉之案,而得出“康学出于廖”的结论了。有学者将其作为康有为承袭廖平的重要证据[注]参见黄开国:《廖平评传》,第242页;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第676页。。皮锡瑞以经学家的学养,对此类案断当然有其专业的敏感,他的结论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但是他的说法是否具有“证据”的资格与力量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好联系张西堂对此案的相反判断来看。
张西堂于1935年曾校点《古学考》,作为“辨伪丛刊之一”,书末附录“丁酉(1897)仲冬,井研廖平自识”之《跋》,与皮氏日记在时间上也很接近。跋文结束云:
广州康长素因《古学考》而别撰《伪经考》,牵涉无辜,持论甚固,殊知(似当作“殊不知”,疑夺“不”字——引者按)《左传》既已不祖周公,而《周礼》今亦符契《六艺》乎?[12](《跋》,P1-2)
流行的所谓在羊城之会廖平将“两篇”一并让康有为过目的传说是如何兴起的,它真的与廖平本人的叙述相符吗?
数年之后在定本《知圣篇》正编(初刊于光绪三十年【1904】)中,廖平亦以已出《古学考》为本述此事云:
初刊《今古学考》,说者谓为以经济(疑衍“济”字。——此为《廖平全集》本编校者校勘记,引者按)解经之专书。天下名流因本许、何,翕无异议。再撰《古学考》,外间不知心苦,以为诡激求名。尝有人持书数千言,力诋改作之非,并要挟以改则削稿,否则入集。一似真有实见,坚不可破者。乃杯酒之间,顿释前疑,改从新法,非《庄子》所谓是非无定?[注]舒大刚点校、李耀仙审订:《知圣篇》,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第211页;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群经类:知圣篇》,第366页。初刊年份,参见《选集》本《点校说明》(第169-170页)。全集本《校点说明》(第319页)以为:“(光绪)二十八年(一九0二)……问世”;郑伟“据《六译馆丛书》本《知圣篇》封面‘光绪壬寅年春三月,射洪邓维翰题’,是书刊刻当在光绪二十八年(一九0二)。”均不可从。著作面世,当以初版为准,较为稳妥。郑氏之说,见郑伟:《廖平著述考》,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With this,the teacher should teach basic knowledge in class,and after class,the students can develop the learning autonom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situation.Teachers should prepare different learning materials and guide the students to learn and finish the tasks.
此说与前引《经话甲编》之说有大不同者,又有大体相同者。《知圣篇》一变而为《古学考》,当属廖平因缘刻意将康有为之著述归本于自己已出著述,而将当年事实搞混所致。而总体印象不误者,为“尝有人持书数千言,力诋改作之非,并要挟以改则削稿,否则入集”之回忆,正与早先叙述“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相合,绝非子虚乌有之事;而“杯酒之间,顿释前疑,改从新法”,则正述其当年与康氏“谈论”之效应,文辞虽颇有夸张,事体是不错的。然必谓《新学伪经考》出于《古学考》,则大乖事实与论理。
张西堂于《古学考》之廖《跋》后下按语云:
康有为《伪经考》撰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而廖氏此书则撰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康书之成明在廖书之前。且《古学考》中明用康氏说(页十九),又已用《伪经考》说称《左传》为《国语》(页四八等处),而廖氏必谓康氏“因《古学考》而别撰《伪经考》”,殊非事实。读者心知其意可也。[12](《跋》,P2)
用初版于1891年的书与初版于1897年的书对勘,而谓先出之书必源本于后出之书,这在学术方法上是犯了大忌的。张西堂于廖、康学术关系所知虽有限,但是这个判断——“廖氏必谓康氏‘因《古学考》而别撰《伪经考》’,殊非事实”——是铁案不移的。从这一点说,我们认为像皮锡瑞的论断(他只是在私下里说说而已)也是虽有理而无当于“证据”之资格。道理很简单,仅凭晚出之“《古学考》、《王制订》、《群经凡例》、《经话甲编》”等材料,不足以坐实此案。非常可惜的是,许多研究廖平的后学无视先贤(这里指张西堂)见解的合理之处,普遍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探讨廖、康学术渊源(以晚出之廖氏《考》、《篇》为根据去推度《辟刘》、《知圣》“两篇”对康氏“两考”的影响)。如李耀仙《廖季平的〈古学考〉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第5期);黄开国《〈孔子改制考〉与〈知圣篇〉之比较》(《孔子研究》1992第3期);陈德述《廖平与康有为》(载黄枏森主编《思想家》第一辑,2005)之“二、《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及“三《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黄开国、黄子鉴《〈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的比较》(载《学术论衡》,2017年第2期);黄开国主撰《清代今文经学新论》第六章第四节“‘两考’与‘两篇’的比较”之“一、《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比较”、“二、《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的比较”(黄开国主撰:《清代今文经学新论》,第546-573页);台湾学者崔泰勋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康有为思想发展与廖平的关系》“第五章《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与《古学考》、《知圣篇》的比较”[注]参见崔泰勋:《论康有为思想发展与廖平的关系》,第93-140页。如论文第94页云:“要研究《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的关系,只有从《古学考》入手了。”就典型地反映了流行的研究思路。,等等,无不如是。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且不论其观点的得失,仅从为学之方法取径上看是彻底失败的。
(三)后《孔子改制考》时代的厘定——《改制考》祖述《知圣篇》、《伪经考》祖述《辟刘篇》之说,以及康有为的反应
廖平本人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中又作了重要的调整,不再援引晚出之《古学考》以为《新学伪经考》的渊源,再一变而指认为更早的《辟刘篇》。其述经学“二变记”云:
于是以尊经者作为《知圣篇》,辟古者作为《辟刘篇》。(外间所祖述之《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而多失其宗旨。)[注]见廖平撰:《经学四变记》(据“目次”——引者按),四川国学院《四川国学杂志》第六号,第42页,括号内为原注。正文标题为“《四益馆四经学变记》”,当为“《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之讹。并参见廖平等著、舒大刚校点:《经学六变记》,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2·群经类:经学六变记》,第886-887页。
《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初刊于四川国学院《四川国学杂志》第六号,“目次”标题为“《经学四变记》(廖平撰)”,正文标题讹为“《四益馆四经学变记》”,我所见电子扫描本刊首刊尾均无刊行年月,据该刊最后一文“附录:《杨禹昌传》(李尧勋撰)”落款“民国二年三月李尧勋识”)[13](P73)可知,该《四川国学杂志》第六号当出版于1913年。蒙默、蒙怀敬介绍说:“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四益馆经学四变记》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廖氏门人郑可经所编,由廖氏口授可经笔记。1912年由刘申叔(师培)将其摘编节本刊入《国学杂志》第六号。后又将原版挖改列入《新订六译馆丛书》。”[11](P154)今检《四川国学杂志》第六号初刊本之《序》末云:“壬子(1912年)冬,将前记摘编节本[注]“节本”两字,现存诸本之校勘记所述均脱漏,尤其是后出诸本不加复查订正,殊不可晓。为省篇幅,恕不一一出具。,以付枣梨。四益馆主人又识。”[13](P40)则该《记》之编成之年或在民元之前,而“节本”成于1912年冬,至1913年刊出,乃广为人知。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廖平述其经学“二变”刻意渲染了他与康有为的学术交涉公案。他在“二变记”后下按语云:“按:以上二卷事在二十年前,所有刊播各书为海内所共见。”[13](P42)所谓“为海内所共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闲言碎语。而他以前述其经学之变,并不特别强调《辟刘篇》。如《〈四益馆经学丛书〉自序》云:
癸未(1883)以来,用东汉师法,劈分今、古二宗,丙戌(1886)有《今古学考》之刻。原意约同志讲求,非敢以为定说也。戊子(1888)以后,始悟古学(原编者注:“古学”下原衍“考”字,据文意删。——引者按)起于刘氏,讲书所言渊源多为附会,乃作《古学考》、《周礼删刘》二篇,以《左传》归还今学,此一变也。丙申(1896)以后,《周礼》所删诸条陆续通解,删去刘氏羼补删改之说,至于此而群经传记统归一律,无所异同。以师说论,彼此固有参差;以经传论,不须再立今、古名目,此又一变也。……丁酉(1897)仲冬自叙。[注]廖平:《〈四益馆经学丛书〉自序》,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3·群经类:家学树坊》,第1271页。标点略有调整。
此为廖平自述早期学术变迁之较早而较为确实者。《周礼删刘》,后附入《古学考》,二篇合成为一篇。对廖氏自己经学之变的进程来说,《古学考》确为其经学二变的代表作。其《与宋芸子论学书》亦云:
传统媒体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可以将这些信息资源提供给新媒体,使得信息资源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传统媒体易受到时间、地域的限制,但是新媒体恰恰可以打破时间和地域的束缚,将信息的时效性体现出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可以强化各自的强项,弥补各自的弱项,逐步占据信息受众的每一个零碎时间。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后不仅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同时还丰富了信息量,提高了信息的实现性,增强了新媒体的权威性和信任度。
与《知圣篇》相比,当廖平获得“知圣”之微言之后,此义大体从未抛弃变更,而其他篇什则颇有不同。若要述及其学术之屡变,其变者比大体不变者反而更有叙述的必要。所以我们以为,此等处未涉及“两篇”反而是颇为近情的。我们更认为,单纯自述其学术变迁之迹,实未必提及“两篇”;当他牵涉到与康有为的学术交涉时,乃不得不强调“两篇”尤其是《辟刘篇》。此廖平原为揭发渲染康有为受自己的影响,结果适足见廖氏反而深受康氏之影响,此意若吊诡而实可理解之一事实也。
廖说之修正,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明确定位:康有为的代表作《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本于自己的经学“二变”。
廖氏持此说甚坚。稍后,“民国二年癸丑(1913)”“六月初二”[14](P617),廖平在《答江瀚论〈今古学考〉书》中,也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先看他如何看重《四变记》,该函之《序》落款云:“时癸丑(1913年)夏六月初二日……时年六十二,《四变记》刊本初成之时也。”[9](P636)此亦可参证,载有《四变记》的《四川国学杂志》第六号确刊行于1913年,至“六月初二日”,“《四变记》刊本初成”。廖氏接着在信中又郑重地澄清道:“足下谓我崇今摈古,以《周礼》、《左传》为俗学云云。案,《学考》平分今古,并无此说,此乃二变康长素所发明者,非原书所有。旧说已改,见于《四变记》中。”[9](P640)笔者在这里要厘清钱穆的一个误解。《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引此文,而评论道:“(廖平)至是而又以尊今摈古之见,推为长素所发见,不惟不愿贪天功,抑若不欲分人谤,出朱入素,前后判若两人矣。”[3](P650)钱氏盖一时惑于廖氏“发明”一词,未细读上下文而偶有不确。其实,所谓“崇今摈古……此乃二变康长素所发明者”,是说,康有为只是“发明”了——斥言之——攘窃了自己早已抛弃的经学“二变”学说。他对于康有为的“发明”权之争不是放松了反而益亟矣。下文我们还将看到,正是在1913年他屡屡重提此案。
廖平于此一直耿耿于怀,执之老而弥坚。他于《六变记》中犹云:“至戊子(一八八八)而‘尊今抑古’之论立。‘今’主孔子,‘古’主周公。外间所传《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宗此派也。”[7](P618)像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揭发,是不会没有影响的。章太炎《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云:“而康氏所受于君者,特其第二变也。”[15](P298)我们认为章氏的看法盖本于廖平本人的上述夫子自道,而未必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闻之于乃师俞樾。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廖平生平第一次明确地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自己的《辟刘篇》及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自己的《知圣篇》分别一一对应起来,厘定廖、康之间的“祖述”与被“祖述”关系。相对于自己以前所述来说为一大变,对后世来说,则确立了定型化论述,影响深远。
其实不难理解,之前只针对《新学伪经考》立说,是因为当时《孔子改制考》尚未面世,当廖平看到了此书,发现该书主旨比前书更接近自己的二变学说后,震惊之余,乃不能不调整旧说。
关于《孔子改制考》的著述出版历程,黄彰健有扼要的说明:
据康《自编年谱》,康的《新学伪经考》写成于光绪十七年(1891);光绪十八年(1892),康选同学诸子分辑《孔子改制考》资料,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孔子改制考》一书始写成。康《自编年谱》说,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康广仁在上海大同译书局刻《孔子改制考》。今考李玄伯先生所藏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孔子改制考》,书首有戌戊(当作“戊戌”——引者按)正月元日康自序。光绪二十四年(1998)正月二十一日《时务报》第五十一册有出售《孔子改制考》广告,则《孔子改制考》之付印系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在二十四年(1898)正月印成。[16](P31)
由于中频电炉的主电路包括整流部分和逆变部分,输出功率的调节主要通过调整整流部分的导通角宽度来实现功率调整[1-2],导通角采用V-F变换的电路,通过设定输入电压控制导通角的宽度,内部电路具有电压、电流控制环,使中频电炉能够稳定的工作在某一功率上稳定加热。对中频电炉的温度控制可以通过控制整流部分的导通角,即通过控制V-F变换的输入电压。
如是则廖平等在“二十四年(1898)正月”以后,乃能得见《孔子改制考》。所以初版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十一月”之《经话甲编》及“丁酉(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之《皮锡瑞日记》只能就《新学伪经考》而论廖、康学术关系。
陈文豪则指出,上引《经话甲编》中俞樾所谓“俟书成再议”,“不是指《知圣》、《辟刘》二书未成,而是指廖平所谓‘三《传》合通’的书未成”,“是指《春秋古经左氏说汉义补正》及《左传汉义补证》其时书尚未完成”,“廖平在光绪十六年(1890),至武昌,才将二书稿本给张之洞看”[6](P250-251)。事实上,陈说对钱、房之说都作了商榷。我们认为陈氏揭示了《春秋》“三《传》合通”一事在“俟书成再议”之或可谓之复数之“书”中所占的分量,颇有见地,但是他专执地认为“不是指《知圣》、《辟刘》二书未成”,则不免矫枉过正、推论失当。上文明确地提到“语以已经改易”,如果俞樾看到了“两篇”,以俞氏的学养,自己就可以轻松领会,何必让廖平来告“语”呢?所以我们的看法是:“两篇”与《春秋》“三《传》合通”等书,至廖、俞会晤之时均“未成”、俞樾并均未寓目。我们也得指出,大可不必如陈氏般将“三《传》合通”指实必为“《春秋古经左氏说汉义补正》及《左传汉义补证》”两书,这实在是廖平当时已有而后续大有发展的一个重要而主观任意的治学取向。《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正》之潘祖荫所作之序——《潘序》云:
《经话甲编》又云:
Tennant河地区主要产出铁氧化物型(IOCG)金-铜矿型金矿。此类矿床目前是世界上寻找铜金矿重要目标之一,为含有大量磁铁矿和(或)赤铁矿的矿床,并伴有黄铜矿±斑铜矿,矿产组合变化范围大,与一定的构造-岩浆环境有关,与深成侵入岩及同时期活动的断裂有密切关系(Sillitoe,2003)。其矿床出现于三种环境[7]:①与非造山岩浆有关的大陆地块内部;②与中性岩浆有关的较年轻大陆边缘弧;③褶皱和推覆带。与矿床有关的花岗质岩石大多显示出高钾到橄榄安粗岩的性质,总体看,矿床是一种后生矿床,其矿体形态可分为脉状、筒状、板状、层状和不规则状,矿床最大特点是广泛发育角砾岩筒矿体。
初撰《学考》,意在别户分门,息争调合;及同讲习四五年之久,知古派始于刘歆,由是改作《古学考》,专明今学。[9](P659)
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己间【1878-1879】,从沈君子豐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及还羊城,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行止。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黄季度[以]病未至,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
根据质量通病及控制点,重视对关键复杂节点防水工程,预留预埋隐蔽工程及其他重难点项目的技术交底,传统施工交底是通过二维图纸,然后空间想象。但人的空间想象能力毕竟有限,不同的人想法也不一样。BIM技术针对技术交底处理办法,是利用BIM模型的可视化、虚拟施工过程进行技术交底,使一线工人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复杂节点,有效提升质量相关人员的协调沟通效率,将隐患扼杀在摇篮里。
甲午(1894年)晤龙济齐大令,闻《孔子会典》(已)[也]将成,用孔子卒纪年,亦学西法耶稣生纪年之意。然则《王制义证》可以不作矣。(孙)[生]公说法,求之顽石;得此大国,益信不孤。长素刊《长兴学记》,大有行教泰西之意,更欲于外洋建立孔庙。……长素或亦儒门之达摩受命阐教者乎?[7](P447-448)
说这话时,廖平很可能获睹《新学伪经考》与《长兴学记》。细玩此时廖平的心态,只要康有为承认自己的启发地位(特别地说,指《知圣篇》与“谈论”对《新学伪经考》的影响;泛泛地说,亦可兼指廖氏极端尊孔立场对康氏的影响,详下文),则什么都好说;廖氏大有吾道不孤的得意,及与康氏共扶孔教的壮志。为此他甚至乐观康氏《孔子会典》之成,而谦退以《王制义证》可以不作矣。
廖平那著名的《致某人书》,反映的是同一心境,而时复相接。不同的是,似是直面本人,诉诸要求了:
龙济之大会(“会”当为“令”字之讹——引者按)来蜀,奉读大著《伪经考》、《长兴学记》,并云《孔子会典》已将成书。弹指之间,遂成数万宝塔,何其盛哉!……后之人不治经则已,治经则无论从违者,《伪经考》不能不一问途,与鄙人《今古学考》,永为治经之门径,得朋友欣忭何极!惟庚寅(1890)羊城安徽会馆之会,鄙人《左传》经说虽未成书,然大端已定,足下以《左》学列入新莽,则殊与鄙意相左,因缘而及互卦,尤为支蔓。……今观《伪经考》,外貌虽极炳烺,足以耸一时之耳目,而内无底蕴,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尚未足以洽鄙怀也。当时以为速于成书,未能深考,出书已后,学问日进,必有改异。乃俟之五、六年,而仍持故说,则殊乖雅望。昔年在广雅,足下投书相戒,谓《今古学考》为至善,以攻新莽为好名,名已大立,当潜修,不可骛于驰逐。纯为儒者之言,深佩之。今足下大名震动天下,从者众盛,百倍鄙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久宜收敛,固不可私立名字,动引圣人自况。伯尼、超回,当不至是。……又吾两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知。余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使人有向秀(按:应作“郭象”。——此为钱穆按语[3](P646),引者按)之谤,每大庭广众中,一闻鄙名,足下进退未能自安,浅见者又或以作俑驰书归咎鄙人,难于酬答,是吾两人皆失也。天下之为是说,惟吾二人,声气相求,不宜隔绝,以招谗间。其中位置,一听尊命。谓昔年之会,如邵、程也可,如朱、陆也可,如白虎、石渠亦可。称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闻,患难与共。且吾之学详于内,吾子之学详于外,彼此一时,未能相兼,则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务,不可不深思而熟计之也。方今报馆林立,声气相通,南北二宗,不自隔绝,其得失之效,知者自能知之。[9](P663-664)
2.1 TSH筛查结果百分位统计及确诊情况 209 534份新生儿血片TSH值呈偏态分布,共确诊CH及高TSH血症107例,TSH水平中位数为3.16mU/L,95%、99%分位数值分别为6.37mU/L 和9.63 mU/L。TSH频数分布结果见表1。
此信当作于《孔子改制考》初版之前,《经话甲编》刊行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左右。房德邻以为此信发在“1894年以前”[注]房德邻:《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89页;房德邻:《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第22页。,非是;陈文豪则定在“光绪二十年(1894)以后”[6](P239),亦不甚确。因信中“龙济之大令来蜀,奉读大著《伪经考》、《长兴学记》,并云《孔子会典》已将成书”云云,与《经话甲篇》“甲午(1894年)晤龙济齐大令,闻《孔子会典》(已)[也]将成”云云文辞相接,廖平又以为学多变之己情揣度康氏,自以为对方亦有将变之候,“乃俟之五、六年”,则必在《新学伪经考》出版(1891年)后之“五、六年”,可知也。
这封信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争一戒一望。所谓“两争”,一争著作权,以为《新学伪经考》本于己说,而隐喻康氏之攘窃,将康有为比诸向秀(当依钱说,应为郭象)。文婉而意切,这一指控是很严重的。二争“位置”,廖平所打的如意算盘,他希望的定位,说穿了,是自己得其“内”而康氏得其“外”。廖氏所见未必无理,但如果希望康有为认可,却未免太天真了。所谓“戒”,是戒责康氏、康党当遵守儒行,不可有“伯尼、超回”超贤越圣之类的狂言妄行。这反映了他认为天底下自生民以来只有一个超凡之大圣素王即孔子的思想,与康有为及其党徒那 “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注]用孙家鼐语,见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90页。的政教观念,真是出门即不能合辙。所谓“望”,是温暖地期望,一“内”一“外”,一“北”一“南”,“通力合作,秦、越一家”,共扶大教——“儒门”之孔教。
因为有前面的三大分歧,廖平最后那一点热烈的抱团期望就显得非常苍白了。康氏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城府极深的康有为,或者就像今天的剽窃者们一样,严守“打死我也不说”的口风,不予理睬;或者回信了,但绝不是廖平期望得到的答复。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即廖平此信根本没有发出,只是作为备案的存档保留下来,待时机合适,再刊发出来,给剽窃者以致命的一击(参见下文)。所以此信以既无抬头称谓也无落款的方式,以《致某人书》为名,与《与宋芸子论学书》、《答友人论文王作易书》一道,合为《论学三书》,初刊于1913年《四川国学杂志》第8号,后收入诸多版本的廖氏著作集,持续表达他对康有为那高贵的蔑视(其实也是太过重视)与极度的怨恨。
有学者指出“此编收入《四益馆文集》”,又介绍《论学三书》的版本有:“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四川国学杂志》(第八号)本、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六译馆丛书》本、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四川存古书局《六译馆丛书》本、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六译馆丛书》重印本。”[17](P421-422)初刊本最值得考订具体时间,因为此时才公开刊发的《致某人书》,是1913年廖平重提康氏攘窃案的一系列举动中的重要一环。
《四川国学杂志》创刊于1912年(民国元年)9月20日,每月一期,是当时的四川国学院主办的刊物。创刊号刊登之《简章》有云:“本报月出一册,每月二十日发行。”[18](P8)此杂志从1912年发刊,共出12期。1914年后改名为《国学萃编》[19](P189)。据此推算,刊载《致某人书》的《四川国学杂志》第8号,当刊行于1913年4月20日[注]笔者见过该刊之电子扫描本,刊首刊尾均未署明年月,只能推断。。
这封信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张舜徽就据该函论定廖、康学术关系:“据此,可知康氏之书实出于平(廖平),不可掩矣。”[20](P579)而在稍早的《四川国学杂志》第6号(亦据上文推断当刊行于1913年2月20日[注]这与前引该号“附录:《杨禹昌传》(李尧勋撰)”落款云:“民国二年三月李尧勋识”(四川国学院《四川国学杂志》第六号,第73页)在月份上是有出入的,待考。),廖平刊发《经学四变记》节本,已经将康有为的代表作《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分别界定为“祖述”自经学二变中的《知圣篇》与《辟刘篇》了。廖平还不过瘾。1913年“二月由成都赴京”至“秋初,出京赴沪”这段时间,廖氏出差在北京[14](P615-619)。他“妙晤任公(梁启超)”,但与康有为之间则关系十分尴尬:“君未能遽来,我不能骤往。”[9](P832)还是廖平主动去信,让康有为颇有“故人之书,忽来天上”[9](P833),类似不速之客破门而入般的惊觉。廖平在致故人的信中说了什么?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本旧账:
羊城分袂,倏忽廿载,音书未通(除非是廖平那记性不好的老毛病又犯了,这段叙述使我很怀疑,上引《致某人书》是否曾经发出,这也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性。——引者按),情感常切,想同之也。……忆昔广雅过从,谈言微中,把臂入林。弹指之倾,七级宝塔,法相庄严,得未曾有。巍然大国,逼压弹丸。鄙人志欲图存,别构营垒,太岁再周,学途四变,由西汉以进先秦,更由先秦以追邹鲁,言新则无字不新,言旧则无义非旧。[注]廖平:《与康长素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1·杂著类:集外文》,第832页。此信落款是“四月十六日”,刊载在《中国学报》1913年第8期,又见《庸言》1913年第1卷第14号。康有为的回信《答廖季平书》亦曾刊载于《庸言》1913年第1卷第14号(参见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1·杂著类:集外文》,第833-834页)。查《庸言》该号发行于“中华民国二年六月十六日”,则康氏的回信必在1913年4月16日与1913年6月16日之间,《康有为全集》将之系于“1913年2月”,非是(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10》第19页)。
叙旧至此,显得廖平真是太抬举康有为了,自己的经学“学途四变”竟多半由这“巍然大国”“逼压”所致!紧接着,就图穷匕首见:
前呈《四变记》摘本一册,求证高明,周璞郑鼠,不知何似。[9](P832)
原来在致函这位羡恨交织的故交之前,他已先将刚刚刊发不久的揭露康有为学出于己的“《四变记》摘本”送递至对方,无异于输送去了一发重磅炮弹。而跟进的此信,无异于手举高音喇叭正对着康有为来摊牌、声索、示威而兼垂询:你认不认?你服不服?
我们只有联系这一切相关的论述,尤其是1913年的廖、康交往行实,才能充分理解《四益馆经学四变记》的意蕴。
康有为是何等的聪明!他根本不跟你叙羊城广雅之旧,简单客套一番之后,执拗地回应道:
仆昔以端居暇日,偶读《史记》,至河间献王传,乃不称古文诸书,窃疑而怪之。以太史公之博闻,自谓“网罗金匮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若有古文之大典,岂有史公而不知?乃遍考《史记》全书,竟无古文;诸经间著“古文”二字,行文不类,则误由刘歆之窜入。既信史公而知古文之为伪,即信今文之为真,于是推得《春秋》由董、何而大明三世之旨,于是孔子之道,四通六辟焉。惟执事信今攻古,足为证人,助我张目,道路阻修,无由讲析,又寡得大作,无自发明。遥想著书等身,定宏斯道。方今大教式微,正赖耆旧有伏生、田何者出而任之,非执事而谁归?[9](P833-834)
康氏的回复与廖平针锋相对,有釜底抽薪之狠。这不仅是对刚刚所接之书的答复,也是对前此奉送之《四益馆经学四变记》的答复,甚至还可以说是对《致某人书》的答复。廖平争康氏以“两考”为代表作品的尊今抑古之见皆“祖述”自以“两篇”为代表作品的经学“二变”学说,康有为则謂己说创自独特的《史》、《汉》对读法;廖平争己“内”康“外”的“位置”,康氏以廖“足为证人,助我张目”,则我为主君为从,各安其位可也,颠倒“位置”无门;最可笑者,廖平殷殷以“通力合作”为期,康有为则拳拳以“遥想”“正赖”为望,共扶“大教”的正义,全成虚与委蛇的辞令!
廖平的诉求,可以说完全落空了。所以此案在其心理上烙下了长长的瘢痕,前引《六变记》中“外间所传《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宗此派也”[7](P618)的话,明明可鉴。真是余痛未消。
康有为也是意犹未尽。他将上述因刻意回应廖平而首揭的《史》、《汉》对读以发古文之伪的独得之秘,添油加醋地复述了一遍,安插到1917年万木草堂重刻《新学伪经考》之康氏《后序》中,读者可以对勘得之,不具引。随后更有一段文字隐刺廖平:
今世亦有好学深思之士,谈今古之辨,或闇有相合者。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伪《周官》以为皇帝王霸之运,矛盾自陷,界畛自乱。其他所在多有,脉络不清,条理不晰,其为半明半昧之识,与前儒杂糅今古者无异,何以明真教而导后士?或者不察(“或”即“惑”字,引者按),听其所言,则观其尊伪《周礼》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谋,翩其反而也。[21](P401-402)
这完全是《致某人书》的作风,不具姓名比指名道姓更为狠辣。“何以明真教而导后士?”康有为的指责何其光明正大!两人之恩怨,至此,在康氏一方,连原本“足为证人,助我张目”的客气也消磨殆尽了。“道不相谋,翩其反而”,形同陌路,竟成仇人。廖平曾自期亦自诩“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者也”[7](P412)。康氏诚非一般所谓之“士”,乃自视为圣人素王者,廖氏哪里想得到,他的多变,恰为康氏所乘!
康有为之重刻《新学伪经考》,或有民国“政府布令于学官,已废读经”的语境,或有“丁巳(1917),复辟既败”的心情(均见于《后序》),而在我们看来,就是专为传达对廖平的反击,就是仅仅为了这篇《后序》,也不能不刻。钱穆说得好,“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典出《礼记·大学》)[3](P648),与廖平的学术交往,久已成他的心头大病了。
三、对廖平指控的检讨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很清楚廖、康之间的公案及其产生的纠葛,现在到了我们对此段学术交涉加以公平探讨评议的时候了。我们的考察,还是得从对廖平揭露与认定的说法进行检讨开始。
(一)“祖述”说之确有根据及演绎过当
应该公允地指出,廖平的说法有很强大的杀伤力,但也颇有防卫过当之嫌。让我们再回到前引《四益馆经学四变记》的经典语录,尤其是比正文还重要的注文,即所谓 “外间所祖述之《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而多失其宗旨”。“祖述”二字尤为重点中的重点。
上文“外间所祖述之《改制考》”之“祖述”两字,有学者认为是讹文。如《廖平选集》本出校勘记云:“‘祖述’:据《六变记》二字衍。盖涉下而误。又‘所’字下当有‘传’字,今据补。”[7](P623)如《廖平全集》本亦出校勘记云:“祖述:据《六变记》,二字衍。盖涉下而误。”[22](P887)我们认为此二字未必为误文。借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廖平想表达的其实是“以经术文饰政论”的今文学运动纲领为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论,此为康党及很多有志变法之士所“祖述”,而康氏则“祖述”自廖平的《知圣篇》,这里有两级“祖述”关系。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井研艺文志》录“知圣篇一卷(附《孔子作六艺考》一卷)廖平”,提要云:
(廖)平客广州时,欲刊此本,或以发难为嫌,东南士大夫转相钞录,视为枕中鸿宝,一时风气为之改变。湘中论述,以为素王之学倡于井研者,此也。[23](P1238-1239)
廖宗泽本此而为说,更为明确:
先生欲刊《知圣篇》,或以发难为嫌而止。东南士大夫因转相钞录,视为枕中鸿宝,一时风气为之改变。湘学(《湘学报》)以为素王之说倡于井研者,此也。[14](P487)
凡此所述,大体属实。张之洞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十二日《致长沙江学台(江标)》函电云:
《湘学报》卷首,即有“素王改制”云云,嗣后又复两见。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其说过奇,甚骇人听。窃思孔子新周王鲁,为汉制作,乃汉代经生附会增出之说,《传》文并无此语,先儒已多议之,然尤仅就《春秋》本经言。近日廖、康之说,乃竟谓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孔子所定治世之法,托名于二帝三王,此所谓“素王改制”也。是圣人僭妄而又作伪,似不近理。《湘学报》所谓“改制”,或未必如廖、康之怪,特议论与之相涉,恐有流弊。[24](P244,上栏)
张之洞早先担心的“流弊”,至《井研艺文志》(刻竣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注]参见廖平等撰,杨世文、张玉秋校点:《井研艺文志》“校点说明”,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6·附录:井研艺文志》,第1117页。)述此事,早已经成为过往之“风气”,湘中人士追随发挥康氏“素王改制”之说也是事实(可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而张氏非常清楚廖、康之间的学说先后源流之关系,尤其明了廖平的说法。则可知廖平之争发明权未必尽出于一己之私,亦是知情人士的意见相趣而然也。他的两级“祖述”之说,应该得到了梁启超的认可。1904年12月[注]刊发日期,参见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3论著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梁氏已经指出:“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25](P100)近十六年后[注]刊发日期,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10论著10》,第212页。又称:
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应为《教学通义》,引者按),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有为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者,并夙治考证学,陈尤精洽,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26](P77-78)
一则曰“乃尽弃其旧说”,再则曰“则尽弃其学而学焉”,可谓我们所谓两级“祖述”说的生动写照。所以廖平到北京决不肯主动拜访康有为,而可以“妙晤任公”。这样看来,流行之传闻,或谓“张之洞有书责平,指康为其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23](P943),就未必是无根之谈了。
有必要提醒读者,张之洞的函电更有特别的价值。他不愧是廖平的恩师,他对廖氏的思想学说了如指掌。发此函时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十二日”,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尚未出版,康氏的《春秋董氏学》也还没有出版[注]《康有为全集》编校者关于《春秋董氏学》之“按”语云:“本书(《春秋董氏学》)首次由上海大同译书局于光绪二十三年冬刊行,分八卷六册,其后广州演孔书局于光绪二十四年重刻。”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2》,第306页。。所以,张氏所述,更多反映了廖平的见地。最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揭示了“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这一点最为重要,也最为时贤所忽略。其实“近日廖、康之说”既不是“汉代经生附会增出之说”,也不是清代常州学派的常谈,他们的看法与之虽不无渊源关系,却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新说”了!该“新说”有两个基本点:一,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二,同一个铜板的另一面,是认为,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其核心理念是:孔子是天字第一号大圣人素王,其所造六经,乃为万世制法之章程,非为一时一地而设。这的确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而廖平系统阐释此“新说”,正在《知圣篇》。这就逼近到我们要讨论的核心问题:羊城之会,廖平到底有没有给康有为出示过《知圣篇》与《辟刘篇》?我们考察的结论是,廖平确给廖平看过《知圣篇》,而康有为根本就没有见过《辟刘篇》。其实,只需《知圣篇》一篇,就足以引出激烈的辩论,并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
让我们先排除所谓廖平将两篇一并均让康有为过目的传说,先排除《辟刘篇》也经康氏寓目的捕风捉影之谈,再来证立:所谓廖、康羊城之会,实际是围绕着《知圣篇》的学术思想争论,并让康有为最终接受了廖平的经学二变之基本见解。
上引《井研艺文志》云“平客广州时,欲刊此本,或以发难为嫌,东南士大夫转相钞录”,说廖平的稿本《知圣篇》在广州时多有钞本,流传很广。定本《知圣篇》后有“辛丑(1901)五月十五日季平自识”的《自跋》亦云:
此册作于戊子(1888年),盖纂辑同学课艺而成(这是述《知圣篇》的来源,“戊子”显然只是“作”起之年,而非完成之年,这样看,廖氏之笔语颇严谨。——引者按),在广雅时传钞颇多(可见“在广雅时”,《知圣篇》已经完成,与《经话甲编》卷一云“余以《知圣篇》示之”说合。——引者按)。壬辰(1892年)以后,续有修改。借钞者众,忽失不可得。庚子(1990)于射洪得杨绚卿茂才己丑(1889)从广雅钞本,略加修改,以付梓人。此册流传不一,先后见解亦有出入,然终以此本为定云。[8](P376)
廖平对自己的稿本颇不自爱,一如他的观点,屡变而不知所宗,当人窃己说,乃知珍惜。他的一面之词可信吗?真是绝大的讽刺,有康有为其人者,真正将其“视为枕中鸿宝”,让我们得证廖平此言不虚。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旁证:
今刻《知圣篇》,非廖氏原书;原书稿本,今藏康家,则颇多孔子改制说。顾颉刚亲见之。[3](P652)
此盖《自跋》所云“广雅钞本”之类是也,它当然有证据的资格;从康家得见,尤其有证据的力量。它确证了廖平所称“余以《知圣篇》示之”,是信而有征的。
但是也有学者不信此明据,如房德邻辨道:
但这一稿本的内容、写作时间等情况却不得而知,因此无法作进一步讨论。我认为,如果康有为确曾保存一部廖平的《知圣篇》的稿本,那么这一稿本的写作时间也不会早于一八九四年。[27](P26)
上引钱书明确地说“今藏康家,则颇多孔子改制说”的为“原书稿本”,遇到这种关节之处,笔者只能坦率地说,我们与其相信房氏的臆度之辞,不如相信顾颉刚、钱穆两位先贤的判断。顾颉刚于康死后曾被敦请参订康氏遗文[16](P549-550),又曾经人联系得识康有为之女康同璧,深度介入康氏未刋著述如《我史》等的整理工作[28](P5-9),他对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极为了解也深受其影响;钱、顾又均为严谨的大学者,故此说深可信据。我们之所以作如此之断案,不仅还有下文将要详细讨论的内证,而且也因为我们发现房德邻恰恰误于廖平本人晚出演绎而成的谬说,做了很不恰当的推论,反而质疑于《经话甲编》首揭之“余以《知圣篇》示之”这一基本事实。房氏说云:
按这种说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受《知圣篇》影响而成。这显然是错误的。众所周知,《知圣篇》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内容相近,而与《新学伪经考》无关。《新学伪经考》与廖平的《辟刘篇》(刊行时改名《古学考》)内容相近,而廖平却从未说明他是何时把《辟刘篇》交与康有为的。[29](P89)
我们先说房氏的可取之处,他指出“廖平却从未说明他是何时把《辟刘篇》交与康有为的”,这是对的。我们更要指出,廖平很可能或者未完结此篇,或者根本就没把《辟刘篇》带到广州。上引《井研艺文志》及《自跋》等津津乐道于《知圣篇》之钞本流传之广,而且指实是在广州。但是见在廖氏文献,关于《辟刘篇》之流传毫无类似之记载。与对《知圣篇》的提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井研艺文志》录“《古学考》一卷(附《两汉学案》二卷)廖平尊经刊本”,提要云:“是书初名《辟刘编》,末附《周礼删刘》,皆(廖)平信今驳古之说。”[23](P1240)未提钞本之事。所谓“初名”,当指《辟刘篇》为《古学考》之初稿。所以廖宗泽所编年谱云“又《古学考》即《辟刘篇》”[14](P478),当均指此而言。后又作了很大的修改,所以年谱于光绪二十年(1894)下云:“将《辟刘编》改定为《古学考》。……则此册之非《辟刘编》之旧,非仅易名而已。”[14](P504)我们希望学者、读者诸君注意到此等重要的事实,不要有意无意地将两者混为一谈,或明知不同,而仍要妄引后者任意推度前者。
对本案来说,重要的是《知圣篇》(又名《知圣编》)与《辟刘篇》(又名《辟刘编》)的著述时间与下落。廖平《〈知圣篇〉自序》落款云:
光绪戊子季冬,四益主人识于黄陵峡舟次。[8](P323)
廖宗泽编廖平年谱云:
《知圣篇·序》称戊子季冬作于黄陵峡舟次。[14](P477)
廖宗泽并将“两篇”之完“成”系于戊子(1888):
成《知圣篇》一卷,附《孔子作六艺考》一卷,《辟刘篇》一卷,《周礼删刘》一卷,(《井研志·艺文四》)……[14](P477-478)
今检《井研艺文志》之《知圣篇》提要云:
(廖)平初作《今古说》(当指《今古学考》,引者按),丙戌(1886年)以后乃知古学新出,非旧法,于是分作二编,言古学者曰《辟刘》,言今学者曰《知圣》,取《孟子》“宰我、子贡知(即“智”字,引者按)足以知圣”之义。[23](P1238)
《志》中均并未出示著述年月。是知廖宗泽盖据《知圣篇·序》,混合《序》与正文,并牵合《知圣篇》与《辟刘篇》加以推论所得。
我们认为《〈知圣篇〉自序》与《知圣篇》正文当分别而观;《辟刘篇》与《知圣篇》亦当分别而观。
我们据上引《知圣篇·自跋》,认为《知圣篇》草创“作”起于“戊子(1888年)”,源本于“纂辑同学课艺”[8](P376)。据《〈知圣篇〉自序》落款,其《自序》作于“光绪戊子季冬”。再据《经话甲编》之卷二称:“光绪戊子季冬分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篇》,古学为《辟刘篇》。”更据《经话甲编》之卷一称“(俞樾)先生不以为然,曰:‘俟书成再议。’”(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14](P486)廖平与俞樾苏州之会时),综合而观,戊子(1888)已经有分篇草创之事,至戊子季冬,《〈知圣篇〉自序》已成于“黄陵峡舟次”,胸有成竹,而未展布成篇,至于“两篇”正文至廖俞之会时均未完成。再据《经话甲编》之卷一称“余以《知圣篇》示之”、《知圣篇·自跋》称“在广雅时传钞颇多。……庚子(1990)于射洪得杨绚卿茂才己丑(1889)从广雅钞本”[8](P376),及顾颉刚、钱穆两先贤之旁证,我们认定:《知圣篇》于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之后数月,一直在紧锣密鼓写作中,至廖平来广州之前后,尤其到“己、庚冬春之际”[3](P644),即1889年冬1890年春之际(1889-1890)初晤于广雅书局时,已经完成,且有钞本流传,并给康有为过目,引发激烈讨论,从而对康有为产生强烈的影响。
至于《辟刘篇》,亦发意草创于戊子(1888),它在廖、俞苏州之会时,尚未成篇;及廖、康羊城之会时,或未完成,或有成稿而未带在身边,所以无有《知圣篇》那般携带至广州乃至广为传钞之事,更不可能有让康有为寓目之事。康家存有《知圣篇》而不是《辟刘篇》,这绝不是巧合偶然的事!至于它到底成于何时或是否真正完成,今无从查考,而它的下落是很清楚的。廖平曾有《上南皮师相论学书》[注]此信似应系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冬。与这封信相关而稍前廖平有《与宋芸子论学书》,编校者云:“此书录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眉批:‘此似当移丁酉(1897年)秋。’巴蜀本亦节录此书,系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十月,据移。”廖宗泽撰、杨世文编校:《六译先生年谱》,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5·附录:六译先生年谱》,第523页。我以为不如从最初所系以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为妥。因为这两封信情事时间均相接,上引张之洞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七月致江标的函电已经对“素王改制”之说深为防范,若系于此年(光绪二十三年),张致廖的信中不可能不涉及此类极具政治敏感性的重大话题,所以不如将系年上挪为是,即廖致宋、张两书均在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李伏伽撰《六译先生年谱补遗》均将廖氏至宋、张之函系于丁酉(1897年),均不确。参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54-55页;李伏伽撰、杨世文校点:《六译先生年谱补遗》,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5·附录:六译先生年谱补遗》,第700-708页。:
至于攻驳《周礼》一节,学宜专务自守,不尚攻击。如今、古两涂(即“途”字,引者按),学派别乎两汉,专书成于洨长(指东汉许慎所著《五经异义》,引者按)。受业初撰《学考》(指《今古学考》,引者按),不分从违;见智见仁,各随所好;不是古非今,亦不信今蔑古。此书初无流弊,现在通行,可不必改议。惟《攻刘篇》专攻《周礼》,此书见未刊刻(“见”即“现”字,引者按),即将原稿毁消。[11](P567)
是知《辟刘篇》又可称“《攻刘篇》”,确有“原稿”(廖平无缘跟恩师说谎),只是“见未刊刻”,廖平迫于张之洞的压力,偷偷将其“毁消”了,所以神龙见首不见尾,后人是很难获悉其踪影的。
张之洞真是大清国季世意识形态的警察总长,他的暗探密布朝野,威逼利诱种种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不仅舆论界的风吹草动尽在掌握之中,自己门生弟子的思想学说亦决不能跳出本人所划定之圈外。廖平之受其挟制,不过是个小小的例子而已。不成想,这么一来,实在也是使得本案变得更为扑朔迷离的一个造因了!
我们在这里,又要涉及梁启超指责廖平受张之洞贿逼一案,这就不能不追溯梁任公对廖、康学术交涉的整体评判。康有为对于自己通过羊城之会等受廖平之说之事,先是绝口不提故作沉默,再则矢口否认。其徒梁启超则表现了不同的风度,不为师讳,屡道乃师所受廖平影响之迹。
先是于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一(1904年12月7日)[注]刊发日期,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3论著3》,第14页。,梁启超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第八章“近世之学术”第三节“最近世”中,先推重王闿运师徒尤其是廖平之贡献云:
而湘潭王壬秋(闿运。)、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平。)集其大成。王氏遍注群经,不龂龂于攻古文,而不得不推为今学大师。盖王氏以《公羊》说六经,《公羊》实今学中坚也。廖氏受师说而附益之,著书乃及百种,可谓不惮烦。(其门人某著有《廖氏经学丛书百种解题》。又廖所著书其目皆见于光绪《井研志》。)而其说亦屡变,初言古文为周公,今文为孔子;次言今文为孔之真,古文为刘之伪;最后乃言今文为小统,古文为大统。其最后说,则戊戌以后,惧祸而支离之也。蚤岁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晚节则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至乃牵合附会,摭拾六经字面上碎文只义,以比附泰西之译语,至不足道。虽然,固集数十年来今学之大成者,好学深思之誉,不能没也。[25](P100)
梁启超既以“集大成”推王、廖,尤其是廖,复以乃师康有为治“今学”渊源于廖平云:
吾师南海康先生,少从学于同县朱子襄先生。(次琦。)朱先生讲陆王学于举世不讲之日,而尤好言历史法制得失,其治经则综揉汉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25](P100)
铺垫既毕,梁氏揭示其师之贡献云:“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此南海之言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并高度评价其师之功在“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涂径而已。”[25](P100-101)我们且不论梁氏对乃师之推誉是否有过情之处,但是他断言“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于井研,不可诬也”,认为康有为之走上今文经学路线乃启途于廖平而非得自朱次琦,确为秉公识大之论;其所谓“不可诬也”之强调,实有批评康有为隐“诬”事实的意味,非常难得;他并不拘泥于廖康羊城之会为说(甚至未提及),也是值得注意之处。
近十六年后,1920年11月15日起,梁启超刊发《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后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注]刊发日期,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10论著10》,第212页。,重论此事。为说略有变动,“集大成”之评判归于康有为,而追溯其师渊源于廖平,更为详细:
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平,王闿运弟子。……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26](P77)
梁启超重申“不可诬也”之议,盖其深悉康有为与廖平学术交往始末,如本文所阐释者,乃重出此持平之论,并举出康氏早年著述“《政学通议》”(应为“《教学通义》”)以证其说。因缘梁氏作为康氏弟子的身份极为敏感,所论述又大有关系乎廖、康交涉公案,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有康有为早期手稿《教学通义》整理面世,学术界讨论颇为热烈,梁氏所论确为本案,包括廖、康羊城之会公案以及笔者所称由此所涉及之“后案”的重要侧面,非常值得讨论。明乎此,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探讨廖平思想对康有为的影响。
首先,梁启超的康氏弟子身份,确很重要。以这种身份而能秉公而断,是很值得尊敬的。
以康有为那种死不认账的态度,加上廖平之学术见解屡变而不知所终的性格,非有梁启超这样的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不知情者,尤其是后学很难得其真相的。所以廖宗泽等廖门人士不得不据此为说,像钱穆那样与两造均无瓜葛之学者也不能不据此为说。但是廖门人士只接受其中有利于廖平之论述,过此而反攻梁氏,则颇失公允。若廖宗泽《先王考府君行述》云:
即张文襄公为最初识拔先祖之人,每有成书,皆先寄之。二变以后,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为言,盖虽文襄亦有越轨之叹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谓受文襄贿逼,复著书自驳,观此可知其诬。(自小大之说,以前目为伪经之《周礼》、《左氏》皆为瑰宝,梁所见囿于今文家,故有此语。)[23](P916)
蒙默竟云:
故梁氏用此“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拙劣伎俩,冀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以挽回半边脸面;于后更捏造事实、栽赃诬陷。康氏“始终不一辨”,以犹知自爱,而梁氏此举则完全丧失一个读书人品德,而暴露出其政客面目。然而,君子固可欺之以其方,但难罔以非其道也。[30](P20)
又云:
宾四先生(钱穆)所记,与事大合,虽然,尚未能识破梁氏为说之包藏祸心也。[30](P18)
今按:梁氏“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26](P86),其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时早已不再“囿于今文家”,廖宗泽之说殊为武断,可谓典型的“囿于”为尊亲者讳而为此说者也;至蒙默竟谅解康有为“犹知自爱”,甘受其“欺”,反诬梁启超为“政客面目”、为“包藏祸心”,真是倒置之见!梁氏有时诚会表现出“政客面目”,但是在这件事上,真是秉公执法无所偏私(大节颇可称述)。
梁启超不仅身份特殊,所下断语亦颇有分寸。如他说“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于井研”,盖就所谓“家法”而论;又说乃师“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而未具体指实为哪一部书,其实比廖平自己以及后学穿凿附会之说都为稳妥。尤其是他举出康有为早期著述《教学通义》为证,以明乃师深受廖平影响而有思想大变迁之轨迹,可谓深切著明。这是我们后文要重点讨论的。
至于所谓“受文襄贿逼,复著书自驳”一节,我们只要一检廖氏《上南皮师相论学书》之曲意迎合,以至于将“专攻《周礼》”之“《攻刘篇》”(即《辟刘篇》)“原稿销毁”,致使自己与康有为的交涉案情大为拖累,廖氏之维护者们必谓无此等事,其谁信之?维护者又牵合廖氏之“四变”、“五变”、“六变”为说,以为必自变之,何不惮烦[注]参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第54-55页;李伏伽撰、杨世文校点:《六译先生年谱补遗》,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5·附录:六译先生年谱补遗》,第707-708页。?好像世间真有若是怪变之真知灼见者!论者又好引章太炎之《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为说,章氏所撰之铭揭示了廖氏之经学素养及儒行皆为康氏所不及,可为定评,其他不足论也。
我们既将《辟刘篇》排除,事实更清楚了。这样来考察,从“祖述”的观点看,《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其实均“祖述”自《知圣篇》及相关“谈论”!廖平在《孔子改制考》出版之后调整厘定的所谓“《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说法,是以思想上的相近相通而混淆了实际交往上的“祖述”,在涉及《知圣篇》方面确有根据,在涉及《辟刘篇》方面却是演绎过度,从对康有为死不认账的反应看是防卫过当,仅仅就《辟刘篇》来说,颇有故入人罪的偏颇。而廖平这一说法的影响是极大的。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五册《最后一页》载有《钱玄同先生来信》,钱氏对廖、康作了这样的比较评论:
晚清至今,分析今古文者有数家,弟以为莫善于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莫不善于廖平之《今古学考》,因为前者是辨伪,后者是析“学”。[31]
钱玄同厚此薄彼,自非公允之论。我们认为在经学今古文问题上,大体说来,廖、康两无足取;但是钱氏以为,在学术风格上两人之间有“辨伪”与“析学”之异,则确有所见。我们看到在梳理界定他本人与康有为的学术关系上,廖平沿袭了其一贯的学术风格,将《孔子改制考》与《知圣篇》、《新学伪经考》与《辟刘篇》一一对应,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析学”,看起来很有理致而实际颇乖史实。房德邻质疑说:“众所周知,《知圣篇》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内容相近,而与《新学伪经考》无关。《新学伪经考》与廖平的《辟刘篇》(刊行时改名《古学考》)内容相近。”[29](P89)其中的推论逻辑,说穿了,就是原本廖平《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之一一对应而不可能有其他渊源关系之“祖述”说。此前的先贤若钱穆云:“长素书继《新学伪经考》而成者,有《孔子改制考》,亦季平之绪论,季平所谓《伪经考》本之《辟刘》,《改制考》本之《知圣》也。”[3](P652)钱氏谓康有为“两考”皆本原于“季平之绪论”,甚是;然犹惑于廖平所谓“两考”与“两篇”一一对应分别“祖述”之不实之辞也[注]不仅如此,由于钱穆援引了廖平的“祖述”说,而未注明出处(即《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45页),后学颇多误以为出于《经话甲编》而不知核查,从而遗憾地丧失了考察廖说变迁之迹的契机,如李耀仙《廖季平的〈古学考〉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5期),就认为廖氏此说出于《经话甲编》卷一,盖误用钱书而未检出处。其他学者尚多有之,甚至明引据钱书,而不加复核,殊不可晓。为省篇幅,不具引。。杨向奎甚至说“《知圣篇》为孔子改制事,此事乃今文学派旧说,康氏何事而驳斥之?不久《新学伪经考》成,此乃类于《辟刘篇》而与《知圣篇》不相涉。那么《知圣篇》应当是《辟刘篇》”[32](P352),尤为敷衍廖平后出演绎而成之谬说,而并疑及其早出尚近情之论也。
进而言之,后学之所以纷纷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渊源(以晚出之廖氏《考》、《篇》为根据去推度《辟刘》、《知圣》“两篇”对康氏“两考”的影响),如笔者前所引述之种种,一方面固然因缘于无视版本学上的基本戒律,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未能突破廖平本人给后人设置的思想牢笼吧!思辨的魅力有时候会产生审美的壮观(一一对应的整齐,就是一种美),具有媚惑人误导人的力量,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有为深受其炫惑,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想进一步指出,连廖平本人都从未说过的所谓在羊城之会廖平将“两篇”一并出示给康有为过目的说法,归根到底,也是从此一一对应的“祖述”说衍生出来的。今考此说之最初面世,来自廖宗泽。《中国学报》(重庆)第一卷第一期(1943)刊载有廖宗泽《先王考府君行述》,郑重述及廖康学术交涉云:
初,康长素得先祖《今古学考》,引为知己。先祖己丑会试后,谒文襄(张之洞)于广东。长素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先祖以《知圣编》、《辟刘编》示之。别后致书数千言,斥为好名鹜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先祖以为此事要当面晓耳。后访之安徽会馆,谈论移晷,顿释前疑。未幾而康氏《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告成,盖即就《辟刘编》、《知圣编》而引申之者也。梁氏(梁启超)谓其师见廖氏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者,指此。[注]廖宗泽:《先王考府君行述》,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6·附录:传记与评论》,第916页;刊出时间与期刊,见第920页。
这是笔者所见最早的所谓廖平“以《知圣编》、《辟刘编》示之”康有为的说法,与《经话甲篇》“余以《知圣篇》示之”的近时近情之说不合,冒然多出“《辟刘编》(《辟刘篇》)”,与我们的考察更不合,是典型的“语增”敷衍演绎之说(王充《论衡》,有《语增篇》)。同一文又云:“此期(指廖平的经学二变,引者按)在戊子以后,约十年,所著以《辟刘编》、《知圣编》为纲要,尊今抑古。”[23](P914)我们认为均本于《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中之“二变”论述为说。后说大体可从,而前者“以《知圣编》、《辟刘编》示之”云云,则推度过当,显为失实。因为廖、康之间“祖述”关系与羊城之会“示之”文稿大有分辨,因缘“祖述”自己的经学二变思想,牵合自己的“两篇”犹可勉强附会说之,因有义理上的相通性,实际不过是分篇而论有思想上的各自近似性。若“示之”《知圣篇》、《辟刘篇》(“两篇”)文稿云云,徒然增出之“《辟刘编》(《辟刘篇》)”,如没有彼此相接转手交稿之事实,则决不能妄说也。廖平本人确也从无此说,廖宗泽如此云云,为尊亲者添油加醋的说法,殊失于诬枉。同理,所谓“梁氏(梁启超)谓其师见廖氏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者,指此”,若必指“以《知圣编》、《辟刘编》示之”云云,则亦为臆度无根之谈也。
无奈,“祖述”附和之者纷纷然。稍早有向楚,《文学集刊》(四川大学)一九四六年第二期载其《廖平》一文,云:
自己丑(一八八九)试礼部后,谒之洞于广州。康有为与黄季度同访平于广雅书局,谈竟夕,并以《辟刘篇》、《知圣篇》示之。未幾,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告成,盖《伪经考》本之《辟刘》,《改制考》本之《知圣》也。梁启超谓其师之学说原转变于蜀人廖氏,尽弃其旧说者,指此。[注]向楚:《廖平》,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6·附录:传记与评论》,第942-943页;刊出时间与期刊,见第956页。
文中亦有“并以《辟刘篇》、《知圣篇》示之”的说法(仅有“篇”与“编”用辞之异,以及前后叙述次序之不同),我们不必辞费,比观上下之文,读者自可明其源流矣。所谓“谈竟夕”,则又将在安徽会馆之“谈论移晷”混套在广雅书局之初晤上了。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从中亦可概见廖平所谓“《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云云之说的统制力了!
廖宗泽编著之《六译先生年谱》颇为廖平研究者所本,尤为川籍后学所重,他将廖康羊城之会仅仅系在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述此事亦云:
南海康有为于沈子豐处得先生《今古学考》,引为知己。至是,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先生以《知圣编》、《辟刘编》示之。……康氏乃尽弃其旧学而为先生之学焉。(《经话》甲一,页五十五;《知圣编》上,页四十八;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三。《经话》甲编二卷三十页云:“庚寅(1890),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合。逾年,《伪经考》出。”“庚寅”当系“己丑”之误。——此为廖宗泽原注,引者按)[14](P486-487)
廖宗泽出示之文献根据,若《经话》甲编、《知圣编》(《知圣篇》)、《清代学术概论》均无有“以《知圣编》、《辟刘编》示之”或“以《知圣篇》、《辟刘篇》示之”的叙述,所谓除了《知圣篇》外廖平一并示康有为以《辟刘篇》的说法,实出于廖宗泽的臆度。当然,我们认为总根子也可以溯源到《四益馆经学四变记》的分别“祖述”说。另外,廖宗泽又混淆了廖、康己丑冬之初晤与庚寅春之再会,一概将此事系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不从乃祖正确之说,而将系年提前,一如前述误将乃祖“两篇”完成之年提前,均失之于武断也。此例既明,则所谓“以《知圣编》、《辟刘编》示之”(廖宗泽)或“并以《辟刘篇》、《知圣篇》示之”(向楚)等等诸如此类捕风捉影之谈的风行,就不难理解了。
上述虚说,廖幼平所编《廖季平年谱》于光绪十五年(1889)谱承袭之云:
时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学舍,先生以《知圣编》、《辟刘编》示之。[33](P19)
《廖季平年谱》以廖平有两编并示康氏之说,盖亦本廖宗泽而来,本不可靠;而更附会以“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学舍”之“时”。须知,康有为于“光绪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年)三十四岁。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34](P19),如是,则敷衍之说,错上加错,益无伦次矣! 而李耀仙竟谓,“根据廖平的自述,季平曾于一八八九年底将所著的两篇给有为看过,还相互讨论书中的内容,并有旁人见证”[7](P6)。黄开国近来还说:
陈其泰先生在《清代公羊学》中否定康有为看到过廖平的“两篇”,认为廖平此时的“两篇”并未成书,理由是廖平没有将“两篇”给俞樾、张之洞等人看(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此为黄氏原注,引者按),从廖宗泽的《廖平年谱》看,陈其泰先生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廖平来广州后,《知圣篇》、《辟刘篇》被广为传抄,形成了一定社会影响,康有为从北京回到广州后也有所闻,这可能是康有为首先拜会廖平的又一个原因。[35](P671-673)
论者不能严肃审核根据、分别考察,如此牵强附会,意气相搏,何所底止!本文明例于此,不再多引了。
(二)康有为百般隐讳而廖平早已淡忘的交流秘籍——稿本《知圣篇》主旨及“谈论”要义疏证
如上文所述,《四益馆经学四变记》所谓“《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的说法,乃是廖平激于康有为死不认账的防卫过当之论。此论确有根据之处,我们已经阐明。而其牵强附会之处,即它对康有为的最大冤枉,是廖氏后人后学本廖说而演绎出了所谓廖、康羊城之会康氏亦得见《辟刘篇》的谬论。话说回来,这其实是一柄双刃剑,刺到了对方同时也伤着了自己,任何超出实事求是界限之说的结果效验都只能是如此。这一说法的后遗症是模糊了当年羊城之会的讨论、争辩、接受都围绕原稿《知圣篇》来展开这一事实。所以,稿本《知圣篇》的主旨,是必须重点探讨的。为什么只消围绕《知圣篇》的讨论就能够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彻底的解答。只有旁证与内证结合起来才能获致切实的结论。所以,本篇上下文的讨论,是互相支持的,事实上笔者也不能确忆内外何者先获或如何回环往复之曲折行迹了。我们非常希望读者将下文内容与上文的讨论结合参观,本文之所以最后论述及此,完全出于叙述之方便,此点,谨望识者明而断之。
这桩未了的公案是如此牵动人心,以至于,88岁高龄的老先生蒙默,先引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说有为学术渊源出自井研,有为之思想受影响于井研为“不可诬也”,然后激动地批评道:“然梁氏始终不愿明白具体道出影响于有为者究系何种思想!”[30](P18)老先生对先贤梁任公之评论是有失公允的(详前文),但是他老骥伏枥赤身肉搏的正是这个严肃又久而未决的问题,这个大公案,却很值得尊敬,这也正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他自己或用过早的《今古学考》、或用过晚的《古学考》来推说,于核心文献稿本《知圣篇》反而语焉不详,既犯有时贤共有的不顾及版本前后的通病,也就不可能了断此案。但其志可嘉,应激励后学另辟蹊径攻坚克难。我们认为欲结此案,并非无路可通,还是要回到廖平早期文献或与廖平密切相关的反映其当时思想的文献中,尤其是较廖康羊城之会稍前的文献中去梳理钩沉。
第一重要的,是《〈知圣篇〉自序》。汤志钧说:“《知圣篇》、《辟刘篇》撰于一八八八年”,虽失之于笼统,但是他的注中有“《知圣篇》自序也写于光绪戊子季冬。按戊子为光绪十四年,即公元一八八八年,较康著《新学伪经考》早三年”[36](P41),却是重要的线索,引起笔者对《〈知圣篇〉自序》的重视。黄开国也提到:“今本《知圣篇》还保留有1888年冬天,廖平赴京途中在黄陵所作的序言。”[37](P74)这些先进的研究,都让我们引起对此《自序》的高度重视。可惜的是,《自序》本身未能被加以充分的利用,尤其是运用到此公案的审查上,甚至连引述都鲜见之。其实,此《〈知圣篇〉自序》的内容非常重要,值得全引如下:
测天之术,古有三家,秦汉以来,惟传浑、盖。西人创为地动天虚之说,学者不能难之。或者推本其术,以为古之宣夜。征之纬、子,信中国遗法也。六艺之学,原有本真。自微言绝息,异端蜂起,以伪作真,羲辔失驭,妖雾漫空,幽幽千年,积迷不悟,悲夫!援经测圣,正如以管窥天,苟有表见,无妨更端,踵事增华,或可收效锥管。若以重光古法,功同谈天,则力小任重,事方伊始,一知半解,何敢谓然。独是“既竭吾才”,不能自罢,移山填海,区区苦心,当亦为识者所曲谅焉。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年)季冬,四益主人识于黄陵峡舟次。[注]舒大刚点校、李耀仙审订:《知圣篇》,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第173页;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群经类:知圣篇》,第323页。
这篇《自序》以“测天之术”为喻,讲的是其经学二变的经学观即其孔圣观。所谓“六艺之学,原有本真”,是指以孔子为宗的真“今学”。而“援经测圣”之“圣”,即是“微言”之宗的孔子,也只是孔子,不是别人,而“六艺”群经皆为孔“圣”所制。所谓“异端蜂起,以伪作真,羲辔失驭,妖雾漫空,幽幽千年,积迷不悟”,当指刘歆作伪之“古学”,以伪乱真,使得后世不得真经“微言”。如今廖平自己矢志意欲“重光”的“古法”,其实就是孔圣“今学”。
此序言简意赅,得下文我们将要参证的材料而益明。这里透露的最重要的信息,我们认为就是:《知圣篇》不能排空“辟刘”之议。事实上,我们将看到,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知圣篇》甚至不能不讲到“辟刘”之议,“辟刘”甚至正是“知圣”的必然前提。人们太受制于廖平“《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云云之说了,以至于对此一大关节不能有正确的把握!而手持一篇《知圣篇》的廖平,来在广州,纵然无有《辟刘篇》随身携至(或未完编),他会避而不谈血肉相连的“辟刘之议”吗?更何待言!
第二,见在文献,与《〈知圣篇〉自序》时间相接,能够参证廖平在廖康羊城会晤之稍早思想动态的,有光绪十四年(1888)廖平学友江瀚(叔海)与廖氏论《今古学考》的函件。
有关于此,廖宗泽撰《六译先生年谱》于那年只记下“江叔海致书,论《今古学考》”十个字[14](P477),其实,那封论学之书是非常重要的。
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初刊于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重刻本,这一系统的版本,以“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的金陵状元阁本较早”[注]王猛点校:《续古文辞类纂》之“点校说明”,[清]黎庶昌著,黎铎、龙先绪点校:《黎庶昌全集6》,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728页。,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一日(2月8日)江氏“取黎莼丈《续古文辞类纂》读之,其重刻本将鄙人与王益吾祭酒、王晋卿大令文增入,其板尚在金陵也”[38](P169),说的就是这封论学的书信。廖平于1913年“癸丑夏六月初二日”作《答江叔海论今古学考书(并〈序〉)》才回复老友的商榷质疑。答辞颇与为其时“初成”的经学《四变记》相映证有关,若文中云“前呈《四变记》,即作为二次战书可也”[9](P643)云云,申其得意之情、屡变之旨,本不足贵。惟廖平《序》称“叔海作此书在二十五年之前”、答书所谓“戊子大作”[9](P636-637),廖宗泽撰《六译先生年谱》盖据之系于光绪十四年(1888)。今考江书内涵,准确反映廖平《今古学考》之后,廖、康羊城之会稍前之学术宗旨,原书比答书可贵者此也,与本案有直接之关系者,亦以此也。
廖平《序》称“今年春于成都得《学报》第二册,再读校改之本,二十年老友规过订非,一再刊布”、答书又称“既刊文选,又改登报章”云云[9](P636-637),似于老友的不惮烦颇有微词,其实很可能是廖氏过度敏感了,大概不过是江氏见黎本“刻写颠倒错乱、亟应改正”[38](P268)而然。今以江瀚《慎所立斋文集》本以校黎本,确有少数夺文,很少的误字,若干通用字,而文辞之前后错置则甚为严重,颇影响阅读。全篇大体则未作改动,确是原始文本。我们参考了黎本,而以《慎所立斋文集》为据[39](P142-150),依次述其所见廖平当年之见解如下:
信中称“阔别三年”[39](P142),则江氏于廖平思想不能尽悉,所以是书以“论《今古学考》”为题名,而其实多《今古学考》刊出之后廖氏的见解,然毕竟是老友,还是有渠道获知其学术进境的。
“足下以去圣遐远,大义久乖,慨欲继绝扶微,存真刬伪。”[39](P143)这当是就廖平的尊真今学刬伪古学而说的,确可谓其经学二变之总纲。
“今足下为《今古学考》,有孔子晚年定论之说。”[39](P144)此为述廖氏经学初变时见解,可存而不论。
“足下崇今摈古,果将何以适从哉?”[39](P144)“崇今摈古”,可为廖氏经学二变主旨之准确概括。
“足下谓《王制》为今学之祖”[39](P145),此为廖氏于经学初变时就已有的见解,可存而不论。
“足下谓史公不见《左传》,而《周礼》为莽歆伪书。”[39](P146)这一点非常重要,廖平较康有为早就认为,《左传》、《周礼》为新学伪经“莽歆伪书”,仅凭这一句话就可以给廖康交涉之隐衷定案了!
“至于力攻郑君,论亦非是。”[39](P148)此为廖氏于经学初变时就已有的见解,可存而不论。
江瀚之总结陈词云:
至决别群经,悉还其旧,诚一大快事。虽然,吾生也晚,冥冥二千余载,以迄于兹,何所承受取信?虽欲私行金货,定兰台桼书经字,以合私文,且不可得。徒支离变乱,而卒无益于圣经,奚取纷纷为也!?[39](P150)
江氏对廖平之恣意说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真可谓是廖氏的诤友。我们只采其与本案直接相关的部分;廖平的答书亦复如是,其直接涉及本案的有云:
足下谓我崇今摈古,以《周礼》、《左传》为俗学云云。案,《学考》平分今古,并无此说,此乃二变康长素所发明者,非原书所有。旧说已改,见于《四变记》中。足下以汉师同为诵法洙泗,舍周公而专属孔子,与扶苏谏始皇同,专主孔子,不及周公。此说乃与二变尊今抑古,把臂入林,与郑学大相反对者也。[9](P640)
廖平在多年以后还是觉得有答复江书的必要,原因似不单纯。但是他说“足下谓我崇今摈古,以《周礼》、《左传》为俗学云云。……此乃二变康长素所发明者”,一言以蔽之,此即为康有为所攘窃祖述者,可谓确有其事,今得江书参证而益明也。而与知情故交,叙旧至此,恐颇有我们外人难以把捉的莫名畅快吧。但是他说,如他那般对孔子的“诵法”,与江瀚也能“把臂入林”,却未必然。事实是,在这一点上,与他正真能够“把臂入林”的,也只有康有为!
第三,廖平的另一位挚交学友德阳刘子雄(介卿)[注]参见廖宗泽撰、杨世文编校:《六译先生年谱》,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5·附录:六译先生年谱》,第458页;廖平撰、舒大刚校点:《知圣篇》,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群经类:知圣篇》,第359页。等等。廖平本人以刘子雄字“介卿”,而其女婿李伏伽撰《六译先生年谱补遗》则以刘子雄字“健卿”(详下文),不同,待考。的日记与《〈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亦复时间相接,意旨密合,内容丰富,是更为重要的参证文件。于此,研究先进如廖幼平、黄开国、房德邻等已知重视利用,至于说到助证本案,则犹颇有待发之覆。
该日记,笔者无缘得见稿本,今于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及其夫婿李伏伽撰《六译先生年谱补遗》中所引一鳞半爪来看,已至为可宝。廖幼平编《年谱》卷三述廖平之经学“二变”有云:
刘子雄丁亥(1887)八月日记谓见先生作《续今古学考》自驳旧说,以《周礼》、《左传》为伪,则尊今抑古实始丁亥(1887)。丙午(1906)本《四变记》谓始戊子(1888),盖谓《辟刘》、《知圣》成书之年耳。[33](P39)
贴近当初时空的日记毕竟比回忆述记可靠得多了。廖幼平据此,既不从廖平本人的《四变记》,亦不从廖宗泽撰《六译先生年谱》原作“起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及其后眉批“移丙戌(1886年)”之说[14](P464),而将廖平之经学二变起始之年定在丁亥(1887)——“尊今抑古实始丁亥(1887)”,这是信而可从的。而所谓“戊子(1888),盖谓《辟刘》、《知圣》成书之年耳”,与前引廖宗泽说相同,是将起草之年当完成之年,则不确。戊子(1888)当为“两篇”草创起作之年。此点前文已经论及,今得刘氏日记之参证而益明也。
房德邻进而根据《廖季平年谱》所录刘子雄日记,对廖平的“两篇”完成时间作了推测,作为其主张康有为未见“两篇”中的任何一篇(因为均未完成),而只受“辟刘之议”即“谈论”影响之说的核心根据。这是本文必须辨析的,所以详引如下,作为讨论的基础:
据他在尊经书院的同事、好友刘子雄的日记载:廖于一八八七年九月(丁亥八月)作《续今古学考》,自驳《今古学考》中的观点,谓“周制全不可考,概为孔子新制。《周礼》固为伪托,即左氏之言《周礼》者,亦推例而得……”又谓“文王所演之《易》,即是孔子《系辞》。”(转引自廖幼平:《廖季平年谱》,第39、42页。——此为房氏原注,引者按)这说明廖平主张尊今抑古时,所写的是《续今古学考》,而不是《辟刘篇》和《知圣篇》,很可能在写完《续今古学考》以后,廖平又进一步酝酿写作《辟刘篇》和《知圣篇》。刘子雄的《日记》中没有提到《辟刘篇》和《知圣篇》,刘卒于一八九O年十一月,这似可说明至一八九O年岁末廖尚未完成这两部书稿中的任何一部。[注]参见房德邻:《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第18-26页,引文见第19-20、60页。
廖平的经学二变,有一个过程。先作《续今古学考》,再分述为两篇,一为《知圣篇》一为《辟刘篇》,为事实所容有。从“刘子雄的《日记》中没有提到《辟刘篇》和《知圣篇》”(《廖季平年谱》记刘子雄事迹止于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33](P43),又详下文),而“光绪戊子(1888年)季冬”已经完成《〈知圣篇〉自序》来看,我们将《经话甲编》所云“戊子(1888)分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论古学为《辟刘》”,解读并确定戊子(1888)为作起之年而非完成之年,应是稳妥的。
廖、康羊城之会在1889年冬、1890春,房德邻认为“一八九O年岁末廖尚未完成这两部书稿中的任何一部”,此说殊为失实。房氏不知何所据而谓“刘卒于一八九O年十一月”?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光绪十四年(1888)谱中录云:“又庚寅(1890)端午前二日(廖平)自识云:‘……庶可以告亡友刘舍人也。’”[14](P479)所谓“亡友刘舍人”即刘子雄,据廖平之说可知,刘子雄于“庚寅(1890)端午”节之前已经亡故了,房氏所谓“刘卒于一八九O年十一月”,必误;又且,为房氏所引据的《廖季平年谱》,记刘子雄事迹止于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33](P43),于光绪十五年(1889)谱尾记曰:“十月,友人刘子雄卒于北京。”[33](P46)其夫婿李伏伽撰《六译先生年谱补遗》记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补叙云:
十月,刘子雄卒于北京,年三十二岁。子雄字健卿,德阳人,戊子(1888年)北闱举人,官内阁中书。与先生同住尊经盖十年,多所切磋。工词章,所著有《刘舍人集》及《日记》。(《日记》未刊。——此为李氏原注,引者按)[14](P690)
“《刘舍人集》及《日记》”,尤其是未刊之《日记》很重要,我们希望早日出版。据李、廖夫妇之说,房氏将刘子雄的卒年往后误挪了近一年。这样,刘氏若卒于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盖在康廖羊城之会之前,又不知他何时去的北京,无论如何,他已经不能紧密跟踪廖平著述的最新情报了。这样,房德邻从刘子雄这个侧面来论证“至一八九O年岁末廖尚未完成这两部书稿中的任何一部”,彻底失据。因而房氏所谓“影响”只限于“辟刘之议”之推论,亦不能成立。据我们的上文考证,《知圣篇》的完成,恰在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廖、俞苏州之会之后至光绪十五年(1889)冬廖、康广雅初晤之间。请读者将笔者此处之辨析与前文的讨论互参。
此误既消,我们就可以来深入解读刘子雄的日记了。刘子雄真是廖平的挚友,他的日记足以证明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代表著作中阐发的基本思想,廖平早已有之,它的新奇性、创造性已经惊骇到了他的朋友们,而廖平多年以后在与康有为争著作权(其实只是启发权)时反而淡忘了。
刘氏日记,记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四月六日:
(周)宇仁谓廖意在胜湘潭(指王闿运,引者按),始弃东汉之学求之西汉;又不合,乃弃西汉之学求之先秦诸子;又书不合,(“书”字等疑有讹文,引者按)势必至于疑经疑传,犹不能申其说,此多歧亡羊也。[14](P686)
廖平胆小而志大。在学术上争胜之心强烈,不要说受业之师王闿运欲力争超越之,即东汉经学大师若何休等亦不在话下,廖宗泽谱:“是年常与刘子雄过从,见则必谭经。一日先生谓刘曰:‘何氏以十七年注《公羊》,予以七年成《穀梁》,尚不逮其半。’”[14](P475)此亦非仅廖氏一人而然,一般好谈“今文”者多有此等风概。如廖氏所推崇的邵懿辰,丁晏就曾述邵氏自诩其《礼经通论》,“自谓天牖其衷,启二千年儒先未发之覆”[40](P416),所以像康有为也多有力翻 “二千年”陈案云云的豪言壮语,就很不奇怪了。廖氏之意欲学超王闿运,为本人所承认,廖幼平记其父语:“其意只在求实,非求胜人,但不能谓青不能胜蓝也。”[23](P994)颇可参证。
刘子雄所载周宇仁的看法,忠实地记录了廖平当时“始弃东汉之学求之西汉”、“乃弃西汉之学求之先秦诸子”拾级而上层层“复古解放”的治学路向,后为梁启超作了经典发挥的“以复古为解放”之说,在廖平那里可以找到先驱。
刘氏接下来的日记,就直接触及廖康羊城之会交涉公案的案底了:“(四月)十一日,刘子雄来谈,先生谓《周礼》当以王莽制参考。”这是将刘歆以降相传为周公之典的《周礼》归结为“王莽制”大论断的起点,是康有为大不满于廖平“攻新莽为好名”(见前引《致某人书》)的缘由与实质所在。“六月,成《〈王制〉、〈周礼〉凡例》,以《周礼》为刘歆伪作”,这同样是对《周礼》开刀,拿刘歆问罪。“(六月)初十日访刘子雄,论《左氏》作伪之迹甚悉。”这又是就《左传》而大发“辟刘之议”了。如此详悉,《辟刘篇》稿本之草案已经粗具规模了!这与前引江瀚所闻廖平“足下谓史公不见《左传》,而《周礼》为莽歆伪书”的见解严丝合缝。
廖平“辟刘”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系统。至“归井研,旋携子讳师慎至成都,十二月复归”,乃有这一年总结性的新创观点汇综如下:
作《续今古学考》自驳前说,谓“周制全不可考,概为孔子新制。《周礼》固为伪托,即《左氏》之言周礼者,亦推例而得,以《周礼》同《王制》者多,异者不过数条,又无师说,故知袭今学而作,即《国语》亦是今学。”又谓“文王所演之《易》,即是孔子《系辞》。”刘子雄见先生《续今古学考》,谓不似经生语。[注]以上刘子雄日记内容,均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第41-42页。标点略有调整。
正是以“辟刘之议”为前提,而有“知圣”之创说。图穷匕首现,前古所无、登峰造极的孔子超级圣明伟大之说,喷薄而出。
《今古学考》认为“《周礼》之书,疑是燕赵人在六国时因周礼不存,据己意,采简册摹仿为之者”[8](P74),已经不以《周礼》尽为周公之典,书出一年多后乃“自驳前说”,幡然大变。不仅将相传原为周公之典的《周礼》(康有为《教学通义》近此说),认定为非先秦之书,竟是刘歆伪作而服务于并归结为“王莽制”而非“周制”,即使《左传》中言及“周礼”(因书中亦多述周公之典、周公之制等)并为刘歆“伪托”(所谓“《左氏》作伪之迹甚悉”),廖平此时再将《王制》与《周礼》、《国语》比勘,同者多,异者少,则《周礼》、《国语》所述周制,皆为根据《王制》而修改,原以为属于古学的《周礼》、《国语》等其实大部分皆属于“今学”,今学在前,古学伪托改篡在后,如《周礼删刘》就是要将被刘歆伪托窜入的“周礼”剔除。所以说:“周制全不可考,概为孔子新制。”此即《井研艺文志》所谓“丙戌(1886年)以后乃知古学新出,非旧法”[23](P1238)之要害也。请读者一定要留心“全不可考”一词,以及这一非此即彼的“概”然判断的绝对性与震撼性。这就是前引张之洞《致长沙江学台(江标)》函电揭示的“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孔子所定治世之法,托名于二帝三王”——即(孔子)素王托古改制说——的缘起。
经此去伪存真,周公就遭大幅度的架空虚化,岂可与孔子伦比?不仅周公如此,连“文王所演之《易》”也统归于孔子。《今古学考》曾主“今经皆孔子所作,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8](P26),至此时,则张之洞所概括的“六经皆孔子所自造”之说,亦呼之欲出了!刘氏六月二日日记,载“廖译改之说坚持于心,视群经处处皆有译改”[14](P687)。须知群经皆为孔圣所翻译改制,为日后廖平持之终生的见解(廖氏本人后亦缘此而自号“六译”),早已经造胎于此了。孔子足以卑视文、周,超群圣,俟万世。廖平早有“素王”之说,意谓孔子预垂空文,就等万世之后来实现他的微言大义的。岂不是无限圣明伟大?尊孔而至于如此登峰造极、任性恣意,前古所无。中国近代尊孔之第一人,非廖平莫属。
凡此多为闻所未闻的新说,所以颇为朋友们所骇怪。因此“刘子雄见先生《续今古学考》”大为震惊,“谓不似经生语”。稍早的“润四月”间,刘氏与周仁宇、胡敬亭等学友,已经“皆不信廖说,以为飞行绝迹”;“六月”间刘氏以为“廖近来新说愈无忌惮”;“八月”间,刘氏以为廖“近日说太放肆”;“九月”间,刘氏与胡敬亭“谈”“言”及“廖经论多市井语”而周宇仁则认为廖的经说“言话近于以经为戏”[14](P686-687)。廖平日常相与论学的朋友们已经受不了他这样疯狂的经论经话了。
两年以后,当康有为与廖平在羊城会晤时,听到同样的话题,他会有什么反应呢?这一点,我们后来者已经非常清楚,从任何角度都可以说,真是迥异俗流!
四、余论:羊城之会对康有为的主要影响
那么,如蒙默强烈地质问的:廖平“影响于有为者究系何种思想”?我们的看法是,就羊城之会而论,让康有为受到震憾的主要有密切相关的两个观点:第一,“知圣”的创见,即孔子空前圣明伟大的观点,而且不是一般的圣明伟大,而是盖过周公(也盖过所有圣王)的圣明伟大,近乎创世者的圣明伟大;第二,将“古学”特别是《周礼》归为刘歆伪造,尤其是归结为“新莽”一朝的泛政治化解释方式。这两点,直接决定了升级版康有为“孔子改制”论的诞生。康有为“孔子改制”论的初级版本,见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早期文献,笔者一直认为是受常州公羊学派影响者;而很多学者认为是为康有为后来的今文经学思想改写窜入者或为抄袭廖平者,他们完全抹杀这两者的性质不同与内涵差别。
前引廖平大概作于1897年左右的《致某人书》,不管它有没有发出,确很重要,也是康、廖交涉的第一手资料。该函称康有为曾有“谓《今古学考》为至善”之言,《经话甲编》也说康氏将《今古学考》“引为知己”,这是可信的。相知的基础,从康有为那一方来说,在我们看来,就是《教学通义》中近乎平章周、孔的见解。否则如一些学者所谓一方一味只是勤于抄说,如学生之待尊师,哪里像廖平自己所描述两人之间的可以比拟为朱子与陆象山之类的学友关系呢?所谓“谓昔年之会,如邵、程也可,如朱、陆也可,如白虎、石渠亦可”。
在(1889-1890)“己、庚冬春之际”,康有为与廖平有过两次会晤,先是康携黄季度拜访廖于广雅书局,后是廖回访康于安徽会馆。此信廖先述羊城之会后得见康氏著述后的观感,谈及两人对《左传》的意见分歧,云“足下以《左》学列入新莽,则殊与鄙意相左”,在写信时,廖平已经持《左传》为今学,为群经之传,在“以《左传》归还今学,此一变也”[41](P1271)之后,此“鄙意”所以与“大著《伪经考》、《长兴学记》”中的见解“相左”,他完全淡忘了“以《左》学列入新莽”正是“昔年在广雅”时自己的见解而被康有为所攘窃者,此可由刘氏日记、江瀚书函而推得者也。所谓“《周礼》当以王莽制参考。”、“以《周礼》为刘歆伪作”、“《左氏》作伪之迹甚悉。”、“史公不见《左传》,而《周礼》为莽歆伪书。”不都是早就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著述之底稿打好了吗?
关键是羊城之会第一次的会晤及其后续:“昔年在广雅,足下投书相戒,谓《今古学考》为至善,以攻新莽为好名。”就很重要了,也是廖平所在必争的要害,这也是他采取倒叙法的苦衷。在廖康羊城之会的初晤(在广雅书局)中,廖平当确曾“以《知圣篇》示之”于康有为,康氏显然是见到了稿本《知圣篇》的,否则不会“投书相戒”(即上引《经话甲编》所谓“驰书相戒”)。若是如学者所说,仅仅耳闻“辟刘之议”之类,有不同意见,当场驳斥便可,如何更需书函讨论?很可能“攻新莽”云云,也是《知圣篇》中的内容,不必拘泥于《辟刘篇》为说,此据《〈知圣篇〉自序》可推得者也。但其中的观点却很是惊世骇俗,引起了比《今古学考》所产生的更大的波澜。其核心观点首先是孔子无限圣明伟大,如钱穆所述“原书稿本,今藏康家,则颇多孔子改制说。”间接之传述虽得史实之素地,毕竟有欠于详审。刘子雄等朋友们的惊骇,却是见证了廖平新说的初始反响。所以我们毫不奇怪,尚持《教学通义》见解,只是采纳了些许常州公羊学派平淡无奇的“孔子改制”说,而多少有点平章周、孔的意味,心目中其实周公远远尊于孔子(还是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为本的尊周公、尊《周礼》观念为主脑)的康有为,初悉廖说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
廖平记忆中康有为的指责:“以攻新莽为好名”,却一点也不错,足为明证。除了“《左》学”之外,主要是就《周礼》的见解而说的。这一句话正是康有为他即时反应的生动写照。我们看到《教学通义》虽有“《周礼》容有刘歆窜润”、“自变乱于汉歆”等说法,但是未见攻击“莽歆伪书”(语出前引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的,他还是将刘歆作为“汉歆”而非“新歆”。把“古学”尤其是《周礼》归入奸伪之朝“新莽”,对于尚持平章周、孔甚至周尊于孔的康有为来说(“谓《今古学考》为至善”),这样的解释太政治化也太污名化了,一开始接受不了(“以攻新莽为好名”),所以有致书批评之事。但是在第二次即安徽会馆的再晤畅谈交流讨论之下(“谈论移晷”)、反思之后就不同了。
将康有为征服的正是上述那一种非传统的孔子超级圣明伟大说。这种观念既不是诸如常州公羊学派之“素王改制”论所可比拟,亦非如《教学通义》所呈现的如是“孔子改制”般格局狭小。将康有为从尊崇周公、《周礼》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的霹雳手段,是廖平赋予的。在这一点上,梁启超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26](P77)在距离始从康有为为师及康氏初版《新学伪经考》三十年左右之后,虽把书名记错(当作《教学通义》),但主旨仍颇得其大体。与当代学者之多琐碎支离之见相比,尤为可贵。比如有学者因为梁启超的见解与自己的分析不符,竟得出“梁启超也显然没有见过此稿”的结论[注]参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44页。此为朱维铮的看法。房德邻也说:“(梁启超)他或许未读过《教学通议》”。房德邻:《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第24页。。也有学者就《教学通义》对《周礼》的态度又提出了更为暧昧的说法[注]朱维铮认为“但梁说的书名不对,内容也并非如其说是‘贯穴《周礼》’之作。”见朱维铮:《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94页。朱氏自己也搞不清书名,对《教学通义》之整体把握,亦不如梁氏为确,然其说影响甚大;房德邻认为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崇周公,却并不崇《周礼》”,参见房德邻:《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第24页;并一再区分“《教学通义》前半部分的叙述文字中有些是出于《周礼》的,这是因为康认为《周礼》的这些内容是周公所立的、可信的制度,但不表明他就尊崇《周礼》这部书。”参见房德邻:《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04-105页。此类说法,支离破碎,进退失据,殊不可从。均无视《教学通义》主据《周礼》讲周公之制,亦即梁任公所云“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教学通义》)”,亦即崇尚《周礼》进而崇尚周公的事实。打破这一关节的正是廖平,梁氏所述,参证以刘子雄日记等,颇得其隐曲,殊可从也。。
其实,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处理周、孔关系,颇可以撰著于同时甚或稍早的《民功篇》一句话一言以蔽之:
孔子有元宗之才,尝损益四代之礼乐,于《王制》立选举,于《春秋》尹氏卒讥世卿,又追想大同之世,其有意于变周公之制而光大之矣。[42](P89)
又可以《教学通义》的一句话而补充之:
孔子亦曰,“知我”以之,“罪我”以之。良以匹夫改制,无征不信,故托之行事,而后深切著明。[注]康有为:《教学通义》,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00页。这是关于《教学通义》手稿整理本之首出版本,而且也是标对了书名的本子。此版本,为十四年前笔者草《〈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有为与廖平的学术纠葛》一文时见闻所未及。今郑重引据之,一以志吾疏略之过,兼亦不没前辈之功。而此本,虽亦未臻理想,然未见得比流行诸本为逊色也。
可以说康有为深深困扰于“改制”之冲动与“匹夫”之身份之间的紧张,“周公之制”是他一直跨越不过去的坎。当羊城之会时,他已经历了上书言事之失败,对依靠王权变法由满腔热情一变而为极度失望[注]参见拙作:《〈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有为与廖平的学术纠葛》,《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他的“匹夫改制”的素念被廖平的新思想点燃了。“周制全不可考,概为孔子新制。”刘子雄日记所录的这句话,让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康有为尊崇周公、《周礼》的观念是如何获得彻底解放的。与廖平的羊城之会真是来的太及时了。
《周礼》一旦归于“新莽”之学,《左传》亦划归“新莽”[注]廖平曾将《左传》判归“新莽”(刘子雄日记、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皆可证),后变而忘之。一如诸子皆为救弊而改制,原本亦为廖说(见于《今古学考》),后廖平反攻康有为的诸子皆托古改制之说,亦忘其本为己说之唾余也。关于后者,冯友兰等学者早就讨论过了,已为学界所周知。,这种政治化的解读一旦开启,以康有为那“扬高凿深”的性格(语本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切“古学”皆归入“新莽”,且群经皆为刘歆一手所伪造,则如廖平所说“而多失其宗旨”了。
笔者曾为文探讨过,康有为那刘歆“遍伪群经”的极端看法其实也是承袭自清代考证学的疑伪传统,尤其是从丁晏等所谓王肃伪造群书之说移步换形而来[注]参见拙作:《积疑成伪:〈孔子家语〉伪书之定谳与伪〈古文尚书〉案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收入拙著:《〈孔子家语〉公案探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但是康氏“新学伪经”的题目得自廖平,不可诬也。康氏所大不满于当时或者破碎或者小气均之无当于世用的汉宋诸学,皆可一归于两千年来支配中国的刘歆。我曾称之为“唯政治的一元论的思维方式”[43](P149),今天看来,部分地渊源于廖平,部分地要归咎于康有为本人的性格。
正是廖平帮助康有为将周公之典归于“新莽”,即将周公置换为刘歆,才最终确立了大圣来临之升级版“孔子改制”的主题。赋予康有为孔子超级伟大的观念的,也是廖平。这一主体思想,远远不是一部《孔子改制考》所能涵盖的。
廖平的心灵自从被这位城府极深的学友灼伤之后,久久不能平复,不断调整自己的说法,揭露康有为的著述“祖述”己说,以致于牵强附会将康氏之“两考”一本一本分别皈依于自己的“两篇”。
事实上,若要说到廖平对康有为的思想影响,从施加影响方来看,既不能受制于“两篇”,也不能局限于羊城之会;从承受影响方来看,甚至也不能局促于“两考”。已有学者如蒙文通、张舜徽等均以为《新学伪经考》亦受《今古学考》的影响[注]蒙文通认为:“及既与南海康有为见于广州,康氏遂本廖师之《今古学考》、《古学考》以作《新学伪经考》,本其《知圣篇》以作《孔子改制考》。”见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6·附录:传记与评论》,第1022页。蒙氏以《新学伪经考》本晚出之《古学考》,其说不确,但说《新学伪经考》亦参考了《今古学考》,则有理。张舜徽亦认为:“本其《今古学考》、《古学考》,以作《新学伪经考》;本其《知圣篇》,以作《孔子改制考》。”见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第578-579页。其说之得失与蒙氏同。,我们认为有理。梁启超说“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25](P100)。盖就“家法”以为说,此处所指,或可理解为以宗《王制》为一派,以宗《周礼》为一派的今古文门户之见。为钱玄同所推重的康氏通过《史》、《汉》对读法等所获之所谓“辨伪”成果,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以此为idea前提的地毯式寻证,并加以极端化而已。若《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三上》所谓“今学全出于孔子,古学皆托于周公”[21](P79)云云,不是出于廖平吗?又如《春秋董氏学》云:“盖《春秋》之作,在义不在事,故一切皆托,不独鲁为托,即夏、商、周之三统,亦皆托也。”[44](P136)在《教学通义》与《民功篇》时代,康有为主张“孔子有元宗之才,尝损益四代之礼乐”,当时所谓“四代之礼乐”,康氏皆认为乃真实之制度,此时则“夏、商、周之三统”三代“皆托”,“一切皆托”,只有孔子的托古改制是真实的。看来,不限于“两考”,《春秋董氏学》中也有廖平观点之踪迹可寻。笔者未细究廖平著述之前,碰到此类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亦甚为骇怪;今者徒叹廖平之指控颇有未周,有大出于其所料想者,窃迹之不可掩也有如此。廖平自己的归结,不免太过偏狭了!
当然,廖平坚持不懈的指控揭发,也不是毫无效应,他逼得康有为不得不承认:“吾向亦受古文经说。然自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21](P400)这种道白,未必尽非。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云:“那时候新思想的急先锋,是我亲受业的先生康南海,(有为。)他是从‘常州派经学’出身,而以‘经世致用’为标帜。”[45](P338)这与我们所了解《教学通义》中有关“孔子改制”的论述,即康有为之初级版本的“孔子改制”说,为本于常州公羊学派[5],颇可印证。此决非康氏后来确立今文经学立场之后的新说,即非张之洞所谓“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其说过奇,甚骇人听。”者,可断言也。那些必以我所谓初级版的“孔子改制”论述,为康有为后来添入改窜或必为早就抄录自廖平的学者,不但不能贯通《教学通义》本身的文理,也不能探究廖康学术交涉的实际,割裂支离,牵强附会,失之远矣!
对于康氏避重就轻、死不认账的态度,有学者曾加以同情的理解与辩护云:
康拒绝提廖平,因他不以廖为他的先驱,虽接受廖的一些见解,但不以他为“真理”的共同发现者。假如这是抄袭,则康不仅冒犯了廖平,而且冒犯了所有他未提及的学者。[46](P60)
有一点很清楚,自命先知而绝口不道先驱的启发之功,这是康有为的性格。《教学通义》就没有感谢过章学诚、龚自珍以及常州学派中的任何一位,尽管我们看其思想承袭之迹甚为明显。这种性格源自他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可以《康子内外篇·势祖篇》中一句话概括之:
圣人之言,非必义理之至也,在矫世弊,期于有益而已。故圣人对众人之言,不能尽诚也。[42](P109)
这就是唯我独圣的康有为厚颜无有底线之所以然的内蕴。此种作风深为识者所贬斥,若钱穆在揭示《礼运注》之倒填年月时说:“长素尝谓刘歆伪造经典,本属无据,不谓长素乃躬自蹈之。”[3](P699)若用我已经说过的话来说就是:照妖镜竟然照出的是自己的影像[47](P4)。针对钱氏的严正批评,康有为将何辞以自解?我敢肯定地说,他一样会矢口否认。我替他拟的答复是:不,我康有为仿效的不是刘歆,而是孔子!张之洞曾忧心忡忡地说:“……此所谓‘素王改制’也。是圣人僭妄而又作伪,似不近理。”人们哪里想得到,康有为不但于学术上厚颜出之于攘窃之一途,在行事上更事事模拟“圣人僭妄而又作伪”之作风,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说,廖平都脱不了启发之干系,而真正无辜而又受到连累的,不是别人,正是被他们百般利用的孔子!
参考文献:
[1] 房德邻.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J].近代史研究,2012,(2).
[2] 黄开国.廖平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 崔泰勋.论康有为思想发展与廖平的关系[D].台北:台湾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2001.
[5] 刘巍.《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有为与廖平的学术纠葛[J].历史研究,2005,(4).
[6] 陈文豪.廖平经学思想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7] 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M].成都:巴蜀书社,1998.
[8] 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群经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9] 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1·杂著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0] 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9·皮锡瑞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1] 蒙默,蒙怀敬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廖平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2] 廖平.古学考[M].张西堂校点.北平:景山书社,1935.
[13] 廖平.经学四变记[J].四川国学院,四川国学杂志,1913,第六号.
[14] 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5·附录[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5] 章太炎.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A].上海人民出版社编,黄耀先、饶钦农、贺庸点校.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C].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6]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1970.
[17] 郑伟.廖平著述考[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18] 雷玲.民国初年的《四川国学杂志》[J].文史杂志,2001,(5).
[19] 方磊.四川省近现代国学运动批评空间的建立——以三种期刊为例[J].人民论坛,2015,(3).
[20]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1] 康有为著.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2] 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2·群经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3] 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16·附录[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4] 赵德馨主编.吴剑杰,周秀鸾等点校.张之洞全集9[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
[2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A].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3[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2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7] 房德邻.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28]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9] 房德邻.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J].近代史研究,1990,(4).
[30] 蒙默.素王改制:廖季平先生经学思想的核心[J].国学,2015-12-31.
[31]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2]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四)[M].济南:齐鲁书社,1994.
[33] 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M].成都:巴蜀书社,1985.
[34] 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5] 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6] 汤志钧.康有为和今文经学[A].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C].北京:中华书局,1984.
[37] 黄开国.廖康羊城之会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转变[J].社会科学研究,1986,(4).
[38] 郑园整理.江瀚日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7.
[39] 江瀚.慎所立斋文、诗集[A].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1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40] 邵懿辰.礼经通论[A].顾颉刚主编.王煦华整理.古籍考辨丛刊:第二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1] 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3·群经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42]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3] 刘巍.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4]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A].朱维铮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A].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12[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46]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M].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47] 刘巍.代序:“公案学”引论[A].《孔子家语》公案探源[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Re-examining the Case of Academic Disputes Between Liao Ping and Kang Youwei ——NewInsightsonKang’sPlagiarismandPreemptivePublications:XinXueWeiJingKaoandKongziGaiZhiKao
LIU-wei
(TheInstituteofHistoricalTheory,ChineseAcademyofHistoryStudie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101,China)
Abstract:Exploringthe academic disputes between Liao Ping and Kang Youwei through comparing their works:XinXueWeiJingKao and the later Studyonancientlearning,theKongziGaiZhiKao and the later UnderstandingConfucius,is a popular but problematic method and habit.It seems that Liao changed his charge and statement.In JingHuaJiaBian(1897),when Liao first accused Kang,he justmention XinXueWeiJingKao,notKongziGaiZhiKao.It was in SiYiGuanJinXueSiBianJi(abridged edition)that Liao listed KongziGaiZhiKao as the accused for the first time.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se four books,he redefines the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two works and Kang’s correspondences.The gains and looses of this statement was complicated.The textswritten before their meeting in Guangzhou eg.ThePrefaceofZhiShengPian,The Diaries of Liu Zixiong,can clarify the basic facts that their disputeswe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manuscript of the ZhiShengPian and related conversations.The viewpoints such as Liao Ping gave his PiLiuPianto Kang Youwei;Liao Ping didn’t gave either of the two works to Kang Youwei;Liao’s impact on Kang Youwei was limited only in their“discussion”or“talks”,should not be conclusive.Liao’s influence on Kang is mainly reflected in Kang’s theory of Xin Xue Wei Jing having stolen Liao’s point of view,and the interception of an upgraded theory of Kongzi Gai Zhi.Two core contents in the upgraded Theory of Kongzi Gai Zhi are that it was Confucius himself that forged six classic works and falsely reconstructed institutions of the primitive times in the name of the anci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hisown reform claims,but that was not real facts.This opinion,as Zhang Zhidong said,was initiated by Liao Ping and inherited by Kang Youwei,whose early related works conveyed ideas different to the theory of Kongzi Gai Zhi.Liao violently criticized Kang for that Kang deliberately concealed his contribution.Although Kang Youwei was deeply hurt by Liao’s excessive defense,he should reflect on his own responsibility.His excessive scepticism is indeed extremely harmful to Confucian school.
Key words:Liao Ping;Kang Youwei;Guangzhou meeting;theory of Xin Xue Wei Jing;upgraded theory of Kongzi Gai Zhi
中图分类号:B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9)04-0034-031
收稿日期:2019-05-27
作者简介:刘巍,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春梅
标签:孔子论文; 康有为论文; 光绪论文; 经学论文; 周礼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近代哲学(1840~1918年)论文; 《齐鲁学刊》2019年第4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