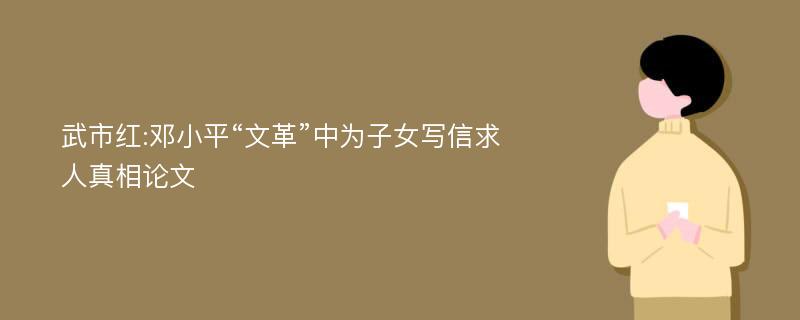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
长女邓林出生在1941年9月。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军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军情紧迫,邓小平夫妇无法带着孩子率兵打仗,就在邓林出生后的第七天,把她送到了老乡家。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二女儿邓楠相继出生。邓小平率领部队打到哪里,卓琳就带着孩子们把家安在哪里。解放后不久,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在重庆出生。
为儿女们的事写信
1970年2月9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 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1970年10月17日,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
“从今年1月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205 元。1月份,曾请省革委会负责同志向你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是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月份的,还是205 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要35 元左右(吃饭25 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10 元),两个大学生每月30元左右,三人即需约90 至100 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100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约需100 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然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100 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邓小平的一片爱子之心跃然纸上。历尽周折,1971年夏天,邓朴方终于获准到了江西。
为大儿子治病写信
这个意义的来源极为深远。青铜器上有关老虎的纹饰很常见,比如饕餮纹。在古代军队的名称运用,“虎”字和“虎”符,也流行千百年。1995年我在乌鲁木齐买了把英吉沙小刀,刀柄就是虎纹。可惜它不允许带上火车,只好留给安检。老虎作为一种权威,一种象征,比它作为凶兽更令人追捧和敬仰。
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儿子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使他惶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小说家对任何一种叙事方式的选择,都是思想与感情表达的需要,和艺术个性、审美情趣的自然流露,张爱玲也是如此。艳异空气的制造,即张爱玲擅长的隐喻象征,而艳异空气的突然跌落,就是隐喻背后的嘲弄和暗示。在某种程度上,张爱玲通过“反高潮”完成的就是对理所应当、顺其自然的反讽,用最直接、最果断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凡事都有意料之外的可能。生活、人性、现实都有其不可理喻的一面,张爱玲做的就是把这一面直接剖开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这是生活,这就是人性,这是现实。
在实践中,学校将课程分为道德、人文、科学、健康、艺术五大学习领域,每一领域又包含基础性、拓展性两类课程。无论是基础性课程,还是拓展性课程,都围绕上面的五个领域落实并强化五种素养。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学校还打破学科与学科之间、课内与课外之间、校内与校外之间的壁垒,突破传统课程模式,自主开发了各类综合性课程。目的是通过课程体系的建构、课程方案的落实,实现“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的办学理念。
从信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当时焦虑的心情。如果儿子真来江西,不但他们三位老人无力照顾,儿子唯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也将丧失。不是处于此种万般无奈的境地,邓小平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
1970年9月,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邓朴方现在的情形,我的妹妹邓先群最近去看了他,把情形写信告诉了我们。现将她的来信附上,不赘。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杂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照料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的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好作准备,免得临时仓促。静候你的指示。”
邓小平与家人在一起
几个月后,邓朴方还是被赶出三〇一医院,送进北京社会救济院。得知此消息后,邓小平毫不犹豫,立即提笔,再次给汪东兴写信。
采用调查点位土壤、稻米和富集系数数据,借助反距离权重插值(IDW)法进行空间插值,并对插值结果进行土壤-稻米-富集系数 Cd协同风险等级评价,结果表明珠三角地区55.0%的稻田为无风险,低风险和潜在风险稻田的占比分别为19.0%和16.0%,中、高风险稻田的占比分别为 9.00%和1.00%(图5)。
“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67岁了。卓琳虽只有55 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100 上升到116,高压180),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小孩子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
为小女儿小儿子上学写信
1972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被分别安排进江西医科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学习(原文如此),令邓小平和家人喜出望外。4月22日,他再次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京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顾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来帮助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30 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生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
当然,预测或推测不会百分百准确,但预测可以减少做题时的盲目性,提高对材料理解的准确度。Nunan指出,“预测有助于听者预料将要发生的事情,并帮助听者对即将听到的材料作做好充分的准备,从而促成更有效的听力理解”。[3]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卓琳说:“因为我们的事连累了孩子们,今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些。”
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毛写的一篇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深情地记述了邓小平在江西的生活。这是她送给爸爸80 寿辰的生日礼物。邓小平很高兴,亲笔在这张报纸上作了批示:写得真实。
(摘自《纵横》)
标签:邓朴方论文; 小儿子论文; 江西论文; 毛毛论文; 南昌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中外文摘》2019年第20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