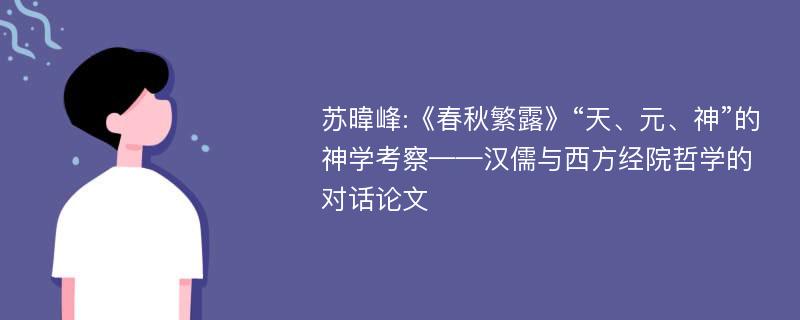
摘 要:“天、元、神”是董仲舒哲学中“天”论的三重维度,涵盖西汉形而上观念中对至高超越者的认识。“天”为实体,是天所有属性的总集;“元”为天的本原,是在时间终始上的永恒性呈现;“神”为形式和现象,以隐与现、变与不变的辩证建构神人的关联。“天、元、神”组合形成了完整的神学系统,它的目的是借助“天”的权威建立一套制衡王权的系统,建立政治权力和神的意向结合的政治神学。
关键词:董仲舒;天;元;神;神学;经院哲学
董仲舒继承春秋公羊学微言大义的传统,汇通上古阴阳学说,建立了以“天”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春秋繁露》中关于“天”的内容实则由“天、元、神”三重维度组成。“天”为实体,是天所有属性的总集;“元”为天的本原,是在时间终始上的永恒性呈现;“神”为形式和现象,以隐与现、变与不变的辩证建构神人的关联。“神”作为现象最终通过五行的系统语言,描述“天”的行动,以五行促进人和天之间关系的变和不变,构成董仲舒庞大的精神及宇宙体系。“天、元、神”三者具备“天”的超越性,即相对于人的有限性的超越,而且能从三重维度中充实“天”的属性,这种区分在《春秋繁露》中已经有明确的阐述,反映了董仲舒思想已具备哲学的系统性。笔者尝试从西方自然神学的角度来论述董仲舒的“天”论的整体,特别以中古时代基督教经院哲学为对照。经院哲学有明确的自然神学色彩,董仲舒哲学有相类似的自然神学色彩,在《春秋繁露》的《正贯》《执贽》《循天之道》诸篇内容中,我们依稀能看到董仲舒由于无法直接阐述“天”的属性(由于理性没法解释超越之存在),而经常使用现象(果)来反正“天”(因)的属性,就是所谓自然神学的论证方式。
董仲舒著作重点在于建立“天”和政治、伦理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借灾异之说和阴阳五行建立一套制约君王的政治伦理。《春秋繁露》中经常将政治现实与“天”类比,从官制、服制、郊祭的内容都能看到,董仲舒借助这种类比证明人间的政治现实和“天”是一脉相通的。中西方自然神学的汇通,也就是董仲舒的“天”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神学本体论”的类比和辩证,有助于更有系统地理解和发挥董仲舒哲学的重要主题,特别是其核心的“天、元、神”为一体的哲学框架,从而明确“天、元、神”在建立汉儒①中西方学界一般认为董仲舒为汉初儒家的重要代表,然而,西方汉学家鲁惟一认为汉初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儒家学派,他认为有系统的儒家学派是发生在董仲舒之后的。本文为行文方便会依然使用“儒家”“儒学”的字眼,以表示孔子以礼法仁义治世的思想。有关鲁惟一的讨论,见其《董仲舒:“儒家”遗产与〈春秋繁露〉》(香港中华书局2017年版,41-43页)。其他学者的讨论可参考周桂钿的《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神学为主导的治国方针上的伦理价值,以及“天、元、神”如何构成汉代儒者对于至高者的思维①笔者认为神的本质不属于外在的本体论问题。神在人类心理结构中处于至高者位置,其形式是幻想性的、普世性的,也就是人类心理的祟高感、内在的超越性。因此,神作为一个心理现象,可以在跨文化的角度中进行有意义的深入思考。。究竟“天”能否在儒家的整体思想中发挥其作为超越者的位置,或者作为哲学中的第一因,要探讨这一命题,必须首先整理和充实“天”的形式和内容。
一、耶儒神学的目的论区分:创造启示与政治神论
从自然神学出发,人作为受造之物,具有上天赋予的神性本质,“天”的本质同时也是人类心灵普遍及先天具有的至高超越者的信念,它反映了人类共有的道德理想和对生命的思考,也就是说,按自然神学的理解,人之所以有对至高者的崇拜、敬畏也是上天创造人的神性本质,所以不在乎神的外在存在,而是神的理念在人类心灵中的内在性(immanence)②关于神学上内在性的问题,始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他们相信理知(nous)构成了世界的意向(intention),由这一世界灵魂构成万物,以至人的灵魂。一切都是透过神的内在性,泛化为世界和人的灵魂。本文所指的内在性,指人类本身的心灵结构和心理中包含了先天为至高者设立的幻想位置,用以承载人类渴求的崇高和超越,这是内在的神性或者至善形式,而非外在的。法国哲学家德勒兹(1925-1995年)在讨论斯宾诺莎(1632-1677年)时,认为斯宾诺莎有相类似的想法。。故此,神性在人类心灵中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也能跨越时空地域。然而,我们对于中西自然神学依然需要一种目的论的区分。
在欧洲,经院神学对神本质的思辨,目的是证明神的存在和性质[1]22。首先西方神学始终是以创造论为主,神创造受造之物同时赋予了受造之物某种神性本质。神性的本质也就是神的性质,即神的喜怒、至善和公义性质。经院神学家从而推论出物和物之间共有的神性,组成世界的总体为神性的呈现的自然神学理念。
在中国,董仲舒的“天”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首先原始儒家着重现世事物,对“天”和鬼神存而不论的态度一直影响着董仲舒之前的儒学,故此,中国哲学中不求证神的存在或内容,只着重神性和人性的模拟,以神性的权威来支撑人性至善的必然性,其中政治道德的目的很明确。此外,儒学传统上是士大夫哲学,在汉初黄老之学流行之际,董仲舒在他的思想中开创性地融汇了上古阴阳和五行学说,建立起完整的体系,以阴阳五行补充原始儒家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士大夫哲学的目的最终依然是对应政治需要,期望儒学可以为王室出谋献策,在这点上,董仲舒学说显然是一种具有政治目的论的神学构建,目的也就是为君主权力架设“授命于天”系统,其对天道神性的讨论主要是为了神化政治力量之目的。
耶儒神学最终结果不同。欧洲哲学家在自然神论上的思想被指为异端,甚至因此入狱;在中国自然神论则成为汉代儒家保持生命力的出路,两者在社会意义上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自然神着力以天命、天意、天威等方式支撑政权的合法性,但却没有其他方式能制衡政权。以往孔子以先王理想及德政诱导王权实行仁政,效果不张。到董仲舒时代,灾异说流行,董仲舒企图将其合理化,期望通过建立神秘力量(也是天的力量)来迫使王权实行仁政,以神权(来自“天”的监察)制衡王权,可惜灾异说最终令董仲舒几近丧命。
二、董仲舒“天”论的范畴
“天、元、神”组成了董仲舒神论的三重维度。“天”是作为外在的自然之天的呈现,而东方神学的幻想性投射令“天”得到了人格化的面纱;“元”则涉及董仲舒对于时空和历史的始源问题,是形上而哲学化的提法,而且透过“元”,董仲舒神学可以接入天人共际的层面。董仲舒的目标是建立神学体系,并运用于政治,就是所谓的政治神学。那么关于“神”的问题,我们就从董仲舒使用“神”这一名号的歧异性开始分析,归纳出其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
正如不少论者提出,“天”在董仲舒的理论系统中既包含了自然的天,亦呈现为道德的天和义理的天,其实后两者只是“天”作为至高超越者的不同体现,表现为普世的道德典范。《王道通三》:“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为了使其儒家的神学体系更为完满,董仲舒不是简单地利用民间对“天”的信仰,而是将“天”看作现象世界的呈现,其满足的是目的论的神的意志,展示自然世界的规律,提供政治权力的证明和道德规范的依据。
从上文可知,“元”是既能通天,亦能达人。“元”和人之间共通,这种思维与灵魂的概念十分接近,而元神在宗教言说中也恰恰是灵魂的意思。在这个理解中,“元”的本质就是具有神的灵气的质料因、范式因,同时元神是可以通达人神,令圣人可以按照神意,以元神的动力因,完成神的目的。
“秦时明月汉时关”[12]是为了表示战争时间上的久远,“旧时王谢堂前燕”[13]是为了突出今非昔比的历史变迁世事沧桑,“月落乌啼霜满天”[14]半夜无霜,只是为了突出凉。“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5]是在时空转换中突出边塞的苦寒。“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16]是为了写战争给家庭带来的痛苦,是作者借此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17]是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是阴阳两相隔的迷惘和无奈。
三、董仲舒之“天”是否具备人格及感情
基督教天主有创造万物的神话始源,中国上古神话中也有伏羲女娲造人之说,然而在汉初儒者那里,对于宇宙和人类的始源悬搁不论(或者以五行说的抽象的方式进行思维),而认为“天”能主宰自然,在农业社会中,天威就显示在灾祸之中。董仲舒的“天”是为了建立政治神学而设定的最高权力。“天”是神国中的最高权力者,其权力表现在“天”对众神的主管。《春秋繁露·郊语》(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写篇目)中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董仲舒的“天”与其说是神学化了的自然世界,倒不如说是政治化了的神学幻想国度。“天”既有其政治权威,统管众神,控制自然世界的正常运作,其意志也是和政治一体同源的政治意志。
很多学者颇受冯友兰的影响,认为董仲舒把物质的天神秘化,视之为有意志的实体,“看成有人的意识和情感的实体”,是作为有意志人格的物质的天[3]。意识是近代哲学关注的题目,黑格尔对意识的讨论专注于用来论证人的自我问题。对于神有没有意识,我们应该先就“意识”进行讨论,不能轻言。西方神学较为接受神意所指的是意志(will),而非意识(consciousness),意志者可以以目的论来理解[1]204。金春峰则认为董仲舒的“天”包括了神灵的天、道德的天及自然的天[4]147。然而,按照前面的申论,我们更认为董仲舒的“天”只在意于天的权威,其对自然和人类的统管,以“天”为大,其大不在于物质上的大,而在于权威上的不可超越。董仲舒令“天”成为儒家的最终权力给予者,天命授予既然主导人的世界,包括政治的活动,其权威性必然需要是绝对的,不受其他力量主导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其天命授予的绝对化神权幻想。
飞禽是中国画艺术题材的分类之一,在远古时期,我们人类祖先是以狩猎为生活,在悠长的演变过程岁月中,人类与飞禽走兽共处,动物就变成人类最初用于绘画的题材之一,也赋予动物意义而表达自己的愿望作为一种载体。早期都可以在岩石上或者陶片上皆可看到飞禽的纹饰。一直到现今对于动物的情感色彩潜移默化的融入人们生活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里。不管是绘画还是雕塑到装饰纹样,飞禽都能有多种的表达手法与表达形态。从观察动物的五官、肢体结构、神情与动态,加上绘画的个人情感色彩,都能带来画面不一样的艺术美感与独具一格的韵味。
《生活用纸》是国内关于生活用纸行业的专业性科技类综合性权威刊物,内容丰富,专业性、时效性强,是生活用纸及相关行业的企业管理人员、市场营销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技术工人的良师益友。
在谈及董仲舒“元”论时,古今学者都依照以下的文字来讨论:
近代不少论者指出,董仲舒的“天”有人格神的本质。可是我们必须理解,人格神的说法只是人们在解读大自然间的神意时(包括天气变化、灾异),幻想性投射了“天”作为个体人格的想法。相比起基督教的神,神的本质和人之间必然存在范式因的相类似,就是神以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说法,这情况并没有在东方神学中明确出现。我们所谓的人格神,只是对“天”的人格化投射,是幻想性心理投射。东方哲学中的这种幻想性的神本质,汉学家葛兰言在《中国的信仰》中称为关联性宇宙论(correlativecosmology),构成了人想象上天有好生之德,从而对天的本质做出各种假设[6]。“天”只能提供一种心灵慰藉给人们,不能说成是人格神。葛兰言甚至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宗教是不合理的,只能被视为没有仪式没有神职人员的“官方宗教”,满足政治的目的,“一种仅建立在社会规范性和道德实证主义上的宗教”[7]。
董仲舒在这段话里加入了“天人之际”的主题,万物包含了物质性的“天”和作为“天”的内涵的“元”,只有圣人透过其“志”,以“元”的“正”论,建立起“天”和“元”之间的中介。学者在解释董仲舒论《春秋公羊传》“元年春,王正月”时,没有注意到董仲舒的“元”往往和“正”共享,“《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玉英》),没有“元”的正,“天”也可以有贼。是故,我们可以反过来论证“天”在董仲舒的神学中不是绝对的意志,其内在也存在有正和贼的矛盾性,能持“元”守正,才能保持天意的顺,天意顺则民和。正如前述,“元”有终始的时间性意义,何以时间性和道德的正和贼、顺和逆的矛盾性有关呢?
然而,如果我们按自然神学的理念来看人格神的讨论,神的本质只在于其设计的事物是否有神意的呈现。这种以世间事物的本质反向投射为“天”的本质的幻想性操作可以说是东方神学,或者董仲舒“天”学的建构逻辑。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向来是奉天、惧天的,对于上天的本质并没有思辨上的建构,较为方便的做法,就是以人世间的事物,特别是人间政治的形式——皇室和朝廷的权力形式来反向投射成为“天”的本质,由具体指向抽象的方法,构成了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结构。徐复观说:“一般地说,对天的性格的规定,一是转述传统的说法,传统对人的精神是一种力量,而容易使人作反省的信服。一是出于个人价值观的投射,即将个人的价值观,不知不觉地投到天上面去,以为天的性格本来是如此。另一是出自主观的要求,自己要求如此,认定天即是如此。”[9]天的幻想性投射,董仲舒在《离合根》中说:“天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天以仁爱布政于人,可以说是理想化了人的愿望,从而返回到君王以相同的仁德,任用贤士,以实行天道的愿景。
四、天人之际与“元”的动力因
汉初民间生活渐趋安定,人们对于世事向往更深层的思考。董仲舒认为的至高超越者应包含“天、元、神”三层概念,令神的本质由外在的自然之天,转至更抽象的道德之天。藏明说:“儒学一直试图将自身所主张的道德律令上升为天的道德律令,并希望通过天的权威来使这种以‘仁德’为核心的道德律令成为自然与社会共同遵行的法则,而董仲舒对道德之天的构建,正是儒学‘以天律人’的重要尝试。”[10]但是,单纯的天意,如何能够达到人,完成天人之际,以天律人?我们必须按着董仲舒的思路,往更深入层面推演,这当中“元”的概念至为重要。
任蜜林认为,董仲舒的“元”理论来自于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11]。《春秋公羊传》以元为事物的起始。董仲舒在《玉英》中说:“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元”有始终、原本的意思,推演为物的始源,其中含有元气为宇宙之端,万物发端在于元气,元气为天的内在,而且和天地人三才共通者,元气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然而,学术界对于董仲舒“元”的思想仍没有明确定论。近人徐复观、金春峰及古人何休、徐彦等均同意董仲舒以“元”为元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周桂钿亦认为元和气合用是董仲舒以后的用法[8]41。而正因“元”被理解为万物本源,董仲舒特意为《春秋公羊传》的“元年春,王正月”提出明确而重要的解读,认为春秋之学,以元为一,以元为本,并以此推演为宇宙事物之“前”的先验思维。周桂钿在论证董仲舒是否能称得上“元一元论”时,其立场是否定的,但其提出的论点只在于否定董仲舒有“元气”的思想,而并没有否定董仲舒以“元”作为万物本源的说法,周桂钿说:“在董仲舒的哲学体系中,宇宙本原是‘元’,而不是‘元气’。董仲舒的宇宙观是‘元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
以单一的元气观来论证董仲舒的哲学体系,可能需要更详尽的论述,不过“元”的确可以被视为董仲舒神论系统中,作为“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余治平说,“元”所指向的是大一统,是一般个体民众所没法知道的,只有专注精神文化建构的圣人、大人才能透过春秋之本,深察“元”在世界和人生中的根本意义,“人生在世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随四时变化消失、毁灭的表象存在和外化物件中,而在于能够找到并拥有那种恒常不变、始终一贯的本体,这才是生命的真正依据和最后凭藉”[12]。这里所说的是,“元”是没法直接把握的,但其本质是恒常不变、始终一贯。
1.2.5 评价标准 ①对糖尿病知识的认知≥60为合格。②综合干预的效果评价包括饮食控制、运动和血糖、尿糖监测。
周桂钿说“元”是时间观念,表述十分准确。前文我们讨论了“天”,“天”是作为至高超越存在的形式,是外在的、可以具体被理解的形式。如果从“天”作为一个空间概念来看的话,“天”首先包含了自然的天,然后才是引申至义理的天、道德的天。而“元”则可以视为“天”的内在形式,是时间的形式,平衡于作为空间的“天”概念,可是这并不充分。董仲舒所指的“元”不存在时间的线性假设,他所指称的是更具有深入意义的时间性,而论者多集中于“元”为一、“元”为本的概念,错误地认为“元”只有开始的意义,其实董仲舒的“元”既为始亦为终,终始运行,是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三代改制质文》)。既始亦终指的是非直线的时间进程,无有所谓终结的循环不息。从这一思路理解,就更接近于余治平的“元”为“恒常不变、始终一贯的本体”的说法,不同的是这里的“元”本质是循环,在循环中体现永恒,也体现终始。在西方神学中,造物者本身既是自有永有,也是历史和时间的终点,如果从这视角而言,董仲舒的“元”是对于“天”的重要补充。
在基督教神学中人类是受造物。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曾指出,受造物和神之间有了形式因(身体形式)和质料因(灵气)的内在相同,而外在因则包含了动力因(神意)和目的因(爱的创造)几个层次,其中范式因作为外在化的形式因是神创造事物的第一原理。神作为事物的设计师,神意不仅仅是表现在“天”对于自然界的统管、惩罚上,事物在自然情状中表现出结构性的关联,也显示了神的智能和超越,其中也呈现了人类受造物和神的相似性[5]22。
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玉英》)
我们认为人格神必须满足前述的范式因,范式因所指的是事物的外在形式。在神的存在命题上,我们起码能在基督教经典中找到形式上人和神共通之处,才能确定神本身能和人的存在共享相同的人格:神的形体和人相类;具备语言并能向人传达神意;神人共享神的气息呼吸,起码在这几种形式上我们能找到人神之间共通的范式,我们才可以接受人格神的说法。在董仲舒的“天”学里,我们看不到“天”人有形式上的相类似。董仲舒的“天”具有动力因和目的因,却没有范式因。董仲舒的“天”本身以意向目的性为主,有论者以为董仲舒的“天”是“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周桂钿并不同意[8]38。在我们看来董仲舒的“天”主要是道德上的超越,是仁义的呈现,也是人在世的道德理想。是故“天”的本质只是人的道德理想对天的反向投射,和基督教的人格神有本质上的分别。
在“元”的理论上,可以引入阿奎那和司各脱的神学“四因说”中的动力因。“元”之可以贯串天人,形成天、君、人、物的一体普世性,主要可视为动力因。“元”本身是抽象的,具有既可变又永恒的本质。天的意向性若没有动力因是不能形成万物的,就如经院哲学家以设计师来比喻神的本质,其设计是呈现神的智慧的外在表现,然而这呈现必须在设计师作为工匠的动力中才得以实现[13]133-162。在董仲舒神学中,人是作为这一动力因的连接,“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不同的是,阿奎那的动力因存在于神,神作为设计师,由其自身向外在的万物世界进行变动的工作;而董仲舒的动力因则存在于圣人,依据天的意向,明白天的意旨,而联系至高的神的“元”和世间的事物。
在这一点上,董仲舒的“天”是天之君,因此我们没必要就“天”作为神的本质是否是西方所定义的信望爱三位一体进行讨论。董仲舒的“天”更多的是在于绝对的权力,而且天之权力是没有更替的,由始至终“天”的权力就没有改变过。自有永有在西方是存有上的自有永有,无需要面对生死。在董仲舒这里,自有永有的是天之权威。《汉书·董仲舒传》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当中所指的“道”,可以解作“天”的现象界呈现,亦可以是作为人的行为的道,亦即道德规范的本源。“道”的本源始终要受到“天”的权力支配,其变与不变,也在于天意。正如前述,董仲舒理想中需要建立的是王权天授的思想,以增强汉室的政治合法性,因此他在《为人者天》中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由“天”授予权力,分层管治,“天”受命天子,天子受命臣民,组成了由神权延伸至政治的系统。在董仲舒这里,上天被视为人的始祖,万物的本源。《观德》中说:“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王者既受命于天,也应恰当地回应天意,董仲舒在天人之间以孝道相连接。《深察名号》中:“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积极指导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做好5G系统试验的基站部署,开展好5G系统基站与同频段、邻频段卫星地球站等其他无线电台站的干扰协调工作,确保各类无线电业务兼容共存,促进我国5G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五、东方神灵的目的论——仁义治世
在自然神论的理论基础上,我们提出神作为超越至高者是人心所寄,乃本于原始社会对于自然的恐惧,进而成为敬神奉天的基础。“天”在董学中涵盖了多重意义,向来论者意见不一。冯友兰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可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之天是也。”[2]董仲舒所指的“天”,其意义比一般学者认为的要复杂得多。
董仲舒说:“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也;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天地之行》)神和明是民间对鬼神流俗的称呼,董仲舒很准确地提出了对于这一名号的表述。“神”者,谓不可见其体者,深居者,所指的是神和人的隔离性,“神”处于人的认知所不能到达的维度,是为不可知的存在。“明”者,则表示像西方神的全知的状况,着重的是知识上的超越。这里不可见、隐蔽和全知的本质,在述说“天”和“元”时都没有这么明确。学者一般都在讨论,董仲舒的“神”是人格神还是道德神的问题,而西方经院哲学对于神的讨论已经比这两点更细致了。董仲舒的“神”展现了一个更丰富的维度,即不可知、隐匿、全知。
比较董仲舒的“天、元、神”,虽然“神”的着墨不多,而且不形成明确概念体系,却也包含了董仲舒神学系统的枢纽元素。其中“天”和“元”都不存在隐匿,“神”的隐匿直接成为尊神的基础。《离合根》中说:“天高其位而下其施,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天地之行》又说:“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隐匿产生了神秘的不可知力量,而光明则彰显神的全知。在隐匿和光明之间,董仲舒从神学再次转入政治,以隐匿为君王执政的风貌,君王的意向不向臣子显露,保有尊贵之位,向臣民的德政以仁为施予,下其施所以为仁。君王的全知在于其能博观,博观者能任贤能,通达用人之道,其光明展示在任贤,任贤则能明达,而不必展示君王的意向。可以说,“元”的本质在于终始,自有永有;“神”的本质则更多在于和人之间的交接。人们不能直接和“天”对接,但透过祭祀,人们可以感受到“天”的意志,天和人之间,可以有圣人作为中介,而“神”则可以透过其既隐匿又光明的特质,通达神人的关系。“重祭事,如事生。故圣人于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独任,事之而不专恃。”(《祭义》)
近年来,关于秦始皇“会稽刻石”的立碑地点成为史学界和书法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综合各家观点,有秦望山说、鹅鼻山(刻石山)说、何山说三种,其中鹅鼻山(刻石山)说流行最广,似乎已成定论。但是在去年,诸暨民间人士忽然在枫桥镇“发现了”秦始皇“会稽刻石”的立碑之处,并抢先在此重立刻石,一时间,争论的风烟又起。绍兴县平水镇组织了十余位学者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坚持原碑立于鹅鼻山(刻石山)说。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和实地考证,认为双方所据资料都缺乏原始真实性,所下结论值得商榷。
“神”在董仲舒神学的本质中是与人沟通的基础,这基础建立在郊祭、执贽、求雨止雨的宗教仪式上,本身更具有目的性。“神”是宗教性活动的具体呈现。神意不管是基督教的创造论,或者东方神学的天人道德论,都可以理解为神学中的目的因。设计师在构思人世万物时,必须在其行动中呈现目的因,正如阿奎那所指出的,动力因往往是目的的原因。司各脱则更主张目的因是先于动力因,而且“由于神圣的爱作为一种意愿可以决定动力因的行动并且要求动力因去推动别的东西,所以动力因被神圣的爱所推动着”[5]29。董仲舒的“神”亦有类似的目的论因素,他十分看重神圣和尊贵,认为神圣和尊贵既是至高神明的本质,也是圣人和天子应该具有的,人们对于神以祭祀侍奉为本,而神灵的目的就是保护和监察。藏明说:“董仲舒哲学之‘天’的属性并不是单一的神圣性或自然性,而是由道德之天、自然之天、神灵之天三者相结合的混合体。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道德之天是核心,统摄自然之天和神灵之天;自然之天是道德之天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而神灵之天则是道德之天得以实现的思想保证。”[10]20
六、灾异之说:董仲舒神论向政治神学的转向
董仲舒神论企图引入灾异之说从而转向政治神学,这令其几乎遭受杀身之祸。我们可以推论,阴阳五行是当时统治者可以接受的理论,但当阴阳五行的神秘色彩延伸到灾异之说时,就会形成政治矛盾。作为董仲舒弟子的吕步舒对老师的理论一点都不理解,有可能是这一理论是董仲舒的不传之秘,或者是新的想法,另一可能就是吕步舒反对这立场,不敢以身犯险。
1#隧洞位于泵站出水口920 m,全长301 m,调压井位于1#隧洞中间位置,距隧洞进口133 m,为高45.4 m,半径4.7 m的圆形竖井,地面以下37.4 m,地面以上8 m。混凝土衬砌完成后,井筒半径为4.0 m。
2.1.6 样品中各指标成分的含量测定及综合评分 取处方配比药材样品(均粉碎,过4号筛)各适量,分别按“2.1.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1.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平行测定3次,记录峰面积并计算样品中各指标成分的含量。以各指标成分的最高含量值为参照将数据进行归一化,再按照各指标成分的权重(本研究将栀子苷、芍药苷和丹皮酚的权重系数均设为1)计算得综合评分:综合评分(Y)=(栀子苷含量/栀子苷最高含量+芍药苷含量/芍药苷最高含量+丹皮酚含量/丹皮酚最高含量)。
当然不应该因为提倡灾异之说就批评董仲舒背离了儒学基本立场。根据汉初的社会情况及董仲舒以后的社会变化,可知阴阳五行已经是当时儒士之间的风尚,董仲舒以灾异神秘说法对应阴阳五行,这是董仲舒神论向政治神学的转向,而这种神学上的转向,也伴随着董仲舒从哲学角度上企图以灾异之说制衡汉皇室的绝对权力,这其实显示出董仲舒的政治理想。黄朴民指出,董仲舒在建立汉初新儒家神学时,由单纯的建立“神道设教”的目的论,发展至有明确政治理念的政治神学[14]。
正如前述,董仲舒的神学由客观具体的“天”代表了超越的天意,天意本身具有道德上的目的论,就是“仁”。“元”是作为天的时间维度,在始源上建构了神学中的自有永有系统,而“元”本身亦是超越时间、超越始终的,到了终极又能返本归原,形成超越历史的维度。“神”则作为宇宙的动力源,由神灵的以灵为动,以欲望、意向、神明,透过神的可隐可显,把非凡俗的超越性彰显,并和人的情感欲望对应共鸣。“天、元、神”为一体的至高者,以仁义的目的推动政治的本真——仁爱、德行、任贤,建构董仲舒的神学国度,亦因此影响到千年儒家思想的发展和传承。
参考文献:
[1]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册[M].高雄:中华道明会,碧岳学社,2008.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8.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1.
[4]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147.
[5]雷思温.邓·司各脱论原因秩序与上帝超越性[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1-34.
[6]John B.Henderson.“Cosmology and Concepts of Nature in Traditional China” Concepts of Nature - A Chinese-Europea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M].Boston:Brill,2010:182.
[7]葛兰言.中国人的信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2:3.
[8]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30.
[10]藏明.“自然”“神灵”映衬下的道德实体——再论董仲舒的哲学之天[J].衡水学院学报,2014(5):15-25.
[11]任蜜林.董仲舒思想的“天”“元”关系[J].衡水学院学报,2016(5):23-28.
[12]余治平.论董仲舒的“天本体”哲学[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25-30.
[13]Duns Scotus.Philosophical Writings[M].Edinburgh:Thomas Nelson,1962.
[14]黄朴民.文致太平[M].长沙:岳麓书院,2013:232-241.
A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Tian,Yuan,Shen”in Chun Qiu Fan Lu:A Dialogue between Dong Zhong Shu's Confucianism and Western Scholasticism
Cyril SU Wei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Tian,Yuan and Shen (天、元、神),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theory of Heaven in Dong Zhongshu's philosophy,cover the metaphysical thinking about a transcendental being in Han Confucianism.Tian,the substance of Heaven,is the collection of all its attributes;Yuan,the origin of Heaven,is the eternal presentation of time both in the beginning and in the end; Shen,the form and phenomenon of Heaven,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n a dialectically way of being visible and invisible,or changeable and unchangeable.This trinity forms a complete theological system,whose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checking and balancing the absolute power of Han's Emperors with the aid of the authority of Heaven,and to establish a political theology of combining political power with divine intensions.
Key words:Dong Zhongshu;Tian;Yuan;Shen;theology;scholasticism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9.05.008
作者简介:苏暐峰(1974-),男,香港人,在读博士。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9)05-0044-07
收稿日期:2018-10-11
(责任编校:曹迎春英文校对:吴秀兰)
标签:董仲舒论文; 神学论文; 政治论文; 自然论文; 本质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汉代哲学(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论文; 《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