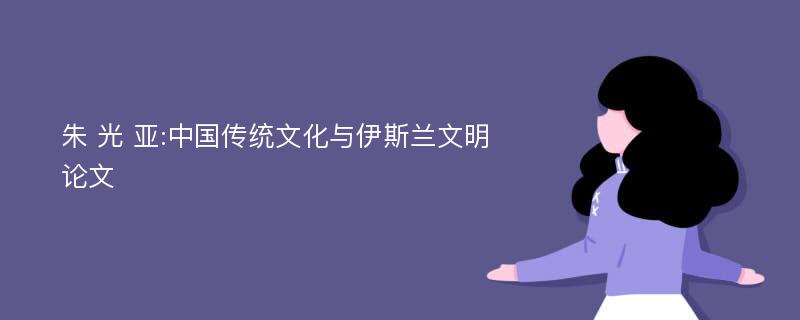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入世与出世相结合的文化:儒家入世,其基本特征是拯救;道家出世,其基本特征是逍遥。出世与入世,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拯救与逍遥,则凝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宗教文明的伊斯兰文化,其基本属性应该是出世的,然其独特处在于,从产生之日起,它便是一种世俗化的体系。这种集世俗化与非世俗化于一体的伊斯兰文化,自传入中国后,就与中国传统文化天然同构,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伊斯兰文化是“中国的”文化,而非“世界的”文化。
关键词: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传播;融合;同构
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告诉我们,世界历史上存在着或存在过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玛雅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欧文化等八种自成体系的文化,而“每一种文化,像每一个人一样,有其幼年、青年、成长、老年的时期”① [德]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田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页。,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都会经历一个从茁壮成长到衰老死亡的过程。施宾格勒的思想影响了阿诺特·汤因比和塞缪尔·亨廷顿,后者写了《文明的冲突》,指出当今世界的冲突,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文化的冲突。直到今天,施宾格勒、汤因比和亨廷顿的观点仍然不算过时,尤其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然而,伊斯兰文明自传入中国以来,一直与中华文明和谐相处,成为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共处的典范。究其根源,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它自身就是一个多种文化元素相融合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它能够不断的汲取新的文化元素而融合创生;另一方面,特殊的历史境遇使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具有区分于原生性伊斯兰文明的特点,它的基本属性已经不再是世界的,而是中国的,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式中,γ,s分别为动目标的幅度和导引矢量,c为杂波分量,n为噪声分量。根据MVDR准则,通过拉格朗日乘子法求解可得使输出信杂噪比(SCNR)最大的最优权矢量为
一
考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诸因素之间存在的“出世”与“入世”互补关系。在汉语语境中,所谓“出世”,通常指脱离社会,对世俗之事漠不关心。北齐颜之推曰:“考之内教,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① 庄辉明、章义和译注: 《〈颜氏家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4页。宋时苏轼也在《书黄鲁直李氏传后》中说:“无所厌离,何从出世?无所欣慕,何从入道?”② 苏轼著,屠友祥校注: 《东坡题跋校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10页。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世”,常常与修道成仙结合在一起。而“入世”则是指回归世俗社会,参与普通人世间的社会生活。汉时刘向在《九叹·惜贤》中说:“妄周容而入世兮,内距闭而不开。”③ 王泗原校注: 《楚辞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8页。当代柳亚子在《自题磨剑室诗词后》中道:“但觉高歌动鬼神,不妨入世任妍媸。”④ 王翼奇、王蛰堪、吴金水等: 《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11年,第324页。“出世”和“入世”常常在一起连用表示相反的意义,比如《老残游记续集遗稿》第五回中说:“近来我的主意把我自己分做两个人:一个叫做入世的逸云……又一个我呢,叫做出世的逸云。”⑤ 刘铁云: 《老残游记续集遗稿》,民国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桂林刊本。清时全祖望在《梅花岭记》中也说:“其气浩然,常留天地间,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⑥ 全祖望著,黄云眉选注: 《鲒埼亭文集选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01—302页。“出世”和“入世”最初指的是一种个人生活态度,后来演变成为一种文化追求,甚至到今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基本基因。对于文化而言,一种文化是入世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就是世俗化的;一种文化是出世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就是非世俗化的。就此而言,宗教化的文化天然具有非世俗化的倾向,成为非世俗化的文化,而非宗教化的文化天然具有世俗化的倾向,成为世俗化的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在产生之初是一种纯粹的世俗化文化。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虽然有神的观念,但基本上不论证神的体系,“中国人一开端便显露出对超自然鬼神的轻蔑态度”⑦ 朱光亚、李朝东: 《德性和知识的分野——论中西哲学与文化精神的差异》,《探索》2013年第5期,第164页。,“子不语怪、力、乱、神”⑧ 程昌明译注: 《论语》,北京:书海出版社,2001年,第8页。。即便到了汉朝,儒学中引入了鬼神观念,演变出谶纬神学,但“鬼神”符号却还是一个宽泛的所指:“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⑨ 班固: 《汉书》卷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9页。这里的“天”不是一个类似于宗教的人格神,而是“一种有意志、有意识、有目的的超越的实体”⑩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页。,最终会通过“天人感应”落实到“人”。
然而,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世俗化的儒家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存在重要的一脉:非世俗化的道家文化。在中国,道家文化虽然始终没有占据主流地位,但道家对儒家却有很大影响,儒道合流也开始的很早。传说孔子最初就问礼于老子,归去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⑪《庄子》,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关于孔子是否问礼于老子的史料记载非常多,但学界争议较大,比较可靠的资料是《礼记·曾子问》中的记载:“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土恒,日有食之’”以及《水经注·渭水注》记载:“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注解转引自丁志刚、黄蕾: 《文化的重构与道德的重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到汉初,整个社会意识开始发生转向,儒生陆贾向汉高祖刘邦进言,天下“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⑫ 司马迁: 《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61页。所以在汉初,社会意识形态就已经确立为儒法合流、兼有黄老。道家分为“着重治国理政的黄老道学、着重精神超越的老庄道家、着重‘贵已重生’的杨朱道家。在先秦尤其是汉初,影响儒家最深的是黄老之学,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影响儒家最深的则是老庄道家。”① 朱光亚: 《儒学的融合历史溯源》,《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到后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开始了一种非世俗化的变革,那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入世的儒家汲取出世的道家和佛教思想,一方面使自身出世化,另一方面也使道家和佛教入世化。
①临床痊愈:症状、体征均消失,食欲正常。②显效:症状、体征显著改善,食欲基本正常。③有效:症状、体征有所好转,食欲一般。④无效:症状、体征无改善,甚有加重。
宋明理学是儒学将伦理道德超越化、神秘化、至上化的结果,更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结果,而“三教合流”的根源却在于儒、释、道之间在文化结构上的互补关系。在“三教合流”中,道教因佛教的刺激而产生,儒家因佛学的刺激而革新,佛学研讨的一些问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讨论的问题,佛学中的一些常用语言成为儒、释、道通用的语言,这使儒、释、道达到了一种融合会通。会通以后产生的宋明理学将入世的义理建立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上从而实现拯救,将出世的义理建立在“道统”之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而实现逍遥,拯救与逍遥,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儒教的出世化表现于“儒教”概念的流行及其对儒家的超越化、神秘化、至上化推动。“儒教”一词首先出现于《史记·游侠列传》,其中讲到:“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② 司马迁: 《史记》卷一二四 《游侠列传》,第2759页。到了汉末,儒者蔡邕正式使用了作为名词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③ 蔡邕著,邓安生编: 《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太尉杨秉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7页。此时对“儒教”概念的使用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发使用,然而随着佛教学说的侵入,儒者有鉴于佛教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开始有意识的使用“儒教”一词,以期建立一种以“儒学”为基本理论的宗教以与佛教相颉颃。这个宗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奉孔子为教主,臆想官僚机构为其组织,尊天坛、宗庙、孔庙、泰山为祭祀场所,定郊祀、祀祖、祭社稷、雩祀、释奠礼、五祀为祭祀仪式,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其最初形态是宋明理学。
传统图书馆多数采用纸质图书来实现学生的阅读教育,但在互联网背景之下,纸质图书愈发不受现代学生的青睐,学生更多地愿意翻阅手机、电脑等网络信息,对于此现象,许多高校都开展了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但收效甚微。在教育改革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传统的教育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学生,需要将现代学生的阅读习惯与阅读教育进行结合,形成新式的教育模式才能再次发挥图书馆的教育功效,因此就诞生了“互联网+”阅读教育模式。
然而,尽管宗教与非世俗化紧密相关,我们却并不能因为伊斯兰文化的深刻宗教背景而将其视为完全非世俗的。就伊斯兰教的起源而言,它创立的目的就是世俗化的,“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和倡导的宗教革命,实际上是一次建立统一国家的政治运动。”① 王灵桂: 《中国伊斯兰教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第10页。伊斯兰教创立之后,主张政教合一、发动宗教战争,它与世俗社会从来没有脱离过关系。到了19世纪欧洲人侵入伊斯兰世界,他们更是将世俗的法律强加到伊斯兰的教理教义中去。
二
之所以出现分歧,根源在于对世俗化的理解不同。就西方社会与伊斯兰社会的分歧而言,西方社会普遍信奉基督教,因此他们对世俗化的理解应该追溯到基督教中去,尤其是自由意志。毫无疑问,从自由意志对人类的限制而言,只要是宗教,其天性就必然诉诸于出世而非入世,因而是非世俗化的。奥古斯丁还仅仅将自由意志局限于人类无法控制的“恶”之存在,而到了康德,他将自由意志转向善良意志。按照康德,善良意志之根源乃是自由,而自由则来源于“物自体”,因为人类根本无法认识到“物自体”,所以人类的认识能力只能局限在感性、知性和理性的领域,而“物自体”将导致我们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神秘主义”,所以康德说:“我不得不限制知识的范围,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④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见《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页。所以,现今世界存在的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佛教以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最终都可以从中找到其非世俗的依据。
2.2 不同感染程度患儿hs-CRP、β-hCG、PCT检测结果比较 重度感染患儿hs-CRP、β-hCG、PCT水平均分别高于中度及轻度感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然而,毫无疑问,在伊斯兰社会中,作为非世俗化宗教的伊斯兰教也可以是世俗的,它只是用非世俗化的信仰来助推了世俗化的目的,就伊斯兰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演变而言,这一点得到了完美的阐释。伊斯兰教大约是在隋唐时期传入中国的⑤关于伊斯兰传入中国的时间,在学界有较大争议,影响力比较大的有“隋开皇中说”(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五)、“唐武德中说”(何乔远《闽书》卷七)、“唐贞观初年说”(金吉堂《回回原来》卷一)、“唐永微二年说”(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等等。本文注重于考察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之间的关系,不注重于伊斯兰传入中国具体时间的考察;因此,一概而论为隋唐时期。,当其时,中国传统文化正处于儒、释、道“三教合流”时期,这是以世俗化的儒家文化引入非世俗化的宗教文化时期。然而,面临“三教合流”,具有非世俗化本质的伊斯兰教却几乎没有参与,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始终是“三教合流”的旁观者。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一样,佛教来到中国以后,无论其内在信仰还是其外在形式都保持了一种非世俗化的形式,然而伊斯兰教多以群体性方式聚集在一起,尤其是他们注重于经商而不注重于对外传教,使中国的伊斯兰文明保持了一种世俗化的形式。
在以“三教合流”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大融合之际,伊斯兰教悄然来到了中国。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世俗化的非世俗体系。所谓世俗化,其英文表达是secularization,词根意义是脱离教会的还俗化,有教育与宗教分离之意,因此就西方宗教而言,世俗化可以理解为脱离宗教化,这与汉语语境中所理解的世俗化是一致的。在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受儒学影响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是入世的,也是世俗化的;他们只有在抱负不能施展、理想不能实现之时,才会去“采菊东篱下、幽然见南山”。此时此刻,他们往往在宗教信仰中寻找慰籍,而中国的宗教往往远离尘世,崇尚隐居,“乐山乐水”,不与俗世接触,因此都是非世俗化的,所以汉语语境中的宗教代表的往往是非世俗化。
其次,环保限产的政策压力可谓全年贯彻到位,尿素行业下半年整体开工率仅维持在53%-55%的水平,综合以往国内尿素表观消费量分析,市场供求基本处于平衡或略微过剩的环境下。导致大多数经销商逢涨必追,促使尿素涨跌交替的频繁出现。
当然,也有人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伊斯兰国家的政教合一不仅仅是其世俗化的证据,更是其非世俗化的证据。在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古兰教和圣训是新国家的主要依据”,甚至“在伊斯兰教的早期,除了伊斯兰教法,别无其它法律”② [印]阿斯加尔·阿里·安吉尼尔: 《伊斯兰与世俗主义是否相容?》,王向珣译,马睿智校,2015年2月14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214/08/15549792_448501425.shtml.。近年来,在欧美,很多人认为因为伊斯兰教的非世俗化,与穆斯林有关联的政治事件或极端主义活动频频爆发,给整个西方社会乃至人类带来了危机。因此他们主张,如果要追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必须剔除伊斯兰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重要措施是使伊斯兰教走世俗化与现代化的道路。”③ 马景: 《伊斯兰教与世俗化理论及其实践困境》,《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4期。
截至2018年10月10日,在PubMed、Embase和Cochrane数据库中分别检索到相关文献91、18和14篇;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通过阅读标题和摘要剔除72篇文献;通过全文阅读剔除26篇文献,最终纳入11篇文献[11-21]。文献筛选流程如图1所示。
三
穆斯林所具有的优势直到明朝建立后才有所改变,明朝建立以后,大部分蒙古人退回到蒙古高原一带,而色目人由于人数较少,并且与蒙古人“不相类属”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迁徙。为了使“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同化”,明政府“明令蒙古人与色目人不许本类自相嫁娶”④ 金宜久: 《伊斯兰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89页。,这“使回回人普遍有了被压迫、被歧视的感觉,开始对来自其他民族的伤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反应”,致使“由各个民族聚合而成的回回人,为了适应明朝的社会环境,开始自发的团结起来”⑤ 王灵桂: 《中国伊斯兰教史》,第136、137页。,出现“奉其教者,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⑥ 陈仁锡: 《皇明世法录》卷八十一,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81页。,“主其教者,或往来京师,随路各回,量力赉送,如奉官府云”⑦ 严从简: 《殊域周咨录》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91页。的局面,“天下回回是一家”的观念逐渐形成。
随着蒙古人对东方的征服,没有参与“三教合流”的伊斯兰文化得到了一次在中国传播的机遇。大约在公元13世纪中后期,蒙古人逐渐确立了在中原王朝的统治地位,他们实行四等人制度①蒙古人、色目人、南人、汉人四等人制度,最早由民国学者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提出,然而学术界迄今并没有发现元代实行过四等人制的法令;但这种等级划分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它主要反映在一些具体政策和规定中。例如,汉人打死蒙古人需要偿命,而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汉人如当兵则不许充宿卫,如当官也往往只能做副贰。这些法律规范大致明确了上等人对下等人所享有的一些特权。,成为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自然列为第一等级,色目人被蒙古人视为统治的重要助手列为第二等级,这就使“不少波斯、河中、突厥斯坦之穆斯林,冀求富贵于窝阔台、蒙哥之朝,相率而至。”② 王灵桂: 《中国伊斯兰教史》,第130页。作为第二等级的伊斯兰在科举、刑律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比如,《元典章》规定:“同一盗窃也,其一般法律,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而蒙古人犯者,不在刺字之条。色目人犯盗,亦免刺刻断。”③ [瑞典]多桑: 《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37页。再比如,仁宗延佑元年(1314)恢复科举取士,在名额分配上不顾四等人巨大的人口基数差异,规定四等人乡试会试录取名额相等,这种平均分配造成了录取率上的极大不平等。
然而,虽然在明朝的时候穆斯林的地位比起元朝有所下降,但并未遭遇歧视,明王朝基本上实行了民族平等政策。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不久就撰写过《至圣百字赞》称赞穆斯林:“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祁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贯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⑧ 刘智: 《天方典礼》卷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5页。与此同时,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穆斯林的政策。洪武时期,“下敕修建江南、陕西两省清真寺。南京净觉寺、西安清修寺、松江清真寺等都是洪武年间新建或重修的。除了诏令修建清真寺外,朱元璋还鼓励各府州县自建礼拜寺。”⑨ 何孝荣、崔靖: 《明代政府对伊斯兰教的基本政策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分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4期。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敕谕保护伊斯兰教:“朕惟人心能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导化群迷,故以天赐福,享有无穷。爱尔赛亦的哈马鲁丁,早从穆罕默德之教,笃志清修,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见兹善行,良可嘉焉。今特赐尔敕修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人等一应毋得侮慢。敢有故违朕命,侮慢欺凌者,以罪罪之。”① 刘智: 《敕诰清修寺护持文》,《天方至圣实录》卷二十,上海:广文书局,1976年。除了这些措施,明政府还重用在华的穆斯林担任政府重要职务,选派专人翻译穆斯林的经典和历法,对甘肃地区的穆斯林免税等,这些都体现了明政府对穆斯林的政策是保护性政策。甚至由于这些保护性政策过于倾斜穆斯林,导致民间一度出现明太祖朱元璋是回族人的传说。②白寿彝先生曾在其《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一书的注释中提到,明太祖朱元璋是回族这一民间传说。后来又有一些认同朱元璋是回族的学者也纷纷提供了史料依据,大致主要有:朱元璋出生于凤阳南城朱氏族群内,元末凤阳北城皆汉民,南城皆回民;朱元璋的原配妻子姓马,这是回民的常见姓氏,而马氏不裹脚,这是回民女子的特征,而当时回民是不嫁汉人的;朱元璋曾出家为僧的皇觉寺,原来是一座清真寺,其出家为僧很可能是在清真寺里做经堂学生等等。但这些所谓的证据仅仅是猜测而已,没有确切的史料能够直接证实朱元璋是回族。其实,明朝建国后有限度地提倡伊斯兰教,并不是朱元璋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出于他“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之需要。这种民间传说的流行,至少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明王朝对穆斯林至少是不排斥压迫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保护性政策。
但是,到了清朝,信奉伊斯兰的回回人和汉族人一样,被满清统治者视为被征服的对象,于是,“与明朝相比,穆斯林的政治地位明显下降了”③ 王灵桂: 《中国伊斯兰教史》,第144页。。清朝统治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本就不承认伊斯兰教,也不承认穆斯林作为民族的存在,警告其“倘自谓别为一教,怙恶行私,则是冥顽无知,甘为异类。宪典俱在,朕岂能宽假乎?”④《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82年。雍正皇帝曾针对署安徽按察使鲁国华的奏折批示到:“回民居住内地……妄立把斋名目,违制惑众。应请严行禁革,恪守典章,违者照律定拟。”为了加强对穆斯林的管控,清政府在回民居住之处“备造册籍,印给门牌,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除设立牌头、甲长、保正外,选本地殷实老成者充为掌教。如人户多者,再选一人为副,不时稽查。”⑤《清世宗实录》卷九十四,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82年。这样,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穆斯林的地位由在元朝时作为统治者的助手,下降到在明朝时作为一般平民,又继而下降到了在清朝时作为被征服统治的对象。近代伊斯兰凝聚力的形成,清王朝的压迫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四
元末明初,蒙古人被赶回蒙古高原尤其是中亚一带,但依然是能够与明王朝抗衡的力量,为了防范来自他们的侵袭,明王朝严守边疆、闭关锁国,造成了丝绸之路的中断。到了十六、十七世纪,阿拉伯国家的海上霸权又被欧洲新崛起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取代,香料之路也基本断绝。丝绸之路与香料之路的断绝使来到中国的伊斯兰文明进入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从此开始了“带有中国社会特色的演变”。
一种思想体系首先应该是语言体系,而中国伊斯兰的传播所缺乏的恰恰是语言体系,“伊斯兰的经学家们认为,《古兰经》作为真主天启的经典,如果翻译成外语,势必会产生曲解和误释,因此在阿拉伯帝国初期,《古兰经》被禁止翻译成外语。”这样,伊斯兰文明传入中国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古兰经》的传播都只能通过口口相传,大多数中国穆斯林对《古兰经》只闻其音,不解其义,甚至“直到清朝初期,中国知识阶层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尚处于片言只语。”① 王灵桂: 《中国伊斯兰教史》,第217页。丝绸之路断绝之后,中国的伊斯兰学者不得不独立研究和阐述伊斯兰教义,这就无法回避《古兰经》的翻译问题。然而,一直以来,伊斯兰传统对《古兰经》翻译禁忌的存在,使他们一般都不涉足对《古兰经》的翻译,这就使对《古兰经》的翻译一般由非穆斯林发起。按照奎因的理论,两种从来互不相通的语言根本无法正确互译,因为语言必然包含理论命题,而理论命题只是解释经验事实的人为的虚构。专业的穆斯林经学家不去翻译,而非穆斯林学者对《古兰经》翻译的曲解更多,这样,伊斯兰传统对《古兰经》翻译的保守态度不但没有阻止对伊斯兰的曲解,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曲解,这就使伊斯兰的经学家被迫打破传统进行《古兰经》的翻译,但出于传统的禁忌,他们反复声明:“天经圣谕,皆本然文妙,无用藻饰,兹用汉语,或难符合,勉力为之,致意云尔。”② 刘智: 《天方至圣实录》凡例。
实际上,翻译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对历史的主观理解同时也是历史造就的客观效果。所以对《古兰经》的翻译史,其实就是中国伊斯兰学者对伊斯兰理论体系的创造史,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创造的客观结果就是形成了当下中国伊斯兰独立的凯拉姆体系。这个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同构义理关系,宋明理学以前的中国传统儒学是世俗化的,而佛教和道教是非世俗化的,宋明理学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合流”,使中国传统文化集世俗化与非世俗化于一体,而穆斯林既然是以非世俗化的信仰助推世俗化的目的,那么其自身就必然也是集世俗化与非世俗化于一体,这就使宋明理学以来的中国传统儒学与中国传统的伊斯兰凯拉姆体系“存在许多相通或者相同之处,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先天的思想基础。”比如,“两者都反对佛教、道教的出世主义,同样看重今世,因此也很重视人生伦理道德的修养以及对现行秩序的维系。儒家主张小不忍则乱大谋,伊斯兰教注重顺从、坚忍;儒家倡导中庸之道,认为过犹不及,伊斯兰教则主张正路,反对过分之举。”③ 王灵桂: 《中国伊斯兰教史》,第205页。
在漫长的融合历史中,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相通之处更多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影响。由于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限制了伊斯兰的话语语境,所以中国的伊斯兰凯拉姆体系所关注的焦点,仍然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之内。比如,中国的穆斯林讨论“真一”与“太极”的关系、格物与致知的关系、信仰与人性的关系、“五功”与“五伦”的关系,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儒学中常见的话题。伊斯兰文化以儒家思想和语言阐述伊斯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典章礼仪、民风民俗,他们“本韩柳欧苏之笔,发清真奥妙之典”,以达到“以儒语明其义”,逐渐完成了伊斯兰文化在教义教理上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伊斯兰的风俗习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比如在伊斯兰的宗教建筑中,引入了中国传统的雕梁画柱,融会贯通了中国的建筑风格,甚至有的清真寺“望之外表,几与僧道庙观无稍差异。”④ 王灵桂: 《中国伊斯兰教史》,第235页。在语言方面,自明朝开始,由于中国的穆斯林与汉族处于“大杂居”的状态,他们淹没于汉语的汪洋大海中而不得不逐渐放弃自有语言,汉语成为其通用语言。在服饰、姓名等方面,他们更与汉俗毫无差别,在婚丧嫁娶等方面也有明显的汉化痕迹。在伦理道德方面,他们接受了中国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以致于伊斯兰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亲属关系与汉族人几无区别;他们讲究与人为善、赈孤救贫,提倡勤俭节约、安贫乐道,符合儒家伦理;尤其是他们重视知识、尊崇学习,认为“归真可以认主、明心可以见性、修身可以治国”,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一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融合的漫长历史中,在穆斯林内部形成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可从穆斯林内部流传的一首打油诗中些窥端倪:“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住海东,惟有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① 严从简: 《殊域周咨录》卷十一,第391页。这是中国穆斯林与儒、道、佛关系的写照。可以说,丝绸之路与香料之路的中断使中国的伊斯兰文化体系相对独立,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影响使中国的伊斯兰凯拉姆体系成为“中国的”而非“世界的”,而中国的穆斯林,在不断的历史演变中,逐渐成为中国儒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之一。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
ZHU Guang-ya
( College of Marxism, Yango University, Fuzhou 350000, China;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Central China Minority,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Zhengzhou 451150, China )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combination of entry into and withdrawal from the world. Entry means salvation in Confucianism and transcendental bliss in Taoism. This entry and withdrawal constitute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Chinese; salvation and transcendental bliss embody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lamic culture as a religious civilization should be marked by transcendental bliss; however, since it came into being, it is a secular system. As a cultural system integrating secularization and non-secularization, Islamic culture is naturally homogeneou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as become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is sense, Chinese Islamic culture has become "Chinese" culture rather than the "world"s" cul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Islamic culture; communication; integration; homogeneous
中图分类号:B9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9)02-0121-08
收稿日期:2018-12-26
作者简介:朱光亚,男,河南许昌人,哲学博士,阳光学院副教授,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中原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现象学、诠释学和宗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潘文竹
注:本文系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2017年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中原地区‘三教合流’背景中的伊斯兰教”(2017YB012)的阶段性成果。
标签:伊斯兰论文; 伊斯兰教论文; 穆斯林论文; 中国论文; 世俗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伊斯兰教(回教)论文; 对伊斯兰教的分析与研究论文; 《东方论坛》2019年第2期论文;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2017年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中原地区‘三教合流’背景中的伊斯兰教”(2017YB012)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阳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中原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