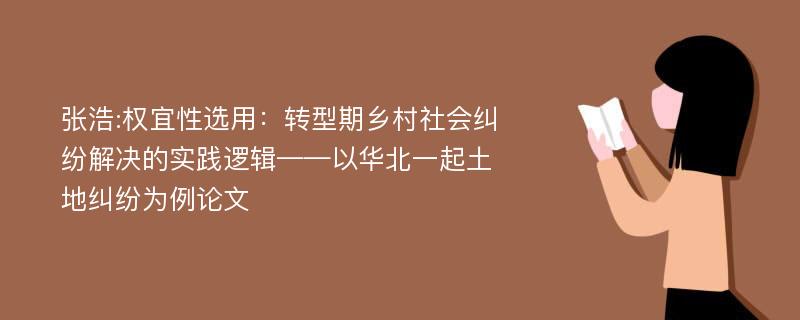
摘要:讨论了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实践与逻辑。指出转型中的乡村社会,存在着多种纠纷解决的途径和规则,供民众权宜性地选择使用,而且多种规则在共同推动纠纷解决的同时,也埋下了潜在的危机。这其中,司法途径虽有一定进步,但囿于内外局限,在民众那里并不享有优先或权威地位。认为法律的制订和实施,需要考虑民众的认知、感受与接受程度。
关键词:社会转型; 纠纷解决; 法律实践; 权宜性选用
一、研究问题: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纠纷如何解决
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快速而深刻的变迁和转型过程中。依据孙立平的说法,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或者“传统、社会主义—现代”的转型过程[1];或者如黄宗智所指出的,中国自近代以来就是一个长时期混合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在当下更是混合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等不同类型,因此“转型”一词用于中国,应被理解为一种持久的并存以及产生新颖现象的混合[2]。在这样的混合过渡之中,旧有的规则不再管用,新的规则尚未建立,新旧纠葛,青黄不接,治理的实现和秩序的维系就成了问题。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本文主要讨论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问题。
云计算平台是一个强大的“云”网络,连接了大量并发的网络计算和服务,可利用虚拟化技术扩展每一个服务器的能力,将各自的资源通过云计算平台结合起来,提供超级计算和存储能力[6]。白酒生产业务云平台把云计算引入到白酒生产业务中,将感知节点采集的白酒生产数据资源汇集在一个资源池中,资源池被白酒生产业务云平台管理之后,动态创立一个虚拟化资源池,把它变成新的白酒生产数据处理中心。用户只需向白酒生产业务云平台发送指令即可上传添加新的白酒生产信息,实现海量数据存储。
乡村社会自身存在一套纠纷解决系统。研究者的田野观察表明,一起发生在乡村社会的纠纷所经历的解决过程大体是一致的:最初或许是谋求在邻里之间获得解决,若此路不通,便会由村里的调解委员会出面调解,再不行,才会上诉法庭,寻求由国家法律权威来作出判决[3]。Michelson提出一种“纠纷宝塔”理论,指出中国农村纠纷解决中包括双方协商、信访、法律渠道等在内的多种方式,构成了一个类似于宝塔形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使用正式司法系统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民个人与政府关系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非正式的协商和当地干部的调解在纠纷解决中发挥着重要得多的作用,只有极少一部分纠纷在正式的司法体系中通过法官和律师解决。在刘思达看来,Michelson的纠纷宝塔理论固然抓住了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本质,但是这一理论假设纠纷解决的多种共存方式相互排斥,忽略了纠纷解决系统不同层级之间的互动。刘转而从法律服务提供者的视角提出一种职业层级系统理论,指出多元的法律服务提供者既无法形成通往法院的目的性路径,彼此之间也并非相互排斥,而是根据自身在系统中的生态位置来对不同的纠纷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农村纠纷解决的模式呈现出高度的个案化,从现场协商、冗长的双方谈判、干部调解、行政信访,直到法律诉讼,一切皆有可能[4]。
步骤1:确定风险标准云模型。根据相关专家的风险评价,确定风险等级的评估范围分别为Z1[0,0.25)、Z2[0.25,0.5)、Z3[0.5,0.75)、Z4[0.75,1.0)。按照公式(11)计算标准云见表8,其中i=0.05。
在由多种规则、机构和人员构成的乡村纠纷解决“场域”[5]中,信访的作用和影响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6-9],而“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10],则被人们寄予更多期望。中国进入改革时期以来,依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一方面,各种法律法规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截至2010年底,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 600多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11];另一方面,司法制度改革步伐加快,一些法律法规相继付诸实施。然而,尽管一批批的法律法规“下乡了”“上门了”,实践中也不乏“迎法入乡”[12-13]“依法抗争”[14-15]乃至“以法抗争”[16-17]的例子,眼见的事实是,法治的理想图景并没有实现:很多法律法规被制定出来,却并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而部分法律的实施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法治固然意味着法律被实施,而单单法律的实施却并不就意味着法治。在法学界,这一问题通常被置换为由法律移植所导致的“制度断裂”问题[18]。苏力对盲目的法律移植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法治进程的推进需要回到中国社会自身,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性以及正在进行的社会制度变革中寻求一种“本土资源”[19]。梁治平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间习惯法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借助于实际案例研究了当下乡村社会中民间习惯法的持续存在及其与国家制定法的互动关系[20-21]。苏力与梁治平的研究,一方面打破了法学界长期以来只关注理论命题和法律法规的探讨而缺乏实证研究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学界关于乡村社会中的法律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促使研究者将目光投向法律之外,从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中来审视法律及其实践[22-25]。
既然诸多方面的因素都影响到纠纷的解决和法治进程的推进,那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那些大量出现却又难以通过某种单一途径和方式加以解决的纠纷,其具体的解决过程究竟如何?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对纠纷解决各自起到怎样的作用和影响?透过位于“纠纷宝塔之顶”的司法诉讼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实践和表现,能否向我们传递出“中国正在走向法治”[26]的积极信号?
然而,村庄共同体具有两面性,其边界并非严丝合缝,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及至谢皮搅浑其中,村庄共同体的脆弱一面就暴露无遗了。村庄成员权(土地是河村的,只能归河村人),是村民们的基本坚持和根本道理,也是村庄动员的主要武器,村庄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全依赖于此。而一俟土地转往村内,即便接手的是令人不齿的小混混儿,村民的上述坚持和道理也就成了无的放矢。村里与董发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与谢皮的矛盾充其量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与董发可以对簿公堂,与谢皮则就万万不可了。同仇敌忾的激情一朝消退,村庄内部的纷繁纷争开始显现,事实上,在村民眼中,供销社纠纷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始终与村里其他因素纠葛杂处。首先是乡村中的情面和私人关系。河村基本上还是一个熟人社会,讲究人情和脸面,村干部都是村民一分子,都不大愿意在短暂的任期中为了一桩公共事务而与村民结下仇怨。其次是家族势力及村庄权力格局。河村人众事多,家族合纵连横,派系势力林立,形成了复杂多变的权力格局,使得供销社一事屡屡沦为权力争斗的工具和把柄。再次是干部腐败和紧张的干群关系。村里因供销社纠纷先后花销十多万元,大部分都是白条入账,在村民眼中,打官司成了村干部营私舞弊的机会。所有这些因素,彼此牵扯关联,都影响到河村团结一致向谢皮说“不”。
二、研究案例
河村①案例所涉人名地名均已遵照学术规范进行了匿名化处理。自2005年以来,笔者先后多次进入该田野调查点,查阅和收集相关资料,累积了大量对村干部、村民、县乡干部、县法院法官、代理律师等的口述访谈资料。在该村1999年03月—2011年11月有据可查的359次村庄会议中,有41次会议(占比11%,文字记录约3万字)涉及本研究案例(其中26次为专题会)。关于本案例的更详尽介绍,参见张浩.规则竞争:乡土社会转型中的纠纷解决与法律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是华北平原一个大村,拥有人口近4 000人,各类土地8 000亩(约533.3公顷)。村南300 m处,一条县域公路自西向东从农田穿过。新中国成立之初,西乡供销社在河村租用原属1户地主的房子办了1个代销店,20多年过去,小小的代销店渐渐无法满足村民需要。1976年初,西乡供销社与河村大队签订协议,选定村南马路边一处地块建设供销社分站。当年10月1日,县革委会下发《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批复》,表示“经地、县同意征用”。由于实际占地面积和补偿额度有所变化,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之后,乡供销社出钱出物,河村出工出力,拥有门店及库房38间的供销社分站建成并投入运营。
兹有西乡供销社需在河村大队盖分站,经公社批准,西乡供销社与河村大队协商,河村大队愿将村南耕地让西乡供销社占用。……共计叁亩柒分,由西乡社给河村大队产量赔款每亩150元……(协议书,1976年3月15日)。
……以上地4.04亩为我大队一级地。按国家规定每亩价格120.00元,共价484.80元。农业税和产量,均按国家规定减免(补充协议,1978年3月10日)。
1983年,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供销社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吸收生产队和社员入股,河村大队缴纳股金1 000元,成为供销社分站社员,分别于1984、1987、1990、1992年领取股金红利70、91、300、180元。进入1990年代,供销社系统渐趋萎缩,与此同时,分站所占土地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随着河村人口的增加和居住条件的改善,村庄渐渐南扩至公路边沿,公路两边陆续出现一些商铺,1992年,村两委在这里规划建起一条长约1 500米的商业街,分站正处在商业街核心地段。
小学数学是学生学习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将直接影响到学生今后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及学习能力。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应该重视学生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习和思考,帮助学生树立学习的信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知学习的乐趣,不断进步,让学生在鼓励和激励中发现数学的价值,为今后的数学学习奠定基础,并使学生的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得以体现和运用。
在本文研究案例中,案子最初是被作为普通民事纠纷处理的,尽管它无疑肇始于“总体性秩序”时期笼罩一切的党政权力。应当看到,在社会转型期,这种将历史遗留问题做“一般化”和“脱敏化”处理的机制和策略是有可能奏效的,虽然这样的处理策略和尝试在本案中没有成功(如果最初是由河村村民或集体买下分站土地,尽管从性质上土地已经转成国有,但是一来村民不见得了解和理解这一地权转换,二来反正是由村里人实际占用,也许就问题不大;如果初期的协调能够有效,董发接受了,那么也许同样问题不大;或者,法院判决被双方接受了,也同样不会有太大问题)。在涉入纠纷解决之初,司法权力也基本上能够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独立自主的裁决者和调停者出现,这表明了国家与法律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国家治理方式与以前相比已有所变化。
1997年8月13日,董发特意选在晚上带人来到河村,意图使用分站,结果与当时照看分站的原分站职工谢文发生争执,董发指使带来的人划破了不少谢文存放的化肥,并强行将分站房屋上锁。冲突惊动了村里人,村干部被紧急通知汇合,不少村民也闻讯赶来。群情激奋的村民将董发团团围住,推推搡搡地把他轰赶了出去。
力控末端执行器的传感器一般安装于恒力补偿作动部件与工具头之间,其检测反馈信号为恒力补偿作动部件与工具头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而非工具头与工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这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值,并主要受工具头和动力部件重力和惯性力的影响。因此,为提高工具头与工件间作用力的控制精度和响应速度,一方面应研发具有高功率质量比的动力部件,减小运动部件的质量,另一方面应开展工具头和动力部件的重力和惯性力补偿技术研究,其中包括利用多轴加速度计或陀螺仪等反馈信号解算力控末端执行器的姿态和质量力的补偿算法等关键技术。
例10.A dragon dance featuring a 56-meter Chinese dragon is performed a the Eighth Cantonese Temple Fair,symbolizing unity among china’s 56 ethnic groups.(附图)(舞龙)
一场波及众多且旷日持久的纠纷由此开始。
(一)协商与强制:软硬兼施的法外世界
轰走董发的第2天,河村村委会向西乡供销社发出通知,宣称将分站的土地和房屋收归村里管理,随即占据分站4间北库房作为办公室,并将剩余门店租给原分站职工谢文,供其销售化肥使用。
董发通过熟人向河村干部递话,并许以好处,结果再次遭拒。“道儿上有人”的董发不免心生恶气,在1998年初的某个夜晚带人手持棍棒闯入河村,砸了谢文租用分站的门,杀死他的狗,又闯入当时村主任家中,打砸一通,扬长而去。闻听声响的村主任匆忙自室内后窗爬出,翻墙逃脱,免遭挨打。村里虽然报了案,但终因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多位村民访谈)。
1128 Short-term clinical efficacy of radioactive 125I seed implantation in treatment of pleural recurrence of thymoma
(二)审判与调解:司法运作及其限制
1998年8月25日,董发一纸诉状将河村告上法庭。7个月后,河村村委会收到了自法庭转来的起诉状。村里随即递交答辩状,坚持对分站土地的所有权。县法院派出法庭组织合议庭审理此案,并于2000年3月14日做出一审判决,依据村庄和村民作为供销社股民的购买优先权,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认定西乡供销社与董发的买卖协议无效。
7月31号,我的家属突然病了,出了这事儿后她思想上有负担,犯病了,大面积脑出血。我是8月1号早晨接到消息,上午10点赶到县医院,她已经不省人事了。当时县里派出工作组,乡里也参加,在县医院维持秩序。县领导立刻打电话到市里,派专家来全力抢救,一天花了两万多块钱,活了几个小时,下午三点多去世的(村主任访谈,2006年7月16日)。
宣判当日,董发提起上诉。市中级法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县法院重审。重审的结果,认定西乡社与董发的买卖协议合法有效,河村村委会败诉。
就在县医院里,县乡主要干部与村主任商量妥善解决后事的办法,最终的协调结果是:拷人的2名法院人员公开赔礼道歉;由县里补偿村主任10万块钱,乡里和村里各自另出5 000块钱;免除河村一年的农业税45 300块钱,免费给村里提供300吨水泥硬化路面(2项相加计有12万元)。除了花钱消灾,县长还亲自责成县法院院长搞定供销社的事情。法院院长保证,只要河村拿出20万块钱,他负责摆平。
作者简介:黄向阳,男,汉族,福建南靖人,南靖第四中学,教师,中学专技10级,本科学历,研究方向:生物教学。
从法院和辩护律师那里,村干部和村民们得知,法院两审终判,案子不大好翻了。抱着仅有的一线希望,他们向市中级法院递交了再审申请书,向市检察院递交了抗辩申请书。2006年3月6日,东市中院发文驳回河村村委会的再审申请。
然而,尽管终审判决已下,董发却难以松一口气,因为他很快就看到,河村村民决心要阻止在他们看来不公的判决的执行。
2003年11月,县法院发布公告,责令河村村委会限期搬出占用的房屋。村两委班子开会商讨对策,会后向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局递交材料进行申辩。限期到后法院暂未执行。2004年2月12日,县法院再次下达通知,明确告知本月24日法院执行庭将来人强制执行。村委会随即展开一系列应对行动。14日上午,两委干部首次开会讨论应付,会后再次打印数十份材料,附上众多村民的联名,紧急送往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局。17日,5名村干部前往县法院执行庭探听消息。19日上午、22日下午、23日下午,两委会连续开会讨论,决定在执行日当天召开全体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大会,阻止执行庭来人执行,同时决定暂时空出村主任一职,以防执行庭追究责任和抓人。2月24日终于到来,大型会议如期召开,会议一开始就围绕着分站官司和应付法院执行展开,前一天定下的会议主题只字未提。会议拖得时间很长,但一直不见法院来人,所幸散会后也没有来,一场执行危机就此度过(分别参见2004年2月14日、19日、22日、23日、24日河村两委会会议记录)。
一次没来,不等于以后不来。2004年9月,执行压力再次出现,村干部到县里了解情况,被告知中央下达了指示,各地累积案件都要在9月份集中清理完毕①200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法院于当年下半年开展集中清理未结执行案件、执行款物及执行案卷活动。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5年3月9日)对2004年工作的回顾,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全年共执结案件2 150 405件,执行标的金额3 320亿元。,供销社的案子最迟缓解到当月20日。9月17日、18日、20日,村里接连召开两委会和扩大会,商量如何有效阻止执行。有人提出派几个老党员天天守护办公室,更有人灵机一动,提议成立一个村老年活动中心,既方便村里老人聚在一起下棋聊天打发时间,又可以凭籍这些老人天天守护办公室,随时阻止法院执行。于是,在最后期限前夕的19日下午,“河村老年活动中心”挂牌成立。
村里办了老年活动中心,不让法院执行。那时候我跟两个老头说:他们要是来了车,我躺在前边,你躺在后边,让他们前后走不了,把他们的车给砸了!(村民SQM访谈,2006年7月18日)。
县法院执行庭终于又没有来人。为什么县法院始终不曾来人呢?从大的背景看,执行难是长期以来积重难返的社会痼疾。就本案讲,河村人多势众,又占据一定情理优势,在涉及广大村民的问题处理上,县乡政府非常慎重,县法院对此是清楚的。
那片地方涉及到村委会和村民,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现在提构建和谐社会,你强制执行吧,就影响和谐稳定。现在很多案子都是社会问题,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出现的,光靠法律解决不了。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都集中到了法院,这是我们基层执法的无奈,我们也很挠头。(县法院副院长,2006年11月20日)。
判决了却无法执行,事情依然无解。不得已法院再次捡起“调解”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法宝。县法院院长比较了判决与调解两种纠纷解决途径的优劣:
执法既要讲究法律效果,也要讲究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要考虑社会稳定,考虑为党委政府保驾护航,这是中国执法的特点。……要是判决,按程序来,两天就判了,要是调解,两年都不一定调解得了,因为得做大量工作;但是判决的案子,很难执行,遗留的社会矛盾很多,调解虽然工作量大,但是双方满意,都能履行,社会效果好。(所以)所有的案子到了县法院,先去调解。(县法院院长访谈,2006年11月20日)。
事实上,早在案子受理之初,法庭便试图通过调解化解纠纷,只是当时双方分歧太大,数次尝试下来,未获成效,不得已才进入审判程序。在之后断断续续的审理与判决的过程中,调解和协商的途径依然持续敞开。其中一次是在2000年,在市中院人员协调下,时任村支书与董发当面达成一致意见,土地归河村,河村支付董发10万块钱,但在签协议时董发反悔,调解遂告失败。
与前几次调解有所不同,此次严格说来应被称作执行和解,因为先前判决已在产生影响了。鉴于案情特殊,法院院长亲自出面主持执行和解的工作,协调由河村拿出15万元,换取董发放弃分站土地,不料董发张口索要40万元,由于双方的要求相距甚远,此次执行和解终告无功。
(三)上访与干预:司法外的运作
如果说执行难可以被视作法院的软肋,那么上访一票否决就是地方政府的软肋。作为一项维护民众权益,拉近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制度安排,信访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其作用,但是随着维稳成为基层政府头等大事,信访指标考核日渐成为悬挂在基层政府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司法运作过程中,董发与河村干部双方都曾通过电话、信件或走访的方式向市县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和诉求。在河村一方,重审败诉后紧急向市、县相关机构发出多封上访信,表达村民对判决的不满和困惑;终审判决出来后,再次向市、县递交上访材料。在等待终审判决的时候,村干部们从一位法官那里了解到,只有推翻董发的土地证,翻案才有希望,他们因此专门到县土地局去,质问对方为何在董发与乡供销社签订协议后的几天之内就给他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按照《土地登记办法》的规定,土地登记应有一定的公告期),迫使县土地局表态:只要中院改判,立刻注销董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在董发一方,多次找市县法院和政法委要求强制执行,未获回应后曾试图将情况捅给媒体(被县法院劝阻),他老婆甚至跑到县政法委大闹(县法院副院长访谈,2006年11月20日)。执行和解无果后,董发一怒之下跑到北京上访。国家信访局的反馈随即一层层下到县里。
看客这一生态共同体只有围观起哄的“精神”,此外绝无任何价值可言。它创建出的集体人格,扭曲变形、丑陋不堪。而“文化”之所以能称其为“文化”,亦必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看客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传承下去的意识形态,因为,我们想消灭还唯恐不及(虽然这种意识形态延续了千年,一直没有消灭)!
事情惊动到中央机构,县里自然不敢怠慢,县政法委书记紧急召集相关部门商议,责成县法院院长具体负责,加快调解进度。县法院随即提出河村出20万,董发放弃土地的调解条件,软硬兼施迫使双方接受。考虑到河村一方是集体,作决定需要走程序且需要征得大多数百姓同意,所以县法院先做河村的工作,乡党委书记和县法院法警队先后去河村,劝说村干部接受这一安排。
2005年7月14日上午,河村召开两委会讨论,村支书、村主任、副支书等几名主要干部认为村里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太多回旋余地,因而倾向于接受20万要价。但是另有年轻气盛的副主任表达不同意见,认为一旦接受这一要价,村干部会因此背黑锅挨骂。最终讨论结果是只认可出价18万。鉴于兹事体大,第2天组织召开全体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这一决定。大会如期举行,党员和村民代表一如既往对分站土地属于村里进行了坚持,对官司败诉和历经长时间不能解决表示了不满,对干部做事是否尽心尽力提出了质疑。53名党员、村民代表对两委会前一天的决定进行签字表决,同意43人,不同意2人,弃权8人(2005年7月14日、15日河村会议记录)。
2005年7月21日上午,县法院一行4人再次来村协调,带队的法警队队长的规劝颇有施压之意,却再次被村干部顶回。河村干部的表态令法院协调人员感到失望和恼火,但是任务棘手难办,却又要限时解决,协调人员决定加大对村干部施压力度,力争月底前一举解决问题。
谢皮对自己成为村庄舆论的众矢之的丝毫不以为然,反倒是在他一而再的攻击举动下,原来团结坚固的村庄共同体开始土崩瓦解。正如董发所预期的那样,村里面对一个外来人可以做到同仇敌忾,而面对一个村内地痞的挑衅却束手无策。
7月26日上午八点半,我和支书、副支书应约去县法院法警队。刚到法警队,副队长××便拿出拘留手续说:村主任留下,你们两人回去做工作,今天下午5点之前必须拿出20万,把这事儿调解成。我说:我们是给河村老百姓办事的,拿不拿这20万,得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现在村民意见太大,我们得回去做工作。这时候法警队长×××进了屋,他说:如果你们今天拿不出20万元,或者村委会不搬出,明天就送村主任去拘留所。我对×××的说法非常不满:你们凭什么拘留我,我犯了什么法?法警队长叫来政治处主任,以态度强硬为由,强行给我带上手铐,时间长达63分钟(村主任上访信,2005年7月26日)。
当天回村,村主任立即写出上访信,第2天一早进城,要求县法院3天之内开除拷人者并赔礼道歉。法院院长表示认错,提出请吃饭作为赔礼;政法委书记表态法院这一做法过激了,会调查此事。3天之后,没有答复传来,村主任以身体不适为由抽身去了北京,面见其在某大医院任副院长且在当地拥有相当影响力的叔叔。村主任北上京城的同一天下午,村里召开党员、村民代表大会,村主任被拷的消息公开了。党员村民代表群情激奋,要求两委干部停止一切工作,集中全部力量为村主任讨公道。闻讯赶来的村民迅速向村小学校聚集,准备挺入县城。村支书一看局势要失控,紧急联系县乡,县乡即刻调集人马,由县委办主任带队、多部门人员组成的县乡联合工作组,当天傍晚进驻村里。工作组一入村,首先安抚村两委干部,对他们的努力和工作成绩表示肯定,接着到村主任家表示慰问,并连夜到一些态度激愤的村民家里苦口婆心地做劝说工作。第2天上午,工作组组织召开两委干部、生产组长、党员、村民代表扩大会议,两百多名普通村民自发到场参会。工作组表态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答复,20多位村民先后发言,要求法院公开道歉,要求严惩拷人者,要求重新处理供销社案子。一番安抚工作初步稳住了村民的激烈情绪。当天下午,工作组兵分3路,一组继续做村民安抚工作,处理被拷事件的善后;一组设法联系村主任,商谈其检查医治费用和精神损失的补偿;一组负责供销社案例的研判和重新处理。终于,一系列紧张工作之后,村里局势渐趋缓和,村主任也捎回了善意的口信。
然而一起突发事件的出现,使得局势急转直下——村主任的老伴儿得知村主任被拷消息后,一时急火攻心,脑溢血病犯,死在了县医院。
法院判决的依据,村民据以认为村里应当胜诉的理由及二者之间出现的偏差,值得在此稍作讨论。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来变动剧烈,鉴于数十年来剧烈的社会变动,土地制度变更频繁,土地权属认识模糊,由此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土地纠纷,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剧烈社会变动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本案例即属此类。为化解此类问题,在《土地管理法》之外,国家土地管理部门特别出台《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对不同时期的情况予以限定和澄清。其中第16条明确规定:“自一九六二年九月《六十条》公布时起至一九八二年五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公布时止,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所有:(1)签订过土地转移等有关协议的。(2)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的。(3)进行过一定补偿或安置劳动力的……”在本案例中,最初乡供销社与河村签订用地协议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供销社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基层社既是国营商业的基层单位,又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公社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所以适用上述条款。除了土地管理部门的这一规定,国家其他相关部门也曾先后针对一些典型案例给出指导意见或发布相关文件,例如国土资源部曾在2002年对河南一起类似的供销社土地权属纠纷案例给予复函作答,明确认定那一时期供销社所占用土地的国有性质[27]。然而,在本文案例中,不但村民对相关法规一无所知,因而始终坚持自己的“情”和“理”,认定分站土地属于村里;连司法机关相关人员对此也相当隔膜,缺乏对法律适用的掌握,因而只是笼统地援引《民法通则》作为判决依据。这一事实耐人寻味。一项法规,倘若未经广泛讨论,未得到大部分民众的了解和认可即行颁布,其合法性和有效性难免令人生疑。
村里的地块被人拿走,村里又莫明其妙成了被告,一个村主任家中被砸,另一个村主任更为此被拷,其老伴命丧黄泉。村主任老伴猝死的消息一经传出,悲愤莫名的村民们迅速涌入县城,围堵了县委、县政府和县法院。一位村民估计,六七百人去了县城;另一位村民表示,去的人不上千也有七八百。
人命关天,维稳至上,县里顿时慌了手脚。被撇在一边的工作组眼看横生意外,下访功亏一篑,只好仓促回撤,在县城里继续斡旋。县委书记当时在外,自县长以下,县乡领导全部出动,竭尽全力做安抚工作。一村民形容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就跟不是书记一样,就跟一个大队办事员一样”;村主任的弟弟回忆,法院院长兄弟长、兄弟短地叫他,他回敬道:“你甭这么叫,也甭来这一套!”
败诉的消息传回,河村一片哗然。同一个法院前后做出截然相反的判决,令村民们感到困扰和愤怒。村委会很快提起上诉,与先前的答辩状不同,上诉状有意识地强调了股民购买优先权,而不再坚持对土地“所有权”声索。然而,最终传来的消息还是令人失望,2003年7月27日,东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河村村委会上诉,维持原判。
依照当地丧葬习俗,逝者殡葬之后,第3日上坟,第7日上坟,之后每隔7日上一次坟,直到七七,丧事才告结束。9月21日,七七已过,距离拷人事件发生也已整整55天,县乡政府提出的补偿已经予以落实,这一天的下午,两委班子第一次召集在一起开会,结束了村里的无组织状态。
(四)“回到村庄”:共同体的坚固与脆弱
经历了村主任被拷以及其老伴去世的风波,村民们普遍以为,供销社纠纷可以籍此“划上一个句号”,土地回归村里已是“板上钉钉”。村干部甚至开始讨论起如何开发利用那片土地(河村两委会2005年9月21日会议记录)。
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河村干部拎着仓促借来的20万元送到县法院,却并没有换来预期中的最终了断。法院院长立下保证,亲力亲为,死追董发,迫其就范。董发情急之下,再递申请,撤销了原来的执行申请。依据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申请人撤销申请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一旦终结执行,作为一桩司法案件,也便就此终结。院长颜面尽失,大为光火,却也无可奈何。村里只好把钱拿回来,赶在农历大年三十还给了借主,并为此支付了1.8万块钱的利息(河村两委会2005年12月29日和2006年1月3日、19日会议纪录)。
案件虽到此为止了,但事情本身却并没有结束。当下的局势令董发的期望彻底落空。失望之余,他决定退出,不过,退出却不意味着认输,而正可趁这退出之际设法出一口恶气。董发倒手将分站转给了河村一个地痞混混儿谢皮。谢皮果然“不负厚望”,很快就去找村干部吵闹,宣称董发将供销社土地房屋作价28万转让给他了,一切善后事宜由他处理。
村里再次舆论哗然,村民同声挞伐这桩“不义的买卖”,谴责谢皮“吃里扒外抄村里后路”,是个“十足的卖国贼”。村民普遍怀疑,谢皮一直暗中与董发勾搭,先前村主任家里被砸,就是他给指路认门儿;此次2人的协议很可能只是一个“假买卖”,谢皮不过是充当董发的一颗棋子,从中渔利而已。然而,村民的怀疑和舆论讨伐以及村委会的拒绝提供证明(根据相关法规,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需要先征得土地周围四邻的签字同意,供销社土地三面环绕村道,其过户必须经过村委会出具同意证明并签字盖章),都无法阻止谢皮之后的一系列举动:2006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谢皮砌砖封死村委会大门(后经乡政府及派出所出面施压才重新打开);4月,占据了整排西屋,并在大院里拴了一条大狼狗; 7月中旬,连续锯断老年活动中心的三把门锁;8月初,将村委会办公室及老年活动中心房屋屋顶掀翻;9月,在老年活动中心门前堆上2堆沙子,阻止老年人进出;年底,私拉村委会办公室电线至西屋装空调,导致村委会2个月耗费近2 000块钱的电(村委会拒付电费,电管所断电,村喇叭自此断音,村两委也终止了办公室办公,此后每次开会都成了打游击)。在不断蚕食分站房屋土地以造成事实上的占有的同时,谢皮还试图通过恫吓村干部和抓村干部的“短处”迫其就范。每逢两委开会,他都去滋扰会场,施以威胁。在一封名为“关于河村主要干部大搞腐败的举报材料”的上访信中,他一口气罗列了时任村支书、村主任的七大罪状。考虑到村里不大可能出具证明,他干脆铤而走险,伪造了村委会印章,假冒村主任签名,制作了虚假的村委会证明,去土地局申请办理土地过户并竟然侥幸通过。不过,即便手持土地证,他终究还是心存忌惮,始终不敢明目张胆启用那片地方。直到他于2011年农历新年突然宣称以59万元将一半供销社分站土地转让给另一位村民郑增(村庄经济能人,与被拷村主任的儿子是“一挑儿”,在商业街核心位置经营着村里最大一个超市),他伪造公章、签名的行径才被村里觉察(2011年2月24日和3月16日村庄会议记录,邹堂访谈,2011年4月29日)。
2005年7月26日上午,河村主要干部村支书、村主任、副支书3人应法警队长之约前往县法院。不料,一次预想中的调解,演变成一场出人意外的拷人事件。
村庄共同体有其边界,这一边界可以是有形的、物理的,也可以是无形的、象征的,边界的存在宣示了共同体的存在。抵制乡社与董发的卑劣交易,拦阻董发抢占分站,朴素的自发反应促成了村民的首次集体行动;村主任家里被砸,进一步增添了村民的义愤;从吃上官司开始,村民们被真正动员起来(在他们心目中,打官司是仇人之间才会有的事情,当地有个形象的说法“坐法院”,坐牢的意思,可见法院与牢狱之灾连在一起);通过包括成立老年活动中心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成功阻止法院的强制执行,村民协作的力量开始显现;及至村主任屈辱被拷,其老伴病发身亡,引发村民悲愤围城,横扫官府,村庄共同体的巨大力量磅礴而出。在这时候,供销社分站那片地方,在村民心目中具有了特殊意涵,它不再仅仅是一块土地或者一个泛泛的名词,转而成为村庄共同体的象征,成为共同体边界上牢固的一环。
本文尝试通过华北乡村社会一起土地纠纷案例,讨论乡村社会转型中的纠纷解决,以期能够为认识当下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实事”提供些微助益。
现在问题摆在了村干部们面前。从道理上讲,私刻公章是触犯刑法的行为,既然村里已经去县土地局查证,证明印章、签名都是假的,那就应当追究谢皮,撤销其土地使用证。但是,原被拷村主任、现在的村支书邹堂和他的两委班子却不准备这么做。因为村里很快又要换届,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村干部也是村民的一部分,做干部只是做一阵,在村里生活则是世世代代。在这里,乡村社会自身的逻辑再次显现。村两委会讨论的结果是:谢皮的土地使用证已办,毕竟他是村里人,干脆把地方给他算了,不过他得给村里交五万块钱,算是给全村百姓一个交代(2011年3月20日村庄会议记录)。接着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两委会决议,谁有不同意见举手。大多数党员和村民代表显然有不同意见,但是没有人举手,会场静默一片。村支书于是宣布:既然形成不了统一意见,就此散会;10天之内,谁有不同意见,就来反映(村民ZT访谈,2011年4月29日)。10天过去,自然不会有人去反映。既然村干部都不愿领头追究,那些党员、村民代表和普通村民,纵使心有不满,谁又愿意直接出头与一个地痞混混对着干呢?
2012年农历新年前后,村里新一届两委换届选举,很大程度上受对供销社事情处理的影响,邹堂黯然下台。2013年6月8日,笔者再次来到供销社分站,偌大个院落,只留下半堵斑驳的墙,上面隐约能辨识出“保障供给”4个字。这片土地最终会“保障供给”谁呢?
三、权宜性选用:转型期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实践逻辑
一件看似普通的土地民事纠纷,持续近20年之久,其间几经波折,案中套案,前后将村干部、普通村民、县乡党政部门、县市法院悉数卷入,乃至引发一场轩然大波,迄今余波荡漾,悬而未决,这本身就构成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
从纠纷出现的原因看,民众对国家相关法规的隔膜与不认同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国家法规与民众普遍认知的情理相悖,需要检讨的便是国家法规的内容及其制定。法律的制订和实施,需要考虑民众的认知、意识、情感和态度。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法律文本无法脱离具体的时空和制度背景,任何法律如果要发挥实效,就必须首先成为一种适合当时当地情势的“地方性知识”。体制与法律的变革可以是跳跃的、间断的、急剧的、刻意人为的,而农民的认知固然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却是平缓的、连续的、缓慢的、自然而然的,有着极强的前继性。
死树在流动的水里获得重生,看起来都只不过是漂浮着的残骸的树枝、树皮和树心,在流动的水体中变成了许多海洋动植物的家园和食物。古老森林里倒下进入水中的树木中仍然含有多达70%的有机物,足以滋养细菌、真菌和昆虫等各种生物体。石蛾和蜉蝣的幼虫会依附在漂流木上,完成它们化为成虫的蜕变,这些虫子继而成为鲑鱼、火蜥蜴、蝙蝠和鸟类的食物。大的漂流木会对水流产生影响,形成水塘和回转涡流,成为鲑鱼的栖息地和产卵地,为鲑鱼幼鱼的成长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庇护之地,它们在这一片片由浮木开辟出来的海上“绿洲”中孵化、捕食和躲避可怕的捕食动物,直到长大离开游向辽阔的大海。
从纠纷解决的途径和过程看,多种方式和规则,如协商、强力(武力或武力威胁)、非正式调解、信访、司法审判与调解、党政权力,等等相继出现,交互并存。在其中,司法途径虽然被寄予了解决问题的期望,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受到的限制,其实践和表现却未必能够满足这一期待;相应地,在民众眼中,它也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可能途径,与其他解决途径相较并不享有优先或者权威的地位。应当说,历经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司法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和长足的进步,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大量的问题、矛盾和纠纷。
1997年初,在时任社主任魏某的操纵下,西乡供销社将河村分站以8万元价格转让给同属供销社系统的县生产资料公司经理董发。河村听到风声,派出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前往交涉,声称分站土地属于河村,应优先由河村买下。乡社主任当时应允,但过后还是私下与董某达成交易,后者随即向县土地局申请办理了为期50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根据河村干部的说法,魏某之所以坚持将分站卖给董发而不是河村,是因为对私不对公便于私下索取好处,也因为董发是“道儿上混的人”,有钱有势。
但是,司法途径自身的缺陷和所面临的困难(比如执行难的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它的角色承担和作用发挥。在本文研究案例中,一场拷人风波成为关键转折点。为什么会出现拷人事件?这虽系偶发的意外,却有必然的因素蕴含其中。首先,它反映出转型期乡村社会纠纷的解决难度之大,竟使得法院迫不得已出此下策;其次,作为具有相当位阶的执法人员,不可谓不知法懂法,却轻率以拷人相威胁,逼迫一方当事人就范,司法系统之鄙薄简陋,体制机制之不健全,人员专业素养之缺失,一叶而知秋矣。判决和拷人引发村民的愤恨与围攻,院长以其身份之尊亲自参与和解却终遭董发拒绝,拷人事件与执行和解破功又招致党委政府的不满与批评,司法的权威非但不能彰显,反在相关各方那里皆不受待见,转型期法院的尴尬、委屈与郁闷由此可见一斑。
拷人事件的发生,使得案子溢出民事纠纷的范畴,演变成为一个具有社会政治敏感性的事件,地方党委政府的中立态度和超脱地位也随之不复,在司法权力之外,党政权力的政治解决手段由此出场。拷人事件给法院落下个执法犯法的不光彩印记,宣告了以相对自主、不偏不倚面目出现的司法解决尝试的失败和黯然退后,同时也成为党政权力出场展开政治解决的开端。之后尽管司法途径依然开放,司法工作依然开展,但是其性质已迥然不同,此时它所履行的已不单是解纷止讼的职责,更多的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任务,想方设法摆平理顺,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党政权力由原来的超脱事外到后来的不得不出场,正体现了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司法途径难以独担大任迫使它时不时出面施以援手,但是悖谬的是,它的每一次出场,都对脆弱的司法造成负面影响。不过,毕竟法治已经成为治国方略,法律至少需要表面上的尊重,司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程序和做法。当董发申请执行的时候,法院就执行和解;当董发主动撤销申请的时候,案子也便就此终结,法院院长纵使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尽管受到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是没有人明目张胆地违抗法律的程序和权威。这一点不是无意义的,它反映了中国法治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的推进。
因此,我们看到,在乡村基层民众眼中,纠纷解决的各种途径和规则相互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分,司法审判、调解、信访、党政涉入等等都属于“上边”“政府”的“断案”,都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纠纷出现后,一旦初始的常规尝试无法奏效,当事者就面临下一步采取何种方式途径与何种行动策略的选择。在纠纷之初,一些解决途径尚未尝试的时候,当事双方均对己一方有利的解决有所期待。在经历了一些途径尝试之后,各自发现事情解决并未如己方预想的那般容易,在认清现实不再抱有幻想后,对各种解决途径和手段的有效性和成本也有所了解,然后又重新捡起先前使用过的一些途径和手段。
更多的徒步,给我一种新的打量城市的视角。我开始东张西望,发现这个城市的细部和内部。有时候心情沉重,有时候又感动想哭。在深夜的街头,我看到一个打扮入时的女子站在街角,一两分钟后她的男友骑着电瓶车过来。女孩上车,把头深深地埋在男友的背上。车水马龙,豪车呼啸而过,但是也有平凡甚至贫穷的人,在为自己的幸福打拼。
民众对各种途径和规则的选择、使用,取决于其对各种规则的熟悉和接受程度,各种规则选用上的方便程度,规则是否管用和管用的程度,等等。对规则的选择是权宜性的,目的只有一个,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在朝向自己希望的方向上解决纠纷,获得自己最满意而对方亦能接受的解决。从对途径和规则的选用看,这种对规则的偏好、比较、排序、筛选显示了各种规则机制在被用来解决问题时存在竞争和互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5]“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明确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向,适应经济发展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以新动能推动经济转型,以经济转型缔造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转型中的社会事实过于复杂难料,而任何一种规则各有其利弊短长,都不能一下子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都只是在将问题推向解决(或复杂化)的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从这方面看,各种途径和规则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促进和合作的关系。
如此一来,转型期的纠纷解决,就如同通竹竿,不求务必一下全通,不求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通一节算一节,一节节通下去,直到通完为止。至于每一节如何通,在通的过程中采用何种方式并无定规,全在当事者权宜性地权衡何种方式有效有用,法行则用,无效则扔。
经历了权宜性的选择和尝试,事情进入似是而非的模糊之中,但是这不是一团乱麻的模糊,而是有迹可循的模糊,乡村社会的某些特征蕴含其中。每一个阶段和场景都存在模糊之处,每一方都有部分道理同时各有其软肋,每一条规则都只是部分有效,每一种解决途径都只能发挥部分作用。多元规则并行使用的结果,便是折中、妥协和权宜的解决,由此形成一个所有当事人都不满意,同时却又都不得不勉强接受的结局,一种表面看上去四面光鲜,但是危机却蕴含其中的结局。转型时期的社会秩序就生成和存在于这种似是而非之中。在本文案例中,事情演变的结果耐人寻味。土地最终回到了村里,但却是以一种村民最不甘心最不情愿的方式回归的。一方面,土地终于没有直接回到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河村,尽管先前村委会反复表明这宗土地只能由村委会来接管。以国家相关法规为支撑,董发通过这一转手倒出的动作,一定程度上贯彻了自己的意志。强大的司法体制和政府都未能令村民屈服,然而一个人的搅局却令村民犹如被点中穴道般束手无策,这表明国家法规最终否决了村民的地方认知。另一方面,土地毕竟落在了河村村民手里(尽管是个边缘村民),民众的诉求尽管没能完全实现,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国家法规在这里体现了其妥协。在法理与情理的纠葛中司法判决没有被推翻,但是也没有完全照此执行,河村百姓总算将土地留在了村内,但却是在表面上承认了司法判决的前提下和基础上。无论如何,这也算是一种解决,尽管这是令所有人都感到不满意的一种解决,在这一解决的后面,村民的不满在郁积,村庄被进一步撕裂。
四、简短结语
在完成于1948年的著作《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正处于从传统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向现代社会的法治秩序蜕变的过程中,但是,当时的司法制度在乡村的推行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却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民众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以及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28]。
由图8可知,随着风干过程的延长,猕猴桃蛋白酶处理组干腌羊火腿的肌原纤维蛋白发生了降解情况,而且降解程度明显大于对照组。分子量为 63.0 ku~48.0 ku和 48.0 ku附近的蛋白条带逐渐变细;35.0 ku~25.0 ku中间的蛋白条带有所增加,颜色也逐渐变深;25.0 ku~20.0 ku中间的的蛋白条带逐渐变细;17.0 ku附近的蛋白条带逐渐变粗;说明猕猴桃蛋白酶可以降解干腌羊火腿的肌原纤维蛋白。
在岩溶裂隙发育,溶沟、溶槽较多的岩溶地层中钻孔容易发生卡锤,另外在钻锤冲破溶洞顶层时出现梅花形孔洞容易卡住钻锤。
70年的时间过去了,即便是在费先生写下《乡土中国》的年代,传统乡土社会就已经渐行渐远了。在70年后的今天,原来的乡土社会蜕变成了什么样呢?当下乡村社会的纠纷是如何解决的呢?人们得着法治的好处了吗?本文以华北一起土地纠纷作为研究案例,尝试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在依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的今天,法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力和有效的推进。与此同时,司法途径自身的缺陷和所面临的困难,再加上转型期社会矛盾冲突的极端复杂性,极大地限制了它的角色承担和作用发挥。中国的法治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
需要指出,本文关于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讨论是对一个有限范围内的单一案例进行微观考察的结果,这一考察无疑具有局限性。但是转型社会的最为复杂也最为引人入胜之处,便在于“实事”的多个面向,任何研究所揭示的都只是复杂面向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的内容。本文无意否定既有研究所涉的事实和所做的贡献,只是尝试提供和补充复杂“实事”的其中一个方面、一点内容。就此而言,笔者并不讳言指出:本文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较广泛的意义,因为存在着大量类似的纠纷案例,它们有着共同的过程、机制和逻辑,我们可以由此触摸转型期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某些特征。
参考文献:
[1] 孙立平. 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 社会学研究, 2005(1):1-24.
[2] 黄宗智.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1):83-93.
[3] 赵旭东. 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M].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2.
[4] 刘思达. 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39-42.
[5] 布迪厄. 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J]. 北大法律评论, 2000(2):496-545.
[6] 应星.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
[7] 胡荣. 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J]. 社会学研究, 2007(3):39-55.
[8] 张泰苏. 中国人在行政纠纷中为何偏好信访[J]. 社会学研究, 2009(3):139-141.
[9] 冯仕政. 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J]. 社会学研究, 2012(4):25-47.
[10] 贺卫方. 司法的理念与制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1-84.
[11] 中新网. “十二五”期间将重点加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以及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的立法[EB/OL]. (2011-03-14)[2018-05-25].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1/03-14/2904463.shtml.
[12] 应星. “迎法入乡”与“接近正义”:对中国乡村“赤脚律师”的个案研究[J]. 政法论坛, 2007(1):79-94.
[13] 董磊明, 陈柏峰, 聂良波. 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5):87-100.
[14] 肖唐镖. 中国农民抗争的策略与理据——“依法抗争”理论的两维分析[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4):27-34, 90.
[15] 应星. 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7(2):1-23.
[16] 于建嵘.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 社会学研究, 2004(2):49-55.
[17] 于建嵘. 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 文史博览(理论), 2008(12):60-63.
[18] 强世功. 法治与治理:转型国家中的法律[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19] 苏力.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20] 梁治平.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21] 梁治平. 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M]∥王铭铭, 王斯福. 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415-487.
[22] 强世功. 乡土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J]. 战略与管理, 1997(4):103-112.
[23] 赵晓力. 通过法律的治理:农村基层法院研究[D]. 北京:北京大学, 1999.
[24] 张静. 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1):113-124.
[25] 刘思达. 法律移植与合法性冲突——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基层司法[J]. 社会学研究, 2005(3):20-51.
[26] 苏力.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1-2.
[27] 国土资源部关于供销合作社使用土地权属问题的复函[M]∥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国土资源部土地争议调处事务中心. 土地矿产争议典型案例与处理依据(第一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364-365.
[28] 费孝通. 乡土中国[M]∥费孝通文集(第五卷). 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9:359-363.
ExpedientChoice:thePracticalLogicofRuralSocialDisputeSettlement——A Case of Land Disputes in North China
ZHANG Hao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Following Weber′s Sociology of law tra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social dispute settlement and legal practice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ere are several ways and rules of dispute resolution in rural society,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people to choose and use. The judicial way has a certain progress, but because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mitations, does not enjoy a priority or a position of authority.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rules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jointly promotes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ut also plants a potential crisis.
Keywords:social transformation; dispute settlement; law practice; expedient choice
中图分类号:C 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19)03-0025-10
DOI:10.12120/bjutskxb20190325
收稿日期:2018- 05- 25
作者简介:张 浩(1977—), 男, 河南许昌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博士
(责任编辑 刘 健)
标签:村民论文; 纠纷论文; 法院论文; 供销社论文; 村里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