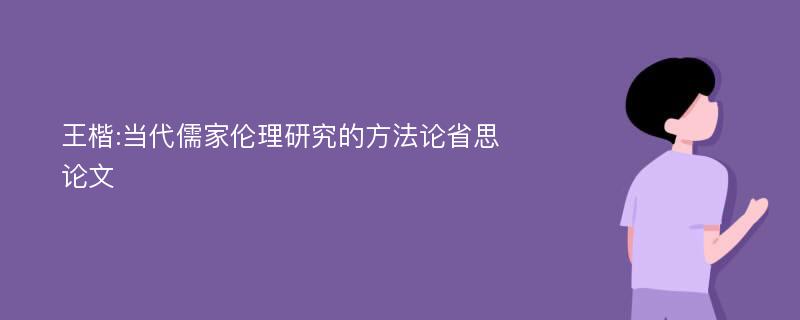
对伦理学形态问题的自觉反省原初只是发生在现代伦理学的语境之下。然而,这一问题本身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甚至是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伦理学的逻辑基点。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儒学在现代社会仍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伦理思想,而不止是一种历史的陈迹,就得直面这一理论问题,做出儒家式的省思和回应。唯有如此,儒学朝着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化方不失为一种真实的开新。这里所说的伦理学形态问题,不是运用伦理学的概念、命题或理论对某一特定事物进行论证,即不是评判某一特定事物在道德上的性质和意义,而是指对道德本身的论证,亦即“终极的道德论证”。对这一问题不同的解释正体现出对道德不同的运思方式,进而也就意味着不同的伦理学建构进路。于是,以此为基点,西方伦理学就有了三大流派的分别:以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为典范的后果论,以康德伦理学为典范的义务论,以及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为典范的德性论,即德性伦理学。
式中,A0为单井控制灌溉面积(hm2);Q为单井出水量(m3/h);t为灌溉期机井每天开机时间(h/d);T2为每次轮灌期天数(d);η 为灌溉水利用系数;η1为干扰抽水的水量消减系数,经抽水试验确定,要求不大于0.2;m为最大灌水定额(m3/hm2)。
后果论与儒家伦理
在道德终极标准问题上,后果论的核心理念在于: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不是动机。譬如,在竞技体育领域,服用兴奋剂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据信是因为它伤害了公平这一道德原则。然而,如果公平真的是终极的道德理由,那么,解禁兴奋剂也就自然地实现了公平(只是在部分人违禁的前提之下,才会出现公平与否的问题),而我们没有这样做,可见在公平这一道德理由的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层的价值诉求,这就是保护运动员的生命健康(兴奋剂会对运动员的健康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准此,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反兴奋剂以维护公平的价值基础其实在于保护运动员的生命健康这样一个非道德意义的目的。推论开来,不仅仅特定的德目,就连道德本身亦是如此。说到底,作为道德判断的终极标准本身则是非道德的,易言之,道德原是为了实现非道德意义上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后果论又称为目的论,其最典型的形态是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按照功利主义的理念,道德的最终标准在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跟我转述这个故事的小说家没有交待,好像这个男人没有固定职业,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说到特长么,就是在脂粉堆里称雄,嗜好谈情说爱而又厌倦婚姻,却又终于遇到了使他真正终结单身的女人。S的背景一片模糊,面目也含混不清,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劣迹斑斑而又悬崖勒马的猎艳者。据小说家后来在其小说中的考证,在遇到让他为之痴狂的那个女人之前,跟一个比他大得多的女人有过短暂的婚姻——该女人自称是一个通灵者兼瑜伽教练,一个性爱大师,有点神神道道。这在那个男子跟小说家讲述时不知为何没有提及。S苦恼于那个女人是一个外遇的瘾君子,而S也总能找到平衡的理由。”
功利主义可以是个体层面的,也可以是社会层面的,就后者而言,则一转而有国家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本位的道德观,国家功利主义与一向强调民生福祉的儒家伦理精神颇有契合之处。如所周知,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一个基本的特色就在于其强烈的入世情怀,时时以天下苍生为念。明乎此,则不难理解孔门品评古今人物道德优劣何以特别肯定事功的意义。《论语·宪问》载:
在道德的终极标准问题上,后果论认为“好”独立于并优先于正当,是一种典型的目的论理论。所谓“好”独立于正当,是说“好”本身无所谓正当或不正当,是一种非道德意义上的物件。所谓“好”优先于正当,是说一切道德行为的价值应视其与“好”的关联而定,凡是能够增进“好”的就是正当的,反之,凡是背离“好”的就是不正当的。简言之,赖以判断行为之道德价值(对/错、正当/不正当)的终极标准本身则是非道德的。与这种目的论立场相反,以康德伦理学为典型的义务论则认为正当是独立于并优先于“好”的概念。正当不依赖于“好”,并非达到某种“好”的手段,它本身即为自在的目的、自在的标准。在康德,一个行为在道德上的对/错取决于行为本身,而不理会后果因素。质言之,正是行为本身具有的特征或行为所体现的规则的特征使其在道德上是对的,或者是错的。也因此,康德特别强调道德规则的神圣性。
较之强调行为后果的目的论和关注行为本身(包括动机)的义务论,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为古典形态的德性论的思路又有不同。德性论聚焦在道德主体,将道德主体的品格特征作为道德判断的根本标准,实现了从外到内的视角转变,即从外在的行为到内在的精神性品格的转变。目的论和义务论关切的核心在于“什么是要做的道德上正当的事”?而德性论伦理关切的核心则在于“什么品格使得一个人成为道德上的好人”?前者的焦点在于“我应当做什么”(What I ought to do),而后者的焦点在于“我应当成为什么”(What I ought to be)。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来说,在目的论和义务论所重视的doing well之外,德性论更关注being well。从而,做一个道德上的好人成了道德判断的根本标准。
其在儒家,夫子所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正表达出以主体自我人格成长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儒家的“为己之学”实为一种德性论的运思进路。夫子有云:“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观此可知,不同的主体践履同样的道德法则,或出于“安”,或出于“利”,其内在的心志状态是不同的。在儒家,这种不同的心志状态具有根本性的意义。须知真正的道德行为并非仅仅在外在形式上符合特定的客观标准,还得出自特定的心志状态(作为精神性定势的道德品格)。当然,这并非说“利”而“仁”在道德上就全无意义。儒家肯定善,既欲求理想道德的愿景,同时又不失对现实道德的层次性的体认,故而有“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礼记·中庸》)的讲法。然而,这里的“一也”只是就行为及其客观的社会性效果而言的,如果说到主体自身内在品格的状态,则其间的层次性的分别实无从“一也”:
然而,如果转换到道德与存在的视角,我们所看到的将会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情形。其在功利主义,主体的自由被设定为首要的价值,道德之于主体则仅仅限于外在的工具性价值,而无关乎存在自身的实现和完满。不特如此,道德甚至因其是对主体自由的一种限制而被视为一种恶。而作为一种恶的道德的存在之所以是必要的,仅仅在于它能够防止更大的恶,比如社会的无序或恶序,人与人之间无限制的相互伤害,凡此等等。准此观之,在典型的后果论那里,道德并无任何内在的价值可言。其在儒家,一则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再则曰:“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人(格)的内在价值与尊严正在于道德,舍此则无别于禽兽。因此,整体而言,后果论对道德与社会关系的解释只是儒家政治伦理中的一个有限的环节,并不足以概括整个儒家伦理的理论形态。
义务论与儒家伦理
笔者依据实际工作经验及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详细分析现阶段我国青少年实际阅读情况,而后提出全民阅读活动的产生背景,最终介绍全民阅读活动在培养青少年阅读兴趣的过程中发挥出的作用,希望能够让青少年逐渐养成一定阅读兴趣,将人才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最终在我国构建可持续发展型社会的过程中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自其异者视之,则康德与儒家之间根本性的分别亦非寻常。基于反功利主义的义务论立场,康德强调道德法则的绝对性,既不考虑特定情形下的经验性因素,亦不理会行为所(可能)造成的后果。儒家虽然也同样重视道德的超功利性,但并非不考虑行为对他人或社会(可能)造成的后果,而是另有不同的理据在。在儒家,“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儒家对道德法则的理解重在其内在的意涵和精神,而非一味地拘泥于形式化的僵死教条。否则,“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也”(《论语·子路》),只能是得其形而遗其神,而一个通达的人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能够根据特定的情形做合理的“通变”,从而使法则的意义以恰当的方式及分寸得以实现。譬如,“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当然,儒家的经权观亦非是寻找某一个固定的点,否则,将如“子莫执中”(《孟子·尽心上》)一般枉费精神,而是基于对道德法则的意涵和精神有深刻、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在特定的情形下做出合理的反应、判断和选择,能够做到“以义变应”(《荀子·不苟》),“体常而尽变”(《荀子·解蔽》)。无疑地,这意味着一种高度成熟的实践智慧。孟子将这种境遇性的伦理原则概括为“时”,明乎此,则不难体认孟子对孔子何以有“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的赞叹。不特如此,同样是对道德庄严性的守望,相对于义务论以法则为基点的视角,儒家则表现出一种以主体为基点的视角。其在儒家,道德意味着存在的品质,由不得用外在的功利来衡量和交换。诚如孟子所言:“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在这里,儒家道德的超功利性所凸显出的是道德主体的人格尊严,要求行动者独立而不迁,不以外在的境遇为转移,自觉超越一己之私的考量。质言之,相对于外在的道德法则,对儒家而言,真正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乃是主体内在的道德品格。在这个意义上,与儒家伦理旨趣相合的是德性论,而非康德的义务论。
“王九,不要着急,慢慢的会有人来的,你瞧,这莲蓬,不是大爷们的路数?咱们呆一会儿,就来玩个什么给爷们看看,玩得好,还愁爷们不赏三枚五枚?玩得好,大爷们回家去还会同家中学生说:嗨,王九赵四摔跤多扎实,六月天大日头下扭着蹩着搂着,还不出汗!(他又轻轻的说)可不是,你就从不出汗,天那么热,你不出汗也不累,好汉子!”
与康德伦理学的对话,对于传统儒家伦理的理论重构有着深刻的意义。自其同者视之,被康德作为道德至高原则的可普遍化性原则实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恕道精神息息相通。其在儒家,人的觉醒不仅仅停留在自我主体性的觉醒,更意味着在生命的感通中体认到他者的存在,故当“审吾所以适人,人之所以来我也”(《荀子·王霸》)。吾人只需观“从人从二”的“仁”字而玩味之,自当知此言非虚。因而,“仁者爱人”在本体论的层面首先就意味着将他者视为与自我对等的价值存在。推而下之,康德的可普遍化原则和目的/手段(工具)之分自然无悖于儒家仁道精神矣!不特如此,康德在道德的意义上对人的尊严的肯定更足可为儒家引以为知音。其在康德,不同于本能支配之下动物,作为理性存在者,人服从的是道德律,能够克服感性欲望的支配而超脱于动物。道德出自主体的自我立法,人服从道德乃是服从自我的自由意志。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正是道德自主使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超越于作为自然物的动物之上,拥有了作为人的尊严。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儒家这里,孔子就特别强调行动者的道德自主性,于此反复致意。一则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述而》)再则曰:“吾欲仁,斯仁至矣!”(《论语·里仁》)又则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不特如此,儒家更进而透过“人禽之辨”的观念肯定人之作为道德存在的尊严。这显示出,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儒家同样以自律道德作为中心的价值关切,与康德并无二致。
德性论与儒家伦理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在孔子,不受异族侵扰,社会的和平、安定与秩序,是为民众福祉之本,若有为此者,自当谓仁之大者。在这里,孔子显然是以民众福祉作为对为政者道德评价的基本考量。孟子发挥夫子之义,论仁政每以民生为衡准,以此评价政治治理的优劣,“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如果为政者不能保证民众的基本福祉,就不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这在政治伦理的层面显然是一种后果论的道德观。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郭店楚简·五行》)
在这里,就行为之符合特定的道德规范而言,“德之行”与“行”若不异也。然而,二者在道德上的价值实不可等量齐观。“德之行”不仅符合特定的客观的道德规范,更在于由内而发,以特定的精神性的心志状态为基础,在道德动力的意义上乃是出自主体“不容已”的精神品格,而所谓的“行”则只是符合特定的客观的道德规范的行为。分析此二者的分别,“行”只是客观道德上(不错意义上的)正当的行为,而“德之行”不仅在客观道德意义上是正当的,更呈现出道德主体德性人格的魅力和光辉。在此意义上,只有“德之行”才是真正的“德行”。明乎此,则不难理解孟子何以在“由仁义行”和“行仁义”之间做刻意的分别。在伦理学的意义上,这正表现出一种德性论的理论旨趣。
然而,儒家伦理又自有其独特的理论形态,多有德性论所不能范围者。论其大者,则有二焉。其一,儒家伦理虽然强调道德行动者的主体性,然儒家意义的道德主体并非原子主义式的个体,相反,它内在地蕴涵着社会的向度在其中,寻求在完善世界的过程中完善自我。事实上,仅取《大学》首章而观之,即当知此言非虚。委实,亚里士多德也同样将政治视为(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一种完善的过程。然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个体的善与城邦的善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而此二者的一体两面则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特色。就此而言,儒学当可谓即伦理即政治。其二,同是寻求主体的道德成长,不同于德性论,在儒家哲学的语境之下,人的完善并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完善的层面,更进而渴望对天人之际发生深刻的觉解,在天人关系中安顿生命与价值,从而超越人固有的有限性,上升为一种宇宙论意义上的存在,一如《周易·文言传》所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其在西方文化,此等有限者与无限者之间的沟通,更多地是宗教中事,哲学则少有措意者。准此观之,儒学又可谓即哲学即宗教。合而观之,儒家伦理虽与德性论旨趣相合,然其自身独特的理论形态亦有德性论所不能涵盖者在。
意义与限度
笔者浅见,在会通儒家伦理的语境之下,三种西方伦理学理论各有所当,亦各有所偏。后果论——特别是国家功利主义形态的后果论——有助于理解儒家伦理的社会(民生福祉)关切。然而,儒家伦理对于存在价值的关切就不是后果论所能够解释的了。儒家与义务论都肯定道德的非功利性,强调道德的庄严。然而,与义务论的反功利主义的立场不同,儒家道德的非功利性并非不理会行为对他人或社会所(可能)造成的后果,而是重在强调主体做道德选择时应将一己之私利置之度外。同时,与义务论一味固守乃至僵化道德法则不同,儒家更关注道德法则所蕴含的精神实质,表现出一种实践智慧意义上的境遇性原则(“时”)。儒家与德性论都认为,较之外在的行为或规则,主体的内在品格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二者都强调真正的道德行为须以主体内在的品格状态为基础,寻求主体在道德上的完善,成为道德上的“好人”。然而,儒家语境下的人的完善,并不满足于单纯的道德完善(moral perfection),更进而寻求在宇宙论的层面安顿生命和价值。并且,儒家主体内在地蕴涵着社会的向度,致力于在完善世界的过程中完善自我。这就不是德性论所能范围的了。概言之,后果论、义务论、德性论,三种伦理学进路之于儒家伦理的会通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当然,本文的写作并非为了得出这样一种破坏性的结论——西方伦理学理论进入当代儒家伦理研究是不合法的,只不过是要对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意义和限度做自觉的省察,从而把握一种哲学会通中必要的分寸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摘自《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2期)
标签:儒家论文; 道德论文; 康德论文; 孟子论文; 伦理论文; 《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4期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