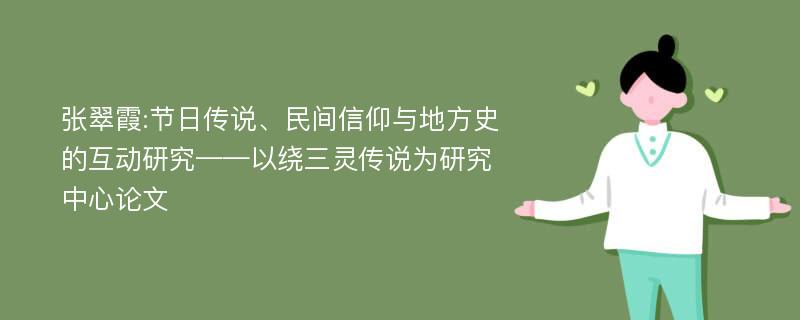
摘要:绕三灵传说在大理地区广为流传,口头传说与民间信仰彼此粘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节日传说在外来佛教本土化过程中被借用,后又被叠合嫁接到南诏地方王权的传说叙事体系中,成为目前流传最广的解释绕三灵节日起源及南诏王权来源的基本版本。绕三灵传说不仅是一个民间文学“文本”,更是一个社会史“文本”。它不仅承载着白族民众深层的自然崇拜与农耕信仰,而且在与民间信仰的广泛互动中,为佛教本土化播布提供了一个粘附性支点,并在与南诏、大理国政治王权的博弈中成为民众历史叙事的“地方性话语”。
关键词:绕三灵;民间传说;民间信仰;地方史
引 言
近年来,作为民间文学传统文类之一的传说,不断为民俗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所关注,这些学科开始重新审视传说并赋予其作为历史记忆的研究价值。学界对于这一有关口头叙事传统与民众历史记忆问题的研究取向,主要源于后现代思潮给民间文学和历史学研究两个研究领域带来的研究范式转换。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传说研究由传统 “文本”(text)研究转向 “语境”(context)研究,或者说是民众 “生活世界”(life world)研究,在文本研究基础上,开始关注“文本”背后隐藏的意义。这种研究趋势,有两种研究取向,一是关注民间文学“文本”作为一项社会知识生产,如何被能动地创造出来,关注“文本”知识生产过程,尤其是文本产生过程中各方社会力量的博弈与互动;二是关注民间文学“文本”如何“结构性地”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关注口头传说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勾连。这种研究取向,一方面挖掘口头传说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 “结构性意义”,关注民间文学“文本”的活态口头叙事及其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功能和价值;另一方面呼吁口头传说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关注口头传说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态”表演、传承及其变迁。
在历史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史研究领域,后现代史学动摇了传统史学探寻客观科学历史的终极追求。以福柯为代表的“知识考古学”打破了传统文字“信史”的客观真实幻象,对包括文字“信史”在内的史料进行重新审视,认为所谓的历史客观性和历史真实性只是文化建构的结果。所谓正史记载也好,野史记录也罢,同无文字表述,凭借口耳相传代代传承的口头传说一样,都是有关 “过去”的一种叙说,是社会权利话语建构的“文本”。因此,在有关历史记忆的研究中再去解释、甄别文献真伪已经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事实上,“历史记忆研究不是要解构我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而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史料,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然后由史料分析中,我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context),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认同与区分体系。”[1]历史正以各种异质、复杂、诡辩和矛盾的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有关民众历史的各种异质性表述恰好说明了人类历史的丰富性和鲜活性,所以福柯才说,“应当使历史脱离它那种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历史正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即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2]“知识考古学”就是要寻找这些看似不相统一,甚或自相矛盾的历史话语“构成的规则”,使我们关注的焦点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转移到“如何”成为真假并“为何”成为真假的问题上来。
绕三灵,白语称为guertsallat,也称作 “绕山林”、“绕桑林”等,节期为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①,是大理坝子春末夏初最为热闹的节日。2006年,绕三灵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出现。②本文有关绕三灵的研究,与以往学者聚焦节日仪式实践研究模式不同,主要关注绕三灵节日传说与民间信仰、地方史的互动关系。绕三灵传说在大理地区广为流传,口头传说与民间信仰彼此粘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节日传说在外来佛教本土化过程中被借用,后又被叠合嫁接到南诏地方王权的传说叙事体系中,成为目前流传最广的解释绕三灵节日起源及南诏王权来源的基本版本,为我们有关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民间传说与地方史的互动研究提供了一个民间文学样本。因此,对传说文本仅作静态的、微观的研究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追问:地域社会中的绕三灵传说是如何历史地被建构并广为流传的?遵循这样的思考路径,本文的研究以顾颉刚“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传说研究为原则,秉其“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和方法[3],将传说还置于其所属的地方社会,探讨绕三灵传说与民间信仰之间彼此粘附、借用的关系,并最终定型成为南诏王权传说,成为地域社会日常生活节日仪式实践的动态过程,并由此探求传说“层累叠写”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从信仰到传说:绕三灵传说的信仰神圣叙事
民间信仰是民间传说神圣叙事的内核。然而,从信仰到传说的过程十分漫长,其中,民间信仰世俗化是导致神圣信仰走向世俗传说的根本原因。“植根于民众深层心理结构之中的民间信仰的最早形态是原始信仰,它以神圣的叙事方式在民间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经过长期发展,这些带有浓厚神灵色彩的民间信仰逐渐走下神坛呈现大众化和模式化的流动态势,在此基础上诞生了许许多多民俗事象和民间传说。”[4]民间信仰由神圣走向世俗,民间传说也即开启了其以民众口头传说叙说、阐释、“操演”神圣信仰的历程。同时,伴随民间传说的讲述和流传,民间信仰在传说的时空播布中得以再次确认和深化,进而也扩大和实现了传说所承载的神圣信仰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和传播。
大理白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和农耕信仰是绕三灵传说叙事的信仰内核。首先,绕三灵传说是白族先民古老自然崇拜的神圣叙事。“很早以前,大理一片汪洋,人们居住在苍山上打猎放牧。他们每逢打到很多的野兽,便认为这是山神帮助了他们,便欢聚在山林之间,烧起火堆,烧烤野兽,边吃边唱,绕着山林尽情歌舞玩乐,以此赞颂‘苍山神’,并祈求继续得到保佑”。[5]无独有偶,《大理民间故事精选》“绕三灵”传说也说,山林打猎,庄稼丰收乃是“山林里的神赐给的”,“于是大家砍了漂亮的树枝当作神树,又找来些漂亮的竹杖,拉着、甩着、舞着、跳着,在山林里聚会,感谢山林之神的恩赐,也求天神年年降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好让大家生活安乐”。[6]与这两则传说类似,笔者在田野调查时搜集到的传说异文也说,“大理一带是水乡泽国,人们都是在山上住着,人们住的都是山洞和窝棚。人们认为天是最大的,只信天神。因此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到二十五,住在苍山上的人就来到现在文阁村上面的桑林谷去祭天,祈求风调雨顺。”③上述传说虽表述各有差异,但均表明节日起源与自然神灵崇拜相关,并将绕三灵视作娱神祭祀的节日。
④ 例如,白语中 huoflat一词,huof意为“花”、“花朵”,而lat为“园子”,huolat一词即为“花园”之意。
其次,绕三灵传说包含深厚的农耕信仰文化因子。大理洱海流域农耕文化也十分深厚发达。在传统农耕社会,男耕女织是一种常态的社会分工。其间,桑蚕养殖对传统农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且桑树在民间信仰中被赋予“神木”的地位。有学者认为,绕三灵节日中,作为祭祀队伍引导的“神树”,其最初形态也应当是桑树,只是随着社会生计方式变迁,神木桑树被更易于攀折的柳树所取代。[7]此为一说,但在许多有关绕三灵的传说均说道“桑树”、“桑林谷”、“桑树枝”等,也确有对“桑树”、“绕桑林”的特殊叙说。传说,五百神王建国皇帝和白族人民在一起,教大家种桑种柳、植树造林,盘田织布。他自己就住在庆洞庄,和村民共同中了很多桑树、柳树。每逢农历四月间采摘桑叶的时候,人们欢聚在庆洞庄,和建国皇帝一起,一面采摘桑叶,一面唱歌跳舞,唱累了,跳乏了,就把柳枝折来顶在头上遮阳。此后,便形成了一年一度的盛会,人们称为“绕桑林”。[8]此外,在有关绕三灵白语称呼guertsallat的语言学考证中,白语“guer”有 “游玩”“闲逛”之意,“sallat”,有研究者认为,“sal”汉语的对音字为“桑”,明代白语读作“soul”[9],而白语“lat”是“园子”、“园林”的意意④,因此,有学者也认为“绕三灵”应当正名为“逛桑林”[10],至于现在所用“绕三灵”、“绕山林”等”,颇有附会和想象之意⑤。此为一说,但白族农耕文化及农耕信仰之深厚我们可窥见一斑。
此外,如前所述,绕三灵节期在春末农历四月底,此时正是大理坝子准备移秧插种的时节。传说“东海龙王专管行云布雨。凡栽秧之前,坝子里的人们就又唱又跳,以使龙王得知后,即降喜雨”[11]。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原始农耕社会,人们对司雨主水之神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相传,“有一年,快到五月五端午节了,天上没下一滴雨,连洱海也快要干涸了。眼看庄稼种不下去,人们不知怎么办好。一个年寿顶高的老人说,可能是许多年没有朝拜山林之神,神灵发怒了。于是,大家唱的唱、跳的跳,一直闹了三天。巧事,第四天果真乌云盖顶,下起了大雨。从此,人们就把朝拜山林之神的这三天(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定为绕山林节日。”[12]雨水丰沛于稻作耕种的意义不言而喻。因此,在插秧前夕举办的绕三灵节日,其为稻作生长“祀神祈雨”的传说便显得易于理解。传说,“有一年,大理干早,到栽秧季节,天一直不下雨,后来人们就在喜洲‘九坛神’本主庙里搭了一个祈雨台,念经祈求本主下雨。到四月二十五这天,真的下雨了。从此,百姓非常信奉本主。每年四月二十五日,都去本主庙里朝拜求雨,后来发展成为绕三灵。”[13]又有传说,“有一年,天旱无雨,庄稼种不下去,人们焦虑不安。到‘绕三年’时人们来朝拜建国皇帝,祈求早降大雨。晚上,建国皇帝显灵,赐给他们一个宝葫芦。他们拿着宝葫芦找到了段赤城,段赤城在葫芦中装满洱海里的水,叫他们带回去。到栽秧的时候,大雨果然来了。各村各寨的秧苗都裁下去了,这一年获得了丰收,于是便有人称“绕三年”为‘祈雨会’”。[14]
总之,民间信仰通过人格化的叙述和表达,实现了神圣信仰向世俗传说的转变。民间信仰演化为民间传说之后,“主要通过神话余音、民间祭祀的叙事话语和历史表达等方式存在于民间传说之中”。[15]如今,沿袭至今的绕三灵节日仪式中的“花柳树”⑥、对歌应答“花柳曲”⑦所使用的牦牛尾巴、“花柳树”装饰的葫芦等象征物及文化符号,乃至颇受众议的男女春日野合习俗等,无一不折射着传统农耕社会“稻作祭仪”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自然崇拜和农耕信仰文化因子,并凭借口头传说、节日仪式等实践方式在民间社会世代传承。
二、从传说到信仰:绕三灵传说的佛教粘附叙事
民间传说表面看来充满时间、空间错置与幻想的迷雾,但作为某种历史记忆的符号,它们的产生和流传过程恰恰是包含着丰富社会舆论与情境的一个历史真实。[16]绕三灵传说由本土传说向佛教传说演变的历程就是在丰富的社会情境中推进的,传说的发展演变是外来佛教本土化的一个明证。
公元7世纪左右,佛教经由中原、西藏和印度分别传入大理洱海地区,并由此开始了本土化的历程。一方面,佛教运用自身优势结合中原儒家思想,以观音幻化“君权佛授”的传说溯源统治阶层之神圣出身,以神权巩固王权,由此获得了上层统治者的支持而渐呈兴盛之势。此后,“佛授”君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频繁见载并流传于本地史志文献及民间传说之中。如《南诏图传·文字卷》叙述了观音幻化及南诏国兴宗王罗昇参与“三赕白大首领张乐进求”铁柱祭天的传说,民间流传的绕三灵传说亦有“观音梦示以禅位细奴逻”之说⑧;另一方面,佛教不断向世俗化和大众化发展,不断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渗透。值得关注的是,在佛教地方化发展历程中,一些佛教精英结合大理洱海区域广为流传的传说故事,通过人物附加、情节粘附等手段改编和创造了“观音开辟大理坝”“观音选王点化细奴逻”“观音负石阻兵”等大量本土化的佛教传说,并借此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和推动了外来佛教信仰及佛教文化在大理地区的影响和传播。由此,洱海地区的佛教信仰开始兴盛,至劝丰佑时期,南诏统治者将佛教尊为国教,至大理国时期,佛教浮屠广布,甚至国王也避位为僧[17],出现了如郭松年《大理行记》所言“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菇荤、饮酒,至斋戒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的佛教信仰盛况。其间,佛教以粘附和借用大理民间口头传说的形式,通过大众化、模式化的叙述和流传,不仅加快了佛教信仰世俗化、本土化的趋势,而且也为佛教信仰在大理地区的传播和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⑥“花柳树”为一株用红色布条、葫芦等装饰的大柳树,是村落绕三灵队伍的引导树,位于队伍最前方。花柳树一般由一男一女一左一右合执,有时也可是两男两女,但分别扮演男女两个角色。他们分别身着白族传统服饰,女子为绣花包头,男子为绣花八角帽,分别戴着装饰有各色绣球的黑色墨镜,一只手手执花柳树,另一只手里,男子拿着牦牛尾巴卷,女子拿着绣花手帕,一齐手执花柳树向前走,花柳树起,两人身体也向前,花柳树落,两人身体在前方隔着花柳树相遇,并又向后分开,将各人手里的牦牛尾巴卷和绣花手帕搭在肩上,身体分别都向后仰,唱着“花柳曲”,一问一答,有节奏地向前迈步。
从民间传说发展到民间信仰,是由口头叙事到行为模式,从表层言语沉淀至深层民众心理的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历程。“从传说到信仰的过程,是口头叙事影响人们行为,口承文学积淀为民俗心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传说独特魅力以外,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诸如宗教、国家等人为政治的干预,因此,从传说到信仰的文化运动既有民众不自觉的创作,又有上层文化‘精英’的合目的的改造,既是传说自身演化规律的展示,又是民众心灵情感依托的必然结果。”[22]就上述传说而言,在口头传说承载并推动佛教信仰本土化历程中,外来佛教与本土信仰及其口头传说广泛互动,通过多维文化主体,即地方上层统治者、佛教文化精英、本土普通民众等的行为实践不断发展,在借用与粘附、妥协与融合中,使得绕三灵传说得以成为承载并融合自然崇拜、农耕信仰、本主崇拜、佛教信仰等多元民间信仰的口头叙事载体;同时,外来佛教信仰在其本土化过程中,通过人为的、能动性地粘附、借用、改编、创造,使得流传广泛、社会影响力大的传说为其所用,不仅以“新传说”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还确立了其在南诏大理国政权统治中的正统地位。当然,这样的能动性实践,反过来也会推动并扩大“新传说”的进一步传播。随着佛教本土化和地方化历程,新的口头传说势必会借助佛教的影响和播布在民间广为流传。
三、在传说和历史之间:绕三灵传说的政治王权叙事
“送金姑驸马”是如今绕三灵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传说版本。与上述段宗榜传说的王权楔入模式不同,传说讲述了一段王权更迭的地方史。据文字记载,洱海地区的白蛮、乌蛮各部落为争夺统领权长期斗争。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白国主”张乐进求禅位于细奴逻,和平解决了部落争斗。《云南古佚书钞》一说,“永徽三年(公元653年),蒙氏细奴逻始代张氏,立国号曰‘封(白)民’,称蒙舍诏”。[26]关于此段历史,《南诏图传·文字卷》记载:“初,三赕白大首领将军张乐进求并兴宗王(即细奴逻)等九人,共祭天于铁柱侧,主鸟从铁柱上飞憩兴宗王之臂上焉。张乐进求自此已后,益甚惊讶。兴宗王乃忆,此吾家中之主鸟也,始自欣悦。”[27]《僰古通记浅述》亦载:“僰国酋长有张乐进求者,为云南诏,都白崖,闻观音命细奴逻为国王,其心不怿,乃嘱诸部酋长,同约细奴逻,具九鼎牺牲,诣白崖铁柱观效于天,卜其吉者而王之。众皆悦而从之。祭毕将卜,忽有布谷飞在细奴逻右肩,连鸣大鸣于细奴逻者三,返与白檀香树上。众皆惊服,不复占卜,而咸顿首,请细奴逻登国(王)位。时张乐进求知天命有德,遂避位于落,而以其女妻之。”[28]大理地方典籍乐言张乐进求禅位而不疲,清代胡蔚本《南诏野史》及《康熙大理府志》中也有类似的文字记载⑨。
注释:
林白轩常念叨:“常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外面的世界云垂海立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小的落星湖恐怕也会有煮沸的一天。唉,先不管这些十年之后的烦心事,应付眼下的急所吧,明天的司徒一一,明天的那个刑天,眼下的这三个孩子,这三个奇迹般穿过万花因,来到谷里学艺的少年。
在当前流传的绕三灵传说中,涉及政治王权的有两种:一是与“建国皇帝”(又称“爱民皇帝”)有关,传说绕三灵是建国皇帝忽然暴毙,大理百姓为其奔丧;二是与“白王张乐进求”有关,传说绕三灵是送“白王之女金姑及驸马回巍山”。以下,我们将简要分析绕三灵传说与政治王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进而探求传说作为历史记忆之于地方史研究的可能价值及意义。
文字区分了阶层与类。在无文字书写及阅读能力的底层社会,传说也被视作社会记忆过去、记忆历史的一种手段和方式。[29]在民间,这段张乐进求逊位细奴逻,并“以女妻之”的地方史,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传说:“金姑是大理国王张乐进求的三女儿。张乐进求家教很严厉,一天,金姑踩了家里堂屋的门槛,被父亲狠狠训斥,便一气之下赌气离开了家。三公主金姑从来没离开过家,饥寒交迫便晕在荆棘满布的苍山半山腰。蒙伙(今巍山)的猎人细奴逻救了公主。黑夜中,两人互生情谊,私定终身。细奴逻相貌极为丑陋,但还是随他回巍山成亲,日子越过越好。后来,张乐进求召集各部落酋长在白崖城会盟。晚上观音托梦以“祥鸟落肩”属意张乐进求传位于三公主驸马细奴逻。细奴逻精明能干,于是便做了大理的王。张乐进求不赞同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但还是让金姑的姐妹们去接金姑驸马回大理来省亲。”⑩于是,在大理民间,“金姑的姐妹们”每年都会在农历二月初九至十四日,从大理奔赴巍山天摩崖寺“接金姑”回大理“省亲”,又在每年农历三月三“送驸马”先回巍山,并于每年绕三灵期间,即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送金姑驸马”一同回巍山。⑪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搜集的“莲池会”口传经文《金姑经》,生动叙说了这一节日庆典过程:
金姑出来常围绕,拜佛弟子诚心好。天长地久重重生,石榴开花后结果。紫金城驸马公,二月朝山来请你。干你加打紫净城,⑫国泰民安好欢喜。紫金城小金姑,二月朝山来请你。初十日起脚,十一走到天门衙,十四绕起脚,绕路山途下雪山。明日我往雪山过,兵荒马乱请回来,善男信女来朝贺。三月修行三月三,善男信女来串串。⑬合会弟子绕山途,送驸马回家。四月修行二十三,善男信女去烧香。合会弟子来朝贺,送金姑娘娘。⑭
随着冠脉积分数值的增加,UA、TC、LDL明显升高,而TBIL、IBIL、DBIL、HDL均明显降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可见,文字记载、口头传说、仪式实践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记忆系统。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细奴逻始代张乐进求”的史实是文字记载与传说讲述的核心事件,然而在口头传说讲述中,所谓的政治之“王”细奴逻备受传说叙事的批判和鄙夷,他不仅相貌丑陋不堪,而且还以不符合社会道德的姻亲关系的缔结最终获得王权。[30]同时,由于“金姑驸马”传说口头叙事与仪式身体叙事互为支撑,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绕三灵节日叙事及实践系统,因而“金姑驸马”传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渐渐成为解释绕三灵节日起源的基本版本并广为流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民间社会记忆历史、阐释重大历史事件的张力。
大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产生了特殊且多元的民间信仰与历史记忆。以上论及的绕三灵传说,内容分歧迥异,看似分属不同的传说类型。然而,究其“分歧”根本,两个传说类型,有可能都与政治权利话语参与设计相关。如前所述,“建国皇帝”段宗榜的传说,权力楔入的政治设计色彩十分明显,“本主传说作为一种攀附资本,折射出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31],建构了一套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制度;“金姑驸马”传说,尽管表面上似乎难寻王权设计的痕迹,但是深究之,如果没有“一套政治王权参与设计的普及于民间的社会机制”[32],那么试问“接送金姑驸马”这样一个长达三月之久,跨地域、跨民族的节日仪式实践及民族文化交流系统如何能在大理地区代代传承?其间,一只无形的“政治之手”一直影响和制约着绕三灵王权叙事的发展、演变和流传。
结 语
绕三灵传说异文众多,多元交错的民间信仰、千沟万壑的地方历史均在口头传说文本中得到汇聚和融合。在这个意义上,绕三灵传说不仅是一个民间文学“文本”,更是一个社会史“文本”。它不仅承载着白族民众深层的神圣民间信仰,为外来佛教传播提供了一个粘附支点,而且还是南诏、大理国历史叙事的“地方性话语”,揭示了普通民众对地方史的记忆与认知。我们将以上诸多内容迥异的绕三灵传说并举,不是去甄别各种传说孰对孰错以及孰真孰假,而是将各种传说异文视作不同时代民众记忆历史的不同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从“知识考古学”出发,试图在各种异文表述中探求不同传说产生的“社会情境”,寻找传说“层累叠加”中的文化整合策略,并进而展示传说叙事与政权更替、社会变迁之间的张力。总之,作为文化传统的传说,是不同历史时代“层累叠写”的结果。从历时来看,传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其“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时间链上是具有连续性的,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传承与变迁的节点已然难以分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传说发展历程中,每个时代均会在传说上打下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文化“烙印”。这种“时代烙印”和“历史印记”,以极为隐秘的文化符号印刻在传说“文本”上,在民众选择性地遗忘、借用、粘附、嫁接、创造与改编中,实现传说的传承和发展,并反过来成为社会时代变迁的明证。
(7)通过上面粒子群和遗传算法不断迭代寻优,分别得到群体最佳个体gbest_PSO和gbest_GA,信息共享,比较gbest_PSO和gbest_GA好坏,选择较好的作为PSO和GA下一代进化依据,进而获得全局最佳值global_best。
“建国皇帝”传说叙说了绕三灵节日核心地点圣源寺奉祀主神“灵镇五峰建国皇帝”段宗榜的事迹,及其主庙被祀为“神都”,其被奉为大理最高本主“中央皇帝”的缘由。传说,“国王段宗榜本事出众,大家尊他为“爱民皇帝”敬如父母。农历四月二十三,他到点苍山五台峰下的庙子里敬香,谁知暴病便死在这庙里。消息传出,百姓失声痛哭伤心至极。大家抬着祭奠用的帛吊,端着净水碗,柱着哭丧杖,披麻戴孝,赶到庙里奔丧守灵。就这样,百姓们一直哭了三天三夜。事后,人们又在那个庙子旁边,盖起了一座圣源寺,称为‘神都’,尊爱民皇帝为本主之神。”[23]据《僰古通记》记载,段宗榜为南诏中期统帅,曾任南诏国清平官。公元858年,奉南诏国王劝丰佑派遣,助缅甸击退入侵的狮子国部队,被南诏国王封为十八功臣之一。大理国建立后,开国皇帝段思平溯段宗榜为先祖,将其奉为大理本主神中最高神灵——“中央皇帝”。据调查,大理地区每个村落均奉有各自本主,本主各有辖区,尽管部分本主神灵由于水系及水域的关联,在传说中时有亲属或姻亲关系,但各村本主神灵之间并无大小等级之分。[24]但是,“中央皇帝”段宗榜却是例外,他是大理坝子的最高本主,接受各村小本主的朝拜。至今,绕三灵所在地“神都”白语依然称作“caolhet”,意思是“朝廷里”。 因此,绕三灵也被视作“中央皇帝”段宗榜接受大理坝子七十二村本主“朝拜”及各村百姓“朝圣”的节日。[25]可见,统治王权政治话语的楔入,打破了原本地位平等的本主神灵系统,“中央皇帝”段宗榜由于政治博弈的需要不仅被奉为神灵,而且被抬高至最高本主。一方面,政治统治“以王权确定神权”,统治者创造节日传说并赋予先祖段宗榜以神圣地位,以政治等级话语证明王权统治者的“神圣”出生;另一方面,政治统治也“以神权巩固王权”,统治者凭借口头传说流传及祭祀仪式操演使得 “神权”、“等级”等观念深入人心,以巩固王权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此过程中,一支无形的“权力之手”以其“柔性的”、自上而下的统治策略不断向民众日常生活及精神领域渗透,而这种以传说传递的“柔性的”思想统治一旦为民间社会所认同,必将产生出一种生生不息的“草根力量”以维护和巩固政治王权的统治。
①根据笔者调研,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大理喜洲一带村民便已经来到大理南门城隍庙并寄宿于南门附近人家,实际上节日活动在这一天便已经开始。但问及“绕三灵”节期,还是一致认为农历二十三才是正日子,他们于二十二日来到城隍庙,只是为了四月二十三日清早能够在南门城隍庙外“送金姑驸马”。
②重要研究成果有:杨宴君,杨政业:《大理白族绕三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张翠霞:《神坛女人:大理白族“莲池会”女性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赵玉中:《地方风俗的诠释与建构——以大理白族“绕三灵”仪式中的“架尼”为例》,《思想战线》,2008 年第 1 期;白志红:《实践与阐释:大理白族“绕三灵”》,《民族研究》,2010年第 5期;沈海梅:《白族社会“绕三灵”中的性阈限》,《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等。
这首七律写在小溪边生活的游禽,描写它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写它们美丽的羽毛和如云的溪花、如练的溪水混成一色,写它们快若闪电、隐现无常的飞翔姿态,写它们翻动羽毛自我炫耀的神情面貌,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最后两句曲终奏雅,点出主旨,提醒鸟儿们,不要以为这个偏僻之地就没有了罗网,到时被罗网网住,就只能被人类豢养在樊笼中了,那时虽然有吃有喝,但这种生活哪有自由飞翔时的生活值得羡慕。这首诗就把形象和哲理结合得非常好。
③被访谈人:ZGZ,男,白族,1953年生,喜洲庆洞庄人。访谈人,张翠霞,访谈时间:2011年4月23日。访谈地点:庆洞庄ZGZ家中。
根据散射参数曲线的物理意义和特征,散射参数的均值代表液体在测试频段内对微波吸收的整体情况.散射曲线平滑程度反映了液体受外界影响产生的不稳定性,主要和液体的粘稠度等物理性质有关.因此将散射参数的均值和散射参数曲线平滑程度作为感知机的输入参数,即可以达到降维的目的,也便于观察超平面的物理意义.
再次,对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水利建设基金进行分析。商业银行应当以增值税额为计税基础,申报缴纳附加税费。
这样教语文,也许几节课,几十节课都无法看到孩子的语文能力有所提升,(我一向认为上一节语文课就希望能看见孩子的语文能力有较大提升,就好比让孩子吃一顿饭就希望能看见他长高一样不切实际。)但是一年、两年、三年……
⑤李正清认为“绕三灵”是附会《三灵庙碑记》,菡芳认为“绕山林”是“民族风情”热情杜撰者的杰作。参见:李正清:《白族“绕三灵”的起源和性质》,《昭通师专学报》(哲社版),1985 年第 2 期;菡芳:《“绕山林”、“绕三灵”和“逛桑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6期。
如果说在民间信仰与民间传说的互动关系中,从神圣民间信仰到世俗民间传说的演化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的话,那么,从民间传说推动甚或生成民间信仰的过程则展现了上层统治者、佛教文化精英、本土普通民众等多维力量的互动、较量与博弈。正如林继富所言,“当民间信仰一旦演化成民间传说,原有的民间信仰仍然以各种形态存在于民间传说之中,于是在历史的坐标上,民间信仰与民间传说互为作用、互为表里,构成民间基层社会极具活力的文化运动”。[18]一则有关绕三灵的传说开篇说道,“以前,大理是一片汪洋大海,白族人民住在苍山上从事打猎放牧,他们欢聚在山林之间,尽情歌舞玩乐,以此赞颂苍山山神,就成了最早‘绕山林’”[19]。 可见,“山神”崇拜是传说的信仰内核,折射着最古老的自然崇拜。本土信仰根深蒂固,在大理 “最古的本主是自然崇拜的宗教,与生产有一定关系”[20],传说只是本土神圣信仰世俗化发展历程中的 “神话余音”。然,这则绕三灵传说以“后来”一词扭转叙事,讲到“后来,观音下凡,制服海中恶魔罗刹,海水向东流去,苍山下现出一片陆地。从此,白族人民就从苍山上搬到寨子里居住。观音归天时,把辅助她制服罗刹的西天护法神——五百神王留下,封为建国皇帝让他教大家盘田织布。每逢农历四月间采摘桑叶的时候,人们和建国皇帝一起,一面采摘桑叶,一面唱歌跳舞,由此形成了一年一度的‘绕桑林’。”[21]传说被佛教粘附借用的痕迹十分明显。然而,传说流传至今,粘附也好,借用也罢,现在看来已经显得理所当然,作为“地为观音开辟”“罗刹为观音制伏”“王为观音封选”等等诸如此类的“历史真实”已深深烙在大理人的历史记忆之中。传说广为流传,大家亦对此传说解释笃信不疑。就此,笔者认为面对多元迥异且在地域之内皆有流传的绕三灵传说,考究传说异文及其流变固然重要,但从现象学和“知识考古学”出发,直面并回到生活现实,转而承认这些看似迥异,甚或矛盾的传说叙述及其历史记忆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寻求并揭示传说叙事背后的结构性意义和能动性价值或许更显重要。
⑦“花柳曲”为绕三灵花柳树队伍男女即兴对唱应答的,含有男女挑逗意味的调子。
汪曾祺有一首诗,柔软得像春风十里:“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只记花开不记人,你在花里,如花在风中。”反复咀嚼,这首诗趣味盎然。客人来访,主人不在,会心生些许不悦,不过没关系,门外的花儿会陪着你,它们会如同好客的主人一样,给你宾至如归的感觉。见花如面,那些花是主人给予客人的精神喂养。
⑧《南诏图传》佛教借用本土宗教铁柱祭天仪式过程中,铁柱神鸟落在南诏王手臂之说,预示王权将转移至兴宗王,而白王张乐进求以祭天的方式让位于南诏兴宗王,这就是阿嵯耶观音点化“君权佛授”的结果;绕三灵《金姑驸马的传说》中有“观音梦中告诉张乐进求,将王位传给三女儿的丈夫细奴逻”的情节叙述。
⑨清代胡蔚本《南诏野史》亦曰:“因社会祭柱,柱顶故有金镂鸟,忽能飞,集奴逻左肩,相诫勿动,八日乃去。众骇异,谓天意有属。进求遂妻以女,举国逊之”。(胡蔚:《南诏野史》(线装本·上卷),成都:巴蜀书社,1998 年,第 9页。);《康熙大理府志·卷三·沿革》记载:“(贞观)二十三年建宁国张乐进求逊位与蒙氏。……白国王龙佑那十七世孙张乐进求,因以国让之细农罗(细奴逻)”。
本次实验选择的100例患者的资料来源于一项皮肤疣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入选冷冻治疗组的患者。本次实验方案得到医院委员会批准,对患者的资料的收集也得到患者的许可。年龄>18周岁,学历在初中以上。其中,男56例,女44例,平均年纪(31±8)岁,平均患病时长(2.2±1.5)年。实验中选择的患者均排除其他病理影响。
⑩根据访谈记录整理。被访谈人:ZGZ,男,白族,1953年生,喜洲庆洞人。访谈人,张翠霞,访谈时间:2016年5月5日。访谈地点:庆洞庄ZGZ家中。
⑪传说,驸马公相貌丑陋,不好意思见老丈人,便在大理湾桥保和寺住下等待金姑省亲归来。农历三月初三,因为驸马久不见金姑回来,想着巍山家里还有事,于是决定先回巍山,后面又觉得扔下金姑一个人不好,于是就在四月二十三这天在城隍庙等金姑一起回家。”于是,绕三灵也被老百姓看作是“送金姑驸马回家”。
⑫此为汉字白音,“干你加打”意为“将您接到”的意思。
⑬“串串”意为“逛逛”的意思。
⑭“莲池会”经文《金姑经》,张翠霞依据喜洲庆洞莲池会“经母”ZDD提供手抄本抄录。
参考文献:
[1]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2][法]米歇尔·福珂.知识考古学[M].谢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8.
[3]顾颉刚.顾领刚民俗学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15.
[4][15][18][22]林继富.神圣的叙事——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互动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
[5][8][14][19][21]大理县白族文学研究小组搜集.白族民间故事[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23~25.
[6][12]杨恒灿主编.大理民间故事精选[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74~77.
[7][10]李正清.白族“绕三灵”的起源和性质[J].昭通师专学报(哲社版),1985,(2).
[9]菡芳.“绕山林”、“绕三灵”和“逛桑林”[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6).
[11]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绕三灵组舞”部分[C].北京:中国舞蹈出版社,2000.
[13]张文勋.白族文学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302.
[16]户华为.虚构与真实:民间传说、社会记忆与社会史“知识考古”[J].江苏社会科学,2004,(4).
[17]张翠霞.神坛女人:大理白族“莲池会”女性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97.
[20]徐嘉瑞.大理文化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94.
[23]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白族神话传说集成[C].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371.
[24]杨政业.白族本主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86.
[25]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50.
[26]王叔武辑著.云南古佚书钞[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22~23.
[27][28]尤中校注.僰古通记浅述校注[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176.23.
[29][30]张翠霞.王权传说:地方史的民间叙事——兼谈传说文类的历史解释力[J].大理大学学报,2018,(5).
[31]孙艳丽.逃离与攀附:云南大理白族族群记忆中王权神话的变化[J].贵州民族研究,2017,(8).
[32]连瑞枝.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和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7:10.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olk Legends,Folk Beliefs and Local History:--Takin“gRao San Lin”Legends as the Research Center
ZHANG Cui-xia
Abstract:“Rao San Lin”legends are widely spread in Dali.In the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oral legends and folk beliefs adhered to each other,and legends were borrowed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Buddhism.It was superimposed and grafted into the political narrative system of Nanzhao kingdom,which became the basic version of the most widely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 of“Rao San Lin”festival and the origin of Nanzhao kingdom.The legend is not only a text of folk literature,but also a text of social history.It bears the deep natural worship and farming belief of the Bai people,and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folk beliefs and local history,legends not only provided an adhesive fulcrum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Buddhism,but also became the Indigenous discourse of native people's historical narration.
Key words:Rao San Lin;Folk Legends;Folk Beliefs;Local History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2-0215-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白族民间信仰结社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批准号:16CZJ02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洱海流域人水关系与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批准号:18YJCZH038)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8-12-08
作者简介:张翠霞(1983-),女,白族,云南大理人,云南大学滇西发展研究中心讲师 博士,主要从事西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社会治理与农村社区发展研究。
[责任编辑 先 巴]
[责任校对 徐长菊]
标签:大理论文; 白族论文; 王权论文; 佛教论文; 民间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白族民间信仰结社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批准号:16CZJ02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洱海流域人水关系与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批准号:18YJCZH038)阶段性成果论文; 云南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