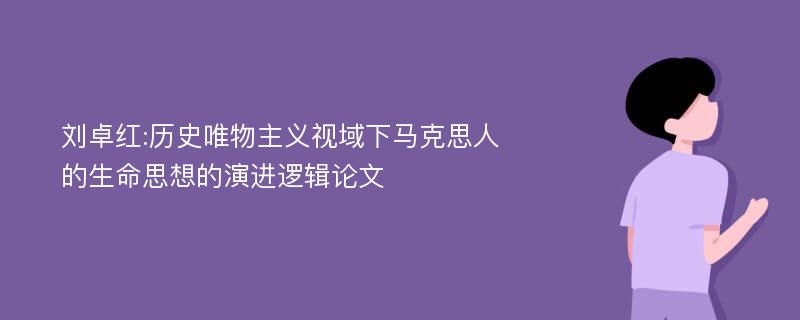
[摘 要]与西方人本主义相异,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虽未直接提出人的生命问题,但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中,对人的生命的关注,始终是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伴随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命思想也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批判性继承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哲学,将人的生命理解为自然实体生命与感性类本质生命的统一;其次从历史的动态过程确立了处在历史场域中的人的自然实体生命;最后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体考察,拓展了人的社会关系性生命的研究。尝试对马克思人的生命思想的分析,有助于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人现实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境遇的多维度认识。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人的生命 劳动 资本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固有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其理论的起点和归宿是具体的、现实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 23页。生命既是人存在于世的确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前提。对于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而言,人的生命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命题。虽然在著作中,马克思没有以专题的方式讨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和生存结构这一议题,但不可否认马克思对人的生命的讨论始终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人的解放的学说中。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汉娜·阿伦特所言:“马克思的整个理论都围绕着这一个早期洞见:对劳动者来说首要的是通过维持他生存的手段的生产,来实现他自身生命的再生产。”②[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可见,拓展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命思想的研究,是当前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的角度。
一、对感性类本质生命的批判性继承
马克思早期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类本质思想,认为应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唯物主义颠倒”,以“感性的具体存在”为哲学的起点,从自然和社会的角度对人的本质进行还原。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生命有两种理解:自然实体生命和感性的类本质生命。高清海将这两种生命概括为“种生命”和“类生命”:“把人看作是有着双重生命的存在:他既有被给予的自然生命,又有自我创生的自为生命。我们可以称前者为‘种生命’,称后者为‘类生命’。”③高清海:《“人”的双重生命观:种生命与类生命》,《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
马克思首先继承了费尔巴哈以自然为起点的人本分析逻辑,认为应从自然出发来探讨人独有的生命特性。在他看来,人的自然实体生命具有两个特征:“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7页。一方面人的自然实体生命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表现为潜在的自然力或生命力,即欲望,这种内在于人的自身的力量驱动着人们去行动,通过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满足自身肉体的需要。这种力量之所以是能动的,在于人能将外在的存在物当做对象来看待,即将自身与周围的存在物区分开来,并确定自身;同时,将外在的环境和存在物当做自身生命的对象,与对象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传递和交换。“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页。但这同样也意味着人的生命受到对象的限制,所以另一方面人的自然实体生命具有受动性。这种受动性表现为他的欲望的满足依赖于外在的对象,受到外在对象的制约。人虽然可以在与外界的接触中确定自身,但人的生命还是需要受到自然法则的限制的。人和动植物一样,是以肉体为基础的自然存在物,需要外在的对象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人的生存需要特定的自然环境,离开了这个自然环境,人的生命将无法持续下去。所以人的自然实体生命指的就是人和动物所相同的生命,即以欲望为导向,以肉体为存在根据,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自然进行交互作用的生命。
其次,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一样注重人的本质还原,他将人的生命理解为人的本质:“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页。因此,人的类本质生命具有两个内涵:生命是作为存在物——人的内在本质;生命的表现需要“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概括起来就是关于人的本质和本质的显现的问题。但对人的本质、人的生命的分析结构及其内涵,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费尔巴哈是从人的认识出发思考人的类本质,认为人的类本质是通过对感性对象的认识才得以体现,通过对象来确认自身的本质,即人在认识中将自己的本质规定赋予感性存在,使自己的本质对象化,人的绝对本质是人类整体通过感知自我的完善性、无限性,达到至高本质——上帝,即“你的本质达到多远,你的无限的自感也就达到多远,你也就成了这样远的范围内的上帝。”④ [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 11页。然而,费尔巴哈并没有对人的意识是如何把握感性对象做进一步讨论,也没有在对外在认识对象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同一性问题上做进一步的讨论,导致了他在关于人的本质是如何通过对象和人的存在实现同一性的问题上缺乏说服力。马克思则是从人的劳动,即能动的对象化活动出发,在人的存在与本质之间建立起内在的同一性关系,也就是说,人的存在应该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即人的生命的实现。在他看来,人首先将整个自然界当成满足自身肉体需要的生活资料,其次将自然界当成劳动的对象和工具,由此将自然界改造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意味着:人在将自然当成对象之后,可以通过改造自然的感性活动实现对自然的转化,这种转化并不仅仅是受肉体的需要支配的,还可以根据人的任何一种需要和尺度实现对自然的改造。这是因为人的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但可以把自然当成对象,也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成对象,即将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生产)区分开来,正是由于这种区分,人才同动物区别开来,成为类存在物。而动物则服从于自身的自然本能,其肉体的需要支配着它的生命活动,这种活动仅是“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即“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因此,人作为类存在物,是由于人具有有意识的和自由的活动,而并不是像费尔巴哈所说的,是作为“自我意识”的表现的“理性、爱、意志力”的结果。“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综上所述,在马克思的早期研究阶段,人的类本质就是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特性的“自由和自我意识”,“对象化”就是实现人的类本质的感性活动。因此,人的感性的类本质生命从根本上说就是指以人的劳动所展现出来的自由和自我意识的特征。人的生命体现为双重生命,一方面自然实体生命受制于自然,但另一方面因感性类本质生命的特性而不断地超越这种自然的限制,并在这种人类独有的生命活动中实现自身的本质,实现自我创生的自为生命。
二、建构历史性的自然实体生命
很快,马克思就发现了这种利用抽象理性设立哲学价值悬设的做法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即无论赋予“人”“劳动”再多的内涵,仍然是抽象的哲学概念,类本质仍是“撇开历史的进程”的抽象的主体本质。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92页。要实现对人的现实的解放,就必须完全走出费尔巴哈式的哲学价值悬设,进入历史和社会领域中,对人的生产性劳动展开深入的考察。马克思通过对历史的考察,确定了讨论的对象——现实的自然生命。“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结合表1数据可以得出,在22 ℃环境下,肉鸡采用坐姿休息的百分比最大,26 ℃和30 ℃环境下,肉鸡坐姿休息的时间显著低于22 ℃处理组别(P<0.05)。18 ℃和26 ℃,肉鸡生长休息的差异性不显著(P>0.05),18 ℃和22 ℃、26 ℃和30 ℃,2个温度区间肉鸡处于俯伏休息的差异性不显著(P>0.05)。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1.在供给主体方面,要提高教师的教学魅力。教师是个有光环笼罩的职业,是一群被社会贴了标签的人:别人可以那样,但你不可以。学生具有天然的“向师性”,教师是学生最直接的榜样。一名礼仪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实施礼仪教育,而且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也要时时处处注意礼仪,以身作则,规范自己的言行,以良好的风范影响学生。
很明显,此时马克思眼中的人是现实的、整体意义上的人。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一样都具有自然基础,都是自然实体生命,即肉体的持存,但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即人的生命具有历史基础,人不会仅仅满足于自然生存状态,而是会随着工具的发展而不断产生新的需求,从而摆脱对自然的依存状态,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这种创造历史的活动就是“生产”,这种生产活动并不是指脱离社会之外的个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活动,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生产,这就意味着生产既包含自然关系,同时也包含着社会关系。在邓晓芒看来,这种关系“相当于海德格尔作为‘此在的基本机制’的‘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或译‘在世’)。”①邓晓芒:《马克思论“存在与时间”》,《哲学动态》2000年第6期。“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生产的自然关系,是指人在生产中所构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这两个方面得到实现:首先是人自身生命的生产,其次是他人生命的生产。在人自身生命的生产中,自然关系体现为人与物的自然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人的生产所决定的,人凭借工具对自然物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改造,将其变成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资料。其中,保证人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同时也是贯穿人类发展的永恒的基础,也就是阿伦特所说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③[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74页。只要人类还存在于这个世界,生产就不会停止,“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32页。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本身就是不变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基础这一事实才是不变的。然而,人们的生产并不会仅仅停留在保障人的生存的阶段上,在满足人的生存的需要后,满足这个需要本身的工具又引起了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既是第一个历史事实——生存性物质生产的结果,同时也是推动物质生产的内在要求。新的需要引发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就成为了第二个历史事实,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历史关系就在这种生产和再生产的发展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最初,人同动物一样慑服于自然界,但随着人的“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前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人逐渐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将自然界当成对象,实现对自然界的改造。而这个过程并不是单个人孤立的生产过程,而是“许多个人的合作”的过程,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33页。是人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的体现,表现为社会生产力。人自身生命和繁衍的需要都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得以实现,人的历史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发展。
马克思认为跳出哲学思辨的圈子,从事物背后的彼岸理论的桎梏走出来,返回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第一步,就是对现实的历史具体的社会进行考察,就是对“市民社会”中的经济生活,即对分工、交换和物质生产进行考察。他以人和动物的区分为切入点,认为不应该像费尔巴哈和鲍威尔那样用人的感情关系和异化的宗教来区别人和动物,也不应该像斯蒂纳那样从观念上摆脱了一切理性类总体性的利己主义来规定人。区别人和动物的根本在于人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人是在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活动中确证自身,即“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在生产中,人并不像动物一样直接从自然中获取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质资源,而是通过以工具为中介的生产活动获取他们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更重要的是,人通过物质生产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人不再从属于自然,人在生产中生产着自身的生活方式,人的生产决定着人在社会形态中的存在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正是由于生产,人才具有了超越感性之上的抽象的语言和意识,才有了属于人的异化的宗教和类本质。由此,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原始状态的考察,从人的生产方式的现实角度,将人的生命、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联结起来。人的生命是生活的载体和前提,生活方式是建立在人的生命之上的个体所承担的人特有的一种社会形态的展开和实现方式,生产方式既为人的生命提供物质基础,确定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也生产了人的生活方式,人正是通过生产确定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
定干能减少树体对营养和水分的消耗,能集中营养,促进剪口下芽子的萌发,明显提高成活率。苹果树根据树形要求及苗木质量进行定干,一般高度为80~100厘米。选择迎风方向,并且在饱满芽位置上方适当距离定干,剪口距离饱满芽0.5厘米,定干之后应注意剪口的保护,可以涂抹愈伤膏等药剂保护伤口。
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对人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分析,描绘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人的生命与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呈现并不是静止的、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获得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只是个人的生命所表现出的直接现象,更根本的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所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任何的个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身的生存条件,现实的个人为了保全自身生命所进行的劳动受制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成为个人的生命在进行劳动时所无法回避的历史的现实基础。但个人的生存状态受制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并不意味着人的历史是无法进步的、人是无法创造自身的历史的,因为“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人可以继承前人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条件,并以此作为基础进行新的历史条件的创造,这种创造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生产工具的创新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由此为人的生命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进步。
到了“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①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41页。马克思“希望建立一种讨论经济学的正确方法,即由简单的理论像价值和劳动这样的概念开始,然后再进入到较为复杂的但却观察到的整体。”②[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但这些概念在前资本主义历史背景中只是些简单的抽象范畴,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发展出充分的意义和复杂的形式。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对这些概念予以充分的考察,才能运用这些概念去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马克思把这比喻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页。所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之后的著作中,他将目光聚焦于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最发达、最复杂的生产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也内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之中。
三、开拓生命的社会性存在方式
可见,马克思通过生产将人的生命放置于历史的领域进行考察,因此,个人所展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并不是个体静止的生存状态,而是基于物质生产所形成的历史的社会生存状态。此时的马克思用生产来说明人的生命的历史特性,人的生命虽然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历史生存条件,但同时也因生产力的进步获得新的历史生存条件,人的生命存在方式表现为历史性生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性的物质生产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是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劳动者同一切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作为人类个体又同单独推动社会劳动资料的任何能力相‘分离’”,④[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55页。劳动者无法独自生产出自身所需的所有的生活资料,必须靠出卖自身的劳动力给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实现生产,一般性的劳动的支配权在看似“平等”的交换原则下变成商品被买卖,转变成雇佣劳动。被资本雇佣的劳动者不再享有产品的所有权,劳动也不再是为了劳动者的需要而展开生产,而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值。在资本增值的过程中,人的生命表现为资本增值的一个要素——活劳动,即人一天内体力和脑力的支出与耗费,而作为消耗生命的回报,劳动者获得的是等同于其劳动力价值的货币。“工资归结为工人作为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工人作为活劳动能力保存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总之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保持自己生命所必需的生活资料。”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9页。货币是作为等价物而出现的,是资本家对工人暂时的出卖生命的支配权的结算方式。而衡量劳动价值量的则是劳动者所需的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命被量化,并通过劳动时间予以衡量。所以马克思才会说“时间是生命本身的尺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由为了生产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需要的劳动时间来精确衡量的。因为时间是生命本身的尺度,就如重量是衡量金属的尺度一样,所以,工人劳动能力的日价值就是维持工人一天生活平均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劳动能力每天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人的生命的再生产——繁衍也是如此,“有生命的有机物的再生产不取决于直接用在它身上的劳动,即花在它身上的劳动,而取决于它所消费的生活资料(而这也是再生产它的一种方式)的价格”。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2、48页。但马克思所说的衡量人的生命的时间并不是纯粹物理意义上的时间,而是劳动时间,其衡量的也不是人的生命的持续时间,而是人的生命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表现的价值量。在资本为主导的生产过程中,人只不过是资本实现自身增值的工具,人的生命不过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要素——活劳动。由此,人的生命和商品一样被标上价格,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固化为“自然原则”的商品交换原则所控制,变为物与物的关系。这导致了人的生命本身被简化,在物质生产的语境中被简化为功能,人成为仅仅只能维持自身生存的“动物”。因此,人的社会关系性生命是指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生命状态,为了不致于死亡而依附于资本,成为资本增值的要素——活劳动,从而被量化、功能化,成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1页。丧失自身潜在的发展的可能性。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中,马克思对人的生命的理解实现了一个转向,即从对单一的自然实体生命的关注转至对人的社会关系性生命的关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命不再从属于自然,人的生存不再完全依赖于自然,而是依赖于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受资本的支配,只有在资本的支配下人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命持存。作为人的劳动的主要目的的产品,其使用价值将被交换价值所代替,人的生命成为资本的附属品;人的生存方式也不再是直接从自然中生产出符合自身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产品,而是在资本的支配下出卖自身的劳动时间以获得维持自身生命的货币。这个转向并不是一种对人的自然实体的生命的抛弃,而是一种扬弃的过程,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对人的生命认识的再发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人的生命一直处于历史先在地位,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仍然受制于这种自然的必然性——人为了生存必须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自然实体生命成为社会关系性生命的基础。而社会关系性生命是自然实体生命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里的展开,人在商品交换市场出卖自己的劳动支配权,在受雇佣状态下不断损耗自己的脑力或体力,即损耗“生命力”,这种损耗可以通过人的身体消费生活资料来进行补偿。在人的身体获得满足后,人则具备展开新一轮活劳动的能力,“他出卖的只是对他的劳动能力在一定时间内的支配,因此,只要他能吃到半饱,有一半睡眠时间,只要他能得到适当数量的物质,以便有可能重新生产出他的生命活动,他就总是会重新开始同一个交换行为。”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13页。人通过出卖社会关系性生命——活劳动来获得维持自然实体生命的生活资料,自然实体生命得到满足后,生产出新的活劳动并展开新一轮的交换。这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自然实体生命和社会关系性生命之间的转换,其中流动的是生活资料,中介是货币,工人出卖自身的社会关系性生命的暂时支配权所获得的便是计量工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货币,然后工人再通过货币购买维持自身自然实体生命的存在的生活资料。支配这种循环过程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由此可见,工人的生命被牢牢地控制在资本下,只有依附于资本,活劳动才能获得生产对象,工人的生命才有存活的可能。为了存活,工人只能不断地出卖自身的活劳动即他的生命,但出卖的活劳动并不能为他自己积蓄力量,而是“表现为[资本]本身的生命力,表现为资本再生产自身的力量”,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9页。为统治他的资本提供力量。对于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身的资本家而言,最大限度地占有并吸收活劳动,是他生命的本能,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吸收工人的活劳动,才能实现资本的增值、扩大再生产,才不会在资本之间的残酷竞争中被淘汰。此时,资本成为了建立在自然界之上对人的生命起着主导作用的力量,人只能依附于资本才能保证自身生命的维持与再生产,新的必然性由此而形成。这个必然性是建立在“自然必然性”之上的“资本逻辑”,并“对迄今为止的人的活动和历史发展具有一种外在强制性和异己性,甚至作为一种盲目性的异化力量在发挥着威力。”③衣俊卿:《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契合机制——对社会历史规律和必然性的反思》,《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1期。资本属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生产力,将人类从对自然的依赖中独立出来的同时,也为人类带上新的必然性枷锁,成为一种盲目性的异化力量牢牢地控制着人的生命和劳动。
BIM所具有的特征主要为协调性、优化性和可视性这三点。可视性是指的是应用BIM技术能够直观的将工程建设信息显示出来,便于工作人员找出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善;优化性指的是BIM中涵盖了较多工程建设所需信息,能够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充足的数据支持;协调性则是通过该技术的应用加强了各部门之间沟通,保证了施工作业的有序开展。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人的生命思想是随着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不断深化而逐步发展的,并表现为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侧重费尔巴哈式的哲学解释转向建构自然实体生命的历史场域,第二次是从自然实体生命转向社会关系性生命。这两次转变过程被阿伦特总结为:“从现代早期对个人‘唯我的’生命强调,转向现代晚期对‘社会’生命和‘社会化的人’的强调。”④[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253页。这标志着马克思对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认识从抽象转向具体,从历史走向现实。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中折射出现实的人真实的生存境遇:人的生命被束缚在持续增长的生产力基础上,人的生活被削减为生物意义上的自我保存。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9)01-0030-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观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18ZDA002)、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重大委托课题“习近平新时代观研究”(2018GZWTZD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卓红,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紫旭,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631)。
责任编辑:罗 苹
标签:生命论文; 马克思论文; 自然论文; 恩格斯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论文; 《学术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观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18ZDA002)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重大委托课题“习近平新时代观研究”(2018GZWTZD34)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