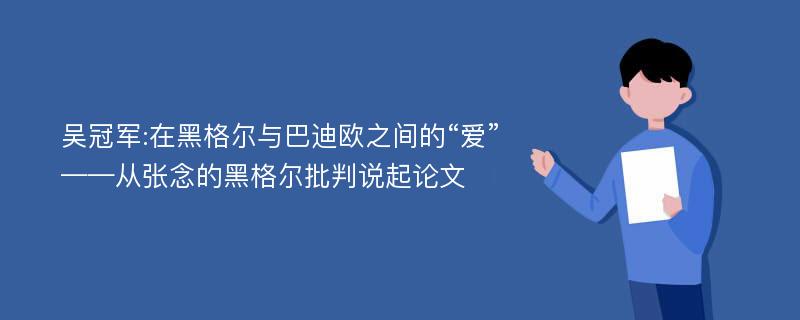
摘要:张念在其新著中对黑格尔展开了一个女性主义的哲学批判,这个批判的实质,是以黑格尔反对黑格尔:勾画主奴辩证法的黑格尔对抗作为“爱的哲学家”的黑格尔。而巴迪欧开启了另外一条后黑格尔主义的解放路向:继承黑格尔对爱的“礼赞”,同时实质性地改写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在张念对爱的女性主义批判视野下,巴迪欧的路向更清晰地显现出其思想史上的深邃意义。
关键词:黑格尔;巴迪欧;张念;爱;女性主义;真理
张念写了一本很具学术分量的著作:《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在此书中,张念用“扬弃女人”这根思想钢针把哲学史上的多重线团牵引到了一处,以呈现西方哲学内核性的“伤痛”。本文旨在从张念此书中对黑格尔论爱的批判性分析出发,将其“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的考察视野,进一步向前推进到当代哲人巴迪欧(Alain Badiou)。在我看来,巴迪欧对“二的真理”的阐述,正是旨在用爱弥补“伤痛”的一个卓越的思想努力。
一作为“爱的哲学家”的黑格尔
黑格尔是《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整本著作的论述起点。张念是迷恋黑格尔的,她写道:“在黑格尔的方向上,聚集了作为当代人的几乎所有的困惑和不安。”[注]在张念眼里,黑格尔的重要性,在于他实质性地让“女人”在哲学中“绽出”。这个论断的根据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1)写作《精神现象学》的黑格尔,无法对作为在时间中存在之现象的“女人”予以否认;(2)辩证法的结构,将“女性意识”真正纳入了哲学思辨。[注]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上海: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296页;第40、 47页。随后,张念进一步讨论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爱和婚姻的论述。较之早年的《精神辩证法》,“女人”的论题在该书中得到了更具体的处理。黑格尔本人认为“智慧女神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注]Georg W.F.Hegel, ElementsofthePhilosophyofRight, ed. Allen W.Wood, trans. H.B.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3.,那么,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黑氏在这本晚年著作中是怎么谈论爱、婚姻和女人的。
在黑格尔那里,人(“精神”)是通过“辩证”的过程——经由扬弃不断达到更高层次的综合——中接近真正的整体(抵达整体的那一刻,精神上升成为绝对精神)。于是,“辩证”成为了“绝对知识”自我展现之方式,以及历史进步之结构:经由正题、反题、合题(即综合,同时取消与持存正反题并将它们提升到更高层次)这个不断重复的辩证过程,“绝对知识”在(自我)扬弃中最终实现自身。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开篇即写道:“真理是整体,但整体除了以下状况外什么也不是:通过其自身的发展,本质将自身完善化。”[注]G.W.F.Hegel,PhenomenologyofSpirit, trans. A.V.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1.在晚年的《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进入到具体的自然—伦理层面来论述作为“自我知识和真实性”的精神所展开的辩证进程(精神“自身的客观化”)——尤其是其所经历的家庭、公民社会和国家这三个时刻。[注]Hegel,ElementsofthePhilosophyofRight, pp.197-198; p.199.在第一个时刻“家庭”部分,黑氏认为:男人和女人经由婚姻把他们变成“一个人”,通过扬弃各自“自然的和个体的个性”而让彼此成为这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看似是他们的一个自我限制,但实际上是他们的“解放”——他们获得了实体性的自我意识。经由婚姻形成的统一体(“一”、“一个人”、“家庭”),是男人(正题)与女人(反题)经扬弃自身后形成的新的辩证性综合(合题)。[注]
(三)实现高端文艺演出“零”突破。投资1.2亿元建成天上黄水大剧院,造型美观,大气恢弘,充分突出了“天上黄水”歌舞主题,由国家级艺术团队倾力打造的一部土家大型歌舞。是一部以石柱山水文化为“点”,以土家儿女追求美好生活为“魂”,以唯美浪漫的现代高科技舞台为“景”的大型演出,极具民族性、艺术性、震撼力的土家大型歌舞。
教育部新制定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指出:“鼓励教师建设和使用慕课、微课,利用网上优质教育资源改造和拓展教学内容,实施基于课堂、慕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使学生朝着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方向发展。”这一规定为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指明了方向,也意味着我国的大学英语课程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所以,对于黑格尔来说,婚姻绝对不只是一种“契约关系”,而是精神在世界中的辩证性—伦理性展开、最终上升为绝对精神之历史进程的关键一环。黑氏声称,进入婚姻的状态,是辩证进程的“客观性目标”,从而亦是“我们伦理的义务”。婚姻这个统一体,就是“精神的直接实体性”;而精神对其自身统一性的感受,就表现为爱。[注]G.W.F.Hegel,Hegel’sPhilosophyofRight, trans. T.M.Kno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11-110; pp.111-112.黑格尔这样论述爱:
爱就是指我关于自己同另一个人的合一的那个意识,我不再是只有我自己的那种隔离状态,而是通过以下方式来获取自我意识:(1)抛弃我独立的存在;(2)知晓我自身是自己同另一个人以及另一个人同自己之间的合一。但爱是一种感受,亦即,是伦理生活的自然形态。……在爱中的第一个时刻就是,我不再希冀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足的人,如果那样,我会感到缺乏和不完整。第二个时刻就是,我在另一个人之中找到我自己,在那个人身上我获得了确认,那个人随即在我身上也获得了确认。爱因此是最巨大的矛盾;理解力无法化解它……爱既制造了这个矛盾,又化解了它。作为矛盾的化解,爱就是伦理性的统一体。[注]Hegel,ElementsofthePhilosophyofRight, pp.197-198; p.199.
PCDH10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PCDH10过表达对A549细胞功能的影响(张 洁)(9):847
在黑格尔的论述里,爱使得两个独立个体各自扬弃自身。于是,它首先是一个否定性力量,随后又是一个肯定性力量:第一个时刻,爱否定个体的完整性与独立性;而在第二个时刻,爱使两个个体获得辩证性综合,彼此在对方之中找到自身,形成新的伦理性统一体。作为这种“最巨大的矛盾”,爱是理解力(知性)所根本无力化解的,只有爱自身才能应对这个矛盾。爱使得一个人发生主体性的改变、获取全新的自我意识:先是抛弃其独立存在(否定性力量),随后知晓自己与另一个人的合一(建立统一体)。而从个体上升到这个新的伦理性统一体,便是辩证意义上的“解放”。
那么,相遇事件所开启的爱,对于那两个个体(独体)意味着什么?一种不旨在取消“二”(绝对差异)的爱,是否可能?巴迪欧继承拉康(Jacques Lacan)而提出:就人的体验而言,存在着两种位置,我们可以用性别化的方式标识它们(“男人”和“女人”);这两个位置是绝对地离散的,不存在任何相同的体验;并且,第三位置并不存在。勾连这两个位置的不是第三位置,而是一个独特的事件(相遇),该事件开启爱的程序。[注] Badiou, “What Is Love”, op.cit., pp.54-55; pp.57-58; p.59.所以,“男人”和“女人”(作为两种位置)所构成的“二”,不是计数意义上的“二”、不是“三”里面的一个元素;这个“二”,是结构性的离散(structural disjunction)。所以,一对情侣(couple)里有可能会出现“小三”,但爱里没有“小三”,那是因为“情侣的现象性表面,仍从属于计算的外在律令,因而并不代表是爱”。相遇是这样一个事件,它使“关于‘二’的设定”得以到来,但随后它会立即消失(两人返回各自生活),除非由一个爱的宣言把它固化下来。[注] Badiou, “What Is Love”, op.cit., pp.54-55; pp.57-58; p.59.爱,真正打开了从“一”通向“二”的通道,把人从“一的场景”推到“二的场景”。[注] Badiou, “What Is Love”, op.cit., pp.54-55; pp.57-58; p.59.
下面,让我们转到张念对黑格尔的批判上。张念的批判首先建立在如下洞见上:在婚姻问题上,黑格尔拒绝把婚姻视作关于财产所有权的民事行为,拒绝把它视作人对物的一种新的调介关系;婚姻在黑氏这里实则指向两个主体之间的一种政治关系,张念把它称作“性别政治的第一发生场所”。[注]基于这一见解,张念认为黑格尔对爱的论述是反动的,因为它恰恰抹杀了这种政治关系,将性别政治(“二”)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统一体(“一”),它造成了“女性迷踪”却称之为“解放”。张念针对黑格尔做出如下追问:
我们依然不清楚的是:之于女人,到底是婚姻让她自动获得承认,还是要面对另一性别另一主体的承认?难道黑格尔认为没有进入婚姻的女人,不具备独立人格?那么婚姻中的女人,她会以“自我意识”之名,与丈夫们进行一场主/奴意识的殊死搏斗吗?[注]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第56页;第58页。
上述最小化问题是一个非凸二次约束二次规划问题(non-convex Quadratically Constrained Quadratic Program,non-convex QCQP)[18],可描述为,
现在,我们便能清晰地定位张念黑格尔批判之核心:辩证法的结构,使得“二”、“他者”、“女人”,只是一个过渡性环节,因为辩证法的最终地点(“历史的终点”),是“一”、“真理”、“绝对精神”。而在迈向这个终点的历史进程中,“女人”会被自行抹除。[注]在这个意义上,张念提出:黑格尔还不如魏宁格诚实。
我们知道,比黑格尔晚一世纪的奥地利哲学家魏宁格(Otto Weininger),是女性主义者眼里最大的反动人物之一。魏氏在其唯一著作《性与性格》中,以惊世骇俗的笔触从哲学角度处理了“女人问题”:“男性”是生产性的、主动的、道德的/逻辑的,而“女性”则是非生产性的、被动的、非—道德的/非—逻辑的;“男性”指向“有”,而“女性”则指向“无”。由于魏氏将“女性”排斥在理性、道德、逻辑等等基本的“人性”领域之外,他的著作自问世后(并因他本人的随后自杀而得以畅销),一直是女性主义者攻击的目标之一。而张念在这本书中,认为黑格尔实际上会同意魏宁格观点,但比后者更加不诚实![注]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第57页;第48页;第47、 49页。
二巴迪欧的反黑格尔主义
有了张念彻底拒斥作为“爱的哲学家”的黑格尔作为思想参照,巴迪欧对黑格尔的“扬弃”以及对爱的“礼赞”,便显现出思想史上的深邃意义。尽管巴迪欧晚近著述中黑格尔并不占核心位置,其早年在黑格尔研究上却曾倾注过大量心力——包括对中国黑格尔研究者张世英的论著做过专门的研究性评注。[注]See Alain Badiou, Jo⊇l Bellassen, Louis Mossot, TheRationalKerneloftheHegelianDialectic:Translations,IntroductionsandCommentaryonaTextbyZhangShiying, ed. & trans. Tzuchien Tho, Melbourne: Re.press, 2011.以《是与事件》之出版为标识,巴迪欧成为了黑格尔的一个强劲批评者,诚如巴勒特(A.J.Bartlett)、克利蒙(Justin Clemens)所论,《是与事件》“显著地是一部有力的反黑格尔主义作品、一部后黑格尔主义作品、一部非黑格尔主义作品”。[注]A.J.Bartlett & J.Clemens, “Measuring Up: Some Consequences of Badiou’s Confrontation with Hegel,” Jim Vernon and Antonio Calcagno(eds.), BadiouandHegel:Infinity,Dialectics,Subjectivity, London: Lexington, 2015, p.21.
张念的黑格尔批判,始自于如下女性主义哲学规划:“如果存在一种基于共同生活的真正意义上的共同性,就必须把‘二’放在主体之内,在‘一’之内”。[注]在此规划下,张念拒斥黑格尔对爱的论述,因为爱成为了黑氏对男人和女人进行辩证性综合为新的统一体(婚姻)的根本力量。爱,化解了“二”,使之复归于“一”。而女性主义哲学所内涵的政治立场(性别政治),就是必须坚持“像女权女人那样去思考”,必须追问“在这个被言说的‘世界’里,女人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她们在哪里出现又在哪里失踪?她们是经验性的存在,还是主体性的存在?有没有一种解放政治,可以抛开政治主体性,免除真理所有权的诱惑?”[注]
故此,对于巴迪欧而言,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真理,真理总是关于特殊局势、特殊“世界”的真理;而真理的永恒性,就在于它可以不断地被再主体化,可以在不同的局势和世界中不断被实验、不断以全新的方式被刻写。真理在柏拉图—黑格尔传统中被认为是绝对知识、作为整体的知识,而巴迪欧这里,真理恰恰是知识的反面,不断刺破知识的各种确定性、揭示它的不连贯性。关于真理,巴氏总结如下:
多元化的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也是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的基础保障。通过多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有序地发挥了地方党委、地方政府、地方人大、地方政协、司法机关、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环境共治的格局正在形成。环境保护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通过投融资机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第三方治理。公民和社会组织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加强了对企业和执法机关的监督。”[注] 常纪文:《生态文明进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十年》,《中国环境管理》,2017年第12期,第38页。
在巴迪欧这里,事件是无可预知的、对既有状态——巴氏的术语是“局势”(situation)——构成激进断裂的发生(occurrence),并具有在其中打开全新可能性的潜力:“一个事件是这样的东西,它照亮一个之前看不到甚至无可想象的可能性”。[注]Alain Badiou, PhilosophyandtheEvent, trans. Louise Burchill, Cambridge: Polity, 2013, p.9.对于巴迪欧,“是”(being)就是不可缩减地多元的、不连贯的、未被结构化的元素的大团/杂众,这些存在性的元素构成了一个局势。事件属于非—是(non-Being)之域,具有潜力去使得被局势之现状压制或被消失的东西变得突然可见。故此,事件性的地点,“不是局势的一个部分”,而是“在空无之边缘上”。[注]Badiou,BeingandEvent, p.175.在巴迪欧对事件所做的这个本体论阐述中,事件并不需要其他使它发生的肇因,事件本身就是肇因;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消失的肇因。[注]⑤ Badiou, LogicsofWorlds, p.144; pp.143-144.
快速性心律失常性心肌病作为一类可逆性心肌病,逐渐受到医务工作者的关注。只有对该类心肌病做出准确判断,及早进行干预治疗,才可能令患者获益,提高其生存率及生活质量。目前,针对该类心肌病的研究有很多,但在心脏超微结构方面尚未获得明确结论,今后仍有必要开展大量临床及基础研究。
爱,就是这四种进程类型(“真理—程序”)之一。[注]其余三者是科学、艺术和政治。真理是普遍的,而知识则总是性别化的,对于巴迪欧而言,爱通向无性别的真理而非知识:“我们喜欢去爱,也喜欢被爱,那正是因为,我们爱真理。”[注]Alain Badiou and Nicolas Truong, InPraiseofLove, trans. Peter Bush, London: Serpent’s Tail, 2012, pp.39-40.就此而言,巴氏实则呼应了黑格尔的论断:爱是通向真理的必要通道,而知性(理解力)则对其无话可说。
张念的黑格尔批判之策略,实则是用黑格尔批判黑格尔:勾画主奴辩证法的黑格尔对抗作为“爱的哲学家”的黑格尔。她要反对的,就是同时制造并化解矛盾的爱。这才是张念黑格尔批判的实质:黑氏用爱取消了男人与女人“因欲求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从这个角度出发,她引用一位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而声称:“爱欲辩证法实际上是为了诓骗女人,以便于她们在爱的名义之下去签署那古老的父权制所制定的‘性契约’”。[注]这样一来,张念实质性地取消了黑格尔和契约论者的区别,并且强调前者更具欺骗性(用爱的名义诓骗女人),故此作为“爱的哲学家”的黑格尔是女性主义者更大的敌人。
试验试剂:异淀粉酶(1000 U/mL):爱尔兰Megazyme公司;醋酸钠、冰醋酸:(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就其可能性而言,它受制于机遇;就其持续性而言,它是主体性的;就其素材而言,它是特殊性的;就其地点或其结果而言,它是普遍性的;就其存在而言,它是无限的;它根据四种独特的进程类型而被展布。[注]Quoted in Steven Corcoran, “Truth,” in his(ed.), TheBadiouDictionary, p.368.
黑格尔声称“我们必须坚守如下的确信:真理的自然会盛行,当其时间到来的时候”。[注]Hegel,PhenomenologyofSpirit, pp.11-44.黑格尔对真理盛行的这种“确信”,是后结构主义批判所瞄准的一个靶心。然而,不同于上一代后结构主义者们,巴迪欧仍将真理视作为哲学的核心范畴;但他一方面坚持真理是普遍的,同时则强调它无法被提前符号化——真理只能由事件来打开。巴氏写道:“我们和黑格尔共享关于真的一种普遍性的确信。但对于我们而言这个普遍性由诸真理—事件的独体性所保证,而不是被整体是其内在反折之历史这个观点所保证。”[注] Alain Badiou, BeingandEvent, trans. Oliver Feltham, London: Continuum, 2005, p.169; p.23.可见,分享黑格尔之确信的巴迪欧,却实质性地把真理—整体(“一”)替换成了诸真理—事件。真理,不再指向终极性、封闭性的整体,而是成为了新不断得以产生的“程序”。[注]进一步分析请参见吴冠军:《绝对与事件:齐泽克是一个怎样的黑格尔主义者》,《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观察到上述问题,笔者在学校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针对高中生如何进行有效的物理纠错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成果,为了验证其可行性,笔者在任教的高三班级中做了初步的尝试,就日常教学感受以及今年高考的情况来看,结果令人欣慰,主要体现在,教学过程中,师生的压力都有所减轻,学生养成了主动纠错的习惯,物理学习的积极性得到了提升,教师能够获得学生学习的真实情况信息,教学效率得到了提高,在最后的高考中,班级的表现也比较喜人.下面,笔者就简要谈谈自己针对上述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
我们看到,几乎是对黑格尔的严格继承,巴迪欧同样把爱放在哲学的核心位置上——把爱视作通向真理的通道,“在我们的世界里,爱是真理之普遍性的守卫者”。[注]Alain Badiou, “What Is Love”, trans. J. Clemens, in S. Žižek(ed.), JacquesLacan, Vol.4, London: Routledge, 2003, p.59.可以说,巴迪欧是继黑格尔之后最纯粹的“爱的哲学家”:对于他,爱并非哲学可能会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而是哲学的根本“条件”之一。然而,此处同样关键的是,巴迪欧对真理的界定完全偏离柏拉图—黑格尔传统,这导致在他这里,爱通向的真理并不是“一”,而是一种“关于‘二’的真理”。
张念以黑格尔对抗黑格尔:以男人和女人围绕“承认”的性别政治(“二”),来对抗那能够同时制造“二”(最巨大的矛盾)并化解“二”(建构新的统一体)的爱。而巴迪欧同样既反对黑格尔又继承黑格尔,但方向恰好相反:巴氏继承黑格尔对爱的“礼赞”,但把爱视作为通向“二”而非“一”的真理—程序。也就是说,在爱中的两个个体并没有经由辩证方式(扬弃)来合一,他们并未被新的统一体(婚姻)化解,而是通过一种独特的程序进行“合体”(incorporation),并创建“二的真理”。在巴氏看来,“爱是经由一个悖论得以阐述的一种操作,爱并没有缓解这个悖论,而是应对它,从悖论自身中制造真理”。[注]Alain Badiou, “What Is Love”, p.56. op.cit.
那么,一种矛盾/悖论(“二”)并未被化解/缓解的爱,是否可能?如果爱是一种阐述矛盾/悖论而不是化解它的操作(亦即,不是一种“计数为一”的操作),那么,这种操作还能不能构建起一种具有“解放”价值的统一体呢?
三从辩证性综合到离散性综合
对于巴迪欧而言,爱由事件所开启——一个相遇(encounter)的事件。这个从日常生活中突然刺出的事件充满偶然性,无法依据世界的诸种法则来加以预计或计算。[注]⑦ Badiou and Truong, InPraiseofLove, p.31; p.29.没有人能提前对它进行安排。你没有赶上班车而很偶然地走进咖啡馆,你很偶然地参加了室友组织的一个狼人杀活动,你正好这一秒而非上一秒站在了那个拐角扶住了差点滑一跤的他/她……稍微一点点的变化,相遇不再可能发生。相遇这个事件,完全不受人的操控,它彻底随机、偶然,和运气相关。而爱,就是一个后事件的真理—程序,或者说类性—程序(人类定义自身的程序),它旨在驯服偶然性,在事件(偶然性)中建构真理(永恒性)。
作为事件的相遇,以及该事件所启动的爱的程序,彻底打断日常的生活秩序,一如巴迪欧对事件的描述:“事件就是纯然打断法律、各种规则、局势之结构,并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注]Alain Badiou, “Affirmative Dialectics: From Logic to Anthropology,” 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BadiouStudies, Vol,2, No,1(2013), p.3.你没有准备,突然之间“fall in love”。“fall”是坠落,是一种失重状态、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状态。甚至你也不想要这种状态,但就是赶不走,一种强大的力量就这样侵入了进来,你被另一个人所占据,茶饭不思,魂不守舍,平时的生活节奏全部被扰乱,被吸到一个漩涡中。平时对你那些重要的事,现在却变得不再重要,你也不再受制于日常生活的规则或律令——爱让你对此前一切有了彻底全新的体验。[注]参见吴冠军:《爱与死的幽灵学:意识形态批判六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2—4页。故此,爱的相遇(amorous encounter),是对日常平衡状态的一个灾难性破坏,对个体此前原子式体验的“世界”的一个激进打断。
在这个意义上,爱是通向真理的关键通道。故此,黑格尔同当时自由主义者们在看待婚姻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后者把婚姻视作一种契约关系,其哲学根基是把订立契约的双方视作自足、独立的单元;但婚姻在黑格尔这里并非契约关系,正是因为爱恰恰使双方皆发生存在性—主体性的激进变化,使他们不再自足、独立,而是通过彼此确认(承认)在对方之中的自己,来构成一个新的伦理性统一体。
因此,爱不化解“二”,相反它使“关于‘二’的设定”、“二的场景”得以产生——它使两个“一”之间偶然发生的激烈反应固化下来、使两个“一”变成“二”、使两个人变成“男人”和“女人”。什么是“二的场景”?在该场景中,人不再是一个独体,不再是“一”,差异被插入到同一中,“爱根据‘二’而将‘一’打碎”。[注] Badiou, “What Is Love”, op.cit., pp.54-55; pp.57-58; p.59.此处,巴迪欧对爱的论述,实际上仍然契合黑格尔,在后者这里,爱让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单位,不是一个“满”,而是一个“缺”。经由爱,“自我”的虚假的整全性彻底被打碎。但黑格尔进一步从打破自恋和自满的爱,走向建构一个包含他者的整体的爱(“伦理性统一体”),而巴迪欧则拒绝了进一步用爱对“矛盾”去做出辩证性综合。为此,他开辟了另外一种进路。
在黑格尔那里,原来的“一”(个体),被新的统一体(婚姻)所取代:“婚姻的伦理面向就在于双方把这个统一体作为他们实体性目的的意识中,因此,就在于他们的爱、信任、与他们作为个体的整个存在的共同分享”。[注]Hegel,Hegel’sPhilosophyofRight, p.112.于是,“二”只是作为辩证进程的中间环节而暂时性存在,该进程的首尾端点都是“一”。但在巴迪欧这里,婚姻并不是辩证性综合,而是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的“离散性综合”(disjunctive synthesis),这种综合结构性地把握两个序列,但不把它们简化到一个聚合中心或一个统一体。“二的场景”,就是“离散性综合”得以产生的场景,在其中“二的真理”能够被建构出来。巴迪欧写道:“爱是对真理的一个生产,不是一的真理,而是二的真理。”[注] Badiou, “What Is Love”, op.cit., p.53; p.53.我们所熟悉的真理,都是关于“一”的真理,这个“一”可以是太阳、黑猩猩或者美国、特朗普……“一”本身构成了一个整体单元。而“二”的真理不是关于某种统一体的真理,而是关于绝对差异的真理。“二”的真理首先不是让我们获得普遍性,而是有限性。“二”,被巴迪欧称为“有限性的第一次打开、最小但是最激进的打开”。[注]Badiou,PhilosophyandtheEvent, p.54.
饮水安全,实乃民生大事。作为一个水资源极度短缺的省份,农村饮水安全受到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从“饮水解困”到“饮水安全”,从“饮水安全全覆盖”到“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我省农村饮水从“面的覆盖”迈向了“质的提升”,广大农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在爱中,人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体验是彻底有限的。爱把“二的场景”(绝对差异的场景)带入每个个体生命,这个场景,在你碰上相遇事件之前,并无法进入。在该场景中,个体冲破对世界原子式、唯我式、自恋式的体验,转到对“二”的体验,也就是说,对绝对差异的主体性体验:他/她开始通过“二”的视域(亦即,去中心化的视域)来体验世界,重新审视一切事物。于是,成为一个爱人(lover),意味着你不再是此前的你,意味着你必须去想成为“二”而非“一”意味着什么。“lover”,绝不意味着你仅仅是某个人的“爱人”,而是意味着你自身的一个主体性剧变。在巴迪欧这里,“lover”,是和“thinker”(思想者)、“philosopher”(哲人)一样的词,它指向的不是一种人际关系,而是主体自身的实践——“to think”、 “to philosophize”、 “to love”。对一个个体而言,在爱中,意味着和另一个人共同—存在,建立“二”的视域。
那么,作为离散性综合的爱,其“综合”部分体现在哪里呢?巴迪欧认为,在爱中,两个人“合体”成为独特的主体——爱的主体。“通过一个爱的相遇,这样一个主体出现了,在这个相遇中,两个性别化的位置发生了离散性综合。因此,爱的场景是关于两性(最终关于纯粹差异)的‘二’的一个普遍的独体得以被宣称的真正场景。”[注][法]阿兰·巴迪欧、[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当下的哲学》,蓝江、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译文有改动。这个新的主体(独体),从差异性构建世界,以“二”而非“一”的方式构建世界。爱,开创一个独独属于两个人的世界,并产生出关于差异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爱成为了建构真理的一种独特程序。
爱通向“二的真理”意味着:爱,不是对你爱的那个人的一个体验,而是对世界的一个体验。“爱不是对他者的一个体验,而是在存在着‘二’的后事件状况下对世界或局势的一个体验。”[注] Badiou, “What Is Love”, op.cit., p.53; p.53.从巴迪欧“二的真理”这一洞见出发,爱实则意味着:两个人不再是各看各的(契约主义爱情观),也不是满满地只看到对方(浪漫主义爱情观),亦不是抗争性地盯着对方看(女性主义爱情观),而是通过“二的场景”来看世界。所以,流行歌里唱到的“我的眼里只有你”[注]《我的眼里只有你》,黄小茂词、三宝曲、景岗山演唱。,但这恰恰不是爱,因为这种看还是唯我式、自恋式的。一旦没有转换成“二”的视域,那现在“你的眼里只有她”,之后你的眼里还会出现别的对象,你仍然可以一个人看得目不转睛。甚至就算你对眼中的她“爱”到耗尽生命,仍然不意味着你在爱中。很多艺术作品讴歌那种耗尽自己生命的爱情,称之为真爱,但实质上这仍然是“一的场景”。当真正通过“二”的视角来看,你的眼里不会只有她,而是有整个世界。故此,爱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一个“关系”(不管是契约关系、强烈的浪漫关系抑或男女对抗关系),而是迈向真理的一个通道,是生命的一个重新创造(婚姻、孩子的诞生……),是让世界重新诞生的激进实践。
四后黑格尔主义的两个“解放”路向:张念抑或巴迪欧?
巴迪欧从数学本体论出发,挑战辩证法所旨在抵达的终点(“一”、“整体”):“数学在这里作为辩证的中断而发生”[注] Alain Badiou, BeingandEvent, trans. Oliver Feltham, London: Continuum, 2005, p.169; p.23.。数学的无限性拒绝任何“历史终点”意义上的闭合性。进而,巴迪欧在该著中耗尽心力重新阐述了作为哲学概念的“事件”。诚如科可然(Steven Corcoran)所评论的,该概念的“机遇导向之本质逼迫他决定性地远离如下理念:历史中存在着扬弃,或一种辩证性的长程”[注]Steven Corcoran, “Dialectics,” in his(ed.), TheBadiou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98—99.。巴迪欧反复强调:“整体并不存在”、“(大写的)历史并不存在”;而事件,就是“整体的纯然对立面”[注]Alan Badiou, LogicsofWorlds, trans. Alberto Toscano, London: Continuum, 2009, p.141, p.144; Badiou, BeingandEvent, p.176.。辩证法所抵达的“一”,实则只是一种“计数为一”(count-as-one)的操作。《是与事件》的开篇名句就是:“一就是不是”⑨。不存在统一体(“一”),只存在“统一化”的操作(“计数为一”)。一旦被计数,所有的差异都被整合成作为计数标准的“一”的坐标系下的参数点。在计数为一的尺度之下,一切人和事物的独体性(singularity),都被抹除、并被暴力性地强行纳入作为整体的“一”之中。
张念的书以黑格尔作为起始点,正是因为在她看来,女人在西方哲学上就是在黑氏那里首次出现却又在那里失踪——女人以经验性存在(现象)出现,但随后被爱化解了其主体性存在(意识),没能从“自在”上升为“自为”。相对于黑格尔所规划的朝向真理(绝对知识)的解放进程,张念呼唤一种祛除真理所有权的解放政治——女人必须拒绝一切的被“言说”(被真理的“一”所言说),必须成为“不是东西的东西”。[注]而爱,就是“黑格尔意识哲学的‘女性迷踪’”的罪魁祸首——“一位伟大的辩证法大师,其逻辑的力量之于女性问题,显得如此疲弱与荒唐”。[注]张念贯穿全书的批判方案,实则便是用黑格尔反对黑格尔,让作为“辩证法中的斗争环节”的女性意识持续苏醒,来对抗“来自‘一’的理性规定”。[注]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第36页,第283、 290页;291页;第60页;第60、 36页。
在张念对爱的这一激进女性主义批判视野下,巴迪欧对爱的“礼赞”,便彰显出其作为后黑格尔视域下另一种哲学努力的重要政治价值。代之以黑格尔笔下那作为辩证性综合、通向“伦理性统一体”的爱,在巴迪欧这里,爱指向离散性综合,一种向“一”的秩序中插入“二的场景”的操作。巴迪欧继承拉康之论:男人与女人的性差异,不是某种经验性—生物性的差异,而是标识了绝对差异。故此,这里的“二”指向一种离散性结构,它并非“三”的一个元素,也拒绝被收拢到“一”中(计数为一)。
基于这种离散性结构的“二”,在政治面向上,巴迪欧并未如同张念那样,走上以“二”抗“一”、以捍卫女人的名义拒绝爱和真理的“解放政治”道路。相反,巴迪欧赞颂爱、捍卫真理,并声称爱就是四种真理—程序之一。巴迪欧的解放政治,不是“女权女人”孤单地在这世界上去抗争一切,而是在爱中的两个人“合体”成为爱的主体,以“二”的视域重新建构世界。在巴氏看来,爱,正是“最小的共产主义”。[注]爱让我们置身“二的场景”,超越“一”的自私、自恋、对事物的私人占有,真正地共同—生活,在共同中持存。故此,作为激进哲学家,巴氏声称:爱,让我们对共产主义始终保有信心。人的共同—生活能够整合所有的“前政治”的差异,那是因为:他/她是谁、出生于哪里、讲什么语言、什么文化,都构不成爱的创造的障碍。[注]Badiou and Truong, InPraiseofLove, p.90; pp.62-63.
(4)兼职偏好:学生兼职会优先选择家教类兼职,其次会选择服务类与代理类兼职,这几类兼职一般收入较高,且能发挥自身价值。
张念以勾画主奴辩证法的黑格尔对抗作为“爱的哲学家”的黑格尔,而巴迪欧则恰好反转过来:继承黑格尔对爱的“礼赞”,同时实质性地改写黑格尔的辩证法。晚近,巴迪欧把自己从《是与事件》至今所有著述所构建起来的理论框架,正式称作为“肯定的辩证法”(affirmative dialectics)。我们知道,在抵达其最终终点之前,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是“否定”。[注]参见吴冠军:《辩证法之疑:黑格尔与科耶夫》,《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12期。巴迪欧写道:“这就是黑格尔主义框架:你有一个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建构与否定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运动的真正原则以及创造的真正原则,是否定。”而这种框架的伦理—政治展开,就是一种“同情”视域,“在该视域中,我们意识之英雄是受苦痛的人体、纯粹的受害者,而且我们也知道,那在民主面具下的资本主义统治,完美地胜任这种道德主义。”[注]Badiou, “Affirmative Dialectics: From Logic to Anthropology,” op.cit., p.2.张念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以及2017年10月至今蓬勃兴起的“me too”运动,实则都没有摆脱这种道德主义控诉的逻辑。[注]2018年刚过去的半年多,“me too”运动进入中国并不断壮大,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社会与性别文化。然而,它所主要采取的受害者站出来揭露性侵者/性骚扰者的抗争形态,按照巴迪欧的论见,仍可以完美地被既有秩序(“民主面具下的资本主义统治”)所吸纳。张念在她支持“米兔”运动的《性契约:女性解放的投名状?》一文末尾追问:“在语言和身体的亘古对抗之中,意愿究竟站在哪一边?”(参见微信公众号“电影剧场”2018年7月31日)而巴迪欧会回答:这种站队基于“同情”逻辑;如果“米兔”运动本身是个事件的话,那么在道德控诉之后,我们需要开启真理—程序,形成离散性综合以构建出全新的主体性。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艰难的穿越开始了。管道沉重地向前顶推着,每顶进一米,就抽回来清除管道里的土,然后再向前顶进,同时测量方位,稍有偏差及时校正。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保护管终于顺利顶过去了,每百米偏离误差不到5厘米,路基也没有受到丝毫破坏。整个穿越铁路的工程仅用了3天,费用只花了一万元。后来工程进展到永定河一带,又遇到了新的障碍。表面看去挺干燥的河床底下,流动着地下水,河床上全是流沙土,施工困难很大。
相对于张念仍然困限在黑格尔主义辩证框架内,巴迪欧则旨在改写这个框架(亦即,改写肯定与否定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肯定的辩证法”——在其中“否定”仍然扮演重要角色,但“肯定”居先。事件虽然具有否定性力量,但它并不直接改变既有局势(如1968年五月风暴对国家的局势并没带来真正的改变,戴高乐仍手握大权、政府仍保持运作),事件所具有的力量,仅仅是打开一个新的可能性。在事件之后,这个新的可能性的诸种后果,惟有经过在真理—程序中的阐述(如爱的宣言),才具有了被“物质化”的可能(如全新的世界)。更关键的是,在真理—程序的阐述中,新的主体(如爱的主体)经由离散性综合而诞生出来。巴氏写道:“自然地,在这些后果中存在着不同形态的否定(斗争、造反、反对某事物的一种新可能性、解构法律的某个部分,等等),但这些否定形态皆是全新主体性之诞生的后果,而不是反过来。”[注]Badiou, “Affirmative Dialectics: From Logic to Anthropology,” op.cit., pp.3-5.换句话说,事件之后,新的主体性(忠实于事件的主体)必须先于各种否定形态诞生出来。
这就意味着,当你有了一个可以真正在局势中创造新可能性的事件,你必须在各种否定以及它们的后果产生之前,通过真理—程序创造出一个新的主体性,否则你就浪费了这个事件,让它白白地消散无踪。以爱这个真理—程序为例,如果你不用“我爱你”这个宣言把相遇这个事件固化下来,并进而创造出爱的主体,相遇事件很快就会消散如烟,一切回归日常生活。在黑格尔这里爱首先是一个否定性力量(第一个时刻,否定个体的完整性与独立性),随后进一步成为一个肯定性力量(第二个时刻,否定的否定/辩证性综合,诞生新的统一体)。而在巴迪欧这里,爱首先是一个肯定性力量(诞生新的主体),随后才产生诸种否定性和肯定性的后果(告别原来日常生活、以“二”的视域重构世界)。
在张念的以黑格尔反黑格尔论述里,女人构成了男人的否定,而爱则构成了否定的否定(新的肯定/综合),女人被再次取消、收摄到婚姻之中。张念力图保留前者而截去后者,在她这里,女人本身指向解放。但在巴迪欧这里,女人无法指向解放,因为这样的“解放”永远无法到达共产主义。爱指向解放(最小的共产主义):相遇的事件开启爱的程序,在该程序中新的主体性(爱的主体)经“合体”诞生,该主体打碎旧有的“一”(否定),并以“二”的视域重新建构世界(肯定)。
在这个全新的辩证结构(肯定的辩证法)中,真理不是被发现,也不是在辩证进程中自动抵达,而是被创造出来——在一次又一次具体的科学、政治、艺术和爱的实践中被建构。正是在此处,巴迪欧区分人的生活和动物式生活:动物仅仅追求自然欲望的满足、幸福、安全等,而以人的形态活着,就意味着不断把自己“合体”到真理中:“主体的合体,就是一些人类动物合体到某种可以称作为真理进程的东西中。这就是在肯定的辩证法语境下,我们可以用‘人性’和‘人类’这些词的全球场域”。[注]Badiou, “Affirmative Dialectics: From Logic to Anthropology,” op.cit., p.12.巴迪欧在其人类学论述中,提出一种非人类主义的“人性”概念:“人性”提供四种类性程序或者说真理程序:科学、艺术、政治和爱。只要存在着这四者,“人性”即可以被证实仍然存在。在巴氏这里,“人性”是无数独体性的真理的历史集合体。See Badiou, “What Is Love”, op.cit., p.55.作出爱的宣言、进而以“二”的视域创造“世界”,就是从动物上升到人类、从事件上升到真理、将偶然上升到“命定”(永恒)的一种激进的主体性实践。爱的主体,不会只是女人(“女权女人”、“不是东西的东西”);相反,“只有在爱的场域中,才有‘女人’和‘男人’”。[注]Badiou, “What Is Love”, op.cit., p.65.
张念为了女人而反对爱;而巴迪欧会对她说,在爱中,你不再执着成为一个女人,因为你成为了一个爱人。[注]希望在我们的时代中,“me too”不只是在否定(女人被侵犯)的意义上被说出,同时亦有越来越多人在肯定(我亦是爱人)的意义上说出“me too”。
【作者简介】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项目编号:18ZDA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欧陆前沿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8ECNU-QKT012)。
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11
(责任编辑刘晓虹)
标签:黑格尔论文; 真理论文; 巴迪论文; 事件论文; 女人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项目编号:18ZDA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欧陆前沿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8ECNU-QKT012)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