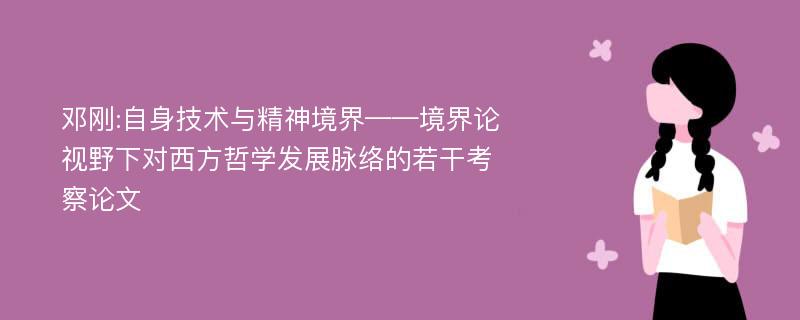
摘 要:福柯晚年提出的“自身技术”问题,若从中国哲学视角来看,可视作一种工夫论,但福柯这一学说的局限性在于,作为一种工夫论它是不完整的,因为其缺乏一种境界论的指导。境界论与工夫论二者是互相补充的,缺一不可,无境界的工夫论是盲的,无工夫的境界论是空的。从境界论出发,可获得考察西方哲学的一个全新视角。境界论问题是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的一个盲区。然而古希腊哲学仍具有境界论的维度,柏拉图、普罗提诺、伊壁鸠鲁等人的哲学思想,在境界论方面亦以某种掌握智慧、具有美德之人为归宿。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境界论问题渐渐淡出西方哲学的视野。笛卡尔等人开启的近代哲学,其理性主义本身实际上包含两大前提:一,人具有某种自然光明;二,此种自然光明是可以自我扩展的。这两个前提其实可以扩展到理想人格之问题,即境界论问题。由此视角出发,可看到斯宾诺莎、尼采与柏格森三位哲人其实分别从不同方向论及了境界论问题。
关键词:自身技术;福柯;境界;工夫;理性主义
一、福柯的“自身技术”学说及其局限
在晚期福柯的思想中,“自身技术”(technique de soi)、“关心自身”(soin de soi)是相当重要的概念,由此概念出发,福柯重点发掘和梳理了古代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所呈现出来的诸种不同的自身技术。他晚年的著作《性经验史》即是以“性”问题为核心进行的对自身技术的探索与展开。自身技术“无疑是存在于一切文明中的对个体进行建议或规定的一系列措施,为的是按照某些目的、通过自我控制或自我认知的关系,去确定个体的身份、保持这种身份或者改变这种身份”(1)福柯:《福柯文选》III,汪民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页。。自身技术也就是对于自身的关怀、关心、关照。由此视角出发,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只是“关心自身”的诸种方式之一。“自身技术”可以视为一种主体化的方式。主体化的方式对应于两类分析:“一方面对应于对象化模式,此模式把人变成主体,这意味着只有对象化的主体,而主体化在此意义上就是对象化实践;另一方面对应的,则是通过一定的自身技术从而把与自身的关系(rapport à soi)构建为其自身生存的主体的方法”(2)朱迪特·勒薇尔:《福柯思想辞典》,潘培庆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5页。译文根据法文原文有改动。。在福柯看来,现代性条件下的主体化方式和“自身技术”,满足于将自身建构为知识、道德、权力的主体,通过无孔不入的生命权力,不断地强化对于个体的监视和管理。不满于笛卡尔以来的近现代哲思方式,福柯要求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来思考生命与自身。在福柯这里,通过“自身技术”概念,对古代哲学生活智慧的强调,并非为了“复古”,而是为了摆脱现代性在制度、文化、语言、观念等领域强加给人的种种束缚,从而使得自身有可能不断地超越自身,如同福柯本人在《逾越序言》中所指出的,应当不断地去逾越种种界限(3) Michel Foucault,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uvres, vol. 2, Paris: Gallimard, 2015, p. 1199.。对于通过“关心自身”而展开的各种各样的自身技术,古代文化中的不同流派都进行过诸多富有意义的探索,并且古代人能够将身体、心灵、性爱、婚姻、友谊、言说、政治等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纳入“关心自身”的视域中,将所有这些都视为发展自身、完善自身的积极手段。“自身技术”的宗旨在于实现自身的自由,对于自身的关怀就是“自由的实践”。这种自由实践,最终实现的是一种生存美学,即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正如高宣扬先生所指出的,“福柯的生存美学,要求人在其自身的一生中,对自己的生存内容、方式和风格,进行持续不断的艺术加工的实践活动”(4)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36页、523页。。
如果从中国哲学的视角加以审视,那么或许可以将福柯所说的“自我关怀”理解为修身,从而进一步将“自身技术”理解为一种“工夫论”。当然,这里所说的“工夫论”应当作最宽泛的理解,即用于关心自身、发展自身、提高自身、完善自身的各种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工夫论”解决的是“怎么做”(how)的问题,涉及的是各种各样的方法,需要考虑这些方法的效率、效果、可行性,这些方法有时涉及人的身体,有时涉及人的心灵,有时同时涉及人的心灵和身体。但是,要使“怎么做”(how)的问题得以可能,得以被提出,必然在此之前已经提出“为什么”(why)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已然知道我为什么需要关心自身,因此我才去考虑如何去关心自身。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返回“什么是自身”的问题,而这实际上也就是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所提的“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une ontologie historique de nous-même)的问题。在福柯的笔下,批判不再是去发现知识的普遍形式,而是将这些普遍形式视作历史的、偶然的、特殊的,视作有待去逾越和超越的边界。“这种批判,去澄清那些使我们成为我们的偶然性,以及使我们不再是我们的可能性……这种批判,不再寻找使形而上学变成科学的可能性;而是寻找尽可能远、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重新启动自由的无定限的工作”。为了让这种自由不是一种空话,福柯强调一种实验态度(attitude expérimentale),这种态度体现在,一方面进行历史调查,另一方面则是去体验现实和当下性。因此福柯拒斥一切宏大的计划,一切计划都可能导向对自由的取消。相反,福柯偏爱的是一些局部的、部分的体验,这些体验乃是“我们自身作为自由存在对于我们自身所做的工作”(travail de nous-même sur nous-mêmes en tant qu’êtres libres)。总的来说,这种“我们自身的本体论”,乃是“一种态度,一种伦理(ethos),一种哲学生活,在这种哲学生活之中,对我们之所是的批判,既是对强加给我们的种种界限的历史分析,又是对这些界限的可能的逾越的体验”(5) Michel Foucault,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uvres, vol. 2, p. 1393, sq, p. 1394, p. 1397.。如果说福柯早期和中期的考古学和系谱学,主要侧重于对这些界限的历史分析,那么他晚年的自身技术,则是侧重于体验。
关于“我们自身的本体论”的简略分析,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福柯何以会提出“自身技术”之问题的关键钥匙。在福柯看来,人、主体、自身其实都只是历史的存在,既不存在关于人的普遍适用的定义或者本质,也不存在人不得不服从的知识形式和权力形式,一切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基于一定的历史事件而后天形成的。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自身形式之外,我们显然还可以设想和实践其他可能的自身形式。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显然需要深刻的批判精神,以及敢于去逾越界限的生活态度。就此而言,福柯提出“自身技术”,正是要通过借鉴古人的智慧,拓展生活形式的领域,提高生活的情调,丰富生命的意义,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不过福柯英年早逝,使得他未能顺着晚年的研究和思路深入下去,从而也就未能穷尽“自身技术”学说的全部理论意义,令人倍感遗憾。由于人的身体和心灵都具有无穷多的潜能,因此只要人顺着某个特定的方向,持之以恒地努力修习,就有可能取得杰出成就。例如,通过持续锻炼身体,一个人就有可能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我们可以追问,至少在理论上,如果一个人不断地致力于德性和智慧的提升,是否就有可能成为古希腊哲学中所说的有智慧的人,或者成为中国哲学中所谈到的圣人,即理想人格。如果有工夫论,如果有人持续不断地做工夫,那么应当有可能出现将工夫做到极致,从而达到完美人格境界之人。因此,理想人格乃是自身技术之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再次借用中国哲学的术语,将有关于理想人格与精神境界的学说称为境界论,那么显然在福柯这里境界论是缺失的,或者至少是模糊的。因为对于福柯而言,他的自身技术和生存美学所强调的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态度和逾越精神,而丝毫无涉理想人格之设定。
实际上,对于福柯,以及对于包括德里达、德勒兹等人在内的大多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而言,尽管他们的理论互相间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这些理论却有一个共同的旨趣,即对西方传统哲学、传统思维方式、传统规范加以批判和颠覆,从而使得人们在思想、意义、艺术、行动、政治等领域可以“获得更多的可能性”或者“创造新的可能性”。这些“后”理论,都积极致力于对各种既有规则的批判、突破和超越,但是并未提供某种确定的出路或者方向,用来取代旧的“理论”。他们的思想背后,大都预设了这样一种关于人性的看法:人是没有本质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关于人性的任何一种述谓或者指向,都是对于人的一种限制。因此,也就不存在理想人格,因为任何一种被理想化的人格,都有可能在现代性的话语体制之中,被转化为施加于个人身上的压迫性话语。因此,尽管这些哲学并不缺乏各种类型的批判、解构、否定等工夫,但这些工夫并不以某种理想人格为依归。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无境界的工夫”,即无理想人格作为工夫之指向和目标。正因为缺乏境界论,或者说缺乏理想人格作为人生之理想和人生之典范,因此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屡次陷入危机和迷途,从而既无从为学者以及一般人提供一种人生理想,亦使得哲学本身之合法性成为危机。借用一种康德式的表述,我们认为,无工夫之境界是空的(白日梦、大话),无境界之工夫是盲的(不知去向何方)。若无境界之开启与指向,则做工夫只是枉然。
尽管福柯发展出一套作为工夫论的自身技术学说,但却忽视了这一学说本身如果充分展开,将涉及理想人格问题,即境界论问题。尽管福柯对“关心自身”的重视,一定程度上与晚期希腊哲学中的伦理学转向殊途而同归,但是福柯却忽视了这种伦理学转向同时伴随着对某种理想人格的构想。众所周知,晚期希腊哲学以及后来的希腊化时期,宇宙论、知识论问题相对淡出,而对于“伦理”的关怀成为各派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都将伦理学视为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时期的伦理学,关心的并非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人生意义问题,即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一个人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德性、有智慧的人。为了获得真正的人生智慧,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对于获得智慧的方法也有着丰富的思考,即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如何“做工夫”的学说。斯多亚派的工夫论可以视作对苏格拉底所谓“德性即知识”命题的进一步发展。此派工夫,其关键在于通过某种知识论进路把握“善”的理型,同时认识到,此种善的理型,既是宇宙论的法则,亦是人的灵魂的法则,人的灵魂中最高的部分乃是努斯(nous),努斯即理性,其本身即已经是一种光明而良善的力量或者能力。一旦获得对善的理型以及灵魂自身之认识,即能够用这种理型来规范灵魂,规范自身,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就能跃居于感性的欲望、冲动、意见之上,成为灵魂的真正主宰,从而灵魂也转化为纯粹的、干净的理性灵魂。当然,具体来看,这一时期有着各种类型的修行方式:如写书信、记日记、加入某个学校、追随一位导师,等等。福柯在晚期的不少著作和讲座稿中,对此有所讨论。正如哈多(Pierre Hadot)所指出的,在这个时期,哲学乃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晚期的罗马帝国,哲学与基督教、摩尼教等处于竞争状态。随着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渐渐衰落。因为,就人应该如何生活而言,基督教已经给出了答案,即人的正当生活方式不是别的,就是去做一个基督徒。
二、境界论问题与中西方哲学
第三个维度所论述的问题,即中国哲学所说之境界论的问题。冯友兰在《新原人》中,区分了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并且从其“觉解”说出发,对各种境界以及各境界之间的差异,皆作出理性的说明,例如他说天地境界:“人有此等进一步底觉解,则可从大全、理及道体的观点,以看事物。从此等新的观点以看事物,正如斯宾诺莎所谓从永恒的形式的观点以看事物。人能从此种新的观点以看事物,则一切事物对于他皆有一种新底意义。此种新意义,使人有一种新境界,此种新境界,即我们所谓天地境界”(6)冯友兰:《贞元六书》下,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79页。。唐君毅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中,亦发展出一套体系宏大、义理精深的哲学。他根据心灵活动的遍运与境的遍通的程度,而区分出三界九境。在谈及“哲学之任务”时,唐君毅写道:“至于此人之心灵活动,及其所感通之境,与此立人极之目标,人皆可自觉其相关者,即为此心灵活动之具遍运一切境之意义者,或其所感通之境之遍通于人之一切心灵活动者。此活动与此境,亦人所共有。唯此活动之遍运与境之遍通,更可有程度之不同。程度高者,其所运愈广,其所通愈大。”(7)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称这一境界论为“人生理想论”,并且在该书的结论中指出:“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生活准则论即人生理想论”(8)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46页。。当代学者杜保瑞将“境界论”“工夫论”“宇宙论”“本体论”视作中国各派哲学所共同关注的最为核心的四大问题。关于“境界论”,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哲学家的理论终点在于提出一个完美人格的典范,他的世界观和自己的人格景象统合为一,他获得了一个感通天地宇宙的理想自我人格,不论他的称谓是圣人、君子、贤者、真人、神仙、菩萨或成佛,这个理想人格的状态,笔者给它一个名词叫作境界哲学,也就是‘我要成为什么’的问题。境界哲学就是要将这些完美的理想人格典范当作一个重要的基本哲学问题”(9)杜保瑞:《中国哲学方法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3页。。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境界”一语,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界定:第一种泛指不同层次的认识方式、生活方式和心灵状态,于是既有高阶的境界(天地境界),亦有低阶的境界(自然境界);第二种则专指理想人格或者完美人格。前者取其广义、普遍义,后者取其狭义、最高义,本文主要根据第二种界定来使用境界论一词。那么,究竟什么是境界论所主张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早在先秦时期,儒家、道家各有其关于最高人生境界的论说,如《论语》中,孔子自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孟子则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集大成者”。而宋明理学也主张“圣人可学而至”,而在理学开端时期的北宋五子中,程颢以其高尚的人格,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儒家圣贤气象的体现。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形容程颢:“纯粹如精金,湿润如良玉……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10)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77页、638页。。正因为程颢心胸宽广,行为洒脱,待人友善,做事得体,因而能够具体而微地呈现出一位儒家式的圣贤的形象。例如游定夫从游数月,感觉如沐春风(11)游定夫访龟山(杨时),龟山曰:“公适从何来?”定夫曰:“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而来”。龟山问其所之,乃自明道处来也。见黄宗羲《宋元学案》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78页。。因此,程颢其人其学,可以视作境界论哲学的最佳例证之一。杜保瑞在《北宋儒学》中指出“程颢儒学的特点或最具创造力的义理建构部分就是境界哲学”(12)杜保瑞:《北宋儒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68页。。程颢的“识仁篇”“定性书”实际皆是从已经达到的境界来言说工夫。在“定性书”中,程颢指出“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13)程颢、程颐:《二程集》上,第460页。。冯友兰对这两个文本有着精彩的解释,道学不仅是要认识到自身与万物是一个整体,而且“要实在达到这种境界,要真实感觉到自然与物同体”,通过修养达到这种境界之后,方可言“对人的精神境界是与天地同样地廓然大公”(1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109页。。
众所周知,康德将其哲学概括为四个问题,即:我可以认识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在笔者看来,这四个问题也许足以概括康德自身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但并不足以描述和概括哲学的全部问题。仅就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而言,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回答:(1)在其实际性之中人是什么,即通过观察一个人在实在的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可以得出一种描述性的考察,这种考察很容易导向“性本恶”的结论;(2)就其规范性而言,人应该是什么,即根据某种规范对人之本质及其行为进行要求,例如儒家要求一个人应当成为一个君子、一个好人,而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要求一个人应当成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这样一种考察容易导向“性本善”“人是理性的动物”等观点;(3)就其理想性而言,在理想状态下,人可以成为什么,人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即一个人如果按照上述规范性之要求,最完美、最彻底地实现了这些要求,人可以抵达何种人格或者何种理想境界,例如,儒家的完人乃是圣人,道教的完人乃是神仙,而在斯宾诺莎那里理想境界则体现为理性之完善(这种完善体现为对神的理解,以及在神的必然性的光照下去理解万物)。
改造直接收益方面,以SNCR系统年运行8 000小时计算:稀释水泵电能消耗8 800kWh,约3 960元;除盐水消耗量减少1 816吨,约7 264元;氨水消耗量减少110吨,约81 767元。而单台炉整体改造费用为42 000元,可见从SNCR喷嘴系统改造中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节能减排工作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在同类型锅炉中值得推广应用。
然而,理想性的人的问题或者说理想人格的问题,尽管是中国各派哲学普遍关心的问题,但是对于西方哲学却并非如此。实际上,许多西方哲学家完全无视或者完全忽略了这一问题,又或者,虽然意识到这问题却并不重视。也就是说,在中国哲学中极为重要的境界论问题,在西方哲学那里却时常处于缺席状态。为什么西方哲学会缺乏境界论?为回答此问题,有必要对西方哲学史作简单之梳理。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希腊哲学中,可以找到对理想人格或完美人生境界之描述。柏拉图的《会饮》与《斐德罗》两篇皆讨论了灵魂复归理念世界之后所达到的完美境界。例如,在《会饮》篇中,苏格拉底转述了狄欧蒂玛关于爱的“最高深、最神圣的道理”,这种道理就在于从追求美的形体,到追求美的灵魂,进而上升到追求品德的美、知识的美,以及美本身。“眼睛里有了各式各样美的东西,就不再像奴隶似的只爱一个个别的东西,只爱某个小厮、某个成人或某种行动的美了。他不复卑微琐屑,而是放眼美的汪洋大海,高瞻远瞩,孕育着各种华美的言辞和庄严的思想,在爱智的事业上大获丰收,大大加强,大大完善,发现了这种唯一的知识,以美为对象的知识……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亲爱的苏格拉底,人见到那个美本身,它是人最值得活的阶段”(15)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37~338页。。显然,这段文字描述的这一通过爱的不断升华而实现的“美的历程”,最终所抵达的,正是灵魂返归理念世界之后的理想状态或者完美境界。
随着基督教成为西方的主流宗教,基督教思想相继与柏拉图主义及亚里士多德主义相结合,从而形成基督教神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并进而构成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论背景。据基督教神学,人皆有原罪,从而最完美的人在上帝和耶稣面前也是罪人,是有限的、不完美的人。在基督教的理论背景下,设想一个完美人格,这种设想本身就构成对上帝观念的一种挑战。尽管在中世纪一些神秘主义者那里,并不缺乏可以称为工夫论的修行手段,以及可以称为境界论的关于通过修行所达到的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之描述,然而这些思想观念始终屈从于神学之大背景。
自培根、笛卡尔以降,理性主义渐成主流,神学渐趋淡化,甚至出现了对基督教加以激烈批判的一些无神论哲学家。然而,神学的一些基本设定,未经批判就被哲学家们拿来作为前提使用,从而仍然潜在地支配着西方人的思考方式。例如,笛卡尔认为人的精神作为我思,包括知性和意志两方面的能力,就知性而言,其能力是有限的;而意志,就其能够意愿任何东西而言,则是无限的。但总的来说,只有上帝才是无限的实体,而我思则只是有限的实体,有限与无限之间有着无限的距离,存在本质性的差异。认为上帝是无限,人(主体)是有限,这显然是从基督教传统中传承而来的一个未经反思的前提。
三、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三种境界论进路
信度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以及可靠性,一般多以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来检验。如表1所示,各构念的Cronbach’ α系数的变动范围在0.919~0.951之间,均大于0.7,因而可以说研究中采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另一方面,构念的组合信度(CR)也是判别内在质量的标准之一,各构念的CR值均在0.60以上,表示量表的内在质量理想。
对境界的哲学描述,其实构成西方近代哲学之必然归宿或者必然推论。因此,对于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而言,设想一个完美人格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完美人格,或者被转变为上帝,或者被归诸为理念,几乎不曾被设想为现实之中可能出现的人物(即实际上未出现,但存在出现的可能性)。当然,在近现代哲学之中,仍然有一些哲学家,独具慧眼,意识到理想人格的重要性,从而在其哲学之中展开了一种境界论的思考。限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斯宾诺莎、尼采、柏格森三位哲学家为例,他们正好代表西方哲学中境界论思考的三个方向,即分别将自然光明归诸知性(斯宾诺莎)、意志(尼采)与生命(柏格森)。
理性主义哲学在其出现之际,就已经包含如下观念: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拥有一种原初的肯定性能力,特别是体现在认识方面,这种能力即知性(Understanding, Verstehen),这就是笛卡尔所说的自然光明。而在现代条件下(理性与技术、理性与经验、理性与权力等的结盟),这种自然光明可以获得两种根本的规定性或者属性:(1)自然光明是自明的、自治的,无须他者就可以自行揭示自身,自行建立自身,例如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通过普遍怀疑,最终确立了“我思故我在”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2)自然光明是可以自我发展、自我扩大的。例如,卢梭指出,人有自我完善化的能力(16)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01页。。当然,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倾向,或者将这种自然光明赋予人的知性(如斯宾诺莎),或者将这种自然光明回溯于人的意志(如尼采),或者归诸其他的原则(如柏格森所说的生命)。如果说理性本身既具有自明性,又具有自我完善性,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设想一种达到无限或者接近无限的完美理性,作为这种无限的自我完善过程的结果。由此也就必然意味着,人可以依据这种原则不断地发展自身,完善自身,从而上升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理想人格或者完美人格,发展出一种最高的人生精神。
至于尼采,他所说的超人,则是从意志层面,对完美人格进行的描述。超人能够摆脱一切既有的社会道德和规范之限制,为意志创立新的法则。尼采对西方的传统哲学和宗教进行了十分犀利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非对一切价值的摧毁,而是试图在一个新的层面来建立新的价值,正如他的书名所揭示的,要“超善恶”,但并非“超好坏”(19)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45页。。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白中,查拉图斯特拉对众人说:“我教你们超人。人是应该被超越的东西。”(20)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之所以人需要被超越,乃是因为在一切有生命的事物中都有着强力意志,而这种意志是一种不得不自我超越的东西(21) “在我发现有生命事物的地方,我就发现强力意志”。“生命本身把这个秘密告诉我。‘睢’,它说,‘我就是总是不得不超越自我的东西’ ”。见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14页、115页。。各种传统的哲学和宗教,反映的都只是弱者的思想或奴隶的道德,而尼采呼唤的是真正能够肯定意志、扩大意志、发扬意志的强者的思想或主人的道德。但是,超人到底是怎样的,尼采则语焉不详,只是用一些诗意文字加以暗示。例如,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如此描述:“需要另外一种精神,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出现的。那被战争和胜利强化的精神,那要求征服、冒险、危难甚至痛苦的精神;为了达到那个目的还需要习惯于凛冽的高山空气;为了达到那个目的需要一种高明的鲁莽,一种去认知的最自信的勇气,这勇气是来源于伟大的健康;一言以蔽之,为了达到那个目的需要的正是这种伟大的健康!人如今还可能有这种健康吗?但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那个怀有爱和蔑视的人,那个拯救世界的人,那种创造精神,还是会来临的”(22)尼采:《论道德的谱系》,第90页。。对于这种“伟大的健康”,《快乐的知识》中如此描述:“我们这些新人、无名者、不明事理者……我们也需要一种新的手段,即一种新的健康,一种比所有至今的健康都更强壮、更精明、更坚韧、更大胆、更快乐的健康”(23)尼采:《快乐的知识》,杨恒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63页。。尽管尼采将超人的实现或者出现,寄望于未来,但超人在他那里,仍可以被视为某种程度的理想人格。超人作为强力意志的最高体现,并不是现有的价值体系的最高体现,而毋宁是新的价值体系的创造者,而要使得这些创造得以可能,无疑就要求超人具有远超普通人的更为强健、充沛、博大的身体和精神,从而使得自身所创造的价值,不仅成为个人的价值,也进一步成为社会中的其他人也承认和接受的价值。
对于斯宾诺莎而言,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的心灵中的理智的部分。理智使得人获得真知识,从而由被动的心灵转变为主动的心灵。斯宾诺莎还提出了“人性的模型”(natura humana exemplar)概念(17)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169页。,即“完美的人的观念”,此概念近乎中国哲学所谈到的圣贤。斯宾诺莎的哲学是一种一元论哲学,试图从神出发来考察世界万物,包括人本身。“只有包罗万象的整体,即被理性所理解的自然,才能够满足人类情感的要求。这样,神成了知识和行为两者的开端和终点。最高的生活境界是在对神的充分意识中生活”(18)罗斯:《斯宾诺莎》,谭鑫田、傅有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7页。。而要达到对神的认识,只能是通过某种直观,即在感性知识和推理知识之外的第三种认识。认识神,意味着认识到神即自然,神才是唯一的实体,人世间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依赖于神。意识到神才是万物的运动的唯一原因,人就可以免于受制于情感和欲望。唯有这种认识,才能让人真正地克服情感和欲望,从而成为自身的主人,真正地获得理性和自由。
原料:低筋面粉160克、融化的黄油和细砂糖各60克、鸡蛋 150克、牛奶100克、玉米淀粉40克、泡打粉3-4克
在笔者看来,自笛卡尔以降的理性主义,其实隐含着一种对人性本身光明的原初肯定,以及对人性本身不断进步的真诚信念,顺此思路自然而然可以推出关于理想人格的若干问题:如果具有理性的人在理性的各个方面(认识、道德)不断进步,那么是否存在作为最高程度的理性的理想人格?如果存在,这种理想人格是怎样的?这样一种理想人格在现实中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如何才能抵达?
柏格森在《论意识的直接材料》一书中,提出“绵延”概念,用以说明真正的时间。绵延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进展,一种不断更新的创造,一种生生不息的涌现,是未经人为分割的大全,因此绵延亦用来描述自由、生命、精神。不只是人的心灵绵延着,在人之外的各种物质也绵延着,只是其绵延的方式与节奏不同于心灵。物质本身并非笛卡尔所说的广延,而仅仅只是当物质落入知性的目光从而被安置到某种空间之中,才被转化为具有秩序和量的对象。如果说一切物质都以某种方式绵延着,那么唯有生命体最能体现绵延本身的强度和创造性。柏格森通过《创造的进化》一书,发展出一套生命哲学,将一切生物都解释为生命冲力(élan vital)的产物。因为人具有清醒的意识和自由的行动,因此可以被理解为生命进化的高峰。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的进化就此结束,因为生命冲力迈向更高点的努力从未停止。如果说自然进化已经停滞,无法导致新的物种的产生,那么更高层次的生命就体现在道德和宗教方面,体现在一些英雄人物的伟大人格之中,正是这些伟大人格为人类创造出新的价值、新的精神坐标,以及“开放社会”的伟大理念。柏格森晚年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1932)一书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自然而然形成的封闭社会(部落、民族、国家),还可能出现一种超越封闭社会的开放社会(泛爱众生,世界大同)。然而,“通过推扩的方式从特殊性的爱上升到普遍性的博爱是不可能的,因为爱父母、爱邻人皆是对特殊个体的爱,不同于具有普遍性的爱人类,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爱”(24)邓刚:《从总体义务到开放道德——论柏格森的道德哲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我们在社会义务这一基础上所窥见的社会本能仍然只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无论该社会的规模有多大。……但该本能本身并不关涉人类,因为在民族与人类之间,其间隔有着有限到无限、封闭到开放的全部距离”(25) Henri Bergson, Lesdeuxsourcesdelamoraleetdelareligion, Paris: PUF, 2008, p. 27. 。
那么,博爱是如何可能的?只能是通过某些道德、宗教上的英雄人物的创造。这些英雄人物(如耶稣、佛陀、孔子)通过他们的行动和人格展示,不仅影响人们的理智,而且打动人们的情感,使得人们对他们的崇高人格产生向往,这才是使封闭社会被超越并且使人们有可能进入开放社会的唯一可能。柏格森尤其通过对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之研究,证明宗教亦有两种含义:一是静止的、封闭的,体现为固定的教会组织、仪式、戒律等,此即静态宗教;二是动态的、开放的、精神性的,体现在神秘主义者的修行和伟大宗教家的人格之中,此即动态宗教。因此,柏格森揭示出:一,某些英雄人物和神秘主义者,通过其言行、实践、人格,体现出某种极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乃是生命冲力的创造成果,而且此种境界不是通过理智的手段或后天的积累而获得,而只能是出自某些天才人物的创造,即通过其一生之行动和努力所实现之创造;二,在封闭社会之上,还有一种更广阔、更高超之开放社会,后者是精神性的,有赖于上述天才人物的创造,通过其精神境界而获得开启和显现。
四是人大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监督作用,各省都建立了省政府向人大汇报环境保护工作的机制,既包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汇报,也包括政府向地方人大常委会专门汇报,但是形式重于实质,少有问责的现象,如对于专门汇报方面,大多数情况是,政府的代表先在常委会全会上汇报,然后由人大常委会分组讨论,提出意见,但是并不付诸于全会表决,监督作用有限;人大的监督在人大的信息公开方面不全面不系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市县层面,一些领导人的认识不到位,仍然有一些政府没有建立向地方人大常委会专门汇报环境保护工作的机制。这和《环境保护法》修改时规定不具体有关。
四、结 语
正如前文所揭示的,借助中国哲学中的境界论,可以获得一种考察西方哲学的新视角,并且对西方哲学做一种全新的梳理。在古代哲学时期,晚期希腊哲学进行了伦理学转向,并且发展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工夫论与境界论——尽管其境界论往往是用一种神话的方式或者神秘主义的方式来表述的。在中世纪时期,如果说斯多亚派的工夫论,被整合到基督教的教义之中,转化为基督徒的伦理规范的一部分,那么希腊化时期关于境界论的思考,则完全被否弃了,因为在神学的背景下,这一部分内容不但是无意义的,而且是不合法的,是对神的亵渎。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哲学,以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而理性主义的内在要求,则是人的发展应实现为某种理想人格。但是,早期近代哲学中只有斯宾诺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在他的《伦理学》中发展出了一套境界论。而在柏格森、尼采等人那里,则通过“动态宗教”“超人”等概念,提供出一种值得人们追求的人生境界。在20世纪末的西方哲学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伦理学转向,即以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对“自身技术”的提倡,其可以被视为某种关于自身的“工夫论”。但是,正如本文所试图指出的,无境界的工夫论,是一种盲目的工夫论,只有在一定的理想人格的引导下,在确定的价值意识的引导下的工夫论,才是真正的工夫论。就此而言,从境界论视角出发,补充关于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的思考,也许可以让福柯所说的“自身技术”理论得到更为完备的发展。如果进入更广泛的跨文化比较哲学领域,中国哲学所提供的境界论哲学的视角以及相关的丰富理论资源,也许可以为中西方哲学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我国在原材料、合金成分、半成品加工材料、铸造产品、材料组织结构、相关试验方法和废料回收等方面制定了国家钛合金材料标准,基本满足了航空业钛材料及相关需求。[7]这些标准的建立、制定与实施,为中国航空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一,农村集体在机体构成上具有非自然性。农村集体是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人,是集体范围内成员个人结合的整体[9]。农村集体是一种社会存在,不能像自然人一样形成意思,必须依赖于作为集体财产管理者的自然人。由于利益函数的现实差异,实际控制人极可能侵害集体利益。正如耶林所说,“团体财产的管理者对于一个社会最是危险。没有哪一个窃贼会像管理他人财产的管理者那样发现偷盗是如此容易”[10]。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9)05-002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生命哲学的新进展”(14ZDB018)
作者简介:邓刚,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上海 200240)。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9.05.004
责任编校:余 沉
标签:境界论文; 哲学论文; 人格论文; 工夫论文; 理想论文; 宗教论文; 世界哲学论文;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生命哲学的新进展”(14ZDB018)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