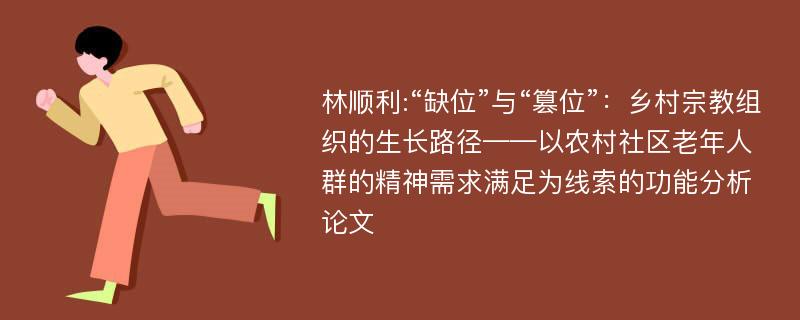
摘要:现代性与传统性这两股历史潮流的交叉相撞定格于当代的乡土社会场域中,它们之间的分与合打破了传统组织与乡村老人之间“精神需求”与“满足”的关系链,衍生出多元化的乡土问题。基于此,本文以X福音村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需求为线索,透过村庄生活的嬗变记忆,探寻宗教势力嵌入农村老人的意义体系之中,且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力量显现在乡村内部权力格局之中的生长路径与实践逻辑。重点从“基督下乡”的实践逻辑看出农村老年人养老生活的组织化需求,以期对农村社区功能完善和后乡土中国组织建设等意义性话题给出现实性的回应,实现乡村自治力量与基层正式权威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乡村宗教组织;生长路径;结构功能;“缺位”与“篡位”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快速转型的特征,社会结构的“解构-重组”力量使得处于社会宏观结构之下的个体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乡村生活中熟悉的集体组织系统(如公社和生产队)已经瓦解,社区与个体层面的邻里记忆面临销蚀殆尽的趋势,而一些宗教组织则在这种背景下迅速获取了生长的机遇,替代旧有的社区组织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个体需求满足的新型场域。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调查结果,我国基督徒在2006年与2010年的两次追踪调查中分别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1.7%与2%,且总体规模分别推算为2230万与2680万,4年间数量增加了450万人,平均每年基督徒增长人数已超过100万人。[1]年龄特征上,老年信徒比重增加,60岁以上信徒的比重已由11.4%上升至27.2%。[2]“老年基督热”现象在农村则更为显著,2010年中国基督教网站的官网数据表明,全国超过2000万的基督徒(不包括15岁以下的人)中,有70%为农村信徒,而近 1400多万的农村信徒中,60岁以上的老年信徒占比则超过了50%。[3]农村老年人加入宗教组织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在引入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的基础上,从农村养老的精神需求满足的功能选择出发来考察一个基督教福音村基层社会组织的演变史,力图从国家——社会在组织力量上的此消彼长的角度来厘清农村宗教组织生长的路径和动力机制。
二、现有的研究路径
(一)国外宗教社会学的功能主义范式
早期的结构功能理论遵循着“在承认社会存在整合需求的前提下,分析系统组成部分”的理论预设。在此框架下,孔德(Auguste Comte)指出,对于生物有机体的分析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有机体,依据生物有机体的划分标准,社会有机体可被分解为家庭、社区、城市等层次,它们作为社会总体的器官维系其生长运作。”[4]在其后对宗教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分析中,后继者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探究重心则转向了“整合”的主题,在他看来,社会的巨大力量与平衡的维系是通过集体意识来表现的。[5]那么,对应到对宗教的功能分析之中,涂尔干认为宗教的本来面目就是一股被披上了神圣面纱的实体性团体力量,它的团体特征与集体化表象实质上对于人类个体而言是具有依赖性的支撑意义的,若扩展到社会层面上则是发挥着维系社会,使之一体化的整合作用的。[6]总体而言,早期的理论家们多持有一种传统与现代两分式的社会观,并普遍性地假设与强调宗教在维持和保障传统社会的集体秩序中承担着关键角色。
伴随着宗教新变化的出现,学界的关注焦点开始转向于宗教的世俗化方向,并由此开始新一轮理论构建的尝试。贝拉(Robert N.Bellah)的宗教功能论和卢曼(Niklas.Luhmann)的系统功能论最富典型性。贝拉结合韦伯与帕森斯的理论框架对宗教的功能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宗教的两大社会功能:提供终极价值的模式维系功能与缓解挫折打击的紧张处理功能;[7]卢曼是站在前人关于“系统”的论述基础上认为社会面临着分割、分层与功能分化的三层次的变化现实,在此现实之中,社会才得以不断进化。那么,在此社会体系之中,“功能发挥”便被解释为社会分支在整体社会之中的交互配合;可将这一看法放到对宗教功能判定的分析上,他的论断则是“中庸”式的,一方面他否定了传统宗教观中对宗教具有整合性功能的片面观点,他认为到了分化严重的现代性社会,宗教仅仅是此系统之一,其传播与运行不足以穿越系统界限去支配整个社会体系。在现代社会语境里,宗教的重点活动范围仅能存在于社会子系统领地中,且必须要在遵循其他系统原则要求的前提下才可进行,这与传统的宗教色彩自然是相悖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在功能分化社会里,宗教虽然失去了整合整体社会的功能地位,可这也正是宗教系统发展出一个不受系统其他分支约束的,适用于碎片化社会的新简约工具的机遇。[8]
(二)国内宗教的功能主义研究
在涉及到农村权力体系与宗教关系的探讨上,学者陈占江曾在皖北的田野调查中探析过农村基督教在乡村结构体系中迅速发展的实践逻辑和内在原因。他发现基督教作为一种外域宗教却在农村社会之中得到了迅猛扩张,其实践成功点在于基督教本土化的传播策略具备着植入农民生活系统并与其进行深层次互动的功能性优势,且借以社会转型的契机得以取得加速生长的温床。[9]而黄剑波则认为,基督教作为镶嵌于村庄体系中的一支,其生长经历实质上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因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压力而不得不作出的另一种心灵选择,在他看来,是乡村基层政治与乡村个体对话的断裂“催熟”了宗教等文化现象。[10]
吴理财与张良在《农民的精神信仰:缺失抑或转化?——对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反思》中表示导致现代社会中出现“农村基督热”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转型期农民传统信仰体系的崩塌,而基督教则作为新功能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农民的精神依靠空白。此外,他们在指出这一事实后,又强调了基督教文化在乡村地域的反作用,即基督教的深入传播亦会反作用于农民的主观世界、客观生活方式以及农村原有的权力文化体系,甚至对乡村组织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11];李华伟在涉及到宗教对豫西李村宗族的影响议题上也引入了默顿的“功能替代”理论。在他看来,社会变革的“阵痛”与种种矛盾,导致地方社会中存在着精神失序与制度混乱的场面,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个体往往无法坚守原有的生活框架,极易陷入焦虑的状态,而对稳定性的追求本能又使得民众对于社会体制与信仰准则表现出一种捍卫的惯性,出于这种惯性动机,人们才急于寻找新的意义系统。[12]
三、理论关照
本文重要的分析框架是基于功能主义范式中的多维功能论与功能替代论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功能替代论”的初提者——默顿在批判继承前辈们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认为,系统中的某一结构组成部分可同时承担着多种不同功能,而相同的功能也可由系统中具有相似结构的不同子系统所实现。若将功能替代论置于社会发展的实景中分析,即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原有社会系统的均衡秩序被打破,极可能导致部分子系统分支中制度供给与需求满足的链接中断,进而便会推动着其他子系统“上位”发挥其代偿作用,以维持社会系统整体与部分的相对均衡。[13]他的这一概念事实上是对早期功能主义的“功能不可或缺性”的颠覆与批判。默顿所强调的核心在于社会系统中功能选择的可能性,就某一子系统而言,如果它的某个功能项目存在着具有同等功效的功能项目,这就意味着,在某一体系的维系与运行中,功能项目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存在着被他者替代更换的可能的。那么,关注到“乡村基督热潮”的事件上,同样具有相似的机理。也就是说不同情境与时代下,宗教作为乡村场域中的一支,同样具备着替代其他分支的可能性,在国家力量渗透地方的强弱变化历程中,基层组织难免具有某些层面上的有限性与不完善性,诸如在现有组织无法满足老人组织上的精神需求这件事上,宗教势力就可被视为基层组织的一个“备选项”则随时准备伺机而动。
四、基层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老年人群体精神需求满足方面的功能发挥的历史考察
(一)X福音村的概况
本文要集中研究的个案是X福音村,该村位于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北部,属于典型的华北平原农村。该村隶属于S乡,距乡镇中心约6.7公里,距县城约18公里,村子四周仅有两条柏油路与外界相连,交通较为不便。现有380户人家,全村人口共计1085人,拥有耕地4000多亩,人均耕地2.5亩左右。当前村中常住人口多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主,年轻一代多选择外出上学、务工。故此,该村耕地多荒废或转租他人。且因青年人口外迁现象严重,该村出现了“空心化”趋势。
村庄的变化史往往是纷繁的事件交织在一起的历史,透过个体的语言表述传递给我们一种历史嬗变的直观性。那么,我们姑且沿着村庄的历史记忆出发,透过村庄体内的组织形式、生产生活的重塑历程。去实际性的触摸一个村庄组织的演变。
(二)乡村生活格局的“组织化”过程及其养老功能的发挥
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来看,乡村治理过程是国家与社会力量此消彼长的一部互构史。在二者的力量互动中,村民的组织性记忆在各个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片段,村庄组织格局的形塑也直接导致了老人不同时期养老需求发生着相应的变化。由此,我们可在分析不同时期国家权力渗透的基础上,梳理出不同时期村庄组织格局与老人精神需求满足的演变逻辑。
图5(a)中实线是基于Delaunay三角网的线面混合数据中轴线提取结果,虚线是本文提出算法的中轴线提取结果。重点放大线面连接处,从(b)图中可以看出,对于混合数据Delaunay三角网仅能提取面状要素中轴,无法保留原有的单线数据,该中轴线与原有线状数据未建立拓扑关系。图5(c)中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形态学的细化方法则能很好的避免以上问题。
1.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4 年)
近代的地方自治就始终遵循着 “官主民辅、中央与地方联动”的政策主线。[14]因此,建国初期的村庄组织格局是村政府和农民协会替代地主与村落长老的场面。回顾到近代时期,该村的权威体系是国家权力与乡村自治力量良性互动的场面,国家政权对乡村社区的治理是依托农村内生的民间自治力量展开的,即传统乡绅与村落长老等角色权威占据了当时村庄治理体系的至高点。在乡绅、长老等自治力量覆盖下,该村衍生出道德、习俗、家族家规等人造秩序约束乡民个体的行为。村落长老在调解纠纷、平息事端、维系村落秩序等方面弥补着国家对地方控制能力层面的不足。事实上,这一时期属于国家权力低度干预下的乡村自治。
1.主日敬拜
教师不但要在教学实践中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监管和引导,同时在发布各个任务之前,应该设定对应任务规划目标。在任务设计完成以后,需要开展项目分析及课程结构分析等工作。探究教学提纲以及课程框架,获取各个知识模板教学框架。同时,将各个项目任务划分为多个模块,同时各个模块均要结合对应知识点将其划分成多个部分教学内容。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要求和内容实现对应教学任务的设计,将各个学习知识隐藏在各个任务中,让学生在落实各个任务时实现知识点的科学应用,提升学习能力[4]。此外,结合项目开发模板及各个学生学习特性进行小组分配,同时下发对应的学习任务,给实施环节做好准备。
“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 《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其中规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行政村与乡作为一级地方政权机关,并依法设立村级政府和相关组织机构。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该县依据文件指示,在该村及周边村庄均设立了村政府和行政村,逐步形成了“基层党组织+村政府+农民协会”的新基层结构。
在这种国家权力逐步渗透的组织格局下,村庄的公共土地与财产被没收,村庄老人所需的社会保障物资由农协会统一再分配,原先处于边缘群体的贫雇农成为了村庄组织的骨干。那么,旧式的带有温情面纱的宗族关系与封建租佃关系被国家力量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了,老人们进入到新政权与基层力量的事无巨细的组织管理体系中,其精神世界也被阶级斗争与农村运动所占据。
定级单元划分需要遵循主导因素差异原则和相似性原则,主要方法有重置法、地块法、网格法和多边形法[12]。本次金安区采用地块法来划定定级单元。土地利用现状图以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为基准,综合金安区多年耕地等别更新数据,以确定获取最新的耕地分布图。本次金安区定级单元共计39858个。
2.合作化时期(1954~1958 年)
土改完成后,村庄组织格局进一步改变深化,走上了农业合作化的集体化道路。在这短短的过渡时期里,农村老人亲身感受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不同组织化阶段。初期的互助组仅是根据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将其集中起来进行生产互助;而发展到初级社阶段,土地已经可作为个人股份参与到合作社经营之中并进行收入分配;转至最终的高级社阶段,已经形成了土地归集体所有,社员“集体劳作,按劳分配”的原则组织生产。有村庄老人对该时期回忆:“
“到了这个时候,高级社就包圆了村里的一切,劳动生产、村庄管理、老人保障都靠它,我们没有私人财产,平日的生活都依赖于高级社,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入了大家都熟悉的那种集体劳动,挣公分的生活。”
梁、王两人寻碑、拓碑事俱见《嘉泰会稽志》卷十六《碑刻·秦颂德碑》。也可以参考绍兴丛书第一辑(地方志丛编①)〔M〕,北京:中华书局,2006,307。
那么,到了这一时期,在村庄组织内部中,老人的身份再一次发生了转变,由多等级转为了有组织接收的社员,掩盖了农民的不平等与差异。其次,农民的生产生活终于由分散的个体集中于高级社之中,统一生产劳作。这看似是国家权力的触角由乡镇向村庄的进一步延伸,但就老人的情感层面上而言,是老人组织性依赖的进一步强化,他们在集体劳作与合作社管理的新基层组织下,对村庄组织共同体产生了更深层次的依赖感。
3.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1 年)
而1958~1981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则是村民组织性意识最强的时期,X福音村的组织制度以人民公社制为核心架构形成了全能型的组织格局。从纵向的组织结构分析,该地域的人民公社体制是由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结构搭建的,该时期的组织政策表明:一级行政村之内应设立相应的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作为公社制的下级组织可统一管理临近4~5个村庄的事务,生产大队的权力继续向下渗透,则有了周边自然村的生产队或生产组,生产队、生产组作为生产大队的下属组织交由后者管理。分批领导村民的日常生活与劳作。
该村的经济生产也是嵌入在公有制的权力体系之中的。村民的日常劳作遵循着“统一劳作、按工分分配”的生产劳动政策,在此劳动体系中,民众也享受了一段时期集体经济带来的稳定。如笔者依据一位村民的回忆所整理的该村生产队翻种时节的上工时间表见表1。
宗教自身独有的活动仪式与教义是宗教体系表达超现实价值的一种凭借,也是将宗教有形化的重要工具是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表达宗教信仰的一套符号体系。[17]诚然,透过一整套的信仰仪式,人们往往才能加深与超越的神性之间的联系,将生存世界与想象世界混合起来,以求得心灵的安宁。那么,对于X福音村的老年基督徒而言,主日崇拜、聚会点活动、查经班、祷告会、个人灵修等信仰活动作为“走近主”,引发情绪,维持其心灵平静的重要工具是值得我们观察靠近的。
表1 ×福音村翻地时节上工时间表
事项 时间上午 上午敲钟上工 6:00-7:00田里集合清点人数 7:00-7:30组织翻地 7:30-10:30收工领饭回家 10:30-11:00下午 下午敲钟上工 2:00-2:30田里集合清点人数 2:30-3:00组织集体拉粪 3:00-4:30完工总结 4:30-4:40收工领饭回家 4:40--5:00
五、“正式组织”的削弱与老年人的“组织剥离”
(一)组织格局的嬗变
1981年后的后乡土社会时期,村庄组织结构经历了极大的重组,乡土社会由威权制的集体社会逐渐转型成了强社会——弱国家场面的现代性村落,弥散化、弱控制是其当下的面目特征。一方面就权力组织而言,自1981人民公社制在该村真正解体以后,村庄的权威组织便改头换面为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即原来的乡公社转变为乡镇政府,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人民政府,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责时,需向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而曾经的生产队则转变成“村民委员会”,它作为农村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接受村中党支部的领导。在此原则的贯彻下,重组的基层权力组织出现了集体权威的退场与流于形式的治理问题。从国家政策对村庄和农民个体发展的层面上看,个体依附于组织的惯性被个体与个体的互动所打断,私人意识开始在乡村领域萌发,即农村组织格局由“国家号召、村庄组织、村民参与”的发展路径转向了“国家主导和个体努力”的道路,基层组织力量和村庄的功能在这样的道路转换中便自然而然地被弱化了。
另一方面,组织控制的弱化同样影响到生产生活之中,曾经的 “上工制”与集体性经济也在1981年后重新改写了,该村在1981年才实际废除公社制,实行土地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再遵循集体劳作的方式,而是由各户自主经营。不再统一分配农业产品,自产自处理。由此,内生性的集体经济被打破,外向性的市场经济主导着村庄经济体系的发展趋势。农民的生计要素开始全面商品化,土地种植作物不再以粮食作物为主,而是迎来了高收益的经济作物的种植浪潮(见表2)。事实说明,集体化的组织消解了,农民在职业农民的新经济身份中将热情转向了获取利润的经济生产中。因此,后乡土社会里由权力组织凝聚起来的集体性生产生活也同样得到了消解。
实验组、对照组体检采血人员均有皮下血肿情况,详细血肿形成率结果见表1。经统计学计算,实验组体检采血人员皮下血肿形成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表2 X福音村的土地种植结构变化
种类 1958~1981年(烟叶时期) 1981~2017年(后烟叶时期)小麦 主粮食作物,基本覆盖全村三分之二的土地,一般亩产100斤左右主粮食作物,亩产提高,可达到一亩1500多斤,但种植面积已缩小到总土地面积的二分之一左右红薯 主粮食作物,亩产一般150-200斤 亩产虽提高,但已非主粮食作物,仅满足饮食需求,小面积种植烟叶 主要经济作物,覆盖全村三分之二的土地 非主要经济作物,基本上已无人种植花生 仅有村民自留地中小面积种植 为主要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且引进新式化肥、种植技术改进,亩产提高药材 无人种植 为主要经济作物,且2010年全村引发了种药热潮草莓 无人种植 为主要经济作物,至2017年,种植面积占比约二分之一,且引进塑料大棚,科学种植
(二)老年人的边缘化
帕森斯在其社会系统论中将秩序、行动和共同价值体系扮演的关键性角色视为分析社会结构的突破口。他认为,社会结构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秩序的问题,且必然涉及秩序中的人的行为问题。[15]而从建国初期时期至人民公社时期之后的村庄秩序已经位于组织原子化的解构——重组情境之中,国家力量对乡村秩序的影响日趋式微,而彼时内生乡村秩序所凭借的组织力量也正处于弱化阶段。[16]那么,这种现代性的冲击在导致乡村系统结构混乱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体所依赖的意义世界坍塌,这其中首受其害的便是曾切身体验过从大集体时代到碎片化生活深刻分化进程的农村老年人,其赖以依靠的信仰价值体系失去了团体价值的支撑,更易引发心灵秩序的危机。
诚然,农村老人精神层面的无所适从是由乡村公共空间的断裂所导致的。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旧式公共空间的瓦解的更加彻底,但新的乡村公共服务体制与秩序并未完整的建立起来,有位88岁的老年基督徒感叹:
“90年以前,村里还是公社集体经济,各家日子不好过,但是每个月大队上放的有电影,有红色文化服务站,有广播,有村民大会。那时候,每个生产小队都有自己固定的开会地点,小队不光管队里的生产,还包圆各家各户的婚嫁、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啥都要问,俺们也乐意交给大队。可现在世道变了,村里公社砍了,只有个村委会,不碰见村里修路、停电啥大事不开门。村里的会不开了,电影也不放了,各家各户都关起门各过各的。现在俺们闲了就呆家看看电视,不是过节,也没人来串门,后个就常跟人上教堂,听圣经,对俺这没文化的老头老太,那是个好去处。”
转型期农村社会的标签便是断裂式、碎片化,这也是诸多社会问题的分院所在。历史经验早已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熟不仅是个体的生活安全阀,更是国家与个体矛盾的调节器。而现今,集体对个体的关照性依托早已失灵,老人们的生活情景已不再是依赖集体秩序维系的场面了。那么,他们在失去了集体组织这根主轴的现实下,自然急于寻找一个新的身份,重建自己的意义系统,以取得归属感,实现生命晚期阶段的生存意义。作为具有社会性的高级动物而言,人类个体尤其在步入生命历程晚期阶段更易引发对集体性生活的依赖与集体归属感的获取。因此,我们若从群体性的层面上思考,则农村老人急需的不仅是异质乡村生活里的自我实现感,同时还缺少了一条群体性生活模式的出路。没有了集体,则没有了归处,组织性的精神需求没有了“供给处”,那么,最终的后果便是,他们出于对生命处境的困惑,而选择“走到了神的面前来”。
六、养老需求“组织化”满足的“替代选择”与宗教组织的“篡位”
(一)村庄基督教的生长史
该村历史悠久,信仰文化积淀深沉,据村志记载,1941年前,该村村民多以信奉祖先神为主,无西教信仰者,1941年外县基督教传教士刘景全来到X福音村讲道布经,并在周围村庄组织建设起几处临时聚会点,由此,基督教由传道士引入该村场域之中,但该时期投身于基督教的本村信徒仅有60余人,总体上占少数。而转至1958年—1981年间的公社制时期,该村乃至全县的教会均停止活动,基督徒的宗教活动转为“地下状态”,信仰人群迫于政治批斗的压力而在急速减少。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逐步贯彻实施了 “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该村的基督教才得以设立了2-3个聚会点,逐渐的恢复了信仰活动,并于1983年在本村筹建了教堂,此后该村基督徒队伍逐渐扩大,发展成为今天拥有680多名基督徒的福音村。①
1.信徒齐来颂赞,哈利路亚,阿门!
就信仰规模而言,X福音村的基督徒发展到今日也已经壮大为680多人。从社会学特征上分析,X福音村的基督徒多数属于村庄的边缘群体,即以老年人群、女性人群为信仰主力。在年龄层面上,该村的689位基督徒中,60岁以上的信徒约为460位,占比已超过该村信徒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性别维度上看,则女性基督徒总数为448人,远超过信徒总数的二分之一。②乡村基督教受老人与妇女等边缘性群体青睐已是事实,而若以村民信教的起始时间为切入点考量,则该村信徒开始信仰基督教的时间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么,我们不难看出,X福音村教会的出现,乃至占领阵地与村庄的组织嬗变时间及老人心灵依靠的变化是具有一定的时间契合性的。
(二)宗教锲入下的村庄信仰生活
在公社制时期的村庄场域中,国家权力已经屏蔽了村庄自治力量与宗法制度而渗透于村庄日常生活意义系统之中。因此,我们可以用“全能主义”来概括这一阶段国家权威在乡村地区全面渗透的格局。在人民公社化的制度设计下,该村公有化、集体性极强的生产队成为了村庄组织力量的核心,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功能于一体,农民个体的信仰体系也被政党意识、集体意识所重构,从而形成了强集体——弱个人的组织格局。事实上,集体化的意识与模式已经贯彻于日常劳作与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村民作为公社体制中的一员,也逐渐形成了依靠集体生活的惯性认知。
而建国后,村级组织层面上则相应设立起了村政府与农民协会。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已经在华北地区尝试着进行基层政权的建设,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保甲制,建立村级政府,定期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在土改未完成地区则由乡农民代表大会或乡农民代表会议代行乡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除此之外,农民协会同样是组织力量中的重要一支。农协会成员多为贫下中农中的 “土改积极分子”,在土改时期被吸收后参与到村庄管理的任务当中去。由此,逐步将国家治理权力渗透到农村地域。该村的村志记载:
官962-17断块低承压地层井段沙河街组生物灰岩、玄武岩裂缝及孔洞十分发育,连通性好,漏失主要还是以裂缝性和溶洞性漏失为主。
主日敬拜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信仰活动之一,通常被该村的村民称之为“守礼拜”,其内容包括圣经解读、教唱赞美诗、捐献“奉献金”及做见证等。西方宗教传统规定主日敬拜的时间为每周日上午,主要由固定的讲道者与信徒工作者在教堂主持举行。这里有相关的本村教堂礼拜日活动时间表可供参考见表3。
表3 X福音村教会礼拜日敬拜活动时间表
事项 时间祷告唱诗 7:30~8:30教唱赞美诗 8:30~9:00听道 9:00~10:00讲道者带领集体祷告 10:00~10:20个人默祷 10:20~10:40作见证 10:40~11:00(可延迟)散礼拜 11:00会计核算 11:00~11:30
一般情况下,众信徒由讲道者带领祷告时,敬拜活动就已进入尾声。祷告完毕,若是某位基督教信徒家中有孩子考上大学、生孩子等喜事,便可认为是主赐福于他(她),应当这一天请讲道者为其做见证并召开小型的见证会,以宣扬基督耶稣的仁爱。
2.灯下聚会
在信徒家中举行且由内部信徒参加的定期聚会活动被称为灯下聚会。灯下聚会的性质同参加教堂活动与“守礼拜”的性质差异很小。事实上,在基督教最初传入本村时,教会的初级形式便是聚会点,随后在国家力量对宗教势力的政策变化中,聚会点也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早在人民公社时期,灯下聚会活动被严令禁止,直至改革开放后,村中的教会才逐渐从零散的家庭聚会点逐渐扩张成为有公共空间与设施依托的制度性教堂。
对X福音村而言,其村中的聚会点设置不得超过5个,聚会点的选择遵循轮流制,每个聚会点的活动与反馈均关系到村庄教会的兴衰成败。灯下聚会的时间不与主日时间相冲突,一般会选择在周二、周五下午。且由于该村老年基督徒为信仰主力,故聚会时间多定于下午两点之后开始。灯下聚会的仪式过程同礼拜日的主日敬拜流程大同小异。首先信徒们进行个人祷告,然后齐唱唱赞美诗,笔者曾参与到一场家庭聚会之中,发现该村基督徒家庭聚会的开场常以一首《信徒齐来颂赞》为开场诗歌,大家往往要重复的唱两遍以上。
原来这次大会规定凡是提交抗议书的要付二十美元的手续费。女教练还坚持要重放现场摄制的电视录像,以证明时间并没有短缺。
袁安、李离、上官星雨等三人早早起来,梳洗后,即踏着朝霞,在关关鸟啼中,来到仙迹岩一一拜访诸圣的码头。苏雨鸾在二十余级石阶之上的琴台抚琴相候,命三人由她春秋冬三季的琴曲里辨别物候,她又命袁安由《阳春白雪》、李离由《听松》、上官星雨由《平湖秋月》里,分别依律自创一段剑法,三位小友左劈右砍,一文一武,宫商角徵羽,也算有模有样,雨鸾还特别赞许李离,说他的听松剑里,有隐隐龙吟,不妨具体而微,更进一步。
《信徒齐来颂赞》
X福音村的固定聚会点为该村村东的基督教堂,其始建于1983年,在1981年前的人民公社制时期,村庄格局仍遵循集体化生活趋势,“一切听党指挥”号召使村民不去想也不能想投靠宗教,按村中老人的话:“信教就是跟党作对,要斗你!”而1981年公社改组后,村庄生活格局重塑,脱离集体的个体面临着意义世界的失序,信仰自由的政策更推波助澜的导致了农村的 “宗教热”。由此,X福音村教堂的修建才有了眉目,故此,该村教堂于1983年创建,历经两次翻修,至今已有30多年历史,是该村及周边3个村庄基督教徒聚集的主要场所。
每年,媒体都会曝光大量的关于火锅食品安全问题,比如“火锅增香剂”“火锅红”“辣椒精”等不明添加物,对于食用的牛羊肉等原料,鸭血、黄喉、毛肚、鹅肠、笋片等涮品被相继曝出存在巨大安全隐患,也被曝光出现以次充好等问题,这不禁让爱吃火锅的人担心:火锅还能放心食用吗?
赞美我主基督,哈利路亚,阿门!
万众一心颂扬,在主座前欢唱;
主必喜悦赞赏,哈利路亚,阿门!
芒沙是一个极具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文化的村寨。除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还有富饶的物产和独特的气候,因为该地的气候和地形,给当地作物生长提供了天然的养分,不仅让村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还对自然环境加以改造利用,是村里的水电等的基础设施更好的为村民服务。
2.来齐心高声唱,哈利路亚,阿门!
赞美声达穹苍,哈利路亚,阿门!
他是牧民、良朋,为我众他屈尊;
慈爱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
(1) 持压稳压阀。从5#、4#分水口分水管道末端300 s同时或依次关闭的最小水力包络线图7中可以看出,管道沿线驼峰处的水力坡降线距驼峰高点处的内水压力不大,各支管及主管道末端流量如不加控制,造成总体输水流量过大时,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压降,造成驼峰高点处出现负压,还会出现部分支管由于供水压力过低,造成引水困难,产生半管流或明满流交替的问题,影响整个管道系统的安全,因此考虑在主管道末端要设置持压稳压阀,以保证整个管路系统的水压力。
接着,聚会点里的长老,即有威望的老年基督徒开始讲某一段圣经的片段规劝信徒们应按时祷告,认真听道,抛去私欲,荣神益人。同时,讲道者在解读圣经的过程中,其重点多聚焦于“人本有罪,要向上帝忏悔与交托,才能得到上帝的庇护”这一重点之上。在聚会的最后,高潮部分则是集体祷告。一般由讲道者带领群祷。他们认为祷告是与上帝沟通的有效方式,祷告文如下:
“主啊,求你饶恕我们这群小婴孩儿犯下的罪,洁净干净我们的灵魂”。往下则是感恩季度耶稣的恩典与赐福,在此则具体涉及到了聚会点的各位信徒,对于家中遭受灾害或有困难的信徒,带祷者会逐一列举出来,以求主帮助其渡过灾难。最后,祷告式常以主祷文结束。
3.节日庆祝仪式
圣诞节又称耶诞节,译名为“基督弥撒”,定于每年的12月25日,主要把它视为基督耶稣的诞辰来庆祝。这一天里为了祝贺神的诞生,西方基督教徒们会举行唱诗、敲钟、游行聚会等活动。那么自然而然的,X福音村中的信教老人们在圣诞节也有相应的活动。他们所组织的圣诞节活动从平安夜开始,平安夜作为一次比较特殊的聚会,有着特殊的活动流程,诸如教会长老讲道、唱诗班献唱、信徒聚餐等环节。其繁杂的筹备活动往往于半个月前便着手筹备,主要负责人包括教堂负责人员和多数的自愿信徒。圣诞节最主要的活动还是在圣诞节当天。村中教堂会在晚上举办圣诞节聚会,他们会挑选教徒组成唱诗班,在聚会中歌唱赞美耶稣基督,在赞美诗集的目录上,笔者发现关于节日,尤其圣诞节的歌曲,不在少数。
《圣夜静歌》
明星灿烂,天地宁;
天使显现,牧人惊;
救主耶稣今降生;
水寂山眠,万籁无声,卿云缭绕拥着伯利恒,
金琴玉筝,漫天歌韵,哈利路亚!山歌欲齐鸣,博爱、牺牲、公义、和平,圣容赫华犹如日初升!(阿门)
这种以丰富的宗教活动和公益性的助人活动所链接起来的认同技术具有嵌入性的莫大优势。我们以上提及过乡村老人在个体层面上面临的是自我怀疑、意义缺失的心灵困境,而基督教的传播策略似乎可以实现老人将失序的痛苦置于宗教这个合情合理的框架之中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因此,在与乡村组织力量进行养老博弈的对抗中,基督教首先具备着满足老人个体层面需求的替代性优势。
(三)基督教在“精神养老博弈”中的功能优势
1.组织嬗变下老人的真实心灵需求
(1)自我实现的追求
一切信仰的出现归根究底都是为了人所服务的,只有个体意义系统出现了豁口,外在的种种力量才能拥有发育窜长的契机。那么,在这个社会分化、组织分割的现代化社会中,体制的转型在个体的中心意义脉络即私人领域上无疑是切上了狠狠的一刀。尤其对于老人而言,这一刀极有可能“毙命”。他们所赖以为生的集体早已逝去,视之为天的村庄传统权威也已退场。原子化、碎片化的村庄体系与全能性组织的退场引致的是“银发群体”的自我封闭、自我怀疑。
(2)群体归属感的需求
有鉴于此,笔者们认为,当农村的权威结构在社会变迁的洪流中被不断消解时,村庄公共空间与农村老人精神需求供给的关系链中也出现了断裂。村庄老人已经习惯了从集体经济时期的集体生活,深深尝悟人生趣味,所以,一旦外在生存环境由集体转变到个体层面,支撑其精神满足的组织面临着坍塌状况,老年人就很容易陷入那种精神空白、可怕的无政府状态。
2.“十字教”与老人心灵所需的互嵌
(1)基督教教义对话老人的个体性需求
据悉,该村的基督教宣扬的是“信神者,得永生,爱人者,得福音”的教义。从基督教回归到乡村社群的生长现状而言:一方面,它所创造的公共空间改变了老年人的人际关系与交往范围,将原本可能毫不相干的个体联系在一起,以唱诗班、感恩会、神学培训班等形式丰富着老年个体的生活,以达到自我实现的精神满足。诸如我们所探讨的镜像场域——X福音村,它的教会组织所组织的活动涵盖了主日敬拜,青年班、老年班、赞美会、奋兴会等,此类丰富的信仰活动把日常生活置于了永恒实体的笼罩之中,不仅可以使人精神充沛,而且使人获得最深厚的充实感。
而另一方面,基督教“爱人如爱己”的信仰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助人的功能。田野调查中发现,村中的基督徒平日里会自行组织传福音,看教友的互助活动。他们自发的到周围的村庄讲道布经,此类活动多是公益性的,传福音的过程,是一段自我满足的过程,助人成了常态,至善的力量使他们获取了自我实现的充实感。
除此之外,聚会开始前由各家提供相应的食物,信仰基督教的老人们围聚在一起祷告庆祝耶稣的复活,然后可共同享受聚会晚餐。与此同时,对于前来的村里的孩童,教会还提前准备了糖果等礼物分发给他们,预示着接纳新的希望。
(2)“团契生活”会遇老人的群性体需求
前面我们提及过,村庄嬗变中,由群体记忆所承载的集体性组织已经变了模样,个体在新的乡村组织体系中对群体归属感的需求同样值得注意。如今的乡村场域充斥着社会缺席,归属何在的需求拷问,而基督教因其存在的“团契性”社会形式得以形成新的群体认同,减少老人们失序的痛苦。我们在考察中看到,基督教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民间信仰,其关键在于他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宗教”,呈现出一种社会系统的“社会性”。信徒们往往形成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使他们对我群——基督群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如一位讲道者常以这样一段话规训信徒:“兄弟姊妹们,是神的旨意,让我们来到了主的面前,我们都是主的孩子,无论是做了功,还是犯了罪,都要跪到主的面前,乞求见证或饶恕。是主,让我们聚合在这里,为的是洁净我们的灵魂,完成主的使命,一同得永生。所以,从今往后,我们要悔改,自我反省,真心实意的投靠主,把教会视为天国的门,进了这道门,我们就要相亲相爱,荣神益人,与主,与兄弟姊妹们同在,等候主的恩典!”
我们暂且不提基督教教义的唯心主义缺陷,但在信教的团契生活中,听道、讲道的宗教文化互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稳定村庄老人的心灵世界。基督教的信仰共同体,通过讲道、祷告、聚会等一系列群体互动行为强化了信徒们的群体记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看似正规、合理的群体框架,满足了老年个体在群体层面上所需的归属感。他们认定了自己是“神的众多孩子之一”,通过新的身份的构建,老人们自动划分了身份边界,提高了认知安全感,甚至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找到了归处与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国家政治力量对农村意识形态弱控制的中国语境下,农村老人在群体性层面上表现出了对整合性组织的强烈需求。而基督教在进入老人日常生活时,恰巧使其身份在晚年社会生活中的表达方式由个体再次转向了群体。那么最终,它的这一套信仰价值体系自然被老人所青睐,使得乡村老人在个体与群体两层面上的心灵所需与基督教的信仰生活实现了替代性的深层次互动。
七、乡村宗教生长路径的逻辑梳理
(一)旧有组织对乡村老人精神养老功能的满足
本文在开篇已经表明了我们要将宗教锲入农村老人日常生活的现象置于功能主义框架下分析的意图。那么,结构功能主义范式旨在以立体化、系统化的思维路径去探讨事物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关注子系统之间的有机结合与功能配合。就老年人的精神养老事件而言,功能主义提醒我们的是要看到社会体制及其分支在满足老年个体精神需求的层面上能否达到良好的互适效果。回顾村庄的组织记忆,农村老年人群体的精神养老需求即“信仰依靠”是始终存在的。只是不同时期满足这一需求的依托组织不同,近代时期的需求功能有地方宗族与民间信仰满足。到建国后,地方组织历经了农民协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不同阶段的重组,逐渐形成了全能型的集体性组织渗透乡村地区的场面,由此,人民公社、生产队等正式组织替代了宗族与乡村长老的角色继续承担起满足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任务。
具体而言,在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化时期,从权力组织来说,以全能型的国家组织为支撑,基层国家力量得以深入渗透地方情境;公有制的经济体制掌控了村庄个体的生产生活,从孩童到老人的生存均依赖于高度集中的集体性经济;而彼时的传统道德也置于村庄文化系统的最高点,教化规束着村民个体的意义系统。如此一来,宗族组织开始退场,一个由权力组织、经济生产、文化生活等多个子系统所推崇的“人造秩序性社会”便构建起来了。这样一个强调集体记忆的村落共同体对于村庄老年群体而言,是提供安全感、归属感、包揽一切稳定感的安全阀。我们且先不谈及该时期全能型组织对个体自主性抑制的负面效应,至少就老人这一层面上,这一时期的乡村组织所架构起来的这个整体性社会是他们所依附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公社制时期,国家对乡村治理的能力与设计,在与满足农村老年群体精神需求的对话上是呈现出良性互通的局面的。
据广西163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受银行审批权上收影响,35.6%的企业认为银行贷款耗时过长。部分企业反映从贷前办理资产价值评估、贷中经承办行初审和上级行批准到最后放款,基本需要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期间若提供材料不全更是影响放款进度。如柳州市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末申请一笔贷款,耗时3个月都不知是否获批。广西某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办理银行贷款时提交的材料较细,包括每一份原材料采购合同和发票等。
(二)形塑化组织与老人精神养老的 “对话”断裂
但是,社会组织的嬗变与社会政策的调整自然会导致乡村场域政治、经济、文化配置的变动与调整。公社制时期之后的村庄已经置身于组织权威弱化的无秩序困境之中。那么,原本承载集体记忆的集体符号与集体行为都已随着体制的重建而流变。去集体化的趋势下,地方便会充斥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这种不确定性危机更多的是精神世界里充斥的恐惧与焦虑,导致其生活与意义系统也往往失衡。在此现实下,他们往往对村庄集体性认同的缺失表现出极大的不舍,对晚年的家庭生活抱着悲观失落的心态。因此,到了人民公社制时期之后,社会体制的结构处于调整重建的变迁点,国家触角出现了地方场域“功能空白”、“制度真空”的负面效应,这里所表现的正是结构与功能发挥上的矛盾互斥,它甚至会引来整个社会秩序处于断裂性的场面,那么站在断裂面上的村庄老年群体由于自身认知的局限自然无法快速地建立起对现存村落秩序的认同。通俗来说,正式社会组织的功能弱化难以负担起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满足量,那么,当老人无法通过现实的组织系统对自己的生活世界进行构建并以此来理解周边世界时,他们的意义系统便陷入了失序状态。后果便是村落组织与农村老年群体的功能互动逐渐由曾经的良好对话转至中断破裂,造成了地方情境下老年群体对“灵验”的重视。
(三)精神养老“供给”与“需求”失衡下宗教复兴
我们还是以本文的分析工具——“功能替代”论解释乡村社区制度真空下宗教意义系统的 “篡位”事实。原本的农村社区秩序是镶嵌于社会大秩序之中的,集体性的正式组织发挥着精神慰藉的功能。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乡村秩序的形塑虽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控制性却大大减弱。这种乡村组织弱化的后果之一便是农村老年人群体普遍性的精神危机。那么,基于我们所强调的功能替代原理下,宗教系统的组织化、社会化特点使基督教拥有了“篡位”的契机。国家制度安排曾经在农村老年群体中发挥的心理调适、精神慰藉等功能,现在被农村基督教在一定的人群范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所替代了。
具体而言,在乡村社会秩序解构、重组前,个体已经习惯于从集体化系统中获取所需,一旦这个共同体的结构与功能不能实现互适,那么生长于其中的个体的意义世界必定失序,在功能空白与心灵失序的矛盾现实中,宗教这个替代品就应运而生了。涂尔干在分析原始的宗教制度时,就曾指出过,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成员为契合心理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象征体系,其往往产生和生长于社会动荡与转型的关键节点之上,即乡村宗教的扩散实质上是制度的真空驱使它作为体制的替代物医治社会创伤。那么,当下的社会现实是乡村组织与村庄老人精神需求满足的对话已经破裂,老年群体表现出个体与群体层面上的双重精神需求,但却面临着现有乡村体制不能良好回应其愿望的尴尬境地。故此,他们因急于摆脱心灵失序的痛苦,对生命的处境做出回应,而最终选择了生活化的宗教,去建构一个新的身份,以获取群体生活中的生命满足感。这样一来,制度性的宗教便从疏离于乡村社会外的一群,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社群之中。
八、余论
通篇文章之中,我们所要论述的文章脉络无非是“去集体化”趋势的现代乡村与村庄基层制度触角的空白对农村老年群体精神层面上的影响。在X福音村的镜像中,我们看到了乡村生活的现代性转变,也看到了集体系统的瓦解下,个体做出了透过基督徒身份构建新的群体化互动模式的现实选择。那么,我们既然已经窥探到了如此深刻生动的事实,为何不做出一些现实性的反思,给出一些针对性的回应?在这个现代性的地方语境中,老人之所以选择走到了神的面前是因为现代性乡村基层组织的大门没有做好接纳拥抱他们的万全准备,甚至某些乡村场域还存在着制度真空、供给空白的管理问题。事实上,宗教力量的在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上的功能替代效应仅是我们所要表达的一个引子,我们透过宗教锲入乡村场域的事实所要强调的旨意也在于此,透过它,走出一条农村基层社区管理创新的路子才是我们应聚焦的点。而对于具备真正有效整合机制的现代性组织社区而言,它的抓手在于协商共建,而不是严密控制的等级制度。因此,现代性农村“微观组织”的再造应是国家力力量与地方力量的协力合作场面。
在生态系统运行中的信息要与高校教育资源开发中的能量保存相互之间进行交换,从而促进高校教育资源体系的构建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稳定、可靠的关系。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源于生态资源的再生,而高校教育资源体系的构建会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资源的再生,所以需要两者之间的能量互补,从而保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通过高校教育资源的开发、整合以及利用,与生态系统信息能量之间的交换,保证高校教育资源的合理发展。从而实现高校教育资源体系构建向着生态化发展,并促进高校教育资源生态化发展向着科学性、合理性的方向进行开发、整合以及利用。
具体而言,在构建农村基层社区的实际操作中,要实现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的互构,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具备自主性却又不失凝聚力的国家依靠。[18]在乡村治理之中,要明确乡镇政府在乡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引导性地位,政治力量于乡村组织建设中的关键性经济、政治、社会等问题上必须掌控话语权、强化治理能力,进而方能依托良好的政治权威展开乡村建设工作。具体举措上,政府应当走在引导和培育乡村社会组织的前端,明确自身作为治理权力的掌控着,应为农村新型的社区体系提供资金援助与物质保障。其次,政府必须参与到农村内部社区体系建设的管理、监督工作中去,切实保障农村社区建设任务落到实处,并完善服务监督体系,增强工作透明度,形成良好的建设氛围。简言之,政府在农村社区养老体系的构建中必须明确自身责任与使命,广泛动员,从物质资源、经济政策、思想观念等诸多社会因素寻找切入点。只有这样,构建的过程与结果才不会偏离正轨。
与此对应的是,明确国家力量的前提下,也不能略过乡村自治力量与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应当依据乡村组织的协同作用,实现国家力量与乡村组织自治的有效衔接。具体到措施上,地方乡村可引进老年协会、老年互助组等城市性特征的组织形式;就村中养老层面而言,也可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医疗机构,及多种类的老年人休闲方式。要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加强农村老年人科学知识普及和健康维护,开展针对性的生命历程和生命意义教育,从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维护农村老年人的发展权益,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安全感,增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信心。其目的在于要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社区养老服务,凭借养老机构的力量改善地方治理;不难想见,当农村老年人的“本体性安全”获得现实社会制度的切实保障、精神归属有所依托、生命价值认识得到提升之后,宗教信仰在农村老年人生活意义系统中的可替代性将会进一步显现。农村老年人也终将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的晚年生活中实现真正的人生完善。最终期望能够形成一个 “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组织共生”的和谐场景。
对于X福音村这样的特殊案例,我们应当意识到宗教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本身就兼具整合资源、维系群体秩序、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积极功能。因此,我们不妨选择妥善引导与合理利用宗教力量,利用宗教资本重建乡村社区的信任资本与现代性的团体秩序,最终则有利于提升乡村社区自我服务与治理的能力。
注释:
①数据所得均来源于该村村史及访谈中村民相关回忆的记载资料。
②数据来源于X福音村教会发展史及田野中访谈资料。
参考文献:
[1][2]韩恒.近年来我国基督徒群体特征的发展演变——基于CGSS 2006、2010年度数据的分析[J].宗教与民族(第八缉),2013:195~207.195~207.
[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A]//金泽,邱永辉.中国宗教报告(2010)[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61~264.
[4]斯宾塞.社会学研究[M].张红晖,胡江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10~213.
[5]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115~118.
[6]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6.
[7]Bellah,Robert N.Beyond.Belief:Essays on Religion in a Post—Traditional World,[M].NY Harper&Row.1970,pp.168.
[8]Niklas.Luhmann.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
[9][16]陈占江.“基督下乡”的实践逻辑——基于院北C村的田野调查[J].重庆社会科学,2007,(9).
[10]黄剑波.“四人堂”纪事——中国乡村基督教的人类学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3.
[11]吴理财,张良.农民的精神信仰:缺失抑或转化——对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反思[J].人文杂志,2010(2).
[12]李华伟.乡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民众生活秩序的建构——以豫西李村宗族、庙会与乡村基督教的互动为例[J].民俗研究,2008,(4).
[13]龙书芹.论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J].广西社会科学,2006,(2).
[14]俞可平,徐秀丽.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04,(2).
[15]孙尚扬.宗教社会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8~159.
[17]孙凤.信徒与非信徒的相遇:乡村基督教传播研究[D].南京大学,2011.
[18]段绪柱.国家权力与自治力量的互构与博弈——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研究[D].吉林大学,2010.
“Absence” and“Usurp”:The Growth Path of Rural Religious Organizations——The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LIN Shu-li ZHU Rui-fan
Abstract:The cross-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historical trends of modernity and the traditional nature is fixed in the contemporary local social field,and the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between them breaks the relationship chain between the"spiritual demand"and the"satisfy"between the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rural old man,which is derived from a variety of local problems.Based on this,the paper takes the spiritual support of the old people in the X-Gospel village as a clue,through the memory of the life of the village,and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system of the religious power embedded in the rural old people.And as a social organization force,the growth path and the practice logic in the rural internal power pattern are shown.From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the lower part of Christ",it can be seen that the organization demand of the old-age life of the old people in the countryside,with a view to giving a realistic response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unction perfection of the rural commu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st-rural Chinaundefineds organization,and realizing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ural self-government power and the formal authority of the grass-roots level.
Key words:Village Religious Organization;Growth Path;Structure Function;“Absence” and“Usurp”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2-0188-10
收稿日期:2018-12-11
作者简介:
林顺利(1978—),男,河北徐水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朱睿钒(1994—),女,河南周口市人,河北大学社会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乡社会治理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徐长菊]
标签:组织论文; 基督教论文; 乡村论文; 社会论文; 村庄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教会组织及教堂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河北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