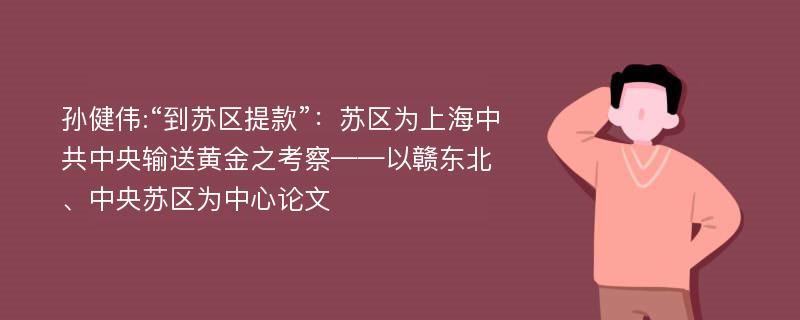
提要:在漫长的革命进程中,作为硬通货的黄金,一直是支撑中共革命的重要战略资源。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经费不能有效供给上海中共中央之时,由各苏区自下而上提供经费支援,成为上海中共中央的战略选择。“运金上海”正是中共中央“到苏区提款”的内容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赣东北和中央苏区通过“打土豪筹款子”收集了大量黄金,它们在战时交通员输送下,经由不同的秘密交通线而运抵上海。苏区支援的大量黄金为中共中央继续立足上海,指挥全国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关键词:黄金;上海;中共中央;苏区;交通线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苏区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在此过程之中,各苏区收集了大量的黄金、白银、钞票等财物。在上海中共中央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这些财物由苏区秘密送往上海,有效充实了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注]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凌步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经费与物资援助》,《苏区研究》2015年第1期,第42-56页;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第4-24页;何益忠:《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活动经费来源及影响》,《史林》2010年第6期,第150-155、191页;徐元宫:《中共建党初期活动经费来源的历史考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1期,第3-14页。,发现以往学界重点关注共产国际对上海中共中央的经费帮扶,而上海中共中央“到苏区提款”[注]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收集的黄金、银元、钞票等财物要集中输送上海党中央,“到苏区提款”是中共秘密交通线的一个重要任务。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东党史资料》第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的重大历史事件却鲜有专门的探讨。本文拟从苏区收集的黄金着手,择取赣东北和中央苏区两个区域,对苏区运金上海的史实进行考察和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一、缘起:上海中共中央的经费支绌
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此后,中共中央驻扎上海指挥全国的党组织建设和工人运动。建党初期的中共,其工作重心不在武装斗争,而主要在于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了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出版书籍报刊和建立工人学校等等。[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众所周知,每一项组织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大量的组织经费来支撑。由于党创建初期的革命者除了少数有社会职业之外,多数革命者并无固定收入或多为青年学生,所以党的活动经费并不充实。[注]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与此同时,作为革命经费重要来源——党费,在当时的收入也是十分有限。据统计,中共“三大”结束之际,“多数党员没有职业”,“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注]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因此,在建党初期,“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注]《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68页。正是由于自身筹集经费的能力有限,共产国际的经费扶持有力地支撑了建党初期中共的组织运行和工人运动的开展。
目前,大多数指南不推荐临床淋巴结阴性(cN0)的PTMC患者接受预防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14,16-17]。然而,由于CLNM的高发病率,一些学者仍支持其在cN0的PTMC患者中的应用。通过预防性清扫中央区隐匿性淋巴结可以减少肿瘤残留风险,同时可评估患者病情及侧颈淋巴结转移风险并指导治疗方案。虽然在生存分析中,CLNM与预后无显著相关性,但从肿瘤根治性及复发风险角度,PTMC患者仍需考虑预防性中央区颈淋巴结清扫术的意义。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继续驻扎上海,指挥着全国的武装起义和红色苏区的发展。在此期间,虽然共产国际依旧对中共进行拨款补助,但此时中共的活动经费显然已呈支绌之势。首先,共产国际的经费通常借助上海的德国银行汇入中共中央,但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加之德国法西斯政权的上台,共产国际通过上海德国银行的渠道给中共中央提供经费愈发困难。[注]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吴德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其次,共产国际方面的经费拨款“存在着严重不足和拖欠的现象”。[注]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第14-15页。伴随着国共两党的争斗角逐,上海中共中央及地方各省的财政支出十分巨大,已经远远超出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数目,实则是“供不应求”。最重要的是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为汲取失败教训,开始独立自主搞革命。革命的开展必然需要经费的大力支持。在中共接续不断的武装暴动中,武器和经费的支撑举足轻重。此外,对于职业革命者必须要提供一定的生活费补贴;革命机关驻地或革命者居住地也需要一定的经费支出;各地之间的联络亦需要交通费的支出;革命斗争的宣传机器也免不了宣传办公费的开销等等。[注]何益忠:《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活动经费来源及影响》,《史林》2010年第6期,第151-152页。总体而言,“当时党在白区的活动经费很大,上海党中央虽从各方面筹措,但有时也难以按时发各地。”[注]李沛群:《关于中共中央交通局从上海至闽西苏区的交通路线情况(节录)》,江西省邮电管理局编:《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版,第520页。面对如此状况,由各地建立起来的红色苏区自下而上对中共中央进行经费补给,便成为了一种特殊的选择和长久之计。
公允价值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使企业的财务信息更能准确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为外部投资者提供更加客观、有用的财务信息,以便投资者作出更加理性的决策。但公允价值的使用是有条件的,需要财务人员谨慎使用,并能利用一定的技术方法准确确定。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共领导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发展起来,苏区各地陆续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在处置地主豪绅的财物时,“除粮食、衣物等发给群众外,黄金、白银、钞票等都集中送中央。”[注]李沛群:《关于中共中央交通局从上海至闽西苏区的交通路线情况(节录)》,《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第520页。在赣东北苏区(亦称闽浙赣苏区),苏维埃政权在反对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中,也时常组织武装力量“到敌人的后方去抓敌人的军、政官员,抓大地主、恶霸,向他们筹款子”,或者“趁机对白区进行军事打击,打进中、小城市去,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注]方志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苏区交通运输工作的回忆》,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西省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页。可以看出,在苏区创建初期,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土豪筹款和从战斗中缴获。当然,“为了奠定苏维埃财政来源的稳固基础,在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时期,苏维埃政府迅速建立了人民的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经常性来源,即在取之于敌的同时,亦取之于民。”[注]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因此,随着苏区在财政上的稳固与自足,将苏区收集的黄金、银元、钞票等秘密运往上海,成为了中共中央解决自身经费问题的另外一种途径。
径向力波特征参数如表1所示。表1中,fe=ω/2π=np/60;k为磁导谐波次数,k=1,2,3,…。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区送往上海的诸多款项之中,黄金作为一种更具价值的硬通货,对于驻扎于大城市的中共中央来说更是急需的特殊资源。土地革命时期,赣东北苏区和中央苏区曾经搜集缴获了大量的黄金。香港交通站在给中央交通局的信中曾提及“闽西来信云有大批金子,由中央苏区运出的,等你们派人去运到沪去。请你们派可靠的人直接运到沪”。[注]《香港交通大站给中央交通局的信(总字三十一号)——交通工作情况与最近送去人员名单》(1931年9月22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2)》乙3,1985年版,第269页。在赣东北苏区,“方志敏带领红军相继打下了景德镇、都昌、彭泽、波阳、湖口、乐平众埠街等地,缴获了很多的黄金和白银”。[注]陈显东:《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建立的回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578页。1931年至1932年间,方志敏曾两次率领红十军入闽作战,第一次赤石之战,没收了官僚买办资本家财产,筹集了银元10万多元,黄金3000余两。[注]中共南平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闽北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赣东北和中央两苏区“运金上海”的历史事实也正是在“到苏区提款”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总之,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中央苏区,除几次较为短暂地迁离上海以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长期驻扎上海指挥全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经费不能有效支撑中共独立开展革命之时,“到苏区提款”也就成为了上海中共中央指挥全国武装斗争和组织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也诚如杨奎松先生所言,中共依靠共产国际拨款开展活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据地、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注]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第4页。。
基要主义者之所以否定伊斯兰教的世俗化,实际上源自于对世俗化的曲解。 因为按照近年来西方宗教社会的普遍解释,他们将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退出叫做世俗化。 但如果要这样理解世俗化的话,还不如将世俗化理解为韦伯的怯魅化(disenchantment)。 怯魅过程在使人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由意志局限性的同时,使得人类控制自然力量的范围逐渐扩大。 人们虽然不再祈雨,却在进行人工降雨,人们虽然不再用巫驱魔,却可以用医治病。
二、路程:中共开辟的运金交通线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危局。“自七月初旬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动以来,本党中央政治局已转入秘密状态而组织上有所改变。”[注]《“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小引》(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47页。为加强中共中央与各省之间的联系,“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于8月21日发布《中央通告第三号》,“议决中央须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注]《中央通告第三号》(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编:《党内交通史料选编》第1辑,内部资料,1981年版,第19页。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汉口回迁上海,之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央外交科和军委交通总站。“在党的正确领导与严肃督促下,在各省帮助之下,两个月中将与各省的交通完全健全起来。”[注]吴德峰:《中央交通局》,《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第496页。
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共领导下的各地苏维埃政权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明确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白区同苏区的斗争,要互相联系,为在苏区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斗争”。[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6页。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将军委交通总站改为中央交通局,同时将中央外交科也一并划归交通局,受中央政治局直属领导。中央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鸣和吴德峰五人组成委员会,由吴德峰担任局长、陈刚担任副局长,其主要任务就是“打通苏区的交通线,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注]吴德峰:《中央交通局》,《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第496页。
中央交通局成立后,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指示下,逐步打通了上海通往各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在当时,以上海为轴心的秘密交通线主要有三大主线,“一条由上海到北方局(北京),一条到南方局(广州),一条到长江局(汉口)”[注]王凯:《地下交通线——大革命时期地下交通的片断回忆》,《党内交通史料选编》第1辑,第52页。,也称之为北方线、南方线、长江线。其中,各主线又下设多条不同的支线,为有效连接各苏区和各地省委。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北方线上海—郑州—驻马店—鄂豫皖苏区上海—河南、陕西省委上海—北平—河北省委—河南、山西、察哈尔省委上海—满洲省委
长江线上海—衢县、上饶—赣东北苏区上海—合肥、六安—鄂豫皖苏区上海—黄石—湘鄂赣苏区上海—武汉—株洲—湘赣苏区—中央苏区上海—沙市、宜昌—湘鄂西苏区上海—重庆—成都—四川省委南方线上海—香港—广州—南雄—江西上海—香港—汕头—饶平—饶和埔诏苏区—闽西上海—香港—汕头—潮安—松口—梅县—蕉岭—平远—江西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虎岗—瑞金
资料来源:《党内交通史料选编》第5辑,1987年版,第284-285页;陈汉初:《周恩来与革命战争年代粤东秘密交通》,《党的文献》2016年第2期,第125页。
在国共内战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的秘密交通线肩负着诸多任务,主要包括:沟通上海中共中央和各苏区的文件信息往来,向苏区输送大量的物资以及护送干部进入苏区。此外,秘密交通线还承担着一项特殊的职能——“到苏区提款”,其中运送黄金正是“到苏区提款”的具体内容之一。虽然中共开辟的秘密交通线集多种功能于一体,但就运送黄金而言,这一功能亦会有所不同。黄金作为一种极具价值的特殊资源,必须由运金人员包装好后随身携带。而向苏区运送的诸多物资,有时会利用社会关系采用托运的方式进行输送。[注]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20页。在黄金交接的具体过程中,也必须严格把关黄金的数量。因此,在整个运金的过程中,对安全性和机密性的要求更为严格和周密。
本文根根“压载水公约”的相关规定,采用10倍稀释涂布平板划线法,将样品中的致病菌培养成菌落,通过菌落的不同特征确定对应致病菌的种类,通过观察菌落的数量来完成对致病菌快速准确计数。
总之,纵横交织的交通线、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生动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也共同构筑了苏区运金上海的坚强堡垒。
结合卫星定位技术、信号检测与处理技术、多模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研究了集装箱实时监测的卫星定位、分布式环境监测、安全保障和多模通信等技术方案,设计实现了一种集装箱远程实时安全监测系统。实验测试结果表明,利用相关技术方案搭建的集装箱远程实时安全监测系统功能完善,能够对集装箱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状态、位置信息、箱内环境进行远程实时监测,不足之处在未对系统的功耗进行严格的测量和控制,如果能结合低功耗设计、电源管理和新能源发电等技术手段实现系统的长时间工作,则具有一定的应用推广前景,有助于促进集装箱物流运输行业的发展。
(一)赣东北苏区交通线
战时黄金输送是一项极为特殊而又高度保密的工作,必须由专人负责,并经由地下的秘密交通线才能安全地运抵上海。在当时,中央交通局对线上交通员的选拔颇为严格,须具备多重标准。“首先,要党龄长,政治上坚定可靠;其次,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警灵活,枪法要准;第三,身体要健壮,能够胜任长途跋涉。”[注]蓝松英、吴锡超:《周恩来与中央红色交通线》,《福建党史月刊》2016年第3期,第17页。除此之外,还要求交通员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记忆力要强,以适应“无纸化”的交通情报工作。土地革命时期,战斗于秘密战线的交通员往往身负重金,穿梭于赤白两区之间,跋山涉水将黄金送往上海。可以说,游走于秘密交通线上的战时交通员真正担负起了运金上海中共中央的重要职责。通过挖掘相关史料,可以发现,参与输送黄金的人员不仅有赣东北、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的专职交通员,也有中央交通局和地方交通站的主要负责人。
(二)中央红色交通线
当时,中央苏区内的交通系统称为“工农通讯社”,附设在国家保卫局之下。除总社以外,通讯社还有许多分支机构,共同形成了区内交通网。中央红色交通线经闽西苏区后,便与中央苏区的交通系统相对接。之后,从闽西永定通往瑞金的交通路线是:永定—合溪—大地—虎岗—大洋坝—坑口—白沙—归县—南阳—涂坊—四都—茶坑—瑞金。[注]陈显强:《编后记》,《红色交通线》,第279页。由此可知,中央红色交通线由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共同指挥管理。“凡属赤区的交通站归闽站管辖,白区的交通站归港站管辖。赤区应向外布置交通路线,港站应向内布置交通线在赤白分野的地方去合接起来。”[注]《伯温致中央交通局并转中央信——香港交通大站目前状况与要解决的问题》(1931年10月19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2)》乙3,第278页。这条由中央直接管控的秘密交通线为苏区的黄金输送提供了坚实的客观保障。
级别站点负责人大站香港华南交通总站饶卫华闽西永定大站李沛群中站大埔青溪站卢伟良汕头交通站陈彭年小站宝坑、铁坑、桃坑等邹日常、蔡雨青、谢新基等
资料来源:《江西省邮电志》,第419页;《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第516-517页。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指上海中共中央建立的上海与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之间的秘密交通线,它的实际路程与南方线相互吻合。土地革命时期,南方线的四条支线中有三条线路先后被敌人破坏,“只有经大埔清溪的交通线保存下来”[注]邱立志:《论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11页。。“我们从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闽西苏区这条地下交通线……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是归中央直接管的。”[注]李沛群:《红色地下交通线的汕头交通站》,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色交通线》,内部资料,1986年,第97页。1931年初,这条长达数千里的秘密交通线正式贯通使用。纵观中央红色交通线,它由多个秘密交通站衔接而成,而交通站又分为大站、中站、小站,以有效加强白区和苏区之间的联系。
在各秘密交通线工作的专职交通员亦参与了战时的运金工作,他们是运金上海的主力队伍。曾昌明和肖桂昌[注]1930年中共中央交通局成立后,曾昌明、肖桂昌、熊志华、李沛群四人担任中央交通局的专职交通员,被誉为中央交通局的“四大交通”。参见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9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155页。在1930年后任中央交通局的专职交通员,他们二人经常奔走于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肩负着“到苏区提款”的重大使命。根据曾昌明的回忆,“1931年夏,我(曾昌明)从上海到厦门,同肖桂昌同志去苏区领款,我们此行是接受中央任务到苏区领款回上海党中央机关。我们两人到了漳州,见到聂荣臻同志。他给了我们价值约5000元的金条。肖(桂昌)带一半,我带一半,分别带回厦门、上海”。[注]曾昌明:《中央交通局工作概况(节录)》,《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第509页。此外,在线上的交通站之中,也有专职的运金交通员。卢伟良1931年初担任大埔交通站站长,在此之前,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的秘密交通员,经常来往于闽西苏区、香港和上海之间。1930年7、8月间,卢伟良亲赴闽西苏区取回闽西特委交给他的十多斤黄金,从龙岩返回香港。为了不使黄金暴露,他把金子垫在箱子底层,机智勇敢地通过了敌人的搜查,顺利地把黄金送到了香港交给了广东省委。[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论东江苏维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309页。除了中央苏区送出的黄金以外,赣东北苏区的黄金也通过线上的交通员秘密运抵上海。在赣东北苏区,有一名专职交通员(姓名不详),“个子不很高,方圆的面孔,两只大眼睛,为人颇机警,他能把被查禁的无线电器材从上海带到浙赣线上的玉山、常山一带,交给我们在那里的秘密交通站再转到赣东北苏区领导机关,并把苏区送交中央的金条带回上海”。[注]李培南:《四年工作交通纪实》,《党内交通史料选编》第5辑,第284页。
三、人员:身负重金的战时交通员
赣东北苏区是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领导的“弋横暴动”基础上开辟发展起来的。至1932年底,赣东北苏区已经发展到闽浙赣三省边界。1932年10月前,由于“上海党中央的交通组织则相对稳定和严密,因此,闽浙赣苏区实际主要还是与上海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注]《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苏区党内交通概要》,《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第345页。为此,赣东北苏区先后建立了与上海中共中央直接联络的秘密交通线——安徽线和福建线。安徽线由中共信江特委(后为赣东北特委和赣东北省委)起始,经由屯溪、歙县、芜湖或杭州等地,进而再转上海中共中央。1930年7月,闽北苏区并归赣东北苏区之后,“为保证与上海中共中央秘密交通的安全畅通,赣东北特委还沟通经闽北苏区通向上海中共中央的秘密交通线,此为福建线”。[注]王孝槐、张庆亮主编:《江西省邮电志》,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23页。此外,中央交通局成立后,在其开辟的长江交通线中,也下设一条专线直接通往赣东北苏区,它的实际路程为“从上海乘浙赣线火车在衢县和上饶之间的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注]李培南:《四年工作交通纪实》,《党内交通史料选编》第5辑,1987年版,第284页。土地革命时期,赣东北苏区收集起来的黄金一般都是经由以上秘密交通线运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一)中共中央交通局负责人
中央交通局吴德峰、陈刚二人曾亲赴苏区将黄金秘密地运送至上海。1930年秋冬,中共鄂东特委通过“打土豪”没收了一批黄金,并要求上缴党中央,周恩来因此笔黄金数额较多,遂派遣吴德峰赶赴苏区取回。在鄂东,吴德峰见到鄂东特委书记吴致民(化名胡梓),两人交接约10斤左右的黄金。[注]吴卅生、吴爱生、吴持生:《怀念我们的父亲吴德峰同志——亲爱的爸爸诞辰100周年祭》,《吴德峰》,第406-407页。鄂东特委书记胡梓也曾回忆说:“他(吴德峰)曾经到鄂东来过一次,利用背子弹的方式,将特制的‘子弹袋’内装上金条,一次就背了5公斤回到上海。”[注]黄火青:《忠实于党的优秀战士吴德峰同志》,《吴德峰》,第265页。
陈刚更是先后两次赶赴苏区,星夜兼程地将苏区的黄金运抵上海。1930年8月,陈刚被任命为中央提款委员(化名易尔士),同时以中央巡视员名义前赴苏区收集黄金。整个冬季他奔波于第一次反“围剿”前夜的危险地带,走遍江西、闽西、湘东南、东江等苏区,将苏区“打土豪”所没收的千余两黄金赶送上海中共中央。[注]《陈刚年谱》,《陈刚纪念文集》,内部资料,1999年,第432页。据陈刚夫人石础(何叔衡之女)回忆,“他(陈刚)把从江西苏区上交的千余两黄金首饰熔成金条,我(石础)和夏尺冰协助他运送到上海。我们同行几人都把黄金捆在腰上,他的身上带得最多,一路上要与各地团防周旋,严冬季节经常走得大汗淋漓,晚上投宿,劳累一天的陈刚常常整夜守住黄金,经过千辛万苦把黄金安全送到了驻上海的党中央”[注]石础:《我对陈刚同志的怀念》,《陈刚纪念文集》,第66-67页。。1931年2月,中央提款委员陈刚(易尔士)刚回到上海,随即又奔赴苏区,在湖南醴陵一带再次为中央提回大量黄金。[注]《陈刚年谱》,《陈刚纪念文集》,第434页。可以说,正是吴德峰、陈刚的亲力亲为,才有力确保了黄金输送中央的实效性和机密性。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央交通局负责人亲赴苏区接运黄金,也充分体现了黄金对于上海中共中央的急需性和重要性。
(二)线上交通站负责人
线上交通站点的负责人不仅参与了各自交通站的建设,而且相互配合、通力协作,为苏区和上海中共中央之间的物资、文件输送作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1月,陈彭年、罗贵昆与顾玉良三人按照中央指示前往汕头建立秘密交通站。汕头交通站以一家电料公司为掩护,秘密地开展情报和物资运送工作。[注]顾玉良:《汕头交通站建站情况记忆》,《红色交通线》,第153页。陈彭年任汕头交通站负责人,其主要任务是实现汕头与中央苏区的有效联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经常护送经费、钞票、弹药和党的机密文件来往于上海、汕头等地。“有一次听说他一人提了两皮箱的钞票,说是提供敌后地下工作活动经费。他身穿西装,头戴呢帽,手拿文明棍,绅士华侨商人的打扮,出入敌人的封锁线,奔走在红色交通线上。”[注]《陈德芳同志<关于胡广富电器材料行>的来信摘录》,《红色交通线》,第217页。1931年,中央交通局派遣李沛群任闽西永定交通大站站长。在此期间,李沛群将中央苏区收集的黄金及时送往汕头交通站,再由汕头交通站转送上海党中央。据李沛群的回忆,在汕头交通中站里,“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注]李沛群:《关于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若干问题的回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29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由此可见,线上秘密交通站点之间的相互合作,使得苏区的黄金得以顺利安全地运抵上海中共中央。
(三)秘密交通线上的专职交通员
“每一把吉他和电吉他,都要经过成型、打磨、喷漆、抛光、组装等100多道工序。比如,成型又分为破板、烘干、拼接、压板、切割、修边等,打磨又分为磨白茬、磨油漆、打光等等。我们的产品多为中高端,质量有很好的保障,使用多年也不会出现木坯开裂、变形等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外国客商选择昌乐吉他的原因。”郝洪旋说。而此话我们同样在乐器展厅得到了验证,在这里摆放了数百把10多年前制作的吉他产品,尽管经过寒霜酷暑的考验,它们并没有因为环境和温度湿度的影响,而发生性质的改变。同样,雅特乐器厂总经理赵卫国对他们的产品也有如此的保证。
综上所述,赣东北苏区和中央苏区收集起来的黄金会经由不同的秘密交通线送抵上海中共中央。就中央苏区而言,在不断的反“围剿”斗争中,没有被敌人破坏并唯一保留下来的中央秘密交通线[注]曾昌明:《保卫交通站的斗争》,《党内交通史料选编》第1辑,第169页。,为黄金的安全输送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可以说,象征着“苏维埃动脉”的秘密交通线生动再现了赣东北和中央两苏区运金上海的独特历程。
在复杂的战时情况下,两个苏区的黄金若要被安全顺利地送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必然要经历一番曲折。在当时,中共领导下的赣东北苏区和中央苏区集中位于南方地区,两苏区输送黄金的路程亦会经由不同的秘密交通线而运抵上海,以确保运金的实效和安全。
从提要的著录情况来看,明代文学整体呈递减趋势,从前文的文学分期也可看出,四库馆臣对明代文学持倒退衰敝的态度。反观开国洪武期间的文坛,短短三十余年,就有“59位作家的65部作品被收入”。[7]四库馆臣褒扬洪武期间的文学平正典雅,称其“一扫元季纤秾之习,而开明初舂容之派”。[2]479而对于晚明文坛的代表——公安、竟陵两派,《四库》则将其贬为“交煽伪体,幺弦侧调,无复正声”。[2]820可以说,馆臣对于明代文学的整体把握,不仅与史实不符,与当今的学界观点也是相悖的。
四、数目:支援上海中共中央的大量黄金
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筹款子”既是红军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群众工作)之一,“还是目前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注]《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财字第六号——目前各级财政部的中心工作》,《红色中华》1932年9月13日,第7版。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曾将区内搜集的大量经费送往上海,以扶助党中央开展工作。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赣南、闽西挺进,于当年3月占领了长汀城。在长汀党组织的帮助下,红四军共筹得经费5万余元。红四军前委随即决定“通过邮局的地下党员罗旭东汇一笔巨款给上海党中央作活动费”。[注]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闽西人民革命史(191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1930年,在红军攻克吉安后,又进一步“取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其中,黄金的收入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注]郑火编著:《毛泽东财会思想研究——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在当时的情况下,“土劣如无现钞、现洋的,准以黄金饰品每两折大洋60元交纳”。[注]江西省财政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江西省财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页。因此,黄金作为中央苏区筹集经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作用毋庸赘言。此后,在上海中共中央建立起与中央苏区的交通联络之后,中央苏区收集的黄金也被陆续送往上海。虽然中央苏区运金上海中共中央的“具体数量难以查证”,但是“从中央苏区和闽西苏区缴款到中央的不会是小数目”。[注]赖立钦:《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历史定位研究》,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纪念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汇编》,2012年版,第265页。
在赣东北苏区,方志敏等人领导干部群众不仅建立起被服厂、兵工厂、纺织厂等独立的工业体系,还创建了苏维埃银行等金融机构。与此同时,区内“各县设立对外贸易处,以管理并监督苏区与非苏区的贸易”。[注]曾洪易:《设立对外贸易处》(1931年8月14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410页。可以说,赣东北苏区在独立自主进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然而,在经济逐渐好转、财政逐步充足的情况下,赣东北苏区的工作人员“往往只用少数的经费”[注]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年3月),《方志敏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而选择将更多的财力积极支援上海的党中央。就上交中共中央的黄金数量而言,赣东北苏区于“1931年上交中央黄金650两,1932年两次带给中央黄金350两,1933年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送去黄金两箱、银洋18箱”。[注]刘国云主编:《方志敏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总之,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先后为上海中共中央输送了大量的包括黄金在内的活动经费。苏区搜集并提供的黄金、银元、钞票等经费,为中共中央继续驻足上海开展革命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石。其意义之特殊、效果之显著,正如杨奎松先生所述:“这意味着,中共不再完全指望从共产国际那里取得经费支持了。”[注]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第20-21页。
结语
1927年“四一二”国共分裂以后,迭遭血腥镇压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武装起义,独立自主进行革命。革命斗争的开展必然需要革命经费的扶助,对于驻扎上海的中共中央而言,虽然共产国际方面会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但是革命经费的自我筹措也是当务之急。在内外两重因素的作用下,由中共领导的苏区向上海党中央输送黄金也就应势而生。除此之外,关于苏区运金上海的重大历史事件,还可以进一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评析。
第一,苏区运金上海是中共秘密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秘密战线担负着诸多职能,既有白区内的锄奸运动,也有通往各苏区的秘密交通。实现白区与苏区之间的物资、经费、文件、干部的联系往来,亦是中共秘密战线的重要使命。因此,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去审视,苏区运金上海,不仅是中共中央“到苏区提款”的具体内容之一,也是中共秘密战线领域的特殊任务。
末次治疗后4h,取血后剥取大鼠右后踝关节滑膜和部分软骨组织,经10%甲醛固24h后,用10%EDTA溶液进行脱钙,按常规方法进行石蜡包埋、切片,HE染色后光镜下观察关节及滑膜组织的病理学变化。
第二,苏区黄金的来源并非仅来自于区内的地主豪绅。各地苏维埃政权成立后,陆续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为苏区的黄金筹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苏区在向白区进行革命渗透之时,也会没收一些官僚、买办和资本家的财产。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他们的财产处置问题,也并非全部没收,是有所区别的。在筹款中,工作人员需要“调查地主富农的家庭,适当的说定罚款捐款数目,报告区苏”。[注]《怎样去筹款?筹款的意义与其正确路线》,《红色中华》1933年9月30日,第3版。除此之外,“对一般地主兼资本家,我们只没收地主的封建剥削那一部分,不是全部没收”,“我们当时抓到土豪劣绅也不是全部杀掉,对一般情节较轻,罚了款以后,我们仍释放他回去,只是对个别的罪大恶极有血债的才加以镇压”。[注]薛子正:《有关赣东北、闽北的部分情况》,方志敏、邵式平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0页。总之,在“打土豪筹款子”过程中,既有不同的筹款对象,亦有不同的筹款措施。
第三,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移瑞金,在党中央驻扎上海的十余年间里,各地苏维埃政权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起来。在此期间,除了赣东北和中央苏区向中共中央输送黄金以外,诸如鄂豫皖、湘鄂赣等苏区也曾将收集的黄金秘密运往上海。也正是在各苏区财力支援的基础之上,才使得中共中央能够摆脱对共产国际的依赖,进而长期立足上海,指挥着全国的武装起义和苏区建设。因此,苏区支援上海党中央的历史贡献值得关注和铭记。
综上所述,土地革命时期,红色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为驻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持。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之间的条条运金路,不仅是象征着红色政权发展的“苏维埃动脉”,也深刻勾勒出了中共革命苦难而又辉煌的历史轨迹。正如金一南先生所说:“如果当年红色首脑不集中在现代化的大城市,那么中共不可能获得马列主义这样最先进的思想体系,而且也不会收获后来众多的精英的领导;如果红色武装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也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物质给养和顽强的革命战士。”[注]金一南:《浴血荣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42页。
"DrawingMoneyinChineseSovietArea":TheInvestigationonGoldTransportfromChineseSovietAreatotheCPCCentralCommitteeinShanghai——CentralizingontheNortheastJiangxiSovietAreaandCentralSovietArea
SunJianwei
Abstract:During the long revolutionary process, as a hard currency, the gold had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 to support the CPC revolution.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wh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unds could not effectively suppl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Shanghai,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from soviet areas from bottom to top had become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Shanghai. "Transporting gold to Shanghai" was one of contents of "Drawing money in Chinese soviet area".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period, the northeast Jiangxi soviet area and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had collected much gold from the local tyrant. They were carried by traffic officials, and transported to Shanghai by way of different secret routes in the wartime. The gold supply of the soviet area provided large material support for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this basi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uld continue to comman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Shanghai.
Keywords:gold; Shanghai;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soviet area; traffic line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2.003
作者简介:孙健伟,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
责任编辑:黄秀
标签:苏区论文; 上海论文; 中共中央论文; 中央论文; 交通线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