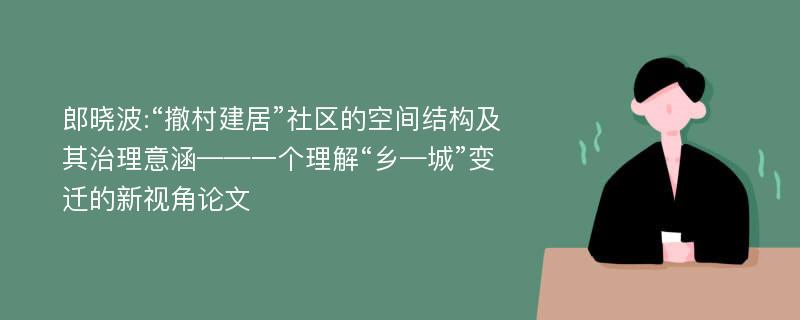
摘要:国家主导下的城镇化战略催生了大量“撤村建居”社区。“撤村建居”社区是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的中间场域,是农民实现市民化转变的空间载体。当前,“撤村建居”社区建设中存在“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治理的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两个突出矛盾,原因在于没有系统考察社区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治理转型与秩序重建的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空间是“乡—城”变迁过程中社区内各种社会关系变迁的产物和体现,既在纵向上反映了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总体性空间变迁,也在横向上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三个维度体现了“乡—城”变迁的动态变化。空间变化对社区治理的主体、单元、网络、范围和机制等均形成挑战和冲突。“撤村建居”社区应转向以空间为基础的现代治理模式,以此增强人、空间与治理的协调从而降低城镇化风险。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撤村建居”社区 空间 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关系变迁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进入工业化社会后一切社会变迁的主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论及,城乡关系一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将为之改变。[1](P159)城市化是改变城乡关系的重要途径,但其推进有不同的动力。由产业结构升级拉动的自发城市化一般是在城市产业吸引力和乡村排斥力双向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而在中国,还存在着以国家积极城市化政策为主要动力的道路——“国家主导式城市化”。[2](PP7-18)国家战略对城市和区域城镇化起了决定性作用,农村自身的推动作用则基本可以忽略。自上世纪90年代末,在国家主导式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双轮驱动下,中国的城市空间不断拓展,全国各地加快了推进城市城镇周边农村融入城区的步伐。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就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2014年,国家正式出台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规划,明确要求到2020年全国将全面完成“三个1亿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其中包括要促进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以及引导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3]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量从262个增加到295个,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由36.2%上升到56.1%;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0%。[4](P3)于是,大规模的村庄合并、“村改居”和城中村改造成为不少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普遍选择。一方面,各级政府对“撤村建居”社区开展了城市路网改造、标准化高层住宅安置及景观绿地物业配套等系列工程;另一方面,按照城市社区建设的要求从干部队伍、制度架构及方式手段等方面对“撤村建居”社区进行变革。
作为中国农村“乡—城”变迁的重要形态,“撤村建居”社区的形成和激增改变了长期以来学者在进行社区研究时按地域划分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取向[注]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发展”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报告》中曾首次提出过“中介社区”的概念,认为“中介社区”是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而同时兼有两者成分的社区,主要是指县镇,还包括超级村庄。但“中介社区”概念提出后,后续研究者并不多。折晓叶、陈婴婴在《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中提到了“中介社区”,他们也将“中介社区”等于小城镇。2000年以前,社区研究仍主要关注农村或城市社区二种类型。。城乡绝然对立的二元状态已被打破,介于两者之间的“撤村建居”社区被形象地称为“都市村庄”、转型社区或中介社区。[5](P1)“撤村建居”社区成为传统农村转向现代城市社区的重要空间场域,也成为农民实现市民化转变的空间载体。政治和经济系统的核心制度转变可以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但空间居住结构的变化却需要数十年的时间。[6](P117)从这个角度而言,“撤村建居”社区的转型与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民能否顺利转变为城市居民,关系到农村城镇化后能否可持续发展从而保障基层稳定,也将间接影响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得失。中国行政主导下的快速城镇化模式带来社区“乡—城”变迁过程中两个突出矛盾: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治理的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无论从地方实践还是学界探讨来看,当前对社区转型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治理的主体和能力、治理的手段和技术等结构性、能动性问题上,而对治理发生的社区空间结构变化及特征缺乏足够的关注,没有考虑空间结构变迁的社会意义及空间重构对治理转型的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因此,本文以“撤村建居”社区为分析对象,提出从空间视角勾勒社区“乡—城”变迁与重构的微观机制,并分析空间的社会意义及其对治理转型与秩序重建提出的挑战。
二、“乡—城”变迁中的社区空间研究回顾
空间是社区研究中的重要视角,但在历史决定论盛行的20世纪中期之前这一视角几乎被淹没。[7]这中间只有少数学者对空间的社会属性表现出了敏锐的思考。涂尔干认为空间和时间一样都是社会的构造物,特定社会的人都是以特定的方式去体验空间的。[8](P30)齐美尔强调客观物质空间和主观心灵空间之间的互动性,以空间为物质条件有可能构造出一套蕴含实践意义的观念或精神空间。[9](P13)因此,城市化进程中“乡—城”转变可以通过空间来呈现。空间不仅包含居民的特点,也浸染居民情感,看似平面划分的几何空间因而能够成为具有情感和传统的邻里。[10](P8)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出“空间”是社会理论的核心主题之一,将空间定义为社会存在的物化,具有“空间再现—空间实践—再现空间”三重性。[11](PP170-173)这些观点都为空间视角下的城市化和社区转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一)“乡—城”变迁的空间之维
从“乡—城”变迁的世界趋势来看,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经历“农村瓦解”的特殊时期,甚至连乡村研究也逐渐淡出了西方社会学的主流话语。[12]置于“城市导向”(urban-oriented)的发展框架下,乡村社区的转型集中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病理性问题,例如有西方学者提出农村转型实则是城市居民迁移乡村对村民产生剥夺而引发的社会冲突。[13]由于乡村天然的“共同体导向”,一旦面对全球化和城市化冲击,乡村瓦解是正常并且必然的。在城市化过程中,以“乡—城”移民或流动人口为主的城市特定社区成为集中呈现社会变迁问题的主要空间。美国芝加哥学派以犹太人聚居区、波兰移民区、贫民聚居区、上流阶级邻里等系列特定社区空间为对象进行深入调研,重点研究了非法团伙、流浪汉、青少年犯罪以及犹太移民等群体产生的社会排斥问题。围绕移民文化与社会组织、劳动分工和社区组织结构关系及社会组织对移民心理的影响等社区融合议题也形成一批经典著作。在这一阶段,“空间”仅被视为社区内各种社会关系运行其间的自然既定处所,不同的社区作为特定的社会结构类型彼此独立且在各个空间上高度一致。[7]20世纪后期,以法国为代表的社会学者通过深入挖掘空间背后的权力、结构和关系内涵来理解居住区(grand ensemble)及其治理。居住空间、邻里空间、绿地等对邻里、教育及家庭结构演变都有明显的影响,不同群体在不同空间的使用行为上存在差异,由此可能产生社会隔离。该阶段研究旨趣的变化与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苏贾、卡斯特、哈维等人提出了成熟的空间社会学理论密不可分。这批田野成果开始聚焦空间背后的权力、结构关系,从而改变了城市社会学在区分了乡村和城市空间后思想上的贫困,并推动实现了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14](P35)
婴儿禁止使用酒精擦浴,没有表达能力的婴幼儿禁止使用冰枕。对发热的过度处理,可能增加宝宝身体的不适感,必要地给予物理和药物降温,有助于增加舒适感,但降温不宜太快。如在物理降温时,宝宝有痛苦烦躁甚至手脚发凉、全身发抖、口唇发紫等表现,须立即停止。
纵观上述研究,基于空间之维理解社区“乡—城”变迁已有破题,但尚存不足。
第二,空间在“国家—社会—市场”互动过程中被置于静态、被动地位。国家、社会和市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主体,三者的互动过程及互动结果形塑着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空间等同于“进入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资本主义通过城市化占有空间使其生产方式得以延续,商业主义和工业主义带来的城市化改变了空间特征。[20](PP326-383)空间本身已经变成商品,受资本、权力的争夺,成为可以买卖的抽象单位。[21](P437)空间的具体性质被压缩、差异性被简化,交换价值成了其外在的量化标准。在城市化进程中,空间与利润、权力、权利关系密切,形成国家、市场和社会成员对空间的竞争。[22](P115)空间的形式与过程包含依据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享有其利益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冲突的价值与策略所导致的矛盾。中国的“乡—城”空间转变则表现出更强烈的国家政权建设逻辑。国家的空间逻辑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以行政力量实现农民的搬迁。[23](P248)空间设计和使用首先满足土地需要而未充分考虑农民的需要。“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博弈形塑了新的社区公共空间。[24]发现并提炼空间背后的权力结构和互动关系是对社区研究的一大推进,但在这个过程中,空间被置于静态、被动的地位,其本身的能动性和反作用没有体现。社区的空间不是静止、外在的,而是内置于整个转型或博弈过程。“乡—城”变迁也是在特定空间中完成的,空间是变迁的要素和手段,有待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补充。
(二)空间研究中的三大困境
同时,锦鲤式营销利用的网络营销平台,大多为微博或者微信等社交网站,可以充分发挥病毒式营销的“让内容带来客户、让用户带来更多用户”的营销功能以及低成本、传播速度快的营销方式,最终有利于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
《一线》:外界认为O2O行业失败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此前服务业的标准化相对比较差,在58到家看来,现在到家服务业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乡—城”变迁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总体而言,中国学界对此存在两种不同判断:第一种可描述为“村落终结论”。传统村落在开放社会的趋势下,经济、自然、行政、文化等空间边界和乡土认同被全面动摇瓦解,因此传统村落共同体解体的时代已经到来。[15](P51)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村落作为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它的终结也意味着产权的重新界定和关系网络的“重组”。因此,在城镇化转型中,一些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展现了这一转型对传统网络进行改造和利用的“重组过程”。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学界形成了一批以城中村、棚户区、城郊村等为对象的经典个案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浙江村、广州城中村及上海棚户区研究等。学者们通过描述特定社区空间类型来呈现中国的乡—城社会互动及其变迁。“三元社会”、“二重社会”等概念的提出都反映了城乡关系在空间上的叠加。第二种可描述为“村落再生论”。学者在研究“超级村庄”时发现,在中国农村的非农化过程中此类村落的空间变得多元化,但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基本空间单位没有改变,城镇化反而强化了它的这一功能。[16](P51)现代化的侵入并未完全让传统村落解体,村落的共同体本质和社会网络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为其在不同层面的再生提供了机遇。[17]
第三,对以空间为基础的社区治理转型出路尚未进行充分的探讨。空间变迁与治理转型两个命题紧密相连。尽管社区治理、城市治理、区域治理、全球治理等具有明确主体定位的研究内容已经成为治理研究的主流,但需要强调的是学界对此仍没有给予空间足够的重视。[25]治理总是在特定空间中进行的,主要针对空间内存在的关系与问题。空间的具体形式与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冲突性已经挑战了既有的治理模式。[26]空间是治理的具体场景,因此空间本身就是权力、知识、主体运作的基本条件进而完成治理的过程。[27]中国的城市化及其规划已经成为一个对空间资源的使用和收益进行分配、协调的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28]可见,空间是探析乡城秩序变迁轨迹与治理转型路径的重要维度,传统以土地为基础的农村社区治理方式已经难以适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改制社区的空间格局。因此,面对“乡—城”社区空间变化,如何应对由此导致的秩序冲突并走向现代化治理之路还有待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关注。
三、“乡—城”变迁中的社区空间特征及社会意义
列斐伏尔将空间结构分为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与再现的空间三个要素,即空间的实在、构造和认知三个层面。他进一步解释,“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模式,包括物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其中社会空间是物质和精神空间的结合体。[29](PP170-173)
(一)空间的界定与组成结构
第二,新型现代化公共空间的崛起。城市化的进程改变了传统农村亲密无间的邻里格局,加快农村公共空间的式微乃至消失,以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管理中心为代表的新型现代化公共空间取而代之。第一,邻里空间变得界限明朗。传统农村作为熟人社会不仅仅是“熟悉”,更是“亲密”,其基础是“邻里”。在“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邻里人情连接下,传统村落空间被整合为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31]区块居住呈封闭性,邻里联系减少,彼此的边界清晰明朗,邻里沟通、支持功能减弱。空间变化导致邻里作为重要社会资本的维系功能降低,并进一步弱化社区互动和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第二,一站式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出现。在中国传统农村聚落中有诸多如戏台、寺庙、晒场、碾粉站等公共空间,村民在此聚集交流、传递信息并实现互助。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些传统公共空间多数消失了,城市社区为统一标准建造的一站式公共场馆和服务中心,满足了新居民社区参与、寓教于乐、活动健身、社区服务等系列需求。但这些新型的现代化服务场所短期内还难以承载传统公共空间基于集体记忆和历史沉淀而发挥的作用。走进社区服务中心,图书室、文化活动室等地方通常门庭冷落,可见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并没有匹配农民自身文化水平和沿袭的农村惯习。第三,远离“视线”的社区自治组织。另一个伴随撤村建居发生改变的公共空间是村委会,村委会往往处于村庄的中心具有醒目的标识度,一般居于村庄主干道交汇处具有较强的可及性。村民自治制度决定村干部产生的主要方式。村集体经济状况和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是影响村庄治理的两种关键资源,其中村干部个人能力本身是最重要的可变资源,并且可受监督。[32]而“撤村建居”后的居委会带有强烈的“规划”色彩,往往由多个村合并而成,受制场地和面积限制其办公用房很多都不在社区中心。由乡镇、街道安排或者选举出的新居委会行政倾向明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管理社区的行政成本,但由于熟人社会基础的缺失及过度规模化,使之运行的信息成本、交往成本极大攀升,由此也带来了居民对公共事务关心程度下降、社区参与感缺失等问题。
(二)空间结构的特征与社会意义
各地“撤村建居”社区在土地征迁和安置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在空间结构上却呈现出明显的共性。
第三,精神空间的理性化再造。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以特有的方式影响居民的行为和互动,而这种方式是最初的空间设计者未必考虑到的;个人又通过互动改变了现有的空间安排,并建构了新的空间来表达他们的欲求。[33]第一,代际关系呈现相对独立性。费孝通先生将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概括为“反馈模式”,即下一代与上一代之间形成“哺育与反哺”的双向伦理性平衡关系。[34]传统农村“几代同堂”的居住模式和空间条件也有助于代际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进行与共存。但居住空间形式和数量的变化使得父辈与子代多个核心家庭并立的代际居住模式成为可能,由此打破了代际空间既有的生产逻辑。一方面,分居的过程就是分家的过程,在代际之间形成相对独立的张力容纳空间,有助于形成权责明确、平等协商的代际关系,代际交往趋于理性化。另一方面,居住分离也易产生代际隔离,降低了父辈对子代的依附程度,赡养责任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之间得以分摊,父辈的情感需求与子代的投入趋于低度平衡。第二,角色认知呈现交叉性。从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而言,“撤村建居”社区已经告别农村趋近城市,社区成员的身份已经变为市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角色认知上也已经成为真正的市民。他们在精神空间的各个方面都处于过渡和调适阶段,而这个周期因外在因素与自身条件的不同而不同。部分居民已经适应新空间并逐渐完成市民化,但也有相当居民仍保持农民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或者两者交叉。第三,社区交往呈现工具性。空间的变换影响了人们之间的互动和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居住空间距离增大的过程中,邻里联系减少,邻里沟通、支持功能减弱,原邻里关系这一重要社会资本难以维持。但新居住空间也扩大了居民的交往界面,新的邻里关系和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公共参与机会。原本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情感性交往空间被以业缘、趣缘为纽带的工具性、社会化交往所取代。
参照列斐伏尔“空间三元组合概念”,本研究中社区的“空间”是指在“乡—城”变迁过程中社区内各种社会关系变迁的产物和体现,既在纵向上反映了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总体性空间变迁,也在横向上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三个维度体现了社区“乡—城”的动态变化。地理空间属于空间的实践,主要包括居住空间、公共绿地、网格单元等物理场所。社会空间属于空间的再现,主要包括邻里空间、服务交往空间、自治组织空间等社会交往媒介。精神空间则属于“再现的空间”,主要指涉社区居民在转型过程中呈现的代际认同、身份认同和社区认同,它既受制于也反作用于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区别于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两类总体性社区空间样态,“撤村建居”社区是国家城镇化背景下兴起的新类型,处于“乡—城”变迁的连续统之中。以三种形式存在的多维度空间在分割、流动和整合过程中又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格局,对社区的社会秩序和结构方式进行着再生产。
第一,“空间”被简化为“城—乡”或“社会—共同体”的二元既定概念。正如Soja所言,早期研究多将社区“空间”笼统地划分为“城”或“乡”两种社区类型,它们彼此独立且在各个空间高度一致。关于农村瓦解或复兴的讨论也始终摇摆在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中,以城市为归宿的单向度发展是理解农村变迁的一条主轴。[18](P250)该传统在早期西方“乡—城”变迁研究以及国内“村落终结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到来,学界在后期逐渐形成了基于农业变迁研究转化而来的“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框架来理解乡城变迁及城乡差异的视角。[19]该视角批判城乡二元分立,认为变迁应该处于城乡连续体之中。伴随全球经济转型和社会重组,乡村由于城市通勤、休闲商品化、工业化等驱动使农村和农业的功能朝多样化发展,从而实现了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的转型。这与持“村落再生论”的学者有共同之处,但问题在于“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框架仍属于宏大叙事,并未进一步从微观机理上破除城乡二元分立的困境,也没有提炼出城市化背景下“乡—城”转型的社区如何实现空间连续发展的中间机制或路径。已有研究由于并未对“空间”进行概念操作化而使之仅仅成为“社区”的另一代名词,没有揭示空间的样态差异与实践意义。
第一,地理空间标准化设置。与传统农村相比,地理空间的标准化和立体化是“撤村建居”社区的显著特征。第一,居住空间垂直集中。空间布局和房屋的建筑形式经历了从传统农村的风格各异、不规则、散点状向相对立体化、垂直的集中单元格结构转变。平面、开放性极强的独立院落被整齐的区块和立体的高楼取代,居住空间的内部开放性降低,成为多个相对封闭叠加单元格中的具体组成。集中居住的实现方式通常采用减少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和置换建设用地指标,高层单元可以安置更高密度更大规模的居民数量。置换的动力来源于国家获得更多的建设用地,农户也拥有了多套住房。居住空间的变化既是“乡—城”迁移和空间集聚的过程,也是农民转变为居民进行社会重组的过程。土地对于农民与农村来说是可持续生计的生产资料,只要农民手中有土地通常情况下他们就可以自给自足以满足基本需要。第二,公共绿地从生计变为景观。绿地和花园被认为是城市精神的重要体现。[30](P477)“撤村建居”社区普遍有较高的绿化率和景观设施,但并非所有绿地都能按照设计初衷成为“城市精神”的体现。农民对作为生计的土地理性主义使用倾向明显,而对绿地景观式、付费管理的使用方式短期内难以认同。第三,网格管理单元标准化。村民小组是农村最小的组织单位,在原生产大队的基础上建立村民委员会,在原生产小队的基础上设立村民小组协助村委会开展工作。村民小组涉及发包土地、社区服务、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村民小组集体资产管理、协助征兵和发放国家补贴救助资金等事项。因此,村民小组是村民天然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村民进行利益表达的直接平台。“撤村建居”后,属地政府打破村民小组的设置方式,将社区作为管理辖区按一定常住人口数量的标准划分为标准化单元网格,并对网格范围内的人、地、事、物等进行全面的信息采集和管理。
精准举措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在全面摸清摸透贫困村、贫困户基本信息的基础上,大力整合多方资金,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充分依托贫困群众现有资源和自身优势“开方子”,以“十大工程”为抓手,突出产业扶贫、安居扶贫、保障扶贫三大工程,让“项目资金跟着穷人走”,把“血液”输到“静脉”,有效激活贫困群众的自我“造血”功能。
四、迈向以空间为基础的治理转型与秩序重建
空间维度是窥探治理转型的重要密码。[35]“撤村建居”社区这一新的城市空间被生产出来,但与管辖主体的“乡—城”变化及农民户籍性质的转变相比,更重要的是上述空间结构的变化与其呈现的特征和社会意义,并由之对社区治理转型与秩序重建所带来的挑战。空间变革易引发转型不适,难以顺利实现城市化和市民化的目标,甚至长期处于“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对于基层政府,还是对于“撤村建居”的新居民而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尽快重建社区生活的新秩序,并认同、适应社区新的基层组织系统及运行方式,而这种治理转型与秩序重建也正是在正视并积极应对空间变化中形成的。
(一)治理转型中的空间挑战与约束
“撤村建居”社区的空间结构特征变化使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并由此带来新的治理问题,对社区治理的主体、单元、网络、范围和机制等均形成挑战和冲突。目前,“撤村建居”社区虽然在积极通过推行网格化管理、物业、社区服务中心的建立等制度化模式和策略,进行新的社区空间诠释与治理架构的更新,但尚未打破空间分割、空间生产和管理、空间权益配置中存在的约束壁垒。治理转型中的空间挑战和约束集中表现在:第一,从相对封闭的传统村落转向开放的城市异质空间对治理主体提出了新要求。从村委会到居委会的转变不仅仅是牌子和名称的更替,社区的组织结构、管理主体、干部队伍以及相应职能范围的调整都面临挑战。城市空间异质程度和流动性极高,必然要求社区和社区干部向社会化、专业化转变。第二,标准化通用性的网格设置打破了以村民小组为基础的治理单元。调整和确立治理单元是现代治理的重要策略。[36]将社区划分为一个个平行、单一和相对同质的网格,并发展出“政府—社区—网格—居民”的纵向管理体系,表面上实现了行政监控技术和复杂多样化社会的低成本匹配,但也丧失了传统“村民小组”天然的自治优势,反而不利于社区新旧治理机制的自然过渡与良性衔接。第三,从水平分散到统一集中的居住模式改变家庭邻里结构从而破坏治理网络。社会资本在最初的阶段被赋予了集体性特征,邻里初级群体是形成集体的重要形式。[37]居住空间的变化使邻里社会资本流失,也使社区治理网络断裂。第四,以土地、村籍、集体经济为边界的治理范围被打破从而加剧治理的复杂性。土地、村籍、集体经济作为传统村庄代表性的边界具有相当稳定性,“撤村建居”过程中多村合并及外地人的大量涌入重塑了村庄传统意义的空间边界。原有的边界与新社区的治理范围之间产生张力必然会加剧社区治理的复杂性,但这也是社区变迁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难题,即超越传统边界重建更广泛意义上的社区自治和公共能力。第五,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建设逻辑与原村庄自下而上的治理机制形成冲突。如前所述,中国的城镇化带有明显的“国家主导”色彩,既表现在城镇化的推进动力上,也体现在“撤村建居”后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上。在“拆—建—治”的完整径路中,多种类型的行动者参与其中。各类行动者都有自己依托所属空间而袭得并传承的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机制。作为尚未定型的新生社区,政府行政主导的建设逻辑与原村庄及村民自下而上的自治机制仍处于互动博弈的过程中,因此,社区治理机制的成熟必然要通过两种逻辑相互协商与融合以避免冲突的形成。
(二)空间视角下的治理转型方向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地域迁移、社区的空间变迁与基层社会的治理转型几乎同时发生。空间不但是“人与事的聚合体”具体呈现的场所,同时也是探析治理知识成长的重要标准。[38]城乡不同空间下的发展失衡、隔离分化、断裂失序都是当前城市化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撤村建居”本质是人的生存和交往空间从农村转向城市,并形成适应城市空间的社区治理体系过程。将社区“乡—城”变迁置于传统农村空间消解、新型城市空间建构、新旧空间交融的视野,撤村建居社区治理转型应从革新社区组织架构,厘清各个治理主体的职责分工,整合网格与原村民小组治理网络推动单元治理效应最大化,发展社会组织培育包容多元的社会化服务力量,加速现代产权治理改革实现生产和生活的有效分离,构建协商共治机制以维护和保障各方空间权益等方面入手。“撤村建居”社区通过基于空间的治理转型,一方面,面对农村传统空间的式微与消亡,依然能够有效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失范”危机,维系社区共同体的整合功能;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乡—城”过渡中的新型社区,又能突破空间的约束逐步构建起现代城市基层治理格局。
她在郊区找了份幼教的工作,其实就是教那些打工者的孩子们。星期天的时候她打车往市里去,找老乡聊天,或者盲无目的地瞎转。半年后她所在的幼儿园忽然办不下去了,幼儿园的一个学生出了事,家长闹得厉害,幼儿园被当地的管理部门查封了。她在广州瞎撞,想再试图找一份合适的工做,她的手里紧紧地攥着在幼儿园里挣来的几千块钱,她狠狠心报了个电脑设计班,这使她后来有了一份结业证书,后来她在广州又辗转干了将近一年的排版设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Chan,Kam-Wing.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M].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3]国务院: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城镇化问题[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2-06/7751517.shtml
[4]吴莹.上楼之后:村改居社区的组织再造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5]轩明飞.村(居)改制:城市化背景下的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6]陈映芳.中国城市的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7]Soja ,Edward.Postmodern geographies: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M].London:Verso,1989.
[8]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0]帕克、伯吉斯、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M].宋俊岭、郑也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1]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 Smith.Malden:Blackwell,1991.
[12]Cloke,P. Country backwater to virtual village?:rural studies and “the cultural turn” [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97(13)
[13]Cloke,P.& N.Thrift.“Class and change in rural Britain.” In T.Marsden,P.Lowe & S.Whatmore.Rural restructuring:global processes and their responses [M].London:Fulton,1990.
[14]何雪松.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J].社会,2006(2).
[15]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6]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7]文军、吴越菲.流失“村民”的村落: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基于15个典型村落的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7(4).
[18]B.Koppel.,J.Hawkins & W.James.Development or deterioration?:work in rural Asia[M].Boulder,Col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4.
[19]Evans,N.,C.Morris & M.Winter.Conceptualizing agriculture:a critique of post-productivism as the new orthodoxy[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2(26).
[20]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 Smith.Malden:Blackwell,1991.
[21]芒福德、刘易斯.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2]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 Smith.Malden:Blackwell,1991.
[23]施芸卿.再造城民:旧城改造与都市运动中的国家与个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4]艾云、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民众抗争形式:一个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J].社会学评论,2017(4).
[25]陈晓彤、杨雪冬.空间、城镇化与治理变革[J].探索与争鸣,2013(11).
[26]Castells,M.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M].London:Blackwell,2000.
[27]Foucault,M.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 [M].London:Allen Lane,1997.
[28]张京祥、陈浩.空间治理:中国城乡规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J].城市规划,2014(11).
[29]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 Smith.Malden:Blackwell,1991.
[30]芒福德.城市文化[M].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31]陈柏峰.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EB/OL].http://www.snzg.cn/article/2011/0616/article_24439.html
[32]贺雪峰、何包钢.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型态——尝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J].江海学刊,2002(6).
[33]司敏.社会空间视角: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J].社会,2004(5).
[34]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
[35]茹婧、杨发祥.迈向空间正义的国家治理:基于福柯治理理论的谱系学分析[J].探索,2015(5).
[36]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
[37]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8(3).
[38]Foucault,M.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Cours au College de France( 1977-1978)[M].Paris:Gallimard,2004.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43(2019)02-0058-007
作者:郎晓波,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文化学与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农民市民化与城市社区治理。邮编:3100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撤村建居’社区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研究”(18BSH05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黄鹏进)
标签:空间论文; 社区论文; 社会论文; 城镇化论文; 城市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撤村建居’社区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研究”(18BSH058)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文化学与社会学教研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