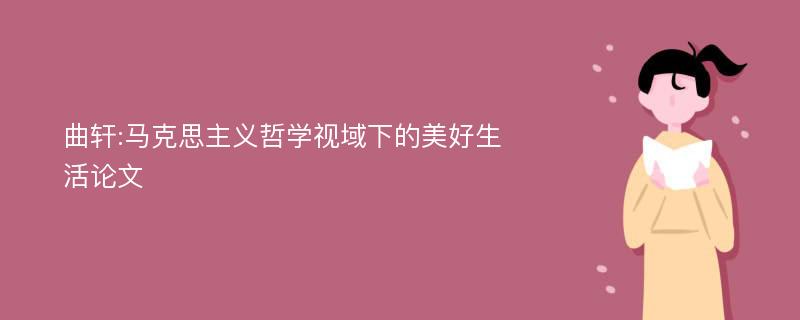
[摘 要]古希腊以来关于美好生活的哲学之旅以其不同的理解图景,为处理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不同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体现在共产主义的图景之中,并且依托于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指向更美好的人类社会。它所蕴含的独特意蕴在于:“自由人联合体”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解决;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统一;共产主义社会对个人发展丰富性的强调。
[关键词]美好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共产主义
长期以来,何谓美好生活都是政治哲学乃至哲学追问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好生活的哲学之旅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理解图景,并且在此过程中提出了为实现美好生活所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帕帕国没有学校,整个帕帕国就是一个大学校。孩子们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自己的职业,有的当军人,有的当司机,有的当老师,有的当科学家……完全实行自治。虽然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肤色,但是他们友好相处,互相帮助,比在大人身边生活快乐、自由多了。遇到一些连总统也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就到“勇敢城”去找一台名叫“三瓣蜗牛”的大计算机。三瓣蜗牛的体积有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那么大,外形像三只脑袋挤在一起的大蜗牛。它被放置在一个全是用金刚石做的、透明的、半球形的基地里面。基地的名字叫“三瓣蜗牛基地”。孩子们有了问题找三瓣蜗牛准能解决,另外,三瓣蜗牛还负责了整个帕帕国的安全。
一、美好生活的哲学之旅
众所周知,哲学乃爱智之学。古希腊自苏格拉底把哲学的关注点由天上拉回人间、从外部自然转向人类自身之后,能否过上美好生活与智慧和知识的获得直接相关。由此,获得某种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成为过上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对客观上何谓美好生活的追问——尤其是对明辨是非善恶的追索,逐渐成为哲学的一个显题。
柏拉图的理想国所隐含的美好生活,是理性善治的政治生活。他承继了苏格拉底以“美德即知识”为底色的伦理关怀,并将其贯彻在《理想国》对“正义”的追求及其对历史上第一个乌托邦的建构中,美好生活由此指向以理性可知可辨的客观的善为支撑的政治共同体。柏拉图虽然承认“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国家”[1]612,但他仍坚持认为,理想国已然包含传统哲学孜孜以求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意涵。亚里士多德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因将法律排除在外而造成的经验描述层面上的欠缺,从而因其能更加正视现实呈现的复杂性,而在一定程度上把理想国作为美好生活的模型由天城拉回世间。[2]104,135[3]166
遗憾的是,当时的社会现状没能给予古希腊哲人更多的机会来实现上述城邦政治的理想所蕴含的美好生活,人们在继之而来的希腊化时代放弃了城邦政治,转而追求个人自足和私人幸福以实现美好生活。这一转向充分体现在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学说中。伊壁鸠鲁强调快乐即幸福,并且认为苦乐都是周遭世界给个人带来的自然感受,因此而区别于理性对真理的追寻。[4]207这种自然主义的内涵后来成为霍布斯契约论的内在助力,甚至也蕴含着边沁效益主义的萌芽。由此,作为美好生活之根本的道德的善进一步带有脱离其普遍性和绝对性意涵的倾向,而与其现实效果的利弊得失直接相关。
最后,共产主义终究是一种“现实的运动”,它对美好生活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不仅意味着美好生活不是由意识形态所虚构出来的抽象概念或空洞遐想,也不仅因为它的实现离不开现实所提供的上述物质前提和社会基础,而且还意味着其具体的实现路径是永远向现实开放的,因而是多元的、依据变化的现实需要得到不断调整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马克思晚年结合俄国公社对唯物史观的反思中,如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里,他就极力反对不顾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环境而将其作为“一把万能钥匙”套用于一切民族[11]467,并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明确把自己所证成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11]589。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运动性也不仅限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革命性和颠覆性,而且还意味着其所指向的美好生活蕴含不断向“更好”发展的内在趋向。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对美好生活的实现不是一个静态的终点,即人类理性思考或想象力之所能及的“最好的”生活,否则它就与那些以超验的、超历史的道德理想为基础的因而沦为空想的社会理想无异。相反,它是源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一个永远在路上的动态发展过程,它的实现既需要经历社会主义作为其初级阶段的“一个极其艰难而又漫长的”[9]232过渡过程,又包含着继续走向“更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内在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9]197[12]8,65
(3)股权划拨方式。这是指将某些金融机构以股权划拨方式划至大型企业集团名下,使得该企业集团能够迅速进入金融业务领域,完善该企业集团的金融体系,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促进企业自身的机构改革以及金融机构的改革。
直到近代个人主义的兴起,伊壁鸠鲁主义所蕴含的契约论和效益主义萌芽才真正孕育而成。霍布斯将契约论直接奠基于个人的自然本性对安全的需求之上,从而使美好生活依存于一种理性建构的规则和秩序之中。这种理性的规则和秩序由于奠基于对抽象个人的设想,在现实中展开的是自然状态下的丛林状态,即人们彼此势均力敌的野蛮状态,“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因此美好生活的实现首先需要通过强力国家来“重建均势”以保全生命。[6]144个人在自利—自保的本能欲望的驱动下,一方面作为非政治性的自足整体而存在,另一方面又因个体安全之需而在理性的支撑下达成契约,普遍同意把社会交由利维坦来维持秩序。洛克虽然强调了政府在通往美好生活的契约精神中的重要性,但他不仅没有动摇个人主义的立场,反而更加突出政府公共权力在促进个人美好生活过程中的限度意识。
类似地,基于道德价值或宗教信仰的共同体也因其空想性而应被排除于实现美好生活的共产主义的共同体形式之外。如对以道德价值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普遍的人类之爱了。”[9]590对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斥责道:“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10]56;尽管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中不乏“批判的成分”,但它们仍然“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10]63-64。
其次,就“现有的前提”而言,共产主义对美好生活的实现有赖于市民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前提及其对传统社会关系的改造。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对以往美好生活设想的理想性及其抽象性展开彻底批判,源于他们将美好生活奠基于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之上。这一实实在在的基础不仅使具有个体意识的个人成为具体的现实的个人,而且使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依据暴露出来。因此他们才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力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0]36的确,如果没有市民社会所集聚的这种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交往”就无法冲破传统家庭、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桎梏,成为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不仅如此,甚至还会导致“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538。可见,市民社会的发展为共产主义对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然而,不论是古希腊将个人裹挟其中的道德理想和城邦政治,还是中世纪寄托于彼岸精神世界的上帝之城,抑或是近代个人意识觉醒以来依托社会契约对理想政治国家的重构,其中勾勒的美好生活图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都难掩其抽象本质。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美好生活,人们很容易想到共产主义社会。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为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提供某种具象化的描绘,但很明确的是,“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9]539。
可见,随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问在哲学之旅中的不断推进,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影随形,并且逐渐成为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凸显出来,尤其是在近代个人意识觉醒以来,要实现美好生活就不得不正视其所包含的难以折衷的复杂性。
二、共产主义对美好生活的批判性诠释
不过,个人主义立场在哲学对美好生活的追问中没有销声匿迹,效益主义就力图证成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美好生活。它明确以趋乐避苦作为人的惟一动机,进而以其“有关道德、政治和经济的价值论取代了自然法理论所追求的内在善的理性标准”[6]226,最终,它所主张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仍然以绝对平等的个人为基本单位。尽管约翰·穆勒后来又增加了对“效益”之质的区分,通过“幸福”与“快乐”之间的对比,为个人幸福增添了道德共同体的理想成分,并指出“功利主义的行为标准并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8]12;但从根本上说,其自由主义的个人立场是更为基础的,因为幸福生活最终的实体承载者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存在。
(1)随着对SO2排放限制越来越苛刻,硫磺装置在开停工过程中SO2排放同样有严格限制,仍需要达标排放。在目前情况下,仅仅靠优化工艺、高效催化剂和高效溶剂仍无法实现开停工或紧急情况下的达标排放,需要增加其它手段把关,如后碱洗工艺等,以实现SO2达标排放。
首先,这意味着并非任何共同体都是共产主义实现美好生活的有效形式。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了通过政治国家来实现美好生活的局限性,这一批判同时揭露了霍布斯、卢梭以及约翰·穆勒的美好生活图景所蕴含的抽象本质。具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实际上无异于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9]30。但对这种市民社会状态的超越却无法通过霍布斯式的政治国家来实现,因为正是市民社会中的物质关系决定了国家而非相反。或言之,以市民社会原子式的利己主义个人为前提和基础的政治国家必然是空洞的、抽象的,它也只能赋予政治人以空洞的、抽象的权利形式,因此徒有政治革命和解放不可能走向美好生活。这样看来,不仅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政治人和政治国家没有摆脱这种抽象意义上的个人及其联合体,约翰·穆勒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绝对的消极自由,也正如平等、安全、财产等其他所谓的人权一样,无不因市民社会中人的私有财产关系和利己主义本质而走向各自的反面。[9]40-43,46,574马克思基于对政治解放图景下的美好生活的批判直言道:“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9]46
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些干部来源本身就不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他们均是政府任命的,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这样的体制不仅不利于职业经理人的合理配置,也容易使企业管理蒙上过重的政治色彩而失去应有的活力。
“先生,请点餐。”服务生把食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关切地说,“您看起来有些疲倦啊!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
1.“重大轻小、重国轻民”。银行机构信贷投放仍侧重于大企业、大平台和房地产行业,而民营、小微企业贷款由于金额少、频度高,且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情况难以掌握,贷款管理成本高,对民营和小微企业采取“少贷少错”的做法。
在契约论传统中,卢梭从个人主义的立场中解放出来,使对美好生活的实现依托于以“公意”为基础的道德共同体。在他看来,社会在本体论上是先于个人及其权利而存在的,因为个体被赋予的幸福欲求、自利冲动和财产权利观念以及订立契约等诸多能力,都无一不是从社会中获得的,社会所共有的语言、利益甚至幸福“并不是私人利益的总和,而是其渊源”[6]271。他进而认为,社会因其固有的一种集体道德意识即“公意”,而在道德人格上成为独立自足的共同体整体,人们的美好生活必然要凭借这种道德凝聚力来实现。[7]21,25,131
再次,这种生产力的大发展进一步为实现美好生活提出了“消灭现存状况”的要求,即要求超越脱离共同利益的庸俗狭隘的私人利益共同体。尽管冲破种种传统束缚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较之从前饱含了现代性精神,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0]37。进言之,市民社会所促成的生产力的大发展要求真正的普遍交往关系,但其“现存状况”却是以私有财产或私人利益关系为基础的虚伪的普遍交往关系,因其主体范围“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9]41。这种状态下的个人看似独立自主,实则陷入对物普遍的依赖之中;社会整体在表面上看起来欣欣向荣,然而维系彼此的只是庸俗狭隘的利益诉求。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包含内在固有矛盾的社会状态,不仅凭借自身无力消解由其发展所带来的内在矛盾,而且由此提出了被超越的必要性。由于市民社会的核心是私有财产关系,而私有财产所反映的是异化劳动的本质,如此一来,共产主义要“消灭现存状况”,就是要超越被资本主义制度化的私有财产关系,也即通过共同劳动取代雇佣劳动从而使劳动摆脱异化。或言之,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美好生活即以摆脱异化的共同劳动为基础,实现个人充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生活。
不过,不断趋向现实体验并非希腊化时代哲学的唯一走向,中世纪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更多沿承的是斯多葛主义通过突出理性、规避自私性所铸就的宗教性。最终,对美好生活和幸福完满的向往充满神性,并被寄托于与尘世相对而立的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强调,幸福的生活是公义的、永久的,幸福的人是正直的、永生的,并且“绝对不会犯错误”[5]493。遵照《圣经·诗篇》,他进而指出:“使人幸福的,不是人自身,而是人之上的东西……上帝就是人的幸福生命。”[5]531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所蕴含的对非人格的超人力量的信奉、顺从和依附,使得人相对于神而言的具有普遍性的类意识更为凸显,人性由此成为所有人所普遍共有的。这意味着从横向来看,包括奴隶、外邦人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平等的权利意识而非强力的权力意识进一步推广并得到增强;而从纵向来看,理性再次凸显并成为贯通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甚至人与上帝的根本力量,不仅使差异免于形成狭隘的对立,而且使平等概念也包含有抽象意味。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美好生活的意蕴
尽管面对美好生活的哲学之旅所留下的思考轨迹,共产主义没有给出人们对美好生活追问的终极之解,但其上述批判性阐释无疑彰显出美好生活追求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别样意蕴。
其一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对共同体与个人之间关系问题的解答。对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美好生活的实现离不开共同体,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9]571。他们进而明确指出,超越并替代资本主义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53。这是由于这种共同体的基础——共同劳动作为“第一需要”,已经成为个人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之所需,因此,参与其中的个人不仅可以不再因受制于普遍至善的道德原则而理所当然地隶属于城邦共同体,进而丧失个体自身的独立自足性;而且可以不再作为子民心悦诚服地拜倒于上帝面前,充斥着对纯粹的精神生活和彼岸世界的向往;更重要的是,人们也不再迫于生存需要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进而作为无产阶级成员集体性地陷入共同体的剥削关系中,遭受制度性的剥削。相反,在共产主义以共同劳动为基础的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9]573。
而上述联合体之所以能够恢复共同体与个人之间自然的依存关系,结束共同体对个人的吞噬状态甚或个人利益对共同体利益的裹挟状态,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其中的个人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抽象个人,而是物质生产关系中具体而现实的个人。[13]98-113这就完全不同于以往哲学家基于道德理想、宗教信仰抑或政治本能的对人的理解,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个人与共同体之间貌似坚不可摧、实则抽象无力的纽带。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不仅是满足个人生理需要的方式,而且“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9]520。因此,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个人首先是基于生产而自足存在的个人,在此前提下,个人之间的自由联合才成为个人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
其二,唯物史观下的美好生活是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唯物史观对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强调,使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回到人间现世。具言之,以往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要么寄托于政治国家的各种善治理念中,要么建基于崇高至善的道德信念之上,甚或直接被视为脱离物质生产、鄙视世俗生活的一种精神生活。尽管这些美好生活的图景都以各自的维度呈现出何为“美好”的价值向度,但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它们皆因忽视了社会生产的基础性作用而在其合理性的现实意义上大打折扣。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的诞生地恰恰在于“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9]351,因为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就是为了生活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9]525。不论是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还是其他形式的美好价值追求,作为人类意识的观念形态,都离不开个人从事现实的物质生产的生活。不能因为生活包含对“美好”价值的向往而使其脱离这一历史事实,否则,这些“美好”就会因其丧失实现它们的现实基础而沦为意识形态的虚伪说辞,甚或搁浅于无根的彼岸世界。
另一方面,唯物史观对掩盖在意识形态迷雾之下的物质生产的强调,决不意味着这一基础性作用能够对一般的思想意识及其所凝聚的精神财富的价值和作用的否定或替代。针对庸俗粗陋的“经济决定论”的误解,恩格斯曾在致布洛赫的信中加以澄清:“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4]591。其中的“上层建筑”就包括政治、法律、宗教、道德、哲学、艺术等人类创造出来的各种形式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也对其相对独立性直言不讳,他以艺术为例写道:“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5]34由于唯物史观所指明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参与其中的一个物质与精神之间复杂的互动体系,而绝非仅有物质力量或者经济基础就能自足成立的,因此偏废物质或精神的任何一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美好生活的误解。
其三,对生产关系中具体而现实的个人精神层面的观照,也预示着美好生活应该包含个人多向度的全面发展,而不仅只是局限于或者停留在对人在动物性、政治性抑或经济性等不同层面的需求的片面满足之上。当然不可否认,满足动物性本能的需求仍然是生存的首要条件,不过,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9]160而他之所以要对资本主义现实展开彻底批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劳动的异化正在把人们原本丰富的类生活抽象为满足肉欲本能的机械活动,由资本主宰的世界正在把人的物欲无限放大,以至于“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也就是,“你越是少吃,少喝,少买书,少去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餐馆,少思考,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积攒的就越多……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多”。[9]226-227相反,“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9]537。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要实现的美好生活,就是要使人们真正回归社会及其所带来的类本质的丰富性,进而摆脱社会与个人单向度发展的恶性循环。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6]9的确,随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以及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足以概括人们日益得到丰富和拓展的现实需要,以对“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满足为前提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失为一个更妥贴的表达,这也印证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对未来人与社会多向度的全面发展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美好生活兼顾了个人与共同体、物质与精神等方面,无疑可以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参 考 文 献]
[1] [古希腊]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2卷)[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 [美]乔治·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上卷)[M]. 托马斯·索尔森修订,邓正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 [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 政治哲学史[M]. 李天然,等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4] David Furley ed. RoutledgeHistoryofPhilosophy (Volume II) [M]. London and NY:Rougledge,1999.
[5] 赵敦华,傅乐安. 中世纪哲学(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6] [美]乔治·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下卷)[M].托马斯·索尔森修订,邓正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 [法]让-雅克·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 [英]约翰·穆勒. 功利主义[M]. 徐大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摘编(英汉对照)[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3] [美]卡罗尔·C.古尔德. 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M]. 王虎学,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An Interpretation of A Good Life in the View of Marxist Philosophy
QUXuan
(The Fourth Research Department,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32, China)
Abstract: Since ancient Greece, the philosophical journey about a good life, with it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has provided different solutions for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Marx and Engels’ demand for a good life, embodied in their prospect of communism, relying on the association of free individuals, refers to a “better human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The distinctive significances of “a good life” in the view of Marxist philosophy are implied as follows: (1) the association of free individuals sorts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2)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rganically combines the material and the spirit; (3) the communist society underlines the richness of the individual development.
Keywords: a good life; Marxist philosophy; communism
[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9)02-0037-07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9.02.005
[收稿日期]2018-11-10
[基金项目]中央编译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美好生活”(17C10)
[作者简介]曲轩(1988-),女,山西大同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在站博士后,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李长成]
标签:美好生活论文; 马克思论文; 恩格斯论文; 社会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央编译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美好生活”(17C10)论文;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