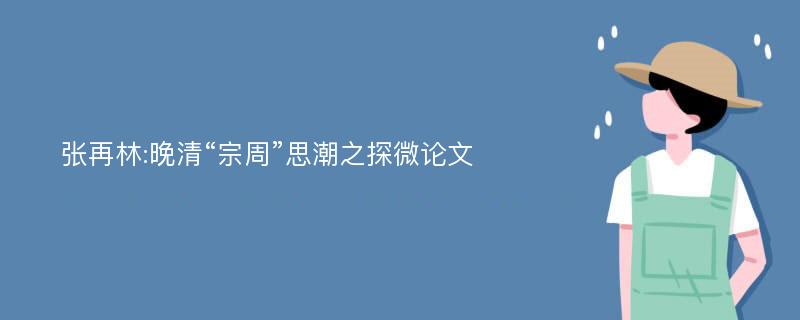
内容提要晚清维新派的“宗周”思潮无疑是近现代中国极其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该思潮是以回归“周礼”为其真正的旨趣。一种历史的全新语境决定了,晚清维新派旨在回归的“周礼”,与其说是后儒所鼓倡的作为等级秩序的周礼,不如说是原儒所仰慕的作为双向对等交往的周礼。对于维新主义者来说,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才是礼之所以为礼的最终皈依。无疑,这种别有新意的复礼思想,不仅为终结既有的清朝的政治统治提供了自己“内源性”的理论依据,也从中使一种冲决一切网罗的人类“无限交往共同体”的社会理想得以坚实地确立,并最终为今天中国积极走向全球化、互联网化时代奠定了自身根基。
关键词晚清宗周思潮 周礼 人类无限交往共同体
正值中西相颉颃之世,晚清波涛汹涌的时论之风,一变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再变为维新派西学的“本末一贯”“体用相承”。与这种新变化相偕而来的,则是由西返中的“以古国之古证西来之新”。而其中的一种“宗周”思潮也正是在此新理论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门椒开始膨大时追1次肥,每667平方米追复合肥15千克、钾肥10千克,或结合浇水进行冲施复合肥15千克,加尿素15千克,也可用腐熟的人粪尿1000千克。每次追肥都要浇水,后期根据长势进行追肥,隔1水追1次肥,同时结合喷药可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或其他叶面肥,隔10天喷1次。
晚清“宗周”思潮
无疑,晚清“宗周”思潮显属晚清“回到三代”的思潮之一。然而,就该“宗周”思潮明确地回归周的“礼乐政教”,并通过这种回归“援古以师西”,为维新寻找更为坚实的本土依据而言,它却不能不使自身在那种大而无当的“回到三代”思潮中显得别有新意和独树一帜。
论及这种“宗周”思潮,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可视为其真正的先驱。他所谓“孔子拨乱生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孔子改制考》)这一“托古改制”观点的推出就将其“宗周”思想表露无遗。康有为如此,其他维新人士亦不遑多让,遂使言必周礼、言必周制成为晚清维新浪潮中一大气象。如曾纪泽曾指出“西人政教多与周礼相合”(《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黄遵宪认为西人“实则设官多本于《周礼》”,①郑观应指出“西礼之暗合乎中国古礼之遗意也”(《盛世危言·典礼上》),薛福成宣称“若夫夏、商、周之世,虽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意诸国君民共主之政乎?”②梁启超则以《周易》“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周官》“朝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证西议院之义(《古议院考》)。此外,冯桂芬不仅以所谓“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借天合以维系之,而其合也弥固”为由主张回到周人的“君之宗之”的宗法制(《校邠庐抗议·复宗法议》),而且还考之周制,力倡恢复周人的乡人任职之古制,以期建立自足的地方自治组织,乃至由此使其获得了“近代中国提倡地方自治的第一人”的称誉(《校邠庐抗议·复乡职议》)。在这方面,作为晚清维新思想巨擘的王韬走得更远。他不仅明言“然则华夷之辩,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弢园文录外编卷十·华夷辩》),而以周人所重的“礼”为基准彻底颠覆了国人长期冥顽不化的“华夷之辩”,而且还从“《诗》始《关雎》,《易》首乾坤”这一古老的周文明出发,提出“平治之端,必自齐家始。欲家之齐,则妇惟一夫,夫惟一妇,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故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先自一夫一妇始”(《弢园文録外编卷一·原人》),从而既弘扬了“泰西诸国于夫妇一伦为独厚”的现代人伦观,又揆之元典地使后儒的独尊父子之见彻底流于欺世之谎言。
从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紫云看到了阳光。房子是新的,丈夫特别疼爱她,生活比蜜还甜。林志特别会疼人,不让妻子做任何家务。做饭、洗衣服,他都包了。
在晚清议论涛涛的“宗周”思潮中,尤值得一提的是郭嵩焘的观点。这不仅由于他遍历泰西、睹其国并观其政的经历所造就的特有的中西通观的视野,还由于该视野与本人深厚的国学学养的结合而形成的其自诩为“所及见透顶”的思想特点。这使他的观点既跳出了顽固派的井蛙之见,又与不无新潮的“西学中源”论者的见解相距甚远,而深谙人类普世性公理之大本大端。
(2)经济效益显著,该井在不防砂的条件下应用该工艺实现了稠油(原油黏度6.3Pa·s)冷采生产,且不需要电热杆辅助降黏措施,极大地降低了能耗。
正如他的亲戚李翰章“居今稽古,学礼从周,正士大夫所宜究心者”(《郭嵩焘先生年谱》)这一观点所说,对于郭嵩焘而言,周人所创制的“礼”恰恰就是人类普世性公理之大本大端。因此,一方面,郭嵩焘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日益衰败,就在于其于“礼”渐行渐远。如他谓“圣人制礼缘人情,制律亦缘人情。今之治律者,务使人情郁而不宣,逆而不畅,其于律意远矣。”(《郭嵩焘日记》一)。另一方面,郭嵩焘又认为,观当今之世,反倒是那些素被目为“蛮夷”的泰西民族却“以礼义为教”,其文明却更近乎“礼”义。故他看到英议院辩论是非均无不付之公论时写道:“《周礼》之讯群臣,讯万民,亦此意也”(《伦敦与巴黎日记》);又,他在受英王室之邀参加白金汉宫的舞会后写道:“男女杂沓,连臂跳舞,而皆着朝服临之。西洋风俗,有万不可解者。自外宫门以达内厅,卫士植立,皆有常度,无搀越者。跳舞会动至达旦,嬉游之中,规矩仍自秩然。其诸太子及德国太子,皆与跳舞之列。以中国礼法论之,近于荒矣。而其风教实远胜中国,从未越礼犯常,正坐猜嫌计较之私实较少也”(《郭嵩焘日记》三)。再联系即使是清廷“极顽固之旧派”的刘锡鸿亦在赴英时所留下的某公爵夫人会见华使“坐谈良久”,而身为侯爵的儿子却一直“立侍其旁,无倦容”这一躬行孝顺的纪实,可知郭嵩焘这些西人“尊礼”之见并非是崇洋媚外的溢美之词,而实为当时赴外人士业已公认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维新阵营中,与这种“宗周”思潮桴鼓相应的,还有一种“排秦”的思潮。二者此唱彼和,互为激荡,从而也正是在这种一褒一贬中,使“宗周”思潮之旨得以更为明确地豁显和揭扬。
另一方面,如若我们对周人贡献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家族秩序以及相应的国家秩序建设上,那么我们对其贡献的理解就以偏概全而大谬特谬了。因为一种完善的家族关系的建立,除了家族秩序的“宗亲”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家族拓展的“姻亲”,并且二者相较,一如古人所谓“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序卦传》),戴震所谓“人之伦类肇自男女夫妇”(《原善》)所说,后者甚至比前者更为根本、更为重要。而论及这方面周人的贡献,最集中地体现为周人对“同姓不婚”之制的创始。此即《礼记·大传》所谓的“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也即王国维所谓的“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殷周制度论》)。虽然在王国维关于周家族制革新的分析里,这种“同姓不婚之制”曲居于“立子立嫡之制”之后,但实际上无论就发生学还是就伦理学而言,其重要意义都应首出众制而当属第一。原因在于,一如古人“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礼记·坊记》),“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礼记·郊特牲》)所言,这种“同姓不婚”最终是和周人的“男女有别”的家族伦理原则联系在一起的。从而,“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礼记·昏义》),惟有男女有别,才能使一种真正“两人世界”的专偶式夫妇关系得以建立,进而才能使我们人类彻底告别不知父母更谈不到父子的原始的氏族关系,并最终由家及族,使根深叶茂的“华夏民族”在东方大地真正崛起。
采用SPSS18.0系统软件统计分析资料;两组患者ICU天数、住院天数、器官支持天数以及不同时间段炎症指标变化情况其中计量资料用(±s)表示,并用t检验;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其计数资料用(n,%)表示,并用X 2检验;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天下虽大,犹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犹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沉疴可去。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故礼乐刑政,可因时以为变通者;宽猛张弛,可随俗以为转移者也。而独至民志之孚,民情之洽,则固有其道焉,初非智术得而驭之,权势得而驱之也。(《弢园文録外编卷三·达民情》)
显然,这里所谓的“道”恰恰就是周之道。这再次说明了,晚清维新人士之所以极言“排秦”,乃旨在力主“宗周”。进而,其之所以力主宗周,不过是为了向现代西方学习,并且是从自身传统出发,借助于自身话语向现代西方学习,以至于这种学习最终不过是之于自身的“原道”反求诸己而已。然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维新人士的宗周排秦并举一变为全盘的反古反儒,在沸沸扬扬的批判“吃人的礼教”“打倒孔家店”的喧嚣声中,数千年来不绝如缕的中国传统之音顿时统统成为历史的绝响,连同为维新进步人士所高山仰止的周的文明也玉石俱焚,一起彻底埋葬。因此,在今天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的激进主义之际,对晚清“宗周”思潮的积极合理意义的研究,就不能不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一个重要理论议题。为此,让我们从周文明核心——周礼的重新解读谈起。
新语境下对周礼的重新解读
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并称“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殷周制度论》)。而“由是制度,乃生典礼”(同上),这种周的制度亦即以礼治天下的礼制,易言之,周制即周礼。无怪乎《史记·周本纪》记曰:周公,成王之时“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也无怪乎“吾从周”的孔子必然是“克己复礼”的孔子。正是在周代,中国人迎来了被孔子慕为“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礼的世纪”。
那么,到底什么是周礼?抑或说,周礼的真正实质是什么?正是由于这种实质,不仅使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寤寐思服地兢兢以求礼,甚至在两千多年后国人走向现代的全新历史语境下,亦使晚清维新人士对其依然是那样的膜拜顶礼,以致于如同当年的孔子,其同样把“复礼”视为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就不能不回到周人那种“君之宗之”的“家国一体”的社会体制。而要回到周人“家国一体”的社会体制,就不能不首先分析其家族组织。按摩尔根的说法,“由家族组织产生的亲属关系有两类,一类是由世系决定的宗亲,另一类是由婚姻决定的姻亲。”④如果说“宗亲”一类体现了家族同姓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的话,那么“姻亲”一类则体现了家族异姓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礼记·大传》),一如古人所说,一种普遍广泛的家族亲属关系的建立,不仅取决于同姓成员之间的关系的健全,而且也取决于异姓成员之间关系的完善。⑤
令人惊叹的是,无论在家族亲属关系建立的哪个方面,周人都为我们民族做出了划时代的重要贡献!
事实上,周人对“姻亲”家属关系的贡献,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正如周人以一种亦“建构”亦“生理”的“天人合一”方式,从“宗亲”的“立子立嫡”中发掘出政治中的尊卑、贵贱、上下的等级秩序那样,周人亦以一种同样的方式,从“姻亲”的“和两姓之好”中使政治中的对等交往关系得以光大。正本而清源,“由是制度,乃生典礼”的“礼”之所以为礼,与其说是体现在前者的等级秩序中,不如说恰恰体现在后者的交往关系里。故真正意义上的礼,乃是“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这一你来我往的“双向交往”之礼,是“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这一“对称交往”之礼,而非“以上责下,以长责幼”那种单向主宰的刑名之具,而后者不过是后儒煞费苦心地为现存统治秩序缘饰而已。舍此,我们就难以理解何以与周礼联袂推出的周易无处不以阴阳能否两两相交的原则为至谛;舍此,我们就难以理解何以作周礼忠实信徒的原儒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以至于从中不仅为我们推出了普世性的儒家“仁恕”之道,还使所谓的“从道不从君”作为千年不易的思想旗帜永远飘扬于中华大地。
既然周人的社会体制是一种“君之宗之”的“家国一体”的体制,那么,这意味着周人的政治秩序服从其家族秩序,意味着“尊祖敬宗”是统治者维系政治关系的坚实基础。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所谓“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诗经·大雅·板》),所谓“王者,天下之大宗”(同上),如此等等,无不是其说明。尽管自秦以后郡县制开始取代了封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法制随之寿终正寝,原因就在于它依然顽强地体现在中国民间社会的管理之中,体现在民间的“乡绅”系统(如汉的豪强,魏晋隋唐的庶族,两宋的主户,明清的缙绅)之中,体现在民间的“族规乡约”之中。⑥因此,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以其所谓的“超稳定结构”闻名于世,溯其源由,与其说取决于它不无完善发达的社会控制论系统,不如说取决于早为周人奠定的那种既由人建又由天生的“天人合一”式的家族秩序系统。
在舒兰,像于小明一样的农民还有很多,他们都因受益于撒可富的产品和服务,而成为撒可富的忠实用户。姜友善告诉记者:“我经营撒可富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肥料质量事故。农民一开始确实嫌贵,但是也都承认撒可富的肥料品质好,肥效高。时间久了,农民都把撒可富当成像阳光、雨露一样不可或缺的种植要素。”其实,中阿撒可富不仅是农民的阳光雨露,也是合作伙伴的坚实后盾。
从目前的情况看,把传统工艺单独视为一个学科是不合适的,它应该是不同学科的结合体。比如,冶铸类传统工艺属于冶金学,纺织类传统工艺属于纺织学,所有这些分支统称传统工艺。
一方面,就“宗亲”关系而言,按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里的说法,周人确立的所谓“立子立嫡之制”,不仅产生了古代明确的宗法制,也彻底清除了殷人家族关系中的原始氏族制的孑遗。如果说“立子”以其从殷人的“兄终弟及”一改为周人的“父子相继”,而更多地体现了“亲亲”的天然的身体“生理”原则的话,那么,“立嫡”则以其对殷人无视继统的尊卑、贵贱、上下的纠拨,而更多地体现了“尊尊”的人为的思想“建构”原则。这样,由于将“亲亲”与“尊尊”二者有机加以结合,把人为的“建构”纳入天然的“生理”之中,一种“天人合一”式的层次分明、有条不紊的家族谱系、家族秩序最终诞生了。惟其如此,才使“大宗百世不迁”在有周一代成为真正的历史可能;惟其如此,也才使敬宗收族、撰修家谱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也惟其如此,才使服制之周详完备、家属称谓之细密繁多成为中华民族之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大特征。
如果说周人的“宗亲型”的家国系统,以其生命差序结构指向一能指与所指严格相应的知性识辨的符号系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论乃是其集中反映)的话,那么,周人的“姻亲型”的家国系统,则以其生命开放结构指向了一“无所指的能指”的审美象征的符号系统,也即一“无目的合目的性”的生命象征的符号系统。借助于这种符号系统,我不仅可以与生者进行交往,而且亦可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地与死者进行交往。借助于这种符号系统,我既可以从事物的交往,又可以从事“超然物外”的意义的交往,并从中最终使一种有别于“商品交换”的“象征性交换”成为可能。而周人的礼的交往恰恰为这种“象征性交换”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故当后现代主义的大祭司鲍德里亚“象征性交换”的提出被斥为典型的社会“乌托邦”时,殊不知中国古人却通过创制的周礼,实际上早已把这种“象征性交换”贯彻于自己的社会实践之中。因此,礼是一切拜金主义、唯利主义的墓志铭。在这里,孔子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的质疑,在这里,那种完全“无利可图”的身体动容周旋、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皆为礼,在这里,你终于明白了遵循古制的大清皇帝为何宁可割地赔款也不可让渡跪拜之礼,在这里,人们发现了至今哈尼族所存在的“即赠即还”的送礼方式无疑乃为周礼“象征性交换”的孑遗。⑦总之,在这里,现代哲学家威尔默所谓“艺术形式本身成为主体间传递的媒介”思想并非虚语。换言之,一如古人“礼义以为文”(《荀子·臣道》)所说,一种审美的超功利交往形式借助于周礼终于找到了自身坚实的依凭。
正是回到这种意义上的礼,我们才可以为孔子闻风而慕的“吾从周”、矢志不移地“克己复礼”找到其真正的依据。同时,也正是回到这种意义上的礼,我们才可以使晚清维新人士痴心不改的“宗周”思潮的原始初衷大白于世。
从周礼到“无限交往共同体”
晚清维新人士“宗周”之旨证明,其真正的社会理想与其说是走向西式的民主共和,不如说是回归中式的周代礼制。而前者不过是照我之镜鉴,攻吾玉之他石而已。即使是“共和”概念本身,按孙中山的说法,亦不过是“三代之治”的“神髓”。在这里,并没有那种策略性的所谓“委蛇以道古”,而是径直要求我们去复古、宗古、法古。此即梁启超所谓清思潮与欧洲“文艺复兴”绝相类,也即皮锡瑞所谓“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反其初,一变而至于道”(《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它不仅说明了中国社会变革一如其他民族社会变革,其最终都是源于思想的“内源性”而非“外源性”,而且说明了何以辛亥革命帝制的轰然倒塌,是那样的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既没有南明那样的挽狂澜于既倒的勤王之师,更没有诸如刘蕺山这类的以身殉道的义士。
如果说全球化以其资本逻辑统治的有限性尚为共同体交往留有遗憾的话,那么,与全球化携手并行的国际互联网,尤其是那种有别于“工具理性”的互联网的纯粹“交往理性”的社交型互联网,则有可能为“无限性”的共同体交往大开绿灯。无独有偶的是,正如中国人乃今日全球化大潮中的弄潮儿一样,其亦以自己无比积极的投入,不啻成为今日互联网大潮中当仁不让于任何人的生力军。
尽管朱熹称“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乎天地之间”,尽管谭嗣同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然而,这种社会理想却是早已深入我们民族骨髓、融入我们民族血液的千年不易的社会理想。一言以蔽之,这种社会理想就是人类的交往相通,一种无条件的、超越一切利害权势关系的交往相通。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社会理想之成立,既不需要我们诉诸“社会契约论”那样的推理,也不需要我们求助罗尔斯“无知之幕”那样的假定,而是就如我们自身健康身体必然血脉流通那样不证而自明。故王韬不无雄辩地写道:
如薛福成提出,较之孟子“民贵君轻”犹行于其间的夏商周之世,“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矣”。③如黄遵宪提出,与自周以前的“其传国极私,而政体乃极公也”的封建之世不同,自秦以后的郡县之世“设官以治民。……沟而分之,界而判之,曰此官事,此民事,积日既久,官与民无一相信,浸假而相怨相谤,相疑相诽,遂使离心离德,壅蔽否塞,泛泛然若不系之舟,听民之自生自杀,自教自养,官若不相与者,而不贤者复舞文以弄法,乘权以肆虐,以民为鱼肉,以己为刀砧”,“故郡县之世,其设官甚公,而政体则甚私也”(《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冯桂芬亦提出“嬴政并天下。始与井田、封建俱废。秦亡之后,叔孙通等陋儒,不知治本,坐令古良法美意浸淫澌灭不可复”,故“三代以上之民聚,三代以下之民散”(《校邠庐抗议·复宗法议》)。同样的“排秦”观点还可见之于王韬:“祖龙崛起,封建废而为郡县,焚诗书,坑儒士,乐坏礼崩,法律荡然,亦孔子之所未及料者也。汉承秦弊,不能尽改,自是之后,去三代渐远,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弢园文録外编卷一·变法上》),“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弢园文録外编卷一·重民下》)。此外,郭嵩焘的“排秦”观点尤显得旗帜鲜明和鞭辟入里。他说“秦汉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李斯之言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郭嵩焘日记》三),并借他人的话指出“秦并天下,划封建为郡县,海内大势尽易,三代政法扫地略尽”(同上)。在他看来,这使中西格局处于彼长此消之中,泰西之国(指英国)“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而“国势益张”,而“中国秦汉以来二千年适得其反”(同上)。对于他来说,这种悲哀不独是中华文明的危机亦是其“道”的危机:前者是指“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同上),后者则是指“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同上)。故他在发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伦敦致李相伯》)这一感叹的同时,大声疾呼:“秦汉以后之中国,失其道久矣”(《郭嵩焘日记》三)。
耐人寻思的是,虽然这种人类的交往相通的社会理想早在中国古人那里就被先发其覆,如《周易》提出“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周易·否·彖曰》),《礼记》提出“天下有道,则君子欣然以交同”(《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下》),但在晚清之季,随着“宗周”思潮的兴起,对其的再次提撕又一次凸显为时代主题。例如,康有为在1895年上书中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上清帝第四书》)的政治主张;郑观应主张“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⑧王韬声称从秦以后“君日尊而日骄,臣日卑而日谄,于是降交之道无闻”(《弢园文録外编·求言》),坚持“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弢园文録外编·重民中》),“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弢园文录外编·上当路论时务书》);郭嵩焘则感叹“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郭嵩焘日记》一),并告诉咸丰帝“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同上)。
其实,在这方面,被梁启超誉为“中国20世纪开幕第一人”的谭嗣同的思想尤值得一提。这不仅由于他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学》),通过一种“以通训仁”而使“通”升华为儒学的第一公理,从而使儒学实质上重返那种“君子欣然以交同”的周礼,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从晚清维新人士所更多强调的“上下通”进一步地走向了所谓“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这一“无之不通”,极大地拓展了人际交往相通的领地和畛域,以至于宣称“近身者家,家非远也;近家者邻,邻非远也;近此邻者彼邻,彼邻又非远也。……啣接为邻,邻邻不断,推之以至天垠,周则复始,斯全球之势成矣”(同上),宣称“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庄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治者,有国之义也;在宥者,无国之义也。曰在宥,盖自由之转音,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贫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倡随。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同上),并由是与他的“冲决一切网罗”(《仁学·自序》)的思想互为表里,使一种堪称人类“无限交往共同体”的社会理想得以正式推出。
然而,实际上,这种人类“无限交往共同体”又不完全同于西方哲学家哈贝马斯的那种人类“无限交往共同体”。这种不同表现为,如果说哈贝马斯的人类“无限交往共同体”更多地指向了基于“语言互动”的人类“无限交往共同体”的话,那么,谭嗣同的人类“无限交往共同体”则一如他“仁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仁学》)所示,更多地指向了基于“生命(男女阴阳)感应”的人类“无限交往共同体”,而该共同体不过是“感应交织,重重无尽”的生命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体现而已。其情况,恰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周人通过“联姻”无限地拓展了其家国的版图和领域。故较之哈贝马斯的“无限交往共同体”,它是一种深植于我们文化传统根性的更为原生态、也更具生命力的“无限交往共同体”。⑨
①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第503页。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e Kezhen
从闭关锁国的自闭者,到无限交往的互联网世界的达人,这也许是百年中国我们民族最不可思议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又并非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积淀的历史基因的,因为在这里,不正是生动体现了谭嗣同所谓的“以太”(心电之仁)无间距的流行,不正是以一种草蛇灰线、余脉不绝的方式,使我们见证了那种“感应交织,重重无尽”的周人的“交道”魅力之无穷了吗?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我们民族更为原生态、也更具生命力的“无限交往共同体”的思想,才使中华民族一旦打开国门,便对种种外来文明、外来思潮无不虚怀若谷地以礼而待之、兼容而并蓄之。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我们民族更为原生态、更具生命力的“无限交往共同体”的思想,才使中华民族较之那些固守原种族、原教旨的民族,之于今天的全球化大潮更具亲缘性。从中国大地林立的国际跨国公司,到海外中国游客、投资人士的急剧攀升,从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国游客,到一波又一波的海外中国移民,都无一不使你见证了今日中国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人类全球化的急先锋和排头兵,都无一不使你感受到谭嗣同的“邻邻不断”,庄子的“在宥天下”正在一步步地梦想成真。
②③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06、606页。
④《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405页。
正如品牌的公益之旅从未停止,天王表对时尚的探索也从未曾停歇。2018年,天王表将对征服者智勇齐备、一往无前的无畏探索精神融入腕表时间哲学之中,传递和演绎了天王表对“征服者”的臻意相颂。随着一众外籍型男超模登台,将作为活动主咖的天王表征服者系列腕表所蕴含的精神内涵进行了丰富演绎及魅力展示。
⑤张再林:《中国古代身道研究》第七章“父子伦理还是夫妇伦理”,三联书店,2015年,第78页。
⑥刘文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绪论第二章第一节,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
⑦郑宇:《箐口村哈尼族丧礼献祭礼物的象征性交换》,《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⑧《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4页。
⑨当然,在对谭嗣同思想做出这种分析的同时,我们并不否认他的思想同样受到诸如佛学、墨学这类“天生”哲学的一定影响。
探讨区块链在应用中的战略价值,必须要解决区块链技术普遍应用的问题,究竟企业要采取什么战略路径,才能获取区块链红利,不同行业区块链的具体应用一定不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项目号:18ZDA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再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华山学者。西安,710071
〔责任编辑:吴 明〕
标签:周礼论文; 晚清论文; 思潮论文; 共同体论文; 中国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学海》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项目号:18ZDA020)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