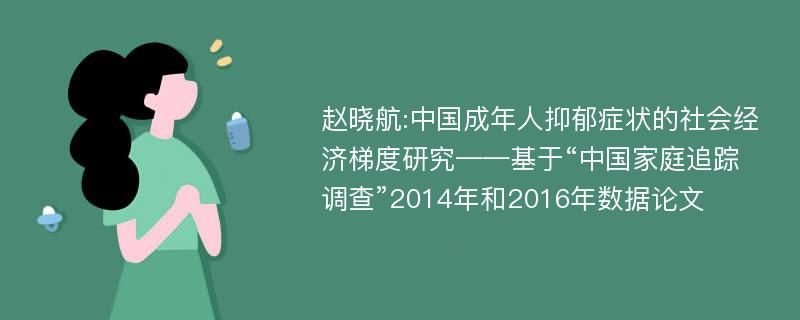
[摘 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数据,探讨中国成年人抑郁程度的分布情况及抑郁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个人受教育程度、人均家庭年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中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抑郁的发生率较高(其中23.4%的人有抑郁症状,4.6%的人患有抑郁症);个人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越高,则其抑郁水平越低;通过Wagstaff分解法分析各类因素对和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的贡献发现,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对抑郁不平等的贡献率依次为23%、22%和33%。此外,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水平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抑郁水平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扩大,呈现出发散趋势;女性和农业户籍者通过教育获得的精神健康回报要高于男性和非农业户籍者。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 抑郁 健康不平等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不平等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历来受到多个学科的关注,健康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中国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在社会学领域,有关社会经济地位和精神障碍之间关系的探索可以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1](P2-16)之后,西方国家的不少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罹患抑郁症的风险越高,[2]因为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往往缺乏良好的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也更有可能遭遇负面的生活事件,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这些发现与健康研究领域的“社会因果论”相契合。[3]已有的中国研究也指出,抑郁症状同年龄、退休与否、身体健康、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经济状况、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4-7]不过,由于人们的抑郁程度通常存在较明显的地区差异,[8]而现有的中国研究多采用区域性数据,因此难以得出具有全国意义的推论。同时,社会经济地位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文化情境的制约。例如,有研究指出,在美国和日本,高收入有利于抑制人们的抑郁水平,但高学历只有利于降低美国人的抑郁水平,对日本人则没有显著影响。[9]鉴于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情境,西方研究的结论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近年来,一些中国研究通过分析全国代表性数据,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针对45岁及以上中老年群体的研究指出,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学历越低、人均家庭消费性支出越低)的人抑郁程度越高,这是因为他们更容易经历不幸的生活事件(如近期丧偶、子女亡故)、处于较差的健康水平(如残疾、记忆力较差)。[10]还有学者利用该数据进行了相关研究,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测量社会经济地位,即通过潜类别分析将户籍、受教育程度、是否是体力劳动者、人均家庭年收入等合成一个代表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指标,结果同样显示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抑郁程度越高。[11]目前仅有一项研究以中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作为分析对象,该研究通过分析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指出,人均家庭收入和抑郁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受教育年限对抑郁程度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呈现出抑郁程度随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12]
虽然以上研究基本得出在中国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抑郁程度相对越低的结论,但其中的一些分析仍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一些研究的分析对象是中老年群体,[10-11]因此其中的一些结论可能未必适用于中国的青年群体。第二,虽然有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和抑郁程度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12]但以往西方研究既有发现U型曲线关系的情况,[13]也有发现线性关系的情况,[14]故需要进一步验证。第三,以往研究选取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主要是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但当前中国不同家庭拥有的财产数额有较大差异,财产的不平等程度甚至高于收入不平等,[15-16]因此有必要将财产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第四,以往研究采用的都是截面数据,这增大了模型引入联立性偏误(双向因果)的风险,因为根据健康选择论的观点,较差的精神健康不仅会对人们的工作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减少其收入和财产积累,还会阻碍青年人的教育获得。第五,以往研究都只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关联,而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对抑郁不平等的贡献度方面缺乏探究。
据了解,四川省目前大概拥有各类家庭服务机构5000个。其中,家政服务公司约3000家,公益性家庭服务组织2000个。家政服务公司主要分布在成都、绵阳、乐山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以中介式服务为主。全省拥有家政服务员培训资格的培训机构约300个,年培训规模20000人左右。
健康不平等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影响的年龄模式,从这些研究中衍生出“发散假定”、[4-5][17-18]“收敛假定”和“年龄中和(age-as-leveler)假定”等竞争性理论。[19-21]“发散假定”指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不断累积,社会分层导致的健康不平等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扩大,老年时期的健康不平等要大于中年时期,即呈现出“优势/劣势累积”(cumulative dis/advantage)的发散趋势。“收敛假定”描述了刚好与之相反的过程。“年龄中和假定”指健康的阶层差异在青年期增大,在中年后期和老年早期达到最大,但在老年后期有缩小或趋同趋势。虽然以往研究指出,在中国,自评健康和身体功能的不平等趋势满足“发散假定”,[11][22-24]但也有研究支持“收敛假定”。[25]此外,有西方研究证明抑郁程度的差异满足“发散假定”,[14][21]但目前尚无明确的结论表明抑郁不平等的发散趋势在中国成立。虽然有研究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抑郁程度差异没有显著的发散或收敛趋势,但这有可能和该研究分析样本的年龄限制(45岁及以上)有关。[11]
其中,μ为CES-D得分的均值,βk为回归系数,为自变量xk的均值,CIk为各自变量xk的集中指数;表示CES-D得分关于因素xk的弹性为抑郁不平等中可以由各影响因素解释的部分,称为“因素xk对抑郁不平等的集中指数(CI)的贡献度”;GCε为相对于回归方程残差项εi的广义集中指数(generalized concentration index),即抑郁不平等中不可以被各影响因素解释掉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因素xk对CI的贡献率(percentage of contribution):
二、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4年和2016年数据。CFPS调查的目标总体为中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香港、澳门、台湾、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中的家庭户及其所有家庭成员。在调查实施上,CFPS采用城乡一体的多阶段、内隐分层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借助先进的调查技术提高访问质量,设计了兼顾研究需要和可操作性的追访原则。[26]为了削弱分析模型的联立性偏误(双向因果),以2014年数据提供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以2016年数据提供的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2014年CFPS数据中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成人个体样本(16岁及以上)有24822个,家庭样本有9416个。2016年CFPS数据中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成人个体样本有24722个,家庭样本有9464个。研究的分析对象是2014年受访、2016年被成功追访的全国代表性成人样本,2014年的成年受访者中有74%的人(N=18473)在2016年被成功追访,剔除信息不完整的样本后,最终的分析样本为18344个。
(二)变量
因变量是2016年CFPS测量的抑郁程度。调查利用美国流行病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进行了测量,该量表由拉德罗夫(Radloff)开创,至今仍是被最广泛应用的抑郁水平测量工具。[27]调查中分别采用了20个和8个题目的量表,其中对20%的受访者采用的是CES-D 20量表,对剩余80%的受访者采用CES-D 8量表,受访者使用的量表是随机分配的。本研究利用等百分位等值变换(equipercentile equating)的方法将CES-D 8量表得分转化成CES-D 20量表得分。[28]经转化后,两组受访者的CES-D 20量表得分的百分位分布情况基本一致,并具有几乎等同的均值、标准差、峰度和偏度。CES-D 20量表测量了受访者过去一周内产生以下情绪的频率:①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②我不想吃东西,我的胃口不好;③我觉得沮丧,即使有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也不管用;④我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差(反向题);⑤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⑥我感到情绪低落;⑦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⑧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反向题);⑨我觉得一直以来都很失败;⑩我感到害怕;我的睡眠不好;我感到愉快(反向题);我讲话比平时少;我感到孤独;我觉得人们对我不友好;我生活快乐(反向题);我哭过或想哭;我感到悲伤难过;我觉得别人不喜欢我;我觉得生活无法继续。回答包括“几乎没有(不到一天)”“有些时候(1-2天)”“经常有(3-4天)”以及“大多数时候有(5-7天)”,依次记为0、1、2、3分,该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达0.86。抑郁程度即为各题目分数的加总。
关键自变量是表示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包括个人的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年收入(自然对数值)和人均家庭净资产(以万元为单位,将其绝对值加1再取对数,并判断正负性)。受教育年限指受访者接受教育所花费的年限,包括了受访者正在接受某阶段的教育而尚未获得学历所花费的时间。家庭收入由家庭成员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指家庭成员从事农业或非农受雇工作挣取的工资(税后)、奖金和实物形式的福利。经营性收入指家庭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经营扣除成本后的净收入(包括自产自销部分),以及从事个体经营和开办私营企业获得的净利润。转移性收入指家庭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如养老金、补助、救济)和补偿金(征地补偿金、住房拆迁补偿金)以及社会捐助(包括现金和实物)获取的收入。财产性收入指家庭通过投资、出租土地、房屋、生产资料(如机械设备、运输工具、耐用品、牲畜)等获得的收入。其他收入指通过亲友的经济支持和赠予获取的收入。家庭净资产是在计算土地、房产、金融资产和各类有价实物价值总和的基础上减去包括房贷在内的各类债务而得到的数值。人均家庭年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的分母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家庭内的人数。
Analyzed metabolic changes in patient groups are shown in Table 3.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婚姻状态、政治面貌、职业类型、身体健康状况(近两周是否身体不适、近半年内是否患慢性病、近半年内是否住院)、区县(或省份)虚拟变量。所有的预测变量(关键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除年龄是2016年的情况外,其余变量都是2014年的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N=18344)
变量均值/百分比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抑郁程度(CES-D得分)12.38.2051年龄(2016年)47.017.11898受教育年限7.54.7020男性50.101农业户口72.201人均家庭收入(元)13972.030085.03003620000人均家庭净资产(万元)10.222.1-75.2701.5
续表
变量均值/百分比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婚姻状态有配偶76.401未婚15.901离婚1.601丧偶6.201中共党员6.101职业类型非农受雇32.001自家农业经营31.101非农自雇8.801农业打工/散工2.901上学4.801退休9.301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11.201最近两周身体不适是26.201否59.801未知14.001近半年内患慢性病是14.001否72.001未知14.001近半年内是否住院是9.901否76.001未知14.001
注:(1)样本经过加权处理;
(2)2014年成人代答问卷未提问身体健康状况,故未知。
(三)统计方法
1.抑郁不平等的测量和分解方法
根据瓦格斯塔夫(Wagstaff)等的研究,集中指数和集中曲线法能够较好地反映全体人群健康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特征,并且能灵活、灵敏地反映社会经济特征的分布与变化情况,因此我们使用该方法来测量抑郁的不平等状况。[29]
[18]Willson, Andrea E., Kim M. Shuey and Glen H. ElderJr. Cumulative Advantage Processes asMechanisms of Inequality in Life Course Health[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 112(6).
图1 抑郁不平等集中曲线示意图
为了简明计算集中指数的大小,卡克瓦尼(Kakwani)等提出如下计算方法:[30]
在这里,μ指的是CES-D得分的均值;Ri表示第i个人在人均家庭年收入分布中的分布秩次(fractional rank),故本研究所谓的“抑郁不平等”具体指的是与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在以往的研究中,Ri通常代表人均家庭消费(降低收入瞒报、漏报的影响)或人均家庭收入的分布秩次;[29][31]yi表示第i个人的CES-D得分。由于在分析过程中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Ri的计算方法如下:[32](P101)
因分小组的时候,成员是成绩好差搭配的,讨论的时候可能由于后进生的学习态度不好或者基础太差,无法参与讨论或不想参与讨论,成绩较好的学生能力不够或较为性格内向沉静,导致课堂上小组合作讨论的时候,无法带动起整个组的讨论氛围,气氛冷清,无法开展落实下去。
其中,wi和wj表示权重,且w0=0。
对于抑郁不平等的分解,即对抑郁不平等的各个影响因素的贡献加以分离,我们采用瓦格斯塔夫等的线性方法。[29]其基本思路与线性回归类似:将抑郁不平等的集中指数(CI)分解为由可观测变量x1,x2,…,xk解释的部分和不能由数据解释的部分,以个人的CES-D得分yi作为因变量,各种影响因素xk作为自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并使用OLS模型对xk的系数βk进行估计:
yi=β0+β1x1i+β2x2i+…+βkxki+εi
其中,εi为误差项,集中指数CI可以分解为:
为弥补以往研究留下的知识盲点,致力于探究以下问题:第一,对中国的成年人而言,教育背景、收入水平和财产水平如何影响他们的抑郁水平?第二,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抑郁不平等的贡献率有多高?第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抑郁程度差异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第四,社会经济地位对不同群体抑郁程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父母的信仰是儿童信念发展的锚定起点(Boyatzis et al., 2006; Ozorak, 1989),不同信仰的父母有着不同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亲子谈话是传递父母的信仰及信念的重要方式(Boyatzis et al., 2006)。因此,父母可能通过亲子谈话传递他们的来生信念,进而影响着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及来生信念。研究二考察儿童来生信念与父母来生信念、死亡相关话题亲子谈话的关系,帮助我们理解儿童来生信念的特点,以及父母来生信念对儿童来生信念的影响过程及机制。
2.调整样本追踪流失情况的加权方法
“妹子,冷静点,来,坐下,听姐慢慢给你讲讲我的事。”田志芳很不情愿地别着脸。“我也是从你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你心里想的啥,姐一清二楚。姐是1951年从湖南当兵来得新疆。三年十批,八千湘女上天山,轰轰烈烈啊。从老家热闹的长沙营盘街出发,到达这僻远的南疆县整整七个月。不信啊?妹子,那时火车只通到西安,然后坐道奇牌卡车,一摇三晃好不容易捱到星星峡,差点丢命。车队的头车是给养车,为了提前到达宿营地给我们做饭,他们惨遭土匪埋伏袭击,司机被倒汽油活活烧死。“多惨!为什么不还击?!”田志芳冷不丁愤恨地插一句。
由于各模型中自变量为2014年的测量结果,而因变量为2016年的测量结果,因此会出现样本在追踪过程中流失的情况。为了降低因样本的系统性流失而造成的估测偏差,本研究采用倒数概率加权(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的方法对分析样本进行加权处理。具体的方法是,将2014年的全国代表性样本分为2016年被成功追访和2016年未成功追访(样本丢失)两类,之后以一些指标为预测变量用Logit模型估算成功追踪的概率,以该概率的倒数作为抽样权重,即删失权重(censoring weight)。在2014年的全国代表性样本中,25.6%的样本在2016年的调查中流失(N=6349)。在预测样本追踪成功概率的Logit模型中(N=24594),预测变量包括了年龄、性别、城乡居住地、户口性质、是否是中共党员、婚姻状态(有配偶、未婚、离婚、丧偶)、自评健康(分类变量)、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职业类型(自家农业经营、非农自雇、农业打工/散工、上学、退休、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人均家庭净资产的对数值、身体健康状况(是否最近两周身体不适、是否半年内患慢性病、是否半年内住院)、2014年的抑郁程度(Kessler量表得分)、是否有代答、居住省份等指标,伪决定系数(Pseudo R2)为0.111。
三、实证结果
(一)中国成年人的精神抑郁现状
拉德罗夫将20项CES-D量表得分在16分以下的情况归为精神健康,[27][33]16至28分为抑郁症状,28分以上为患有抑郁症。依据这一标准,2016年中国成年人(18岁及以上)中的72.0%为精神健康,23.4%的人有抑郁症状,4.6%的人患有抑郁症(N=21716)。根据CFPS 2012数据,2012年68.2%的成年人为精神健康,27.7%的人有抑郁症状,4.1%的人患有抑郁症(N=19794)。在这4年间,中国成年人之中精神健康的比例上升,但重度抑郁的比例也略有上升。不过从CES-D量表得分的均值和中位值来看,2016年的情况略好于2012年:2012年的均值是12.85分,中位值是12分;2016年的均值是12.15分,中位值是10分。
图2展示了分城乡居住地和性别的精神抑郁程度的核密度图。从城乡角度看,城镇男性的抑郁水平低于农村男性,相较于农村男性,城镇男性中抑郁水平较低的比重相对较高;同样,城镇女性的抑郁水平低于农村女性。从性别角度看,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男性的抑郁水平都低于女性。
图2 分城乡和性别的精神抑郁水平核密度图
图3展示了以人均家庭年收入人口累计百分比为横轴的抑郁不平等集中曲线示意图。从图3可以看出,集中曲线位于绝对平等线的左上方,这说明相对较高的抑郁水平在来自较低收入家庭的人群中堆积,即来自较低收入家庭的人更可能有较高的抑郁水平。根据前文提到的公式计算可得,与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的集中指数为-4.7%,这同样说明精神健康状况更好的人集中于较高收入群体。与之类似,在以受教育年限或人均家庭净资产的人口累计百分比为横轴的抑郁不平等集中曲线示意图中(未展示),相对较高的抑郁水平在学历较低、财产较少的人群中堆积。
图3 与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集中曲线示意图
(二)对抑郁水平集中指数的分解
表2报告了对抑郁水平集中指数进行分解的结果。从OLS模型(因变量是CES-D得分)的回归系数可知,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人均家庭净资产)、政治面貌、职业类型、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人口学特征都对抑郁程度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男性、有配偶、中共党员、良好的身体健康等属性有利于降低抑郁程度。从各因素对抑郁不平等的贡献百分比来看,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对与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的贡献率分别是23%、22%和33%。这说明财产的不平等是造成与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的关键因素。
(三)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影响的年龄差异
表3中的模型1是在控制了区县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出,良好的教育背景、较高的收入和家庭财产有利于降低人们的抑郁程度。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抑郁水平持续升高并在大约54岁时到达峰值,此后的抑郁水平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在青年期和中年期人们的压力随年龄增长不断增加,而在退休年龄前后压力减弱,年龄成熟效应(maturity effect)也在此后显现出来,即经过人生的历练,老年人调和行为和观念之间冲突的能力更强,能更好地将自己的情绪波动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此外,男性、非农业户口人员、中共党员、学生和退休人员、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者的抑郁水平也显著更低。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受教育年限和年龄的交互项,该交互效应为负效应,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对精神抑郁的抑制作用有所增强。同样,模型3和模型4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和财产对精神抑郁的抑制作用也有所增强。图4至图6分别对应模拟了模型2至模型4的预测结果,模拟中预测变量是定类变量的取参照组,预测变量是定距变量的取均值。从图4至图6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收入和财产对抑郁水平的影响呈现出发散趋势,从而支持了“发散假定”。
表2 各因素对抑郁水平集中指数的贡献率
自变量OLS回归系数X均值弹性系数集中指数对CI的贡献度贡献百分比年龄组(18-29岁)[0.42]30-39岁0.823∗∗∗0.1508 0.0103 0.0542 0.0006 -1.1840-49岁0.892∗∗∗0.2024 0.0149 0.0075 0.0001 -0.2450-59岁1.004∗∗∗0.1920 0.0159 0.0233 0.0004 -0.7960-69岁0.877∗∗0.1704 0.0123 -0.0504 -0.0006 1.3270岁及以上0.5810.1063 0.0051 -0.1208 -0.0006 1.31社会经济地位[78.39]受教育年限-0.157∗∗∗7.3947 -0.0958 0.1121 -0.0107 22.85人均家庭收入(ln)-0.209∗∗9.0675 -0.1566 0.0666 -0.0104 22.19人均家庭净资产(ln)-0.742∗∗∗1.8581 -0.1140 0.1375 -0.0157 33.35
续表
自变量OLS回归系数X均值弹性系数集中指数对CI的贡献度贡献百分比男性-1.253∗∗∗0.4881 -0.0505 0.0085 -0.0004 0.91农业户口0.2140.7316 0.0129 -0.1064 -0.0014 2.92婚姻状况(有配偶)[-0.40]未婚1.915∗∗∗0.1307 0.0207 0.0486 0.0010 -2.14离婚2.690∗∗∗0.0146 0.0032 0.1191 0.0004 -0.82丧偶1.873∗∗∗0.0582 0.0090 -0.1334 -0.0012 2.56中共党员-0.961∗∗∗0.0705 -0.0056 0.2464 -0.0014 2.93 职业类型(非农受雇)[-3.15]自家农业经营-0.449∗0.3493 -0.0129 -0.2428 0.0031 -6.69非农自雇-0.511∗0.0933 -0.0039 0.0982 -0.0004 0.82农业打工/散工-0.776∗0.0267 -0.0017 0.0246 0.0000 0.09上学-2.290∗∗∗0.0447 -0.0085 -0.0478 0.0004 -0.86退休-1.132∗∗∗0.0984 -0.0092 0.1648 -0.0015 3.23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0.0940.0984 0.0008 -0.1584 -0.0001 0.26身体健康状况[6.18]两周内身体不适3.164∗∗∗0.3042 0.0795 -0.0328 -0.0026 5.55半年内患慢性病1.714∗∗∗0.1623 0.0230 0.0042 0.0001 -0.21半年内住院0.832∗∗∗0.1154 0.0079 -0.0497 -0.0004 0.84省份固定效应YES(略)(略)(略)(略)[11.80]常数项14.681∗∗∗R20.125
注:(1) *p<0.05,**p<0.01,***p<0.001(双侧检验);
(2)采用以家庭为组(cluster)进行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3)N=16766(剔除了所有含缺失值的样本)。
图4 教育背景对抑郁水平影响的年龄差异
图5 人均家庭收入对抑郁水平影响的年龄差异
图6 人均家庭净资产对抑郁水平影响的年龄差异
表3 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程度影响的年龄差异(OLS)
自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年龄0.077∗(0.030)0.112∗∗∗(0.032)0.089∗∗(0.030)0.075∗(0.030)年龄平方-0.001∗(0.000)-0.001∗∗∗(0.000)-0.001∗∗(0.000)-0.001∗(0.000)受教育年限-0.185∗∗∗(0.019)-0.174∗∗∗(0.019)-0.188∗∗∗(0.019)-0.188∗∗∗(0.019)人均家庭年收入(ln)-0.311∗∗∗(0.074)-0.306∗∗∗(0.074)-0.256∗∗∗(0.072)-0.302∗∗∗(0.074)人均家庭净资产(ln)-0.645∗∗∗(0.075)-0.649∗∗∗(0.075)-0.645∗∗∗(0.076)-0.641∗∗∗(0.075)年龄×受教育年限-0.003∗∗∗(0.001)年龄×人均家庭年收入(ln)-0.028∗∗∗(0.004)年龄×人均家庭净资产(ln)-0.018∗∗∗(0.004)男性-1.200∗∗∗(0.120)-1.147∗∗∗(0.121)-1.193∗∗∗(0.120)-1.198∗∗∗(0.120)农业户口0.372+(0.192)0.389∗(0.192)0.289(0.192)0.368+(0.192)婚姻状态(有配偶)未婚1.335∗∗∗(0.263)1.250∗∗∗(0.265)1.212∗∗∗(0.262)1.291∗∗∗(0.263)离婚2.701∗∗∗(0.531)2.714∗∗∗(0.530)2.710∗∗∗(0.529)2.697∗∗∗(0.530)丧偶1.649∗∗∗(0.369)1.556∗∗∗(0.371)1.613∗∗∗(0.369)1.604∗∗∗(0.370)中共党员-1.066∗∗∗(0.236)-1.032∗∗∗(0.237)-0.994∗∗∗(0.237)-1.001∗∗∗(0.237)职业类型(非农受雇)自家农业经营-0.640∗∗∗(0.194)-0.572∗∗(0.193)-0.479∗(0.193)-0.603∗∗(0.193)非农自雇-0.720∗∗∗(0.217)-0.686∗∗(0.217)-0.607∗∗(0.216)-0.707∗∗(0.216)
续表
自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农业打工/散工-0.488(0.385)-0.419(0.385)-0.362(0.384)-0.459(0.385)上学-2.062∗∗∗(0.313)-2.109∗∗∗(0.313)-1.815∗∗∗(0.311)-2.048∗∗∗(0.312)退休-1.023∗∗(0.320)-0.843∗∗(0.324)-0.613+(0.323)-0.847∗∗(0.322)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0.026(0.255)0.090(0.255)0.146(0.255)0.069(0.255)最近两周身体不适(是)否-2.982∗∗∗(0.154)-2.964∗∗∗(0.154)-2.940∗∗∗(0.154)-2.945∗∗∗(0.154)未知-2.660(3.552)-2.852(3.592)-2.422(3.565)-2.771(3.430)近半年内患慢性病(是)否-1.605∗∗∗(0.198)-1.630∗∗∗(0.199)-1.634∗∗∗(0.198)-1.631∗∗∗(0.198)未知-2.439(3.431)-2.533(3.414)-2.521(3.454)-2.493(3.456)近半年内住院(是)否-0.733∗∗(0.224)-0.731∗∗(0.224)-0.743∗∗∗(0.223)-0.726∗∗(0.223)未知1.169(4.152)1.441(4.161)1.080(4.158)1.362(4.080)区县固定效应YESYESYESYES常数项16.031∗∗∗(0.819)15.905∗∗∗(0.818)15.868∗∗∗(0.819)15.953∗∗∗(0.822)R20.1760.1770.1800.177样本量18344183441834418344
注:(1)+p<0.1, *p<0.05,**p<0.01,***p<0.001(双侧检验);
(2)括号内是以家庭为组进行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3)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年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经对中处理。
(四)教育对抑郁水平影响的群体异质性
一些研究指出,教育对人的心理适应能力有积极的形塑作用,高学历群体拥有更好的心理调节能力。[30-31]不过,考虑到教育对不同群体心理调适能力的塑造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教育对不同人群精神健康影响的差异还值得进一步探究。表4中的模型5和模型6分别考察了受教育年限和性别、受教育年限和户口性质之间的交互效应。可以看出,教育对抑郁水平的抑制作用在女性和农业户籍者等弱势群体中更强(受教育年限和户口性质的交互项是边缘显著的,p=0.052)。换言之,在精神健康方面,教育对女性和农业户籍者产生的健康回报率高于男性和非农业户籍者。具体表现为:在其他因素一定的前提下,对女性而言,受教育年限平均每增加一年,其抑郁水平平均降低0.22个单位,而在男性中仅降低0.15(=|-0.215+0.071|)个单位;对农业户籍者而言,受教育年限平均每增加一年,其抑郁水平平均降低0.21(=|-0.137-0.068|)个单位,而在非农业户籍者中仅降低0.14个单位。同时,收入和性别、收入和户口性质、财产和性别、财产和户口性质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这反映了教育对精神抑郁影响的特殊性,女性和农业户籍者通过教育获得来抑制抑郁水平的效果优于男性和非农业户籍者。图7和图8更加直观地展示了模型5和模型6的模拟预测结果。
表4 教育对抑郁水平影响的群体差异(OLS)
自变量模型5模型6年龄0.073∗(0.030)0.074∗(0.030)年龄平方-0.001∗(0.000)-0.001∗(0.000)受教育年限-0.215∗∗∗(0.022)-0.137∗∗∗(0.032)男性-1.203∗∗∗(0.120)-1.184∗∗∗(0.120)受教育年限×男性0.071∗∗(0.026)农业户口0.374+(0.192)0.468∗(0.210)受教育年限×农业户口-0.068+(0.035)人均家庭年收入(ln)-0.316∗∗∗(0.074)-0.308∗∗∗(0.074)人均家庭净资产(ln)-0.644∗∗∗(0.075)-0.647∗∗∗(0.075)婚姻状态(有配偶)未婚1.330∗∗∗(0.263)1.327∗∗∗(0.263)离婚2.724∗∗∗(0.530)2.699∗∗∗(0.533)丧偶1.592∗∗∗(0.369)1.637∗∗∗(0.369)中共党员-1.095∗∗∗(0.237)-1.111∗∗∗(0.237)
续表
自变量模型5模型6职业类型(非农受雇)自家农业经营-0.635∗∗(0.194)-0.639∗∗∗(0.194)非农自雇-0.714∗∗∗(0.217)-0.685∗∗(0.217)农业打工/散工-0.471(0.385)-0.459(0.385)上学-2.075∗∗∗(0.313)-2.042∗∗∗(0.313)退休-1.021∗∗(0.320)-0.938∗∗(0.323)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0.019(0.255)0.055(0.255)最近两周身体不适(是)否-2.976∗∗∗(0.154)-2.974∗∗∗(0.154)未知-2.332(3.551)-2.807(3.551)近半年内患慢性病(是)否-1.599∗∗∗(0.198)-1.607∗∗∗(0.198)未知-2.566(3.434)-2.423(3.491)近半年内住院(是)否-0.746∗∗∗(0.224)-0.737∗∗∗(0.224)未知0.957(4.160)1.306(4.183)区县固定效应YESYES常数项16.007∗∗∗(0.819)15.864∗∗∗(0.825)R20.1760.176样本量1834418344
注:(1)+p<0.1, *p<0.05,**p<0.01,***p<0.001(双侧检验);
(2)括号内是以家庭为组进行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3)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年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经对中处理。
图7 受教育年限对两性抑郁水平影响的差异
图8 受教育年限对不同户籍人群抑郁水平影响的差异
四、结论与讨论
[22]郑莉, 曾旭晖. 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 [J]. 社会, 2016(6).
由“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年数据可知,在中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当中,23.4%的人有抑郁症状,4.6%的人患有抑郁症。通过分解各因素对与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的贡献发现,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等的贡献率依次为23%、22%和33%。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教育和收入,财产是造成与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我们通过探究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水平影响的年龄模式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抑郁程度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扩大,呈现出发散趋势。并且,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对抑郁水平的影响都印证了这种“发散假定”。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水平影响的群体异质性体现在:教育对女性产生的精神健康回报率高于男性,教育对农业户籍者产生的健康回报率高于非农业户籍者。但收入和财产对抑郁程度的影响没有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差异,这体现了教育对抑郁的影响不同于收入和财产的方面。
注释:
[1]Faris, Robert E. L. and H. Warren Dunham. Mental Disorders in Urban Areas: An Ecological Study of Schizophrenia and other Psychoses[M].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2]Lorant, V., D. Deliège, W. Eaton, A. Robert, P. Philippot and M. Ansseau.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Depression: A Meta-Analysis[J].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03, 157(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企业或单位经营都存在风险,因此医院要从财务会计管理工作的发展出发,做好规避各种风险的工作,建立健全完善的内部核查制度与考核体系,确保医院资金的使用更规范与有效。构建科学的内控核查制度,严格按照相关标准与流程开展核查工作,才能提高医院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的效率。
[3]Turner, R. J. and D. A. Lloyd. The Stress Process and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Depression[J]. Journal of Health & Social Behavior, 1999, 40(4).
在市政工程管理中,相关部门必须监理完善的都市生态保护机制,除了要做好工程建设中的保护工作中,对建后的维护工作也不能忽视。以都市自然生态为例,在市政建设工程中,道路工程、园林工程、地下管道工程等都会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地下管道工程,工程建设会产生大量的废气、粉尘和废水,若是处理不当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在工程建设前,必须要做好工程区域生态标准检测工作,并对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污染进行分析预测。为市政道路建设的生态问题分析表,基于此,可以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应的管理标准和应对措施。
为有效解决回声问题,最初的算法思路是采用一种非线性的回声抑制器[3]。但这种机制会使通话断断续续,故在实际运用中,很少使用。上世纪60年代,贝尔实验室首次结合自适应滤波技术设计了回声抵消器,使得该技术得到了广大支持并迅速应用开来。在众多自适应算法中,最常用的是NLMS[4-5,7]算法,其算法原理是运用最小均方误差准则,使自适应滤波器逼近真实路径的频响特性。NLMS算法收敛性能好,稳定性强[6],但计算量较大[8],当N(滤波器阶数)增大时,运算量以N的平方的比例迅速增加,这会影响VoIP电话这类系统的实时性能。
[5]Li, Lydia, Jersey Liang, Amanda Toler and Shengzu Gu. Widowhood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Older Chinese: Do Gender and Source of Support Make a Difference?[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5, 60(3).
[4]Chen, R., J. R. M. Copeland and L. Wei. A Meta-Analysis of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in Depression of Older Peop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1999, 14(10).
[6]Lim, Lena L., Weining Chang, Xin Yu, Helen Chiu, Mian-Yoon Chong and Ee-Heok Kua. Depression in Chinese Elderly Populations[J]. Asia-Pacific Psychiatry,2011, 3(2).
[7]Strauss, John, Xiaoyan Lei, Albert Park, Yan Shen, James P. Smith, Zhe Yang and Yaohui Zhao. Health Outcome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mong the Elderl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CHARLS Pilot[J]. Journal of Population Ageing, 2010, 3(3).
[8]Pan, An, Oscar H. Franco, Yan-fang Wang, Zhi-jie Yu, Xing-wang Ye and Xu Lin. Prevalence and Geographic Disparit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in China[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07, 105(1).
[9]Inaba, Akihide, Peggy A. Thoits, Koji Ueno, Walter R. Gove, Ranae J. Evenson and Melissa Sloan. Depr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Gender, Marital Status, and SES Pattern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5, 61(11).
[10]Lei, Xiaoyan, Xiaoting Sun, John Strauss, Peng Zhang and Yaohui Zhao.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ES among the Mid-Aged and Elderl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National Baseline[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4(120).
[11]焦开山.健康不平等影响因素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14(5).
[12]Qin, Xuezheng, Suyin Wang and Chee-Ruey Hsieh.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ults in China: Estimation Based on a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8(51).
[13]Bracke, Piet, Vera Van De Straat and Sarah Missinne.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and Education-Labor Market Misfit[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014, 55(4).
[14]Miech, Richard Allen and Michael J. Shanaha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Depression over the Life Course[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000, 41(2).
[15]Jin, Yongai and Yu Xi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Wealth and Income in Urba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7, 3(2).
[16]Xie, Yu and Yongai Jin. Household Wealth in China [J].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5, 47(3).
新课程理念要求我们初中化学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为每一位学生提供相等的学习机会,并基于他们的差异提供多样化的评价方式,从而使学生可以在原有的知识水平上得以发展。在实际教学中,我们会发现学生因其成长环境和家庭背景的不同,其思维方式也会千差万别,而其学习动机的不同,也导致学生在学习积极性方面存在差异。而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化学教师应采取个性化的教学方式。而具体执行,教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为参考。
手工书籍的创作特色就是其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设计者的个性,它无需考虑工艺上的制约,只需要构思并将其创作出来。例如,以“轮回”为主题,要求学生在书籍制作中表现出生命的循环新生。个性化手工书籍的制作者首先会在材质上力求环保,在内容上体现“轮回”的概念,同时引导学生在制作创意上避免与传统书籍发生雷同,更追求书籍意境化和艺术性的表现方式。其中,书籍制作的纸张新旧、糙滑以及薄厚等都需要提前考虑,并通过最原始的手工方式制作,怀着崇敬的心情完成整本书籍的制作仪式。
集中曲线和集中指数法分别与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的计算和表达方法有类似之处(见图1),横轴表示某一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由低到高的累计人口比例,纵轴表示抑郁得分(CES-D)从低到高的累计人口比例,曲线L表示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抑郁不平等的分布状况,L与对角线之间的区域的两倍即抑郁不平等的集中指数(concentration index,CI),-1≤CI≤1。如果L与对角线重合,则CI=0,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抑郁不存在差异;如果L位于对角线上方,CI<0,表明抑郁总是集中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如果L位于对角线下方,CI>0,表明抑郁总是集中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L偏离对角线越远,则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抑郁不平等越严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CI=1或者-1。
试验结果表明,随着水稻秸秆覆盖量增加,溶液中可溶性离子浓度随之增加,但却未成倍增加,1 500 kg/667m2覆盖的电导率峰值也未超过严吴炜[10]的研究结果(500 kg/667m2覆盖春季试验在19 d时达峰值1 766 μS/cm),说明试验土表溶液中可溶性离子浓度在1 700 μS/cm左右时接近饱和。从达峰值的时间看,秸秆的加量覆盖以及高温会使秸秆腐解后土壤表层溶液电导率更快达到峰值。但高温下1 000 kg/667m2覆盖的土壤表层溶液电导率峰值明显低于严吴炜[10]的春季低温状态,应该是温度高时蕹菜生长加快,吸收养分更多所致。
[19]Christenson, Bruce A. and Nan E. Johnso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Adult Mortality: An Assessment with Death Certificate Data from Michigan[J]. Demography, 1995, 32(2).
[20]House, James S., James M. Lepkowski, Ann M. Kinney, Richard P. Mero, Ronald C. Kessler and A. Regula Herzog.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Aging and Health[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94, 35(3).
[17]Dupre, Matthew E.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in Health Risks and Illness over the Life Course: A Test of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Theory[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8, 37(4).
[21]Kim, Jinyoung and Emily Durd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ge Trajectories of Health[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7, 65(12).
与以往关注中国人社会经济地位和抑郁水平之关系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采用了两期纵贯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削弱双向因果偏差。第二,分解了不同因素对抑郁不平等的贡献率,从而更为直观地展示了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对抑郁不平等的贡献程度。第三,对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既涵盖了通常使用的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又考虑了财产状况,从而更加全面地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抑郁水平之间的关系。第四,关注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精神抑郁之关系的年龄模式,从而加深了对二者间关系历时性变化的认识。第五,探究了教育对不同群体抑郁水平影响的异质性,从中发现了教育对于精神抑郁的影响不同于收入和财产的方面。
[23]Chen, Feinian, Yang Yang and Guangya Liu. Social Change and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Health over the Life Course in China: A Cohort Analysi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0, 75(1).
[24]Lowry, Deborah and Yu Xi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Differentials in China: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at Older Ages?[R].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Research Report 09-690, 2009.
[25]李建新,夏翠翠.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收敛”还是“发散”——基于CFPS 2012年调查数据[J]. 人口与经济, 2014(5).
项目化教学法的应用,解决了传感器课程的不连贯性和不系统性在讲授过程中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最终实践项目的实现,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学习效率,增加了课堂知识的容量。
[26]谢宇,胡婧炜,张春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理念与实践 [J]. 社会, 2014(2).
[27]Radloff, Lenore Sawyer.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J].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77,1(3).
[28]Budescu, David V. Selecting an Equating Method: Linear or Equipercentile?[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1987, 12(1).
[29]Wagstaff, Adam, Eddy van Doorslaer and Naoko Watanabe. On Decomposing the Causes of Health Sector Inequalitie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Malnutrition Inequalities in Vietnam[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3, 112(1).
[30]Kakwani, Nanak, Adam Wagstaff and Eddy van Doorslaer.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Health: Measurement, Computation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7, 77(1).
rulei∈Rules(访问规则)有三个组成元素:敏感话题(sti)、请求者类型(rci),访问水平(ali)。
[31]阮航清, 陈功. 中国老年人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分解——以北京市为例[J]. 人口与经济, 2017(5).
[32]O’Donnell, Owen, Eddy van Doorslaer, Adam Wagstaff and Magnus Lindelow. Analyzing Health Equity Using Household Survey Data[M].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8.
[33]Radloff, Lenore Sawyer. The Use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991, 20(2).
SocioeconomicGradientsinDepressiveSymptomsAmongChineseAdults——Evidence from the 2014-2016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ZHAO Xiao-hang1 RUAN Hang-qing2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999077, China;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MD 20742, USA)
Abstract:Using data from the 2014-2016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ults in China and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SES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income (household income per capita) and wealth (net household asset per capita).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estimated with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is high (23.4%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4.6% for depression in 2016) and unevenly distributed across socioeconomic status. Specifically,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income and wealth a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Employing the Wagstaff decomposition method, it shows that education, income and wealth account for 23%, 22% and 33%, respectively, of income-related disparities in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dition, it shows the divergence in mental health differentials with age by SES, and suggests that education contributes more to mitigating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women and agricultural Hukou holders than among men and non-agricultural Hukou holders.
Keywords:socioeconomic status; depressive symptoms; health inequality
[收稿日期]2018-09-17
[作者简介]赵晓航(1992-),男,河南南阳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阮航清(1992-),男,湖北恩施人,美国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08-0034-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804
标签:抑郁论文; 社会经济论文; 不平等论文; 家庭论文; 地位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论文;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中国香港论文;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系美国马里兰州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