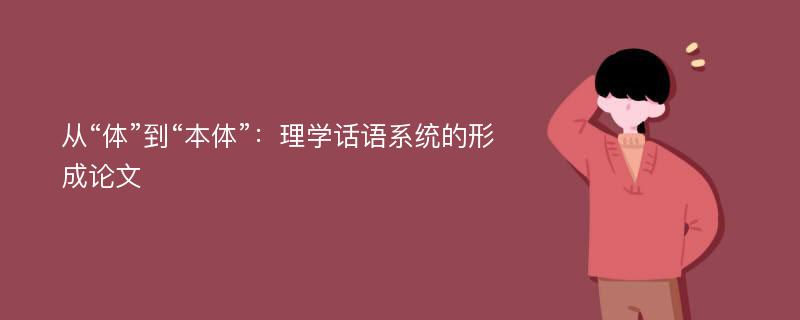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从“体”到“本体”:理学话语系统的形成
刘峰存, 丁为祥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体与用、本体与工夫不仅代表着宋明理学的基本方法,也是理学家建构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但从历史角度看,它们又具有先后继起并相互生成的特色。在中国思想史中,“体”最早是作为指谓肢体、状貌的名词出现的,以后又由人之自觉运用而成为动词,以指谓对某种性质的分有性,当然也代表着这种性质的普遍性;但当此动词再次名词化后,“体”就不断地凸显主体的涵义,并以主体作为其存在的基础。佛教传入后,由于对人生世界整体性把握的需要,所以“体”也就成为拟对象化的“本然之体”;与之相应,原本作为“体”之属性的“用”,也就成为“体”之存在表现的现象了。但如果立基于“体”之主体动用的涵义,则“用”既可作为拟对象化的现象来运用,同时也有专门指谓主体性能的“工夫”一义。这一过程,既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儒、玄、佛相融合的理论表现。
关键词: 体; 用; 本体; 工夫; 宋明理学; 话语系统; 中国古代哲学史
一、 引 言
体与用、本体与工夫都属于宋明理学中的经典话语,不理解其基本涵义,简直就无法进入宋明理学的世界。但这些经典话语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是其自身涵义不断地提炼、集中,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对其含义的再丰富。因而也可以说,体与用以及本体与工夫就典型地表现着中国文化自身之演变及其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历史。
在中国思想史中,最早对“体用”概念进行追溯的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与李二曲。顾炎武曾从李二曲的书信中读到“‘体用’二字出于佛书”一说,便立即催书李二曲,认为“体用”应当是儒家固有的概念,并举出儒家经传中言“体”言“用”的不少案例。但李二曲并不认同顾炎武的这一看法,并以答书的方式展开讨论。这里将他二人的讨论一并征引:
承教谓“体用”二字出于佛书,似不然。《易》曰:“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又曰:“显诸仁藏诸用”,此天地之体用也。《记》曰:“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又曰:“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此精粗之体。”又曰:“无体之礼,上下合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此人事之体用也。经传之文,言“体”言“用”者多矣,未有对举为言者尔。(1) 此处关于顾炎武的看法是出自李颙《答顾宁人先生》中“来书云”的转述。详见李颙《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8—149页。
顷偶语及“体用”二字,正以见异说入人之深……《系辞》暨《礼记》“礼者,体也”等语,言“体”言“用”者固多,然皆就事言事,拈体而不及用,语用则遗夫体,初未尝兼举并称。如内外、本末、形影之不相离,有之实自佛书始……然西来佛书,虽无此两字,而中国佛书,卢惠能实始标此二字。慧能,禅林之所谓六祖也,其解《金刚经》,以为“金者,性之体;刚者,性之用”。又见于所说《法宝坛经》,敷衍阐扬,谆恳详备。[1]149
从顾炎武和李二曲的这一讨论来看,李二曲显然是一种哲学的视角,而顾炎武则是文字学或历史学的视角。但李二曲的看法也只具有部分的真理性,因为其以“兼举并称”作为“体用”范畴形成的标志固然正确,但他同时又认为“内外、本末、形影之不相离,有之实自佛书始”,这一看法却是无法成立的,起码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观点。因为无论是《易传》还是《孟子》《大学》,都出现了“内外、本末、形影之不相离”的现象(详后)。这说明中国哲学史中“体用”范畴的形成,可能还有其更为深入的根源。
也许正是为了总结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20世纪80年代,方克立先生特撰《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一文,以探索中国哲学中“体用”范畴的形成与演变。方先生也从顾炎武与李二曲的讨论入手,在详细分析了他们的不同视角与观点之后,方克立指出:
《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10]198
对于顾、李的不同观点,方克立先生评价说:
指出宋明理学“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思想与佛教体用观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并非毫无道理;但是,要说佛教体用观就是整个中国哲学史体用观的源头,那是远远地违背了历史实际的。[2]
2.6.1 Lut-PC的制备及纯化 采用溶剂挥发法制备Lut-PC。取Lut和卵磷脂(物质的量比为1∶1.2)置于四氢呋喃中。于45 ℃水浴条件下持续搅拌4 h至溶液体系变澄清。减压旋蒸除去有机溶剂,于真空干燥箱中过夜干燥后即得Lut-PC粗品,置于干燥器保存备用。取制备的Lut-PC粗品,采用二氯甲烷溶解,0.22 μm微孔滤膜滤过,减压旋蒸除去有机溶剂后即得高纯度Lut-PC。继续采用无水乙醇溶解,按相同操作,即得安全性更高的高纯度Lut-PC。
二、 从“体”到“本末”
作为有具体所指的实体字,“体”字出现得很早,起码在《诗》《书》中就已经被广泛运用了。比如: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3]3 063
方苞方体,维叶泥泥。[3]1 150
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3]521
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偶。[3]4 621
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3]25
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3]3 108
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3]3 536
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3]3 532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3]5 989
在从《诗》《书》一直到孔孟对于“体”的运用中(《中庸》里面的“体”都是子思对于孔子原话的转述),其似乎只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即“肢体”之“体”,且这种含义一直到孟子都保留着,如“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3]5 852。其二则是作为名词动用的“体”,比如“体仁足以长人”“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等,“体”的这种名词动用的含义一如《墨经》所概括的:“体,分于兼也”[4]308,意即通过动用性的“体”以表现其所体对象的普遍性。不过,虽然如此,“体”的前一含义也仍在《墨经》中保留着,比如“同,重体合类”[4]315,这里的“体”就指“体貌”与“体型”而言的,所以《墨经》才会以“重体合类”来规定“同”。
摘 要:所谓白板教学,主要是指借助电子白板去完成教学引导的教学方式,也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新兴教学方式。电子白板在信息化的时代下,是与计算机等智能设备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甚至有更高适用性的教学设备,对电子白板教学在幼儿教学中的应用进行思考,能够更好地服务和改进教学。
这个茶壶与普通水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壶嘴有个过滤管,茶叶放入过滤管中,水烧开后,一壶香茶便出来了。从外形看上去挺时尚的,不过总觉得有点像古时候的尿壶,不知道使用它喝茶会不会感到恶心。
那么,原本作为名词的“体”为什么会形成动词化的转用呢?这是因为,“体”首先是和作为主体的人连在一起的,也是由人主体动作性的“体”进而转用为人的“体仁”“体物”以及“体群臣”之类,这就形成了动词化的转用。正是这一动词化的转用,也就形成了其“分于兼也”的蕴含。不过,这一“分于兼也”并不仅仅是指作为主体的人而言的,同时也可以指谓为人所“体”之事物由于人自觉地“体”从而具有“分于兼也”的特征。这样一来,作为人所“体”的事物,同时也就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性,所谓“体仁”“体物”之说正是这样形成的。但这种“分于兼也”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比如孔子所谓的“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3]3 532,这里所谓“体物而不可遗”就是指鬼神之德之神妙莫测的普遍性而言的,并且也首先是通过孔子对鬼神之德之“分于兼也”式的“体”,从而才使鬼神之德获得了“体物而不可遗”之普遍性的。
通过这一简略的分析可以看出,推动着“体”从其原始含义不断演变发展的首先是一种拟对象化的思维,(3) 所谓拟对象性(化)思维,主要指人们因为整体性把握的需要而将其所追求的事物作为一种对象呈现出来,比如老子对“道”的形容:“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二十五章》,《诸子集成》第3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页)再比如善慧大士(傅翕)形容形上本体并且为程颢、朱子所反复征引的“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傅翕《傅大士集》卷3,义乌市志编辑部2004年影印版,第4页)都是对人所蕴含其中的天道形上本体加以整体性把握而呈现出某种对象性的色彩。由于中国儒佛道三教都是一种典型的主体性思维,所以笔者将其称为拟对象性思维。 这当然也是因为“体”的重要性,因而也就有必要对“体”进行一种整体性把握的表现,于是,这就出现了所谓内外、本末之类的问题。至于“体”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演变与发展,又首先是因为其名词动用所蕴含的主体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正由于这种名词动用以及其“分于兼也”的特色,因而所谓内外、本末之类的问题就既可以沿着主体性的向度展开,也可以指向一种客观的拟对象化维度。比如孔子对“鬼神之为德”的形容,其之所以会走向“体物而不可遗”之神妙莫测的方向,首先就是沿着客观外在的拟对象化方向进行拓展的。不过在这里,首先是孔子对“鬼神之为德”之“分于兼也”式的“体”,然后才有其所谓“体物而不可遗”之类的普遍性拓展。所以,一般说来,这种通过整体性把握所表现出的拟对象化思维,实际上是沿着主体性的方向展开的。
所谓拟对象化思维与主体性的方向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呢?这就主要是从内外、本末的角度对名词动用之“体”加以整体性把握实现的。比如内与外,这无疑是沿着主体性的方向展开的,而《孟子》与《大学》就已经系统地展开了关于内外关系的思考。比如:“有诸内,必形诸外。”[3]5 999“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3]3 631显然,孟子可以说是率先将内与外通过必然性联系起来的,而《大学》则为其必然性关联追加以“慎独”的动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学》发现“小人闲居为不善”的事实,不过虽然如此,《大学》也同样看到了相反的事实:“小人闲居为不善……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3]3 631这说明,只要以拟对象化思维对“体”进行整体性把握,那么所谓内与外的关联以及其对举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走向。
892 Application of feature matching algorithm based on grid-based motion statistics in medical service robot
至于本末,就其字根而言,显然是出自一种对象性评估,而这种对象性评估在中国最早的思想流派——儒道墨三家中都广泛地存在着。比如:
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主要从事钨粉、碳化钨粉、硬质合金和切削刀具等钨系列产品的生产,是中国最大的钨粉、碳化钨粉供应商和出口商之一,是高品质硬质合金及其精密切削刀具的制造商。该公司在拥有高性能超细晶棒材的基础上,生产硬质合金整体立铣刀、钻头、铰刀以及印刷线路板用微型钻头、铣刀等,产品具有高耐磨、高韧性以及加工性能卓越等特性。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3]5 335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5]25
君子战虽有陈(阵),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4]7-8
假使孝、宣能尽其力,亦不过整齐得汉法,汉法出于秦法而已。[8]290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体”究竟是先有其名词含义,然后才有其名词动用的含义?还是先有其动词含义然后才有其名词的指谓?从中国文字的形成特点来看,一般都是先有其实指性的名词含义,然后才有其名词动用的含义。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可以认定“体”是先有其“肢体”“实体”“体貌”方面的含义,然后才有其因为名词动用的动词含义。
到了“与徐爱论学”,王阳明在表达其“知行合一”主张时又提到了“本体”。他举例说: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3]187
广东粤垦农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金人民币30,000万元,注册地在珠海横琴自贸区,运营总部在广州。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广东农垦及成员企业占65%,中国人保资产占30%,横琴金投占5%。公司2016年3月29日经省金融办批准开业,系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股的省级国有小额贷款公司。
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3]5 995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3]3 631
当《大学》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作为建构其内圣外王之道的基本原则时,国人的“本末”“终始”(包括老子之“有无”对举)的思维方式就已经在娴熟运用了。问题在于,这还仅仅是沿着“体”之向度进行主体性运用与对象性评估两方面思考的产物。
三、 “本末”的两种不同走向
随着秦汉大一统专制政权的建立,先秦所有的思想流派也都形成了会归于一的趋势。这一过程实际上从荀子就已经开始了——当荀子通过儒道融合进而又通过道墨递进的方式以形成其思想体系时,(4) 这是指从荀子到李斯、韩非的思想演进而言的。总体而言,荀子思想表现为一种儒道融合的形态;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是通过道墨思想之递进形成的。关于这一点,请参阅丁为祥《发生与诠释——儒学形成、发展之主体向度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中《现实问题之“现实”解决——法家的产生》(第281—292页)与《道墨两家之“现实”统一——韩非子的法、术、势》(第335—353页)两节。 作为先秦儒学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其对儒学与专制政权的结合;而当其将孟子所谓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5 884的五种人伦关系扭转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6]163时,也就表明孟子原本立足于个体立场上的人伦关系——“父子有亲”已经被荀子提到首位的“君臣”关系取代了。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表达顺序的问题,而是代表其考察人伦关系之基本出发点的问题;而荀子所谓“隆礼重法”的社会治理之策,实际上也主要是从其君臣本位关系推导出来的。所以,就连最能触动人之心灵的“乐”,对荀子来说似乎也一定要从君臣关系出发:“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6]379显然,凡荀子所讨论的人伦关系,无不以“君臣”关系为首出,虽然我们并不能以此来断定荀子的思想性质,但在表现其从大一统的君臣本位为出发点这一点上却是确定无疑的。这就开始了从孔孟儒学之个体性立场向大一统专制政权立场的转变。
这一转变不仅培养了大秦帝国的两位“助产士”——李斯与韩非,而且由此也形成了大一统专制政体维护其统治的基本方略。所以,即使残暴的秦王朝很快就被推翻,但继起的汉帝国在经过一段黄老之术的统治外(这才是真正的让步政策),却仍在汉武帝时代通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式实现了“刑名法术”之士的统治,即使被视为“群儒宗”的董仲舒,其作为儒者的精神也就只停留在自我立身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7]2 524一点上;至于其在国家大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则只能通过所谓“天人感应”的方式发挥一点可有可无的规劝作用。这样一来,儒学虽然与专制政权联姻,但却只能起到为王权统治之合理性进行论证的作用;至于辅佐朝政,也就只能借助墨家无所不能的“天志”来发挥一种警示作用。而由此演绎而来的经学便成为两汉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至于从今文经学到古文经学,则是从借助天人感应之微言大义到陶醉于家法传递、字句考释来维持的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模样。
关于两汉经学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历史上既有大汉天子的直白,也有后世儒者鞭辟入里的概括和分析,这里一并征引:
笔者基本赞同方克立先生对顾炎武、李二曲关于“体用”之争的分析与评论。但由于方先生此文作于20世纪80年代,其认识论的进路与范畴研究的方法往往使方先生更多地是从本体与现象的角度去理解体用关系的。就中国体用范畴之原有含义而言,当然也包含着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但却并不限于这一关系,而“体”之主体蕴含与“用”之属性功能的含义也并非认识论就可以穷究其全部含义。除此之外,方先生将中国“体用”关系之成立定位于魏晋玄学,尤其定位于玄学家王弼的体用、本末之辨。(2) 方克立总结说:“正是王弼最先赋予体用范畴以哲学本体论的重要意义,使体用、本末之辨成为魏晋玄学的主要理论支柱之一,成为带有时代特征的一种理论思维方式。”见方克立《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但如果从中国“体用”关系之具体发生而言,此中其实是包含着一条可以继续向前追溯的历史线索的。所以,笔者这里将沿着方先生的思路,主要集中于“体”之主体蕴含与“用”之属性功能的角度来继续探讨中国哲学中的“体用”关系。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扬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7]277
今之人灭天理而穷人欲,今复反归其天理。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8]273
当我们将中国的儒、道、墨三家之对象性评估联系在一起时,那么这种整体性的把握与对象性的评估实际上也就成为国人认知事物最基本的方法了;而墨子则既以“本”对举于“阵”,又对举于“丧”、对举于“学”,所以中国人“本末”对举的思维其实很早就形成了。李二曲所谓“如内外、本末、形影之不相离,有之实自佛书始”一说之所以无法成立,就因为其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未见到处。
上述3条,第1条出自汉宣帝对作为太子的汉元帝的训诫,但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以及其“纯用德教,用周政乎”的批评,则道出了汉代君主专制的本质。至于后两条,则是作为宋明理学开创者之一的张载对汉代制度与儒学的批评。在这一背景下,从今文经学到古文经学,其实不过是汉代儒生在专制体制里面获得的一个谋生的“职业”或“饭碗”而已。
国人思维的再次振兴是通过魏晋玄学实现的。魏晋玄学是以“越名教而任自然”[9]234的方式表达其对两汉经学的鄙弃之情的,仅这一点而言,也就可以看出其对两汉经学的扬弃与超越指向;这也必然会推动着其对先秦以来的本末之辨做出新的探索。同时,由于玄学家又醉心于“有无之辨”,而这两个方面就集中表现在王弼的哲学探讨中。
王弼首先是以“圣人体无”[10]639,645之说彪炳史册的,而其“体无”之“体”也坚持着先秦以来“体仁”“体物”的传统,这就是《墨经》所谓的“分于兼也”。但另一方面,王弼却通过“本末”关系的辨析,高扬起玄学家的超越追求;而这一高扬超越追求的努力,仍然是通过拟对象化的整体性把握表现出来的: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10]195
顾、李之争接触到了一个真正实质性的问题,那就是在中国哲学中,体用观念到底产生于什么时代,它们到何时才形成为一对有确定涵义的哲学范畴?由于时代和儒家立场的限制,顾、李二人都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而给后人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课题。[2]
在王弼对老子思想的这一诠释中,他从“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的角度高扬老子“有生于无”的智慧,认为“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这就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拟对象化思维与整体性把握的视角。就是说,他是把人所置身其中的生存世界作为一种拟对象,从而进行整体性的叩问,这就必然要回归于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5]25的逻辑。但王弼对老子“有生于无”的思考,却主要是通过对“本末”关系的辨析实现的,所以他认为老子的思想就可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崇本息末而已”。也就是说,王弼已经将老子“有生于无”的关系诠释为一种“本末”关系了,并通过“崇本息末”的方式高扬了魏晋玄学的超越追求精神。
从普通教师心理健康调查结果与全国常模比较数据中(见表2)可以看出,中小学普通教师在SCL-90症状自评量表的健康均分以及9个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其中只有敌对因子差异显著(P<0.01),其余8个因子差异极其显著(P<0.001)。
佛教传入后,玄学家以“本末”诠释“有无”的方式遭到冲击,这主要是因为无论是老子的“有无”还是玄学的“本末”,对于一意追求“栖神冥累之方”[11]249的僧肇来说,还算不上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之道,所以僧肇也就必须借助佛教的般若智来重新解决老子的“有无”问题。而僧肇的解决方案则是以佛教的中道智慧对“有”与“无”的一并扬弃,从而以“缘起性空”之说将现实人生归结为“空”“有”两重世界:
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虽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若有而不即真,无不夷迹,然则有无异称,其致一也。[12]52
《中观》云: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寻理即其然矣。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有非真有,虽有不可谓之有矣。不无者,夫无则湛然不动,可谓之无。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以明缘起故不无也。[12]52-56
很明显,无论是道家所辨析的“有无”还是玄学家所辨析的“本末”问题,也都受到了僧肇来自佛教中观智慧的批评;而其批评的根据,则在于佛教的“缘起性空”之说,即所谓“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意即支撑“有”的并不是有本身,而是缘起;支撑“无”的也不是真无,而是缘灭。那么所谓“有无”又是如何成立的呢?这就是所谓“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意即既然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起,因缘而灭,那么它就既不是真有,也不是真无;既不是真正的“本”,也不是真正的“末”。既然道家的“有无”包括玄学的“本末”问题都要通过缘起缘灭来获得自身存在之规定,那么这就证明了佛教的“万法无自性”——所谓缘起缘灭之“空”“有”两重世界而已。
僧肇的这一缘起性空之说既没有涉及“体用”,也没有涉及“本末”,但其“空”“有”两重世界却为人们理解“体用”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除此之外,就僧肇本人而言,他主要在于以佛教的缘起性空之说消解儒道两家所陶醉的“有无”两个世界。这一消解固然有其极为成功的一面,但佛教作为一种人生信仰却并不仅仅是为了消解这两个世界,而是为了自己的成佛追求。正因为如此,在僧肇消解了儒道两家所执著的“有无”两态生存世界后,佛教也就必须凸显人的佛性以促成其成佛追求,这一点就成为禅宗六祖慧能的主要任务。这就使慧能必须重新回到儒道两家所共同认可的“体用”世界。
据说慧能在初见弘忍时,其为自己辩解的“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13]49一说就已经为自己的主体性立场廓清了地盘,而其所自我介绍的“不离自性,即是福田”[13]50自然也就成为其成佛的主体基础。所以,当他形成“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13]80时,也就通过“自性”与“佛性”的当下统一展现了一条主体性的顿悟成佛之路。在这一背景下,慧能就既不论“有无”,也不论“本末”,而是直接就“体用”立论:“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灯是光之体,光是慧之用”。[13]126慧能这里通过“灯”与“光”来说明“定”与“慧”的体用关系,说明中国传统的体用关系已经全然被慧能加以主体性地诠释了。结合前边李二曲所征引的“金者,性之体;刚者,性之用”,包括慧能在广州法性寺所阐发的“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13]175,说明整个客观世界也都被慧能以主体性的原则统摄到其心性体用关系上来了。这样,从王弼、僧肇对带有客观面相的“本末”“有无”的辨析到慧能完全立足于主体性的“体用”关系之阐发,也就代表着从中国传统的“本末”思维出发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走向。
四、 “本体”与“体”——理学的两种不同落实
正因为从玄学到佛教对于“本末”“体用”思想的精彩发挥,因而也就构成了宋明理学崛起之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但问题在于,这样一种“体用”“本末”式的思维,其究竟应当沿着主体性的方向拓展还是应当沿着对象性的立场展开?而在主客并存的条件下,究竟是由“体”以形成所谓“本体”还是由“本体”而收摄为“体”?凡此,都集中表现在作为宋明理学开创者的张载哲学中。
“体”与“本体”两种不同的表达,在张载哲学中都已经出现了。但其究竟是由“体”而走向“本体”呢还是由“本体”而走向“体”?让我们通过张载对其哲学的自我表达来澄清这一问题: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之。[8]7
Study on the variation law of pollutant mixing zone in the bend river
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体虚空为性,不知本天道为用,反以人见之小因缘天地。明有不尽,则诬世界乾坤为幻化。[8]8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学习也是如此。实践证明,该方法无论是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还是学习成绩都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我要求学生们巧读书、会读书。读书要有计划性、目的性。在以前的教学中,我给学生五分钟时间阅读教材,但讲课中发现这对学生理解问题的帮助不大,原因就在于只注重读的过程,而没有提出这节课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即缺乏目的性,阅读也只能流于形式。因此,我指导学生带着问题阅读。首先粗读,通过把握本课目与目之间的关系大致了解本课的主要内容与脉络。其次,细读,用笔划出你认为重要的知识,或你认为比较难的知识,再或者你的疑惑、你的收获。
这是集张载一生理论创造之大成的《正蒙》首章中的内容,但这里却既出现了“气之本体”的说法,同时也出现了其批评佛老的“体用殊绝”一说,前者是以“本体”出现的,而后者则是以“体用”之“体”的方式出现的,包括“体虚空为性”一说。这就出现了其“本体”与“体”之究竟如何形成的问题。
通过试验示范,云天化复合肥14-8-20受到当地棉花种植户的一致认可。在试验示范田的跟踪过程中观察发现使用云天化复合肥的棉花植株茎秆粗壮、根系发达,分枝较和花蕾较多,叶片较厚且颜色较深;同时实现了棉花的增产增收,给农户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在当地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但在张载哲学中,也有以“体”来表达并定位“太虚”的情况,比如其如下说法:
太虚者,气之(所)体。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故神之应也无穷;其散无数,故神之应也无数。虽无穷,其实湛然;虽无数,其实一而已。阴阳之气,散则万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则混然,人不见其殊也。[8]184
在这一表达中,由于“气之体”与“气之本体”都是指“太虚”而言的,而张载这里所运用的“体”则正是对孔子“体仁”“体物”与“体群臣”以及《墨经》所谓“分于兼也”的直接运用。就这一点而言,所谓“气之本体”一说无疑是高于“体”的;即就张载所加注的“所”字来看,也说明其所谓“气之(所)体”就指对象性的“气之本体”而言。如果再参酌以张载对其理论之体系化表达,比如从“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8]9来看,则其所谓“太虚”绝不可能是作为“气”的说明语或形容词来运用的(因为这就完全无法说明“由太虚,有天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这种具有具体指谓的表达了)。这就证明,“太虚”就是张载通过“稽天穷地之思”(5) 范育在《正蒙序》中说到:“子张子独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与尧舜孔孟合德乎数千载之间。”见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页。 所形成之客观的天道本体;正因为其客观性的要求,所以张载才会有“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这样的拟对象化表达。
那么所谓“体”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虽然张载“太虚者,气之(所)体”一说对于“体”的运用是严格按照孔子的用法,而且也符合墨经“分于兼也”的基本规定,但从其对老子“有生于无”所导致的“体用殊绝”的批评来看,则其所谓“体用”显然已经不再是动名词式的运用,而是直接是作为名词出现的,也是在慧能所谓“定体慧用”基础上对于佛老之学反戈一击式的批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本体”显然是从客观的角度并且也是作为对认知对象之整体性把握角度来运用的,但所谓“体”则仍然是在主体自觉肯认的基础上以“分于兼也”的方式来言说的。也就是说,从“本体”到“体”,是从一种拟对象化、整体性把握的客观性认知角度到内在性之肯定与“分于兼也”的方式加以展现的,所以“体”才会与“用”构成一种固定的搭配。比如对佛老而言,站在客观的对象性立场上,便可以说佛老是“以空无为本”,即以“空”和“无”作为其“本体”,但如果进入佛老之学的内部或站在佛老的主体性立场上,则又可以说其理论不过是一种“体用殊绝”,即其“体”与“用”并不统一。所以,张载这里“体用殊绝”的说法,实际上是在接受其“体用一致”理论基础上对于佛老之学反唇相讥式的批评。
受国务院委托,水利部部长陈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农田水利建设工作情况。该报告在本次会议分组会议审议中获得充分肯定。委员们认为,农田水利建设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1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突出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一年多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积极落实中央文件要求,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工作,持续增加投入,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
这样一来,“体”与“本体”不仅存在着不同价值观立场上的根源,而且也存在着不同认知视角的根源。从认知视角而言,“本体”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并且也是从对象认知的视角立论的,比如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就是在“稽天穷地之思”的基础上“先识造化”的结果;如果以此指谓佛老,则只能说其是“以空无为本体”,即佛老所认知的“本体”不是“空”便是“无”,所以才有对老子“虚能生气”之“虚无穷,气有限”之“有生于无”的批评;至于佛教,则其所谓以“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正是“以空为本”的表现,而所谓“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一说,则又是其“以空为本”思路所以形成的认识根源。但“体”则有所不同,与其说它是不同人生价值观之相互观照的产物,不如说它是同一价值观内部之自我审视、自我观照的表现,因为它始终建立在主体之自我肯认的基础上;也只有在主体自我肯认的基础上,“体”才与“用”紧密相连,而“用”本身也就成为“体”之内在本质的具体表现了。至于张载之所以要以“体用殊绝”来批评道家的“虚能生气”,而又以所谓“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来批评佛教,则是因为与佛教相比,以为“虚能生气”的道家毕竟还属于中国思想界的毛病,虽然其与佛教“天人不相待而有”同样属于“体用殊绝”,但佛教还是不足以运用“体用殊绝”来批评的。
正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张载之后“体用”关系就只用于儒家思想之自我肯定了。最典型地表现着这一精神的就是程颐的《易传序》,比如被其形容为“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14]582的《易传》就被程颐作了如下概括:“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其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14]582。显然,这里所谓的“体用”,都是从人伦道德实践的角度展开的。因而由此之后,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也就成为宋明理学关于体用关系的一种经典表达。
五、 从“体”到“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
从“本体”概念的形成到“体”概念的凸显,表现了宋明理学从客观性认知到主体性担当的进展。但理学的发展并不止于此。由于方克立先生对“体用”关系的分析主要是从“本体”与“现象”的角度展开的,而且也比较侧重于从朱子到王夫之的认识论进路,(6) 方克立指出:“宋代以后,不论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还是唯物主义哲学家,都经常从本体和现象的关系的意义上来使用体用范畴。不论他们对‘体’和‘用’的内涵作了怎样不同的规定,对二者的关系作了怎样不同的说明,但是只要是从本体和现象这个意义上来了解和使用体用范畴,有些基本的特征还是他们所一致认定的,没有明显的分歧。”方克立《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因而笔者这里将主要从“体用”关系之主体性角度展开,以探索宋明理学是如何将“本体”与“现象”“体用”化的,从而形成一种“本体”与“工夫”的特殊结构。[15]
在这一点上,最典型的莫过于王阳明心学。关于阳明对“体用”关系的认识,还在“与徐爱论学”之前,他的《答汪石潭内翰》就明确谈到了“体用”关系。王阳明写道:
性,心体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无以加矣,执事姑求之体用之说。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者也。虽然,体微而难知,用显而易见也。执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谓“自朝至暮,未尝有寂然不动之时”者,是见其用而不得其所谓体也。君子之于学也,因用以求其体。[16]146-147
由此之后,由“体”之主体性的“分于兼也”与由整体性把握而形成的对象性评估,也就成为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请看这种方式方法在先秦典籍中的运用:
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16]6-7
这两段引文,前者在于强调“体微而难知,用显而易见也”,就是说,所谓体用一源,从可见可闻与可以感知的角度而言,二者无疑就源于“用”;但从二者更为根本的关系来看,则体用一源又必须根源于“体”,所以才有“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者也”。而在其他地方,阳明又说:“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16]17。其次,从阳明所谓“性,心体也;情,心用也”来看,则“性”与“情”就是一种体用关系,而“性”又内在于“心”和“情”,因而其所谓的“体”,总是指内在之体而言的,这就排除了对象化的可能,从而使原本作为天地万物之形上根据的“本体”一说除了内在化于“体”之外再无其他存在的可能。当然,在阳明看来,“本体”还可以在“本然之体”或“心体之同然”的涵义上存在,从而成为“本然关系”“本来体段”的涵义,所以,直到其晚年的《答顾东桥书》,阳明还在强调:“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16]42。在这里,从“知行本体”“知行之体”以及“知行体段”来看,其所谓“本体”也就成为“本然之体”或“内在之体”的指代了。这等于是王阳明以主体的内在之“体”消解、融摄了原本作为天地万物形上根据的“本体”。
Energy simula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 potential analysis of an office building in Qingdao
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阳明作诗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16]790。那么,这是否是说阳明就像慧能一样也是将“风动”“幡动”一概归结为“仁者心动”的呢?如果仅从其理论及其表达形式来看,那么阳明确有这一走向,而其“万化根源总在心”的说法也确实包含着这种可能。但王阳明又确实不同于禅宗,这就在于王阳明既讲“本体”,同时也讲“工夫”;而所谓“工夫”不仅是“本体”的表现,同时也是“本体”之所以成为“本体”的决定性因素。当然从总体上说,“本体”与“工夫”也就如同“体”与“用”一样,也可以说是“体”与“用”的一种逆运算:当立足于主体的内在之“体”时,那么主体的一切外在活动都可以说是“用”,当然也可以说是本体的发用流行;但如果以内在的本然之体包括本然体段作为追求对象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体之启动发用,由于完全以内在本然之体作为追求指向,因而这时候主体的一切活动,也就都可以视为“工夫”了,而严格指向“本体”的工夫,也就可以称之为“本体工夫”,即内在的本体精神直接发用为“工夫”。
“本体”与“工夫”的这一指谓几乎成为阳明晚年的主要“话头”。比如“天泉证道”后,由于王龙溪与钱德洪将王阳明“三有一无”相统一的“四句教”割裂为“四无”与“四有”而又一时无法统一,所以这两大“教授师”又追送阳明于严滩,继续讨论“四无”与“四有”的关系问题:
个人能够与潜在的侵害者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能够减少侵犯行为的发生。Gail(2009)[24]研究表明,与顾客维持积极联系,避免触发顾客的厌倦和挫折感是第一线情绪劳动者避免受到侵犯的有效方式。Salman等(2010)[25]研究提出,员工与顾客的成功互动依赖于员工能够创造一种吸引人的、积极的情绪氛围,包括能够付出极大努力控制消极情绪,保持积极情绪状态,让自己有适当的声调、面部表情、身体语言等。这些研究表明,员工培养良好的沟通能力,善于与潜在的侵犯行为实施者良好沟通能使自己免受侵犯。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16]124
这一“本体”与“工夫”以及“ 实相”与“幻相”的反复言说,绝不是一种理论上的绕口令,而主要在于从“本体上说工夫”与从“工夫上说本体”两个不同的角度。所谓从“本体上说工夫”就是从“体”——“本体”之启动发用的角度看工夫,这时候就必须坚持“有心”,一如人之实践活动的发起必须要有对善与价值理性的执著一样;这也是儒与佛禅之间一个最根本的区别。但是,一当转向具体的工夫实践,即所谓“工夫上说本体”时,这时候就必须坚持所谓“无心俱是实”。因为如果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仍然处处执著于自己“有心”的出发点,那么这就不仅错却了当下的实践工夫,而且其“有心”的出发点就只能成为对具体实践的干扰了。所以在这一层面,儒与佛老又是完全相通的,而所有的文化、智慧,也都是在这一层面上相通并融合的。
但由于王阳明对“体”与“用”以及“本体”与“工夫”的灵活运用及其高度的思辨化诠释,因而这一点也造成了阳明弟子后学中的一个很大的毛病,这就是为刘宗周、黄宗羲所讽刺的人人谈光景、说效验,也就是到处卖弄思辨的理论光景的招数,所以刘蕺山就提出以“慎独”来修订。到了黄宗羲,由于这种风气有愈演愈烈之势,于是黄宗羲也就提出了一种新的评价与批评的标准:
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万物之万殊也。[17]3
所谓“心无本体”当然不是说心中就没有“本体”,而是说所有的“本体”都只能落实在具体的“工夫”中,并且也只有通过“工夫”来彰显“本体”,而那种完全脱离“工夫”的“本体”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思辨的理论“光景”而已。当黄宗羲这样来归结阳明心学时,其实也就回到了国人最初的传统,这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8]2 878也就是说,只有具体的实践工夫,才是检验其“本然之体”是否自觉的试金石。
这样看来,阳明心学不仅拓展了“体用”关系,而且将由“体用”关系拓展而来的“本体”与“现象”、“本体”与“工夫”全然囊括于“体用”模式之中了。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诠释的问题,而是其通过主体精神的高扬与拓展,从而将“本体”所指代的天地万物之形上本体及其作为“现象”之发用流行统统含括于主体道德实践的行为宇宙之中,这就使整个世界不仅处于道德心体的观照之下,而且整个世界也必然会映现出道德的色彩。王阳明之所以被视为中国心性之学的集大成者,也就在于其以“体”与“用”的关系来讨论“本体”与“工夫”,进而探讨“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从而使整个世界完全成为主体之“体” 与“用”的关系。
近代以来,从洋务派以“本末”(7) 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载《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孙家鼐也说:“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参见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4页)实际上,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之主体性立场上所能得出的必然结论,只要站在中国文化的主体立场,也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对洋务派而言,重要的并不在于其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立场,而在于其已经认识到中国当时的格局是必须“辅以西学”,并坚持对中国文化“以西学补之”“以西学还之”。这就是所谓“知其缓急,审其变通”。 来界定中西学术到张之洞以“体用”关系组装“中学”与“西学”,(8) 提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人们马上就会想起严复对张之洞的责难与批评。其实在这一问题上,张之洞的看法是积极的,而且也是最具建设性意义的,而严复反驳之所谓“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载《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9页)的说法反而是消极的。因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之说起码还坚持了一种对西学之开放、吸取与积极融合的态度,而严复之所谓反驳则只能使中国文化僵死于其传统的体用模式中。 再到熊十力通过“体用”关系界定“见体”之学并由此发挥其“量论”建构的展望,既表现了传统“体用”模式的成熟,也表现着国人试图通过传统的“体用”模式来吸纳西学、开发“量智”的努力。而熊十力将原本作为“玄学”所穷究的“实体”(9) 熊十力在其《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开宗明义地写道:“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实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2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落实并诠释为“一切物的本体”,[19]13也就更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哲学的这一指向。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中学”与“西学”一直未能改变其彼此外在的格局,而“量智”与科学精神屡遭扭曲的现实,也说明中国传统的体用模式遇到了全新的挑战。如何能使传统的体用模式在“中学”与“西学”“性智”与“量智”之间实现自由转换而又不扭曲其各自的原有含义,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体用”之学所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这一指向,也应当是黄宗羲“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一说的应有之义。
[参 考 文 献]
[1] 李颙.二曲集[M].陈俊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
[2] 方克立.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J].中国社会科学,1984(5).
[3] 十三经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4] 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以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5] 诸子集成: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 张载.张载集[M].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9]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0]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 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12] 张春波.肇论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3] 丁福保.六祖坛经笺注[M].济南:齐鲁书社,2012.
[14] 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 丁为祥.宋明理学形上本体意识的形成及其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16]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7]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3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9]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3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From “Body” to “Ontology” ——The Formation of the Neo-Confucianism Discourse System
LIU Feng- cun, DING Wei- xiang
(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 ,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Xi ’ an 710119, Shaanxi )
Abstract : Body and use, ontology and Gong Fu , not only represent the basic methods of Neo-Confucianism, but als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systems by philosophers.However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cessively starting and generating each oth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body” first appeared as a noun referring to the body and appearance, and later became a verb by the conscious use of human beings, with the meaning of a certain nature, of course, also representing the universality of this nature; but when this verb is re-nominized, the “body” constantly highlights the meaning of the subject and uses the subject as the basis of its existence.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due to the need to grasp the integrity of the world of life, the “body” became the “natural body” of the objectification; correspondingly, the “use” originally used as the attribute of the “body” has become a phenomenon of the existence of “body”. However, if the meaning based on the subject of “body” is used, then “use” can be used as a phenomenon of quasi-objectification, and there is also a “Gong Fu” that refers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ubject. This process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tself, but also the theoretical express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Xuan and Buddhism.
Key Words : body; use; ontology; gong fu;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the Ming Dynasties; discourse system;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图分类号: 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9)06-0116-12
收稿日期: 2019-05-22
DOI: 10.15983/j.cnki.sxss.2019.114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宋明道学核心价值研究”(15ZDB008)
作者简介: 刘峰存,男,陕西绥德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丁为祥,男,陕西西安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杨 军]
标签:体论文; 用论文; 本体论文; 工夫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话语系统论文; 中国古代哲学史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