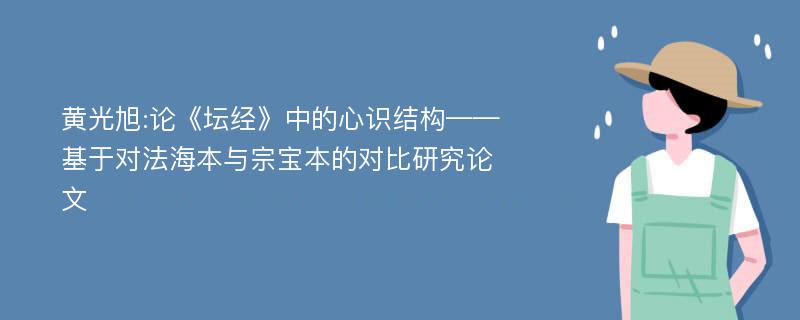
[摘 要] 法海本与宗宝本《坛经》虽然都将“六根”称作“六门”,但二者所建立起的心识结构却完全不同。法海本所主张的心识结构是自性在思量作用下生出万法,再由超越诸法及六门的物质性而生六识。而宗宝本的心识结构是以自性为根本出发点,在内转生出思量识,向外生出六尘和六门;其中思量识又进一步转生出前六识,构建起一心的三个层次。法海本的心识结构类似于“一种七现”,继承和发展了真谛系的学说,比较契合《坛经》的整体思想。宗宝本的心识结构更接近“八识现行”,吸收了玄奘系唯识思想的特长,在心识理论上较为精密。
[关键词]心识结构 《坛经》 六门 含藏识 转识
《坛经》是中国佛教南宗禅的根本经典,其思想来源相当复杂。概而论之,般若思想和如来藏思想对《坛经》理论的形态影响较大,毘昙式和唯识式的理论构建在《坛经》中并不多见。但例外的是,经中记载慧能在圆寂前不久,教授弟子“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1](P343),[2](P360)的说法技巧,讲述了含藏识、转识、六识、六门等内容。短短几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上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心识结构。虽然法海本与宗宝本在文字上只有细微差别,但二者所表现出的心识结构却迥然不同。
一、六门之喻
在对十八界和十二入进行解读时,《坛经》说:“何名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何名十二入?外六尘,中六门。”[1](P343)这里的“六门”就是通常所说的“六根”。在一般的佛教语境中,用以指代眼、耳、鼻、舌、身及意的法数即“六根”。其中“根”一字,是指人体的感觉器官(浮尘根)。如果进一步引申的话,还可以指这些器官所具备的认识能力或认识功能的物质表现形式(净色根)。《俱舍论·分别根品》中说:“……根是何义?最胜、自在、光显名根。由此总成根增上义。……眼等五根各于四事能为增上:一庄严身,二导养身,三生识等,四不共事。”[3](P13)根的体胜,名为最胜;根的用胜,名为自在;根的体用双胜,名为光显。为了体现根的殊胜,可以从根的作用角度来观察。根的增上作用有4种:一是让身体比较好看,二是能够使人趋利避害并让身体受用,三是能够引生相应的识及心所法,四是各根功能不相混杂。早期佛教主张根是识产生的必要条件,“经由六根而生六识”的观点即使在瑜伽行派思想中仍保有一席之地。[4]
而在任何一个版本的《坛经》中,“六根”都变成了“六门”。虽然“六门”的用法在佛教文献中也不鲜见,但到了慧能的时代,依据玄奘所译经典而建立起的佛学话语表达体系已经基本完成,奘译惯用的“六根”早已流行。《坛经》不说“六根”而用“六门”反而成了一个特殊情况。“门”字除了普通的用法外,在佛教语境下有其特殊的涵义,如“门别不同,故名为门。又能通入,趣入名门,舍相证会,名之为入”。[5](P481)也就是说,佛教中“门”的意思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表现分类差别,另一个是说明能够从某处通向另一处。《坛经》这里讲的“门”,在第一种用法上表现得并不明显。因为经文中并没有关注六根的差别,而且这种“有分别”的思想正是《坛经》所极力反对的。从六根导向生识的功能这个角度来说,将“六根”称为“六门”是比较合理的,这里是采用了“门”的第二种涵义。
商量来商量去,我俩只商量出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一个字:拖。李老黑不是给我一个月的期限吗,我就给他来个消极怠工,拖一天是一天,不做任何准备,他总不至于让自个的闺女像邻居串门一样给嫁过来吧。再一点,就是抓紧摸清李老黑的真实想法,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然后再想对策,这才是最要紧的。
《坛经》此处的“门”更多地取比喻义。法海本有这样的一个比喻:“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1](P341),[6]宗宝本中的比喻基本相同,只是将“心即是地,性即是王”一句改为“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 。[2](P352)新增的“王居心地上”这一句的涵义与宗宝构建的心识结构是相适应的,这一点将在后文讨论。这里的比喻也不难理解,“门”就是一个沟通内外的通道。这里的内和外,不是简单的内意门和外五门,而是更内在的心或性和在凡夫看来完全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
通过以上简单讨论可以得知: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关节疼痛评分得到了明显的改善,P<0.05。主要原因有:关节镜下清理术主要是通过刨削吸引器械切除增生滑膜和游离碎片,然后切除打磨增生骨赘,修整半月板,关节镜手术可以有效的清除患者关节内炎性刺激物,然后清除蛋白溶解性金属蛋白酶和软骨碎屑等,调节患者的关节液渗透压和酸碱度,及时补充电解质,改善患者的正常滑液分泌和关节内环境,该治疗方法跟保守的药物治疗相比,可以更加有效、直接的缓解患者临床症状,缩短治疗时间[5]。
既然内外相通,于是就产生了“出”和“入”的问题。换言之,在心识的活动中,有可能出现作为“王”的“性”通过“六门”向外驰求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外在的一些东西经由“六门”来影响城中“王”的情况。两个版本在这一点上也是有分歧的:法海本不偏废讲“入”,“入”则要求善护六门,不让外在的尘劳染污城内之地和性王;而宗宝本更侧重谈“出”,“出”则更能发挥王的作用,使得外在也转染成净。前者包含出离,希求离苦得乐;后者凸显慈悲,反身普度众生。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就体现在一出一入之间,这也是六门在佛教徒的修行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二、法海本的心识结构
法海本《坛经》对心识结构的表述是这样的:
三科法门者,荫、界、入。荫,是五荫;界,是十八界;入,是十二入。何名五荫?色荫、受荫、想荫、行荫、识荫是。何名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何名十二入?外六尘,中六门。何名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是。何名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门,六尘。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思量即转识。生六识,出六门、六尘。是三六十八,由自性邪,起十八邪;若自性正、起十八正。恶用即众生,善用即佛。用由何等?由自性。[1](P343)
《坛经》对“荫、界、入”的解释并没有显著的创新,但其中对“十二入”的解释却和心识结构直接相关。“十二入”包括了“六尘”和“六门”两个方面: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六门是眼、耳、鼻、舌、身、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六尘”对应的形容词是“外”,“六门”所用的形容词是“中”。色等六尘是外在性的,这一点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眼等六门为什么是“中”而不是“内”呢?“内”是与“外”相对的概念,如果单纯从十二入的角度来看,六尘是外,则相对应的六门就应该是内,这也或许是宗宝本将“中”改“内”的直接原因。但在法海本中,解释十二入之前,先讲了十八界的概念,十二入即是十八界的前十二界。所以将六尘和六门放到十八界当中考察的话,与外六尘相对应的应该是内六识,而六门既不能说是内,也不能说是外,只能用一个“中”来形容。既然六门是“中”,而不是“内”,那这里所说的六门更多地是在强调具有物质性的、作为感觉器官的六根(包括浮尘根和净色根),而非功能性的六种认识能力。因为只有物质性的根才能说既不是识,也不是尘,居于内外之间。而纯粹的认识能力及其所依则应完全归属于“内”。
剑鼻蝠生活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属于杂食性动物。蝙蝠科动物的吻鼻部均长有鼻叶,这是一种构造复杂的皮肤衍生物,和蝙蝠自身具备的发射超声波的功能息息相关。
自性的功能是含藏万法,但现实世界的存在要求说明万法是如何从一种含藏的状态而成为显了的。《坛经》以“思量即转识”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识中含藏的万法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万法,前者是隐,后者是显,使隐变显的动力就是“思量”。受玄奘系唯识思想的影响,“思量”经常被解读为第七识,这也和“转识”的名相匹配。这种解读在宗宝本的心识结构中是合理的,但在法海本中却并不适用。因为如果转识被当作第七识的话,那下句“生六识,出六门、六尘”中“生六识”的主语则应该是第七识。虽然第七识生六识是可以被允许的,但“出六门、六尘”的主语又是什么呢?显然第七识或六识都不合理,因为第七识所生的我执和外在六尘并没有直接相关性,而六识也是如此。所以此处的“思量”应该就是指思量这个行为本身,思量这一行为导致了含藏识的转变。“转识”就是“转变含藏识”,这里的转变就是识中含藏的万法变得显了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思量”的作用下,自性之中含藏的种子向外发生为现实的万法。自性生万法就是一个由内而外、由功能而至物质的物化过程。
既然六识的产生是一个由万法而至六识的内化过程,那这个过程的起点——万法是从何而来的呢?经文中说:“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万法是自性之中本来具足的,也正因为自性可以包罗万法,所以可以被称作含藏识。含藏识即是阿赖耶识,其作用也是非常清楚的,即“含藏万法”。[8]自性,也就是含藏识,和六识一样,不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功能性的作用。因为万法是至多无外的,不可能有某样物质性的东西可以大到包含万法。只不过含藏识的功能是含藏,这一点与表现为了别功能的六识不同。
居于“内”的六识又是如何生起的呢?经文说:“法性起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门,六尘。”六尘、六门和六识都是依法性而起,这是从根本上说的,因为法性是“空无我所显真如,有无俱非,心言路绝,与一切法非一异等”。[7](P6)但因为一切法都可以说是依法性而起,所以具体到六识生起这个问题,还是离不开对六尘、六门的考察,必须澄清六识与六尘、六门的关系。经文中除“法性起六识”一句外,还有“生六识,出六门、六尘”的表述,这是有意识地将识、门、尘三者放在一起讨论。但这一表述本身就存在较大争议:较晚出的惠昕本《坛经》在“六尘”前加“观”字,经文变成了“生六识,出六门,观六尘”,则识、尘、门三者是平行的关系;而在大英博物馆藏和敦煌博物馆藏的法海本中,均无这一个“观”字,则意味着“生六识”与“出六门、六尘”并列。因此可以认为,在法海本的心识结构中,六识的生起和“出六门、六尘”有密切的关系。这里的“出”不能理解为由内而外的“出”,因为这种“出”可以出六门但绝不可能做到出六尘。“出”在这里解释为超越、出离更为合适,“出六门、六尘”就是要超越六门和六尘的共同特性——物质性。换句话说,六识不是物质性的东西,而纯是了别,是功能性的作用。从“出六门、六尘”进而“生六识”实质上是一个由外而内、由物质而至功能、由万法而至六识的内化过程。
至此,法海本《坛经》建立起一个自性在思量作用下生出万法,再由超越诸法及六门的物质性而生六识的由内而外再回归于内、由自性而物化再内化的心识流变结构。在这样的心识结构下,经文中各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非常清晰的。“法性起六识”一句是总说,强调五荫、十二入、十八界都不离真如自性。接下来三句按照逻辑顺序进行分说:“自性含万法”一句说明自性至大,并描述了万法在含藏位的状态;“思量即转识”一句说明世间流转的动力,并描述了自性由内而外的物化过程;“生六识”一句描述了自外而内的内化过程。
这样的心识结构对于解决“自性邪”问题有很大启发。《坛经》不止一次提到过“自性清净”,如“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世人性本自净”等。既然自性清净,那怎么还会有“自性邪”呢?其实自性就是含藏识,含藏识是一种功能而非物,既然自性只是含藏的功能,那就根本不存在善和恶的问题。这种含藏的功能非善、非恶、常清净,所以说自性清净。但是自性之中含藏的万法是有正有邪的,这些万法的种子显发出来的时候,正邪才有了区分。在引生出的正邪业用上,假立“自性正”“自性邪”之名,但实际上自性本身仍不能冠以正邪之名。换而言之,思量自性中的邪法,邪法就会显现于前,六尘、六门、六识起邪业用。反之,思量正法亦然。所以趣向解脱的修行也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断思量,没有思量就不会出现自性不能自守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在没有办法断思量的情况下,思量正法,使产生的业用为正。
三、宗宝本的心识结构
在宗宝本中,心识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2](P350)
法海本与宗宝本《坛经》心识结构的不同也在这里。法海本中的自性或含藏识仅仅是种子,其在思量的作用下转生出万法,万法内化而生六识。这种心识结构虽然在末那识的问题上与《摄论》稍有差别,但因为只是种子与六识的差别,所以基本上与“一种七现”的结构相同。宗宝本的含藏识和转识都被视作为具体的识;自性在内生出思量识,再由思量识生出六识;同时,自性作为能变的识,直接在外生出根身、器界等相。这与《成唯识论》“八识现行”的心识结构高度契合。
“师长话语”给人的感觉始终是一种严谨、拘束的状态。在中国这样的礼义之邦,适当的严肃能够树立一定的威严,但面对现今普及化的大学教育,过于严肃的话语方式很难起到实质性的教育效果。学生不会对大而空的套话、官话感兴趣,他们所需要的是新时代励志教育所注入的新的思维话语模式。
妄执含藏识的第七识实际上就是“若起思量,即是转识”中的“转识”。这里的“转识”不同于法海本中的“转变含藏识”,而是具有恒审思量功能的具体的识。法海本的“转识”只能是动宾短语而非名词,因为“转识”不可能“出六门、六尘”。而宗宝本中的“转识”可以而且必须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否则后一句“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缺少了能生、能出、能见的主体。“转识”区别于六识和第八含藏识,称作第七识;又因以含藏识为所依而转起,称作转识;又因具思量功能,称作思量识。转识执着于含藏识所具备的含藏万法的功能及其所含藏的万法,并且恒常相续地进行思量,错误地生起了“我”的概念,妄认有一个“我”存在,最终在个人认识层面上形成主体之“我”与客体之外物的对立。
入选标准:①颅脑CT或MRI检查下均发现梗死灶;②有糖尿病既往史;③入院时随机血糖值均高于正常水平;④梗死灶不再发展、病情稳定。
基于大乘佛教分别心、意、识的立场,唯识学进一步阐述了心识的结构,但不同传承的唯识思想对于心识结构的认识大相径庭。《摄大乘论》主张:“心体第三,若离阿赖耶识,无别可得。是故成就阿赖耶识以为心体,由此为种子,意及识转。”[13](P134)真谛系宣扬的唯识思想认为:如果从自外而内、由浅入深的角度来看,心在心、意、识三者中应该放在第三位来说;心就是阿赖耶识;因为心与阿赖耶识是等同的,所以心就是无量的种子;在这些种子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末那识与前六识,并且发生功能作用。而玄奘系的唯识思想有另一套心识结构。《成唯识论》中虽然也引用了诸如“阿赖耶为依,故有末那转。依止心及意,余转识得生”[7](P20)这样的偈颂,但其旨趣终归于世亲(Vasubandhu)在《三十论颂》中说的“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识所变,此能变唯三,谓异熟思量,及了别境识”。[14](P60)玄奘虽然也认同推动世间诸法产生和变化的根本原因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但更强调凡夫看见的世间种种相是阿赖耶、末那和前六识三种能变的识转变而产生的结果。三能变的各自转变意味着阿赖耶识不但是末那与前六识的种子,而且是能够产生现行的识之一。从种子的角度说,阿赖耶识是根本;从现行识的角度说,八识同是心法,阿赖耶识与前七识平等。印顺法师曾概括了《摄论》的心识结构,并兼谈《成唯识论》的心识结构:
1)作业过程中,导线未与横杆上凹槽或挂钩固定,较容易从凹槽或挂钩中脱离,悬在空中不受控制或与支架上部分金属材料短接,对作业人员造成安全隐患;
六识从转识生,转识从含藏识生,所以从根本上说,六识依于自性而生。六门和六尘的产生直接和含藏识相关,是含藏识中直接生出的现行法,所以六门和六尘也是从自性生。这一方面进一步阐释了“自性能含万法”,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能含”背后还隐藏了“能生万法”的可能性。但是《坛经》并不重视这种“能生”,而是从体用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皆从自性起用”就是说自性是体,从自性之体而生起了与之对应的用。这里的用是对十八界的认识,而十八界又可以代表一切法,所以依于自性之体而起用可以看作是对一切法生成的说明,也是对一切法本身的认识。
同法海本面临的问题一样,既然“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则自性邪的出现会遇到逻辑上的困难:作为体的自性是本来清净的,是不可能邪的,但当起用时就可能分出正邪。既然所起之用是对一切法的认识,那么“恶用”就是错误的、违背佛教理论的认识,“善用”是正确的、符合佛教理论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假立“自性若邪”“自性若正”。这个问题再反过来说,若对于法的认识正确,则一切显为正;若对于法的认识错误,则一切法显为邪。所以自性的邪正不是真正的自性有邪有正,而是假名的若邪若正。这种诠释正契合般若系典籍中极为推崇的“佛说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的思维方式。
综合上文所述,再来看之前提到的比喻——“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前两句的比喻很清楚,是在说眼、耳、鼻、舌、身、意六门。“性是王”也好理解,是说作为体的自性具有大势用。以“地”作喻的“心”不是特别好理解,但根据整体的心识结构,可以推测“心”所指应该是含藏识、转识和六识的集合体。心不可能只是含藏识,因为含藏识是王,而地和王毕竟不完全相同;而心又必须包含含藏识,因为无论是王还是六门,都需要由地来承载,不可能出现离于承载体的王和门。所以包含了三类功能而又不离于含藏识的三类识的集合体,就是承载一切的大地。“王居心地上”才从人的角度赋予了地存在的价值。所以对于一片土地而言,较之于城、门等,王才是最重要的存在。同样地,在三类识的集合中,作为王的自性含藏识是最根本的。
[1]法海集.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C]// .大正藏(第48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四、对唯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对心识结构的讨论既非南宗禅所长,也非中国禅师们的兴趣所在。但法海和宗宝能够在《坛经》中提出各自的心识论,无疑是与初唐时期唯识思想的兴盛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在进行文本创作的过程中,虽然他们不在心识上多作论述,但也必须对之前的理论问题进行回应,并将之吸收融合到自己的组织架构中。
精装修的施工周期管理、质量要求等作为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精装修的施工工序顺利开展存在较大关系。部分管理人员由于没有意识到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导致其没有将质量要求与相关规范作为基础对施工质量进行控制,也没有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使精装修工程施工质量无法获得保障,还会浪费施工成本。
佛教对心识结构问题的探讨源远流长。心识结构问题最初的形态是对心、意、识三者关系的讨论。心、意、识的概念虽然在非常早期的佛教中就有所提及,如《杂阿含经》卷二第三十五经就提到:“比丘,此心、此意、此识,当思惟此,莫思惟此,断此欲、断此色,身作证具足住。”[9](P8)南传《长部》第一经——《梵网经》中的表述与《杂阿含》有相通之处,将心、意、识三者视作同类事物,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心、意、识与肉身及感觉器官不同。[10]佛教的部派出现后,论师们逐渐开始探讨三者的差别。早期的阿毗达磨论藏中仍主张:“心云何?谓心意识。此复云何?谓六识身,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11](P692)晚出的经典,如《俱舍》等论,则更重视三者的不同:“心以增长为义,能解故名意,能别故名识,善恶诸界所增长故名心。或能增长彼故名心,此心为他作依止说名意,若能依止说名识。”[12](P180)大乘经典将三者彻底区分开,如《解深密经》中直接出现了一位“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这位菩萨的特长就是如实认知阿陀那识、阿赖耶识以及前六识。
与此同时,思量识在作为转识的时候,还具备了转生前六识的功能。既有妄执的“我”,接下来就进一步妄认为“我”具有种种功能,如见、闻、嗅、尝、感觉、思维等功能,于是就有六识的出现,即“生六识”。再加上前文所说含藏识生转识,构成一个完整的自性隐藏于内的生的过程。作为主体的“我”,不满足于内在的种种功能,便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向外驰求,即是“出六门”。在六门之外,这个假“我”接触到的、认知到的无非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即是“观六尘”。“我”的出六门还伴随着六识出六门。“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2](P351)宗宝本注意到在理想状态下,六识应该不染著六尘,这是对法海本说法的吸收容摄;另一方面,思量识既要使六识生起,还要负责在凡夫位时对六尘生起认识。六识是从思量识中转生的,所以是“生六识”;而六门和六尘并非由第七识中转生,是可以不依于第七识而独立存在的,因此才有“出”和“观”。这是自性表现于外的生的过程。
总之,从种生起(即转识,转即是现起)的现识,只有七识,本识是七识的种子,是七识波浪内在的统一。它与转识有着不同,像整个的海水与起灭的波浪,却不可对立的平谈八识现行。《摄论》、《庄严》与《成唯识论》的基本不同,就在这里。[15](P40)
宗宝本《坛经》心识结构的逻辑起点也在于“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但在这里说的含藏识与唯识学所说的阿赖耶识更为相近。唯识学认为阿赖耶识具有能藏、所藏、执藏三义。法海本的含藏识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能藏之义,即只有能够含藏万法的功能。而宗宝本的含藏识除此外更兼执藏义,即含藏识被第七识妄执为实我、实法。
测试仪软件界面是用户直接操作测试仪的接口,设计以简洁为原则,具有直观性。整个界面划分为测试项目区、测试结果区、过程显示区、状态监控区和功能选择区五个区域,软件界面如图2所示。
宗宝本的心识结构继承了《成唯识论》的传统,在理论构建上较为细密、完备。《摄论》的“一种七现”模式应该是较为原始的心识结构,原因有二:一是《摄论》等论典出现时间较早,二是“一种七现”的说法与经量部主张的种子说有较多的共通之处。相比之下,“八识现行”模式不但充实了阿赖耶识的内涵,而且借由阿赖耶识的转变区分出亲所缘缘和疏所缘缘,从而使得八识理论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论,还兼具宇宙发生论的功能。虽然《坛经》将慧能塑造成一副没有知识文化的形象,宗宝本甚至明确提到慧能“不识字”,但正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獦獠”,却能一听经文即解经义。这样的故事叙述模式非但没有让人觉得慧能无能,反而强烈烘托出他的“根性大利”。宗宝本采用“八识现行”的心识结构实际上突出了慧能说法准确精密,从而表现慧能的高超智慧。无论是从叙事效果,还是从对于增强《坛经》的可信度并劝人信奉的作用来看,援引成熟的唯识理论是一个高明的选择。从版本角度说,“八识现行”也印证了宗宝本是一个晚出的、经过较为系统性整理的文本。这种整理表现为后人不断地对《坛经》进行修饰和增益,使得所谓“慧能的讲法”更加完善和丰富。
法海本“一种七现”的心识结构虽然较为粗糙,但却与《坛经》的整体思想更为契合。《坛经》强调“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1](P339)虽然自性与含藏识能够关联起来,但自性本来清净则是典型的如来藏思想。自性清净的立场在缘起论上的表现必然是一心二门论,这也是中国佛教大多数宗派选择的理论进路。“八识现行”结构兼具的宇宙发生论功能与一心开二门的缘起论是直接冲突的,而“一种七现”结构则避开了这一点。同时,“一种七现”的认识论特质保证了心识结构的完全内在性,这种内在性恰是禅宗特别重视的,如《坛经》中说:“外修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闻其顿教,不信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即是见性。”[1](P340)可以看出,“一种七现”的心识结构与《坛经》的修行解脱论也是更相适应的。从这一点上讲,法海本中的心识结构虽然不善于分辨心、意、识,但却保证了自性作为根本而存在,进而以自性为基础展开教理讨论和修行实践。这不仅是对唯识学心识结构论的发展,也是法相唯识思想向真常唯心思想转化的一个缩影。
注释:
宗宝本《坛经》的心识结构以自性为根本出发点,自性在内转生出思量识,思量识又进一步转生出前六识,三者共同构成心;另一方面,自性向外生出六尘、六门;在自性为体的基础上,内在的六识向外展开对一切法的认识,形成了自性之用。所以从修行解脱角度讲,可行的办法也是两个:一是停止思量,思量止息则没有妄执的“我”,更没有六识,纯是守持自性;二是若有思量,则起善用正确认识一切法。虽然两个版本《坛经》的心识结构有非常大的差别,但它们在解脱论上却是殊途同归的。
如,在教学中,曾经遇到一位身份调皮的学生,他对课程几乎没有兴趣,而且学习积极性不高,在教学中经常和老师作对。但是,这名学生对机械制图部分的内容有一定的见解,而且课程练习完成的也不错,就是学习状态不太好。因此,在教学中,笔者经常在其他同学都在的情况下激励他、鼓励他、赞赏他。同时,还与他一同畅谈理想,关注他的言行。针对课堂的作业,我经常将一些相关的任务派给他。在潜移默化的引导中,他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学习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也开始主动地学习知识。
[2]宗宝编.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C]//. 大正藏(第48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3][印]世亲(Vasubandhu)造, 玄奘译. 阿毗达磨俱舍论[C]//. 大正藏(第29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4]虽然形成体系的瑜伽行派思想突出强调“识”的主体性,但早期的根、境、识关系是比较混乱的。如护法在注释《唯识二十论》时认为由眼根而生色尘,进而在根、尘的基础上说有识。参见护法造, 义净译. 成唯识宝生论[C]// . 大正藏(第31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第88页.
[5]慧远撰. 大乘义章[C]//. 大正藏(第44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加快实施绩效工资制度。要不断加大“普惠性”稳定支持力度,提高高校和科研院所运行保障水平,提高基本支出定员定额标准,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尽最大努力缓解科技界多年来反映强烈的人员费保障不足问题;稳定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自主选题的研究和科研条件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6]“五门”,敦煌系统《坛经》的三个全本——大英博物馆藏S.5475、敦煌市博物馆藏BD.077、旅顺博物馆藏本——原本皆作“六门”。如果外有六门,则意门应当指第七末那识,但这与后文含藏识及转识等内容的论述相冲突。《大正藏》及杨曾文校订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4, 第37页.)均将“六门”改为“五门”。“身心”,原本皆作“心”。从比喻的合理性考量,“性去身坏”似更合理,但这一问题与本文无涉。本文采用校订本说,直接引用《大正藏》本。
[7][印]护法(Dharmapāla)等造, 玄奘糅译. 成唯识论[C]//. 大正藏(第31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8]慧琳认定“含藏识”的梵语是阿陀那识,而阿赖耶识“或曰阿陀那识”。永明延寿将“含藏识”直接称作“第八含藏识”,“亦名种子识”,认为含藏识等同于阿赖耶识。参见慧琳撰. 一切经音义[C]//. 大正藏(第54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第422、648页;延寿集. 宗镜录[C]//.正藏(第48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第707页.
[9][印]求那跋陀罗(Guabhadra)译. 杂阿含经[C]// . 大正藏(第2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10]经文中所举“心、意、识之我常住”的观点被作为错误思想而受批判。但考察文末对六触和有支缘起的论述,经文意在阐述苦、无常、无我的道理和从六触支灭苦的修行,并没有否定心、意、识与眼、耳、鼻、舌、身的差别。参见段晴等译. 长部[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2.
[11][印]世友(Vasumitra)造, 玄奘译. 阿毗达磨品类足论[C]// . 大正藏(第26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采用SPSS20.0软件处理研究数据,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进行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 s)表示,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2][印]世亲(Vasubandhu)造, 真谛译. 阿毗达磨俱舍释论[C]// . 大正藏(第29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该协议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筛选锚点,第二部分筛选出不被锚点支配的数据点,第三部分在筛选出的数据上计算skyline。
[13][印]无著(Asaga)造, 玄奘译. 摄大乘论本[C]// . 大正藏(第31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14][印]世亲(Vasubandhu)造, 玄奘译. 唯识三十论颂[C]// . 大正藏(第31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15]印顺. 摄大乘论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TheCittaStructureofRostrumScriptures——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Fahai Edition and Zongbao Edition
HUANG Guang-x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RostrumScriptures, six roots of sensation are called six gates, but the citta structure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Fahai edition and Zongbao edition. Fahai edition contends that all dharmas originate from Svabhāva with the action of thinking. Svabhāva generates six consciousness by outstripping the materialities of all dharmas and six gates. In contrast, Zongbao edition thinks that Svabhāva is the origin point of citta structure since it produces the manas, six sense objects and six gates. The manas gives rise to six consciousness. Svabhāva (ālaya-vijnāna), manas and six consciousness represent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itta. Fahai’s citta structure which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relevant doctrines of Zhendi Group is called Yi Zhong Qi Xian. It is more compatible with the main idea of RostrumScriptures. Because of absorbing the expertise of Xuanzang’s thought, Zongbao’s structure is closer to Ba Shi Xian Xing and relatively more precise.
Keywords:citta structure; RostrumScriptures; six roots of sensation; ālaya-vijnāna; manas
[收稿日期]2018-04-03
[作者简介]黄光旭(1990-),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942.1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08-0118-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811
标签:自性论文; 法海论文; 结构论文; 佛教论文; 功能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对佛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论文; 北京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