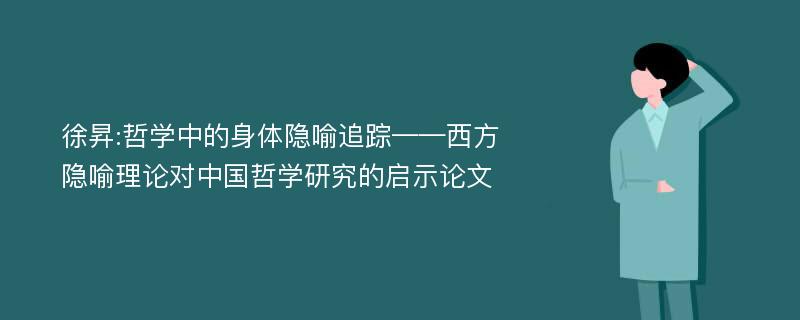
摘要:针对受西方形而上学影响所导致的用抽象概念和思辨方式做中国哲学的倾向,倡导一种追踪概念中身体隐喻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具体包含如何可能、如何操作以及优势何在三个方面。通过考察当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与隐喻关系的反思,可以破除传统认为哲学必须使用抽象概念进行思辨的偏见。通过引介莱考夫等人的“概念隐喻”理论,可以从“概念化”的角度说明概念的意义从根本上都是由身体感官活动塑造的,这也意味着通过身体隐喻来回溯概念意义之生成并进而理解哲学是合法的。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三种回溯哲学中身体经验的方法:当下体验、词源回溯、结构性回溯。这些方法会给中国哲学的研究在自我理解、中西比较与当代发展方面带来一定的优势。
关键词:概念化;概念隐喻;身体隐喻;身体体验;中国哲学
哲学常常给人以抽象、晦涩的印象。其原因在于,哲学从其形式方面看表现为运用概念进行思考的活动,而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所追求使用的概念,诸如“存在”、“形式”、“一”等等,往往是高度抽象、脱离了实际经验的,以这些抽象概念间的相互关系来运思(即思辨),自然就给人以云山雾罩之感。运用高度抽象概念进行思辨,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西方哲学家视为哲学之所当是,还以此看低概念未能充分抽象化的中国哲学。为了“哲学”地建立起“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不断地在传统典籍中找寻抽象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概念,并引入各种西方哲学概念对其进行解释,希望以这种方式使中国哲学思辨化、体系化。这就导致用不可经验的抽象概念做中国哲学的现象一直伴随着中国哲学这门学科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哲学自身不断地被“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经典图式)化。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摆脱这种做中国哲学的方式,取得了不少成果,这其中的基本趋势就是回到“经验”。这种“经验”,当然早已不是传统经验主义所说的“感觉”,而更多地具有现象学的特征(渗透着精神、带有意向特征,被动与主动合而为一的东西)与生存论的意味。陈少明教授更是直言:“说到底,首先就是从研究者自身体验到的经验出发,这样我们才踏上做中国哲学的坦途。”[1]本文所尝试提出的“用身体隐喻做中国哲学”,正是一种具体该如何从抽象概念回溯到身体经验的方法,也是一种用可感话语做中国哲学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如何可能,如何操作以及优势何在?
一、形而上学与隐喻
要回答用身体隐喻做中国哲学如何可能,首先就要破除用抽象语言做哲学的偏见,这是一个深植于西方文化中的偏见。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开始就在哲学(形而上学)与文学之间划定了界限。与总是以抽象概念示人的哲学语言相比,文学中的语言显然要生动活泼、富有情感的多,是可感的语言,而这其中隐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隐喻,通常地说就是用一个领域的事物去表达另一个邻域中的事物,其中,用以表达他者的往往更加切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感性经验,从而更容易让人理解。隐喻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象征着具有暧昧的、异质的和不确定性的感性语言。文学语言正是运用这种语言使得自身变得可感起来。但是,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其目标就是要超越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超越感性语言达到一种严格的概念语言。所谓的“概念语言”,就是运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概念,这种概念的特点是“外延越大,内涵越小”,因而最具普遍性,但同时也具有抽象性。哲学家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语言才能够摆脱感性的束缚,从而与更真实的世界(理念世界)进行交往。因此,哲学与文学的对立也就意味着抽象概念语言与可感语言的对立。柏拉图第一个系统地划清了哲学与文学的界限,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隐喻视作与追求“真理”的伟大哲学事业无关的一种诗人和诡辩者的修辞把戏,认为文学艺术都是诉诸于我们的低等本性,如感知、想象、情感等,缺乏关于“理念”的知识。吊诡的是,柏拉图自己就是一个运用隐喻的大师。伴随着哲学越来越抽象化和体系化,哲学家对隐喻的排斥也在不断地加强。
一是从必要性角度而言,将政府规章纳入行政诉讼附带审查有利于保护公民和合法权益,有利于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恣意。将政府规章纳入行政诉讼附带审查也是确保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有效衔接。将政府规章附带审查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如果没有及时将规章附带审查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那么对于当事人而言可能面临有权提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后却无法提起司法救济的尴尬境地。对于不服行政复议机关复议决定而求诸行政诉讼,法院对于复议附带规章无权审查,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救济权。将政府规章纳入行政诉讼附带审查也是对于行政诉讼法的完善,是对于规章的“参照适用”的修正,也有利于行政诉讼制度内在逻辑的完整。
不过,随着现代西方哲学对自身传统的反思,许多重要的哲学家都开始重新反思这种界限。尼采指出:“那么,什么是真理呢?一大堆动态的隐喻、移情、拟人化,总之是人类关系的总和,被诗意的、注重修辞地拔高、改写、修辞,经历长期使用后,在一个民族那里被认为是稳定的、规范的、有约束力的了;真理就是人们忘记其是幻觉的幻觉,是变得破旧而无感性力量的隐喻,是没有了自己上面的图像、现在被当做金属而不再被看做硬币的硬币。”[2]海德格尔则说:“倘若我们把思想理解为听和看的一种类型,则那种感性的听和看就被接纳和移交到那种非感性的觉知即思想之领域中去了。……学者们的语言把这种移转叫作隐喻。思想因而只可以在隐喻的、比喻的意义上被称作一种听(倾听)和看(发见)。”[3]100又说:“但只有在形而上学中才有隐喻性的东西。”[3]104罗蒂则认为:“决定着我们大部分哲学信念的是图画而非命题,是隐喻而非陈述”[4],并指出整个西方哲学史,尤其是近代认识论传统就是由视觉隐喻支配的历史。对哲学与文学关系的反省,到德里达那里发展成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在《白色神话: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一文中,德里达用解构主义的方法,即揭示出传统认为处于边缘项的隐喻其实已经包含了作为中心项的概念语言,形而上学本身就是一门植根于隐喻中的学问,从而消解了文学与哲学的对立。在德里达看来,西方文化中之所以存在哲学与文学的对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发现哲学的隐喻本性。他继承了尼采的比喻,把制造概念语言的形而上学家比作磨刀人,他们用磨刀石将徽章和钱币上的标记、价格、头像统统抹去,从而声称这些硬币已从一切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具有了无法估量的交换价值。其实,每个抽象概念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感性具体的隐喻,都是由感性肖像的磨损而来的,磨损象征着从可感的具象语言进入形而上学的抽象语言。形而上学家自以为能通过抹去具体标记的方式达到普遍性,却不知如果将硬币上的标记完全抹去,硬币本身也将一文不值。因此,“抽象概念的表达只能是一个类比。神奇的命运在于,那些想要摆脱外表世界的形而上学家不得不永远生活在譬喻之中”[5]213。如此看来,形而上学的历史,其实是不断试图用抽象概念代替具体形象的历史,同时也是哲学忘记自己隐喻本性、忘记作为本义的可感的自然语言的历史。德里达还指出,所有的形而上学话语中都含有“感官类型的隐喻性内容”,人们在谈论形而上学时,“实际上是在谈论视觉、听觉和触觉的隐喻(在那里,知识问题作为它的要素),甚至于嗅觉和味觉的隐喻,尽管十分少见,但也不是无关紧要的。”[5]227
通过采用折线滑动法分别计算滑坡各剖面的稳定系数及剩余下滑力,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滑坡在自重工况下,处于稳定-基本稳定状态,与宏观分析结果一致;在暴雨工况下,滑坡处于基本稳定-不稳定状态。
“概念隐喻”理论告诉我们,作为所喻的抽象概念是通过作为喻体的结构性得以理解的,这种结构性又是基于在身体感知经验中获得的意象图式,而这种图式先于抽象概念而具有原初的意义与逻辑。这启发我们,不论面对多抽象的哲学概念乃至体系,都可以用回溯其源头域之身体经验的方式,通过身体感知(具体表现为感官感知)意象图式的结构性去理解它。
概念化是我们思维、语言中最基础的环节,它是指“通过突出某些特征,淡化其他特征或是隐藏其他特征来标识一种物体或经验类型的自然方法。”[7]148至于概念化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当且仅当一些事物具有某些相同特征时,这些事物才能归于同一范畴。而这些相同特征,在界定范畴时又是必不可少且非常充分的条件。”[8]前言·50这就是说,概念化活动必须遵照客观实在的特征,从由多种特性组织起来的对象中抽出与其他对象所共有的特征,这种概念化过程也称之为“抽象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概念是一个对象特征的“集合”。然而,抽象化理论所说的这种从成员的共同特征中获得意义的方式,实际存在着一种循环说明,即如果不是在抽象前就已经知道了那个要抽象的共同点,我们又靠什么抽象出那个共同点?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已经有了某种先见,我们才能找出那个共同点,“一般”总是走在了“个别”的前面。所以,传统获得概念的抽象方法并没有处理好“一般”与“个别”这对足以贯穿西方哲学史的范畴的关系。也正由于此,西方哲学中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先验主义,认为“一般”是先于“个别”而存在的。但是,先验主义依然是将“一般”与“个别”分离开来,把“一般”看作实在的,且带有神秘的色彩。莱考夫概念化理论实质上还是在处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按照他的理论,在任何个别的感知体验中我们直接就能获得一种“一般”,这种“一般”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结构性的东西,因而任何“一般”都是源自于身体感知上的这种获得。
二、概念隐喻与身体经验
该如何打通感性语言与概念语言呢?莱考夫和约翰逊(以下用“莱考夫”一人名字代替)的“概念隐喻”理论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说明了抽象概念是如何通过隐喻映射而建立在可感的身体经验基础上的。
总之,由于文学与哲学,感性语言与概念语言对立,导致二千多年来作为西方哲学主流的形而上学家,总是希望使用抽象概念把一切感性的、具体的东西都消减掉,从而获得一个高度普遍的不变体,他们认为这样会更便于人们认识世界,其实他们所追求的不变体只是一个僵化的虚构物而已。感性语言与概念语言的对立反而使哲学失去了一切可感知的生活经验的支持,最终成了空中楼阁。
范·弗拉森将其自己的观点称为“新图景”,他对科学理论的建构首先是刻画一组模型,即结构的族;其次是对模型的特定部分加以细致刻画,以其作为对可观察对象的表征候选;再次,在实验测量报告中对表象加以结构观察,如果一个理论的部分模型实现了其实验测量报告中的表象与加以细致刻画的模型的特定部分同构,那么这个理论便是适当的。[7]64-65范·弗拉森将模型类看作理论的载体,当该模型的部分子集同经验世界同构时,就将抽象的模型世界或结构与经验内容统一了起来,从而形成了其科学理论观。
末次给药后4h,麻醉大鼠经股静脉取血分离血清,-20℃冰箱中保存待测。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中IL-17和IL-23水平,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中操作步骤进行操作。
什么是“概念隐喻”呢?莱考夫解释说:“我们是否系统地使用从一个概念域来思考另一个概念域的推理模式?‘是的’。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概念隐喻。将这些跨域的系统对应称之为隐喻映射。”[7]212概念隐喻是指从一个概念(而非仅仅是语词)出发去思考(而非仅仅是修饰)另一个概念。每个隐喻的基本构成是:“源头域”、“目标域”和从源头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对于源头域,莱考夫认为:“对隐喻而言,为了起到源头域的作用,这个域必须独立于该隐喻且能够被理解”[8]285,也就是基于身体经验而来的“基本图式概念”和“动觉意象图式概念”才能成为源头域。对源头域的这种规定意味着隐喻映射具有不对称性,即要从“界定不那么清晰的(通常不怎么具体的)概念可以依据较明确的(通常更具体的)概念去理解——这些清晰界定的概念是直接基于我们的经验”[7]103。也就是从具体域映射到抽象域,而具体域之所以是具体的,是因为它有某种结构,这种结构既可用于理解也可用于推理,二者都是基于我们身体经验得来的。如此一来,抽象概念也就不再抽象,也具有了可体验性,而理智作为一种推理的能力也具有了身体基础,具有隐喻性、身体性。又是什么决定了源头域与目标域的匹配以及映射中的具体细节呢?这些从根本上说还是受我们在世界中的身体经验所塑造和制约的,隐喻的配对“来自我们日常经验中的结构关联,日常经验激发了特定隐喻隐射的每一细节”[8]285。成功配对的隐喻中源头域(喻体)和目标域(所喻)只存在一种相似关系,这种相似性是一种结构上的相似性,而这种结构是来自于源头域概念中基于人身体经验而来的意象图式。因此,隐喻中的相似性不是客观主义认为的外在的、客观的,而是隐喻创造的相似性。这种创造性是一种想象力的体现,但这种想象力又不是完全无章可循,它离不开我们身体经验。因此,在我们获得抽象概念的方式中,是蕴含着身体经验、想象、实践等多种因素的,非干枯的理智所能完成。而“隐喻不是基于相似性而是创造相似性”的观点,已经突破了传统对隐喻的理解,隐喻不是用A来解释B,而是有了A,对B 的理解才得以可能。
莱考夫和约翰逊不仅看到了西方形而上学与隐喻的根本关联性,而且深入到隐喻思想机制的内部,从正面告诉我们形而上学是如何通过隐喻构建起自身的。他们分析道:“纵观历史,没有这样的隐喻,哲学家几乎不可能研究自然本元学。对于大多数哲学家而言,提出本元的主张,正是从认知无意识中选取了一组具有一致性的关于本体论的现存隐喻。也就是说,通过使用无意识的日常隐喻,哲学家力图对由这些隐喻界定的概念实体做出互不矛盾的选择;然后再将这些实体变成真实的并且系统阐述这些选择,来试图解释我们运用自然本元经验中的蕴涵。”[6]13也就是说,哲学家使用较少的一个或几个核心隐喻,又叫作“根隐喻”,形成其核心学说,这些隐喻贯穿了哲学家工作的各个方面,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哲学理论体系。如此看来,形而上学无非是把一些感性、个别的东西当做一般的东西去解释另一些个别而已,并不具有什么先验性、绝对普遍性。哲学其实是被文本中的隐喻结构所左右的,“拒绝隐喻就等于扼杀哲学。没有大量的概念隐喻,哲学就不能腾空翱翔”[6]128,如果将隐喻从哲学上清除出去,哲学也将空空如也。
三、具体方法与意义
要想搞创作,就要敢于冲破旧框框的束缚,最大限度地进行新的探索,犹如猛虎下山蛟龙入海;犹如国庆节一下子放出了十万只鸽子;犹如孙悟空在铁扇公主肚里拳打脚踢翻筋斗云,折腾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一佛出世二涅槃口吐莲花头罩金光手挥五弦目送惊鸿穿云裂石倒海翻江蝎子窝里捅一棍,然后平心静气休息片刻,思绪开始如天马行空,汪洋肆意,天上人间,古今中外,坟中枯骨,松下幽灵,公子王孙,才子佳人,穷山恶水,刁民泼妇,枯藤昏鸦,古道瘦马,高山流水,大浪淘沙,鸡鸣狗叫,鹅行鸭步——把各种意想叠加起来,翻来覆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一唱雄鸡天下白,虎兔相逢大梦归。[4]
莱考夫认为,概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能直接被理解的概念,或者说是直接有意义的概念,另一类是需要用隐喻通过直接有意义的概念才得到理解的概念,即间接被理解的概念。直接有意义的概念又分为两类:一是“基本层次概念”,二是“动觉意象图式概念”。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互动体验形成了“意象图式”,最基本的“意象图式”就是“基本层次图式”和“动觉意象图式”,由这些图式而形成的概念,都因其对应于图式的结构和逻辑直接来自身体经验而可被直接理解,或者说这些概念直接具有意义。这种意义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这种结构蕴涵在“意象图式”中,且直接产生于人的感官机能以及基于这种机能的活动,它的直接可理解性就源于它是“亲身的”(Embodied,也有学者译作“体塑的”,取“身体塑型”之意)。所谓间接被理解的概念,就是需要以某种方式通过直接有意义的概念才能得以理解的概念,而“概念隐喻”就是创造间接理解的方式,它是我们一种至为重要的概念化方式,几乎所有间接理解的概念都是通过隐喻形成的。
事实上,以感官经验特征来解读哲学已经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在西方,以“视觉主义”标识古希腊与现代文明已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而要求用“听觉文化”超越“视觉文化”的呼声也是不绝于耳。在中国哲学界,杜维明先生很早就指出先秦哲学中“听德”的重要性,而近年来贡华南教授则直接以“味觉思想”作为中国哲学的特质,用超越视觉融摄听觉走向味觉来刻画中国思想发展中的基本脉络,并以此来解读包含形上与形下各个方面的中国传统思想。通过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回答用身体隐喻做中国哲学该如何操作,优势何在。
在操作层面上,回溯哲学文本中的身体经验可以采取以下几种的方式:第一,发掘文本中的“基本层次概念”,直接用当下的身体经验理解其意义并进而理解与之相关的概念。例如,在先秦哲学中被广泛使用的“刚”、“柔”概念,就是基于触觉经验获得意义的概念。在《易传》中,作为触觉性质的“刚”与“柔”与身体的“伸”与“屈”紧密相联,取得了“施与”与“顺承”的意象,并逐步将这种意象的结构与逻辑映射到“阳”与“阴”、“乾”与“坤”、乃至“仁”与“义”这些更为抽象的核心概念中,最终确立起《易传》“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的宇宙生成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感应机制以及“乾尊坤卑”的价值取向。又如,儒家常用“温”来形容儒者的气质,而“温”正是一种触觉、味觉性质的概念。作为一种触觉、味觉性感受,“温”具有“投入”、“融化”的意象,这种可触可感的“温”映射到超感的“仁”概念中,形成了作为儒者精神气质之标志的“温德”,即“投入热情与爱意,以融化对象。融化以融合,热量热情让对象成为与自身一体者,对象凭借我的热量热情而再现再生,我藉新融入的对象而成就自身”[9]。而与“温”相呼应,佛家常用“凉”、道家常用“淡”(不温不凉、不损不益)来标榜自己。通过这种回溯我们对三家的精神气质就有了真切的感受。
第二,通过词源学的方法,回溯到概念构成时的原初身体经验中。有些概念虽然已不能直接被体验,但是借用德里达的说法,其“感性肖像”的磨损并不严重,因此我们能从文字学层面获得其原初身体经验的蛛丝马迹。例如,西方哲学中的一系列核心概念:theory(理论、原理)、idea(理念、相)、speculation(沉思、思辨)、illumination(阐释、启发、光照论)、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intuition(直观)、phenomenon(现象)、lichtung(澄明)等等,在词源上都是“视觉”以及与之相关的“光”密切相关[10]。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西方哲学深植于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中,正是视觉这种“距离性”感官(具有直接性、不介入对象的特点,因此是最具“客观性”的感官),以其对对象形状方面的把握(逐步演变为对形式、理型的把握),以及对普遍性、确定性的追求塑造了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的基本品质。而在中国哲学中具有重要方法论地位的“感”则在词源上源自“咸”,而“咸”正是对盐之性味的刻画。正是以味觉之“人与物无距离的交互作用”为意象,中国哲学才形成了与西方基于视觉隐喻而来的“沉思”传统不同的“感思”传统。
第三,从哲学体系或思维方式的结构性中回溯其原初的发生情境,最终回溯到产生这种结构性的身体经验上。有些哲学上的概念,其“感性肖像”已经几乎完全被抹去,但感官经验带来的结构性则往往早已嵌入思维的基本范式中,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挖掘其思维中深层次的“意象图式”的方式重新还原该概念发生时的身体经验(也可说是一种发生情境再现)。罗蒂对西方哲学中基础主义、表象主义,乃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所采用的正是这种方式。在罗蒂看来,西方近代以来的“笛卡尔—洛克—康德”认识论传统,预设知识有其外在的基础(基础主义),这些外在基础又能被人的心灵所把握(表象主义),并最终预设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这些预设都是在“镜喻”的图式中才能完成的。如果不是把心灵看作“自然之镜”,把认识看作是一种表象活动,那么认识论传统中所讨论的真理如何与实在相符合的问题、语词与指称的关系问题就完全没有了意义。因此,罗蒂的批判正是对作为思维范式的“镜喻”图式的批判,说到底是对西方哲学视觉隐喻的反思,他提出的“后哲学文化”正是一种无镜式图式的哲学。同样,福柯对西方现代社会“监视的文明”的批判,也正是对视觉的扇面结构的反思。贡华南教授则以味觉活动的基本情境,即物我距离的消弭以及由此而来的形式的打破、内外的融合,作为中国文化的特质,而与西方视觉思维之距离性特征相对照。
以这种方式理解中国哲学,相较于长期以来将中国哲学中的概念抽象化、体系化的做法相比,具有极大的优势。其一,有利于降低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曲解,呈现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若不把看似抽象的核心概念回溯到其可感的身体经验,如上文提到的将儒家的“仁”概念回溯到触觉性的经验“温”、“不麻木”,则会出现概念意义上的真空地带,导致习惯性地用现行的西方概念对其进行解释,如将“仁”理解为“实践理性”、“情感”等,从而曲解传统思想。其二,这种方法也将使得那些完全不能被思辨哲学所解释却又在传统哲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概念,如“温”、“淡”、“刚柔”等,从边缘地带进入哲学思考的中心,展示出传统哲学的自身特质。甚至就如有学者所预言的,“如果我们从哲学话语建构的维度对不同时期哲学中的‘根隐喻’、‘概念隐喻’和‘结构图绘’进行分析,可以写出全新的哲学史”[11]。这句话对中西哲学史的考察都是适用的。其三,有利于实现中西哲学的真正平等对话。将中西哲学中概念回溯到身体经验,也就使得中西哲学彻底被放置在同一个平台上,即“实际身体经验”,从而真正实现中西对话与互通有无。这样既能避免“以西释中”的屈己就人,破除“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伪问题,也能防止“中体西用”式的自我傲慢。其四,有利于中国哲学参与到时代精神的构建中,将中国哲学的发展融入“世界哲学”之中。正如张再林教授指出的:“当代人类哲学也正处于这样一个‘范式’的转型期,即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型,具体来说就是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从思辨世界转向生活世界,从意识哲学转向身体哲学的转型。”[12]中国传统哲学在这些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源,理当充分挖掘,主动地参与到新范式的构建中,而用可感的方式做中国哲学正是挖掘这些资源的有效方法。
从更一般的角度看,哲学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新的方法论的出现。100年前分析哲学兴起,倡导用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方法做哲学,梦想着用拿笔算一算的方式解决哲学问题,开启了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如今,我们认为应该对哲学概念进行隐喻分析,将抽象概念还原为直接可感的身体经验,用身体隐喻做哲学,由此哲学可能会为我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参考文献:
[1] 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47.
[2] 尼采.尼采全集.第1卷[M].扬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623.
[3] 海德格尔.根据律[M].张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4]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
[5] Derrida.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M]//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 Alan Bas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6]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肉身哲学:身体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M].李葆嘉,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7.
[7]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8] 乔治·莱考夫.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范畴显示的心智[M].李葆嘉,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
[9] 贡华南.从“温”看儒者的精神基调与气质[J].学术月刊,2014(10):46.
[10] 高秉江.现象学视域下的视觉中心主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
[11] 牛宏宝.哲学与隐喻——对哲学话语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31.
[12] 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8:296.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9)01-0095-05
收稿日期:2018-10-20
作者简介:徐昇,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暨中西哲学比较。Email:337340548@qq.com
(责任编辑何海涛)
标签:哲学论文; 概念论文; 中国论文; 身体论文; 经验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