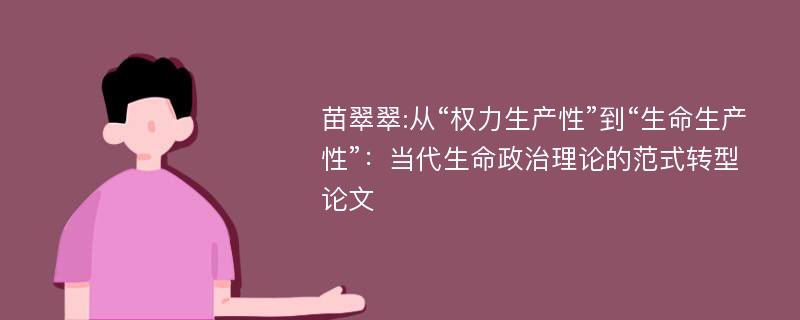
[摘 要]生命政治作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其术语的框架与内涵存在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型。福柯从谱系的视角分析权力治理形式的变化和阿甘本悬设先验原初结构对赤裸生命的分析,皆囿于权力场域对生命进行治理或宰制。奈格里、哈特认为,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逻辑具有深刻的片面性,因为他们所强调的权力的生产性不仅蕴含着生命政治的悖论(死亡政治),而且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命生产性维度的缺失。究其根源在于忽视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现实基础的分析。正是在这一点上奈格里、哈特回到马克思同时又试图超越马克思,他们从后福特制时代生产模式和劳动的技术性构成发生新变化这一现实基础出发,作出在当代社会非物质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的判断。非物质生产的核心是生命或主体的生产性,由此更新了当代生命政治的理论内涵,阐发了当代社会关系中生命主体蕴含的潜力。这种激活革命主体和重塑阶级逻辑的理论进路,进一步凸显出切中生命本身的生命政治理论所蕴含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生命权力;生命政治;“非物质生产”《;大同世界》
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将生命政治定义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a new technology of power)。奈格里、哈特在《大同世界》中所探寻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基于两个核心要素:作为历史背景的“非物质生产”和追求共同性的革命主体即“诸众”。这两个核心要素共同指向生命本身的力量。由此窥探出生命政治理论研究的历史谱系呈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径。一种是以福柯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着眼于从权力和治理的视角分析控制策略问题;另一种是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聚焦于生命和反抗的立场研究革命主体问题。虽然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活跃于欧洲政治舞台上,为难民、犯人、同性恋等群体呐喊,但福柯的权力理论将权力视作关系网络,犹如毛细血管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在始终充斥着权力展布的现代社会中反抗与革命的呐喊显得脆弱、无力。如果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体现为后现代的无能为力,那么奈格里则选取了生命政治中“生命生产性”的一支进行纵深研究,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中彰显了“生命”的价值,为重构新时代的革命主体提供新的可能空间。
一、权力视域中的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的术语并非福柯首创,但把生命政治作为一种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却肇始于福柯。福柯的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它是以生命权力为主导统治模式的政治,关注对生命的控制。“生命”包含个人的身体(肉体)和社会的身体(人口)两个维度,与此相适应,对生命的控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权力形式即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系列:“肉体系列—人体—惩戒—机关;和人口系列—生物学过程—调节机制—国家”①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规训权力是一种把“个人身体”的肉体进行精确地分解、监管、诊断、矫正,以使肉体达到既驯顺又有用的效果的微观治理方式,也称为“身体的解剖政治学”。“生命权力”是一种针对“社会身体”的人口,以概率统计的安全配置方式,综合分析难以准确把握的一系列现象,达到提高国民全体的健康、人口整体的安全、社会人口的质量的目标的一种新的权力治理方式,也称为“人口的生命政治学”。生命权力是“调节的权力”,根本上不同于君主权力。君主权力是一种“使人死”的致死权力,突出权力的压抑性、否定性的力量;生命权力是一种“使人活”的调节权力,凸显权力的生产性、肯定性力量。生命政治是从“活着的人”或“人口”开始的,在总体性的“人口”的层面、在干预“怎样活”的层面提高生命的价值。
福柯是在治理术的框架中研究生命权力的。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揭示了“治理术”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总体,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这种权力形式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①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0页。“人口”是动态变化的,干预人口、提高生命必需了解和掌握与“人口”相关的一系列因素。因此生命权力首先要以概率统计(如出生率、死亡率、疾病率、感染率、升学率、就业率等)的方式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策略干预人口的变迁、保障人口的安全和健康。在治理术的框架中考察生命政治,不仅仅要考察权力的治理方式及其变化,而且要考察治理的合理性及其相关原则。治理的合理性和原则集中体现在《生命政治的诞生》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中。“一旦我们知道了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掌握什么是生命政治学了。”②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不同于国家理由的治理艺术。国家理由的治理以国家富足强盛、长治久安、国民安全幸福的名义对国内事务进行过度管治。这种过度管治方式的合理性问题受到质疑,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凸显出自由原则的重要性。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是以自由为原则,将市场经济的自由原则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生命政治不仅仅是国家权力基于自由原则对人口的干预和调节,而且是生命体基于自由原则的自我投资和规范性力量的生产。至此,生命政治具有了完整的内涵。
在此意义上,生命政治诞生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新自由主义与18世纪的自由主义都主张尽可能少的干预,但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划分出独立的经济领域,让自由原则、经济人模式贯穿于经济领域之中;新自由主义的焦点是“弄明白如何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③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116页。二战后德国秩序自由主义把“企业”形式从经济调控层面普遍化到社会治理中,构建“竞争型社会”、“企业社会”。美国新自由主义依据自身的自由主义传统,将市场原则和经济人(在原文本中福柯使用的法语词是“homo œconomicus”)模型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以经济原则导向政治决策。因此,自由原则必然贯穿于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之中。生命政治中的生命体不仅是交换活动中的经济人,而且是自由竞争的企业家。“作为自己的企业家,其自身是自己的资本,是自己的生产者,是自己收入的来源”④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200页。,由此我们可知,福柯语境中的“经济人”就是“企业家”,企业家进行一种自我投资也称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通过先天基因的遗传、后天的教育培训、医学的检查改善、成长环境的优化等方式自由地优化生命,形塑生命。生命体的自我投资和规范性力量的生产实际上是权力的生产性的一种形式。
生命政治的范式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后果:他们转变了生命政治研究的问题域,从权力机制转向革命主体。奈格里、哈特提出的革命的主体并非单一的阶级,也不是完全混乱的杂多或噪音,而是追求共同性的“奇异性的存在”。诸众在非物质生产过程中不断创造和扩大共同性,同时也完成着新主体的生产。诸众需要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政治诉求,这种形式既非私有制的也不是公有制的,而是根植于共同性的共有形式。从《帝国》中“帝国的控制是纯粹否定的和消极的”③Michael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2000,P.361.到《大同世界》中对共同性进行制度化的政治筹划——使“共产主义必须与共同性建立直接的关系”④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74页。。至此,奈格里、哈特的生命政治转化为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倾向,非物质生产条件下的生命政治积极构建共产主义的新道路。
综上所述,福柯的“生命政治”实质上是一种权力治理术或权力治理方式。不论是通过概率统计的方式保障人口总体的安全与健康,还是以“经济人”或“企业家”模型优化生命、形塑生命,皆构成权力对生命进行构建的有效方式,从而凸显出权力的生产性之维。
沿着福柯权力视域中的生命政治的脉络,学者们从诸多不同的角度对“生命政治”进行深入阐释。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Agamben)以“至高权力”的生命政治逻辑对生命政治的概念进行了最重要的修订。福柯从历史谱系学的角度探究“生命政治”,将生命政治置于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中。阿甘本则从“法律秩序—法律例外”的结构性角度看待“生命政治”,认为生命政治并非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现代性的产物,而是一直镶嵌在整个西方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当代的状况只是生命政治漫长历程中一个极端的新阶段⑤吴冠军:《生命政治:在福柯和阿甘本之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第95页。。“法律秩序—法律例外”的“结构性分析”标识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之间的关系。“赤裸生命”指的是“几乎没有我们通常归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的权利和期望”⑥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页。,但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依旧活着,处于生命与死亡之间的界限中的人。简言之,赤裸生命是没有政治生命的人,没有政治和法律保护的人,如难民、无国家之人、被除去国籍的人、被剥夺国民资格的人。赤裸生命栖居于法之悬置状态,至高权力可以将其致死,而不犯杀人罪、不被惩罚、亦无需为此负责。因此,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是至高权力对赤裸生命的征用,这种生命政治正是通过死亡政治的操作得以体现的,生命政治直接蕴含着死亡政治。
埃斯波西托(Esposito)沿袭福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路,在《Bios,生命政治与哲学》中提出生命政治受到“免疫范式”(paradigm of immunization)的支配。免疫通过限制生命的扩张性、生产性力量而保存和发展生命。“死亡政治”既有对生命的破坏作用,也有对生命的保护作用,德国纳粹以保护德意志公民的身体和基因的健康与优化的名义,对残疾人、精神病人的身体和精神进行灭除式摧残。这种极端方式直接表现为对保护生命太过敏感,甚至走向死亡政治。埃斯波西托从生物-医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免疫”表现为通过医学研究反抗疾病、保护生命,强调治疗或限制这种对保护生命的敏感性和极端性,把死亡政治颠倒为以“生命为中心”的政治。埃斯波西托的医学免疫角度的“生命政治”无疑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是一种居于福柯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生命政治”和阿甘本结构性中的“死亡政治”二者之间的具有限制性的积极性。
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标准、国家政策是对卫生经济研究与实践者的最大褒奖。近年来,成研中心所完成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逐步上升为国家标准,是中心创建以来一大创新转变。中心以系列课题研究成果为基础,接受当地医院实践检验,证实其符合当前医改政策取向,进而被国家主管部门采纳。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也被称为“死亡政治”,可以看出他对“生命政治”的研究从福柯“生命政治”中权力的生产性转向至高权力的极端否定性维度。赤裸生命作为政治主体揭示了至高权力的面貌,然而赤裸生命这一政治主体完全排除了自主与创造性行动的一切可能。
集中营是现代生命政治的典范,集中营代表了现代生命政治的一种典型结构,即“至高权力—赤裸生命”“法律秩序—例外状态”的结构。具体而言,至高权力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悬置法律,使法之例外状态成为一种常态,在这样的空间和场所中“权力面对的只有纯粹的生命”①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第229页。,因此,致死或灭除赤裸生命就成为生命政治的常态。例如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极端操作。在“保护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障德国公民整体的安全和健康的名义下,德国纳粹对起初作为公民的犹太人进行“祛政治身份”的政治化操作。希特勒正是通过悬置原有法律、颁布新的法令、政策使犹太人成为次等公民,经由纽伦堡法案进而将次等公民身份降为普通居民,最后剥夺了犹太人的基本人权从普通居民身份成为赤裸生命。阿甘本以集中营为典范意在揭示现代社会中的“集中营结构”,指出现代民主制的根本困境。现代主权权力不断制造例外状态将生命降格为赤裸生命,根本无法解决由此带来的赤裸生命问题,正如在机场的等待区、城市的某些郊区等都可能成为施加于赤裸生命之决断的场所。
权力视域中的生命政治从权力的面向看,生命政治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既具有压抑性也具有生产性,尽管政治权力以“积极的生产性”(福柯的分析)、“极端的否定性”(阿甘本式的分析)、“温和的限制性”(埃斯波西托的分析)等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但都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权力的施展。压抑性或生产性的主体都指向“权力”,隐没了生命作为主体的维度,造成生命生产性的缺失。其二,从生命的面向看,不论是对生命的形塑,还是对赤裸生命的征用,亦或对生命的治疗,都凸显出政治权力对生命价值进行衡量,尽管衡量的标准不同,或以“是否高效”或以“是否具有政治身份”亦或以“是否健康”衡量生命价值。然而生命真的可以被量化或衡量吗?从上述两个维度,奈格里沿袭并更新了福柯的“生命权力的生产性之维”,并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现实基础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探讨了生命政治语境下“生命的生产性之维”。
二、生产关系视域中的生命政治生产
奈格里、哈特更新了生命政治的主题:从权力的生产性转向主体的生产性,从权力端转向生命端。这是基于生命主体的视角,奈格里提出“excedence”(逾越)“/measure”(计量)的对子⑥ 参见Antonio Negri“,Marx and Foucault:Essays Volume 1”,translated by Ed Emery.Cambridge:Polity Press.2016.Cf.Part II 6.11”Biopower and Biopolitics:Subjectivities in Struggle Interview with Luca Salza”.同样的对子出现在《大同世界》中的英文分别是逾越(exceed)/计量(measurement)。详见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101页。,旨在表明生命不是以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或转化为利润加以衡量的,对生命、劳动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实质上限制了自由的发展和主体性生产。超越价值规律对生命和劳动的衡量,才能体现生命的自由与反抗、主体性生产的创生与自治。奈格里、哈特把当代社会关系中的生命主体称为“诸众”(multitude)。“诸众”是“无视社会秩序或财产、内嵌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的杂多性(multiplicity)”⑦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25页。,不限于社会底层、不限于无产阶级,具有异质性、多元性、包容性的特点。诸众表征着一种反抗力量,反抗统一性或同质性(identity)对异质性(singulari⁃ty)的排斥,反抗权力对共同性的剥夺。
对于高校的知识产权管理而言,主要的目标是对科研技术成果及其他智力成果的开发、利用、转让和发展进行系统化的管理。但是在目前的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中,还存在以下方面的诸多问题。
“非物质生产”有三层内涵。其一,“非物质生产”包含非物质性产品(如图像、信息、知识、情感、符码等)或物质性产品的非物质维度(如产品中的象征意义、美学价值等)的生产,这种联结心脑共同运作的生产也称为“心脑劳动”(labor of head and heart)。其二,“非物质生产”蕴含着“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②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这种关涉生命的生产也称为“生命政治生产”。其三,“非物质生产”的产品形式——不论是商品的非物质维度还是社会关系或生命关系——具有无法量化的特点,即既不能量化生产,也不能进行量的衡量或统计,它是一种“质”的形式,这种产品很难被圈定为私有或公有,而采取共有的形式,因此“非物质生产”也被称为“共同性”的生产。正是“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层面上的“非物质生产”构成了“生命政治生产”。奈格里对生命政治生产的分析根源于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资本论》三卷以“商品”开头,“阶级”结尾,整个《资本论》所要揭示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与物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7-878页。,也“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意味着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也蕴含了生命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由此表明不能以生产的“主体—客体”的二元结构的方式把握“生命政治生产”或“非物质生产”,而应该理解为主体和客体都是人,人生产人,人既生产同时也被生产。
综上所述,全方位的智慧城市管理,能够增加经济发展红利,对于产业转型和智能服务方面有着重要意义。PPP模式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主推模式之一,能够显著降低政府的建设投资成本,发挥市场导向的活力。然而为了保障PPP项目主体的盈利能力,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多方面防范税收风险,合理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最佳价值。
段主任怕我过于激动会出现什么意外,连忙制止两人不要乱说话。虽然蒙住了眼睛,我也能想象的出来,两个女人在屏幕上看到我气管中那颗假牙时,会是一种怎样的神情。要不是在医院,两个女人或许会抱着跳起来。唉!见过再多世面的女人终究还是女人,沉不住气的本性看来是难改的。没办法。
福柯“生命权力的双重性”为奈格里、哈特更新“生命政治”术语的内涵提供了关键启发。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规训的手段”章,福柯指出“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②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18页。。可知,压抑性和生产性构成了生命权力的双重性。“生产性”是福柯和奈格里共同关注的维度,但是福柯的注意力集中在权力上,所以“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的概念具有相同的含义。而奈格里把注意力集中在生命上,所以进一步区分了“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的术语之间的差异。生命权力是操控生命的权力。生命政治是生命本身的力量,突出生命的潜能,寻求主体的生产。以生命力量为核心的生命政治何以是政治性的?主体的生产又是怎样的一种生产?这两方面内涵成为奈格里“生命政治”术语需要阐明的重要理论任务。
在非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中,生命政治呈现出新的矛盾和困境、新的解决方式和路径。其一,从权力角度看,权力对生命的宰制集中表现为对非物质生产的产品的剥夺、对共同性的剥夺。其二,从生命的角度看,生命主体拥有的自由与对权力的反抗集中表现为对共同性被剥夺的反抗,并致力于创建新的共有的政治空间。奈格里、哈特认为:“我们所浸淫于其中的社会已经完全从属于资本的权力,我们将这种权力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生命权力。这种生命权力就是资本活动的产品,并且它拥有着全球的霸权”①Antonio Negri“,Communism:Some thoughts on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Douzinas C.Zizek S eds.,”The Idea of Communism”,London:Ver⁃so,2010,p.163.。他们用“非物质生产”的概念拓展了马克思“劳动的技术构成”“资本的有机构成”概念的内涵,进而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资本权力剥削共同性的新形式。对共同性的剥削既包含资本对非物质产品以及产品的非物质形式的占有,也指向对静态自然资源和动态的社会交往形式或协作形式的支配。就劳动的技术构成的三种新的趋势来看,对共同性的剥削首先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认知、情感和生命政治的发展的占有与管控,如教育私有化、知识产权化、网络权限化等。其次,对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管控与占用,加剧了劳动者工作的不稳定性,造成时间的贫乏,限制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力。第三,强化对空间的管控,以隔离化、等级化等方式为移民、种族混合的模式设立边界,限制交流与协作,造成空间的贫困。简言之,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已经扩展为资本对生命政治的剥夺。据此逻辑,逾越资本的界限不再是集中于生产领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聚焦于社会关系的多层面平行展开的诸众的革命。诸众的革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暴力革命,而是既包含对共同性剥夺的反抗,也包含主体性的生产,还指向建立基于共同性——既非私有制亦非公有制——的新的政治空间即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
生产关系视域中的生命政治从“权力生产性”延伸到“生命生产性”,构成《大同世界》中独特的“生命政治生产”。奈格里、哈特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生命政治生产进行界说,他们观察到在欧洲后福特主义新的生产模式中“非物质生产”居于主导性地位的新形势,作出“生命政治生产是基于共同性的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的新判断,探索出反抗“剥夺共同性的资本”的革命新路径,找到诸众这一自主性筹划与解放的新主体、新力量,重塑主体性生产的阶级逻辑,开启了以共同性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新方向。奈格里、哈特“生命政治生产”不仅更新了“生命政治”术语的理论内涵,实现了生命政治研究范式的转型,而且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革命主体理论的当代研究。
奈格里、哈特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当下经济生活状态进行分析,提出“非物质劳动”的概念,为“生命政治”理论内涵奠定了现实基础。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从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物质生产”所包含的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产过程、物质生产条件、物质生产资料等因素构成马克思分析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范畴。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增殖为轴心,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物质生产过程之中,物质性商品的生产居于主导地位。奈格里、哈特回到马克思的方法,对生命政治的分析从历史角度出发,考察了当下的生产方式。20世纪70年代后福特主义成为西方最典型的生产模式,意大利所采取的正是这种生产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注重劳动过程的变革。意大利的生产模式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转变为小企业的分工合作。企业组织之间相互分工协作、工人高度技能化、社会管理扁平化等新形式使社会分工更具灵活性。奈格里、哈特结合后福特制时代社会生产模式发生的巨大变化,集中分析了当下劳动的技术构成的三个趋势:在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中,非物质生产居于主导地位;工作的女性化,情感投入的比重增多;移民、种族混合的新模式,交流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三大趋势表明社会生产将经济的重心从“物质生产”转移到了“非物质生产”。“非物质生产”居于主导地位并非完全取代了“物质生产”,而是在当代“物质生产”越来越依赖和从属于“非物质生产”。由此,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新的诊断,即非物质生产越来越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基础。
三、生命政治生产的真实意义
“范式”是共同体所遵循的逻辑与规则,因此“范式转型”绝不是单纯的概念置换,而是与贯穿于特定的理论体系中的逻辑、相关问题域、理论态度、理论旨趣等相联系的。因此奈格里、哈特在《大同世界》中从(生命权力)“权力生产性”转向(生命政治)“主体的生产性”的范式转型,实际上隐含着新的理论支点、新的研究视域、新的理论旨趣。
福柯、阿甘本、埃斯波西托的生命政治研究,贯穿着权力的逻辑,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权力构型即政治权力对整个人口的规训与管控。奈格里、哈特关注生命的一支,贯穿着生产的逻辑,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中自主的革命主体的生成逻辑以及诸众对抗“剥夺共同性的资本”,构建共有的共产主义的政治空间。在奈格里、哈特看来,权力的视域没有生产的基础,缺少了客观的基础,因此生命对权力的反抗是消极的、无力的。“我们的分析必须聚集在生命权力的生产维度上”②Michael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Cambridge: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7.,回到马克思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分析视域,凸显出当代社会形态中“非物质生产”的主导地位,提出生命政治生产就是主体性的生产、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由此,生命政治的理论支点从权力逻辑转向生产逻辑、从治理方式转向生产关系。
缺乏生产关系的考察意味着“生命政治”的研究对象不可能触及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指具有社会属性的“类生命”即“自我创生的自为生命”③高清海《:“人”的双重生命观:种生命与类生命》《,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第78页。,类生命活动的特点是具有自觉性、自为性、创生性、能动性、积极性。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之处正在于:“生命政治不仅以生物性的生命(种生命)为对象,而且也以生活性的生命(类生命)为对象,从而实现了对人的更全面、也更隐蔽的控制。”④王庆丰《:〈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第42页。虽然奈格里、哈特的文本中没有明确提出并区分种生命与类生命,但是在其生命政治语境中强调的新的主体性的创生,指向生命本身的力量和生命的潜能,突出自主性和能动性,这种生命特质属于类生命的范畴。他们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把所有这些讨论引到“生命”的生产性维度这一问题上。换句话说,也就是要确定这一概念的物质性维度,从而超越任何纯自然主义的或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①Michael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p.421.进而他们把“生命”的内涵从福柯、阿甘本、埃斯波西托所针对的自然生命或生物性生命的意义上的生命延伸到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范畴中的能动的生命。以“非物质生产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生命”正是在类生命的意义上谈及生命主体。基于后福特制时代新的生产模式以及在生产过程或社会生活中非物质生产日益占据主导的新趋势的分析,奈格里、哈特看到“劳动力”的积极面向,指出生命政治是“新主体性的创生”“生命本身的力量”“劳动更具自主性”“创造出全新的未来”②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第37、36、102、102页。,以生产的力量确定主体,根据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重构新时代革命主体。
Research on a Soft Measurement Method for Air Volume YANG Chendi,LIU Xinping(81)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把后现代主义的生命政治的政治哲学范畴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之中,不仅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而且使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具有了建构性的维度。就方法论而言,奈格里、哈特和福柯、马克思具有一致性,都着眼于对当下社会发生的变化进行深刻分析,但不同时代背景下,他们的理论之间又显示出内在的差异性。马克思对应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积极主张,构建共产主义新世界。福柯对应于20世纪中叶新自由主义治理的背景,他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权力构型和基本运行机制,但他从未真正提出现行制度的替代方案,而是以批判的方式、减速的方式,使“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就处于一种可能改变(改良)的可能性中”⑤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15页。。奈格里、哈特对应于21世纪后福特主义的变化发展,对资本权力剥夺共同性展开严厉批判,提出“生命政治生产”和诸众革命的主张,积极探寻基于“共同性”的共产主义道路。上述发展脉络表明:奈格里、哈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生命政治”主体性缺失的空白,使“生命政治”从历史分析或结构分析的层面推进到积极构建的层面。在无产阶级革命失语的今天,以主体性生产的巨大潜力进行主体联合或诸众革命也许是一种可能性的进路。
“生命政治”的原初语境从客观性的历史维度分析了权力对生命(身体或人口)的作用,“生命政治”嬗变为“生命政治生产”则从主体-政治的维度强调了革命斗争的历史生成逻辑。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型有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生命政治”的当代境遇。福柯对权力治理形式的历史谱系学分析指出了新自由主义治理形式如何以更合理、更隐蔽的方式形塑主体;阿甘本对现代生命存在方式的结构性分析,指出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之间的契合与张力。如果说福柯揭示了一条当代政治对生命的操作技术的隐性线索的话,阿甘本则显示出当代生命政治依存于死亡政治的悲观立场。奈格里、哈特则重新回到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生产方式的当代形态进行分析,揭示出非物质生产下的生命政治,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生产的成果已越出资本权力所能控制的程度,这种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实际是一种智识、情感、潜能等形式的主体-政治维度上的价值。生命政治的生产范式是一种主体性的生产范式。
奈格里、哈特的“生命政治”立足于对“生命政治生产”或“非物质生产”作出的判断,即在资本主义价值增值过程这种生产形式中已经居于霸权或主导地位。表面上看,“非物质生产”确实存在日益加强的趋势,但实际上,无论从一国视角还是国际视野看,与非物质生产相比较而言,物质生产依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可以说,奈格里、哈特无疑夸大了“非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非物质劳动成果表面上看逾越了资本的控制范围,但实际上情感、智识等劳动在当代同样可以折算为成倍的简单劳动的价值。由此,奈格里、哈特“生命政治”研究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些质疑、争论,的确值得我们审慎思考。
另外,分别对动载荷与巷道顶板的距离、方位等进行了模拟,过程与载荷强度相同,不再赘述。结论为动载荷作用点距离巷道顶板越近,巷道浅层围岩的变形破坏越严重,距离在3 m以内时,变形较大,有失稳的可能;不同动载位置均对顶板有一定影响,动载在顶板时顶板下沉最严重,在两帮时对顶板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
“生命政治生产”作为一种建构性的理论,我们没有必要纠结于面对当代资本权力“生命政治生产”的主张是否太过乐观。《大同世界》的贡献在于为我们呈现出了新的主体视域以及奠基于非物质生产占主导的社会关系的分析方法。这一视角和方法已经构成奈格里和哈特独特的理论洞见,在对非物质生产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与阐释的基础上,更新了“生命政治”的概念系统,“非物质劳动”“协作”“共同性”“社会关系”“生命政治生产”一系列因素构成生命政治的当代内涵,由此滋生出对“共同性”的政治筹划。生命政治不再囿于封闭的权力展布,不再局限于劳动力所从属的生产领域,从而成为一种研究当代社会关系的开放性理论。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W.考夫曼曾说,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对福柯来说,哲学家的任务是“成为权力的减速器”(“modérateur du pouvoir”)。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遵从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说福柯的权力理论批判性有余建构性不足的话,那么《大同世界》中对生命政治理论的阐发无疑是一种从主体维度对权力理论的当代推进。从“生命政治”到“生命政治生产”、从“权力生产性”到“主体生产性”、从权力构型的客观分析到“主体—政治”维度的范式转型,弥补了“主体的生产性”的缺失,为我们完整地诠释了当代生命政治的真实意义。奈格里、哈特挖掘“共同性”的价值旨趣、重塑新的主体逻辑、构建共有的共产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开显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探寻一种新的政治可能性的有益尝试。
排除标准:(1)排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2)排除严重心律不齐、心动房颤的患者;(3)排除传染性、血液疾病。
From“Power Productivity”to“Life Productivity”: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Biopolitics Theory
MIAO Cui-cui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Biopolitics,as a new topic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m research,involves a kind of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in terms of the framework and connotation of a terminology.Both Foucault's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of power -governance forms and Agamben's analysis of the naked life by suspension of the original structure are confined to the field of power to govern or control the life.Negri and art believe that Foucault and Agamben's logic of life politics is profoundly partial because their emphasis on the production of power not only contains the paradox of biopolitics(death politics),but also results in the lack of the dimension of life productivity to a cer⁃tain extent.The fundamental cause lies in their ignorance of the analysis of realistic basis of social production re⁃lations.It is at this point that Negri and art return to Marx and attempt to surpass him.Starting from the new changes about production model and the 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labor in the post-Ford era,they conclude that the intangible production is dominan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The core of intangible production is the product⁃bility of life or subject,updating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contemporary biopolitics while elucidating the po⁃tential of life subject in contemporary social relations.This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activating the revolutionary subject and reshaping the logic of class further highlights the contemporary values embodied in the biopolitics theory of life itself.
Key words:life power;biopolitics;intangible production;Commonwealth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1004-1710(2019)03-0080-07
[收稿日期]2019-0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15)
[作者简介]苗翠翠(1988-),女山西盂县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责任编辑:张文光]
标签:生命论文; 政治论文; 权力论文; 格里论文; 物质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世界政治思想史论文;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15)论文;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论文;
